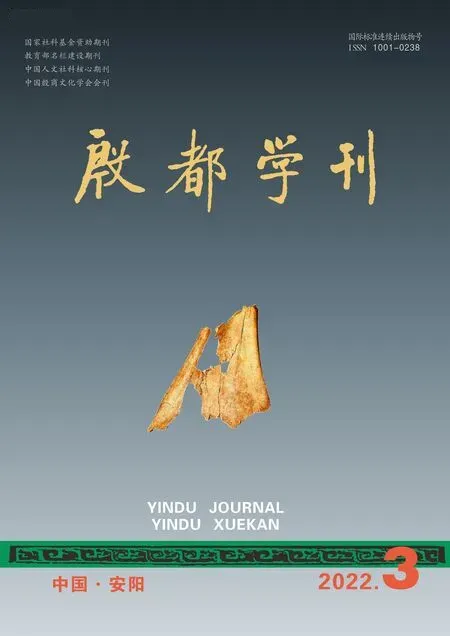新世纪中原剧作家群的戏曲创作与文化记忆
陈晶晶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中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河南戏曲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内容。河南剧作家群的创作根植于中原大地深厚的文化土壤,深刻地、内在地蕴含着地域与民族的文化记忆,并随着时代发展进行戏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新世纪中原剧作家群以姚金成、陈涌泉、杨林、贾璐等戏曲作家为主,创作成就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被业界誉为“豫剧现象”“河南模式”(1)王绍军、李小菊:《地方戏曲振兴的“河南模式”》,《中国戏剧》2016年第4期,第16页。,在全国剧作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及影响,成为新世纪中国戏剧发展的一个时代缩影。
一、新世纪中原剧作家群的构成
河南历史上涌现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留下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2)如元代的白朴、郑廷玉、李好古、宫天挺、陆显之、钟嗣成等;明、清又有朱有燉、李络、李树谷、耿应房、王慎余、欧波亭长、吕公溥等;民国年间则有樊粹庭、陈宪章、王镇南等;1949年至上世纪末则出现了百余位卓有成就的剧作家,如杨兰春、齐飞、孟华、何中兴等。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河南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10-30页。。新世纪以来,以姚金成、陈涌泉、杨林、贾璐、韩枫等编剧为代表的中原剧作家群更是在全国乃至世界上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其中,姚金成的《焦裕禄》《重渡沟》等作品被认为开创了英模戏人物塑造突破“禁区”的“新路径”(3)傅谨:《新时期戏曲现代戏成就论》,《艺术百家》2020年第5期,第6页。,登上了新时代戏曲现代戏创作的高峰。陈涌泉的《程婴救孤》更是走出国门,2013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登上纽约百老汇舞台的戏曲作品,响彻东南亚、欧美等域外舞台(4)陈涌泉:《程婴救孤》,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4、275-277页。,使豫剧这一古老的中原剧种首次收获了广泛而持久的国际魅力。
以《河南戏剧》2011年第5期和2012年第1期推出的“编剧篇”为例,涉及到新世纪以来的主要剧作家就有20余位,代表性的人物有李学庭、孟华、齐飞、张锡容、姚金成、孔凡燕、张芳、王明山、贾璐、陈涌泉、冀振东、马书道、刘巧珠、韩枫、何中兴、刘巧珠、任金义、姚梦松等众多剧作家,编剧团队庞大,相当数量作品已成为当代豫剧等剧种的保留剧目。
按剧作家创作年龄,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冀振东(1933)、孟华(1940)、齐飞(1945)等为代表的高龄剧作家,他们大多成名于1980—1990年代,新世纪以来仍笔耕不辍,产生了《惊蛰》《榆树古宅》《伤逝》《任长霞》《颖河骄子》《中原警事》《燕振昌》等优秀之作,显示了老一辈剧作家坚守“平民化”内涵,攀登“人性化”的现代意识及尝试崭新化的形式探索的努力;一类以姚金成(1948)、韩枫(1954)、张芳(1955)、王明山(1956)、贾璐(1959)等为代表,以“50后”为主的剧作家群,他们大多成名于1990年代以来,是新世纪河南现代戏的创作主力,其所编的《香魂女》《村官李天成》《焦裕禄》《重渡沟》《常香玉》《嵩山长霞》《清风茶社》《红高粱》《秦豫情》等剧目,代表了河南戏曲现代戏继1950年代《朝阳沟》之后,所达到的新一轮历史高峰;一类是以杨林(1961)、陈涌泉(1967)等为代表的“60后”,他们主要成名于新世纪之后,以《风雨故园》《都市阳光》《常香玉》《红旗渠》等戏为主,尤其是陈涌泉以现代意识的先锋性与浓郁的文学意识取胜,作为新一代河南戏曲的殿军力量,已达到了和同时代全国优秀的中年剧作家相媲美的艺术水准。
二、新世纪中原剧作家群的创作概况
按题材分类,新世纪以来中原剧作家群的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剧目居多,兼顾少量历史题材,充分反映了此阶段河南戏剧贴近生活与民众、介入复杂社会现实的创作倾向,有“公仆戏”“廉政戏”“扶贫戏”“婚恋戏”“民国戏”等戏剧类型。按照剧种分类,中原剧作家群形成了以豫剧为主,曲剧、越调等兼擅的创作格局,艺术上普遍固守剧种本体特色,唱词对白、风格气质、唱腔音乐等都洋溢着原汁原味的地域风格。从跨域创作角度看,杨林、贾璐、韩枫等诸多剧作家都将创作延伸到其他省份,涉猎京剧、评剧、山东梆子等多个剧种。如杨林的京剧《霸王别姬》(2004)被广西京剧团排演,该剧团得以重新恢复建制,2005年入选“全国省级重点京剧院团”,被称为“一个剧本救活一个剧团”(5)杨林、张燕君:《生活历练了我,戏剧造就了我——编剧杨林访谈》,《戏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4页。。评剧《红高粱》即贾璐根据此前创作的豫剧《红高粱》改编,他还给天津、青岛、宁夏等地京剧团创作了《曹操父子》《齐王田横》《庄妃》等众多历史剧。韩枫也为邻省创作了山东梆子《古城女人》《山东汉子》等,为新疆建设兵团豫剧团创作了《戈壁母亲》、为北方昆剧院创作了《荣宝斋》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原戏剧的美学风格更加多元化,如老一辈剧作家孟华将美国现代主义大师奥尼尔的话剧作品《榆树下欲望》等作品改编为意象戏曲《榆树孤宅》《安娣》《马克百万》等,不仅重视对原著“人与人性的深刻思维方式”(6)孟华、程姣姣:《人,是我在戏里一直所思考的——著名剧作家孟华访谈》,《东方艺术》2021年第1期,第41页。的借鉴与移植,更显示了传统豫剧处理西方经典美学形式的“在地化”探索与革新。
需要指出的是,2000年后,国家评奖体制作为政策导向充分介入戏剧艺术的创作实践中,由于现代戏在评奖体系中历来颇受重视,新世纪以来中原戏剧以现代戏数目为最多、成就也最高。以2000年以来河南戏剧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化部“文华奖”的剧目为例,能略窥中原剧作家群这一时期整体的创作观念和编剧倾向。(7)历届“五个一工程奖”豫剧获奖剧目有:2001年《香魂女》(河南豫剧院三团)、2002年《铡刀下的红梅》(河南小皇后豫剧团)、2003—2006年《程婴救孤》(河南省豫剧院二团)与《村官李天成》(河南豫剧院三团)、2007-2009年《常香玉》(河南豫剧院一团)、2009-2012年《苏武牧羊》(河南豫剧院二团)、2012-2014年《焦裕禄》(河南豫剧院三团)、2018-2019年《重渡沟》(河南豫剧院三团)。历届“文华奖”豫剧获奖剧目有:2000年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上的《香魂女》(河南省豫剧三团)、2004年第十一届文华大奖豫剧《程婴救孤》(河南省豫剧二团)与文华新剧目奖曲剧《惊蛰》(河南省南阳市曲剧团)、2007年十二届文华大奖豫剧《常香玉》(河南省豫剧一团)、2010年第十三届文华大奖越调《老子》(河南省越调剧团)、2016年第十五届文华大奖豫剧《焦裕禄》(河南豫剧三团)、2019年第十六届文华大奖豫剧《重渡沟》(河南省豫剧三团)。从获奖单位看,主要是省级的三个豫剧团,即省豫剧院一团、二团、三团,特别是省豫剧院三团,是名副其实的获奖大户。先后有4个剧目(《香魂女》《村官李天成》《焦裕禄》《重渡沟》)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3个剧目(《香魂女》《焦裕禄》《重渡沟》)获得文华大奖,这都说明了该团的实力与水平,也说明了河南省对国家级奖项的重视程度。
从获奖题材看,大部分属于现实题材创作,带有很强的主题性倾向。除了《程婴救孤》《苏武牧羊》《老子》3个新编古装戏之外,其他获奖剧目都是现代戏,体现出国家意志、政策导向、评奖倾向对豫剧甚至全国戏曲建设的直接影响。从获奖结果上看,绝大部分获奖剧种都是豫剧,越调、曲剧亦有少量作品获奖(如《老子》《惊蛰》),这显示了河南戏曲在全国广泛的影响力与艺术魅力。
从艺术成就上看,姚金成执笔的《香魂女》《焦裕禄》《重渡沟》3部戏同时获得文华大奖与“五个一工程奖”,是新世纪以来获奖次数最多的中原剧作家。获文华大奖的还有陈涌泉的《程婴救孤》、孟华的《老子》、杨林的《常香玉》,体现出中原剧作家群活跃、高质的艺术创造力,从文学属性上极大提升了河南戏剧的艺术和文化品格,使河南戏剧尤其是豫剧实现了“从‘俗、粗、浅、陋’向‘雅、细、精、深’的质的跨越”。(8)李小菊:《当代豫剧剧目建设思考》,《大舞台》2016年第Z1期,第22页。
三、新世纪中原剧作家群的文化记忆
中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河南剧作家群的创作根植于中原大地深厚的文化土壤,必然深刻地、内在地蕴含着地域与民族的文化记忆,并随着时代发展进行戏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新世纪以来中原剧作家群在文化记忆上集中表现为“中原”即“中国”的古典文化情结、“天下之中”的政治意识、“土味”文化为基的乡土精神,内嵌着丰富的中原历史底蕴与文化情结。
(一)“中原”即“中国”的古典文化情结
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以古老的历史文化底蕴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标志性地域。史前的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与三门峡仰韶文化遗址、洛阳二里头夏都文化遗址、安阳殷墟商代文化遗址等系列中国古遗址的发掘,将最早意义上的“中国”与中原大地紧密勾连,构成了“中原”即“中国”这一最初的国家意识。古都作为人类文明遗存下的城市景观,在中原这片广袤土地上绵延千年,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即占据四个,分别是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殷商古都安阳和商都郑州,形成了绵长的古都群落。5000年中华文明史,先后有夏、商、西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20多个朝代在中原建都,这里是长达3000多年的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四大发明均源自河南,儒释道三大思想学说皆首传于此,这里亦是“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宗祖姓氏发源地。(9)参见河南省人民政府网《河南概况》:https://www.henan.gov.cn/2018/05-31/2408.html,登录日期2021-12-08。可以说,中原文明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建构了“中原”即“中国”的精神共同体关系。
古老厚重的文明历史使得中原剧作家群拥有一种古典文化情结,他们不断在新时代书写着中原文明光辉灿烂的文化记忆,集中表现在其创作观念和艺术构思中。他们历来重视通过塑造携带传统伦理道德、精神观念、文化情怀的古典人物性情与灵魂,构筑起富有浓郁古典意象特征的戏剧情境,开掘中原传统文化体系中固有的重人伦、重文化的倾向,借此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呈现出现代中原人对传统文明与人文精神的重构与阐释。如陈涌泉的《程婴救孤》(2001)掀开了新世纪“赵氏孤儿”改编热,同时他又超越了同时期同类题材所回避的“程婴献子”情节,重新回归到元杂剧《赵氏孤儿》所传递的传统道德精神与可贵的人性情义立场,弘扬坚持正义、舍生取义的传统道德精神和英雄气质,而又进一步揭示程婴内心的不忍献又不得不献的痛苦和献子后长期灵与肉的双重磨难,丰富了程婴人性复杂和深沉的一面,以现代化的处理完成了程婴形象的内外统一。又如李利宏编导的方言戏剧《宣和画院》(2009)以宋代书画文化为背景,通过当代开封城里两个老文化人经营书画院最终难以为继的故事,来表现传统书画艺术的传承在当代面临的尴尬处境,传递一种对中原古典文化的深情回顾与对当下所失落的人文精神的感喟。
中原戏剧不仅传承了中原文化笃实守信、尊礼崇德的伦理精神和人文传统,也讴歌了中原人民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时代风貌,是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的直接反映。如杨林的话剧《红旗渠》(2012)全景式描绘了长达10年的太行山修渠壮举,成功塑造了2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群像,演出气势恢宏而又时空灵动,细节丰富真实而又富于假定性和雕塑感,深刻揭示了作为中原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核,也是中华民族当代核心价值观重要内容的“为民、奋斗”的“红旗渠精神”。又如孟华《老子》《玄奘》聚焦河南文化名人;舞剧《风中少林》《水月洛神》,杂技剧《水秀》等,通过戏剧艺术将中原古老文化记忆成功进行了现代审美转化,以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高昂的时代精神,为建设中原经济区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与动力支撑。
(二)“天下之中”的政治意识
河南古称“九州之中”,这个“中”乃天下之“中”的意思,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代表着国之枢纽,是王权的核心所在。这种“天下之中”的政治暗示不断在历史中得以强化,影响了中原人的世代文化记忆。虽然近现代以来,中原文明渐趋颓势,但是,对王者之风的崇拜在现代中原人身上依然延续下来,形成一种地域性的“泛政治人格”(10)丁琳慧:《论中原作家群的文化记忆》,《文艺争鸣》2021第8期,第52页。。上千年的王权崇拜,使“中”的政治体制、伦理秩序和权力意识进入中原文化基因深处,政治文化的浸润无形中使中原人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为中原文化注入的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11)李庚香:《中原文化精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培养了河南剧作家潜移默化的政治情结。所以,现实性与政治性特征强烈的现代戏得以在新世纪的河南蓬勃发展。
举例而言,姚金成的“公仆三部曲”——《村官李天成》(2001)、《焦裕禄》(2016)、《重渡沟》(2019),虽然都是“定向戏”(12)姚金成:《理想与生存的变奏——兼谈主旋律戏剧创作的思考与实践(下)》,《大舞台》2016年第7期,第9页。,是应剧团或者演员之邀编创的,但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三部戏作为当代“英模戏”的典型代表,通过塑造不同时代党的好干部形象,传递出强烈的政治情怀与社会使命感。《村官李天成》演绎新世纪初中原基层干部李天成带领村民搞蔬菜大棚的艰辛创业历程,直面农村产业调整、社会体制转型的现实矛盾,聚焦市场大潮下中原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和政治命题。剧作者既怀着对农村产业结构面临调整的高度关切,又对市场经济下农民群体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怀着真诚的焦虑感,对农民精神观念上的保守性和盲目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作出了适度理性的批判,从更深、更广的层面透视了社会和时代的底蕴。《村官李天成》近年来已热演800余场,寄托着人们对“李天成式的能人的殷切期盼”(13)李红艳:《〈村官李天成〉热演800场的思考》,《东方艺术》2012第S1期,第30页。,该剧契合了当今观众的现实期许,实现了主旋律题材与人民诉求的水乳交融。
《焦裕禄》中,通过设置“火车站送灾民”“瓦窑村为‘右派’平反”“买议价粮救荒”“带病抗洪”这些戏剧情境,呈现出焦裕禄所面临的极端的内外部险境,强化其内心所面临的强烈冲突,以及在旋涡中灵魂的激烈搏斗,进而传达出其为民立命的公仆情怀。这部正剧洋溢着浓郁的悲剧气质,是近年主题性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重渡沟》则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为背景,以基层干部马海明的真人真事为素材,讲述了他在开发国家级景区重渡沟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坚持保护环境、在行动上鞠躬尽瘁的感人故事,在乡村振兴主题下展示时代脉搏和个人命运的深刻纠缠,凸显主人公身上的为民、无私的可贵品质。可以说,“公仆三部曲”是新世纪英模戏的典型代表,在核心价值观的阐释与引领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有评论者指出,其“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为底蕴,充盈着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气象,浓缩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托举出那个时代的光彩人物。”(14)孙豹隐、孙昭:《论豫剧“公仆三部曲”对于现代戏曲传承和发展的当代价值》,《当代戏剧》2020年第6期,第12页。
(三)“土味”文化为基的乡土精神
新世纪中原剧作家群站在民间立场创作,在继承“十七年”的《朝阳沟》和新时期以来《倒霉大叔的婚事》等戏中浓郁的生活气息、地域特色基础上,充分挖掘豫剧、曲剧等河南剧种固有的唱腔特色和诙谐机趣的风格,不仅注重审美层面的民间性与民俗性,还尤其侧重社会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对峙、冲突与融合,积极呈现河南新农村的文明景观及新农民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复杂的精神面貌。河南戏剧历来擅长塑造地地道道的河南农民形象,即“河南侉子”。著名作家李准对“侉”有丰富的阐释:“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上外表笨拙,内里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15)李准:《黄河东流去(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305页。
擅写世俗伦理剧的王明山,在《啼笑皆非》(2005)中描摹了一个河南农民做好事反被讹的社会悲喜剧。耐人寻味的是,该剧并不止于展现救助者与被救助者双方的矛盾,而是将戏剧性更多安排在好人孟大宝救了被撞的人后,亲人的种种不理解上。亲属们将他以往的老实诚、爱吃亏的种种行为归结为“神经病”,甚至将他强制性送往精神病院;而另一个致富能手刘金梁本来要作为社会宣传的正面典型,却因撞了自己的亲人而不敢承认,最终内心愧疚沦落为真正的精神病(抑郁症)患者。此剧通过人物种种非常态的行为来反思现实社会的道德困境与人心畸形,充满了黑色幽默式的荒诞色彩,内蕴着对社会不正常现象的审视与批判,体现了作者“基于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的反思意识,是其世俗伦理戏思想内涵的拓展和再度深化。”(16)李红艳:《乡土伦理叙事的坚守和突破——王明山的世俗伦理戏及喜剧风格(上)》,《东方艺术》2019年第2期,第96页。
再如陈涌泉的《都市阳光》(2015)写农民工进城的尴尬与痛苦遭遇,反映出新时代农民融入城市文明的艰辛。正如剧中主人公高天所言:“咱们都是草根,草根就要扎到田野里,城市的水泥地太硬,咱扎不进去。”还有他和朵朵唱的那段《进城难》:“进城难,抛家舍口离故土,一颗心儿两地牵;进城难,家中小院长蓬草,自己却栖身在城市的屋檐……”(17)陈涌泉:《陈涌泉剧作选》,中国戏剧出版社,2018年,第292页。此剧展示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矛盾,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中,直面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等尖锐冲突,同时借鉴音乐剧、摇滚乐、现代舞的元素,将其和所表现的农民进城的现代主题一起,推动了豫剧审美的“现代化、都市化、国际化与豫剧的青春化”(18)陈涌泉:《我的农民工兄弟——〈都市阳光〉创作谈》,《剧本》2017年第6期,第96页。。这些独特的“中原经验”以重构的方式对古老的中原文化进行了全新的现代演绎,对新时代中国戏曲文学的发展亦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