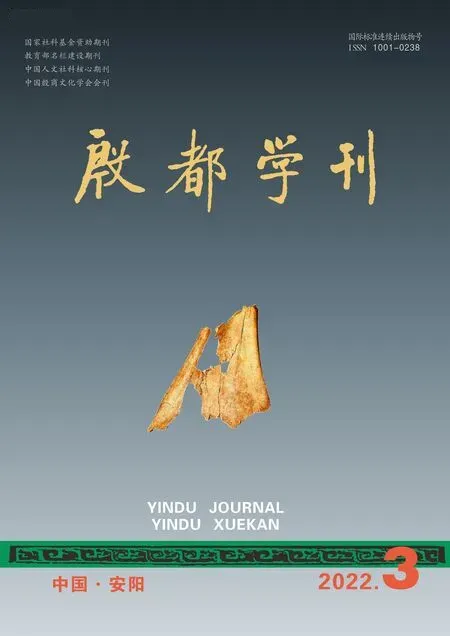唐代诗歌自注发展轨迹探赜
魏 娜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诗歌自注即诗人对自己诗作的解释说明,其与他注构成了两种不同的诗歌注释方式。南齐谢脁、江革、王融、王僧孺、谢昊、刘绘、沈约七人在共赋的《阻雪连句遥赠和》中,将其名字连同官职标注在各自所作诗句之后,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歌自注。至唐代,诗歌自注渐呈勃兴之势,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现象。唐诗自注始于初唐,兴于盛唐,在中唐走向巅峰,至晚唐而式微,经历了持续完整又不失阶段特色的发展过程。学界当前对唐诗自注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某一具体问题或典型个案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碎片化倾向,缺乏对其发展历程的宏观梳理。而唐诗自注在初、盛、中、晚时期的不同特征,不仅体现了其向诗歌内蕴层面延伸程度的变化,也反映出诗歌自注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因而对唐诗自注阶段性面貌的勾勒,是本文拟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初唐诗歌自注的特征
初唐时期共有23位诗人的26首诗歌使用了自注(1)文中所示唐代自注诗人及自注诗的总数,初、盛唐时期自注诗人及自注诗数量的统计,以彭定求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与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所录诗人为线索;各自注诗人的诗歌版本选择,遵循以下原则:有整理校注本别集者,以其中所录自注诗为数量统计依据。无整理校注本别集者,则以《全唐诗》《全唐诗补编》所收自注诗为数量统计依据。并参照《全唐诗重篇索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及佟培基编撰《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核实诗歌重出真伪。同首诗中兼有两种及以上的自注类型,在自注诗总量中不重复计算。。这些自注具有以下四点鲜明的特征。
一是规模未备。就自注诗数量而言,23位诗人人均约1首自注诗,过此平均线者只有魏元忠和王勃。而王勃仅凭3首自注诗便成为初唐诗歌自注最高产的诗人。从自注诗占比看, 23位使用自注的诗人现存701首诗作,自注诗仅占3.7%。再就诗人的参与状况来说,一种诗歌现象能否最终走向繁荣,关键取决于作为诗坛主力的诗人参与度。而诗人现存的诗歌数量是判定其是否为当时诗坛主力的重要依凭,也关系到对自注诗规模的考量。笔者以《全唐诗》为依据,将作品单独成卷的诗人视为主力诗人,以此考察初唐诗人使用自注的情况:31位主力诗人中,仅唐太宗、王绩、王勃、李适、陈子昂、沈佺期6人使用自注。李适自注诗比例最高,为5.9%,其余5人均在1%上下。可见,初唐时期的主力诗人并未成为推动诗歌自注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力量。除主力诗人外,尚有17位非主力诗人也使用了自注,但其自注诗仅有18首,故而依然无法改变初唐诗歌自注规模较小的局面。
二是自注类型相对齐全但发展不均。唐代诗歌自注以阐释对象为标准可分为三类:交代创作时地、动因及诗歌相关人事信息的背景类自注,说明诗歌体裁、用韵、字数的体式类自注以及阐明诗句情意本事、典故来源及内容、字词义的意义类自注。按照出现位置的不同,可分为四类,即嵌入诗题的题中自注、紧随诗题之后的题下自注、出现在诗序中的序中自注与紧随诗句后的句下自注。在初唐诗歌中,依阐释对象而分的三类自注已全部出现;依位置而定的四类自注中,题下与句下两种最主要自注类型也均被使用。可以说初唐诗歌自注奠定了唐诗自注的基本面貌。但各类自注的数量明显不均衡。从阐释对象标准下的自注类别看,使用体式类与背景类自注的诗歌分别为12首与11首,使用意义类自注的诗歌仅3首(2)出现意义类注释的初唐自注诗实为8首。其中5首诗的背景注在一定程度上兼释了诗句本事内容,具有意义注的性质,但不是纯粹的意义类注释。另外3首诗则采用了专门阐明诗句情事内涵的自注,即非兼释性的纯粹的意义注。因正文所述恰好是不同划分标准下几种自注类别的内在联系,故采用相对严格的标准界定此处的意义注,即单指非兼释性的纯粹意义注。。从位置标准下的自注类别看,使用题下注的诗歌为24首,使用句下注的诗歌仅3首。值得注意的是,背景、体式类自注都出现在诗题下,而意义类自注则多紧随诗句之后。这使阐释对象标准下的体式、背景自注的数量优势与位置标准下的题下注数量优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三是阐释角度单一。这在体式与意义类自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就体式类自注而言,不仅包括对诗歌用韵的说明,还包括对诗歌字数、诗体的交代。而初唐诗歌12处体式类自注,除任希古《和李公七夕》题下注“谢惠连体”(3)《全唐诗》卷44,第544页。是交代所效仿的诗体外,其余均为对诗歌用韵的说明:太宗皇帝《赋得樱桃》题下注“春字韵”(4)李世民:《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6页。;魏元忠《修书院学士奉敕宴梁王宅》题下注“赋得门字”(5)《全唐诗》卷46,第556页。,《银潢宫侍宴应制》题下注“得枝字”(6)《全唐诗》卷46,第556页。;崔知贤、席元明、韩仲宣、高球、高瑾五人在同题之作《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中分别注明“得鱼字”(7)《全唐诗》卷72,第785页。“得郊字”(8)《全唐诗》卷72,第785页。“得花字”(9)《全唐诗》卷72,第786页。“得烟字”(10)《全唐诗》卷72,第787页。“得哉字”(11)《全唐诗》卷72,第788页。;张锡《晦日宴高文学林亭》、解琬《晦日宴高氏林亭》,均以“同用华字”(12)《全唐诗》卷105,第1103页。为注;张嘉贞《恩敕尚书省僚宴昆明池应制》题下注“同用尧字”(13)《全唐诗》卷111,第1138页。。
意义类自注重在揭示诗句指涉的本事,极少有对典故或词义的解释。在8处涉及句意阐释的自注中(14)包括3处纯粹的意义类注释和5处背景类自注兼带说明诗句内容的情况。后者本质上虽是背景类注释,但其中的个别信息恰好关涉诗句内容,因此在讨论阐释诗句的意义类自注时,也将此种情况纳入其中。,只有马怀素《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句下注“黄鹤见《汉书·西域传》。公主歌云:‘愿为黄鹄兮归故乡。’”(15)《全唐诗》卷93,第1008页。发挥了释典功能。其余的同类自注则以阐明诗句背后的事实为重点,如沈佺期《七夕曝衣篇》题下注云:“按王子阳《园苑疏》:太液池边有武帝阁,帝至七月七日夜,宫女出后衣曝之。”(16)沈佺期:《沈佺期诗集校注》卷1,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页。照应诗中“君不见昔日宜春太液边,披香画阁与天连。灯火灼烁九衢映,香气氛氲百和然”四句,诗句略去对人物、事件的描述,重在以赋笔渲染宫廷七夕热闹旖旎的场面,自注则与之互补,重在叙述七夕曝衣之俗,突出诗句描绘的场景氛围背后的节俗事项。
四是诗、注关系疏离。一般来说,自注的频次、篇幅与诗人对诗歌释解的深入程度成正比。首先,初唐诗歌自注不仅数量少,而且基本为一诗一注。自注多为词或短语所构成,少数成句的自注也基本是简洁的单句,极少出现篇幅较长的复句或语段。简省甚至碎片化的表达方式势必削弱自注的阐释力,使其很难与诗歌建立深度联系。其次,相对单一的阐释角度使自注的信息容量严重缩水,从而限制了其向诗歌深层内蕴的延伸。具体而言,体式类自注多说明诗歌用韵,诗体与诗歌字数等内容成为注释的盲点;意义类自注则主要阐明与诗歌相关的本事,而极少训释字词、典故。阐释角度的局限导致自注无法实现向诗歌的全面渗透。最后,对诗歌核心层面阐释的匮乏,是初唐时期诗、注未能深度融合的根本原因。诗歌的核心层由事、情、思三要素构成,自注与之的关联度决定了诗、注关系的密切程度。阐释对象标准下的三类自注中,体式类自注对用韵、诗体、诗歌字数的说明与诗歌核心层无关。背景类自注包括对创作缘由、目的、时地及诗歌所涉人事的介绍,虽时有牵及诗歌包含的情思本事,但并未对其深入解读。意义类注释包括对诗中词语、本事、情感、典故等的揭示说明,直指诗歌内蕴层面。可见,体式、背景、意义三类自注与诗歌核心层的关联度依次加强,意义注的大量使用是诗、注深度融合的关键。初唐时期,背景、体式类自注占主体,意义类自注仅零星出现,这必然造成诗、注关系的疏离。
二、盛唐诗歌自注的特征
盛唐时期有30位诗人在其300首诗歌中使用自注。盛唐诗歌自注较之初唐又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从而形成鲜明的阶段特征。
首先,使用自注的意识渐趋自觉。盛唐时期使用自注的诗人数量较之初唐虽未明显增加,但自注诗总量增长了10余倍,人均自注诗数也激增至10首。可见,盛唐时期诗人运用自注的意识与力度已远胜初唐。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主力诗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方面,在使用自注的诗人中,主力诗人的占比明显上升。30位自注其诗的诗人中,属于诗坛主力的就有11位:张九龄、张说、孙逖、李颀、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岑参、高适、李白、杜甫。较之初唐,人数增长近一倍,占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主力诗人的自注诗数量也大幅上涨,达至281首,占此时期自注诗总数的93.7%,构成盛唐诗歌自注规模的主体。主力诗人们对自注的积极使用,从根本上刺激了盛唐诗歌自注的繁荣。
其次,体式、意义类自注的内容及形式呈现多元化。与初唐体式类自注多为交代诗歌用韵不同,盛唐时期该类自注除了说明用韵外,也更注重对诗体的介绍。如丘为《冬至下寄舍弟时应赴入京》题下注“杂言”(17)《全唐诗》卷129,第1320页。点明诗歌采用古体;杜甫《愁》诗题下注“强戏为吴体”(18)杜甫:《杜诗详注》卷18,中华书局,1979年,第1599页。指出此诗乃诗人首创新诗体“吴体”的范本。初唐体式类自注虽也有对诗体的说明,但属于特例,而这在盛唐体式类自注中已变成较常见的内容。盛唐的意义类自注则加强了对典故、词义的诠释,丰富了该类注释的内容。特别是李翰的《蒙求》以31处句下自注详揭诗中62处典故的来源及内容(19)李翰《蒙求》原诗在《全唐诗》与《全敦煌诗》中均有收录,但辑录情况不同:《全唐诗》卷881所载《蒙求》,共存601句,2404字,不带自注;《全敦煌诗》卷45所收《蒙求》,共存66句,诗句字数264字,自注31处。据与李翰同时期的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所言,其曾亲见李翰《蒙求》诗,全诗3000字左右,并且附有详细的自注。可见,《全敦煌诗》中收录的《蒙求》诗虽然文本的残损度较高,但保留了多处自注,更贴近诗歌的原貌,且本文又以自注的探讨为中心,故文中以《全敦煌诗》本《蒙求》为依据。,是自注释典的典型代表。盛唐还首创了“自注来诗”的注解形式。所谓“自注来诗”是指在寄赠唱和类诗作中,酬和诗作者以原唱诗句或诗句大意为己作之注脚的自注形式。如孙逖《奉和李右相中书壁画山水》的句下注“李公诗云:八载忝司存”(20)《全唐诗》卷118,第1196页。以及储光羲《酬李处士山中见赠》的句下注“李诗云:青青此松柏”(21)《全唐诗》卷138,第1397页。,便分别截取李林甫、李处士原作之句嵌入己诗为注。以韵语形式的诗句为注,突破了唐诗自注以散句为主的句式传统,使自注句式骈散兼备。
最后,自注对诗歌的阐释力增强,两者关系趋于紧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一诗多注的情况有所增多。一诗多注是指一首诗歌中至少出现两处自注,这类诗歌可称为多注诗。多注诗在初唐仅有李适的《饯唐永昌赴任东都》,而盛唐时期则增至11首,分别是储光羲的《苏十三瞻登玉泉寺峰入寺中见赠作》《贻丁主簿仙芝别》,岑参的《梁园歌送河南王说判官》《送刘郎将归河东》《稠桑驿喜逢严河南中丞便别》,杜甫的《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王竟携酒高亦同过》《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李翰的《蒙求》。其中有4首诗歌兼用了不同类型的自注,如岑参的《稠桑驿喜逢严河南中丞便别》题下注“得时字”为体式类自注,交代用韵;句下注“参忝西掖曾联接”(22)岑参:《岑嘉州诗笺注》卷3,中华书局,2004年,第571页。则属于意义类自注, 揭示“犹思紫禁时”一句所指之事:诗人曾任中书省右补阙,与时任门下省给事中的严武在朝会上同列横班。又如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题下的背景注“时李之芳自尚书郎出齐州,制此亭”点明诗题中“古城新亭”的由来,而“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句下的意义注“亭对鹊山湖”(23)《杜诗详注》卷1,第38页。,在说明“清湖”具体所指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亭与湖的方位关系。其余7首则均为仅使用意义类自注的多注诗,如储光羲《贻丁主簿仙芝别》中先后出现了四处意义注,“摇曳君初起,联翩予复来”句下注云:“丁侯前举,予次年举。”“兹年不得意,相命游灵台”句下注云:“同为太学诸生。”“联行击水飞,独影凌虚上”句下注云:“同年举,而丁侯先第。”“下愚忝闻见”句下注云:“予后及第,又应制授官。”(24)《全唐诗》卷138,第1399-1400页。四处自注不仅勾勒出诗人与丁仙芝科考仕进的完整经历,而且突显了二人相识相交的情谊,使诗中所表之情、所言之事更为明晰饱满。
综上所言,诗人在多注诗中通过增加自注的数量及类型,拓展自注向诗歌延伸的空间,进而实现自注对诗歌从形式到内涵的全面阐释。
第二,意义类注释数量大幅增长,增强了自注对诗歌内蕴的阐释力。初唐时期8处意义注中,5处为具有兼释诗句意义的背景注,占比62.5%;纯粹的意义注仅3处,占比38.5%。盛唐时期使用意义注的诗歌共105首,纯粹的意义注出现在67首诗歌中,占比63.8%,其中不乏连用意义注的多注诗;采用兼释句意的背景注的诗歌有38首,占比36.2%。背景注兼释功能的弱化及纯粹意义注占比的显著增加意味着自注的着力点正转向诗歌内蕴层面。
第三,自注阐释诗歌内蕴的主要途径基本形成。所谓阐释途径即自注揭明诗歌内蕴的方式,它的成型稳定意味着诗、注关系走向深入。盛唐时期,自注对诗蕴的阐发基本循着以下三种途径。
1.触引式。自注是触动诗歌情思意绪的媒介,为诗中的抒情议论做导引、铺垫。如宋昱的《题石窟寺》是典型的借物咏怀诗,这类诗歌创作的关键在于从咏物到抒怀的过渡,即建立物与情的联系。而该诗题下自注“魏孝文所置”正是引发诗人历史感喟的触点,其对石窟寺限定性的说明将之拉回到北魏孝文帝推进汉化改革的历史时空,为诗人在“邀福功虽在,兴王代久非。谁知云朔外,更睹化胡归”(25)《全唐诗》卷121,第1216页。这最后四句中酝酿发抒历史情怀提供了前提,避免了诗歌从咏寺转向咏怀的意脉断裂。
2.补充式。因篇幅及表达重点所限,诗歌中的情与事多为片段式呈现,自注则对其充实拓展,提供诗句未言或未能尽言的背景信息,使诗情诗蕴的彰显更为透彻流畅。兹以孟浩然《送韩使君除洪州都曹》为例,题下自注云:“韩公父尝为襄州使。”全诗曰:
述职抚荆衡,分符袭宠荣。往来看拥传,前后赖专城。勿剪棠犹在,波澄水更清。重颁江汉治,旋改豫章行。召父多遗爱,羊公有令名。衣冠列祖道,耆旧拥前程。岘首晨风接,江陵夜火迎。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26)孟浩然:《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41-242页。
诗题中的韩使君指韩朝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为荆州刺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采访使,开元二十四年九月,因荐官失当被贬洪州刺史,此诗当作于其赴任洪州之前。全诗对韩朝宗任襄州刺史期间卓越政绩的赞誉溢于言表。但从诗歌前六句看,诗人所敬服的显然不止是韩朝宗。“袭荣宠”“前后”“棠犹在”“水更清”四组词明显带有两者之间交相辉映的意味。但这个与韩朝宗同享清誉之人究竟是谁,其与韩朝宗之间为何会荣耀相续,诗歌并未言明,而自注则给出了答案:韩朝宗之父韩思复曾两任襄州刺史,因治州有方而名动朝野。诗歌竭力表达的同辉之意正是以自注为前提,方显水到渠成、妥帖自然。
3.引申式。诗句言外之旨往往通过修辞技巧被藏匿,自注则直击诗歌潜台词,将其推向台前。杜甫的《喜雨》便是个中典型: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时浙右多盗贼。(27)《杜诗详注》卷12,第1019-1020页。
此诗为杜甫宝应至广德年间寓居梓州、阆州所作。开篇六句为总起,直陈巴蜀百姓的两大苦境——春旱与兵戎。按照诗歌先总后分的谋篇思路,自“沧江”句始,应当分别细述两类灾难。而诗人貌似只表达了目睹春雨缓解蜀地旱灾时的欣喜之情,几乎未涉及战争一事。但结合篇末自注看,却并非如此。自注所谓“浙右多盗贼”是指宝应元年(762)台州袁晁谋反,攻陷浙东诸州郡之事。诗人通过自注陈述史实,则诗末四句话外音全现:诗句中的“群山云”“鞭雷公”“洗吴越”,并非实为吴越之地求雨,而是将能够平息战乱的勇士比作还百姓安宁生活的“鞭雷公”“及时雨”,希冀其如大雨浸透巴蜀春旱一般荡平吴越贼寇以解兵祸。自注一语道破诗句的真实意旨,将“叙兵乱”这条暗线明朗化,从而使喜雨与止战两重情思交织呼应,实现了情感表达上丰富与圆融的兼备。
总之,盛唐诗歌自注通过发挥触引、补充、引申的功能,助推诗歌情感意蕴的充分表达,这是诗、注关系渐趋深入的结果,也是两者关系由疏离转向融合的推动力。
三、中唐诗歌自注的特征
中唐时期,98位诗人在其1294首诗作中使用了自注,诗人与自注诗的规模都达到顶峰,自注也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就诗人而言,主力诗人对自注的使用表现出广泛性与集中性的并存。广泛性是指诗人规模的明显扩大,盛唐时期主力诗人在使用自注的诗人总数中占比36.7%,中唐时期则高达74.5%,主力诗人最终成为自注的主要使用者。集中性则指主力诗人中自注高产者的占比锐减,自注使用的垄断性更加明显。盛唐时期使用自注的11位主力诗人中,6位是自注诗超过均值的高产诗人,该时期93.7%的自注诗为其所有。中唐98位使用自注的诗人中,高产者仅有12位,占比16.4%,其自注诗却占该时期自注诗总数的84.9%。
就诗、注关系而言,中唐时期自注对诗歌内蕴的阐释力度达到顶峰,诗、注的深度融合也最终实现。
首先,从各类自注的数量变化看,使用体式注的诗歌在自注诗总量中的占比由盛唐的30.7%下降至8.4%。而使用意义注的诗歌占比则由盛唐的22%猛增至43%。与诗歌内蕴关联最弱的体式注锐减而与之关系最密的意义注激增,这说明自注的重点已转向揭示作为诗歌核心层的情旨本事。
其次,多注诗中意义注连用的情况更普遍,且注释频次增加。盛唐时期的11首多注诗中,有7首存在意义注连用,占比63.7%。中唐时期的186首多注诗中,意义注连用者136首,占比72.6%。注释频次上,盛唐7首意义注连用的诗歌中,有3首为一诗两注,2首为一诗四注,1首为一诗五注,最多者为一诗三十一注。而中唐136首意义注连用的诗歌中,一诗两注者63首,一诗三注者31首,一诗四注者17首,一诗五注者2首,一诗六注者4首,一诗七注者5首,一诗八注者2首,一诗九注者2首,一诗十注者1首,一诗十三注者1首,一诗十四注者2首,一诗十六注者2首,一诗十七注者1首,一诗十九注者2首,最多者为一诗二十一注。虽然中唐时期意义注连用的基本频次仍为一诗两注或三注,甚至最高频次不及盛唐,但高频段自注的基准却整体抬升:盛唐时期高频段的一诗四注及五注在中唐则降至低频段;一诗六注至十注也仅属于中频段;一诗十注以上者,方进入高频段。盛唐时期,属于高频段意义注连用的诗歌仅有一例,即使用了三十一处意义注的李翰《蒙求》诗。但在中唐,中、高频段意义注连用的诗歌已小有规模。意义注连用诗歌数量及连用频次的增加,说明自注向诗歌内蕴层面的延伸渗透在中唐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复次,自注辅助诗歌明情达意的方式在继盛唐旧法外又有新创,从而推动了诗、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强化式”是中唐时期自注彰显诗歌内在情蕴的新途径,即通过自注对诗中情旨、本事的烘染,增强诗歌的表现与感染力,突显诗人的情感态度。如卢纶的《秋中过独孤郊居》,题下注:“即公主子。”全诗如下:
开园过水到郊居,共引家童拾野蔬。高树夕阳连古巷,菊花梨叶满荒渠。秋山近处行过寺,夜雨寒时起读书。帝里诸亲别来久,岂知王粲爱樵渔。(28)卢纶:《卢纶诗集校注》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49页。
诗中对独孤氏离尘索居的淡泊心境与晴耕雨读的生活状态的叹赏已表露无遗。而自注又特意指出其乃玄宗之女信成公主与驸马独孤明所出(29)卢纶《秋中过独孤郊居》诗中关于独孤氏的身份,参见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3163D《秋中过独孤郊居》条,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545页;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659页。这一非同寻常的出身。如此,不仅使诗中的“帝里诸亲”之说有所依托,也点明了王粲之比的缘由。更重要的是自注强化了独孤氏身份与生活状态的反差,从而突出其通透宁静的心性。诗人的仰慕赞誉之情也因自注对人物身份的揭示而愈加真挚浓郁。
最后,纪事类新题乐府成为新的自注阐释对象,诗、注融合的领域进一步拓展。唐代的新题乐府从题材上分为两类:一类反映普遍而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称为纪事类新题乐府或新乐府正题;一类书写闺情、行役、边塞等个体的情怀、生活,称作新乐府杂题(30)王辉斌:《乐府诗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9-70页。。自注在盛唐已运用于古题乐府中,如李白《上云乐》《司马将军歌》《君道曲》《东海有勇妇》《秦女休行》《怨歌行》的题下自注。而自注在新题乐府中的使用则到中唐才出现,并且仅存于李绅《新乐府》二十首、元稹《和李绅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这些纪事类新乐府中。
纪事类新乐府的创作宗旨在于指陈时弊、疗救社会,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批判性。因此,陈述事件-剖析问题-提出见解主张是这类乐府创作的基本思路。在李绅、元稹、白居易的纪事类新乐府中,自注大多承担的是叙事任务。
一方面,自注为诗中的叙、议衔接做铺垫,避免由叙转议的意脉断裂。如元稹《和李绅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驯犀》题下注曰:“李传云:贞元丙子岁,南海来贡,至十三年冬,苦寒,死于苑中。”(31)元稹:《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指的是贞元九年(793)十月,环王国向德宗皇帝所献犀牛因不抵贞元十二年冬的酷寒,死于禁苑之事。若无自注对驯犀事件的完整交代,那么诗人所发出的重天道、遵物性的警示势必因缺少前情提要而备显突兀。诗末所揭“前观驯象后观犀,理国其如指诸掌”这一治国如同驯物,当使百姓各司其职、各安其份的创作主旨也便失去了根基。
另一方面,自注以叙代议,成为彰显诗人情感意图的手段。“卒章显志”是中唐纪事类新乐府的共同特点,而自注的叙事则是对诗旨的烘托暗示,为诗末的点题蓄势,使诗旨的揭示自然有力,从而更有效地发挥纪事类新乐府针砭时弊、疗救社稷的政治功能。如白居易《法曲歌》首三句句下注“永徽之思,有贞观之遗风,故高宗制《一戎大定》乐曲也”(32)白居易:《白居易诗集校注》卷3,中华书局,2006年,第283-284页。,通过叙述《大定曲》的产生背景,有意突显其作为平夷之乐所承载的贞观、永徽两朝帝王开疆拓土、缔造王朝一统格局的谋略与抱负,从而呼应诗中“治世之音安以乐”的命题。而句中自注交代玄宗变革法曲的详情始末,则作为《大定曲》的反例出现:“法曲虽似失雅音,盖诸夏之声也,故历朝行焉,玄宗虽雅好度曲,然未尝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始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深异之。明年冬,而安禄山反也。”“未尝”一词包含着对胡乐入法曲这一变革的质疑态度。而“识者深异”则是借鉴《庄子》的重言手法,以当朝音乐权威的“深异”之态为己代言,增强反对颠覆法曲华夏正声传统的力度。自注结尾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作为这场音乐变革的后果,将两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巧合刻意转化为因果的必然联系,从而指出胡曲之于华音与胡人之于中原王权一样,具有相同的“入侵”本质。正因为自注将礼乐与政治表里一体的古老命题进行了富于时代性的诠释,并于其中表现出诗人鲜明的姿态立场,篇末“正华音,别夷夏”的呐喊才更显铿锵自然。
四、晚唐诗歌自注的特征
晚唐是唐诗自注发展的最后阶段,共有78位诗人的637首诗使用自注,占其诗歌总数的5.6%,人均自注诗8首。晚唐自注诗在总数上仅次于中唐,但在自注诗占比及人均自注诗数量上,则逊于盛、中唐,可见该时期自注诗的增速明显下滑。
主力诗人参与度的下降不仅是导致晚唐诗歌自注锐减的决定因素,也是这一时期诗歌自注的重要特征。晚唐637首自注诗中,有603首出自主力诗人之手,占比为94.6%。尽管主力诗人依旧是使用自注的主体,其规模与实践力却在萎缩衰颓:就中、晚唐使用自注的主力诗人比例而言,以《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所收年代可考诗人为标准,中唐时期的主力诗人共92位,使用自注的有73位,占比79.3%,人均自注诗约17首。晚唐时期主力诗人共87位,使用自注者52位,占比59.8%,人均自注诗约12首。较之中唐,晚唐使用自注的主力诗人占比锐减近二十个百分点,人均自注诗数减少5首。就中、晚唐时期自注诗高产诗人数量及其自注诗比例而言,中唐主力诗人中的自注诗高产者有12位,自注诗1088首,占主力诗人自注诗总数的84.1%,人均自注诗高达91首。相比之下,晚唐自注诗高产者增至19人,但其自注诗仅530首,人均自注诗减至28首。由于自注诗高产者均来自主力诗人,是其中自注使用力度最强的成员,而主力诗人的自注诗数量往往又奠定了唐代各期(初唐例外)自注诗的基本规模,因此他们实际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关系链。而作为自注发展核心动力的自注高产者在自注使用上的乏力,则直接导致主力诗人数量及晚唐诗歌自注数量的下降。
此外,诗、注融合进程的停滞是晚唐诗歌自注的又一新变化。
一方面,多注诗中意义注连用的频次明显降低。意义注连用仍以一诗两注与三注为主,高频段多注诗仅郑嵎《津阳门诗》一首,共三十二注。中频段多注诗共五首,仅有一诗六注与七注两种情况,若对位中唐的相同频段,只属于其中的低频次层级。意义注与诗歌情旨内涵的关系最密,多注诗中意义注使用频次的下降,必然会削弱诗、注的内在黏合度。而导致此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长篇诗作中意义注连用频次的下降。除《津阳门诗》外,晚唐时期使用意义注连用的16首二十韵至百韵的长诗中,两注及三注诗共13首;其余3首均为四注诗。较之中唐白居易、元稹等人的百韵长篇动辄出现十多条意义注,其稀疏程度显而易见。长篇诗作的信息量更丰富,也更易使意义注发挥作用。而晚唐诗人显然并无详解其长篇诗作的积极意识,零星的意义注散落于规模可观的篇什间,释解的乏力与由此导致的诗、注深入融合的困难便无可避免。
另一方面,晚唐诗人全面继承了盛、中唐时期自注彰显诗歌内蕴的方式,并将其运用得更加灵活成熟。触引、补充、引申、强化四种途径在晚唐诗人手中不但被逐一应用,更出现了像李续《和绵州于中丞登越王楼见寄》的题下注兼用触引与补充两种方式彰显诗歌情旨的现象。然而沉溺于对固有途径的继承,也极大消解了晚唐诗人的探索热情。或者反过来说,正是追新求变上的乏力,才使得晚唐诗人格外努力地恪守旧式,终未能开创自注与诗歌内蕴融合的新途径。而如李续诗注之类,也不过是对旧有阐释方式的排列组合,并非根本性的创变。综而言之,晚唐自注对诗歌内蕴的揭示,看似纯熟自如,实则是失去创造活性的套路操作,从根本上暴露了此时期诗歌与自注深层融合进程的僵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