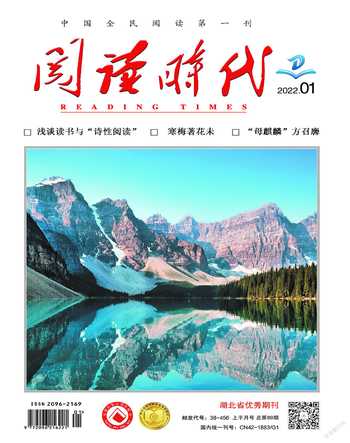林徽因的“太太客厅”
陈学勇
旅欧归来的中国文人,带回西方“文艺沙龙”的风雅习俗。
朱光潜刚到北平,栖身在慈慧殿三号,那里每月有一次作家聚会,大家一起读诗,实验新诗是否具有诵读的可能。
梁宗岱、李健吾读法文,冯至读德文。读英文的多,有叶公超、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和朱光潜,俞平伯则吟诵词曲。这些朱自清似都不太在行,他专注的是中文字音的性能。
朱光潜住处的读诗会还来过周作人、废名、王力、林庚、卞之琳、何其芳、曹葆华、徐芳,热烈可谓盛极一时。林徽因也偶尔光临,她除擅长朗读英文诗歌,还用老家福建闽腔诵读中国古诗。名为读诗会,实际也读散文。
有时读徐志摩、朱自清、老舍的散文,流畅似水,环转如珠,比读诗尤见效果。读诗会其实也是学术交流会,会上免不了分歧、争论。梁宗岱是常发奇谈怪论的一位,也就常遭林徽因反驳,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才女争强好胜,颇有气势,君子招架不住,最后败下阵来的一定是梁宗岱。某次聚餐,能言善辩的叶公超、梁宗岱同时缄口不言,杨振声笑着问叶,你怎么只顾着吃菜?叶公超指了指正慷慨陈词的林徽因,彼此会心一笑。
这样的读诗会早先也有过。闻一多有间闻名的黑屋子,四壁裱糊得漆黑,只拦腰嵌一道金线,徐志摩将其比喻成非洲女人的手臂套了个金镯。
黑屋子聚集过“清华四子”:子沅朱湘、子离饶孟侃、子潜孙大雨、子惠杨世恩,都是诗人。稍后中南海里也召集过类似的读诗会,另外一处中国风谣学会,聚集着胡适、顾颉刚、罗常培、容肇祖他们。
女主人召集的沙龙最早应数陈衡哲的客厅,那里聚会间隔时间略长,每月仅一次,固定在某星期四下午,来的基本全是女性。
当年北平的文艺沙龙,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因为客厅的女主人有才有貌有谈锋。
这个租来的宅院距东皇城根很近,仅百米之遥。它没有朱光潜的慈慧殿三号那间厅堂宽大,却远比它舒适、温馨。
两进的四合院,坐北朝南,客厅里满地阳光。透过玻璃窗望出去,垂花门把都市喧嚣隔在门外,方砖铺地的院子,错落着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几株丁香,浮动的暗香一阵阵飘进客厅。
每天下午举行茶会的这个“太太客厅”,按说还连带后院金岳霖的寓所。逢周六下午,来客便移足金岳霖那间排满八个书架的长方形起居室,它和梁家院子只隔一道相通的边门。
大家叫它“湖南饭店”,轮到这一天,金岳霖管来客晚饭,管饭的东道主一口湖南腔。
朱光潜的“读诗会”直奔主题,与会者有备而来。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则没有主题,随意、即兴、散漫,神仙会,宽松之至,朋友间的私人情谊和共同志趣是联系彼此的精神纽带。
“太太客厅”里不大读文学作品,来客也不限于沈从文之类的作家。哲学教授金岳霖、经济学教授陈岱荪、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考古学教授李济、艺术学教授邓叔存、艺术家常书鸿,都是常客。
而张奚若、周培源、陶孟和则喜欢偕夫人双双而至,陶夫人沈性仁是位翻译家。来者晚年大多成了他们各自领域的巨擘。
梁思成的妹妹、侄女也时常带着女同学凑热闹,她们只为一睹才女风采。这些女孩里便有几年后加入共产党的龚澎、二十多年后名扬四海的作家韩素音,再有是林徽因才相识不久的一对美国年轻学者费正清和费慰梅。陈岱荪说,他在这里遇见过费慰梅的父亲、哈佛校长坎南。
太太客厅里饮茶论道,绝非女主人用来附庸风雅的闲处,林徽因本人已雅到极致。若说附庸,只是别人来附她。客厅的日子是林徽因精致生活的组成,与病中忘我工作一样,都是她追求生活质量的一个侧面,工作与清谈,有岭有峰,一座山。金岳霖说:“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从来不是打发日子的生活,对于他们,日子总是不够用的。”林徽因有首她的各种文集失收的小诗:
优闲的仰着脸
望:
日子同这没有云的天
能不能永远?
又想:
(不敢低头)
疑問同风吹来时,
影子会不会已经
伸得很长,
寂寞地横在
衰柔的青草上?
仅五十余字的短章,看似不甚起眼的题材,意象似乎也平常,谁没有过仰脸望天的时刻,没有过低头凝视草动影移?然而,摄取这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琐屑,油然品味出作者隐隐的一缕情思。日子是人来过的,无云(必须无云)的天则是永恒的自然。希冀岁月久长乃人性本初,若在希冀中白白流逝了岁月,岂不与本初相忤?诗里未必没有一丝逝水如斯的惆怅,但诗人是否也提醒你或她自己,万不可让时光寂寞无聊地磨蚀?有此体悟便明白,诗人借客厅以紧紧攫住悄悄流失的时光,过好日子。
太太客厅里话题十分广泛,进客厅的人都颇具各门学养,可不论他建树哪方学术领域,无不喜欢诗词书画,谁不能发挥几句?议论时政自是不免,个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批饱饮洋墨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体与胡适的立场、态度相仿。他们憧憬西方民主制度,以为那是中国的出路。国民党政权仿照的是西方模式,他们理应支持当局,反对共产党暴力革命。前苏联革命的见闻给他们刺激、恐惧,远庖求安。然而现实又是,数千年封建遗习残留在国民党衙门机制和鱼肉人民的权贵身上,包括蒋介石,弊端、劣迹、恶习,随处可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良知、正直,搬用西方的民主标准,批评当局是异常辛辣尖锐的,十足的书生意气。不过,他们对介入政治活动极为谨慎,即使是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也尽量将话题收束在学术层面,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林徽因是这群知识精英宠爱的中心骄子,费慰梅这样记述沙龙女主人的风采:
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太太客厅”里林徽因的许多见解别具慧眼,虽不着一字,却无字无形地滋润了北方文坛。她在客厅里约见青年作家,提携有为的新人。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向往神秘的客厅、神化的太太,以一登北总布胡同三号院为幸。《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萧乾的小说处女作《蚕》。小说刚上报纸,林徽因立即托沈从文约请萧乾来东城北总布胡同。萧乾就读的燕京大学远在西郊海甸,听说将要见着才女,他兴奋得几天坐立不安。进城那天穿得干干净净,骑了两小时自行车到府右街沈家,随同沈从文进了这座他向往已久的文学象牙塔。萧乾终生难忘林徽因那绰约风姿,原以为身患重症的女主人一定斜倚病榻,满面倦容,不意林徽因全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去外国人的俱乐部骑马,此时刚刚归来。林徽因迎面就夸奖萧乾:“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写作能够投入感情,孺子可教,这是林徽因约见他的原由。林徽因说个不停,在座的金岳霖和沈从文、梁思成全没有插嘴的缝儿。萧乾受此激励,比喻女诗人一番高论犹如在刚起跑的小马驹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一面定终生,他由此飞驰起来,成为京派文学的生力军。萧乾这样记下初见林徽因印象:“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語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对文章常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他与林徽因也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林徽因病逝四十五年后,双鬓染霜的萧乾已然成就卓著,他回顾一生文学道路,虔诚地表白:“在我心坎上,总有一座龛位,里面供着林徽因。”
像萧乾知遇林徽因的还有卞之琳和李健吾,才情十足的两位作家提起这位客厅女主人异口同声,称赞不绝。卞之琳内向、口讷,也说:“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谈吐爽快、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她年龄比我只大六岁,因为师辈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
这么一个“太太客厅”,这么一位睿智的太太,发表过无数启人心智的隽言妙语,它们都如过耳春风,飘逝了,无影无踪。萧乾感叹:“每逢我聆听她对文学,对艺术,对社会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精辟见解时,我心里就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林徽因身边没有博斯韦尔,她自己也难得把即兴言词著为文章,或有例外,不过寥寥数篇。不妨抄录林徽因谈论诗歌创作文章的头两段,读者权当进了一回“太太客厅”,尽力想象女主人酣畅雄辩的谈吐:
写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写诗,或可说是要抓紧一种一时闪动的力量,一面跟着潜意识浮沉,摸索自己内心所萦回,所着重的情感——喜悦,哀思,忧怨,恋情,或深,或浅,或缠绵,或热烈,又一方面顺着直觉,认识,辨味,在眼前或记忆里官感所触遇的意象——颜色,形体,声音,动静,或细致,或亲切,或雄伟,或诡异;再一方面,又追着理智探讨,剖析,理会这些不同的性质,不同分量,流转不定的情感意象所互相融会,交错策动而发生的感念;然后以语言文字(运用其声音意义)经营,描画,表达这内心意象,情绪,理解在同时间或不同时间里,适应或矛盾的所共起的波澜。
写诗,或又可说是自己情感的,主观的,所体验了解到的;和理智的客观的所体察辨别到的,同时达到一个程度,腾沸横溢,不分宾主地互相起了一种作用,由于本能的冲动,凭着一种天赋的兴趣和灵巧,驾驭一串有声音有图画,有情感的言语,来表达这内心与外界息息相关的联系及其所发生的悟理或境界。
责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