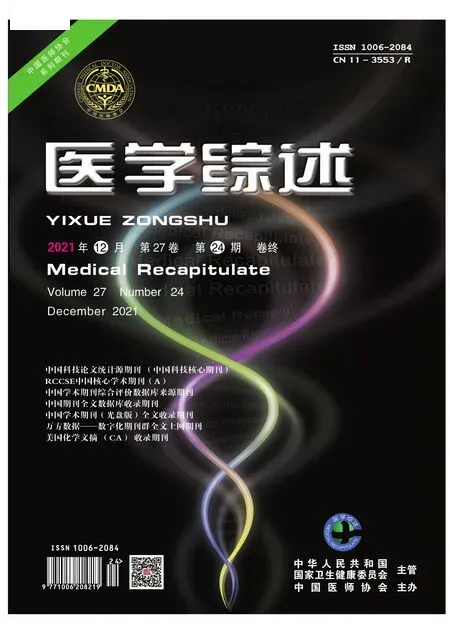PARP抑制剂在乳腺癌中的作用机制及耐药性相关研究进展
罗青松,张季,李臻,杨思原,孔舷淑,邹天宁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乳腺科,昆明 650118)
乳腺癌在女性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较高,对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危害。据报道,约10%的乳腺癌具有遗传性,而高达25%的遗传性乳腺癌与生殖有关,目前研究较多的为乳腺癌易感基因(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BRCA)1和BRCA2,携带BRCA1或BRCA2的人群终生患乳腺癌及卵巢癌的风险较正常人群显著升高[1]。抑癌基因BRCA1和BRCA2可以通过同源重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HR)修复进行DNA双链断裂修复,其功能的缺失容易导致基因的不稳定性,进而导致肿瘤细胞的产生[2]。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是一种DNA修复酶,其能够识别DNA受损的片段并被激活,从而进行碱基切除修复,在DNA单链断裂修复、调控程序化细胞死亡、维持DNA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3]。BRCA与PARP分别通过不同的信号通路进行DNA损伤的识别与修复,对维持基因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PARP抑制剂对BRCA1和BRCA2突变的肿瘤细胞异常敏感,因此PARP抑制剂被用于治疗HR缺陷的恶性肿瘤[4]。由于PARP抑制剂能与HR修复缺陷产生协同致死效应,其在治疗BRCA1/2突变癌症患者中取得了重大成功。但PARP抑制剂的临床研究和应用还存在许多问题,其抗肿瘤机制与耐药性分子机制仍未完全明确。现就PARP抑制剂在乳腺癌中的作用机制及耐药性相关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PRAP及PARP抑制剂概述
1.1PARP的结构与功能 PARP在DNA修复通路中起关键作用。PARP家族有17个成员,其催化区域具有同源性[5]。PARP家族的酶将聚ADP核糖链与目标蛋白酶共价连接的过程称为多聚核糖基化[6]。在PARP家族的所有蛋白质中,PARP1是最重要的PARP,在DNA损伤修复中,PARP1产生了近90%的多聚核糖基化[7]。PARP1有3个结构域,分别为3个锌指结构(Zn Ⅰ、ZnⅡ、ZnⅢ)构成的N端 DNA结合域、1个BRCA1 C端结合域构成的中间调节域和1个C端催化域,其中C端催化域又由3个亚结构域组成:1个富含色氨酸-甘氨酸-精氨酸域、α螺旋结构域和ADP-核糖基转移酶催化结构域[8]。
在DNA未与PARP结合的状态下,α螺旋结构域可以抑制PARP1中的ADP-核糖基转移酶与β-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NAD+)结合[9]。当出现DNA单链断裂后,PARP1中的锌指相关结构域识别DNA缺口并与之相互作用,PARP1与受损的DNA链结合后,α螺旋结构域的自抑制功能被取消,从而激活ADP-核糖基转移酶的催化功能,将NAD+分解为烟酰胺和ADP核糖,再将ADP核糖作为底物,使受体蛋白(主要为PARP)自身聚ADP核糖化,形成PARP1-ADP核糖支链[10]。PARP1-ADP核糖支链可以促进DNA修复元件的募集和染色质重塑[11]。而聚腺苷二磷酸核糖水解酶[poly(ADP-ribosy) glycohydrolase,PARG]可以使解离下来的PARP1-ADP核糖支链分解成ADP核糖和PRAP,烟酰胺可以重新利用ADP核糖再次合成NAD+,PARP则可以继续介导DNA损伤修复[12]。
1.2PARP抑制剂的结构与功能 PARP抑制剂的成分主要为NAD+类似物,其可以与NAD+竞争性结合PARP催化结构域的活性位点,使PARP的活性受到抑制,进而影响PARP1-ADP核糖支链的形成并使之不能招募DNA损伤相关修复蛋白,最终造成DNA损伤修复失败[13]。第一代PARP1抑制剂为烟酰胺,其次为3-氨基苯甲酰胺。随后开发的所有PARP1抑制剂均包含烟酰胺/苯甲酰胺药效团,并与NAD+竞争PARP的催化中心[14]。目前,已有4种PARP抑制剂(Rucaparib、Olaparib、Niraparib和Tala-zoparib)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批准。
2 PARP抑制剂在乳腺癌中的作用机制
2.1协同致死效应 协同致死效应即PARP抑制剂可以选择性杀伤BRCA突变引起的HR功能修复缺陷的肿瘤细胞,而对BRCA正常的细胞没有影响[15]。开发PARP抑制剂的基本原理就是基于协同致死性的概念,其中两个基因的突变构成协同致死效应,但是一个单独的突变则可以维持细胞的活力[16]。BRCA1与BRCA2是抑癌基因,它们通过HR参与双链DNA断裂修复,以维持基因组完整性。但BRCA突变的癌细胞存在HR缺陷会导致染色体异常,进而引起染色体的不稳定[17]。有研究显示,PARP1参与了DNA单链断裂的修复,DNA单链断裂的持续损坏可能会引起复制叉的崩塌,从而产生DNA双链断裂,通常由HR来修复[18]。因此,用PARP抑制剂处理过的BRCA突变的癌细胞会累积DNA单链断裂,导致基因双链断裂不能通过HR途径修复,最终引起细胞周期停滞进而死亡[19]。可见,协同致死效应是PARP抑制剂作为一种单药消灭肿瘤细胞的直接作用机制。
2.2PARP-DNA捕获理论 除了协同致死效应外,Murai等[20]提出了PARP抑制剂的第二种作用机制,即将PARP-DNA复合物捕获在DNA损伤部位,由于长期存在的PARP-DNA复合物,细胞持续存在于细胞周期中的S期,被抓捕的DNA就变成了遗传毒性更厉害的DNA双链断裂,最终干扰DNA复制,而捕获PARP-DNA复合物的能力与PARP抑制剂的细胞毒性有关。临床上,PARP抑制剂可根据其捕获PARP的能力进行排名:Talazoparib≥Niraparib>Olaparib=Rucaparib≥Veliparib[21]。这种作用机制是PARP抑制剂的临床开发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在临床试验中常与常规化学疗法结合使用。
2.3其他 PARP抑制剂的细胞毒性是一个多阶段、多步骤的过程。其能通过阻断PARP1与环状鸟苷一磷酸-腺苷一磷酸合酶的互相作用阻止肿瘤的发生[22]。除DNA修复和复制叉的稳定外,PARP1还参与基因表达调控,RNA加工和核糖体的产生,这可能有助于抑制PARP的细胞作用[23]。有文献报道,PARP1能够调节与p53、核受体、核因子κB有关的转录调节因子的活性[24]。因此,转录失调可能会使肿瘤细胞对PARP抑制剂更为敏感,如核因子κB的过度活化能通过PARP抑制剂得以减弱。此外,抑制PARP功能,将会使核仁中的DDX21泄露到细胞核中,从而减少核糖体DNA转录和核糖体的产生,最终抑制乳腺癌的生长[25]。
3 PARP抑制剂在乳腺癌中的耐药分子机制
有研究表明,在携带BRCA突变的患者及小鼠模型中,BRCA突变的携带者对PARP抑制剂的反应效果通常会因高耐药率而受损[26]。此外,另一项关于BRCA突变肿瘤的研究表明,铂类药物的耐药在一定程度能够预测PARP抑制剂也会耐药,表明它们可能具有共同的机制[27]。根据体内和体外研究结果,现已确定了几种耐药机制,见表1。

表1 PARP抑制剂耐药机制
3.1药物外排蛋白的过表达 在缺乏BRCA1的乳腺癌小鼠模型中,大多数对PARP抑制剂表现出耐药性的肿瘤均显示出药物外向转运蛋白基因Abcb1(也称为MDR1)编码的P-糖蛋白过表达[28]。P-糖蛋白是ABC家族的一个成员,可转运细胞分子、营养素、药物和毒素等。文献报道,Abcb1基因的上调会导致癌细胞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29]。但研究显示,P-糖蛋白的底物目前仅有奥拉帕尼和芦卡帕尼,其他PARP抑制剂(如AZD2461、维利帕尼和CEP-8983)均不是P-糖蛋白的底物[30]。同时,长时间使用PARP抑制剂中的奥拉帕尼会提高小鼠癌症模型的P-糖蛋白水平,减少细胞内的药物摄入、使药物外排增加,最终引起药物浓度降低,从而产生耐药[28]。有学者在耐PARP抑制剂的人卵巢癌细胞中观察到Abcb1的过表达,通过加用MDR1抑制剂维拉帕米共同治疗可以逆转其耐药性[31]。然而,P-糖蛋白的过表达与PARP抑制剂的耐药性有关尚未有充足的临床证据。MDR1抑制剂联合PARP抑制剂治疗可能是未来的一种治疗策略。
3.2PARP1和PARG蛋白的变化 PARP1和PARP2作为PARP家族中最重要的成员,也是PARP抑制剂的主要靶标,癌细胞中PARP1表达水平的变化会导致PARP抑制剂产生耐药性。在BRCA1缺失的HCC1937细胞中发现,PARP1表达水平的升高导致PARP抑制剂耐药性的产生,且与乳腺癌患者的预后较差有关[32]。然而,有文献报道,PARP抑制剂的细胞毒性远大于PARP1基因缺失引起的细胞毒性[33]。不同PARP抑制剂抑制PARP蛋白催化活性的能力与PARP抑制剂的细胞毒性能力无关。相反,不同抑制剂在受损染色质上捕获PARP蛋白的能力能够更好地预测细胞毒性[34]。在人类细胞模型中,PARP1和PARP2均被PARP抑制剂——Olaparib捕获在染色质上[34]。然而,由于干扰小RNA介导的PARP1的耗竭能够减弱Olaparib的细胞毒性,因此有学者推断,改变PARP1捕获DNA的能力是PARP抑制剂耐药的机制[31]。这与PARP1是细胞中最丰富的PARP蛋白的结果相符,且PARP1也负责90%细胞的多聚核糖基化修饰[35]。
此外,PARG的缺失和上调也是PARP抑制剂产生耐药性的原因[36]。有研究报道,PARG的缺失部分恢复了PARP抑制剂处理细胞的多聚核糖基化修饰,减少了PARP1对DNA的捕获,挽救了部分依赖DNA损伤信号的PARP1[37],从而恢复了PARP1的催化活性,阻止了不受控制的复制叉进程,足以使得下游的DNA损伤相关修复蛋白得到补充,进而导致PARP抑制剂产生耐药性。以上数据表明,PARP抑制剂并不能完全阻断PARP活性,内源性PARG活性对PARP抑制剂的细胞毒性作用也至关重要,且这种耐药机制在BRCA2或BRCA1突变的人类细胞系中也被观察到。
3.3HR的恢复
3.3.1BRCA1和BRCA2的重新激活 HR恢复的一个明显机制为继发性遗传改变导致BRCA1/2功能的重新激活。研究显示,在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和前列腺癌中,BRCA1/2以及RAD51C、RAD51D和PALB2等基因的许多继发突变,即回复突变,使得阅读框架重新开放,同时还可以恢复蛋白质的活性[38]。有关肿瘤细胞模型的研究表明,回复突变的发生率很高,从而产生了对PARP抑制剂的耐药性[39]。另有研究发现,回复突变通常显示出微同源性特征,表明它们是由原始HR缺陷细胞中通过易错修复机制修复DNA双链断裂的结果[40]。此外,这种回复突变不仅引起PARP抑制剂耐药,还参与了其他破坏DNA药物的耐药。
3.3.2抑制非同源末端连接(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NHEJ) 有学者发现,恢复HR的第二种方法为抑制NHEJ,DNA双链断裂大部分通过3种途径修复,即HR、NHEJ和微同源介导的末端连接,由于缺乏HR的细胞无法通过HR来修复DNA双链断裂,因此这些细胞中的NHEJ增加,而NHEJ缺陷的细胞会对PARP抑制剂产生耐药性[41]。另有文献报道,HR的恢复是由于p53结合蛋白1(p53 binding protein 1,53BP1)失活而引起,53BP1能通过遏制HR修复所需的DNA末端切除,进而促进NHEJ[42]。因此,失去53BP1功能可促进不依赖BRCA1的末端切除表现出对PARP抑制剂的抵抗。后续研究发现,53BP1 介导的修复下游因子[如RIF1(Rap 1-interacting factor 1,RIF1)和病毒颗粒蛋白表达调节因子 7]的失活也导致DNA末端切除的恢复,从而促进了HR的修复[43]。有学者发现了一个名为Shieldin的53BP1信号转导复合体,其由病毒颗粒蛋白表达调节因子7、SHLD1、SHLD2和 SHLD3组成[44]。Shieldin可以通过限制DNA末端切除而在53BP1途径中充当下游效应因子[45]。从机制上来看,Shieldin复合物直接定位于DNA双链断裂位点,其丢失会损害NHEJ并引起切除过度[41]。同时,由于HR的恢复,Shieldin 基因的突变会导致BRCA1缺失的细胞和肿瘤对PARP抑制剂产生抗性[43]。此外,Dynein轻链LC8型1和HELB解旋酶的失活也可以促进末端切除并恢复独立于53BP1外的HR途径,从而导致BRCA1缺陷细胞对PARP抑制剂产生耐药性[46]。
3.4稳定DNA复制叉 在BRCA1/2缺失的细胞中,稳定的复制叉和HR恢复与DNA双链断裂修复有关,已成为PARP抑制剂耐药性的替代机制。有报道称,在BRCA1/2缺失的情况下,MRE11和MUS81等核酸酶会破坏复制叉,导致新生链缩短,复制叉塌陷和染色体畸变[47]。Zeste 2多梳抑制复合物2亚基的增强子和PTIP(PAX transcription activation domain interacting protein)分别参与将MUS81和MRE11招募到停滞的复制叉中,有学者发现它们可以调节PARP抑制剂的敏感性[47]。有研究显示,miR-493-5p通过下调MRE11和核酸外切酶1从而稳定复制叉,表明miR-493-5p的过表达可诱导BRCA2突变肿瘤对PARP抑制剂产生耐药性[48]。此外,研究还发现ATR/CHK1轴既有助于HR恢复,也有助于BRCA缺陷细胞稳定复制叉[49]。因此,目前正在研究使用ATR/CHK1抑制剂治疗PARP抑制剂耐药性的癌症[49]。同时,SMARCAL1、ZRANB3和HLTF等前叉重塑因子的耗尽也会促进MRE11降解,从而降低对PARP抑制剂的敏感性[50]。
4 小 结
尽管PARP抑制剂在乳腺癌和卵巢癌的临床试验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临床应用开发PARP抑制剂中还存在许多的挑战:①单一或联合用药的方式及顺序;②Olaparib等药物的水溶性低,不易通过血脑屏障;③长期治疗的安全性;④明确和克服耐药性的机制;⑤PARP抑制剂能对正常组织造成DNA积聚性的损害等。目前已知PARP抑制剂能够抑制PARP1和PARP2,但还需要阐明它们对PARP家族其他成员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增加PARP抑制剂对PARP1的特异性[51]。
在临床治疗中,由于PARP抑制剂的协同致死效应与PARP-DNA捕获理论,其为乳腺恶性肿瘤的诊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治疗靶标,但对PARP抑制剂的耐药性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HR的恢复与稳定的复制叉作为PARP抑制剂重要的耐药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虽然目前已对PARP抑制剂的耐药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揭示了不同的机制,但仍需要系统和全面的临床试验来开发克服PARP抑制剂耐药的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