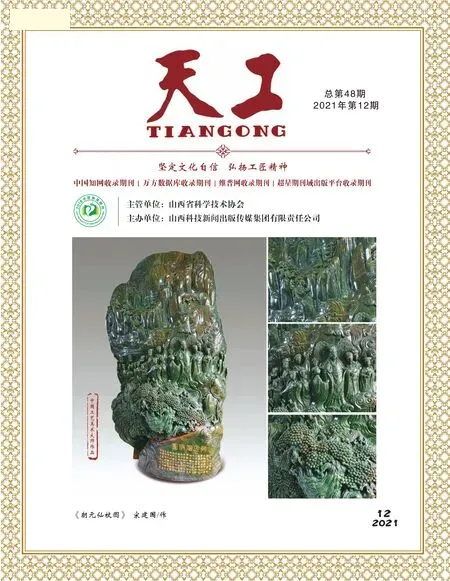从繁峙公主寺壁画中的人物饰品透视明代金属工艺的发展
史宏蕾 张雨晖
1.山西大学 2.太原科技大学
公主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杏园乡公主村,其布局呈长方形,坐北朝南,东西宽40米,南北长96.63米,占地面积4638平方米,属五台山北台外九寺之一,为繁峙县十二大寺院之一。[1]公主寺始建于北魏,后历经迁址和几次重建。据公主寺过殿现存石碑“大元五台山隐峰山古公主寺禅寺开山第一代秋月德公和尚道行碑”记载:“届《清凉传》云,北台之西繁峙县东南有一寺名公主寺,后魏文帝第四女信诚公主所置,年代深远,瓦甓犹在。又唐昭宗乾宁三年,有僧名丑丑于寺得一玉石,自持至都,献武则天,赐绢百束,且需置额重兴殿宇。实值金、宋以来,兵烬之后,堂殿经阁,犹风捧于青云……”[2]依据碑文记载内容,可以推测出关于公主寺的大致历史脉络:公主寺始建于北魏,因魏文帝的第四个女儿信诚公主在此出家而建,也因此得名。至金代,由于战事连绵,寺庙在战争中焚毁殆尽。唐朝时,僧人得到武则天的赏赐后重修庙宇。明代时,原位于繁峙县城东南14千米峪内的山寺村公主寺,迁址到公主村后再重建。而后的岁月中,公主寺又几经修葺,最终成为现在的模样。
公主寺内现存建筑中,除毗卢殿和大佛殿为明代弘治年间遗存,关帝庙、圣母殿以及韦陀殿等均为清代建筑。据考,大雄殿建于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其脊槫垫板下侧留有“大明国弘治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吉时上梁”的墨书题记可为佐证。殿内四墙壁画的绘制时间应与建筑物大致相同或者略晚。依据榜题记载,壁画作者为真定府画匠戎钊、高升、高进、张鸾、冯秉相、赵喜。壁画内容以北水陆法会仪文《天地冥阳水陆仪文》为参考进行绘制,所绘人物形象可分为正位神祇、天仙、下界神祇、冥府神祇、往古人伦和孤魂六大类。但在公主寺壁画中也有未包含在《天地冥阳水陆仪文》中的人物形象出现。
一、金色在壁画人物饰品中的应用
公主寺大雄殿壁画分为东、南、西、北四墙。东、西两壁绘制佛教、道教神祇;南壁绘有由引路王菩萨带领的往古人伦、阿难尊者和由面然鬼王带领的孤魂野鬼和地狱景象;北壁绘制有十大明王和六子闹弥勒。四墙壁画中除北壁漫漶,其余三墙壁画保存均较为良好。
公主寺壁画属于工笔重彩画,整体设色艳丽,色调偏暖,色彩饱和度高,有比较强的民间特色。壁画绘制者在佛祖宝座,菩萨宝冠、衣襟以及天神的冠帽、甲胄、头盔等需要着重描绘的地方使用了沥粉贴金的方式进行强调。这种装饰方式很好地突出了人物造型中的重点,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节奏感,也能让壁画产生更加良好的视觉效果,使整个殿堂看起来更加富丽堂皇。
然而,壁画绘制者在创作过程中使用“金色”,是作为材质色用于展现壁画中人物配饰的金属质地,还是仅仅为了美观而使用“金色”表达?为便于探讨壁画中人物配饰的金属色和饰品质地的关联,以及金色的应用范围,首先依据公主寺壁画中人物饰品的外观造型,根据其显著的区别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以菩萨、帝释天主为代表的佛教人物形象
东壁描绘有呈坐姿的普贤菩萨(如图1),菩萨头戴花鬘冠,冠口装饰以莲花纹,宝冠正中绘火焰纹,填以赤、白、青三色,火焰纹边缘以及整个宝冠边缘皆为金缘,宝冠以金簪固定,金簪尾部弯曲,有一金色圆环穿于金钗内,圆环下缀金色流苏、珠结。菩萨颈部佩戴有多层穿组项圈式璎珞,并垂挂有“U”形单排白色串珠项链。项圈乃是金属部分,用沥粉贴金工艺表达质地,有上下两层璎珞垂挂于项圈左、右两端弯曲处。第一层三类严身轮状圆形饰物为装饰主体,圆形饰物下方分别缀饰流苏;第二层璎珞以垂挂于项圈左、右两端的两条长珠链为线索进行穿组。长珠链垂挂于项圈弯曲处后自然下垂至菩萨像的下腹部,再汇集于一圆形坠饰,珠链在坠饰下方又向左右两旁散开,最终垂于菩萨坐像的腿部及膝盖处。长璎珞整体为“X”形,与“U”形串珠项链、缀流苏项圈式短璎珞组合形成多层璎珞。

图1 普贤菩萨
同样位于东壁的站姿帝释天主像(如图2),其头戴宝冠,与普贤菩萨大体类似。仅在冠口和头冠内部的细微装饰上与普贤菩萨的花鬘冠稍有区别。帝释天主所戴宝冠的冠缘以黄金装饰,冠缘底部插戴有金簪用以固定宝冠,金簪尾部垂以金珠结、金流苏。颈部戴金色项圈式璎珞,主体挂饰为如意形饰物,缀配饰流苏三条;金边如意左右,各接一圆形饰物,圆形饰物下方各垂流苏一条。帝释天主身后跟随有两位侍女,图中二者服饰、装束基本一致:梳双螺髻,左、右两个螺髻顶部各有一支金簪由上而下直插发髻中,依据其插戴方式推测为花头簪子;两鬓插有青色云纹掩鬓;于两发髻之间、头顶正中位置再插一支金色弯弧形分心,分心上方插有似慈姑叶形状的挑心。

图2 帝释天主及侍女
(二)以北极紫微大帝、南斗中斗西斗星君众为代表的道教人物形象
北极紫微大帝(如图3)和南斗中斗西斗星君众(如图4)在公主寺壁画中均以男性形象出现,其配饰的华丽程度虽然不及上文中介绍的普贤菩萨和帝释天主,但在其所佩戴的冠、冕中,仍然可以见到神祇人物配戴金属饰品的大量表现。北极紫微大帝手持白色笏板,头戴冕冠,青色纟 板上覆白色天河带,纟板前后各垂八旒,每旒由数十颗白色宝珠穿组而成;在北极紫微大帝右侧可见一名头戴梁冠男子,梁冠冠额正中绘有纹饰,冠身冒以黑纱,冠口、冠缘为金色,颈饰方心曲领,手持青色笏板。

图3 北极紫微大帝

图4 南斗中斗西斗星君众
在“南斗中斗西斗星君众”这组壁画中,共绘有九位道教星君。画面构图以一位四分之三左侧面,身着黄色法服、手执白色笏板的星君为领头人。该星君身后簇拥有六位身着红色法服的星君,以及两位穿着白色法服的星君。九位星君均头戴青色莲花冠,冠身为莲瓣纹样,冠缘饰金边,有嵌宝石如意形冠顶,冠底插金色子午簪作为固定。相较于金色在佛教人物饰品配饰中的运用,该组壁画中的金属工艺应用于金属冠饰的结构处,面积虽小,但是因其金属冠饰制作精美,再加壁画中沥粉贴金工艺高超,也使得几位星君神祇身份贵气。
另外,研究壁画中神祇服饰的规制可以发现,领首星君身着黄色法服,手执白色笏板,其身后八位星君的法服或红色、或白色。若继续探究众星君手持笏板的颜色、质地,与其所穿着法服颜色的配套规律,从图中却无法找到支撑这一假设的描绘。同样手持白色笏板,星君法服颜色就有黄色、白色和红色三种。而同样着红色法服的星君,手持笏板颜色又或白、或青。足以见得画面中的八位星君手持笏板的颜色确未与其衣着颜色成套匹配。
排除着装规制,若以绘画构图需要保持画面均衡为原则进行考虑,即可见众星君手执的青色、白色笏板,在画面中是以间插的方式出现的。领头星君使用白色笏板,其背侧身后二位星君持青色笏板,而在领头星君的左侧,间隔一个站位的着红色法服的星君手持白色笏板。画面遵循着青、白笏板交替出现的节奏感,这种色彩安排方式有效地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以小面积色彩间插搭配,打破了大面积用色过分单一而造成的画面呆板、无趣。研究推测,在公主寺壁画中,诸位星君手持笏板的颜色填充,或更多为了画面的色彩协调,而并非严格遵循服饰着装规制。
二、对壁画中金属工艺饰品的推测定名
从帝释天主身后侍女的金属饰品中可见明代仕女头面中主要的三种金属饰品的插戴方式,即掩鬓、分心、挑心。插在鬓边的簪子,叫作掩鬓,此即《客座赘语》卷四载“掩鬓或作云形,或作团花形,插于两鬓”。云朵样的掩鬓,或由节日所戴“云月”演变而来。[3]“分心”插戴于发髻正中,靠近颅顶位置,其形为十几厘米长的一道弯弧,背面做出几个扁管以安簪脚,正面上缘一溜尖拱,中心高,两边依次低下来,恰如一扇展开的菩萨冠。其质多为金,或累丝,或錾刻,又或金镶玉、银镶玉,制作每每极尽工巧,图案则多以仙佛为主。[3]“挑心”插于“分心”上方,靠近发髻顶端。
明代女性饰品在南京市江宁区的明代沐氏家族墓群中可得见实物。在将军山沐氏家族墓出土的“嵌宝石头面”,有顶簪一支、挑心一支、分心一支、掩鬓一副、花头簪子一支,所有头饰均为金属制品,上嵌彩色宝珠,精美又华丽。其形与公主寺壁画中侍女的饰品配饰形状大体相似,可以佐证壁画中沥粉贴金的金属配饰确为金属材质饰品。
除女性头面外,南斗中斗西斗星君众头戴的莲花冠,也在沐氏家族墓出土实物中找到对应。沐氏家族墓出土的“明镶红宝石金冠”,宽12厘米,高10厘米,重173.1克。为女性发冠,由三层祥云纹莲瓣重叠而成,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冠顶高处竖一如意形金钗,中间镶嵌一颗红宝石。[4]而公主寺壁画中的众星君所戴莲花冠均为青色、单层莲瓣,饰金边。从二者的整体外观和各个组件的大块面造型上,即可判定二者属于同一类别冠式,区别仅在于莲瓣层次多寡、颜色和冠身的材质。
由图可见,壁画中“星君头戴的莲花冠”和“明镶红宝石金冠”都是以莲花瓣作为冠身的主体,也用作头冠的主要装饰元素,莲瓣在莲花冠的造型语言中同时具备了实用与装饰的双重价值,二者也都具有镶嵌宝石的如意形冠顶。壁画中“星君头戴的莲花冠”与“明镶红宝石金冠”一样,均为仿生莲花形状的头冠,装饰动机如出一辙。“仿生”即冠身莲瓣形态是具象化的,仿照莲花实体而做,未经过多艺术加工,也没有抽象形状。艺术表达追求“相像”,尽可能地模仿天然造型。此处的对照可证明,公主寺壁画“星君头戴的莲花冠”确有实物,而非壁画作者凭空想象臆造。画工在创作星君冠饰时,对实物记录的成分较多,二次创作的成分相对较少。
还值得一提的是,据资料记载,沐氏家族墓所出土“明镶红宝石金冠”为女冠,但公主寺壁画中众星君皆为男性造型。由此还可推测出,莲花冠在当时为男女通用的冠饰。在通用冠饰的基础上,还可以推测出当时的男女发型。此外,莲花冠作为具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头饰出现在贵族女性的随葬品中,也可从侧面映衬出当时的贵族们对道教的信仰和追崇,宗教装饰元素融入了信徒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吉祥寓意运用于人们的配饰设计之中。
再谈及男子冠饰,在公主寺壁画中位于北极紫微大帝右侧的男子头戴“梁冠”,冠缘、冠口、冠梁均有金属工艺的表现。梁冠为明代文武官员在大祀、庆成、正旦、冬至等重要节庆穿朝服时所戴的冠。在参加祭祀活动时,官员们则是穿着祭服、头戴梁冠。梁冠从汉朝至明朝,沿用了1000多年,沿用期间每朝对其形制的规定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梁冠的整体形制并不复杂,自汉代以来变化不是很大,基本保持三个主要部分,即颜题(含冠耳)、冠顶、梁[5]。梁冠上的梁的数量,以及是否配饰重金,是用于区分明代官员品级的重要依据之一。壁画中,男子所戴梁冠冠耳高耸,饰金缘,金冠梁有五或六,额花、颜题、簪纽皆具备,完全符合文献记载中对明代梁冠的描述,同时,壁画中的梁冠在造型上也与现藏于山东博物馆的明代五梁冠实物几乎一致。故此,研究推测壁画中对梁冠的创作描绘也基本是依据明代梁冠实物进行。但壁画中梁冠上的装饰纹样、冠梁的数目是否符合人物身份或事实,以及壁画中对人物冠服的二次创作成分多寡,暂未定论。
三、推测壁画中饰品金属配饰的材质
通过上述对公主寺壁画中神祇人物所佩戴黄金饰品的探讨发现,不论是璎珞、宝冠、钗环,还是发簪、头冠、珠结、流苏,其黄金的使用范围均是在配饰的骨架处和连接处。黄金饰品除装饰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起到固定和连接璎珞的作用。
另据现有资料,在公主寺壁画中,又有如下三处人物饰品可以与现已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对照。第一,帝释天主身后侍女的掩鬓、分心、挑心、花头簪子,与南京市江宁区明代沐氏家族墓群中的头面相互对照。壁画中头饰的外观造型与沐氏家族墓出土的头面造型大体一致,而头面的具体插戴方式,又可以在壁画中的侍女像上找到对应。第二,南斗中斗西斗星君众头戴的青色单层饰金边莲花冠,也可在明代沐氏家族墓群中找到“明镶红宝石金冠”作为实物对照,二者在造型和材质、颜色上都别无二致。第三,位于北极紫微大帝右侧的男子头戴的梁冠,其形和金饰部分与现藏于山东博物馆的明代五梁冠实物基本一致。
由此可见,画师对壁画中人物饰品的沥粉贴金并不只是为画面富丽堂皇的美观效果考虑,也如实反映了饰品的材质,其金属材质体现了神祇人物的华贵。
通过此三处壁画中的人物饰品与现已发掘出土的文物实物的对照,得出如下三点推测:第一,在公主寺壁画中,画工对于人物饰品的描绘,大体上是遵循当下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佩戴饰品的实际形制进行描绘,而非只为画面设计美观考虑,也并不是完全凭空臆造,罔顾现实。第二,壁画中人物饰品的颜色、质地与现已发掘的明代实物颜色、质地也基本保持一致。可见公主寺壁画中人物饰品的形制描绘确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可以考虑用作当代还原明制饰品的参考依据。第三,不论是壁画中的人物饰品,还是现实出土的明制饰品,都可见对金属的大量使用。可窥见明代中后期冶金工业发达,人们热衷于佩戴有贵金属的饰品,并且工艺已经达到了可以用“造型精巧、制作精良”形容的程度。
事实上,关于壁画中人物饰品材质的猜想,若仅凭借壁画内容是不足为证的。因为壁画是二维的,壁画中单幅画面所呈现的仅是一个平面,我们无法单凭一个平面想象其三维的形态。且壁画是艺术作品,从画师创作绘制粉本,再到其将粉本内容绘制到墙面的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二次创作甚至多次创作的成分,我们也无法仅以画面中的描绘就想当然地对壁画中人物饰品的材质进行定性。但如若将壁画内容与现已发掘的明代饰品出土实物相结合对照,以实物的材质、形制、色彩与壁画中所描绘的神祇人物饰品配饰进行对比,二者便可以互为论据。公主寺壁画中人物的饰品与现已挖掘出土的明代饰品对照,其结论无疑为壁画的断代提供了新的证据。
与此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出壁画绘制所使用的粉本也应该是绘制于明代的粉本,壁画中的人物饰品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公主寺壁画对于明代人物饰品、明代金属工艺发展也具有相当大的研究价值。
注:本文图片由史宏蕾、伊宝采集于公主寺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