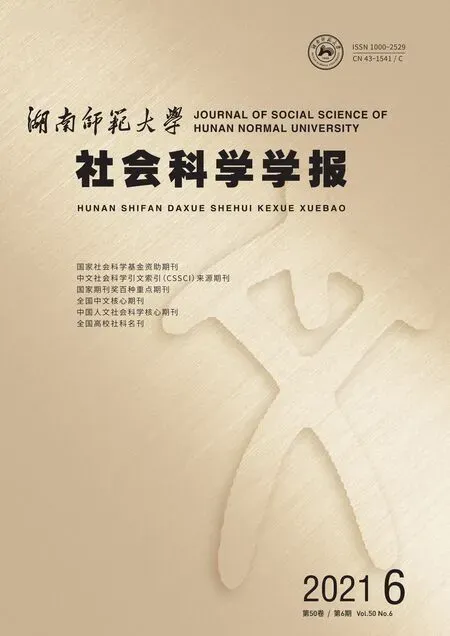“再造地方性”:媒介化理论视角下地方媒体的传播创新
袁星洁,赵 曌
社会学范畴之下,具有区域特性的“地方”,承载着社会与文化的意义,并为居于其中的个体或社群提供体验与实践空间,因而往往关乎“家”的概念。但也有学者直言,在当下这个媒介笼罩一切生活领域的时代,现代人正遭受“无家”之苦[1]。其中缘由,除了物理身体在空间距离上的加速流动之外,更多来自媒介呈现对地方意义的剥离。媒介化研究尤其强调媒介力量对社会、文化系统的这种“介入”和“格式化”。媒介化社会下,“地域消失”的互联网传播以全球逻辑深刻冲击着地方媒体的本土视角;媒介机构集团化、全球化、数字化的加速发展,进一步打破了地方媒体原有的区位特征和传播特色。在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博弈中,地方媒体“再造地方性”的努力将成传播创新的常态。
一、“消失的地方感”:多重流变中的传播语境
随着媒介之于现实生活的深度嵌入,今天我们对地方的理解和判断,越来越依赖于媒介的描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其中隐含着人与族群及其所属地方的联系。长期以来,中国地方媒体无疑是这种“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构建者。尽管我们更愿意强调地方对个体的塑造以及个体对地方的认同,并将这种互动更多归结于媒介的作用,但不争的事实却是,现代媒介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颠覆传统的媒介地理,“地方感”正在消失,人与地方置身于一个多重流变中的传播语境。
(一)边界消弭:交往空间的多元重构
媒介的出现,降低了交往活动中“面对面”的重要程度,并不断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麦克卢汉著名的“地球村”隐喻,揭示了原本依赖地域距离和文化差异建立起来的地理空间(部落),在媒介的作用下变得不再边界分明。经纬织成的空间观被打碎,人依赖媒介技术获得感官的延伸以实现对所能触达空间的拓展。梅罗维茨进而将电子媒介影响下的社会情境概括为“消失的地域”,面对面交流所依赖的地域场景消失,原有的空间隔离不复存在,进而影响人的交往行为,形成新的社会秩序。
在麦、梅二人尚未论及的网络传播时代,这种偏向更加剧烈。数字技术和交互媒介允许物理身体虚拟化,物质空间和精神世界实现深度关联,极度延伸了人的交往场域,即人既置身“在场”的现实时空区域,又处于“在线”的网络虚拟空间。经由媒介沉浸在全球对话当中的人们,前所未有地获得了现实社会和虚拟世界相互交织的复杂交往空间。“边界”不再,“人和事都经历着去距离化(un-distancing)的过程”[2]。原先的物理场所不再如过去那般重要,人类交往活动中的空间感由直接的亲身参与转向间接的媒介体验。
媒介提供的虚拟空间加剧了空间感的碎裂,时间随即开始崩塌,“永久地改变了我们体验和表现空间的方式……从多个视角同时进行观看……以物理边界和时间性的瓦解为标志”[3]。当下,媒介将人们交往活动中的时间体验切割成若干个非线性的、可交错的片段,“媒介时间”开始零碎、无序又无时不在地嵌入人们惯常的社会行动中。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共时状态下在不同平台相互交流和沟通,从而催生出更为复杂多样的时空样态:现实和虚拟的空间相互交织并允许同时共在,跨越时空的人们或真实或虚拟地游走于即时的、碎片化的、自由切换的空间体验中。现代社会景观的快速变化和人员的加速流动,进而加剧了这种时空复杂度,常常出现在“此地”获得“远方”的体验(比如通过社交媒体“共享”好友分享的景观等),以及身在“此时、此地”而心怀“彼时、远方”的延异(比如外出务工人员借由媒介与故乡的沟通等)。媒介使用和媒介消费习惯变迁的背后,实际上是物理身体对地方感的进一步钝化。
(二)身份流变:多重情境下的扮演与认同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人所能亲身经历的空间范围实际上是极其有限的。以往我们所熟知的基于血缘的家庭关系或是彼此熟悉的亲朋关系,以及同一社区的邻里关系等交往模式,更接近费孝通所描述的“熟悉的社会”。在“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交中,主体与有限的地域密切关联。比如,面对面的交往有时甚至会因为物理空间距离带来的方言、习俗等差异而受到阻碍。场景主义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人们在交往活动中的角色扮演实际上遵循场景与行为的匹配,不同场景下对应着不同的角色扮演和与之相应的行为方式。媒介化社会中,时空交错的数字化生存赋予了主体新的存在方式,现实与虚拟的叠加打破了依附于“地缘”的身份稳定性。交往活动的主体可能在同一时间既是现实空间“在场”的物理人,又是依赖媒介得以延伸的“在线”的虚拟人,身份及身份认同表现得更为复杂,呈现出显著的流动形态,“熟人”(家人、同事、亲朋的交流等)——“类熟人”(粉丝群、饭圈应援、直播间内的讨论和互动等)——“陌生人”(弹幕、微博的分享、点赞和评论等)不同身份认知下的交往随着情境不同而共在。当人的主体身份延伸至网络空间,尤其以匿名出现时,便获得重塑身份的契机:现实职场中循规蹈矩的“打工人”,完全有可能是网络游戏世界里叱咤江湖的侠客;真实生活中沉默寡言的人,完全可能在另一个空间里扮演举足轻重的意见领袖……显然,交往空间的流变,带来主体身份扮演的位移,认同困难随之而来。
多重面向的交往行动中,个体本能地需要在不同群体中找到不同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归属感,圈子化成为网络空间的显著特征。具有相似兴趣爱好的人聚集在虚拟社群中,形成“网络趣像群体”[4],从而获得彼此认同的新身份。借由媒介,人与人之间从相隔甚远的异质的“陌生人”发展成为紧密相连的具有强烈归属感的共同体。当然,个体也可能对自己圈子中的关系进行权衡,对不同性质、距离的关系对象采用不同策略进行关系管理与互动[5]。人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惯常采取的“好友分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圈子间的身份识别与认同。由“地缘”到“趣缘”,新的社群在崛起,圈子不断生成,人们依附于媒介所提供的议题聚集,在短时间内凝聚起极强的向心力;但也往往因为议题的结束而解散,人处在不断集合、解散的流动状态中。因而,同一主体总是不间断地被置入不同的圈子,呈现出多重面向的身份特征,更加撕裂人们对所处物理空间的感知。
(三)资本导向:媒介同质化与趋利性加剧
如同商场专柜和主题公园景观的“复刻”一般,消费主义带来的单一性和匀质性侵蚀着地方媒介的本土性。近年来,电视选秀、相亲、真人秀节目的泛滥,社交短视频平台上内容的模仿、复制,同类型网络直播带货的兴起,等等,无一不在推搡着大众媒介走向趋同,资本逻辑在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具有现代性色彩的媒介化,是个体化的、消费者导向的。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在对欧陆媒介的研究中指出,20世纪末,市场化的媒介开始成为社会中的独立机构,“其活动更多地服务自身受众——并常常结合商业市场的逻辑。换句话说,媒介越来越多地以适应个人媒介逻辑和市场的方式组织公众和私人传播”。由此,夏瓦提出了“复魅的媒介”(re-enchanting media)一说,消费社会下经由媒介呈现的商品自身和消费过程被赋予了不可思议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复魅一个没有灵魂的、充满雷同的消费品世界”[6]。
资本席卷之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新闻荒漠”(news desert)蔓延的状况,让社群成为新闻报道的“盲区”,缺乏与之相关的公共事务报道。而这些地区或社群,往往是“最贫穷的、受教育程度最低、最容易被孤立的”[7]。从国内的实践来看,中央级媒体在地方或是地方媒体集团在基层地区设立的驻地机构,往往既是“记者站”也是“分公司”,工作中甚至出现市场经营任务逾越新闻内容生产职能的状况。正如哈贝马斯所担忧的那样,媒介的商业特性导致公众沉迷于消费媒介产品,而非行使权利。对媒介本身而言,资本导向下,当地方内容的生产与拥有更大受众市场的国际、全国内容生产相互掣肘之时,狭小的“地方”往往屈从于更加普适的“全球”。“地方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会被全球化过程不断消解,乃至形成同质化空间”[8]。
另一层面的撕裂来自技术偏见。占据技术优势地位的商业互联网信息平台不断向地方下沉,成为区域内的主要信息供给方之一,蚕食地方媒介的生存空间。随着智媒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所谓“技术中立”的外衣下实际上藏着深刻的算法偏见。批判地来看,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标榜智能算法、精准推送的现代媒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地方信息的偏见性与选择性。信息茧房的隔离之下,区域间“数字鸿沟”不断加大,被技术“无视”的地方难逃再度边缘化。
一直以来,作为“喉舌”的我国地方媒体,担负着沟通中央与地方,宣传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政治任务,其社会效益应始终置于首位。因此,正确引导舆论并兼顾市场规律的二元发展,既是地方媒体始终抱守的定力,又是其必须探索的路径。
二、“媒介地方”:一种新的连接
“全球景观”对地方的冲击无疑是全面而深刻的,地方媒体本土性的消解亦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兼有自然与人文双重意义的“地方”的彻底消亡。地方所提供的归属感和亲近性,对于个人的体验和认同仍是不可或缺的,即便是最“无边界”的互联网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地方的影响。地方媒体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正以其独特的媒介逻辑重塑着地方的呈现与表达,并形塑出地方中人们新的互动形态、新的社群关系以及新的行为方式,搭建起人与地方新的连接。
(一)媒介化:重新理解地方性与地方感

图1 地方性和地方感经由媒介形成互构的作用机制
对于地方的理解,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在《地方与政治》一书中提出了“地方感”的维度。地方感强调主观体验,是个体或社群对地方的认知、理解和情感依附,并由此赋予地方象征性意义。建立地方感的依据是地方性,地方性强调地方本身所带有的客观属性,除天然形成的地形、气候、作物等“风土”特征之外,也包括文化物产、历史事件、地标建筑、特殊人物等“人情”内容。处于地方中的人,通过对地方文化的体验形成归属感;而地方文化的形成和演进,总是与人们对地方的理解和阐释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段义孚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们认为,“意义必须来自亲切的经验”[9],只有感知和经验过后,“空间”才会变成“地方”,所谓的“地方感”“地方性”才有讨论的前提和意义。媒介化社会的当下,段义孚等所强调的亲切感知,必然更多由媒介接替完成,并形成新的“人—地”互动作用机制(如图1)。
人类的传播活动历来就带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不同地方人的交往带着不同地理环境的印痕。从媒介的视角来看,地方的传播者试图通过所生产的文本来塑造某种类型的受众,从而使之打上印痕以成为“地方的人”。由此,地方经由媒介表现出对人的生产和塑造。因而,地方传播媒介之上所承载的内容,不仅是传播者面貌和人格的反映,也是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映射[10]。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地方以自己的特性(地方性),潜在地通过媒介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地方文化并使之符号化。成为呈现在媒介之上的媒介内容,营造出“媒介地方”,进而影响当地人的性格特征、生活习俗、行为习惯等。人由此产生地方想象、地方认同、地方依恋等一系列主观体验,地方感得以建立。
由“风土”和“人情”构成的地方性往往是在地方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自然的、先验的、客观的特征,但并非一成不变,其意义由处在地方中的人来赋予、认知、接受、传递、强化,以及再生产。朱竑认为,地方性在地方感认同过程中产生新内涵,形塑其意义;地方感又受到地方性的主导,在地方性生产中不断实现。地方性和地方感在各自循环过程中不断重构与再生产[11]。媒介化社会中,地方性的再生产过程越来越屈从于媒介逻辑和传播形态,经由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地方媒体,创造出人与地方极富深意的连接。
(二)个体化:对抗中的连接
数字化生存使得跨越时空的人变得容易接近,个体在技术赋权下获得媒介话语权,媒介化社会呈现出“万众皆媒”的特征。但对于肩负地方感塑造的地方媒体而言,“人人都有麦克风”无疑意味着权力的分散。基于网络媒介的交互性,个体意识得以凸显,极易陷于缺乏集体认同、抛离地方的状态,形成与地方的对抗。对此,梅罗维茨甚至在《消失的地域》中提出了“情境合并的‘无地方感’(no sense of place)”[12]。
但实际上,在互联网空间中,与其说是新的媒介样式粗暴地抹掉了地方感,不如说其催生了更加多元化的地方感,地方叙事被媒介置于更宽广、多维的交往空间中。依照夏瓦的观点,媒介化刺激了基于弱社会联系的软性个人主义(soft individualism)的发展。强社会联系对社会凝聚至关重要,但弱社会联系却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流,为社会个体提供了更丰富和及时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因而,新的地方感,往往不再像大众传播时代那样服从于强有力的组织形态或密切的家庭单位,而在网络媒介较弱的社会联系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交化和个人化。过去,大众媒介向社会界定群体传输内容;如今,大众媒介不得不依据人媒交互中多元的个体化需求开展信息生产,大众传媒越来越多的分众化实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媒介所呈现的图像、场景、经验,形成远远超越物理空间但又与物理空间关系密切且相互补充的“媒介地方”。人们经由媒介所提供的参与过程与认同方式,可以形成全新的、超越时空的地方体验。随着地方媒体将这些个体化的地方感积极联系在一起,弱连接在社群、圈子中得以强化,个体化的地方感成为地方性再生产和更新的重要部分。在互联网交往空间中,个体化将是冲破全球化普遍性、同一性桎梏的关键力量。扮演人与地方连接节点的地方媒介,对于崇尚个性的群体之间在弱社会联系下实现地方整合显然十分重要。
(三)标签化:个人与地方的互构
个体化表现为媒介对于个体的追逐。但与此同时,个体也在找寻媒介。因为,媒介提供了一个社会个体展示、分享、行动以及由此获得认同乃至加入“圈子”的舞台。这种来自他者的承认恰恰是社交媒体时代个体在交往活动中立足的根本。社会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总结了现代社会中“承认”的三种形式并进行了区分:爱的承认发生于私人和亲密领域;尊重的承认在公共领域;而尊重所获的承认则在社会领域中。个体在媒介化社会中的交往活动,承认更多来自后两者,并始终依赖媒介实现。交往实践中,个体越来越多地需要遵照特定的媒介逻辑创设其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样貌,以获得外部世界的认知与规范。于是,媒介推动了私人与公共领域的混合。当私人个体通过社交平台对外发布意见时,其同时也是公共的、社会的个体,个体所属的那个“地方”,作为其社会身份的标签变得重要起来。
这一点,由“土味文化”“小镇青年”等近来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的崛起便可见一斑。来自草根、民间的表达,往往与地方的方言、装扮、景观、风俗、物产等紧密相关,并凭借鲜明独特的地方特征在同精英话语、全球话语的对抗中获得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传—受”双方的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接近或是情感依附的地方作为标签。例如网络讨论中经常出现的“今夜我们都是××(某个地方)人”“××(某个地方)发来贺电”一类的句式,既是个体对地方的认同,也是个体借由地方获得身份标签并寻求认同的行动。社交媒体“同城”“附近的人”“位置定位”等功能设计,以及越来越多位置媒介应用的出现,同样展示了个体的地方依赖和地方空间的回归。当“个体的地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并引发广泛的注意和认同时,往往形成重构地方的重要力量。网红人物作为新的“地标”引发崇拜、模仿,塑造出全新的地方景观和体验,甚至开始建构新的地方文化。
三、“再造地方性”:地方媒体传播创新的向度
吉登斯在指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的同时认为,全球化既有可能削弱本土化的某些方面,但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1]。在这种作用下,媒介的地方性会遭受一定程度的削弱,但仍有可能通过努力保持其独特性。这为地方媒体“再造地方性”提供了合理性和必要性。作为大众文化和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地方媒体有责任遵从媒介逻辑,通过传播创新来塑造地方感、重构地方性。
(一)重启连接:作为渠道(conduits)的地方媒体
作为渠道的地方媒体,关注地方信息如何传输。媒介为传播而生,并先天具有再现或表征社会现状的功能,以此同信息需求者产生连接,形成平等、互通的对话与交流。但长期以来的事实却是,传统大众媒介组织化的单向传播剥夺了受者一方的话语权,以致出现“沉默的大多数”。新媒体时代,这一成规被彻底打破,单向度的大众传播开始被摒弃,地方媒体与地方受众之间的连接由此出现不同程度的断裂。
史安斌对“新闻荒漠”的研究极具启示意义。他发现,即便是在拥有逾千家媒体机构的纽约市,当地居民关心的诸多议题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讨论[13]。而关于治理“新闻荒漠”、重振地方或社区媒体以消弭信息鸿沟和意见裂痕的呼吁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水涨船高[14]。疫情之下,民众的“信息饥渴”和“媒介依赖”与日俱增。公共卫生报道成为热门内容,以往被大小媒体遗忘的市政医疗系统一夜之间成为报道焦点[15]。不少地方媒体在疫情期间凭借提供当地的独家专业报道吸引了大量的订户和可观的流量导入。反观国内,区域性的疫情数据、当地防控政策、社区发热门诊设置、相关服务信息等关键信息同样是地方受众信息需求的缺口,部分地方媒体凭借中央媒体无法触及的位置优势成为回应公众信息需求的渠道,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不少新媒体账号、客户端也由此在短时间内赢得可观的用户增长和流量分发。
疫情期间的经验表明,区域性、服务性和实用性的信息沟通对于特定地方的受众来说依旧重要,地方媒体无疑是地方性传达的主要渠道。当然,疫情期间尤其是疫情暴发初期,信息供需处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媒介关键信息稀缺激化了公众需求。在信息供需平衡甚至供大于求的日常状态下,供需间的信息对称成为关键。作为信息沟通渠道的地方媒体如何回归区域信息需求下的传播内涵,使人与地方的交流“回到”更真实的对话状态?依随派迪·斯坎内尔(Paddy Scannell)的观点,地方媒体可以建立这样一种交流结构,即“把普遍存在的针对任何人的结构,当作是为自己的结构”(for-anyone-as-someone structures)[16]。地方媒体既面向“任何人”(如同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介面向大众),又面向“特定的人”(如同人际传播中个体的人),构建一种介于大众媒介和人际传播间的“对话”形式。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话模式下,推动“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差异弥合。当下地方媒体实践中,从“机构”到“平台”的转向已然成为趋势,推动地方媒体基于传统的PGC模式,整合新媒体平台的MGC、UGC等多元生产模式,形成参与、沟通的对话渠道,进而实现“订制化”的内容生产模式以培育黏性用户,这才是地方媒体困境求生的不二法门。
(二)重造画像:作为语言(languages)的地方媒体
作为语言的地方媒体,关注地方表征的叙事。梅罗维茨显然注意到了各种媒介间不同的特点及其对内容的影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媒介生产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传统;不同媒介形态则有着各自的媒介语法,对应着不同的内容格式、内容规范以及隐性意义等。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首先在文本上塑造出异于以往的“媒介地方”符号,碎片化、社交性、伴随性成为地方叙事的特征,凸显个体价值的叙事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亚文化特质。比如,社交短视频平台上的人们,对西安的认知,首先接入的恐怕是配上民歌的摔碗酒而非六朝古都的历史;重庆的标签则更多是穿楼轻轨、洪崖洞夜景,而不是经常见诸地方主流媒体之上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城市……社交媒体平台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体的媒介叙事,于当地人而言是熟悉的日常生活体验,对外地人来说则是“趣缘”经由媒介得到回应从而获得自身认同的地方体验。
作为语言的媒介,以符号建构空间,形成各具特质的媒介审美,实际上是媒介化研究者所考察的“媒介逻辑”中的一个部分。从媒介生产者的视角来看,不同的媒介语法和叙事“画像”出新的地方表征;反观受众视角,多媒体形态之间不同的媒介语言直接影响着受众对地方的感知习惯和情绪反应。以交互为特征的新媒体,创造出受众能够参与其中的媒介现实,跨越时空产生身临其境的在场感,甚至与沉浸其中的其他身体角色建立想象的交往关系,成为同一地方的“成员”。在媒介的塑造之下,这种“媒介化的身体”成为地方体验的主体,客观世界里自在的物理身体开始受到媒介语言的规训,按照媒介所提供的参与途径和感知方式来获取地方信息,产生新的地方感,进而触发现实空间中的身体行动,“打卡”“刷屏”“拍同款”等互联网媒介事件开始涌现。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河南硬核防控在社交短视频平台的呈现,吸引了广大当地网友的积极“扮演”、创作和分享,引发强烈的地方认同并成功塑造了新的地方形象。正是这些日常的语言体系,经由媒介建构,使地方实践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提供了再造地方性的鲜活材料。正如扬·阿斯曼(Jan Assmann)所言,“在这种互动中循环着的,是一种经过共同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Kuitureller Sinn),继而制造出一个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和‘世界观’”[17]。
如前所述,这种地方的象征意义和世界观并不都意味着宏大叙事,地方认同并不仅仅通过宏大的主旋律的语言符号来创造和维持(比如过去我国地方新闻媒体更倾向于以官方话语发布政治属性鲜明的城市宣传片)。媒介化力量驱使下,地方在“我拍故我在”的自我呈现与“我打卡故地方在”的媒介参与中被重新画像,意味着地方性正按照大众流行文化的语言而形式化。同样作为媒介化对象的地方媒体,需要依据特定的媒介类型调整、塑造地方表征的呈现;通过操控语言调节不同语境下受众对地方的感知方式,来弥合“两个舆论场”之间的话语体系差异;以符合媒介使用习惯的叙事,创造能够让受众切身卷入其中的媒介事件,使其在类似于现实空间人际交往的媒介体验中实现与地方的连接和对地方的归属。
(三)重建场景:作为环境(environments)的地方媒体
作为环境的地方媒体,关注人与地方空间的社会性连接。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认为,互联网是媒介之媒介,起着“通过网页进入其他媒介”的连接作用,社交媒体时代,“连接”无处不在。当个体通过媒介获取地方信息、接入媒介所营造的地方情境时,便将现实生活空间中的惯习和行为代入了与“媒介地方”的互动中,并接受媒介的形塑。因而,在地方感的塑造和地方性的重构中,地方媒体是媒介地方(地方想象)的重要生产者,这一点甚至超越了其作为机构信息传递者的角色。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媒介推动着新兴地理的出现,除了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之外,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也在发挥作用,即媒介环境下诸如社区广播、当地报纸、社区网站、家庭博客等形式更加“内向”(introverted)的传播不断涌现,因而“我们仍时常会经历集体的‘我们’复苏的媒介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扮演着象征性黏合剂的角色,使独立的社会个体结合成为紧密的社会整体,创造出“社区共同体”[18]。网络社群的行动特征表明,虚拟世界中的地方体验,必然影响现实社会中的地方实践。媒介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社会交往行动愈加深度地内嵌于媒介逻辑当中,人与地方的连接已然无法脱离对媒介的依赖。这样的依赖,随着社交媒体的嵌入越来越呈现出随时随地的生活化和伴随性,公众的媒介消费习惯变为“随时在线”“随地发生”“随处接入”。
因而,在罗伯特·斯考伯(Robert Scoble)和谢尔·伊斯雷尔(Scher Isriel)所描摹的那个“人媒共生”的“场景时代”下,行业边界模糊,使得媒介的连接属性进一步凸显。更加偏向于基础设施型媒介的地方媒体,需要成为区域内的“媒体+”综合服务平台,既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又提供与现实生活场景接驳的增值服务入口。当前,不少地方媒体正通过加载政务服务、生活缴费、区域电商、社区配送等服务模块延伸其在当地的服务功能,通过满足地方用户对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使用来增强自身与本地用户的黏性。万物互联的技术前景为地方媒体的在地化服务描绘了新的可能性,新的技术条件下,地方媒体抢抓物联网人机交互终端在物理空间的布局,有望凭借其在空间距离上的“接近”获得新的用户积累渠道,从而搭建起人与地方空间的连接网络。不难想见,未来,大量的媒介用户数据和来自地方社会机构的公共服务数据汇聚到地方媒体平台之上,成为极具价值的地方性数据库。因此,若以地方大数据平台或区域综合智慧平台的定位来观照地方媒体,实际上它已经不再是传统认知里单一的媒介机构,而是一个数字化的治理空间,将地方中的个体、机构和系统联结为一个有机运作的网络,支撑着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场景时代依旧是“即将到来”,但对于场景的理解却深远地预见了媒介化社会未来的样态。作为环境的地方媒体,未来既是人们“接入”地方的节点,也将成为地方中人们的媒介化生活世界。
媒介化是一个现代性的过程,新的媒介逻辑解构了个体对地方的认同与共在,塑造了新的地方感,并推动着地方性的再生产。作为渠道的地方媒体,关注传播内涵的回归,实现区域关键信息的畅通对话;作为语言的地方媒体,关注地方叙事的表征,实现对人们的“媒介地方”感知塑形;作为环境的地方媒体,关注“人—媒—地方”的连接,实现媒体融合背景下地方媒体多维功能的重新定义。“地方”仍在,地方媒体传播创新的向度与价值,在于将传统意义上的“地方”与现代语境下“散落全球的人”连接起来,真正构建具备全媒体传播功能的新型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