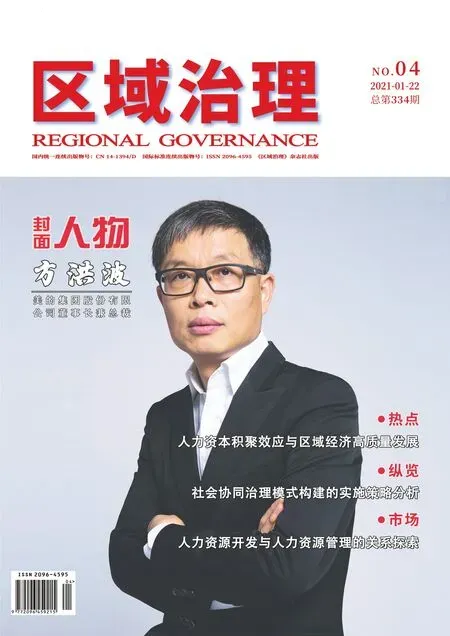分析预约合同违约责任
广东财经大学 何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确立了我国预约合同制度的基本结构。
目前,《民法典》合同编第495条对上述司法解释条文进行了吸收改造,将预约合同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由原来的买卖预约扩大至不限于买卖上的预约,并对预约合同作出了更为清晰的表述,但同时可以发现其并未规定违反预约合同要承担的违约责任形式。面对实务中很多预约合同纠纷,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违反预约合同的责任承担方式。本文在查阅大量文献并结合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分析探讨在《民法典》现有制度下的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以期为进一步明确违约责任形式提供参考。
一、关于预约合同的概述
预约合同指的是双方当事人所订立的、约定在之后一定时间内两方签署本约合同的一种合同形式。预约合同的内涵包括:首先,预约合同给双方施加了缔结本约的义务;[1]其次,双方被预约合同所约束,不得订立与本约具有相同属性的任何其他合同。预约合同的组成要素包含了明确订立本约合同的承诺和明确的预约内容。[2]
依条文规定,如果当事人违反预约合同,则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然而不管是现在的《民法典》还是之前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均未回答实践中存有较大争论的两个问题——当出现违反预约合同的情形时,守约方主张继续履行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当主张解除预约合同时,守约方能否要求违约方赔偿本约履行利益?下文将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两大问题展开讨论。
二、预约合同违约责任的实践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继续履行
两方签订预约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签署本约。因此,如果一方违约,大多数守约方希望违约方继续履行预约合同,直到本约签署。可以说,继续履行这一方式能不能得到适用,是预约合同违约责任存在的最大分歧。
大多数法院认为这一方式干预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不支持继续履行的适用,如仲崇清案[3]、宝莲城公司案[4]等;但许多判决则采取了相反的判决,如在郭志坚案[5]、山东菱重机电设备公司案[6]中,法院认为预约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本约。如果不能保证本约的签署,则预订合同制度将失去其价值,并可能带来额外的道德风险。
(二)损害赔偿
司法判决中关于损害赔偿的主要争议点在于守约方能否要求违约方赔偿本约履行利益。如在吕青案中,法院认为预约和本约有明显差别,预约合同违约的损害赔偿范围不能完全等同于本约的赔偿,故赔偿范围仅包括信赖利益损失,而不包括本约履行利益;[7]但在陈荣根案中法院的观点截然相反,为了合理保护守约方的利益,应让其达到犹如合同全部履行的状态。[8]
三、预约合同违约责任的认定适用
由于缺少制度供给,导致围绕上述关于预约合同纠纷的争议一直存在,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案件比比皆是。因此,对于违反预约合同,建立明确的救济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若预约合同约定的具体义务是磋商,一方拒绝磋商即可成立违约;若约定的具体义务是签订本约,一方拒绝签署本约才成立违约。所以关于违反合同的一般责任规则并不能直接适用于预约合同,需要从预约合同的效力出发,区分类型加以分析。
(一)继续履行
能否将继续履行看作违反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之一,在理论界极富争议性,有否定论、肯定论和内容决定论之分。第一,否定论。这一学说认为预约合同的守约方不能主张继续履行,只能要求违约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实务界大多采纳这一学说,[9]其法理基础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人身不可强制。实际上,这种观点有待商榷。这一方式并没有造成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违背,若把继续履行排除在违约责任外,则会大大降低预约合同制度的功能价值,这与建立预约合同的目的背道而驰。第二,肯定论。这一学说认可继续履行的适用,背后的支撑理论是意思自治、期待可能性和信赖利益保护理论。然而,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其应用于一切预约合同,很有可能会造成双方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平衡。[10]第三,内容决定论。这一观点认为违约方能否承担继续履行责任要分情况讨论。根据《合同法》第12条合同主要条款,一些学者把预约划分为简单预约、典型预约以及完整预约。前两种类型不能适用继续履行,最后一类则能够采用。[11]
笔者认为,继续履行是否可以成为违反预约合同的一种责任承担形式,关键是看适用于什么情况下:(1)当在预约合同中双方约定了必要条款并达成最终合意时,此时预约合同具备强制缔约效力,可以采用继续履行规则。原因是:首先,继续履行的功能在于维持合同的约束力,契约严守原则是其价值基础,所以,其与这类合同的订立目的非常吻合;其次,在这一类预约合同中,当事人之间具有较强的信赖度,反映了他们之间订立本约合同的合意,所以守约方可以采取强制缔结本约的方式进行救济;再次,依合同法一体适用的要求,一般而言,预约和本约合同须受到合同法中违约责任制度的统一调整。但是,应当指出的是,预约合同中的继续履行责任也同样要受《民法典》第580条的限制。(2)当两方签订预约合同时并没有达成完全的合意,约定的具体内容仅为继续磋商时,此时的预约合同仅具备善意磋商效力,则不宜适用继续履行这一违约责任形式。因为针对这类合同而言,由于其与上述那类具有强制缔约效力的预约合同相比,双方之间的信任度较低,因此,违反预约合同不应具有强制缔结本约合同的法律后果,不应把继续履行作为其违约责任形式之一。
(二)损害赔偿
应将什么利益用作计算预约合同违约损害赔偿的基础?是签署本约合同的信赖利益,还是含本约合同的履行利益在内,学界对此观点不一致,主要的学说有“信赖利益论”“履行利益论”以及“内容决定论”。第一,信赖利益论。这一观点认为损失赔偿额只包含直接损失,不含机会利益的损失。在机会利益损失得以赔付的情形下,信赖利益的范围已经无限接近履行利益。[12]第二,履行利益论。这一观点认为应按本约的履行利益确定赔偿数额。第三,内容决定论。这一学说认为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须根据不同阶段区别认定,并非完全赔偿本约合同的履行利益,和信赖利益也有一定的差异,但对于损失赔偿数额,可以依据完全赔偿原则进行计算。[13]
笔者认为,同样有必要从预约合同的效力开始讨论:(1)如果双方约定好了合同的必要条款并在预约合同中达成了将来签署本约的明确合意,在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原则上应该采用履行利益论。主要原因是这类合同的效果让双方有强制缔约的义务,双方的信赖度很高。其保护的对象超越狭义信赖利益的范围,逐渐接近履行利益。所以,由于这类合同成熟度高,其损害赔偿金额可参照本约合同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加以确定。[14]支持“信赖利益论”的学者反对“履行利益论”的主要观点在于,若其损害赔偿范围扩大到履行利益,那此时预约和本约合同又有何不一样呢?此时讨论预约合同违约责任的意义何在?这种观点似乎是合理的,但实则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首先,根据本约合同的损害赔偿制度计算违反这类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是建立在我国合同法上对于信赖利益和履行利益的二元区分较完善的基础上的,但绝非把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与本约的违约责任划等号;其次,与本约合同的损害赔偿不同,预约合同在计算损害赔偿金额时虽然可以参照本约的履行利益,但是赔偿范围不应超过本约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2)如果双方仅约定继续磋商,双方对于是否订立本约处于不明确的状态,此时信赖度较低,所以其保护的对象实则为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以信赖利益论为限;此外,可将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作为计算损害赔偿范围的参照。[15]但不意味着将此处的违约责任等同于缔约过失责任,因为两者存在许多差异,诸如归责原则、具体的责任形式以及举证责任不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