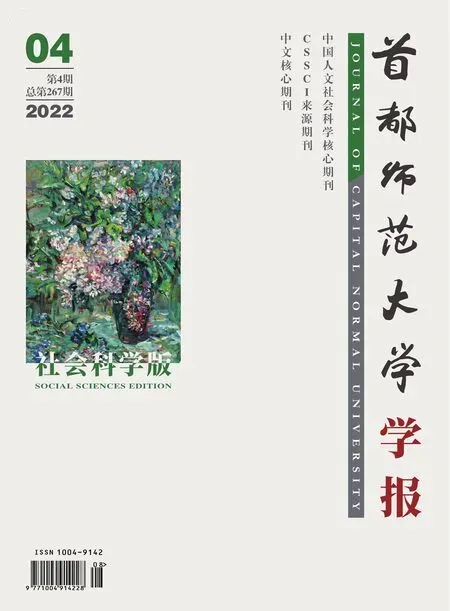二战中的巴尔干:历史与启示
梁占军
巴尔干位于欧洲的东南部,是古代东西方贸易通道的欧亚交会点,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当地民族长期处于帝国专制统治之下,备受压迫和奴役,民族矛盾错综复杂。19世纪末以来,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日渐兴起,各民族独立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正式开启。20世纪的战争,如一战、二战甚至冷战都在巴尔干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中,二战的冲击和影响尤为巨大和深远。客观地讲,战时巴尔干各国不同的政治选择及其历史结局既凸显了这些国家间难解的民族矛盾,也暴露了它们身处大国强权阴影下的无奈,更揭示了其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火药桶”的现实根源,堪称是为巴尔干奏响的一曲现实主义的悲歌。
一、二战前巴尔干的国际格局与各国的矛盾诉求
二战前巴尔干的国际格局是一战后重建的产物。当时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国家有五个,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南斯拉夫。后者即1918年12月1日建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这是历史上巴尔干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南斯拉夫人统一的国家,也是巴尔干地区最大的多民族国家。南斯拉夫的建立标志着一战前巴尔干民族独立建国的进程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然而,一战后巴尔干政治格局的重塑并未消除这一地区积累已久的种族、宗教、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再加上一战后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所引发的新矛盾,这使得巴尔干各国普遍缺乏稳定的政治取向,极易受到大国或外部势力的左右,最终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比如,两次大战之间南斯拉夫王国和罗马尼亚曾联合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小协约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也曾召开巴尔干所有国家参加的巴尔干会议,试图加强巴尔干的团结,但都最终无果。再如一战期间德国的盟友保加利亚,战后作为战败国丧失了不少领土:南多布罗加被割给了罗马尼亚,西色雷斯则划给了希腊。因此保加利亚战后一直是修约的支持者,始终坚持要收回自己的领土。这些涉及领土主权的利益诉求必然会导致它与巴尔干各国的和解无法实现。保加利亚驻英公使莫姆奇洛夫曾坦言:巴尔干各国之间的“互相厌恶和互不信任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它们决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利益纠葛将直接影响战时巴尔干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同盟抉择。
事实上,二战爆发后,巴尔干各国从各自利益出发,重新分化组合,最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投入了德国的怀抱,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则坚持抵抗法西斯的占领,巴尔干民族国家陷入分裂。
二、战争期间巴尔干各国的不同选择
长期以来,欧洲学者普遍把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作为二战的起点,但事实上,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战火最早是在巴尔干点燃的:1939年4月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短短几天内实现全面占领,使之成为巴尔干最早遭受二战荼毒的国家。此后,面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巴尔干各国在合作还是抵抗之间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其战争经历也随之大不相同。从立场上看,战时巴尔干国家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被法西斯全面占领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半岛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历史上长期受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压制,直到1912年才独立建国。一战后意大利将阿尔巴尼亚视为自己侵入巴尔干的跳板,因而一直在谋求对后者的控制权。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借欧洲局势紧张之际,出兵阿尔巴尼亚,仅用5天便闪电般地完成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征服。随后在阿尔巴尼亚召开制宪议会,建立傀儡政府,奉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为国王。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第一个遭到法西斯国家侵占的国家,在战争中被法西斯裹胁,直到1943年意大利投降。
第二类是坚持抵抗斗争的国家,如希腊和南斯拉夫。希腊是意大利侵吞巴尔干的另一个目标。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意大利野心膨胀,于10月28日大举进攻希腊,开辟了巴尔干战场。希腊军民在英国的支持下奋起抵抗,使得意军进展迟缓,不得不向德国求援。然而德国在巴尔干的扩张野心除希腊外,还包括地位更重要的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半岛的核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战后,南斯拉夫作为巴尔干多民族统一的大国一直与法国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凡尔赛体系。二战爆发前,德国法西斯一直在努力拉拢南斯拉夫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1940年法国败降后,南斯拉夫政府一度转变态度,于1941年3月25日宣布加入轴心国。但不料此举引发国内政治反弹。新继位的国王彼得二世撕毁了同法西斯签订的条约,并在4月6日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当天,蓄谋已久的希特勒借机宣战,伙同其盟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大举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短时间内就占领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全境。
面对法西斯的入侵,南斯拉夫内部出现分裂。4月14日,正当南斯拉夫军队还在奋勇抗击外敌之际,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即宣布建立“克罗地亚独立国”。“乌斯塔沙”是南斯拉夫内部不满塞尔维亚人的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意大利的支持下建立的法西斯组织,他们一直希望借外力实现克罗地亚族的独立。乌斯塔沙伪政权建立后,针对塞尔维亚人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种族清洗。截止到1945年南斯拉夫解放,短短几年间,受害致死的人难以计数。据估计,至少有20万人遇难,甚至可能多达80万。“乌斯塔莎”在二战期间的暴行至今仍是阻碍巴尔干各民族和解的难题之一。
不过,整个二战期间,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抵抗一直没有停止: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在斗争中不断扩充实力,1945年3月,南斯拉夫成立了以铁托为首的民主联邦政府,国家恢复独立。而希腊在政府流亡海外后,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直坚持斗争,直到1944年德军撤离。
第三类是法西斯的帮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加入法西斯阵营的原因并不一样。一战后的保加利亚一直把收复失地作为第一目标,因此同巴尔干各国的关系并不融洽,相反与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往来。希特勒上台后着意打击拆散小协约国,支持保加利亚收复失地的主张,进一步赢得了保加利亚的信任。二战初期德国取得的“业绩”激发了保加利亚复仇的欲望:1940年11月保加利亚国王访问德国寻求合作;1941年2月保加利亚允诺为过境的德军提供粮食和运输工具,并达成进攻希腊的秘密协议;1941年3月1日,保加利亚宣布加入轴心国,4月配合德国出兵希腊,并从此登上德国战车。
与保加利亚的情况不同,罗马尼亚作为一战的战胜国,起初一直追随法国维护既得利益,包括它获得的保加利亚的部分领土以及和苏联存在争议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但1940年6月法国的意外败降,打破了罗马尼亚的最后希望。特别是当苏联在1940年6月26日晚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罗马尼亚索取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时,罗马尼亚不得不被迫让步:7月1日,苏军即完成了对上述两地的占领。此事迫使罗马尼亚决定投入纳粹德国的怀抱:1940年7月,罗马尼亚派团访问柏林,在对德国效忠的同时还主动表示归还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失地,以此作为加入轴心国的见面礼。1940年11月23日,罗马尼亚正式加入轴心国。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罗马尼亚的军队参与了进攻。
三、战后巴尔干各国的不同结局和启示
不同的选择导致的是不同的结局。1944年秋,苏联的战略反攻彻底改变了巴尔干的形势:1944年9月7日保加利亚调转枪口对德宣战;9月12日罗马尼亚与苏联停战;12月德国从巴尔干撤军。与此同时,英法美三大国开始谋划战后的世界秩序,包括巴尔干。10月9日,英国首相丘吉尔飞抵莫斯科就巴尔干问题与斯大林达成了协议,即著名的“巴尔干百分比”:苏联在罗马尼亚,英美在希腊各占90%的主导权;苏联和英国在南斯拉夫各占50%的主导权;苏联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占80%的主导权,美英占20%。“巴尔干百分比”实际上划分了大国在战后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最终确定了战后巴尔干国际格局及各国的未来走向。这标志着巴尔干各国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要淹没在大国的阴影中。事实上,二战后期,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在苏联的帮助下,相继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
而根据巴尔干百分比,英美占90%主导权的希腊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1944年末德军撤走后,希腊流亡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回国,并展开对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的大清洗,由此导致希腊内战爆发。期间英美给予了希腊政府大量的援助,内战斗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10月,最终以希腊共产党的失败结束。希腊由此进入资本主义阵营。此后,巴尔干各国将步入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历程。
纵观巴尔干各国的二战经历,我们不难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巴尔干各国历史演进的深刻影响。首先,巴尔干独特的战略地位使其无法摆脱大国的关注和争夺,这在帝国时期如此,大国纷争时期亦是。其次,处在民族国家建构初期的巴尔干本地民族自身的分散和弱小,使之很难摆脱大国的控制和影响,甚至部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还抱有借外力建国的梦想,这些局限使得它们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很难做到一致对外,往往被大国分化利用。最后,巴尔干各国独立建国初期各自胸怀远大抱负,在帝国遗产争夺期间各自追求本民族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武力交恶,导致各民族间的积怨很深。这不仅使其发展进程受到阻碍,并且无疑会为大国的干预提供机会。二战爆发后,面对法西斯的侵略,巴尔干固有的矛盾集中释放,各国根据自身的利益考量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加入了不同的敌对阵营,甚至在内部借机大搞民族复仇,酿成了新的种族清洗的悲剧就是明证。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冲击了巴尔干各民族国家独立建国的进程,它不仅打破了一战后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平衡,而且使巴尔干极端民族主义获得了一个变异发酵的特殊机遇。而二战后无情的事实表明,无论是战前法德意与巴尔干各国结盟的角力,还是战时英美苏与德意在巴尔干的对抗,特别是战后对巴尔干百分比的切割所造成的巴尔干的持续分裂,大国博弈与强权政治的影子在巴尔干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以史为鉴,可以知更替。处大国夹缝中的巴尔干各国的二战经历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现实世界。它们战时的政治选择和客观的历史后果时刻提醒着人们,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实力弱小的国家如何审时度势,在兼顾利益和道义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道路,永远是值得执政者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