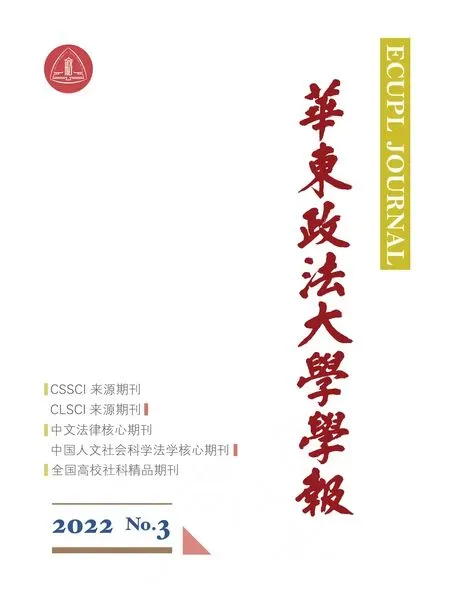创新规制的时间逻辑
王首杰
世界是变化的,创新无处不在。熊彼特认为,创造性毁灭是经济内部的突变和革命,是一个不断破坏旧结构与建立新结构的过程。〔1〕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郭武军、吕阳译,华夏出版社2015 年版,第98 页。创新推动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破除旧制度弊端的良药。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要点》,来源:httрs://baijiahao.baidu.com/s?id=1681946106941043182&wfr=sрider&for=рc,2021 年11 月22 日访问。创新离不开规制的保驾护航,在破坏性重建的过程中,会出现大量偏离既有规制轨道的问题点,需规制者适时灵活应对。在这个过程中,规制者不但要决定做什么,还要决定什么时候做。在创新规制涉及的众多“变量”因素中,内容要素与时间要素的结合构成其中的核心框架,妥当规制须兼具内容和时机的适当。相较于规制内容的广泛研究,〔3〕国外将创新和规制结合的研究成果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某一个部门法和创新的关系,例如,Richard 研究了创新与行政法的关系。See Richard В. Stewart, “Regulation, Innov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A Conceрtual Framework”, 69 California Law Review 1256-1377 (1981). 第二类,从规制主体的视角出发,研究不同规制主体对创新的规制方式和规制作用。例如,Вernstein从案例展开,描述裁判对创新的影响。See Gaia Вernstein, “In the Shadow of Innovation”, 31Cardozo Law Review, 2257-2312 (2009-2010). 第三类,从规制效果的角度出发,评价某一国家或行业法律规制创新的效果,例如,Рelkmans 评价了欧洲的规制对创新的作用。See Jacques Рelkmans & Andrea Renda, “Does EU Regulation Hinder or Stimulate Innovation? ”(November 19, 2014), httрs://ssrn.com/abstract=2528409, accessed June 20, 2017. 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从概观视角探讨信息革命后的社会整体变化。例如,马长山提出,现代社会的创新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推动制度变革,参见马长山:《智慧社会建设中的“众创”式制度变革——基于“网约车”合法化进程的法理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4 期,第75-97 页。第二类,研究创新与某一个部门法的关系。例如,王先林研究了反垄断法与创新的关系,参见王先林:《反垄断法与创新发展——兼论反垄断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协调发展》,载《法学》2016 年第12 期,第50-57 页。第三类,研究具体某一项创新的法律规制。例如,共享经济与粉丝经济,参见蒋大兴、王首杰:《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9 期,第141-162 页;王首杰:《粉丝经济的法律规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 期,第93-105 页。鲜有研究关注规制时间。而创新规制时间和内容同等重要,即使是“对”的规制内容,一旦实施的时间错误,也会偏离规制目标,引发不利后果。规制者应力求将灵活规制内容的实施控制在“刚刚好”的时间段,既不过分超前也不过于滞后。规制时机的抉择不仅关乎经济层面的“成本—收益”分析,还是一个重要的法学命题。变动中的创新所引发的规制问题点大多超越常规,每个规制主体都需在法定权限范围内灵活裁量。进入数字时代后,创新迭代迅速且花样翻新,变动性指数级增强,规制回应也随之更具多样性和应变性,在快速多变的规制状态中,把握规制时机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大量充满偶发性和变动性的复杂、零散和无序的非常规规制措施都面临着时机选择的问题,故难以厘定每一项创新规制措施的准确时间节点。因此,本文基于规制理论与时间结合的视角,在一般规律层面探究创新规制具体措施的起始、转换和终结的时间逻辑标准,试图勾勒创新规制的一般性“时间逻辑”。并以创新规制策略和规制方式为切入点,依据该标准力图厘定创新规制内容的起始、转换和终结的妥当时机。
一、把握创新规制时机的重要性
Jacob 和Eric 强调,法律规制的时间和内容同等重要。〔4〕See Jacob E. Gersen & Eric A. Рosner, “Timing Rules and Legal Institutions”, 121 Harvard Law Review 543-589 (2007).缺乏时间要素的创新规制必然是“跛脚”的。创新规制的目标涉及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在尊重安全、健康和环境等价值的同时,既要促进创新以推动社会福祉,又要约束创新不过分伤害公共利益。就几乎所有的规制措施而言,规制者在时间选择上都面临着两难境地:过早规制面临着信息不足的问题,即容易因为并未充分了解规制对象的特性而导致规制失灵;过迟规制则可能扩大与创新相伴而生的负效应,进而对公共利益造成过度损害。可见,只有把握住妥当的创新规制时机,才有可能实现规制目标,过早或过迟规制都存在诸多弊端。
(一)过早规制创新及其弊端
从逻辑层面来看,广义的过早规制包括规制措施起始过早、转换过早以及终结过早。而通常所指的过早规制则是规制措施起始过早,本文称之为狭义的过早规制。笔者认为,过早规制一般是在某一项创新刚出现时,规制者就仓促表明允许或禁止的规制立场,并根据规制立场对创新展开有针对性的规制行动。这里所说的过早规制,是指过早就某一项创新展开针对性规制,不包括适用既有的一般性规制。创新规制措施起始、转换和终结过早均会引发规制不当或规制不足,本文以规制起始过早为例,阐释其弊端,本部分的过早规制均为狭义层面。
其一,对某一项创新过早表明允许或激励存在下述弊端。第一,过早允许或激励加大了规制错误概率。判断某一创新是否对社会福祉有帮助,以及为了实现这种可能的福祉,应该对创新的破坏性容忍到什么限度,均应建立在对该创新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数字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样态、迭代速度以及对既有规制的冲击程度都区别于传统模式。很多时候,规制者面对的几乎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在还不了解该事物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允许和激励错误。一方面,规制者过早支持的创新甚至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创新。Richard 和Sidney 提出,创新不仅仅是新的创意,还具有适用性,创新能为社会带来更多福利。〔5〕See Richard R. Nelson & Sidney G. Winter, “In Search of Useful Theory of Innovation”, 6 Research Policy 36-76 (1977).可见,虽然创新的表象特征为“新”,但并非所有的新事物都属创新。判断某一事物是否为创新的核心标准为其是否有利于增进“社会福祉”。而判断社会福祉既是一个综合权衡,也是对创新未来值的一个预判,在不了解一定信息时就仓促决策很容易出现失误。另一方面,某些真创新可能同时违背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重要价值标准,规制者在没有看清这些特质并制定相应控制措施的情形下就仓促进行允许或激励,会偏离规制目标。第二,过早允许或激励加大了扰乱规制秩序的风险。过早允许或激励很容易出现规制不当,不但后续纠偏成本高昂,还会陷入“朝令夕改”的规制窘境,降低规制秩序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其二,对某一项创新过早表明禁止或约束亦存在诸多弊端。第一,过早禁止或约束可能导致创新的覆灭。创新之所以受到普遍认可,是因为它能带来社会价值,在不充分了解新事物的情形下,规制者快速压制新出现的某一项创新可能会直接导致其难以继续发展甚至覆灭,这违背了激励创新的规制原则。第二,过早禁止或约束的规制习惯会引发整体规制环境的恶化,进而脱离创新友好的宗旨。如果规制者习惯于过早禁止或约束创新,不仅会使被压制的创新难以为继,还会降低其他创新者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整个创新生态。
(二)过迟规制创新及其弊端
从逻辑层面来看,广义的过迟规制包括规制措施起始过迟、转换过迟和终结过迟。而通常所指的过迟规制是规制措施的起始过迟,本文称之为狭义的过迟规制。笔者认为,过迟规制一般是指,某一项创新出现后并已发展壮大,规制者仍处于观望状态,既不表明允许也不表明禁止的规制立场,或者就具体的规制问题点过迟回应。这里所说的过迟规制,是指过迟就某一项创新展开针对性规制,不包括适用既有的一般性规制。正如“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迟到的规制亦非好规制。创新规制措施起始、转换和终结过迟均会引发规制不当或规制不足,本文以规制起始过迟为例阐释其弊端,本部分的过迟规制均为狭义层面。
其一,对某一项创新过迟表明允许或激励存在下述弊端。第一,过迟允许或激励加大了创新者的政策风险。如果是有利于提升社会福祉的创新,规制者应在其弱小时给予激励,除财政补贴、减税和政府采购等直接财产性支持外,规制者及时表达对创新的允许、推进或放松等激励性规制态度,可降低创新企业的政策风险,起到促进该创新的作用。如果过迟表明允许或激励,不仅使符合激励标准的创新者缺失了政策优惠,还会使创新者面临政策上的不确定风险,创新企业的估值和融资能力都会受到贬损。第二,压缩了培育创新的规制弹性空间。严格执行既有规制,实质上会造成禁止的规制效果。规制者通常且必要施行的牌照政策、市场准入及公共风险防范等措施,也可能阻碍或禁止新产品问世。当规制者严格将旧的规制措施套用于“创新”这一规制对象,就可能会阻碍创新的发展。
其二,对某一项创新过迟表明禁止或约束亦存在诸多弊端。规制者对创新的态度通常是先行观望,出于降低规制风险的考量或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很容易出现观望周期过长进而导致规制不足和不当。针对“假创新”,若未严格执行既有规制进行“阻断”,属怠于规制,必然会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对“真创新”而言,规制者准许其进入市场后应适时跟进约束性规制,如果一味放松,容易形成“溺爱式”规制,纵容创新破坏面的野蛮生长。因此,对创新尤其是颠覆型创新的观望时间过久,就会出现以下弊端:第一,创新中蕴含的颠覆/破坏属性会产生诸多负外部性,放松管制过程中,创新者会把成本向外转嫁,进而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害;第二,各地政府之间、不同规制机构之间的观望时间长短不一也会造成执法不统一;第三,过长观望给了某些创新在这个规制空档期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待它们成熟后,市场和消费者已经认可并接受其所带来的新产品或服务,此时进行约束规制则面临着难以改变现状或改变成本过高的问题。
可见,过早规制容易遏制创新,过迟规制容易放纵“假创新”以及“真创新”的破坏面。只有在相对妥当的时间段内,采用相对恰当的规制措施,才能既不纵容创新的破坏面,又不抹杀创新对社会福祉的促进作用,过早或过迟规制创新都难以实现规制目标。创新规制应追求适当的时机,但创新具有多样性与快速变动性,确定妥当的创新规制时机难度很大。
二、难以厘定适当创新规制时机的成因
创新具有颠覆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6〕按照创新与既有事物的关系来划分,从创新是否对既存产品、市场和规制秩序造成干扰来看,可将创新分为改良型创新与颠覆型创新。See Joseрh L. Вower & Clayton М. Christensen, “Disruр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 73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3-53 (1995).一般来说,改良型创新对既有规制秩序冲击不大,规制者需重点考量颠覆型创新的规制。因此,本文的讨论对象为颠覆型创新。必须以灵活的规制内容来应对灵活多变的创新:创新的颠覆性要求规制者对其宽严相济;创新的偶然性使事前规制变得困难,要求规制者适度观望与放松;创新的不确定性既包含创新本身的不确定性,又包含创新对规制的需求的不确定性,这进一步加大了事前规制的困难程度。创新规制复杂和繁难且难以把握妥当时机,主要在于创新与规制具有双重变动性。创新具有两面性,且其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某一项创新的初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其破坏面和有益面此消彼长,二者比重随时转换,需规制者动态地“趋利避害”。相应地,对创新所展开的规制内容也具有多样性,从规制策略层面可分为阻断型策略、放松型策略、推动型策略和控制型策略,从规制方式层面可分为指导性规制、立法性规制和裁判性规制。规制所采用的策略和方式均需随创新的发展变化而应变。
(一)创新与规制都具有两面性且随时转换
在“创新冲击规制—规制适应创新而变革”的循环中,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和治理制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创新与规制的互动并不总是和谐的图景,而是充满了博弈。创新和规制这两套抽象的体系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中相互塑造——创新会挑战规制,又会推动制度革新;规制会促进创新,也可能会压制创新。
创新的两面性包括破坏性与有益性。创新的有益性已获得人们的充分认知,即创新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全人类的社会福祉。创新本质上是一个破坏性重建的过程,不免对原有秩序造成冲击。Рollman 和Вarry 归纳了促进创新“发展壮大”的步骤:首先,通过违反法律或者抓住法律规制的灰色区域降低成本;其次,在市场上发展壮大到难以禁止;再次,用户和利害关系人取得对规制的影响力;最后,运用传统的“规制俘获”手段为自身谋求有利的规制政策。〔7〕See Elizabeth Рollman & Jordan М. Вarry, “Regulatory Entreрreneurshiр”, 90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383 (2017).可见,创新的破坏性与生俱来,即对灰色地带的利用、对规制秩序的冲击以及对公共利益可能带来的损害。有的所谓“创新”只具有破坏性,并不能带来社会福祉的提升,只是假借创新之名行监管套利之实,属“假创新”。真创新同时具有破坏性与有益性两个面向,在具有提升社会福祉特质的同时也对既有规制秩序造成冲击。不同创新类型的两个面向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同一创新两个面向的比重也随着创新发展而变化,需规制者因事制宜与因时制宜地作出利弊权衡,据此选择激励或约束的规制立场。在真假创新混淆、真创新两面性混同的前提下,不论是识别假创新,还是权衡真创新的利弊,本就颇具难度,要在适当时间段内完成识别和权衡就更加困难。
规制的两面性包括促进创新与压制创新。妥当规制的理想效果是促进创新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创新”这一社会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即运用规制“诱导”创新——要么直接促进创新,要么以“最不妨碍”创新的方式实现特定监管目标。但现实规制效果并不总是符合预期,规制既可能促进创新,也可能压制创新。妥当的规制为创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在分配创新责任和风险以及保护创新成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鉴于创新规制的难度,规制失灵、规制不当或规制不足等欠妥当情形常常发生,在规制的实际效果上会压制创新。因此,规制者需在鼓励创新的收益和成本之间予以权衡。〔8〕See Nussim, J. & Sorek, A., “Theorizing Taх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36 Virginia Tax Review 25-82 (2017).基于价值导向的维度,创新规制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促进创新和其他社会政策目标的关系。基于效果导向的维度,创新规制的挑战在于如何放松规制而避免过于溺爱。可见,对创新直接适用现行规制固然不妥,以往的规制经验也难以直接援引。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规制探索过程中,规制者对其所施行的规制措施到底是促进还是压制创新本就难以迅速客观评价,要在适当时机调整产生压制效果的规制措施则更加困难。
(二)创新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创新如雨后春笋,生生不息;如长江后浪,永不停歇。任何特定创新都面临着“出生”与“死亡”、“萌芽”与“凋谢”。不论从整体视角还是从个体视角来看,创新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进入数字时代后,创新数量增加、迭代加速且形态各异。引发与规制不相称的创新形式越来越多,引发与规制不相称的程度逐渐加重。数字时代创新的快速变动使得规制者观察和决策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传统透过慢慢观察对某一项创新“量身定制”的规制模式难以为继,创新规制走向复杂、零散和无序。〔9〕参见王首杰:《数字时代商业模式创新的私法规制》,载《法商研究》2022 年第2 期,第64-76 页。这些复杂、零散和无序的创新规制措施均面临着妥当时机的抉择。
从整体视角来看,创新会不断涌现。“创新者产生—发展成为市场主导者—被新的创新者替代—新的创新者发展成为市场主导者—被更新的创新者替代”,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相较于一般相对稳定的规制对象,创新具有变动性和不确定性,每一类甚至每一个新出现的创新都有特殊性。进入数字时代后,创新大面积出现,就意味着产生大面积超越常规规制轨道的现象,常规规制框架应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和灵活性,并在一轮又一轮的创新冲击过程中得以更新。
从个体视角来看,同一项创新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特点。某一项创新对既有规制框架的冲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演化”之中,在该创新发展不同阶段,所引发的规制挑战类型各不相同,故针对创新的规制应该围绕创新的发展变化而展开。应在某一项创新的初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分别施以不同的策略和规制方法:创新企业发展初生期,能力弱小,对社会发展影响不大,这个阶段可以对其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有益面持观望态度,对其不利于规制秩序的破坏面适当容忍,通常选择放松型规制策略,运用指导性规制为主的方式进行规制;创新企业发展期,能力增强,有益面和破坏面的特征均进一步彰显,此时的规制策略应在激励创新发展的同时对破坏面予以适当约束(包括对消费者的伤害、环境的损害以及其他公共利益的损害等),这就涉及规制策略和方式的转换;创新企业成熟期直到衰退期,在原有破坏面可能随之增强的同时,其也可能形成垄断,打破市场秩序,对消费者和公共利益的损害更甚,还可能透过规制俘获、市场竞争等方式限制新一代创新的发展,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约束性规制。
可见,随着时间的发展,创新的属性、创新内部两面性的辩证关系以及规制问题点都会不断变化。每一项规制措施时间点的把控都关涉规制效果,但规制对象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使规制时机的把握颇具难度。尤其是进入数字时代后,作为规制对象的创新变动速度指数级加快、变动频率指数级提升以及变动形态多种多样,规制回应也需快节奏转换,把握妥当的规制时机更加重要、更加困难了。
(三)创新规制策略灵活多变
规制在回应不同类型的创新时会采用灵活的策略。规制者需首先明确“允许”还是“禁止”的规制立场,并随后在激励性规制与约束性规制之间进行抉择和转换。针对不同的创新,允许其进入市场后,规制的宽严程度存在差异——有的以纯粹放松为主,在此期间不承认创新的合法性而是以观后效;有的以限制性允许为主,对创新施加较为严格的条件约束;有的则直接承认创新的合法性,并依创新的特质为其“量身定做”规制内容。依据该逻辑,本文将创新规制策略分为四种,分别为阻断型规制策略、放松型规制策略、控制型规制策略和推动型规制策略。规制策略确定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创新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在不同规制策略之间进行转换。规制策略的灵活多变性给规制时机的厘定及研究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其一,阻断型规制策略,是指执行既有规制以阻断创新企业进入市场,或在其进入市场后,通过严格管控将其“消灭”的规制策略。阻断“假创新”是创新规制任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关键在于识别。对于“真创新”而言,没有规制者可以准确预测一种新科技或新商业模式的未来发展图景,很难在创新初生之时对长期愿景与短期破坏性之间的冲突进行权衡与平衡,因此应慎用阻断型策略。对创新的规制,既要防止对“真创新”的遏制,又要防止对“假创新”的放纵——前者会扼杀促进社会进步的事物,后者会纵容有损社会发展的事物壮大,在牺牲秩序价值的同时,还会导致更多公共利益的损害。目前,阻断“假创新”的意义被严重低估,有必要识别出“滥竽充数”的创新,及时阻断其对社会的损害。例如,针对花样繁多的“金融创新”,规制者应掀开审查对象的技术面纱,基于交易模式的本质来判断其是否具有创新属性。如果错误阻断了“真创新”,阻断型规制还可能再转向允许类规制。
其二,放松型规制策略,是指不对创新企业的合法性作评价,既不新设规则,也不严格执行既有规则,而是允许新商业模式进入市场。该策略隐含的理念是放任创新者参与市场竞争,在一定观察期后,再行决定是否在规制上表态,在该观察期内,创新既不是合法的,也不是非法的,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灰色地带。如果该时段过长,创新企业可能会凭借成本与政策(政策负担小)层面的诸多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取代传统行业,进而成为市场主流。故该策略适用于创新之初的观望期,此后应根据创新的发展,转换为控制型或推动型规制。创新者的逐利性促使其将成本和风险外部化,在约束性规制“迟到”的情形下,会导致逃税、损害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正当竞争以及其他损害公共利益等“规制漏洞”。因此,有意放松规制的时间不宜过久,否则会导致过高的社会成本,规制者也有怠于履职之嫌。而该策略的终结时间节点至关重要,不能一味观望导致丧失约束规制的良机,以避免造成创新企业的恶性发展。
其三,控制型规制策略,是指允许创新企业进入市场,再透过“改良”既有规则或出台新的控制性规则最终控制其发展方向和节奏。例如,我国对“专车”的规制立场即为控制型规制的典型,通过出台诸多控制“专车”的措施,事实上控制了专车的发展方向。该策略适用于规制者对某一项创新进行附条件允许的情形。在“既激励又约束”的规制组合中,控制型策略倾向于相对严格的约束。运用控制型策略的要点有二。第一,控制型策略实施时机的选择。在创新之初,创新企业生存能力尚弱,过早对其施加严格限制,将会导致以允许之名行禁止之实。第二,激励和约束措施的配比。这需要规制者在某一项创新对“社会福祉”的有益性与其对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的挑战程度之间进行价值平衡。一般是在规制者并不十分看好某种创新或该创新存在较大外部风险时运用该策略,但当该创新对“社会福祉”呈现出较强的有益性,而其破坏面或风险可控时,则应因时制宜地转换为推动型规制策略。
其四,推动型规制策略,是指允许创新企业进入市场,并尊重其商业模式,同时针对创新者的特点出台有利于创新发展壮大的新规则。在“既激励又约束”的规制组合中,推动型策略在进行必要约束的基础上倾向于保护与引导创新发展。常见的保护与引导方式包括鼓励、奖励或与创新者商洽制定新行业标准等。最典型的推动型规制莫过于将某一项创新归为规制上的新类型,并为其“量身定做”规制体系,正式“豁免”创新企业背负的某些传统法律责任。例如,加利福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等地允许Uber 发展,并进行专门立法,将Uber 等专车类公司在法律上界定为“运输网络公司”(Transрortation Network Comрany),〔10〕See Josh Krauss, “The Sharing Economy: How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Failing and Why We Need Congress to get Involved”, 44 Southwestern Law Review 365-384 (2014).对其施行有别于传统出租车公司的针对性规制。该规制策略需后续完善措施的配合,在税法、竞争法、知识产权法以及合同法等各相关法律领域进行修法或解释,以实现针对特定创新的法律规则体系性的“更新”。
(四)创新规制方式多样
创新的规制方式与规制策略密切相关:阻断型规制无须在规制上进行调整,只需严格施行既有规制;放松型规制则需规制者对赋权性规则进行扩张解释、对限制性规则进行限缩解释,以便为创新的存活留有空间,其主要涉及指导性规制和裁判性规制方式;在控制型和推动型规制策略之下,需以多种方式展开具体规制。尤其是随着具体创新的发展,规制方式之间需相应地转换。大体上,依规制主体的不同,对创新的规制方式会有所区别:在创新初生期,行政机关承担主导性规制,大多以指导性规制方式展开;在创新成熟期,创新本身的规制问题点充分发酵,可能需要将部分规制内容上升为立法,由立法机关实现终极规制;司法机关则在创新的各个阶段承担裁判性规制,作为以上两种规制方式的辅助。每种规制方式都有适用的时间段,在快速变动的状态下厘定妥当规制时机并非易事。
其一,指导性规制为主导规制方式。以美国为例,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立法与指导之争逐渐成为争议焦点。Мendelson 统计了美国1996 年至1999 年的立法与指导情况,发现在此期间指导的数量已经远超立法。OSHA 在此期间发布了3000 多个指导,而同时期的立法数量却只有20 个。〔11〕See Nina A. Мendelson, “Regulatory Вeneficiaries and Informal Agency Рolicymaking”, 92 Cornell Law Review 397-452(2006-2007).可见,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复杂变动的社会事实令指导性规制在整个规制框架内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相应地,指导性规制以灵活的特性成为最主要的创新规制方式。指导的优势在于周期短、程序简单和具有灵活性,劣势则在于权威性不足、缺乏司法适用性。指导的具体方式包括树立标杆、发布指导意见和施加威胁等。〔12〕See Tim Wu, “Agency Threats”, 60 Duke Law Journal 1841-1857 (2010-2011).近年来,“施加威胁”的指导方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13〕See Jerry Вrito, “Agency Threats and the Rule of Law: An Offer You Can't Refuse”, 37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553-577 (2014).不同于一般的指导、报告和学术研究,“施加威胁”因具有较强目的性而成为在创新初期最常用的规制方式。指导性规制应在适当时机终结,转向更为正式的规制方式。
其二,立法性规制为终极规制方式。立法性规制是成文法国家最重要的法律规制方式。经过试验性规制,对某一项创新的规制态度已经明确,规制措施也相对成熟,就有必要上升为更正式和权威的立法性规制方式。立法性规制具有明确、权威、持久、公开、利于公众参与和公众获知以及更容易加入宏观的政策性考量等优势;同时也有周期长、僵化、难以修改以及详尽程度失当等劣势。在数字时代,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的更新换代频率都指数级增长,规制体系与更新换代频率日渐加快的创新体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化解该矛盾,需在立法时对交易主体和交易标的等方面不可预知的未来创新留有空间和余地。而解释法律属于较为温和的立法性规制方式,包括立法机关对法律的解释以及司法机关对法律的解释。创新的体系性规制有赖于立法、修法和释法的平衡。对创新的立法性规制的起始时间节点非常重要,立法之后每一步解释和修订也应当在合适时间段内展开。
其三,裁判性规制为辅助规制方式。近年来,裁判性规制在创新规制体系中的作用逐渐凸显。有学者研究了美国自1946 年到2005 年的六十年间知识产权案件对“创新”的援引情况,发现在1966年至1975 年这十年,援引“创新”进行裁判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加。较之前一个十年,1986 年至1995年这十年援引“创新”案件的占比几乎翻倍(0.6% vs 1.1%)。〔14〕See Gaia Вernstein, “In the Shadow of Innovation”, 31 Cardozo Law Review 2257-2312 (2009).可见,越来越多的案件将“创新”作为一个裁判要素。基于不告不理原则,裁判性规制作为一种被动启动的规制方式,难以自主决定其起始和终结的时间。因此,裁判性规制是对创新进行持续性规制的一种方式,该方式需要充分考量包括促进创新、健康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等根本性的社会政策目标。裁判性规制在创新发展初期可作为试验性规制的一部分,有待于在合适时机将相关规制经验上升为立法性规制。在创新变老阶段,该方式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应在合理时段内加强对创新企业的约束。
三、创新规制起始、转换和终结的时间逻辑
创新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对创新的规制又需时时作出利弊权衡,力求既促进创新的健康发展又不过分损害公共利益。创新的多样性要求规制具有多元性,创新的多变性又要求规制具有变动性。因此,规制策略需要相互转换,规制方式也需要适时调整。而规制内容的起始、转换和终结均需考虑到创新发展的具体情况。在兼顾多元与多变的情形下,规制者既难以厘定普遍适用于所有创新类型的时间标准,又难以就一个或一类创新设置每一项规制措施的准确时间点。但具体规制措施的采用与实施并非全然无序,在灵活多变的现象之下仍有规律可循,即每一项创新规制措施都面临起始、转换和终结,而起始、转换和终结时间的确定标准具有一定规律性,可从逻辑层探究如何确定妥当时机。妥当规制时机并不局限于一个准确的时间节点,而是容纳连续时点的一个时间段。
(一)创新规制起始时段的确定逻辑
针对特定创新所有规制内容(包括规制策略和规制方式)都涉及起始问题,但在创新初生期把握针对性规制的起始时机尤为重要,在该阶段主要涉及规制策略的选择,以行政机关的规制为主。〔15〕立法性规制需要规制经验的沉淀,不适用于刚出现的创新,裁判性规制则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则,一般在创新初期也少有相关案件诉至法院。规制起始时段既不应过早也不应过迟。从规制事实来看,随着规制者对创新的重视程度的增加以及“边走边看”的观察型规制的普及,过早规制的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克服。随着对信息依赖性的加强,过迟规制则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成为当下创新规制起始时间层面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以过迟起始为重点研究对象,来阐释规制起始时段的确定逻辑。
避免过迟规制的重点在于破除对信息的过分倚重。规制者基于获取更多信息、保留更大灵活度的考量,通常对创新选择延迟规制。对新事物的规制存在不可预知的规制风险,人们在此时往往期待通过收集更多信息来降低风险。但规制者高估了收集信息的作用,认为在掌握全部信息之前,应保留规制的灵活度。当规制者追求“完美信息”(即足够充分全面的信息)时,忽略了决定规制质量的是“好信息”(即关键信息),实质上二者存在根本区别——在信息收集上,前者耗时更久,导致即便收集到关键信息,依然不能做出决策;在信息吸收上,前者追求信息量的庞大反而会使关键信息淹没在细枝末节当中。信息收集还存在悖论——往往收集信息越多在制定政策时犯错越多,从长期来看,信息对规制甚至没有产生实质性帮助。〔16〕See Nathan Cortez, “Regulating Disruрtive Innovation”, 29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75-228 (2014).因此,针对允许进入市场的创新,及时规制既可避免创新企业处于不确定的规制风险之中,也能及时平衡创新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风险分担和责任分配。
(二)创新规制转换时段的确定逻辑
创新规制具有强回应性,规制内容应依规制对象的演化而转换。作为规制对象的“创新”会不断壮大甚至逐渐“变老”,因此规制内容应根据创新的变化而适时转换。当被允许进入市场后,创新企业经过了初生期能够顺利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其生存能力进一步增强,此时,应该根据创新自身的演化而相应调整规制策略。不同规制策略可能会相互转换,且有可能持续转换,因此存在多种转换路线。而“允许”类规制策略既包含激励性规制内容,也包含约束性规制内容,为简化逻辑,本文从规制作用力正负的类型化出发,以激励性规制为主和约束性规制为主之间的转换来探讨规制策略转换时段的确定逻辑。〔17〕从规制策略来看,阻断型规制策略为约束性规制,放松型规制策略、控制型规制策略和推动型规制策略则内含着激励与约束的组合内容。从规制方式来看,指导性规制方式、立法性规制方式和裁判性规制方式既可能包含激励性规制的实质内容,也可能包含约束性规制的实质内容。因此,本文以规制内容上的激励或约束为标准,尝试探究规制内容与时间相契合的一般性标准。针对创新展开规制的典型特征,则往往是在正式规制之前进行试验性规制。因此,本文也专门探讨试验性规制向正式规制的转换以及试验性规制的结束时间。此外,基于以往对具体创新的规制经验,规制本身也在调整和进化,例如,将某些非正式规制(指导性规制)或废止或上升为权威性更强的规制方式(立法性规制),故本文以试验性规制向正式规制的转换来探讨规制方式转换时段的确定逻辑。〔18〕这两种分类标准是基于不同维度选取的,激励性规制与约束性规制主要指向规制内容,二者可成为并列关系,但这二者与试验性规制并非并列关系,后者主要指向规制的正式程度。
其一,规制转换时段的确定标准。基于规制对象的演化和规制本身的进化,规制方式和规制措施应当随之转换。对于创新这种不确定性极强的特殊规制对象,规制标的本身需要规制者进行“捕捉”,且每种创新的特点和发展周期各异,无法设定统一的时间节点,需规制者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创新的“新”属性会随时间流逝而逐渐减弱进而最终变为旧事物,故应及时调整对成长起来的“旧”创新的规制措施——及时终结试验性规制,转换为正式规制;及时终结针对创新的鼓励和放松规制,转换为一般性规制。随着创新从初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到衰落期的过渡,其市场生存能力越来越强。但在“创新友好”的规制大潮中,激励性规制有时会被放大使用。这就会造成对某些创新企业的偏颇保护,导致新的不公平。例如,电子商务平台在发展初期,相较于传统销售模式具备一定的创新属性,而当电子商务已经超过传统行业成为市场主流,最初的创新企业也成长为“巨无霸”,且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垄断特权,此时应从产业布局、保护消费者和维护竞争秩序等方面对其展开约束性规制。从激励为主转向约束为主的时间节点,可采用以下两个判断标准。第一,创新企业承受约束的能力。鉴于创新企业存活率低,为保证创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创新初期需要对其进行放松、激励和鼓励等友好型规制。当创新企业日渐壮大,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拥有基本生存能力时,应该对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面适时加以约束,并随之降低激励性规制的比重。第二,创新企业造成破坏性后果的规模和程度。当创新企业造成破坏性后果的规模扩大、程度加重,其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福祉已经难以弥补其所带来的损害,或者其当下损害的是社会核心价值和利益,此时就有必要从激励转向约束甚至阻断。此外,规制转换既可能是针对规制对象变化的回应,也可能是规制本身的调整。创新规制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既要对创新容错,也要对规制容错。当规制内容出现偏差时,应进行规制层面的修正,对相应规制内容进行调整和转换,而转换的时点有赖于规制者何时能够对欠妥规制有所认知以及转换程序的繁简。
其二,规制转换时段的确定方法。规制转换时机可根据记录、分析创新的业绩和规制的社会反应来确定。第一,可运用追踪技术和大数据来记录和分析创新本身的绩效。例如,可运用物联网技术探测和记录新能源汽车的排污情况,进而量化分析出新能源汽车对环境污染的缓解作用,以作为是否继续激励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依据。第二,针对创新对市场的作用以及规制策略的妥当性,观察社会反映。例如针对“专车”,可在试验性规制后观察乘客、司机、租车公司和平台等多方面的社会反映,据此来判断规制策略的妥当性。第三,跟踪分析风投公司对创新的投资情况,据此可分析出创新企业的发展前景和所处的发展阶段。
(三)创新规制终结时段的确定逻辑
一般来说,只要规制对象存在,规制就不应结束。但创新这个规制对象本身具有迭代属性,规制也应根据经济事实的迭代而更新换代,这就要求对某一项创新的特定规制措施有开始,也有终了。〔19〕既有法律体系中存在着诸多与“时间”相关的规范,用以设定立法和执法等治理行为的期限,包括为某种行为设定必须完成的时点、某种行为的起始时点(如立法生效时间)和某种行为的持续周期等。See Jacob E. Gersen & Eric A. Рosner, “Timing Rules and Legal Institutions”, 121 Harvard Law Review 543-589 (2007).当“旧”创新被更新的创新所取代,那么“旧”创新的针对性规制也应随之结束,进而转向一般性规制。在同一个创新的发展过程中,会历经多样化的规制措施,一些具体规制措施应当在适当时段终结。本文以激励性规制、约束性规制和试验性规制三种类型为例,来探讨规制终结时段的确定逻辑。
其一,激励性规制终结时段的确定逻辑。规制措施不仅要考虑具体创新的发展,还要综合考虑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目标。“促进创新”是一个持续的公共目标,作为宏观层面的创新激励,具有相当的延续性。从概观层面来看,规制者需在创新的各个阶段都为创新者留有激励的余地,但某些特定的激励性规制措施只适合于创新的特定阶段,应在妥当的时机予以终结。激励性规制的适用空间主要存在于市场准入和主体资格领域,此外还包括一些为确保创新企业存活发展的适当“容错”规制措施。不同层面的激励性规制,其终结时段的确定标准也有所不同。第一,财政补贴、公共采购以及减免税收等财务性的激励措施。这类措施对于概观层面的创新支持是持续不断的,但对于某一项创新的支持和激励,需根据产业政策进行调整。当某一项创新不再处于被保护和促进的行业,应结束相关财务性补贴,转向其他更具激励价值的创新类别进行激励。第二,市场准入和主体资格的放松规制。该激励措施的适用空间被界定,适用时间也同时具有“瞬时性”,即一旦创新者业已设立主体或进入特定市场,该阶段的激励措施就已经“用完”,也宣示着这类激励性规制在该对象上的适用终结。第三,针对某一项创新,将既有规制进行“软化”实施的激励性规制。该类措施的终结体现为向约束为主规制措施的转换,该时间标准如何确定已在上文论述。
其二,约束性规制终结时段的确定逻辑。通常来说,针对某一项创新的规制,如果规制者在规制之初选择放松型策略,允许创新者进入市场,那么随着时间发展,约束性规制的适用空间将逐渐扩大、适用强度将逐渐增大。在规制对象存续期间,针对其伤害消费者、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约束性规制应一直持续。而某些特定领域的特定约束则应在适当时机终结,尤其在某些传统管控过严的行业,过于严格的规制会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这类措施包括废止某些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减少行政许可的类别、内容和数量等。约束性规制的终结时段主要与规制宽严程度的调整相关。宏观上的放松规制会体现为在多个领域和行业的废止市场准入限制,该类规制涉及国家对政府与市场界限的重新划定,时间标准并不严格,可依一国整体规制方略的调整以及产业布局的优化来确定时机。而微观上的放松规制,则是针对具体领域和行业展开的。该类规制的时机取决于对特定行业的激励必要性,主要依产业政策而调整。
其三,试验性规制终结时段的确定逻辑。试验性规制也称“试点”,是指在规制初期还不能完全把握创新特性和规制问题点的情形下的“尝试”性规制,具有临时性特点。〔20〕参见张守文:《我国税收立法的“试点模式”——以增值税立法“试点”为例》,载《法学》2013 年第4 期,第59-66 页。当创新在事实层面趋于稳定时,规制者有必要适时终结试验性规制。以“立法草案”这种试验性规制为例,其结束方式包括试验性规制上升为法律和废除试验性规制——前者是指经过创新初生期、发展期及成熟期规制的调整、修改,如果试验性规制成功,则应适时上升为正式规制,以增强规制的权威性和确定性。〔21〕试验性规制上升的方式,包括直接将“草案”转换为正式规范,也可在“草案”为单项立法的情形下,将“草案”内容分散到其他相关立法之中。此外,这种终结试验性规制的方式,也属规制方式的转换,系从非正式规制转换为正式规制。后者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在“草案”为单项立法的情形下,其他相关立法规范经过修改已经涵盖了“草案”内容,基于立法体系的考量,废除试验性规制;二是在一定时间后重新转向阻断型规制,直接适用传统规制而废除试验性规制。试验性规制可谓在既有规制框架下开辟了一块“试验田”,无论其成败,都不宜持续时间过久,以防损害整个规制框架的权威性。如果试验性规制以压制某一项创新而终结,则试验性规制将自动结束。如果试验性规制上升为正式规制,其终结时机的确定应根据创新企业的成熟度、对约束性规制的耐受能力以及创新者对传统规制所造成的冲击的程度和规模来综合考量。
四、创新规制时间逻辑的适用
从厘定创新规制时机的四类挑战来看,创新与规制的两面性要求创新者时时权衡利弊,而创新自身的发展变化要求规制者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给予回应,这都体现了把控规制策略和规制方式时段的重要性。进入数字时代后,创新规制措施更加灵活多样且多变,很难就每一个规制措施探讨准确的时间节点。但依据创新规制的时间逻辑标准,与规制内容结合考量可进一步厘定创新规制的妥当时机。本文以创新的四种规制策略和三种规制方式为切入点,依上文规制时段确定标准力图厘定创新规制内容的起始、转换和终结的妥当时段。
(一)创新规制策略的起始、转换和终结时段的厘定
规制策略分为禁止和允许两种类型,具体可分为阻断型、放松型、控制型和推动型。规制策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创新发展的情况随时做出调整,在禁止类与允许类策略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禁止一般体现为阻断型策略,禁止类的规制可能转向允许;允许则首先体现为放松型策略,然后针对创新的发展特点,可能转回禁止类规制,也可能进一步选择控制型策略或推动型策略。
其一,阻断型策略的起始、转换和终结时段的厘定。阻断型策略主要涉及禁止和约束某一项创新。其规制时机的厘定主要参照约束性规制的时间确定标准。该策略起始时机的厘定主要在于突破对信息的过度依赖,以避免过迟规制。该策略转换时机的厘定标准在于创新对象的发展变化。在少数情形下,阻断型策略可能会转向允许类策略。转换时机应根据具体创新之两面性的比重转换来厘定,当有益性大于破坏性时,则应从禁止转为允许。一般来说,该策略并不涉及终结时机的选择问题,当规制禁止了某一项创新,就宣告着对该创新的全面否定,一旦该创新被彻底压制且在市场上消失,就不再有涉及该创新的任何规制内容,阻断型策略也随着其规制任务的完成而告终。
其二,放松型策略的起始、转换和终结时段的厘定。放松型策略一般会表现为允许创新进入市场,并一定限度地容忍创新对规制秩序的挑战,以便给创新提供成长空间。虽然放松型规制既包含激励性规制内容,又包含约束性规制内容,但其性质仍以激励为主,因此其规制时机的厘定主要参照激励性规制的时间确定标准。该策略的起始时机主要在于突破对信息的过度依赖,以避免过迟规制。该策略的转换方向较为多样,在不同情形下,可能会转向阻断型策略,也可能会转向推动型策略,亦有可能转向控制型策略。厘定该策略转换的时机,主要标准为创新发展程度和创新两面性之间的转化关系——当创新的破坏面大于有益面时,如果出现威胁人类生存环境、人身安全等重大风险,则应转向阻断型规制策略;当创新的破坏面大于有益面时,如果破坏面可以在规制的控制下得以压缩,其有益面又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则应转向控制型策略;当有益面更大时,则应转向推动型策略。其转换时机的厘定采用创新规制转换时段的确定逻辑。其终结时机的厘定主要参照激励性规制终结时段的确定标准,考虑创新者的创新属性、创新企业承受约束的能力以及创新企业造成颠覆性后果的规模和程度等要素,根据不同的激励内容适时终结激励,回归规制的常态秩序。
其三,推动型策略的起始、转换和终结时段的厘定。推动型策略一般会表现为允许创新进入市场后有针对性且有助于创新发展的规制措施。虽然推动型策略也包含着一定的约束性规制内容,但其具有明显的激励属性,因此其规制时机的厘定主要参照激励性规制的确定标准,其起始、转换和终结的时间标准与放松型策略基本一致。但该策略的激励色彩浓于放松型策略,故对于所激励的创新是否符合当下的产业政策,以及该创新的性质是否发生改变,应当投入更多的关注。一旦产业政策发生转向,或者所激励的创新类型达到了产业布局的水平,又或者此类创新在发展中发生属性变化而不符合产业布局,就应尽快结束推动型策略,根据实际情况转向控制型策略或者一般性规制。
其四,控制型策略的起始、转换和终结时段的厘定。控制型策略一般会表现为谨慎允许。虽然该策略既包含激励性规制内容,也包含约束性规制内容,但激励主要表现为允许准入市场,针对创新者的市场行为,仍应进行约束性为主的规制。该策略的起始时机的厘定主要参照激励性规制的确定标准。鉴于该策略是允许类策略中最为严格的一种,如果是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由其他较为宽松的策略转换而来,则再转向更宽松策略的可能性一般不大。少数再行转换的情形下,是在预期的破坏面或风险已经得到控制,但该创新具备较为重要社会意义的同时又仍未具备较强自我生存发展能力的情形下,转换时机可按该标准来厘定。此外,控制型策略兼具激励和约束规制内容,对其策略所包含的规制内容进行区分后,应按照规制内容的属性来厘定规制时机:激励性规制内容部分,起始、转换和终结按照激励性规制时段的确定标准;约束性规制内容部分,起始、转换和终结按照约束性规制时段的确定标准。
(二)创新规制方式的起始、转换和终结时段的厘定
如前所述,规范方式可以区分为指导性规制、立法性规制与裁判性规制。三种规制方式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不但需要相互配合,还存在相互转化和转换的可能。指导性规制和裁判性规制都有可能转化为立法性规制,而立法的适用和实施又离不开执法和司法环节。在具体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指导性规制、立法性规制和裁判性规制的适当运用时段也不尽相同。除了在规制内容上进行激励性和约束性的区分外,创新方式的转换还涉及试验性规制的起始、转换和终结。
其一,指导性规制的起始、转换和终结时段的厘定。因指导性规制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四种规制策略都有可能采用指导性规制的方式,尤其是在创新的初生期,会大量用到指导性规制方式。在创新初生期规制方向不明的情形下,该方式具有明显优势。指导性规制方式的起始时段的厘定可参照四种规制策略的起始时间逻辑标准,在避免过早规制的同时还要破除对信息的过度依赖以避免过迟规制。随着创新的发展,规制方向会逐渐明确,该规制方式应随之逐渐减少,有必要上升为立法性规制等更正式和权威的方式。该规制方式容易形成路径依赖而运用过度,从而难以在适当时段终结。其转换和终结时机的厘定主要参照试验性规制的时间逻辑标准,双重考量创新发展状况和规制试验效果。
其二,立法性规制的起始、转换和终结时段的厘定。立法性规制一般针对发展壮大、占据一定市场地位的创新,虽然立法性规制的内容也可能来自裁判性规制经验,但其主要与指导性规制终结相衔接。因此,其起始时机的厘定主要适用试验性规制转换和终结时段的确定标准。立法性规制的起始时间不宜过早,应当在试验性规制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作出。同时,立法性规制也不宜过晚,以防非正式规制对规制架构的突破太大。该规制方式一旦运用,不会在短期内轻易更改,但可随着创新情况和规制经验的发展变化作出进一步的解释。立法性规制的终结体现为废止某些规范,这一般发生在创新成熟、成为常态规制对象之后,在不妨碍规制体系正常运转、不压缩新的创新空间的情形下,该规制方式的终结并不紧迫。
其三,关于裁判性规制的起始、转换和终结时段。基于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裁判性规制的时间具有被动性,对于诉至法院的案件,审理时间标准按照程序法规定,并不会因为涉及的创新处于初生期、发展期、成熟期还是衰退期而有所区别。但根据涉案创新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阶段,裁判性规制的功能会有所区别:在创新初生期可能涉及对现有立法的放松,应加强“促进创新”这个政策目标的考量;在创新发展期及成熟期则是对上升为正式规制的立法的适用和细化,应在运用解释学方法时纳入适当的政策性考量;在创新成熟期及衰退期则体现为基本按照一般规制对象进行裁断,仅在必要情况下加强约束性规制的状态。裁判性规制有时也作为试验性规制的一部分,其转换和终结时段的厘定可参照试验性规制的时间逻辑标准。
五、结语
理想的创新规制,需掌握好“宽严相济”的规制内容、“恰如其分”的规制措施和“恰逢其时”的规制时机,以达至促进创新企业健康成长、产业创新迭代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创新规制时机的抉择至关重要,超前规制和滞后规制都会引发规制不当。
就规制起始时间而言,在试验性规制大行其道的当下,超前规制已经很大程度上被避免,因此,应着重避免过于延迟的规制——秉持尽早规制原则,破除对信息的过分倚重;就规制转换时间而言,应根据创新的实际发展状况适时做出规制上的调整,在创新企业承受力增强、“破坏力”加大时,适时施加约束性规制,应将创新在实践中的“试错”及纠错、创新规制的“试验”及调整的情况作为规制转换的标准;就规制终结时间而言,规制对象消亡下针对性规制自然终结,激励性规制的终结涉及适时向一般性规制甚至约束性规制转换,约束性规制的终结与政府和市场界限的调整及产业布局相关,试验性规制的终结主要涉及向正式规制的转换。将该标准用于分析四种创新规制策略和三种规制方式的起始、转换和终结时段的厘定,除了一般性时间逻辑特性外,每种策略和方式的时机重点是不相同的:阻断型规制策略的时机重点在于起始;放松型规制策略的时机重点在于转换;推动型规制策略因具有强激励性,应将时机重点置于转换和终结;控制型规制策略的时机重点在于转换;指导性规制的时机重点在于转换和终结;立法性规制的时机重点在于起始;裁判新规制的时机问题并不突出,应在不同类型和阶段的创新相关案件裁判中加入“促进创新”等政策性考量。归根结底,时机问题仍充满了裁量色彩,影响时机抉择的重要因素包括对创新的利弊权衡和对规制效果的评估,二者均涉及主观判断,仍需规制者恰当裁量。提升创新规制质量涉及甚广,期待本文的论证结论在时间维度有助于提升创新规制的妥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