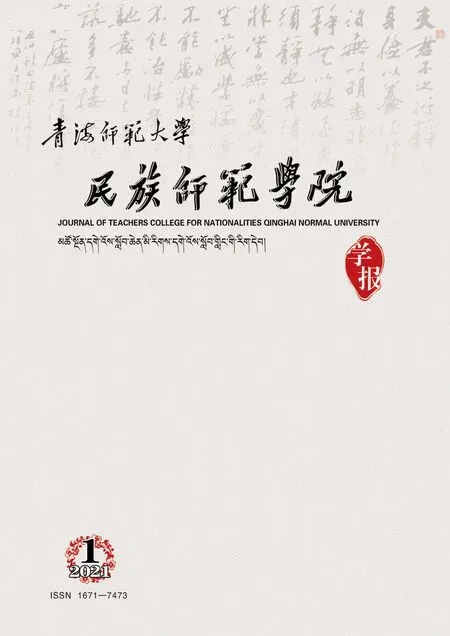唐蕃佛教文化交流及在青海地区的传播
梁 霞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青海西宁 810008)
随着唐蕃古道的畅通,吐蕃与唐朝建立友好往来关系之后,唐蕃之间交往频繁,而佛教文化交流是文化交往中重要的环节。唐代,汉地佛教已经进入了全盛时期,而在吐蕃,佛教才开始正式传入。吐蕃兴盛时期,虽然与唐朝时战时和,但双方文化传播通道的畅通,使得双方文化始终不断交流。此时期,唐蕃之间佛教文化交流以汉地佛教向吐蕃传播为主,而青海作为唐蕃间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随着文成公主的进藏和吐蕃势力的东渐,佛教由内地和吐蕃两个渠道传入青海地区。
一、唐蕃文化交流通道的畅通
唐蕃古道是唐朝与吐蕃间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将青藏高原与中原内地政治、经济、文化有机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唐蕃古道的延伸段将我国与尼泊尔、印度紧密联系起来。吐蕃道很早就存在,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羌人探索开拓自河湟至西藏高原间的道路,并迁徙至西藏高原。说明在河湟与西藏高原间,秦以前乃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着一条比较畅通的交通路线,是为唐蕃古道的雏形。河湟地区是从内地到吐蕃的交通要道和中转点,自汉至唐以来,历朝历代在河湟地区开疆拓土,移民实边,着力经营。唐贞观年间,唐蕃联姻通好,随着唐蕃友好关系的建立,唐蕃古道开启并兴盛,此后双方使节来往,此道路成为连接内地和青海、吐蕃之间的交通要道。
唐蕃古道,史籍中有记载,据《释迦方志》记载:“自汉至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渡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至青海,……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东南或西南,……至北印度尼婆罗国。”[1]此条记载基本勾勒出了唐蕃古道的路线,从长安-陇州-河州-鄯州(青海),再从西南行至吐蕃,再经泥婆罗(今尼泊尔)道到尼泊尔、印度的路线。《佛祖统纪》载:“东土往天竺有三道焉,由西域度葱岭入铁门者路最险远,玄奘法师诸人所经也;泛南海达诃陵至耽摩梨底者,路差远,净三藏所由也。《西域记》云:‘自吐蕃至东女国、尼婆国、弗粟特、毗离邪为中印度,唐梵相去万里,此为最近而少险阻’,且云:‘比来国命率由此也。’”[2]认为唐经吐蕃至天竺的道路被认为是最近且少险阻。
由此可知,唐蕃古道分为东西两段路程,东段是从长安出发,经过凤翔、陇县、秦州、渭州、临州、河州(或兰州)到鄯州、鄯城的道路,唐蕃古道的东段道路是以唐朝设置的长安至鄯州的正驿官道为走向的[3]。西段路线是由鄯城到吐蕃逻些的道路,《新唐书·地理志》鄯州鄯城县条也详细记载了入蕃驿道的走向和驿程。西段从鄯城开始,再翻越赤岭(青海日月山)向西行,经过扎陵湖和鄂陵湖,翻越巴颜喀拉山,渡通天河,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口,经今那曲,最后到达逻些。[4]唐蕃之间时战时和,虽战争不断,但双方文化传播交流通道始终是畅通的,正是这个开放性通道的畅通,唐蕃之间的佛教以各种方式传播和交流着,并延伸辐射到途经的青海地区。
二、唐蕃佛教文化交流
(一)唐蕃和亲与佛教入蕃
吐蕃王朝兴起于青藏高原时,赞普松赞干布巩固统治,发展文化,积极对外学习,借以发展和丰富吐蕃文化。唐贞观八年(634),松赞干布遣使长安向唐朝正式通好,从此正式建立友好关系。贞观十五年(640),松赞干布再次派大相禄东赞使唐请婚,唐太宗派李道宗率队护送文成公主入蕃与松赞干布和亲。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觉卧佛和360部佛经,还带去了寺院建造法式和14种寺院法规。为了供养佛像和佛经,又兴建了小昭寺。除了大、小昭寺外,又兴建了十二座寺庙,有四如寺、四厌胜寺、四再厌胜寺,佛教在吐蕃初成规模。但是这些都是早期的庙宇,只供奉佛像,并没有僧伽组织,也无学经组织。在带去佛像、佛经、佛寺型制的同时,还有一些僧人随文成公主一起入吐蕃,参与译经等。松赞干布也受到佛教影响,将佛教“十善业”中部分规定作为道德规范进行推广。
赤德祖赞(704-755在位)时,再次向唐请求和亲。唐神龙三年(707),吐蕃派遣使者到唐朝进贡,并向唐中宗请求联姻。景龙四年(710),迎金城公主入蕃。金城公主沿着七十年前文成公主的旧道唐蕃古道入藏。金城公主在吐蕃生活近三十年,对唐蕃交往作出了积极贡献,还巩固了文成公主进藏后的唐蕃“舅甥之盟”。金城公主入蕃再次带动了汉地佛教对吐蕃的影响,金城公主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像,从所藏匿的小昭寺南镜门内寻出,建立谒佛之供,朝佛习俗延续至今。[5]将释迦牟尼像移到大昭寺后,也曾安排一些汉僧来管理寺院。同时还将一些崇佛的民风民俗带到了吐蕃,如提倡七期之祭,建立超荐佛事的习俗。[6]
(二)经行唐蕃道赴印求法僧
吐蕃王朝崛起于青藏高原后,巩固统治、安定社会、加强对外交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先后与泥婆罗(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的和亲,使得吐蕃至尼泊尔的泥婆罗道,吐蕃至唐长安的唐蕃道畅通。唐蕃关系的稳定为西行赴印求法的僧人开辟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泥婆罗道,即从长安经唐蕃古道到吐蕃,再从吐蕃取泥婆罗道经尼泊尔到达印度。这条西行求法路线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唐长安至印度的路程,“近而少险阻”,是唐初佛教僧侣和官方使臣选择吐蕃道最主要的原因,使得唐蕃古道成为唐初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通道。
在唐代赴印求法僧中选择尼蕃道的僧人,见于史料记载的就有十多位。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贞观十五年(641)至武后天授二年(691)五十年间近60位僧人西行求法和游历的事迹,其中取道尼蕃道往返中印的僧人,有玄照、慧轮、玄恪、道方、道生、玄太、道希、僧伽跋摩、师鞭、末底僧诃、吐蕃公主奶母二子、悟真、玄会共14人。初期赴印的西行求法僧在往返吐蕃时还得到了文成公主的资助照应并护送出行,如玄照,“远跨胡疆到吐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返程时“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7]。经行唐蕃道的求法僧们,青海地区也是途经之地,也有明确记载途经吐谷浑的,如新罗僧人玄太曾与玄照一起取吐蕃道,经泥婆罗到中印度,返回时在吐谷浑与道希法师相遇,玄太又伴随道希到印度,然后再原路返回。甚至还提到吐蕃公主奶母子,吐蕃公主此处应指文成公主[8],文成公主奶母两个儿子也一同出家,说明当时文成公主周围佛教氛围也较浓。虽然史籍中未见赴印求法僧在吐蕃、吐谷浑的具体活动,但在吐蕃承蒙文成公主资助和护送,至少也增进了吐蕃、吐谷浑对内地佛教文化兴盛程度的认知,也间接地引发了吐蕃向汉地取经求法的活动。
(三)吐蕃遣使赴唐取经求法
赤德祖赞(梅阿聪)时,唐天宝十三载(754),吐蕃赞普派桑希等五人作为使臣赴长安,向唐廷求取佛经和五台山图。史载:“派遣桑希(sang-shi)等4人赴汉地求取经籍。唐主见之甚为喜爱,意欲留之。彼谓:此行乃吐蕃之地求取妙法,吾将三藏经籍归献赞普,一俟返回吐蕃与父商议,再设法来作属民,现在请赐佛经千卷。于是唐主赐予磁青纸金写佛经千卷及其他甚多。……途经汉地代县(devu-shan)之山(按:指五台山),取得文殊宫式样。后归返吐蕃。”[9]唐皇赐给用金液写瓷青纸上的佛经一千部,这应是汉地佛经输入吐蕃最多的一次,也为桑耶寺建成后大规模的译经做好了准备。返程时桑希在五台山取得文殊宫式样,为建桑耶寺做好了准备。途经益州,向金和尚请求传法,和尚还赠送三部重要的佛经。此后,还从中原传入了汉文佛经《金光明经》《律差别论》等。[10]桑希穿梭于唐蕃之间,为唐蕃间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赤松德赞后又派桑希和巴赛囊等率领规模更大的30人组成的使团赴内地求取佛经,学习戒律,迎请汉僧。据《巴协》记载,任章·藏谢日(sbrang-gtsang-bzher)为主使,巴·桑希为副使,赛囊为正法眼(类似顾问),主从三十人。……前往京师。……(帝)随派其师乘御马前往益州请来和尚,得其传授。临行又厚赐丘纸、丝绸、婆罗弥(珍贵的合金)、珍珠串、彩缎……并给赞普复函及回礼等。[11]从汉僧那里学得了“修行教诫”,唐王送佛经,还派僧人赴吐蕃讲经。
(四)迎请汉地高僧到吐蕃译经弘法
据藏文古籍记载:“据说汉地翻译并盛行《般若经》《解深密疏经》和《大圆满》等佛法。……从印度带来佛法,从汉地光临和尚,故称佛法在吐蕃诞生。”[12]在吐蕃王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两位来自吐火罗、和田的译师,曾经邀请汉族堪布李贤(或称李青)赴吐蕃宣讲佛法,但因吐蕃还没有文字,堪布李贤留下了具足五佛规格的佛像和金塔,佛经《百拜忏悔经》《无垢顶髻经》后离开吐蕃返回了汉地。吐蕃历代赞普也遣使入唐迎请汉地僧侣入吐蕃译经弘法。据《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曾迎请汉地僧人玛哈德瓦茨(即大寿天和尚)等来吐蕃与印度和尼泊尔僧人一起译经。据《玛尼宝训》卷下记载,文成公主还亲自参加译经。赤松德赞,曾迎请汉地僧人东松岗哇、摩诃波罗、尚底巴达等到吐蕃翻译汉地医典,同时也译经弘法。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赤松德赞再派使臣到唐朝请求派汉僧入蕃弘法,据《册府元龟》载,“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秀、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13],可知,吐蕃很早就向唐朝延请内地高僧入蕃讲经说法,并规定期限、派人轮换等暂成定制,但直到建中二年才成行。《贤者喜宴》中也说赤松德赞曾派拔塞囊去内地取佛经并迎请内地僧人入蕃。据《莲花生传》载,入吐蕃的译经汉僧有“帕桑、玛哈热咱、德哇、玛哈苏扎、哈热纳波、摩诃衍及毕洁赞巴”。
到吐蕃弘法的汉僧最著名的莫过于禅宗大师摩诃衍(大乘和尚),他将禅宗思想传到吐蕃并得以兴盛。据法藏伯希和P.4646敦煌汉文禅宗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载,贞元年间,吐蕃“请汉僧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781年左右,摩诃衍等前往吐蕃,将汉地禅宗传入吐蕃。他的禅宗“顿门巴”学说发展非常迅速,不仅赞普妃没庐氏和贵族妇女30余人随摩诃衍出家,而且绝大多数吐蕃僧也都开始信奉或跟随摩诃衍。这对以寂护、莲花生代表的印度中观瑜伽行教派“渐门巴”造成了威胁,引发了吐蕃佛教史上著名的“顿渐之诤”。由赞普亲自主持,以莲花戒为首的印度僧人和以摩诃衍为首的汉地僧人进行了大辩论,这场“顿渐之诤”持续了三年。辩论的结果,根据《顿悟大乘正理决》,汉僧取得了胜利,从此汉地禅宗和印度莲花戒派并行于西藏。但大部分藏文资料如《贤者喜宴》《巴协》等认为摩诃衍辩论失败,返回了汉地。而从现有资料看起来,禅宗在吐蕃的影响并没有断绝,而且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宁玛派、噶举派等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等[14]。
自吐蕃佛教史上的“顿渐之诤”后,摩诃衍离开卫藏到吐蕃边地传播禅宗。根据敦煌藏文禅宗文献《大乘无分别修习义》(P.996),摩诃衍曾到“tsong-kha”(一般译为宗哥或宗喀)地方传教,史载摩诃衍在宗哥传教长达30年,后返回内地。[15]收授了不少弟子,后来其弟子吐蕃人虚空藏禅师将汉地禅宗吐蕃化,创建了大瑜伽派,虚空藏禅师的弟子布·益西央又整理了大瑜伽派的理论。最后二人均在阿琼南宗(今青海尖扎)坐化。摩诃衍、虚空藏和布·益西央三人在宗哥一带活动近五十年(790-840年),使禅宗得以传承和流行。[16]
(五)唐蕃战争中的佛教文化交流
在唐蕃佛教文化交流中,战争也起到了文化交流的作用。唐蕃战争中,吐蕃从唐边地掳掠了不少汉地僧人,后来唐蕃关系缓和后,将掳掠的汉僧放还。据《旧唐书·吐蕃传》载:“(建中)三年(782)四月,放先没蕃将士僧尼等八百人归还,报归蕃俘也。”[17]《德宗本纪》亦载:“(建中三年四月)庚申,先陷蕃僧尼将士八百人自吐蕃而还。”[18]《宪宗本纪》载:“(元和二年(807)八月)没蕃僧惟良阐等四百五十人自蕃中还”。[19]吐蕃几次俘虏和放还者都以僧人为主,劫掠去的汉僧数量众多,虽未见这些汉僧活动的资料,但这些僧人的被俘和放还,客观上也促进了唐蕃间佛教文化的交流。
三、唐蕃佛教在青海地区的传播及影响
青海是佛教传播较早的地区,相传早在东汉末年,在今湟源县扎藏寺所在的巴燕乡一带,就有汉僧建过僧舍,后建成了扎藏寺[20]。两晋南北朝以来,法显、昙无竭和宋云等高僧赴印求法时,在青海曾留下活动遗迹。法显曾在平安一带活动留有遗迹,宋代建有静房,后建成夏宗寺[21]。北魏之前西宁北山已建有北禅寺[22],北朝末年建寺并兴盛于唐朝的廓州法讲寺[23]。到唐代,唐廷又多次按州置寺,唐高宗时下诏“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24],武则天时期又“令诸州各置大云寺”[25],唐中宗又诏令诸州置寺以“中兴寺”为名;后又改中兴寺为龙兴寺[26],唐玄宗开元年间又令各州修建以年号“开元”为寺名的佛寺,即开元寺,在各州置寺,唐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在各州建大云寺,当时在鄯州(今乐都)置大云寺[27],在今民和古鄯镇还有“药王洞”,建有汉式殿堂,后来发展成药神寺[28],同时还在战略要地修建寺刹,开元天宝年间在积石军(在今贵德)有多福寺[29],唐后期鄯州龙支县(在今民和)有圣明福德寺[30]等。汉至初唐以来,见于史籍记载的这些汉传佛教寺院,分布区域主要是在河湟流域的农业区。
随着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以及吐蕃势力的东渐,佛教就从内地和吐蕃两个渠道传入青海地区。据青海玉树结古寺名僧桑杰嘉措所著《大日如来佛记摩崖释》,文成公主一行途经今玉树巴塘乡西北约4公里处的贝沟南端,在当地丹玛岩崖上雕刻出9尊佛像,此即玉树巴塘现存的大日如来佛堂,亦称“文成公主庙”。当地还传说,文成公主进藏时,在今巴塘乡东扎隆沟营造佛塔一座,在今巴塘乡境内相古河对岸的邦同滩上亦建塔一座,后在这些佛塔附近相继建成仁青楞寺和拉康寺。玉树地区处于唐蕃古道的交通要道上,又距离吐蕃最近的地区,因为,自唐蕃道开启并兴盛以来,青海玉树地区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佛教的弘传中心。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相禄东赞率兵击溃吐谷浑,将青海的大部分地区纳入吐蕃辖区。天宝年间,又趁唐朝安史之乱,无暇西顾,吐蕃尽取河西和陇右之地。河陇地区又是唐蕃交兵的前沿之地,在唐蕃友好会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吐蕃占领河陇时期,唐蕃之间曾以佛教为媒介,通过缔结盟约,进行政治、文化交往,也带动了佛教在青海地区的弘传。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将印度的两位佛教大师寂护和莲花生迎请至西藏弘扬佛法,并为他们修建了桑耶寺,作为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然后又在贵德修建了罗汉堂寺,作为桑耶寺的支寺[31]。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师来西藏传教之时,莲花生大师也“曾到玉树安冲地区活动,于尕外卡滩上修建了格沙拉唐佛堂和邬金佛塔[32]。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赤热巴巾)北征到此(贵德)建塔,以其发辫装藏”是为贵德乜纳塔的前身,乜纳塔也被誉为“青海第一塔”[33]。相传吐蕃时期,有五名指挥官率部在此屯军,曾建有一座叫“玛公娘哇”的小寺,意为“古老的母寺”[34],后来一度扩建,并形成吾屯下庄寺,该寺后来成为青海“热贡艺术”的发祥寺院之一。随着吐蕃势力在河陇地区的扩张,在青海已修建有佛塔、雕刻的佛像,并有小型佛堂、寺院。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朗达玛禁佛,西藏部分僧人避居青海,在河湟地区弘法,使青海成为藏传佛教后弘的发祥地。当时,在曲卧山静修的僧人藏·饶赛、肴格迥、玛尔·释迦牟尼得知灭佛消息后,带着律藏佛经一驮,逃往西北,辗转来到青海尖扎县城的阿琼南宗,在此居住静修。后曾一度在乐都羊宗沟静修,后来青海地区的许多名僧亦曾到此闭关修行,逐渐形成小型寺院。最后三人辗转来到青海化隆的丹斗地方的岩洞中,修行并弘法。夏住丹斗,冬住东麻囊,在东麻囊山崖上至今有7个山洞,相传是当时的遗迹,后修建大经堂和囊欠,形成寺院。因在尖扎阿琼南宗、乐都羊宗沟、化隆丹斗、互助白马寺、西宁一带等地方静修、弘法,留下了诸多佛教遗迹,后来修建寺院,这些地区也成为佛教活动的中心,藏·饶赛等三人也被后世尊称为“智者三尊”或“三贤哲”。藏·饶赛晚年剃度的弟子贡巴饶赛,在学习律藏佛典后,定居丹斗,广建寺塔,弘扬佛法,声名渐渐传入西藏,当时桑耶地区的领主查那益西坚赞父子,派卢梅·崔臣喜饶等卫藏十弟子(或云七弟子)来青海受戒,贡巴饶赛为卢梅等授戒,此后,卢梅等及其再传弟子弘法西藏,使西藏佛教再度复兴,史称“下路弘传”。西藏佛教复兴得力于贡巴饶赛弘传佛法,后人尊为后弘鼻祖,他所在的丹斗寺被称为藏传佛教后弘的发祥地,在藏传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35]
综上所述,“自佛之来西域也,河湟实为首被教化之地”[36],汉至唐初,青海地区佛教寺院主要集中分布于河湟流域。唐蕃古道兴起后,唐蕃往来交流,均需取道唐蕃古道,青海作为唐蕃间重要的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随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以及吐蕃势力的东渐,佛教从内地和吐蕃两个渠道传入青海,由此呈现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交汇的特点。青海作为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通道,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是唐蕃相争的主战场,又是唐蕃文化交流必经之地,因区位优势和历史文化因素,青海又成为藏传佛教后弘的发祥地,在藏传佛教形成、发展和传播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