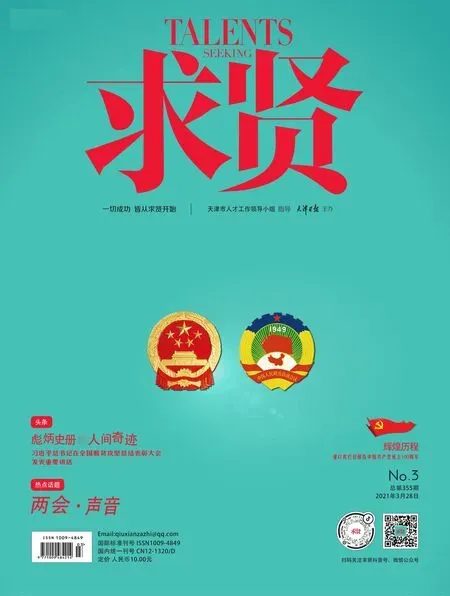潜心破解生态修复的密钥 访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启星教授
REPORTER'S
NOTES
人物素描
2021年的春节刚过,我们迎来了中国农历年中的第三个节气——惊蛰。惊蛰到来,春雷乍动,蛰伏在土地里的昆虫都惊醒了,这正是万物生长的好时光,也意味着农民要开始忙着春耕了。在这一天,记者采访到了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启星教授。周启星是一位与水土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化学教授,他所研究的课题不仅与农业息息相关,更与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周启星出生于1963年,他的童年是在条件艰苦的年代度过的。“辛苦的耕种,却换不来饱饭,那时的我立志要成为一个农业科学家。”物质条件虽然匮乏,但精神力量无比坚定。由于成绩优异,周启星被保送攻读研究生。本科专业学土壤与农化是他儿时的理想,而此时的他却有些动摇。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而繁荣的背后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石油矿产的开采、水资源的污染、土地的过度开发利用等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逐渐暴露且日益严重。看着昔日欣欣向荣的土地因污染被闲置,周启星十分痛心,他意识到,一味地追求高效增产并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于是,他毅然将自己的专业转向了生态学和地球化学,专攻污染生态与环境地球化学。
与研究农业增产受欢迎不同,污染环境研究与控制修复却是个“苦差事”,一是工矿污染地区大多分布在偏远、自然条件艰苦的地区,二是工业企业经常“闹别扭”。因涉及“赔钱买卖”、修复周期长等原因,当时做生态修复的研究及成果也相对较少。“欧美国家工业化进程早,对土壤污染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早,但他们的成果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所以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摸索。”
边学习、边思考,周启星始终将自己沉浸在一线科研工作中。在我国,他最早提出了“复合污染”和“生态修复”的概念与思想;同时,他也是我国最早开展污染土壤修复基准和标准研究的学者。1995年,由周启星著的《复合污染生态学》不仅对“复合污染”概念的内涵进行了阐述,还提出了“联合效应”广义理论;2004年出版的《污染土壤修复原理与方法》一书,是我国关于污染土壤修复最早、最系统的专著,由于它在我国污染土壤修复实践及其产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与贡献,获钱学森金奖。
科研不能只是纸上谈兵,需要在实际应用上见真章。周启星的硕士论文研究成果,为1995年国家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为我国土壤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2003年,在第212 次香山科学会议上,周启星作为执行主席之一,首次提出在我国系统开展污染土壤修复基准研究的建议,呼吁国家重视这一研究方向,为我国尽早制定污染土壤修复标准打下良好基础。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污染问题也在不断“升级”。“我们早在十几年前的调研中就发现,除了重金属等传统污染外,抗生素等新型污染物问题也日趋严重。”新型污染物由于生产使用历史相对较短,大家对其危害和认识也并不明确。“作为科研人员,我们必须要有前瞻意识。”于是,周启星带领团队开始向新的研究方向进发。
新型污染物通常具有环境持续输入、生物累积性和毒性变化大等特点,弥散于土壤、水、大气,富集在动植物体内,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害,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国抗生素用量很大,不仅应用于医疗过程,兽药抗生素在养殖业和畜牧业中也大量使用,一旦他们的粪便作为肥料施用,势必会对土壤和水环境造成污染。”
在抗生素污染领域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了掌握可靠的科研数据,周启星需要与农业种养户合作,采集水土样本。“听说来搞科研,他们都很欢迎,但是深入了解之后,他们又拒绝了。”换个角度想,农户们的顾虑并不是毫无道理,土地是他们的“饭碗”,周启星要证明“饭碗有毒”,那以后吃什么?就这样,本来谈好的合作,一个一个地失去了。“抗生素污染研究迫在眉睫,再难也要做下去。”一如他儿时最初理想的那份坚定,周启星带着团队苦口婆心地去和农户们谈,从国家大义到个人利益,从科研机制到未来展望,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终于有两家种植户同意了合作。
“取样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不仅要研究土壤,还要分析在其上生长作物对污染物的吸收程度。”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连周启星都不记得自己往农田跑过多少趟。“那时候,学校的条件还不是很好,仪器经常需要排队使用,通宵做实验是家常便饭。”在田间沉得下身子,在实验室里守得住寂寞,最初的理想如一盏明灯照亮周启星前行之路。
脚下沾了多少泥土,手中就会收获多少果实。通过十几年的刻苦攻关,周启星与团队首次建立了土壤典型污染物(重金属、PAHs 和抗生素等)的快速与多维度精准诊断方法,阐明了我国典型工业化城市土壤重金属和无公害蔬菜基地抗生素污染时空分布特征与发生机制,并找到了对应其修复的代表性植物。
污染可能只是一个瞬间,但修复污染却需要很久。根据土壤所受污染情况不同,完全修复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停止耕种进行修复,这不现实。”为了让污染修复技术可推广,周启星煞费苦心,“我们最终找到了几种具有观赏性的修复花卉,让农户们在污染土壤修复的过程中也能获得收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我非常激动,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绿水青山的重要性。”除了加速污染修复技术的推广,周启星更为关心的是,污染土壤修复标准的制定。“国外很重视这方面工作,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都有完备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土壤修复标准,他们在研究基准和制定标准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此,周启星迫切希望我国能加快相关工作的推进,“中国目前只有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而且也不全面,像抗生素等新型污染物并未涉及,而对于污染土壤修复标准也还是个空白,污染土壤修复基准的系统研究更是尚未开展。”
从周启星的言语中,记者能切实感受到他的那种急迫而又焦灼的心情。民以食为天,从担心“吃不饱”到担心“吃不好”,周启星始终心系百姓。他用汗水浇灌、用足迹丈量,将自己的大半生奉献给了土地。“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就是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与人生价值。”
EXCLUSIVE
DIALOGUE
独家对话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近期的科研成果。
周启星:这项工作首先是针对典型地区土壤污染诊断,包括典型城市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诊断,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综合诊断方法体系的构建,无公害蔬菜基地抗生素污染诊断,土壤碳纳米材料的污染诊断;然后就是针对污染修复植物的响应机制,包括三叶鬼针草、金盏菊、凤仙花和蜀葵对Cd污染胁迫的响应机制,龙葵对Cd-As 复合污染胁迫的响应机制,金盏菊、凤仙花和蜀葵对Cd-Pb 复合污染胁迫的响应机制,上述污染修复植物对重金属-B[a]P 复合污染胁迫的响应机制,污染修复植物龙葵通过氮代谢应对Cd 污染胁迫的响应机制。
该研究的创新在于首次建立土壤典型污染物(重金属、PAHs 和抗生素等)的快速与多维度精准诊断方法,阐明我国典型工业化城市土壤重金属和无公害蔬菜基地抗生素污染时空分布特征与发生机制;同时,率先系统阐明代表性污染修复植物对上述典型污染物污染胁迫的生理学、生长与超积累响应规律,揭示其交互作用的吸收转运响应及超耐性机制。
这项工作为建立更为强大的污染修复技术体系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科学依据和数据基础;同时,开创了花卉植物修复污染土壤的新方向,为污染土壤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满足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最重要的是,该项工作为顺利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贯彻《土壤污染防治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科技支撑,有助于解决我国突出的耕地污染、农产品质量堪忧等重大农业环保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人民健康。
很高兴这项工作受到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相关的8 篇代表作总被引达2282 次,其中SCI 他引1352 次。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污染土壤和水环境的植物修复。请问目前发现用于污染修复的植物有哪些?它们的应用情况如何?
周启星:20年前,我们利用室外盆栽、小区模拟实验和污染区采样相结合的方法缩小研究范围,从田间杂草中相继筛选到龙葵、球果蔊菜和三叶鬼针草3 种具有重金属超富集现象和特征的植物。后来,又相继发现紫茉莉、凤仙花和牵牛花等花卉植物能很好地促进石油烃的降解和污染修复。
这些观赏性植物,在城市园林建设中经常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同时还能很好地促进石油烃等有机污染物的降解。与传统的石油污染治理方法相比,利用花卉植物进行污染土壤和水环境的修复,具有投资少、工程量小、技术要求不高等优点,而且不会造成二次污染,同时,污染修复进程不仅不会破坏环境,还有助于改善因石油烃污染而引起的土壤退化和生产力下降,恢复并提高其生物多样性。
目前,花卉植物主要用于重金属镉、铅和石油污染的场地,包括湿地和污染农田,以及城市污染水体。比如在张士灌区、沈抚灌区,还有胜利油田、大港油田和天津大沽排污河等。通过与农业农村部环保检测所等单位的合作,将花卉植物修复技术在污染农业区推广,指导农民将花卉植物与农作物如马铃薯、番薯间套作生长,收获后的农作物可以进入市场,使用后的花卉植物一方面可以流入市场作为景观植物,另一方面可以回收继续做研究,而它的种子在国内外专家中流转进行经验交流。
记者:用于修复受污染土壤后的花卉流通到市场上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吗?
周启星:不会的,花卉植物作为超积累植物的好处首先在于花卉吸收污染物后一般是不作为食用的,但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供观赏,污染物因此不会进入食物链,不会影响人体健康,其次,花卉的观赏价值“用”完之后,由于分散在千家万户,大家可以扔进垃圾箱里,通过垃圾收集和卫生填埋,超积累植物生物量的处理就迎刃而解了。加上花卉植物基数小,单株污染物释放到周围环境,由于稀释效应,并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即使少部分污染物通过花卉植物释放到空气中,也不会构成空气污染。
记者:您解决了修复植物生物量处理的关键性国际难题,也就是污染修复后修复植物的去处问题。您觉得目前花卉植物修复污染水土环境面临的最大问题或困难是什么?
周启星:目前花卉植物修复污染水土环境主要面临三个问题和难点。
第一,植物富集污染物具有单一性。现在发现的超积累植物中,能同时对3 种以上污染物超积累的不多,希望能发现可以同时处理多种污染物的超积累植物。我们也在试想结合植物基因工程来强化修复,但目前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用于修复的花卉植物耐盐性不高。我国沿海各油田,如胜利油田、大港油田,其土壤含盐量高,想要降解水土中的石油烃,必须找到既耐盐、又能促进石油烃降解的植物,否则这些植物在油田修复场地很难存活。
第三,多年生花卉植物在北方过冬与发挥修复作用的问题。受地域气候影响,在南方生长的花卉移栽到北方,会因为气候温差的关系不容易生长,尤其在冬天,很多植物休眠或死亡,发挥不了应有的修复作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记者:您对我国未来污染水土环境修复有哪些建议?
周启星:我们国家急需制定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污染土壤和水体修复标准。没有修复标准,修复好坏就无从衡量和评价。现行使用标准已经跟不上国内国际迅猛发展的步伐,因此首先应该开展国家层面的污染修复基准的系统研究;同时,还要重视研究和建立地方环境标准,尤其是土壤,由于东西南北差异太大,统一的标准在不同的地区根本不适用。
其次,应该规范污染修复市场的发展。目前,已经有不少的污染修复企业,但其污染修复能力低下,资金短缺,技术也有待提升;同时,我国必须有一套适合自己的商业运作模式,国外的一些模式也值得借鉴,比如日本,先由企业进行场地风险评估,然后修复,最后再向政府申请验收。
第三,产学研政要密切结合。研究单位首先要与污染修复企业紧密合作,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支持、主动参与。只有政府重视、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产学研政拧成一股绳,污染修复工作才能有效展开。
第四,要提高全民生态环保意识。需要让全民参与到生态保护链中,特别是农田污染区,不但要对农田实施污染修复,还要对农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因为一旦受污染农产品流入市场,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将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