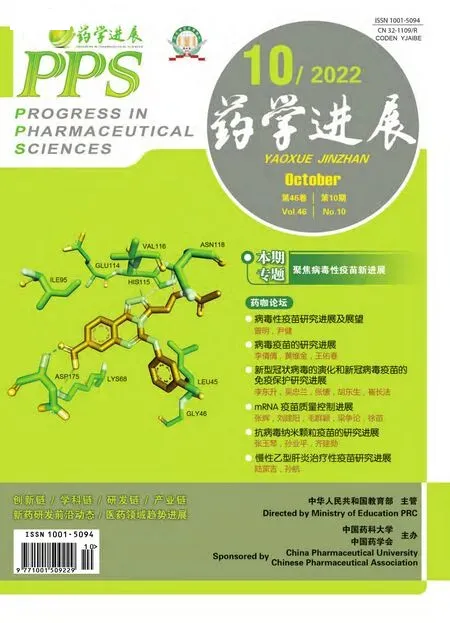病毒疫苗的研究进展
李倩倩,黄维金,王佑春*
(1. 江苏瑞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规划与预研部,江苏 泰州 225300;2.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艾滋病性病病毒疫苗室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制品质量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629)
病毒的数量庞大、种类多样,可通过呼吸道途径、消化道途径、身体接触或体液等方式进行传播。病毒的感染可引起人体多种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生。天花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登革热病毒(DENV)、狂犬病毒(RABV)、流感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马尔堡病毒(MARV)、埃博拉病毒(EBOV)、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1)、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等在人际间传播,均导致人类罹患严重疾病甚至死亡[1]。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出现和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在世界范围的暴发和流行,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回顾人类病毒感染史和传染病暴发史,可以发现疫苗在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3]。疫苗的研发和使用为人类健康构筑了一道免疫屏障,从而保护人类免受病毒的感染,甚至能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传染性极强的天花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等[4]。目前,已有多种类型的疫苗上市,可用来保护多种病毒的感染。然而,仍有部分病毒没有研发出相应的疫苗,而且部分已上市的疫苗也需要利用新平台、新技术进行更新换代[5-6]。
1 病毒疫苗的类型及其新技术
病毒疫苗的类型包括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蛋白疫苗、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等[7]。不同的疫苗类型诱导机体产生的免疫反应的强度、广泛性、持久性,以及免疫效应发挥的部位等均存在差异。其中,基因工程重组蛋白疫苗、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等类型具有可人工改造、快速构建等优势,在应对新突发传染病的暴发,以及高变异、多型别病原体的再感染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不同类型的疫苗研发和生产过程有所差异,总体上包括了抗原选择和设计、表达、纯化以及佐剂选择等,在此过程中新技术和新方法被广泛应用。未来病毒疫苗的设计,需要将病毒特性、机体免疫反应等前沿理论与新佐剂、新剂型、新技术方法等现代生物学技术相结合,从而实现新病毒疫苗的开发和迭代[9]。
1.1 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是一种传统的疫苗类型,通过化学或物理学方法处理天然病毒,从而得到没有感染能力,但保留病毒天然抗原表位的疫苗。通过离心和层析技术对灭活疫苗进行纯化和组分分离,灭活疫苗可进一步分为全微生物体灭活疫苗、裂解疫苗和病毒纯化亚单位疫苗。灭活疫苗具有安全性好、研发速度快、可同时递呈多个抗原等优点,但同时具有免疫原性较弱、诱导细胞免疫反应较弱、存在抗体依赖的感染增强(ADE)风险等局限性。在我国上市和在研的灭活疫苗,包括甲型肝炎(HAV)灭活疫苗、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PV)、乙型脑炎(JEV)灭活疫苗、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灭活疫苗、肠道病毒EV71型灭活疫苗、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RABV疫苗、森林脑炎灭活疫苗、SARS-CoV-2灭活疫苗、带状疱疹(VZV)灭活疫苗等。
在灭活疫苗的研发过程中,新技术和新方法主要集中于病毒灭活技术和纯化技术等方面。病毒的灭活一般采用化学法,常用灭活剂为甲醛和β-丙内酯。此外,双氧水和烷化剂(二乙烯亚胺、乙酰乙烯亚胺)等新的灭活技术,目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病毒悬液的澄清、超滤浓缩,以及各种层析纯化技术的发展,可进一步去除杂蛋白和DNA残留,从而提高疫苗纯度。
1.2 减毒活疫苗
减毒活疫苗指的是将病毒经过基因工程改造或其他方式处理和诱导,使得病毒的毒性基因缺失或改变,从而得到保留原有免疫原性,且能够复制的毒力减弱或缺失的疫苗[10]。根据减毒活疫苗的获得方法不同,减毒活疫苗包括来源于动物的弱毒病毒的减毒疫苗、经细胞或动物体内传代获得的减毒疫苗、经冷适应获得的减毒疫苗[11]、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病毒毒力基因缺失的减毒疫苗、基因重配病毒疫苗等。其中,基因重配病毒疫苗指的是将野生病毒和弱毒病毒一起感染细胞,在培养过程中野生病毒的表面抗原基因与弱毒病毒的毒力基因等进行基因重组,从而得到含野生病毒的免疫原性和弱毒病毒的毒力的基因重配病毒,适用于基因组分节段的病毒如流感病毒、轮状病毒(RV)等。减毒活疫苗具有可诱导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等全面的免疫应答反应,免疫原性好,免疫力持久等优点,但同时具有重组发生表型逆转而恢复其致病性等局限性。在我国上市和在研的减毒活疫苗,包括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OPV)、麻风腮联合减毒活疫苗、JEV减毒活疫苗、水痘减毒活疫苗、五价RV减毒活疫苗、黄热(YFV)减毒活疫苗、麻风腮-水痘联合减毒活疫苗、流感减毒活疫苗、HAV减毒活疫苗等。
在减毒活疫苗的研究中,新技术和新方法主要集中于病毒减毒方法的改进。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可实现减毒活疫苗可控的定向改造。在流感减毒疫苗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反向遗传学技术,通过对流感病毒基因组进行重组、对NS1基因进行截断[12]和密码子去优化[13]等方式,实现了流感病毒的定向改造。在OPV的研究中,为了降低减毒活疫苗神经毒力回复的可能性,研究人员对Sabin2病毒基因组进行了5处修饰和改造,从而得到遗传稳定的安全有效的2 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株(nOPV2)[14]。nOPV2的5处修饰和改造,包括5' 非编码区的2个修饰(cre5的重新定位和 S15domV的添加)、病毒2C编码区内部cre的同义突变、病毒3D聚合酶基因的2个突变(D53N和K38R),通过降低病毒的突变率和重组频率的方式,限制病毒毒力回复的可能性[14]。
1.3 基因工程重组蛋白疫苗
基因工程重组蛋白疫苗指的是通过基因工程方法,在原核和真核在内的各种表达细胞中,将病毒抗原蛋白进行表达和组装,从而得到的病毒蛋白疫苗。根据疫苗抗原成分和组装的差异,基因工程重组蛋白疫苗包括多肽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和病毒样颗粒(VLP)疫苗等。
多肽疫苗的研发依赖于对诱导病毒免疫原性的潜在靶点的清晰认识,其中重要的免疫原性位点包括T细胞抗原表位、B细胞抗原表位及病毒抗原决定簇等。在此前提下,使用基因工程方法,构建多肽片段的表达载体,实现不同多肽片段的表达和组合[15]。多肽疫苗的表达技术成熟,产品质量可控,但由于其氨基酸数量较少,诱导产生的免疫反应可能较弱。目前,虽然有多个病毒多肽疫苗进入临床试验,但尚未批准上市[16]。
重组亚单位疫苗利用重组DNA技术,将病毒抗原基因插入到表达载体后,在细菌、酵母、昆虫细胞、哺乳动物细胞、植物细胞等原核或真核细胞内进行蛋白表达[15]。重组亚单位疫苗具有成分单一,生物安全性好,研发流程成熟,易于大规模生产等优点。然而,重组蛋白的免疫原性较弱,需要在配合佐剂使用的情况下,通过多次注射来完成免疫程序。在我国上市和在研的重组亚单位疫苗,包括重组VZV疫苗、SARS-CoV-2重组蛋白疫苗(刺突蛋白或受体结合域蛋白)、重组流感病毒亚单位疫苗、重组呼吸道合胞病毒(RSV)亚单位疫苗等。
VLP疫苗是由病毒的一个或多个结构蛋白在表达平台中共表达或由体外混合的多个病毒结构蛋白,自发组装形成不含病毒遗传物质的病毒样蛋白颗粒[17]。VLP疫苗与病毒的立体构象相同或相似,表现出与天然病毒类似的抗原表位,因此可以通过与病毒感染相同的方式将抗原提呈给免疫系统,从而诱导出高效的特异性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保护。然而,由于只有个别病毒的抗原蛋白可以自组装出VLP,因此VLP疫苗类型的适用范围较差。同时和其他蛋白疫苗相同,VLP疫苗也需要在佐剂的配合下,通过多次注射来完成免疫程序。在我国上市和在研的VLP疫苗,包括乙型肝炎病毒(HBV)疫苗、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重组戊型肝炎病毒(HEV)疫苗[18]、SARS-CoV-2 VLP疫苗等。
在基因工程蛋白疫苗的研究中,新技术和新方法主要集中于基于病毒结构的抗原设计、纳米颗粒疫苗技术、蛋白表达平台的选择和优化等。近年来,随着病毒结构组学的发展,疫苗的抗原可根据病毒的结构进行设计和开发。以RSV疫苗为例,RSV的表面融合糖蛋白(F)作为主要抗原,具有融合前构象(pre-F)和融合后构象(post-F)。前十几年开发的RSV疫苗的抗原为post-F构象,研究表明该构象的疫苗诱导的免疫保护效果较差,而基于pre-F构象设计的疫苗诱导的中和抗体水平提高,为开发有效的RSV疫苗带来希望[19]。此外,纳米颗粒疫苗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不仅可显著提高疫苗的免疫原性和稳定性,还可实现靶向递送和缓释[20]。研究表明,含20个DS-Cav1三聚体的纳米颗粒RSV疫苗诱导的中和抗体反应比三聚体DS-Cav1高10倍[19]。另外,蛋白表达平台的不同会影响病毒蛋白的修饰,尤其是糖基化修饰的差异,从而导致基因工程蛋白疫苗的免疫原性有较大差异。高产酵母重组蛋白表达平台和昆虫细胞-杆状病毒表达平台被认为是低成本的可快速制造疫苗的技术[21],其中基于酵母表达平台制造了HBV疫苗和HPV疫苗(Gardasil),基于昆虫细胞-杆状病毒表达平台制造了重组流感疫苗(Flublok)和HPV疫苗(Cervarix)。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转基因植物细胞表达平台和无细胞系统作为疫苗生产的新技术,被应用于HIV疫苗[22]、流感病毒疫苗[23]、HAV疫苗的研究中。
1.4 病毒载体疫苗
病毒载体疫苗是一种新兴的疫苗类型,其病毒颗粒内部基因组经过基因工程技术改造,包含了一个或多个目的病毒的抗原基因[24]。病毒载体疫苗感染人体后,通过表达目的病毒的抗原蛋白,来诱导针对目的病毒的免疫反应。根据是否保留病毒载体复制相关的基因片段,病毒载体疫苗可以分为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和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25]。目前,多种病毒载体被应用于疫苗开发[26],包括无包膜双链DNA病毒载体[腺病毒(AdV)、痘病毒、疱疹病毒等]、无包膜单链DNA病毒载体[腺相关病毒(AAV)等]、有包膜的单股正链RNA病毒载体(甲病毒、黄病毒等)、有包膜的单股负链RNA病毒载体[麻疹病毒(MV)和水泡性口炎病毒(VSV)等][27],以及逆转录病毒载体和慢病毒载体等[28]。病毒载体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遗传可塑性,可诱发机体产生较强的细胞免疫反应,制备周期短,可实现快速放大。同时,病毒载体疫苗可用于呼吸道黏膜接种,从而有效抵御呼吸道病毒的侵袭。然而,机体可能预存有针对病毒载体的抗体,从而影响疫苗的免疫效果和适用人群。因此,病毒载体疫苗只适用于单次接种,而且可能会影响相同病毒载体的其他病毒疫苗的免疫效果。已上市和在研的病毒载体疫苗,包括新冠腺病毒载体疫苗[26]、埃博拉腺病毒载体疫苗[29]等。
在病毒载体疫苗的研究中,新技术和新方法主要集中于病毒载体的选择和改造[30],目前最常用的病毒载体为AdV和VSV。其中,AdV作为疫苗载体,具有宿主范围广,可选择血清型多,可诱导强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应答,以及可诱导产生黏膜免疫等优势[31],被广泛应用于SARS-CoV-2疫苗[26]和EBOV疫苗[29]的研究中。为了规避腺病毒载体的预存抗体问题,新冠病毒载体疫苗还选择了罕见的人腺病毒载体26型,以及非人类腺病毒如黑猩猩腺病毒载体等[32]。此外,VSV为单负链RNA病毒,基因组约11 kb,可外源插入4.5 kb的基因片段。通过基因重排或基因删除技术可制备出减毒VSV,同时外源插入基因稳定,表达水平较高,因此VSV病毒载体被广泛应用于EBOV[33]、MARV[34]、SARSCoV-2(VSV-ΔG-spike)[35]、RSV[36-37]、尼 帕 病 毒(NiV)[38]、拉沙病毒(LASV)[39]、基孔肯尼亚热病毒(CHIKV)[40]、寨卡病毒(ZIKV)[40]、HIV[41]等疫苗的研究中[42]。
1.5 核酸疫苗
核酸疫苗是一种新兴的疫苗类型,被称为第3代疫苗技术,包括DNA疫苗和RNA疫苗。核酸疫苗需要通过脂质体或电刺激方法,将疫苗有效导入到宿主细胞质中,进行蛋白翻译及翻译后修饰。核酸疫苗的抗原以天然形式进行呈递,可诱导机体产生高效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抗原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Ⅰ类分子途径激活CD8+T细胞,诱导特异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LT),产生细胞免疫应答。抗原通过MHCⅡ类分子途径激活CD4+T细胞,同时刺激活化B细胞,产生特异性抗体和体液免疫应答。核酸疫苗开发和更新所需时间短,并且没有病毒载体感染风险。然而,核酸疫苗的免疫原性和稳定性较差,对递送技术和产品运输环节的温度要求较高,并且技术标准尚不成熟,安全性有待进一步评估。
DNA疫苗的研发过程,包括表达载体的优化和构建,目的基因的改造和密码子优化,佐剂的选择,制剂过程的优化等。目前只有动物DNA疫苗上市,如马用预防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的DNA疫苗、H5亚型禽流感DNA疫苗等。目前尚无人用DNA疫苗上市,但在研的DNA病毒疫苗种类很多,包括SARS-CoV-2(INO-4800)[43]、流 感 病 毒[44]、SARS-CoV[45]、MERS-CoV[46]、HIV[47]、ZIKV[48]、裂谷热病毒(RVF)[49]等。
在DNA疫苗的研究中,新技术和新方法主要集中于DNA表达载体的选择和改造,以及递送系统的改进。DNA表达载体可以在大肠埃希菌中大量繁殖,其中抗生素抗性基因使得质粒可以稳定遗传。然而由于抗性基因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功能性序列,因此新一代的DNA疫苗表达载体删除或替换了抗性基因元件[50-51]。此外,研究人员还构建了不含细菌骨架的最小DNA表达载体,如半合成的小环DNA[52]和全合成的Doggybone载体[53]等。DNA疫苗必须通过内吞或胞饮作用穿过细胞膜,同时不被胞质内体、溶酶体和核酸酶降解,从而进入细胞核内进行表达。因此,DNA疫苗常规肌肉注射的效力很低,高效的递送系统对DNA疫苗在宿主体内的表达以及疫苗的免疫原性强度至关重要。目前,DNA疫苗使用最多的递送方法是利用基因枪、微针、体内电穿孔进行注射。此外,新兴的纳米颗粒技术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降解性,可包封DNA疫苗靶向宿主细胞,从而提高DNA疫苗的转染效率和免疫原性。纳米颗粒常用的材料包括含有阳离子脂质和胆固醇的脂质体,聚乳酸-乙醇酸共聚物、壳聚糖等可生物降解材质,以及聚乙烯亚胺聚合物等高分子聚合物[54]。
mRNA疫苗作为创新型疫苗类型,其制备工艺简单快速,易规模化生产,且免疫原性强,在应对COVID-19疫情中发挥了其他疫苗类型不可比拟的优势[55]。mRNA疫苗的构建、生产、纯化、佐剂等对于不同病原体是通用的,因此在一个成熟的设施中可以生产多种病原体疫苗,从而显著降低疫苗生产的成本和时间[56]。根据是否含有亚基因组启动子和编码RNA依赖的RNA聚合酶的开放读码框(ORF),mRNA疫苗包括非复制型mRNA疫苗和自我复制型mRNA疫苗。mRNA疫苗的基因序列包含5'端帽结构、5' 非翻译区(UTR)、目的基因ORF、3'UTR和3' 端的poly A尾等基本元件,这些元件对于产生稳定的成熟mRNA、延长mRNA的半衰期、增强mRNA的翻译等具有重要作用[24]。目前,已上市和在研的mRNA病毒疫苗,包括SARSCoV-2疫 苗(mRNA-1273、BNT162b2)[57-58]、流感病毒疫苗(HA mRNA-LNP)[59]、RSV疫苗[60]、ZIKV疫苗[61]、EBOV疫苗[62]和HIV疫苗[63]等。
在RNA疫苗的研究中,新技术和新方法主要集中于mRNA序列元件的改造、编码序列的修饰、递送系统的选择和改进,以及新型RNA疫苗的研发[64]。使用抗反向帽类似物(ARCA)修饰5'端帽结构,可提高蛋白翻译的效率和正确性[65]。同时研究发现,对mRNA疫苗的核苷酸进行硫代尿嘧啶、甲基胞嘧啶、假尿嘧啶等化学修饰,可减少固有免疫激活并增加mRNA的翻译[66]。此外,对mRNA疫苗的核苷酸序列进行密码子优化,可提高mRNA翻译的蛋白质质量[67]。目前,已有多种新型的纳米递送技术用于mRNA疫苗的递送,包括鱼精蛋白阳离子多肽递送技术、聚乙烯亚胺高分子聚合物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技术(LNPs)、基于MF59的纳米乳剂技术等[68-70]。然而,纳米递送技术的作用机制、安全性、质量可控性等仍需进一步明确和规范。除mRNA外,环状RNA(circRNA)也正在被探索作为疫苗的可能性[71]。在SARS-CoV-2疫苗的研究中,高度稳定的circRNA疫苗可诱导有效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反应,并且产生的中和抗体水平较高[72]。动物实验表明,使用脂质体包裹的circRNA疫苗免疫,可为小鼠和恒河猴提供针对SARS-CoV-2的强大保护[72]。基于Delta变异株RBD区设计的circRNA疫苗,可提供针对SARS-CoV-2变异株的广谱保护[72]。
2 病毒疫苗的研发难点
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流行性病毒疫苗和新突发传染病病毒疫苗的研发,以及现有病毒疫苗的更新换代,均存在各自的研究难点或瓶颈。研究人员可通过深入探究病毒的限制、机体免疫反应的限制、疫苗类型的限制、接种途径和递送系统的限制和佐剂的限制等,从中寻找出解决病毒疫苗研发瓶颈的有效突破口,从而实现新疫苗的研发和现有疫苗的更新。
2.1 病毒的限制
不同病毒发挥抗原作用的蛋白有巨大差异,例如冠状病毒的主要抗原为Spike蛋白,流感病毒的主要抗原为HA蛋白,RABV的主要抗原为G蛋白,RSV的主要抗原为F蛋白,HPV、EV71、脊髓灰质炎病毒等病毒的主要抗原为病毒的衣壳蛋白等。因此,合适的抗原决定了免疫应答的特异性和靶向性,对疫苗研发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自然界中的病毒十分复杂,抗原的选择和设计具有很大难度。一些病毒高度变异,不断进化造成对现有疫苗的免疫逃逸,如HIV、SARS-CoV-2等[73]。一些病毒具有多个亚型,并且各亚型之间的交叉保护较差,如HPV、DENV、流感病毒等[74]。其中,DENV的4个血清型之间无交叉免疫,同型别感染可实现终身免疫,由DENV引起的疾病在首次感染时具有自限性,但抗体依赖性增强效应会增加异型病毒第2次感染的死亡率,从而加大了疫苗的研发难度[75]。此外,一些病毒的抗原具有2个构象,如RSV的F蛋白具有pre-F和post-F构象,不同构象诱导的免疫反应不同,也加大了疫苗的研发难度[76]。此外,黄病毒和冠状病毒疫苗免疫可能造成机体产生ADE效应,严重阻碍和减缓了疫苗的研发进展[77]。因此,加强对病毒抗原的结构、功能、致病性、型别差异等基础研究,突破病毒抗原认识不清的限制,是病毒疫苗研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2.2 机体免疫反应的限制
机体的免疫反应是疫苗发挥作用的第一步,不同机体对疫苗的免疫反应类型和强度的差异,也导致了疫苗保护效果的差异。婴幼儿的免疫系统尚不成熟,在成人中免疫原性很好的疫苗,可能在婴幼儿中无法诱导适当的免疫反应[78]。在联合疫苗的设计时,要考虑婴幼儿免疫系统的可承受范围。另外,老年人的免疫系统退化,一些疫苗能在儿童或成年人中发挥保护作用,但却无法保护老年人群[79]。同时,疫苗研发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免疫缺陷人群和过敏人群,避免疫苗接种给机体带来的免疫受损或过激[80]。因此,深入研究不同人群的免疫系统差异,在疫苗研发过程中将目标人群的免疫系统特点加以考虑,是病毒疫苗研发成功至关重要的一步。
2.3 疫苗类型的限制
疫苗类型、疫苗表达系统均对机体免疫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也会诱导出差异巨大的免疫反应。疫苗的有效保护需要机体产生较强的特异性的中和抗体和细胞免疫,而非结合抗体和非特异性的细胞免疫。现有的疫苗类型均有各自的优缺点[81]。灭活疫苗和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仅能诱导体液免疫,而CD8+T细胞免疫反应较差。减毒活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较为全面,但是存在毒力回复的可能性,而且接种免疫缺陷人群免疫后可能不会较快被清除,在机体内存在较长时间。病毒载体疫苗能够诱导较为全面的免疫反应,但会产生病毒载体相应的抗体,影响相同病毒载体疫苗的再次使用。DNA疫苗的开发周期短、无需细胞培养,但其免疫原性较差。RNA疫苗具有较好的免疫原性,但是疫苗稳定性差、递送系统复杂、质控难度较大。随着mRNA疫苗在应对COVID-19真实世界中的良好表现,mRNA疫苗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疫苗开发平台。一些病毒使用传统疫苗类型无法开发出有效疫苗,目前也正在尝试mRNA疫苗类型,期待mRNA疫苗能够带来更多安全性和保护性满意的病毒疫苗[55]。因此,在病毒疫苗研发的初期,需要根据病毒感染、传播和致病特性的差异,选择和设计合适的疫苗类型,从而诱导机体产生能够遏制病毒感染的免疫反应。
2.4 接种途径和递送系统的限制
疫苗接种途径多种多样,包括肌肉注射、皮下注射、皮内注射、口服、鼻腔吸入、经皮免疫[82]等。不同的接种途径诱导的免疫反应强度、广度、部位等有很大差异,原则上疫苗接种途径与自然感染途径越相似,疫苗诱导的免疫保护效果就越理想。黏膜免疫是抵御呼吸道病毒和肠道病毒侵袭的第一道防线,在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中均发挥重要作用[83],机体能否产生足够的黏膜免疫是呼吸道病毒和肠道病毒研发的重点。因此,虽然现有的疫苗接种途径多为注射方式,但肠道病毒的减毒活疫苗通常通过口服途径接种,呼吸道病毒的减毒活疫苗和病毒载体疫苗通常通过鼻腔吸入途径接种。目前,HBV疫苗、RABV疫苗、HPV疫苗等通过肌肉注射接种,MV疫苗、JEV疫苗等通过皮下注射接种,卡介苗、牛痘疫苗通过皮内注射或划痕接种,OPV疫苗、口服RV疫苗等通过口服途径接种[84],鼻喷流感病毒疫苗等通过鼻腔吸入途径接种。注射接种途径可能造成疼痛、交叉污染等问题,因此非侵入性免疫接种是目前的研究热点[85]。非侵入性免疫接种途径可减轻或消除疼痛,但是也有很多限制因素。疫苗口服接种后,需要经过胃的酸性环境,然后在肠道中发挥免疫作用。在此过程中,很多抗原失去功能,可能导致抗原浓度过低,不足以诱导有效的免疫反应的情况[84]。鼻腔吸入可通过干粉吸入器和喷射雾化器来实现,因此对喷入器械、雾化方式、加压系统等有较高的要求[86]。
纳米颗粒递送系统的开发和研究,促进了重组蛋白疫苗、DNA疫苗和RNA疫苗的使用[87]。目前用于疫苗的纳米颗粒,包括脂质纳米颗粒(LNPs)[88]、聚合物纳米颗粒(含壳聚糖、葡聚糖等)[89]、蛋白质纳米颗粒(含铁蛋白、丙酮酸脱氢酶等)[90]、无机纳米颗粒(含金、铁、二氧化硅等)[91-92]和仿生纳米颗粒(含细胞膜、精氨酰甘氨酰天冬氨酸修饰等)[93-94]等。不同类型的纳米载体在体内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特征和行为,从而相应地影响疫苗的免疫效果。其中,LNPs递送系统的成熟,使得新冠病毒mRNA疫苗的批准使用成为现实。此外,微针递送系统的发展使经皮免疫途径成为可能,通过微针免疫的体液免疫与皮下注射相当[85]。目前的微针类型包括实心针、空心针、药物涂层针、溶解针和微针阵列等,被应用于MV疫苗[95]、腺病毒载体ZIKV疫苗[96]、灭活RV疫苗[97]、IPV疫苗[98]、天花DNA疫苗[99]中。因此,疫苗接种途径的选择和递送系统的开发,可实现病毒疫苗的最优免疫保护效果。
2.5 佐剂的限制
佐剂可增强和调节疫苗引起的免疫反应的强度、广度和持久性,对于提高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等免疫原性较差的疫苗类型的保护力至关重要[100]。佐剂通过促进抗原提呈细胞缓释和摄取、激活注射部位的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激活Toll样受体、调节辅助T(helper T,Th)细胞(Th1/Th2/Th17)免疫应答的平衡等方式,触发和调节机体的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反应[101]。然而佐剂的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仅有氢氧化铝佐剂(HBV、HPV疫苗等)、MF59佐剂(三价流感灭活疫苗Fluad)、AS01佐剂(VZV疫苗Shingrix)、AS03佐剂(大流行性流感疫苗Pandemrix)、AS04佐剂(HPV疫苗Cervarix)、CpG1018佐剂(HBV疫苗Heplisav-B)等应用于疫苗中[101]。因此,佐剂作用机制的基础研究,以及低毒性、高效力的佐剂使用许可,是病毒疫苗研究的瓶颈之一。
3 需加快研发的病毒疫苗
3.1 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流行病毒疫苗
世界范围内许多广泛传播和流行的病毒,如HIV、RSV、DENV等,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但利用传统方法尚未研制出针对上述病毒有效的预防性或治疗性疫苗,因此研究人员正尝试研发基因工程蛋白疫苗、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等新型疫苗类型。其中,HIV疫苗设计的目标是诱导产生能够识别一系列不同毒株的广谱中和抗体和功能性T细胞免疫反应[102]。利用生物信息学设计的多价嵌合马赛克疫苗[103]、新型病毒载体疫苗(Ad26、Ad35、CMV)、重组可溶性Env三聚体蛋白疫苗[104]、基于Env gp120和Gag结构蛋白设计的mRNA疫苗[105-106]等在动物模型中表现出巨大潜力,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107]。同时,RSV的发现已超过60年,但目前仍无有效的疫苗来预防RSV的感染[108]。目前,基于RSV pre-F蛋白的mRNA疫苗[60]、重组Ad26病毒载体疫苗[109]、重组亚单位疫苗[110]等的临床试验显示出了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以及对F蛋白特异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另外,全世界每年均有上千万人感染DENV,波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唯一获批的四价嵌合黄热病毒-登革热减毒活疫苗(CYD-TDV)的长期随访发现,DENV未感染人群接种后发生严重登革热和住院的风险均有所增加,因此迫切需要更安全、更有效的第2代登革热疫苗。目前,候选疫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价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和mRNA疫苗[111-112]。除了预防性疫苗外,对于那些容易引起慢性、持续性感染和诱发肿瘤相关的病毒,应加快研发针对此类病毒的治疗性疫苗,如:乙肝治疗性疫苗[113]、宫颈癌治疗性疫苗[114]、艾滋病治疗性疫苗[115]、鼻咽癌治疗性疫苗[116]等。
3.2 新突发传染病病毒疫苗
近些年来,许多传染性疾病由野生动物宿主外溢到人类群体中,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公共卫生压力。尽管已研制出许多人类疫苗并投入使用,但传染病仍然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尤其是新突发传染病的暴发[77]。在对抗新发突发病毒中,重组蛋白疫苗、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等新型疫苗平台,比传统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的研制快捷,并且通常诱导的免疫反应更具有保护效力。一旦疫苗平台满足了安全性和有效性要求,针对新突发病毒只需替换相应抗原基因,便可用相同的系统进行生产和纯化,进一步简化疫苗的研发进程。因此,为了应对丝状病毒(EBOV[117]和MARV[118])、沙粒病毒(LASV[119])、副黏病毒(NiV[120]和亨德拉病毒)、黄病毒(DENV[121]、西尼罗河病毒WNV[122]、ZIKV[123])、披膜病毒(CHIKV[124])和冠状病毒(SARS-CoV、MERS-CoV[125]、SARS-CoV-2)[126]等的突发和流行,亟待相应病毒的疫苗储备。
4 结语
目前,伴随着生物工程新技术和疫苗研发新平台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前沿技术的交叉融合和多平台的协作共进,病毒疫苗的设计思路和病毒载体等得到了快速发展和更新。同时,病毒疫苗的研发取得许多重要的突破,也推进了创新型病毒疫苗的研究进展。本文归纳总结了病毒疫苗的众多类型以及病毒疫苗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指出了需加快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流行病毒疫苗和新突发传染病病毒疫苗的研制。因此,加强和加快对病原体、机体免疫反应、疫苗类型和新技术、佐剂等的基础研究,是应对新发、突发、高变异、高难度病毒疫苗研制的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