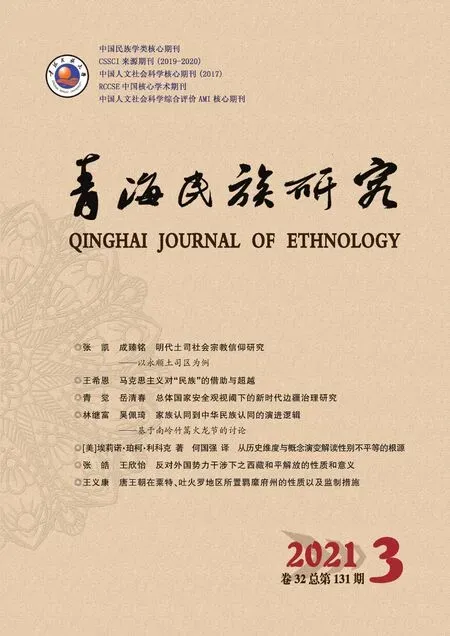永锡难老:重思晋水流域调查
张亚辉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金光亿先生让我们这些学生辈的年轻人重新思考自己的第一本民族志,对于忙于项目和发表论文的中青年学者,无疑是当头棒喝。这让笔者想起了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施耐德,他在博士毕业二十年后带领自己的学生重新回到雅皮斯人那里做田野,并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笔者大概是没这个勇气的。做完博士论文之后,笔者几乎很少真正涉足汉人社会研究,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藏族社会和人类学理论研究上,但金先生是对的,笔者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远离《水德配天》这本书,一直在暗自否定它、重构它,可能不会真的重写它,所以这篇短文权且算是一个无奈的替代品吧。如果说反思,可能主要的感受是当时笔者对西学当中的社区方法如何构成一种整全叙事其实并不了解,因此真的将民族志写成了村落或者流域社会的经验研究。经过这些年的沉思,笔者才逐渐明白了如何在汉人语境下将具体经验与宏观结构联结成一个整体。
本文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重新思考《水德配天》的主要对话对象魏特夫的社会理论,一方面指出人类学用小型水利社会的材料来反驳魏特夫的理论所导致的错位与无力感,另一方面则基于自身的材料,指出对儒家官僚的封建性格的理解,尤其是唐宋变革前后的转变,是走出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现象学窠臼的关键。第二,重新分析了晋祠的宗教系统的政治意涵,与《水德配天》中的社区研究视角不同,将唐叔与水母的传说联系到中国历史的宏观结构及其变迁机制上来。第三,延续近几年对印欧共同体与汉人村落的比较研究,尝试指出水权的物权性质与《罗马法》物权的差异,以及中国政治的家族主义传统如何从先秦时代开始通过等级衰降一路延续到今天。
一、水利社会与封建制度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出版于1957年,实际上最初将这一理论用于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家是卡拉斯科,他在《西藏的土地与政体》当中将魏特夫关于西藏的论述扩展成了一本专著,[1]但在中国人类学界,这本书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反馈。中国人类学界关注魏特夫的水利社会理论,是从萨林斯和格尔茨的著作开始的。萨林斯在20世纪70年代组织了一个项目前往夏威夷进行调查时,特别关注了夏威夷的水利事业,一部分成果后来作为专著发表在了《流动的权力》当中。夏威夷的水利社会状况显然极大影响了萨林斯的判断,使他得出了“国王过着整个部落的生活”这样极端的结论[2]。萨林斯同时也带动了对霍卡王权理论的再研究,在霍卡看来,王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而不是整个政治结构的奇点。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格尔茨在对爪哇的调查中关注到了当地的灌溉社会,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的剧场国家》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力求证明水利在当地并没有导致专制主义。[3]当然这一论述也招来了本地学者以及巴特(Fredrik Barth)的批评。我觉得格尔茨对巴厘岛村落体系的描述充满了一种矫揉造作的客观主义带来的故弄玄虚感,这点甚至从他写作《巴厘人的村庄》(Tihingan:A Balinese Village)的时候就开始了。实际上,他所谓的“多元的集体主义”是由自然社会的法权系统庄社、宗教结社行为和土地交换的后果造成的毗邻土地的所有者共同用水的水会组织叠合而成。在这种组织情况下,庄社获得了近乎绝对的自治法权,只通过官方祭祀与国家相连,而稻田的高级产权几乎总是属于贵族,低级产权属于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和庄社无关,同一个贵族的土地可能分布在很多地方。这种所有权情况显然在农业社会并不十分常见,但在谷苞先生所研究的呈贡化城乡就有类似的状况,而在土地可以买卖的传统社会,则是再常见不过的情形了。由于土地转卖——或者其他什么可想见的原因——水利组织就变成了完全的经济设施而与政治脱钩了。虽然格尔茨利用这个材料来回应魏特夫对巴厘岛的分析是必要的,但就这个研究自身来说,他对魏特夫的回应甚至都是多余的。
利奇关于斯里兰卡的民族志《普尔·埃利亚:一个锡兰村庄的土地保有制与亲属制度研究》(Pul Eliya,A Village in Ceylon:A Study of Land Tenure and Kinship)也涉及到了干旱地区的水利问题,他将水利设施区分成控制在村落手中的小型水利设施和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的大型水利工程两种,并且充分论证了前者是一种区域自治社会的产物。[4]即便如此,也有本土学者争论说,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其实都是数百年间逐步累积而成,并不存在专制主义过度发育的情况。
水利灌溉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更是毋庸置疑的。就在《东方专制主义》翻译成汉文出版后不久,中国社科院就曾经组织了一批专家专门批判过这本书,这本批判文集就叫做《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5]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光直先生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中就力图与魏特夫的理论进行对话。[6]但就我个人而言,这些不论是经验的还是理论的反驳都不令人满意和信服,主要的原因出在魏特夫对中国史的判断是来自韦伯,后者认为中国的家产制帝国起源于秦,秦以前的社会是一个军事贵族战乱不休而且充满活力的松散帝国。[7]而张光直先生直接诉诸商代文明的起源,实在不怎么相关。在经验研究层面,利奇所作的分析在经验上无疑是适用于中国的,历史上所有著名的水利工程与区域社会的小型水利工程的区分都毋庸置疑,但这种表象提供的解释可能与汉人政治系统的内在逻辑相去甚远。事实上,魏特夫的水利社会用一种完全现象学的观察取代了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分析,这种障眼法如此之成功,使得所有力图跟他辩论的人都被事先纳入到了他的论证逻辑当中。利奇和格尔茨提供的“小型水利社会”并非可靠的路径,按照魏特夫的逻辑来说,这不过是被统治者容许的一种状态而已,在必要的时候随时都可能被纳入专制主义的轨道当中。这也是我对格尔茨的德萨研究持比较严厉的批评态度的原因,他完全放弃了种姓法和共同体法对庄社的保护意义,为了构建一个看起来更加经验主义的模型,他模糊了严肃的法权边界。
杰克·古迪(Jack Goody)一生致力于将传统非洲政治制度与欧亚大陆的政治做比较,后者高度发达的农业在他看来是造成欧亚大陆等级制发达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种扩大化的“东西方专制主义”并不会缓解魏特夫的论述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我几乎是出自一种土著的责任感,觉得自己必须跟魏特夫较量一番。从古迪的逻辑出发,灌溉农业就成了欧亚大陆的普遍条件,那么逻辑的重心就从水利社会转变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比较。事实上,魏特夫真正的落脚点也并非水利制度的直接影响,而是基于对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国过度早熟的文官制度的比较形成的。在这一点上,他和韦伯及列文森的区别都很小。我当时已经意识到格尔茨研究的巴厘岛是一个带有封建性质的社会,也从中国水利史的阅读中了解到最初的水利工程事业都是在战国时代的诸侯混战之竞争压力下才出现的,比如郑国渠、都江堰等等。如今回忆起来,我当时虽然认识还不够清晰,但也算是意识到小型水利工程和封建逻辑的结合是否是一个普遍问题,是在中国回应魏特夫问题的关键。彻底否定秦以来的专制主义既没可能,也没意义,实际的问题是,专制主义是否已经发达到“全面的恐怖—全面的孤独”[8]的境地,使得其他政治形态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或者说,在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结构当中,专制主义的位置及其限度在哪里。
关于这一问题,韦伯和列文森一方面认为文官制度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家产制官僚而提供了绝对专制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的儒家官僚的理想并非如埃及或者拜占庭帝国那样来自对王权的绝对崇拜,[9]因而构成了与专制皇权的对张关系。这样一个完全靠俸禄生活的群体,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并不如想象得那么融洽,他们不论对于国家还是社会都是一群高蹈的客,儒家知识分子集团并不像德鲁伊祭司、婆罗门或者犹太教的拉比那样是社会结构中的固有环节,他们的社会学位置甚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帝国的官僚,后者往往是家境殷实的有产者或者是被社会选举出来的代表。儒家的地位更像是中世纪大公教会神职人员,他们的知识高妙而令人敬畏,他们除了一套学说之外谁都不代表,他们在古典文明奠定自己的结构时并不存在,但在旧贵族湮灭之后,他们又成了新兴结构的把控者。乔治·杜比认为,大公教会取代了罗马国王的祭司地位,成为中世纪欧洲“三重秩序”的第一重,[10]这个看法招来了杜梅奇尔的批评,[11]后者认为大公教会所获得的位置应该和爱尔兰的布雷亨群体差不多。无论如何,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日耳曼人长久以来就已经存在武士—祭司的二分法。这一二分法在汉人文化当中显然并非是一个基础结构,略去一切历史细节不说,儒家最初似乎应来源于周代封建制度下封建法和封建礼仪(欧洲和日本的封建法和封建礼仪同样是不分的)顾问群体,在旧贵族存在的时候,这个顾问群体就是由客构成的。在秦汉法的格局下,儒家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而在东汉豪族政治兴起之后,儒家与之结合在一起,对抗法家的实利主义政治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实际上,在中国政治的氏族主义在唐宋变革时趋于式微之前,儒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官僚制度的基本性格是非常可疑的。宋以后豪族势力再难重振,才使得皇权和儒家都松了一口气,后者转而和民间宗族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即便魏特夫所说的专制主义确实和官僚制度有关,至少在秦汉更多是法家该负责任,①唐宋变革之后才该儒家官僚负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包括韦伯和列文森的观点都有值得商榷的空间。不论经过多少改造,儒家的这种封建性格其实从来没有彻底消失过,韦伯说儒家帮助皇权对抗封建势力,更深的原因是儒家认为后来所有的封建形态都不符合自己的封建理想,因此是对政治更为严重的败坏。反过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有停止寻找自己的同盟者,而且儒家的社会学洞见在于,他们从不相信从皇权那里衍生出来的封建形态,而是敏锐地意识到真正有社会基础的封建力量是东汉之后的豪族和宋以后的民间宗族。
二、晋祠诸神
晋祠的主神位在宋以前无疑是唐叔虞,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唐叔虞的册封有三个相关的历史或者神话,其中“剪桐封弟”是最符合我们通常所理解之周代封建制度的,而另外两个,一个是“有文在手”,大致是说,邑姜梦到上帝对她说,我将赐你一子,名字叫做虞,等到唐叔出生的时候,手掌心上确实赫然有一个虞字;[12]另一个是“嘉禾入贡”,大致是说,唐叔在自己的封地里发现了一株奇异的禾苗——根部在不同垄上的植株结出了共同的禾穗,便将其入贡给周成王,成王将其送给了周公,周公因此作《归禾》。前者确认了唐叔虞的卡理斯玛并不完全来自周王室的分封,而是来自其母邑姜梦与神交,连名字“虞”也是天帝直接写在他手上的;后者则表明,不同地望即不同根系,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最终因为同一果实而联结成一个整体。顺便说一句,我个人一直觉得,这才是多元一体格局的本意。要敢于承认不同地望和不同民族的差异,最终的嘉禾才可能更加丰硕,而不是非要强调大家同源同种——同源同种反目成仇的比比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的事实,而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甚至周天子与周公和唐叔虞的血亲关联都无法克服地望带来的多元性,也没有以血亲关系作为多元性的基础。此中深意,颇值得今日学者思之。
直到北宋征服北汉之前,唐叔虞都是一个鲜明的封建符号,甚至唐王室本身也是从这一封建系统当中成长起来的。晋祠历史上留下的秦汉到唐的史料并不多,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尤其是在东汉到北汉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是以豪族封建制度为主,而不是简单的郡县制。豪族兴起的原因一言难尽,杨联升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豪族兴起之原由,[13]杨先生似乎将之归咎于汉武时宰相权力衰微所导致的外戚与宦官集团的崛起,以及选举制必然带来的门生故吏结党。这些历史事件看起来都并非偶然,杨先生所列历史之因恐怕无非是结构之果。另外,杨先生所举皆是东汉的土地贵族,但氏族主义在中古的复兴至少从三国时代开始,就多是武士贵族,其中因果纠葛一言难尽,但究其实,汉代至三国豪族兴起,其影响一直波及到唐末的根本原因是公法之欠发达而导致的私法当政,这一弊病其实始终伴随着中国的政治,近代以前未有彻底之改观,是为费孝通先生所谓“差序格局”之私法盛行之状。唐宋变革之后,儒家官僚彻底把控了政治,武人精神之衰落再无从振奋,皇权由此达到集团之顶峰,惟元清两代,官僚和皇权都对本族贵族之势力尚有忌惮。而民间社会仍旧无从整合到国家公法之内,遂有民间宗教之封神大兴,及平民宗族之发育。所以,晋祠在宋代初年将主神从唐叔虞更换为晋祠圣母,其大背景并不只如笔者曾经在《水德配天》一书中所说的北宋王朝对于太原城及其周边社会的不信任,而是整个国家政治格局大转变的结果。笔者在书中曾经引用过高汝行的话来表达儒家对北汉政权合法性的认可,[14]这也表明,从周代的贵族封建,到唐初李渊任唐国公,再到北汉政权,唐叔虞都是此次基于武士集团之封建政体的根本依据。而到了宋代初年,这个逻辑不再被承认了,晋祠成为圣母的庙,表达的是宋以后的平民宗族世界的新的封建逻辑。其实,这一替换也发生在泉州,顾颉刚在《泉州的土地神》一文中也发现了作为封建之标志的社神在泉州地方神庙中从正祀神灵退居为配祀神灵的机制[15],但因此认定历史上有封建逻辑是一回事,而顾颉刚认为诸如临水夫人一类的神灵纯粹是当地人为灵验之故而自由想象的结果并最终超越了土地神作为“社神”的地位,则未免草率。只要看看妈祖的传说时代,就不难理解,泉州土地神的衰败与其他神灵的出现大抵上都和唐宋变革有着实质的联系。
笔者的田野进行得并不顺利,早期的土地分配制度已完全没了踪影,包括水利系统也已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甚至难老泉都已经干涸了,如今我们看到的难老泉是用水泵抽水造成的人工泉。笔者有一次在晋祠博物馆里面过夜,眼看着难老泉在天快黑的时候慢慢安静下来,觉得无比诡异。好在晋祠的文献资料保留得相当完好,而且当地有一个极为发达的文人团体,不断尝试对文献进行各种分析和解读,由于常年浸淫在当地的历史文化环境里面,这些解读反而格外有意味。笔者穷尽了所有的地方文献之后,发现自己并不能在格尔茨的巴厘岛水利制度之外有什么像样的进展。除了能够再次证明区域社会自己办的水利工程并不支持东方专制主义之外,做的最多的反而是文献的考订和解读,这让笔者很是沮丧。吴世旭、陈乃华和舒瑜曾邀笔者一起去五台山看看,因忙着自己的田野工作,没有去,这成了一个心结;多年之后,笔者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终究还是在五台山上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现在想来,那时还是视野太窄了,如果那时笔者读过李安宅和于式玉先生对佛教名山研究的设想,没准就真的会去看看。
后来去太原的省博物馆查档案时,笔者在旁边的一个小书店买到牟宗三的《周易哲学演讲录》,相比于艾兰的《水之道与德之端》以及巴拉什的《水与梦》,牟宗三基于胡煦易学的解读方式不论对我来说还是对晋祠来说都更为亲近。牟宗三关于乾元四德的分析恰好与汉人社会极为常见的黑龙—白龙的对反关系相对应。笔者后来在一篇文章当中曾经分析过,晋祠水母的故事其实就是黑龙—白龙关系的变体,但在这一分析当中,笔者对水母的“孝行”的分析过于单调了。在水母神话当中,单纯的孝行反而是和“缺水”相互关联的,不论是水母柳春英担水还是她婆婆只要扁担前面的水而不要后面的水,都是跟“缺水”有关系的。这也就意味着水母柳春英是脱离了“孝”的范畴而进入到形而上学。这一点笔者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但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韦伯的理论当中,中国政治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家产制的恭顺”,[16]而在水母的故事当中,最终的结果是婆母在柳春英制造的洪水中淹死了。所以也就是水母这一层的形而上学切断了家产制恭顺与国家的联系,礼下庶人很大程度上跟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阎若璩考证晋祠圣母的身份是邑姜,固然将晋祠社会与国家正统联系得更加紧密,但即便如此,邑姜因为有文在手而生唐叔虞,后者跨过了周天子而与上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由此我们也能看到,嘉禾的隐喻是基于天帝形成的。唐叔和水母的神话共同肯定了中国的分封制度并非基于亲属制度,当然也不是如西欧封建那样基于自由采邑制的纯粹社会学关系,而是以地望的等级性为根基,亲属制度则是传递这种分封系统的凭藉而非其源头和依据。宋代以后,随着北汉政权的瓦解,民间宗教与封建的关系逐渐成为确认新的封建类型的依据。这一封建类型被历史学彻底忽视,也被魏特夫忽视了,因此才导致他在东方的官僚制和西方的封建制之间建立起了过于直白的对反关系。
民间宗教中的主神作为被分封的主体是中国宋以后的典型封建形态,当然这一形态并非汉人所独有。希腊城邦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崇拜和供奉的英雄,西方中世纪的城邦也都有着自己的主保圣人,几个城市争夺一个主保圣人的骸骨的事也屡屡见于历史文献。民间神封建的方式将巫术共同体与封建制度完整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晋祠地区,唐叔虞神几乎是没有任何巫术色彩的,而来历不明的圣母则一方面是巫术的总源头,另一方面又是水权的所有者。两位神的综合基本上可以覆盖先秦时期地望的宗教与政治内涵。顺便说一句,不论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总是免不了注意到中国宗教的功利主义特征,比如在履行了所有的仪式义务之后,如果仍旧不能求下雨来,曝晒龙王像几乎是汉区的普遍现象。但实际上,同样的情况也曾经出现在天主教当中,意大利老太太朝圣母像吐口水并非罕见的现象。莫斯也因此认为,与神灵的交换关系是所有宗教崇拜的基础之一。但实际的情况可能仍旧出在对神灵的分类上。我从未在晋祠遇到过任何有关当地人对唐叔虞和圣母表示不满的情形,但对龙王的不满就比较常见。甚至在希腊和罗马的材料当中,也几乎不会出现对城邦主祭神灵的基于交换关系的抱怨。所以,可以被惩罚的神灵是基于交换关系的,而不可被惩罚的神灵则更多是基于神对人的所有权,这恐怕在全世界都差不多,并非中国人独有的宗教特征,所以能够进入地望的社会学与政治学范畴的,才是民间宗教的核心,其他的大多不过是被呈现为交换关系的巫术实践。至于地望本身的巫术性,总体上是属于政治的巫术性,而非来自自然社会或者个体与集体表象的巫术。我后来在涉藏地区的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神山和佛、菩萨都不是基于交换的,但村落嘛尼房子里面供奉的护法神就是基于交换关系的,如果不能尽职尽责,就会被村落里的耆老咒骂和羞辱。在《皇权、封建与丰产——晋祠诸神的历史、神话与隐喻的人类学研究》[17]一文当中,我曾经指出,元中叶以后的唐叔祭祀一直是由儒家官僚来主持,而明代遣官祭祀时候,来的总是太监,而祭祀对象也总是晋祠圣母。这一分别清晰地表明了文人官僚与国家对封建问题的态度差异,前者坚持了周代分封制度的合法性,甚至将这一态度延伸到对北宋征伐北汉一事的判断上,当地文人高汝行就曾经强调,古太原城的人之所以对抗北宋政法,是因为担心北汉王室从此不得血食,而北汉是通过正当途径得到其政权的。对于圣母为“封神”的封建制度,儒家官僚一向是嗤之以鼻的,从阎若璩装模作样的考据来看,这个矛盾至少在清代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严格说来,唐叔虞的神格之所以在北宋征服北汉之前就得以保留,根本原因在于他自身就属于唐宋变革之前的社会与政治组织,主神位的变化并非由具体的历史原因引起,而是由中国历史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从周代到唐末五代,虽然社会制度屡经变迁,但总体上仍旧是由武士阶层作为社会的主要担纲者——只有东汉是个不小的例外。不论周代封建还是魏晋封建,其分封制度总是以武士家族主义为基础,巫术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地望,且同样由受封家族所控制。唐宋变革之后,社会的担纲者从贵族群体转变成了区域地方社会,望族地位急剧衰落,巫术作为界定地方社会的基本尺度变成由地方社会供奉的主神而非贵族世系作为担纲者。明初改革,要求各地方神只称山水本名,曾经被屡屡加封的晋祠圣母被重新命名为晋源之神,其意义就在于将地望的巫术和神灵的巫术统合起来,作为界定区域社会的象征。
就元明以后的政治架构来说,儒家官僚的态度在实践上其实并没有太过实质的社会学意义,但也不能只将其看作是一种遗存或者是心绪的表达。当其与明代的“封神”制度相对抗时,儒家对唐叔虞的封主地位的坚持构成了对皇权通过封神与地方社会直接建立联系的新做法的反抗,一方面维系了地方分权的政治架构,另一方面则保留了儒家对社会的主张,虽然这一主张几乎没有实践的机会与空间。这两种封建制度之间的张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所谓“礼下庶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其中充满了皇权与儒家官僚系统之间的矛盾与对抗。
晋祠里面有一个我在《水德配天》当中没有太重视的庙,叫做台骀庙,里面供奉的是五帝时期治理西北水患的台骀,他同时也是汾河的水神。关于这个神灵的文献不多,民间除了知道他曾经治理汾河、开辟太原之外,也少有提及。中国古史中这样的治水神并不多,台骀神在山西好几个地方都有建庙祭祀,但历代王朝似乎都并不十分重视,这和魏特夫的假设之间有着不小的张力。更有趣的是,元好问的《过晋阳故城书事》一诗中有载:“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其中的系舟山指的是晋阳城以北的一座小山,传说为大禹治水过晋阳一带停靠船只的地方,赵光义征伐北汉时为了破坏晋阳城的风水,曾经命人削平了系舟山,号称是拔龙角,以防止当地再出帝王。大禹治水无疑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伟业,他在将滔天洪水导向大海的同时,也将尧舜之王化与地方世界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联系,其具体方式就是通过划定地理区域并在各个区域中建立祭祀空间,并将其与圣王相关联。系舟山虽然并没有被官方祭祀的记录,但无疑仍旧起着将晋水地方与圣王传统相互联系的作用,而且,龙角一说似乎意味着,每个大禹过化之地都可能成为龙兴之所,因而,削平系舟山不只是风水所致,更是政治结构变化的结果,赵宋朝廷不再接受大禹所制定的中央—地方关系模式,转而要通过暴力征服和建立新的官方祭祀的方式来重新完成国家统合。
三、村落与家族
当燕京学派将中国的农村看作某种中国式的“共同体”,并将之命名为“社区”的时候,并非没有犹豫,林耀华先生的《义序的宗族》显然和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理论取向,前者更靠近罗马的亲属制度研究的路径,尤其是南斯拉夫人的札德鲁加,而后者则更像是凯尔特人的共同体。社区或者说“共同体”,其基本的经验原型来自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印度人的基层社会组织,其基本特征是共同体的法权系统的高度完善性与独立性,亲属制度已经被完全法权化。社区是一种典型的印欧社会基层组织,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否存在并不确定。比如在广袤的澳洲大陆,印第安人的基础社会形态是队群与部落,在犹太人早期社会中是父系宗族,在阿拉伯人那里则是父系宗族与部落制度的结合。燕京学派在处理村落的时候,似乎只有谷苞先生在云南滇池边上的汉人社会中找到了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而在费先生及其他人研究的个案中则更多是“差序格局”。费先生将礼治秩序等同于这种社区的法,并认为这构成了一个不同于国家法的独立司法领域,从而产生了法隔离,而法隔离则进一步促成了无讼的现象。[18]纯粹意义上的差序格局是只有私法而没有公法的一种状态,但礼本身就包含了处理公共事务的部分——比如著名的乡饮酒礼,所以这其中并非是完全没有张力的。换句话说,在汉人社会研究中,基于宗族制度的东南汉人研究和基于小家户制度的社区研究的内在张力在于,前者希望亲属制度能够同样承担法的功能,而后者则对亲属制度对公法的干预充满疑虑,认为汉人的亲属制度并未如印欧人那般转变成法律,但同时又期待家户之间的协商机制能够承担完整的共同体法权精神。大量的民族志作品证明,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实际上也需要注意到,东南汉人村落同样存在超越宗族的村庙系统,也就是顾颉刚所看到的社的传统,单纯以世系群理论来处理东南汉人社会是不够的,但宗族本身的律法化发展确实使其不同于北方汉人社会。北方汉人社会虽然经济单位几乎总是小家户,但实际上聚族而居并非罕见,在晋水流域,只有北大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祠堂,但这个祠堂反映出来的问题则是,宗族仍旧有着实质的社会学空间。我调查的小站营曾经是个屯军村落,一共有七个姓氏,其中姚姓几乎完全萎缩了,武姓则是大姓,小站村的白姓也是大姓。由于没有祠堂,族谱即使有也很少起到东南汉人社会那种政治与社会作用,但我亲眼见到的则是在村落选举中,同姓宗族会突然间浮出水面,在选举竞争时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个经验让我意识到,单纯以经济或者祖先崇拜来界定宗族恐怕是不够的,在小站营村,几乎看不到像样的集体祖先祭祀意识,但丝毫不意味着宗族在政治利益面前的团结受到影响。
结合魏晋以来的门阀氏族经验来看,我倾向于认为,宗族其实是中国政治的根本载体,其本身也是政治过程的产物。沿着这个脉络,可以把中国政治的家族主义区分成三个时代:从周到秦,是真正意义的贵族家族主义时代,其核心特征是军事贵族与地望的结合以及严格的宗法制度;经过西汉的过渡时期之后,东汉的豪族一直到唐末的世族,包括南渡的大族,我们可以称之为世族时代,其核心特征是后起的土地或者军事贵族凭藉一种实利主义精神或者政治支配权和掌控知识的能力,同时大部分时期都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唐宋变革之后,世族几乎彻底消失,平民宗族兴起,其形态不一而足,但总体上都被去军事化了,北方宗族的政治色彩更重,而南方宗族一方面注重科举——直到现在南方宗族仍旧花大力气奖励进学,另一方面注重经济利益的集中化。三种家族主义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种政治担纲者,其等级是逐步衰降的。附带着天子的等级也是逐步衰降的。这样一种家族主义的特征与印欧人既有关联也有差异,关联在于后者也往往在上层社会保留鲜明的家族主义特征,而差异则在于,对印欧人来说,种姓法一直是一个关键的社会学框架,其作用远比宗族来得根本,与此同时,印欧人的平民在近代以来几乎很难保持大规模的家族主义特征,其政治的担纲者相当清晰地呈现为第三等级的种姓法群体。尽管林耀华在关于义序的研究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单姓村的样貌,[19]但其实这些年不论在哪个地区,我从未见到过真正的单姓汉人村落。一个简单的原因就在于村落与家族是两个层面的社会组织,纯粹单姓村会将两个层面混杂在一起,造成村落道德的内向化。同样,我在涉藏地区调查的时候,也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村落是由单一措哇(一种类似家族但实质上是完全基于法权的组织)构成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村落法与措哇的法不能混合。汉人村落几乎不会像家族那样成为政治的担纲者,反而是一个以公有财产和共同防卫为基础的地域性集团。晋祠有很多“堡”,都是在明嘉靖年间为了抵御蒙古人南下劫掠修建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村落作为防卫共同体的性质。但与典型的印欧村落相比,晋祠的村落的司法性质要弱很多,汉人村落的公共司法权即使有,也很早就在编户齐民的过程中被国家剥夺了。类似领主法庭一类的机制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看法,乡村由此成为一个有天无法的组织形态,其内部的礼治秩序也是通过礼下庶人等一系列运动形成的,至于更加古老的乡村社会,我们除了知道社和里老制度之外,就所知甚少了。不论如何,我们在将印欧人的共同体等同于中国汉人的乡村时,其实都没有做出足够的辨析,更没有描述出一个界定乡村的根本经验类型,这恐怕也是利奇批评费先生的根本原因所在。王斯福在论述“何为村落”的时候得出了一个相当含混和折衷的结论[20],问题可能也是出在这里。
尽管中国汉人一直极为重视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但其基本的权力划分还总是以土地和人口为基础,而非以水权为基础。水作为一种必需的生产物资,其具体的所有权形式在所有的微观水利工程当中都是协商的产物,而非结构的产物。协商的结果,也总是以尽量满足所有土地的灌溉需求为目的,晋祠水源充沛,虽然历史上也偶有水利冲突,但几乎是无碍大局的。哪怕在明代初年屯军进入该地区之后,军屯占有了大片良田和水利之后,冲突也并不明显。但在水利不足的时候,这种协商机制就少有奏效的时候了,冲突就在所难免。实际上,我们最好就把水权当作是一种动态协商与冲突的过程来对待,一如我后来在藏族社会做研究时看到草山的所有权的性质是一样的。这并非对公共物产权的界定不足,而是一种特定的所有权形态。社会科学的产权研究几乎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但如果看看《伊利亚特》中关于战利品的争论,或者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以及努尔人对丁卡人的劫掠,我们就非常容易明白,《罗马法》中对物权的清晰严格的界定才是一种例外的状态,以此作为理解产权的基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莫斯的人类学教诲即在于,这种产权的动态性是制造债的根本机制,当其与武士阶层的对称性相互连接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社会盟约的基础,[21]从而不同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晋祠的水权分配的原则是“水地夫一体化”,也就是说,根据村落拥有多少耕地(或者水磨)来决定分水量和出夫的量,具体问题在相关的历史学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实际情况则是,只要村里的村长或者水利组织的头人足够强硬,实际用水过程中就大有优势,水权实践仍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晋祠最著名的分水设施就是在金沙滩上的三七分水孔,传说是从前根据油锅捞钱的方式通过神判实现的,张小军老师由此发展出关于象征水权的看法。[22]但这个故事其实由两层逻辑构成:[23]一是南河和北河之间分水比例的确定,不论历史真相如何,这都是通过一次献祭完成的产权划分,与土地产权的依据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献祭最多可以看作对动态产权的阶段性固定化,历史上南北河确实也曾经通过调整金沙滩的坡度重新恢复了水权的动态性;另一层逻辑则在北河内部,花塔村的楞后生把手伸进油锅的传说合法化了该村作为北河渠长村落的地位,在我看来,这可能才是问题所在,这个传说根本不是关于水权的,而是关于北河的水利控制权的争夺过程的产物,其言说的对象是北河诸村落而非南河。地方政府和屯军自然也会介入到水权分配的动态历史当中,并力求一劳永逸地解决产权动态性带来的地方社会的躁动不安。但这往往收效有限,直到周围化工厂和热电厂彻底抽干难老泉之前,这种介入几乎从未停歇。
四、结 语
魏特夫对水利社会的批判主要出发点有二:其一是官僚赋役制国家的形成往往要依赖大型基础设施——在传统社会主要就是水利设施和金字塔之类的庞然大物——中的赋役制征调,这一过程需要精密的社会控制和精神约束才能实现;其二则是对水权的精密控制成为国家干预社会的一个强大手段。这些在晋祠几乎是看不到的,但这并不能让我如格尔茨那样直接得出对反于魏特夫的结论,毕竟中国的政治控制手段及其历史的变化过程都远远比巴厘岛要复杂。虽然从秦开始的编户齐民已经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基层社会的法权,但由于东汉以降的豪族与世族的对称性格局,以及军事贵族的崛起,在唐宋变革之前,中国政治的专制程度可能远低于魏特夫的判断。魏特夫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更加符合唐宋变革之后的中国社会,其助手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所引述的大部分材料来自宋代以后,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而至为关键的问题是晋祠圣母的出现,封建形态的变化使得地望的巫术性摆脱了世家大族的控制,并且被具体化了,这是皇权深入民间社会以及宋儒的礼下庶人事业的最重要前提,史家往往强调礼学与巫术之间的对反关系——举人刘大鹏就曾经对求雨巫术嗤之以鼻,殊不知这种对反恰恰是以双方的合谋为前提的。儒生对唐叔虞的祭祀与他们作为官僚的权力上升是并行不悖的,而这正是儒家官僚本身在圣人与天子之间左右逢源的二重性的体现。这一转变的代价则是整个中国政治的去军事化,宋元明清四代,整个山西北部除非在异族政权控制之下,否则几乎是永无宁日的。
魏特夫在日本及西欧的封建制度与中国的官僚制度之间建立的刻板对立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一批评也同样适用于韦伯对中国历史与宗教的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封建性其实从未真正消除过,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担纲者罢了,韦伯和魏特夫都过分夸大了官僚制度的意义,而忽视了内藤湖南及陈寅恪等人对中古世族的研究。韦伯清晰地意识到了春秋战国的武士集团之间的对立冲突对中国思想之理性化的意义,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古封建制度和武士集团再造的过程。北宋征伐北汉时,曾经遭遇到城内弓箭社的抵抗,[24]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晋阳城也经历了一个从武士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的过程。而笔者在博士阶段的田野调查和史料阅读真正能够接触到的几乎都是这一转变发生之后的晋水流域社会,其实已经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了。
笔者在《水德配天》一书中以“乾生坤成,水土相济”作为乡土道德形而上学的根本内容,现在看来并不算错,但这种基于象征的分析终究只能被看作是一个社会学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在葛兰言的框架中,“土地之德”是由诸侯王来承担的,并且从诸侯王和地望一直延伸到社一层。唐宋变革之后,土地之德直接和区域社会联系在了一起,区域社会成为了中国的道德结构中至为关键的一元,但和诸侯王或者世家大族相比,其法权特征相当孱弱,由此造成了皇权的“天之德”过度发育的状态,水母柳春英的神话产生的背景也恰与此有关。柳春英的故事表明,区域社会的公共性已经完全超越了家族主义政治,使得中国基层政治呈现出一种“社会”或者“共同体”的形貌。而在中国东南,家族主义靠着不能完全被国家控制的经济力量顽强地保存了下来,但人类学将这个问题与非洲的世系群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则是一种完全割裂式的比较策略,实际上,中国东南宗族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扮演的政治角色都和非洲世系群完全不同。中国政治的家族主义恐怕既不是印欧人的扩大父系联合家庭,也不是非洲式的主导世系对其他世系的支配,而是封建主义的一种等级衰降之后的结果,只是当地方神成为被封建的主体之后,平民宗族就被掩盖在区域社会的结构之下,从而失去了与封主的直接联系。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家族主义在古典城邦和封建时代都是社会政治活力最重要的来源,但在现代社会,生产者的家族主义该如何评估,恐怕是我们走出魏特夫的阴影后仍旧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特别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的法家传统虽然起源很早,但几乎从来没有获得如罗马法或者印度教法典那般的地位,中国的价值体系的核心一直是“道”,这个词和印度的rita一样都带有强烈的规则、规范的意味,但又同时由于无法客观化而成为一种无规范性的自我宣称。“道”是无法被任何人彻底垄断的,反而随着身份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其运行的逻辑本身就是与法家的主张及郡县制相对反的。唐宋变革之后,道的概念带有了更为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因此也失去了从前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