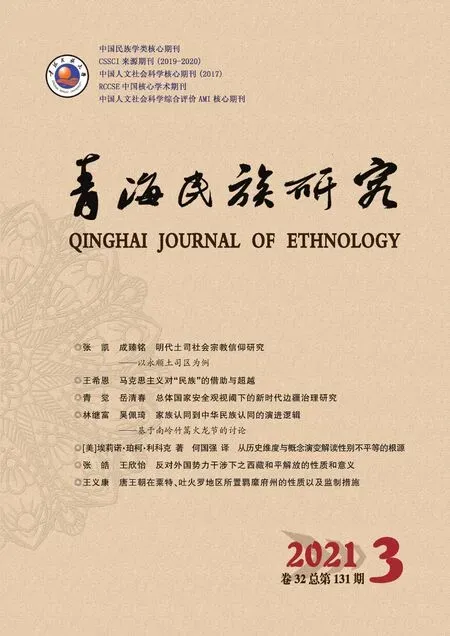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自觉
贾 益 方素梅 张大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81;青岛日报社,山东 青岛 26600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民族发展条件下提出的重大原创性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形成于近代,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对于这一自在实体及其历史形成过程,一般概括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交融中,中国各族人民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逐渐形成不可分的统一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各民族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联系和日益接近;既有各自民族的特点,又日益形成着它们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共同点;既分别存在和建立过不同的国家政权,又日益趋向于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2]关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研究,近30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梳理和分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自觉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解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的连续叙事”的内在逻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术支持。
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是中华民族凝聚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是,在今天中国这一地理空间内,从有史以来,各民族逐渐统一于一个国家政权,这样的趋势却是可以从中国历史发展中明显观察到的。这样一种统一的趋势,不仅构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中华民族整体性逐步得到强化的体现。
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出现,虽然存在很多争议,但从考古资料可以断定,距今5000—4000年间,我国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其他地区,普遍出现了不少城邑,它们已经具备了国家形成的要素,即阶层和阶级的产生以及强制性权力系统的出现。进入公元前2000年之后,中原地区先后形成夏、商、周等较大的政权,这些政权都吸收境内不同部族、邦国而成,具有较大的疆域,形成了较为发达的文明中心。
尤其是自周初实行分封制以后,融合周(姬姜族姓)与殷遗民及东方旧族统治势力,楔入土著,致使“古代以族姓为集群条件的局面,遂因此改观,成为以诸侯相融合的新组合”,诸侯之间又因为同姓祭祀与异姓婚姻的联系,逐步凝结为强烈的“自群”意识,以至“后世的华夏观念,当由周初族群结合而开其端倪”。[3]在此基础上,周朝统治疆域更为广阔,其文化的影响,则散点式推移至中原之外。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国成为政治运作的基本单位,但在文化礼仪上,由西周分封形成的文化网络反而大为发展,成为诸夏之间彼此认同的媒介。[4]这同“尊王攘夷”发展而来的“华夷”之辨,共同造成了此一时期华夏民族的进一步凝聚融合。
秦汉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秦并六国为一,乃是诸夏族群凝聚趋势的完成,至汉武帝北击匈奴、南平瓯越、通西域,在西南夷和东北设置郡县,统一格局进一步巩固扩大。秦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随着这一体制向所有统治区域的推广,促成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文化上共同特征的形成。在思想意识上,与统一王朝相适应的“传之无穷”“施之罔极”的大一统意识受到统治者推崇,被称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5]。另一方面,秦汉统一国家,也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治理,例如在郡县制框架之下设立了道、属国、都护等各级管理机构,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又如,通过和亲、互市等手段,密切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秦汉国家的这些特征,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整体性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公元3世纪初,东汉王朝解体,群雄割据,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到西晋方才形成短暂统一;此后,北方动荡,出现了主要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与南方东晋政权对峙;随后又演变为南朝和北朝的分立。直到公元7世纪30年代,才又开始了隋、唐的统一。在将近500年的分裂混乱中,各民族发生大规模迁徙,民族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在这一背景下,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要素,在分立各国各政权及其相互关系中,都有所体现。具体包括:第一,各政权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都以“正统”自居,试图统一天下,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政权中,更以攀附华夏为据正统之必要条件。第二,在战乱之中,保证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亦是各政权维护自身稳定之基础。在北方,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和经济发展;在南方,大批汉族南迁,与南方各族共同开发,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第三,在南北各政权分立斗争、割据统治下,各民族间不仅有激烈的斗争,也有前所未有的交流融合,北方各族的“汉化”“胡化”现象频见于史书,南方各土著也大量融入汉族。第四,在政权组织中,多民族治理的方式在秦汉制度基础上有所增益。如北方各政权中央和地方体制上对各族的分而治之;南朝刘宋之后,创立以酋帅为郡守令长统辖以蛮户”的“左郡左县”制度等。
隋唐国家的统一,建立在前期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伴随着统一进程,隋唐国家体制逐渐稳定,至唐太宗时期,中央的三省六部、地方的州县制,皆在汉晋体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又行科举之制,人才选拔渠道、方式由朝廷完全把控。经济方面,大运河的修建使南北经济联系进一步增强。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隋唐王朝表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唐太宗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6]。贞观年间,唐太宗以突厥突利、颉利可汗部分治羁縻州府,此后唐代十道中大多设立羁縻府州管辖少数民族。尽管唐廷对于羁縻府州及其部众,以“全其部落,以为捍蔽”而又“不离其土俗”为大原则因俗而治,但从国家体制而言,其皆为唐朝天下声教所及之处。就基本政策而言,隋唐国家对周边各族,以德化、征伐参合用之,总体来说至唐中前期都保持了民族关系的稳定。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盛,以及各民族的发展交融,显示出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进一步增强。
晚唐以后,地方藩镇形成割据之势,唐灭之后,更演变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与此同时,契丹在东北地区强盛起来,以东北为根据地,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统一。此后北宋也基本统一华北和南方地区,大体与契丹所建辽朝形成南北对峙。金灭辽和北宋之后,又形成金和南宋的南北分立。在这一时期,还形成了西夏、大理、西辽等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国家。大体而言,这些政权虽相互独立,彼此战争不断,但相对稳定的局部统一形势下,区域性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政权内各民族关系的增强,则为更高程度的统一打下了基础。此外,各政权多少都以汉唐体制为基本的国家体制,进而在文化上发展出一些共同性的特点和趋势,举其大者则有:一是“正统”意识,不仅两宋自居中华正统,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也以中国自道;一是儒学作为国家统治的基本意识形态在各政权内都受到重视。
公元13世纪初,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逐一平定各政权完成统一。元朝的统一,不仅是王朝在更大版图上的统一,也由于其继承和发展了宋辽金以后合天下为一体、各民族共为“中国”(中华)的大一统观念,而建构起不同以往的“华夷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明朝建立,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统治区和北方蒙古各部的对峙,至明后期,满族在东北崛起,入主中原,又一次形成了全国性的大统一。
元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得到加强。元代中央体制大体承袭宋制,地方则以“行中书省”统驭之,行省制度不仅在元代发挥了维护蒙古贵族统治的作用,还经明代分权改造,成为巩固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有力工具,成为定制;[7]此外,元代还在全国广设驿站,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并为明清继承,成为大一统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明清制度,除进一步完善中央地方各类官职,引人注目的是皇权的加强。在地方上,明代以来在城乡推行里甲制度,设甲长、里长,有催征、互保之责,加强了对基层的控制。这一时期,王朝一统国家对各民族的统治和治理制度也更为严密有效。元代在地方上将宣慰使司、招讨使、安抚使、宣抚使、长官司等“参用其土人为之”,称为土官,在西南民族地区实施因俗而治的治理,并不同程度地因袭至明清,部分地区在20世纪上半叶才完全废除。土官土司制自元至清,其治理原则,虽可追溯至秦汉以来在民族地方实行的羁縻之制,但较之前代,其系统性和制度化程度都更为完备。清代的地方行政体制,除“直省”外,还有“藩部”,其管辖范围明确为内扎萨克及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回部”,以及西藏等地。有清一代,这些地方被称为“外藩各部”或“藩部”[8]。“藩部”和“直省”,均为清代统一治权之下的地方行政治理制度,只是“藩部”行政体制更为多元、与中央关系也较为复杂。其特殊体制包括扎萨克旗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驻扎大臣和“伯克”制,以及八旗驻防体制等。元清两代还专设管理宗教和西藏事务的宣政院及理藩院,尤其是清代的理藩院地位极为重要,“掌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部封授朝觐疆索贡献黜陟征发之政令,控驭抚绥,以固邦翰”[9]。这些制度的存在和相关政策的施行,对于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稳定,既是非常必要的,也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效用。
总之,由先秦至清代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逐渐发展和巩固,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基本特征。这种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得到凝聚和整体性得到强化的一个过程。
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
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共同体不断凝聚的过程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不仅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和共同意识的增强也在多方面起着促进作用,举其要者可以概括为:华夷一统地理空间及其观念的演进、国家政权主导的各民族交融互动、礼法国家与共同文化的发展等。
(一)华夷一统地理空间及其观念的演进
商、周国家形成,尤其是周朝建立后,形成以王畿为“中国”,抚绥四方诸侯的观念和制度。随着“中国”内涵扩大为指代黄河中下游一带以及雏形中的华夏民族,“四方”也涵括了不同的地理单元和民族。在周天子以“王一人”一统“天下”的观念之下,“中国”与“四方”构成的“天下”,皆归一统。这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0]的地理政治观念,逐渐演变为春秋战国以后“大一统”和华夷观念的认识基础。
秦汉的统一,以诸夏为核心,统治的领域北达匈奴、建河西四郡、通西域,东北至朝鲜四郡,南平瓯、越,以西南夷为郡县,建立了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11]与此同时,北方匈奴统一了草原地区。这种统一王朝的传统在以后的历史中得以延续:三国、晋、宋、明继承了农业区统一的传统,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等继承了游牧区统一的传统。局部的统一,为进一步的统一创造了更大范围的地理空间;而汉、唐、元、清含括华夷的大一统王朝的出现,又完成和巩固了这种统一。“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两个统一——农业区的统一和游牧区的统一,终将形成混同南北的一个大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12]。
隋唐王朝统治的疆域比秦汉要大,并且通过征伐和羁縻府州等制度,对周边各族有强弱不等的控制,中华民族统一的地理空间进一步扩大。晚唐以后的分裂最后演变成辽、宋、西夏、金等政权分立的局面,辽金不仅占据中原一部分地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也进一步加强,控制范围东至日本海,北至外兴安岭;而南诏在西南地区,也将原来分散的部落统一至其下。这都为元以后更大范围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元朝统治范围,“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3]较之汉唐盛世,除了“腹里”地区,更设岭北、云南等行省,加强对原来边地的控制;此外元朝政府所设的宣政院,其主要职责之一即是兼管青藏地区的政务。
元代疆域之广大,超越汉唐盛世,成为统治者宣扬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证据,并进一步申说,之所以能如此,是因忽必烈等皇帝得“天命”具“君德”,而能混一天下,行仁德之政。[14]元代这一正统叙述的策略,为明清两代所承认,也为后者所发展,从而形成了元以后正统观念之巨大转变,即以混一华夷的大统一为王朝合法性最重要的表征和条件。以这种正统观为核心的“中华观”逐步为各族人民接受,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元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重要表现。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的地理空间在清代得以确定。正如谭其骧先生指出:“17世纪、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17世纪、18世纪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这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所能够做到的。单纯的、一时军事上的胜利和军事征服要是没有社会、经济基础来维持的话,统一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清朝在完成统一之后,巩固下来了,稳定下来了,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遭遇帝国主义从东南西北各方面入侵,给他们侵占了一部分土地去了,但基本上还是维持下来了。”[15]中华民族地理空间的确立,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互动、共同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在近代得以自觉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国家政权主导下各民族的交融互动
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广泛地存在着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具体体现为军事征伐、政治管辖与服从、经济往来与教化、民族间的婚姻等社会交往,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借鉴。古代国家政权下的一些相关政策,实际上是这些既有关系的政策化、制度化运作,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调节民族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维护稳定统治、保障一统秩序的目标。这样一些政策和制度,如和亲与联姻、册封与职贡、贡市与互市、屯田与迁徙,又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增强。
1.和亲与联姻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之间以婚姻关系来扩大自己势力或者与敌对势力取得和解,是较为常见的现象。此种政治联姻在殷周之时便已见于记载,其中也有殷周王室与周边“戎狄”之结亲。汉初,刘邦听刘敬之计,以“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使刘敬往匈奴“结和亲约”[16]。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和亲之策”。这一策略的目的,短期而言,是暂停兵戈;长期而言,则是不以兵戈而使对方臣服于己。为使对方接受和亲,则需以身份较高之女子(公主)使其贵之,并“厚遣之”,岁时遣使赠物。换言之,“和亲”之策是以联姻为中心的一系列笼络之策。这也是此后历代和亲政策的基本内容。以后各朝,和亲之策因时而有所变化。魏晋南北朝之时,政权林立,此起彼伏,和亲更是成为各国合纵连横之重要手段。如代、魏各政权与各民族政权的和亲就有代与宇文氏、慕容氏、铁弗等,北魏与后秦、北凉、柔然、氐等,西魏与柔然、突厥等,东魏与柔然、吐谷浑、突厥等,以及北周、北齐(北齐高氏与鲜卑人关系颇为密切,也可算在内)与柔然、突厥等,几乎涵盖其建国和发展过程中的周边政权。[17]唐朝与其他民族的和亲,是将其纳入以唐为中心之权力关系秩序,周边各民族为在这一秩序中取得一席之地,也将求取和亲作为争夺或巩固统治权力的重要手段。宋辽夏金时期,辽夏金之间皆有和亲关系,而宋与各民族政权之间则出于偏见而坚持不采用和亲方式,明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清朝建立以后,不同民族之间出于政治目的缔结的婚姻关系,主要指满族与蒙古统治者之间的联姻,其政治性非常突出,婚姻的范围、对象、方式(嫁娶)等等一切,都出于皇室调节与蒙古政治关系的需要。
从民族交往的角度看,和亲或政治联姻能够以婚姻的形式,突破双方在政治或文化上的隔膜,打开沟通的孔道。长期来看,和亲与联姻作为一种民族间的交流方式,密切了民族之间关系,这是无可置疑的。除了统治者和贵族之间在婚姻嫁娶层面的交流外,和亲和联姻所带动的人员、物资、文化的交流,在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往往具有开创意义。如文成公主嫁入吐蕃,带来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物资以及医书等典籍,随行的还有各种匠人,据传文成公主还精通历算风水等术,对于古代汉藏民族关系,影响巨大。而另外一些长期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如,在与汉长期的和亲影响下,至两晋时期,南匈奴的刘渊等人,已经将自己姓氏的由来与汉高祖和冒顿单于的和亲联系起来,自称“汉氏之甥”,欲成汉高祖之业,统一天下。可见,和亲及其后果已经成为边疆民族认同“大一统”的重要思想资源。而松赞干布希望通过和亲,在唐代所建构的大一统秩序中取得一席之地,也表现出边疆民族在文化心理上与中原王朝的紧密连接。无论哪一层次的认同,都为中华民族意识的铸造起到了促进作用。
2.册封纳贡与互市
册封朝贡政策和关系,在秦汉混一六合形成郡县制国家之后,以儒家“服制”观念为依据而建构形成,是“大一统”的产物,其运行有赖于天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共同认可,对册封授予者和接受者而言,也是在这一秩序下各安其分的选择。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安定四方的实际需要,统一王朝莫不以八方来朝、“百蛮”入贡为王朝兴盛的重要表征,上至秦汉,延至随唐,以及明清,四方职贡皆是朝廷彰显一统之盛的重要内容,多见于史籍;通过现存一些图像资料,如《王会图》《朝贡图》等,也能窥见一斑。
就册封的接受者而言,通过册封,不仅有取得和平、获取厚利等好处,同时其权力以天子授予的形式在天下秩序中得到承认,甚至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巩固。正因为如此,册封和朝贡关系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项基本政策,在历朝历代都有所施行,是大一统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各民族的朝贡往来当中,也有贡使将部分贡纳送至指定地点交割,或者将随行物资进行出售的活动,这在明代以后颇为流行,多以“贡市”一词称之。此外,对地区和民族间经济交换活动进行管理和控制,这样的活动被称为“互市”。
作为国家统治政策的一个部分,封贡和互市带有强烈的政治管制与政治博弈性,但其在客观上,无疑对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积极促进作用。例如在唐朝时期,和突厥、回纥、吐蕃、吐谷浑、渤海等民族政权的互市贸易都很发达,主要形式是以缣帛换取牛马的交易,这在经济上符合双方利益。由于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唐之缣帛实际上成为通用货币,北方和西部各族以牛马卖的丝绸,实际上等于获得了进一步交易的中介物,可以用之购买其他所需货物;而唐获取牛马,则主要用于农耕和助军旅。宋辽金西夏时期,各政权虽在军事和政治上对立,但经济往来却通过榷场、和市等方式进行。此外自唐开始,便有将朝贡所贡之物于指定地点查验,并将其计价,依厚往薄来原则,赐予相应回礼的做法。这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行为,唐时许多贡使便是利用朝贡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至宋代,这种所谓贡赐贸易也构成了各民族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对于西藏和西北地区,明初以来便实行“以茶驭番”之法,西藏等地也通过朝贡等形式,获取所需茶叶。
3.屯田与迁徙
古代中原居民向边疆民族地区的大规模迁徙,一开始以戍守士兵为主,随着历史的发展,屯田移民占有的比例越来越高。对边疆民族的迁徙,主要是归附人口的安置,也有出于分化需要而强行迁徙的。前者如汉武帝以后,匈奴和其他北方民族部众大量归附,汉朝一般将其安置于边郡之塞外,助其守边。这些部众一般保持了原来的生产生活习俗,少部分则转为农耕。东汉之后,中原战乱频仍,人口大减,各政权纷纷以招徕或强行掠夺周边民族人口为策,以补充赋税人口和兵役的不足。南朝时期,各王朝对南部山民的征讨掠夺和招徕政策从未停止。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带来的被动或主动的交融,不光发生在南北之间,北方各族与汉族之间、南方各族与汉族之间,也有着频繁的互动。
此后各代,边疆屯田和为稳定统治而实行的有组织迁徙更加频繁。就有组织的边地迁徙和屯田活动而言,明代规模最大,其形式主要有军屯、商屯和民屯三种。由于卫所多分布于边地,边地屯田成为军屯最主要的部分,史载:“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18]按卫所军户计算,其人口迁徙规模不小。如明代万历年间,云南军屯人数达到29万,所耕种的土地达到100多万亩。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大量民人被迁往北平和“九边”之地,以巩固北部边防,明成祖朱棣时期更是将各地田少或无田之民迁来以实京师。在南方地区,则将湖广人烟稠密之地丁口抽调往云南屯田。明初见于记载的有组织民屯,规模都在数万,甚至十数万。总的来说,其数量应当超过军屯。此外北部京师、九边,西北甘州,云南、四川等边疆地区,往往是商屯比较兴盛的地方。
明清时期,除了汉民以屯田等方式向边疆地区移民,将边疆民族移往内地或其他地区,往往也是政府民族治理的一个手段。如清代,驻防各地的八旗兵士实际上包含了满、蒙古、汉、锡伯等民族成分;此外清政府还将改土归流后的一些土司迁往内地,甚至有迁往新疆的;在西北战事中,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将部分回部人口迁往内地。
古代国家主导下的大规模民族迁徙,尤其是大量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的迁入和屯垦,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社会生产方式与民族分布情况。民屯迁入者,给边疆地区带来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卫所制度下的军户累代之后,其驻守之地也便成为故土了。这些变化,无疑是促进中国各民族融合、互嵌,产生互相认同意识的重要推动因素。
(三)礼法国家与共同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礼仪制度为表现的德化政治和儒学为中心的文教设置,是国家统治的基础之一。西周确立的礼治,以“亲亲”“尊尊”为核心,虽经战国秦汉以后法家的洗礼,但一直保存了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西汉以后的儒家,发展出三纲五常的意识形态,通过教化礼乐的倡导,不仅在治国理政中维护了封建等级秩序,更将此种价值观推广至基层社会和四裔边疆,移风易俗,成为稳固统治、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而中国古代所谓“移风化俗”,以达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之目的的措施,主要是指儒学为中心的文教设置,其大端有二:一为尊崇孔子和儒教,建立相应制度;二是与科举制度相配合,形成学校制度。
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定下了其基本制度。至于春秋,虽“礼崩乐坏”,但是否行周礼却成为华夷之辨的核心标准。秦汉之后,历朝历代都以一整套礼仪制度,作为王朝秉承天命、顺天应人的重要表征。历朝历代,皆以正闰,即是否接续正统、感应德运,为王朝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其外在表征则是改易正朔、服色、礼乐制度等。即便在边疆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之时,其正统的礼乐建构,也是如此。如十六国时期,各族胡人相继在中原建立政权,在接受华夏正统观的前提下,纷纷改闰易德,以巩固自身合法性基础。宋辽金西夏时期,各政权争居正统,皆以自己为“天下之正”,行中国之礼往往成为与此相关的重要内容。金世宗称:“本国拜天之礼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筑坛,亦宜。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豈可不行。”[19]元代之正统,强调一统天下而以故俗治天下,故尊崇年号、郊祀天地、宗庙之祭等均以政治需要,因循前代。清代不仅在作为大一统王朝重要表征的意义上继承了中国历史中的“礼治”传统,在祭祀礼仪上也以礼部为中心,承袭明制,管理藩属、外国和国内各边疆民族的朝贡、接待等礼仪。
在儒家大一统的治理理念中,王化政治的实现通过帝王得天之运,行天之道而实现,其最终的效果,则是通过帝王教化而使得天道大行。历朝历代,礼俗教化之法,大约有三:一是依据《礼记》之“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而兴学校;二是通过皇帝提倡和垂范之礼仪以正风化;三是以各种手段宣谕于百姓,即所谓“置木铎以敎民”。其中第二种方法,汉魏以来,朝廷命官中有御使大夫等“宪官”,彰“宣导风化”“正百官纪纲”之事,唐宋以后,礼制下移,朝廷不仅垂范祭祀天地山川之礼,更禁绝民间淫祀,在礼典中规定庶民礼仪,各级令守皆有“宣导风化”之责。至于明清,不仅是朝廷和官员,更有城乡社会中绅士研究礼仪,提倡儒家礼俗,成为一时之风。第三种方法,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置木铎”的制度,尤其以清代的圣谕宣讲制度最为典型,其目的是以汉文化之传统道德规范,向所有民众宣示教化,图谋清朝统治之长治久安。而且,圣谕宣讲从一开始就不是只针对直省的,还包括了八旗;在稳定民族地区的统治之后,往往以《圣谕》的宣讲作为“善后”手段,“化导”少数民族,使其“范围礼教”,如雍正改土归流之后的云南土司义学教育中,则令“先令熟番子弟来学,日与汉童相处。宣讲圣谕广训,俟熟习后再令诵习诗书”[20]。
自两汉以后,尊崇儒学而行文教,逐渐成为政权合法正统的重要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在其政权建设中,以儒学教化乃是由武功走向文教的重要手段。北燕冯跋建政之后颁布诏书:“武以平乱,文以经务,宁国济俗,实所凭焉。……可营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郞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敎之。”[21]大一统的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则有诗书教化,以“渐陶声教”之意。辽宋西夏金时期,各政权皆以儒学治国。宋真宗时期,张齐贤上书朝廷,灵州李继迁“仍闻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覩此作为,志实非小”[22]。可见当时,即以儒士治国,“行中国之风”为有逐鹿天下,争夺正统之志的表现。元朝尊孔崇儒亦是国家行为。不仅如此,元代儒臣还以推广儒学为“丕变华夏”之道。
明代建国,北有蒙古,而南方大体安定,故其民族政策在北方以征伐为主,南方以“德化”为先。对于南方土司地区,除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之外,设立儒学以化导之是重要措施。洪武二年(1369),元太祖朱元璋令天下府州县皆设学,其后,宣抚、安抚等土官也都设立儒学。少数民族士子入学之后,学有所成,亦可参与科举和贡举。就导民成俗的作用而言,明朝对社学也相当重视,在各民族地区,所谓以社学教“民夷子弟”,而使“风化大行”“风气渐变”的记载,多见于史志。清朝入关之后,“清承明制”,尊孔崇儒、设学兴教、开科取士等等措施自不必多说,其八旗学校教育更是体现清王朝大一统与多元并存文教的特点。顺治朝入关之后,即在京师国子监、顺天府学设八旗学校,令八旗子弟入学,后因学生人数日增,又专设八旗官学、义学等作为八旗子弟教育机构,各地驻防八旗也都设立学校培养子弟。在西南地区,不仅延续明代为土官子弟设学的成规,而且随着“开辟苗疆”和“改土归流”的进展,官学义学等也随之大量举办,无论是数量还是深入边疆的程度,都超过了明代。在南方民族地区,对于清政府以民人、熟(番/苗/夷)、生(番/苗/夷)分类治理,“欲其渐仁摩义,默化潜移,由生番而成熟番,由熟番而成士庶”[23]的政策,义学教育体现得最为明显。
总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历朝历代都将礼教祭祀和文教设置视为重要手段,并起到了相应的作用。这些礼仪制度和儒学为中心的一系列文化价值观,经过国家主导的大力宣扬,深入各民族中,成为中华各民族同创造的精神文化的重要资源。
三、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与巩固
(一)“对他自觉为我”:近代国家主权与中华民族自觉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清朝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清朝对自身疆域和“华夷”关系的新理解。至迟在乾隆朝以后,清朝统治者对归于疆理和朝贡互市之国就已经有了清晰的区分,《清朝通典》称,“故以杜典及续通典所载诸国参较於今日舆图”,如挹娄、靺鞨、乌桓、鲜卑、南诏、吐蕃、党项等等,“莫不尽入版图,归于疆理”,而“有朝献之列国,互市之群番,革心面內之部落,喁喁向化,环四海而达重洋”[24]。体现在边疆治理中对“夷”“种人”“土司”与“外夷”的区分,[25]其实在国家认同层面,反映的也是“中国”和“外夷”的中外之分。[26]1840年以后,从西方列强和中国的相互关系看,其在政治上、文化上的互为“他者”,已经逐渐取代传统的“华夷之辨”。对中国人而言,“对他自觉为我”的意识,也以清朝国家与西方列强的对立为表象,开始明晰起来。而这种意识的明晰,正是中华民族认同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晚清时期,这一转变可以从清朝统治者的“国家建设”与边疆各族对列强入侵的反抗两个方面举例说明。
为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晚清时期的统治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自同治年起,即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湘、淮军势力,为应付内忧外患,以军事改革为中心,吸收西方技术,巩固清朝政权的改革。同光时期的一系列新政,虽未触及清朝封建统治制度的根本,但在军事和部分财政治理上,可算是迈出了清朝国家近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改革骤然加速,“保国、保种、保教”的呼吁,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危机的认识,已经由国家间军事力量的比较,深入到国家制度和文化层面。其中,“上下相维”“合同而化”等强调国家治理一体化的话语也开始在制度与文化层面改革的考量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与列强侵略殖民意图的无数角力中,清朝统治者对于边疆地区土地、人民、主权等的整合也逐渐加强。例如经由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台湾的“番地”“番民”在国际条约中被确认为大清国的版图和臣民。而清朝此后开始着眼于巩固海防,对“生番”之地实施“开山抚番”,采取较为积极进取的态度。[27]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清政府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边疆控制的措施。平定阿古柏入侵后,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建省,政治体制实行一体化的郡县制度,经济上改革田赋,加强其与内地交流;1887年台湾建省,继续巩固海防、抚慰“番人”、清理田赋等。辛丑之后,清政府实施“新政”,在边疆地区也推行了一些改革,例如:在蒙古、东北地区实行“移民实边”,开设银行、建立警务体制,广设厅县等;在西藏,则有张荫棠等推行新政,试图改革政教合一体制,以巩固“主国名义”,兴学革教,以“破除汉番畛域、固结人心”;[28]川边地区,则是赵尔丰在“改土归流”名义下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这些“新政”措施虽然大多流于表面,但其维护国家主权、促进边疆与内地治理体制和文化一体化的努力,也是清政府在边疆地区新政中明显的“国家建设”诉求。
1840年以后,列强对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的侵略和殖民,边疆地区首当其冲。在一系列边疆危机中,各族人民表现出了保家卫国的认同感。在19世纪60—90年代抵抗沙俄抢占中国西北、东北、蒙古地区的斗争中,当地各民族人民组织团练,打击沙俄军队,保卫故土;或迁入内地,不愿接受侵略者的统治。在西南地区,各族人民对英法侵略者在边疆地区的蚕食侵吞展开了抵抗。例如1874年阻止英国“探险队”入滇的马嘉理事件;19世纪90年代滇西干崖、陇川、勐卯诸土司和景颇族各山官,为保卫清与缅甸分界地方的铁壁关、铜壁关、虎据关等地,率各族人民进行了战斗,其出发点,即在于为国(清朝)守土,“上报国恩,下保民生”[29]。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上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以及对广大人民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掠夺也越来越严重,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也因此体现在更多方面。例如在19世纪后期各地发生的“反洋教”运动中,除了出于维护本民族固有文化习俗的反抗,更多的是反抗“洋教”与“洋人”与官府沆瀣一气,压榨和侵夺百姓。故当时提出的口号多为“仇官灭洋”等。
总之,从晚清开始,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自觉,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主体性体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复兴富强,则成为这一社会历史运动的趋向。这又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整体性不断加强的产物,也是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将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殖民、侵略对象的过程中形成自觉的。在共同反抗侵略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团结日益增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走向自觉,以天命为基础的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将由以人民和民族为主体的合法性所取代。而这后一方面的变化,则在20世纪初期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逐渐明晰。
(二)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华民族”一词内涵的演变
辛亥革命前夕,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是革命派以“种族意识”鼓动革命,但其本身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在“亡国灭种”危险下,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团结全民族的共有背景;而“反满”的目标,也需要在更能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权民生这一点上,取得推翻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从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的角度看,20世纪初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华民族对外自觉、追求独立解放,对内建立民主国家、追求各民族平等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颇具意义的是“中华民族”一词在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民族自觉的深化而被广泛接受和认同,成为民族自觉的重要象征。
“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于20世纪初,系由“中华”和“民族”组合而成。其中的“中华”一词来源甚早,与“中国”一样,不仅用于正统王朝的国家自称,也是具有历史连续性、与王朝合法性紧密关联的历代王朝的贯通性名号。晚清时期在和西方的交往中,中国和中华作为主权对等国家的称呼,频频出现于中外各种条约文本和法令等制度性文献中,其含义逐渐向现代国家的名号转变。[30]而“民族”虽见于古籍,且有“类族辨物”之意,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却是19、20世纪之交从日本传入,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国民等概念关系密切。在时代背景下,民族观念往往又与“种族”观念合一且掺杂混淆使用。[31]正是在这种民族观念影响下,清末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的意义上使用了“汉种”“汉族”“黄种”“黄族”“中国种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中华种族”等族称。其中“中国民族(种族)”和“中华民族(种族)”都是由上述内含传统观念,到晚清以后有开始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称号意义的“中国”“中华”,加上“民族”组合而成的族称。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较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更是频繁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将之作为“中国主族”之称,认为“中华民族”与“汉族”基本上是同一意义,指的是“中国主族”,其源头可追溯到黄帝,并且后来也以“黄帝子孙”“炎黄一派”相认同;而且,中华民族(汉族)最初就是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此后又经过了多次混合而不断扩大。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革命与改良论战中,“中华民族”一词被赋予了其最初的意义,即基本上与“中国民族(种族)”一样、以“汉族”或扩大的“汉族”为内涵。此外,当时的知识分子皆将“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看成因“同化”作用而不断扩大的群体看待,以此来说明历史上中国民族统一格局的形成,并因应当时的国内各族(主要是满汉之间)的“种界”畛域问题。在这一点上,革命派因为强调“汉族”的主权,更多从“种族”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种族)”;而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则强调“中华民族”作为族称的文化色彩及其融合性。
中华民国以“中华”为国名,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2]。此即为“五族共和”之原则声明。当时社会的主流,多提倡“五族大同”、化除畛域。如革命派的黄兴、刘揆一等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名“中华民族大同会”),袁世凯授意成立“五族国民合进会”等,皆以结合五族为一体为目标。“中华民族”这一名词也成为这种“五族一体”“五族一家”观念的重要指称符号。例如袁世凯在1912年11月致库伦活佛电文中,就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称:“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33]与此相呼应,蒙古王公西盟会议议定的《乌伊两盟各札萨克劝告库伦文》也宣告:“共和新立,五族一家,南北无争,中央有主,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与时推移。”[34]为强调五族之间的融合,当时不少的著作亦将辛亥以前所建立的黄帝世系、“汉族”一元的观念,嫁接到构成中华民国的“五大民族”起源上,认为中国各民族都出于一个源头,甚至认同汉族西来说,认为各民族都来自西方。因出于一源,故能如“一家兄弟”般结合。[35]
辛亥革命后,这类中国民族整体性的论述经常出现在各类报刊、文告和教科书中。一般而言,除了上述民族一元论,更多的还是从各族在历史上相互融合的角度来说明其整体性。1917年一篇名为《中国民族同化之研究》的文章论述了“中华民族同化之史迹”,认为“搜五族同化之迹。罄竹难书。撷其要略。不外兵事之影响。与政术之作用。是以五族之先。支别繁多。始则由内部之镕合。继则与他族相同化”,而“同化之由来,趋于文明之倾向。华族文明发扬,远在他族之上”[36]。当时,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融合论,与辛亥之前的“汉族”发展史叙述互为呼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9年,孙中山开始对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做重新解释,认为民族主义虽古已有之,但兴盛于18、19世纪,而中国则只有“民族”而无“民族主义”,故现在“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37]。此后直到1923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在多个场合讲到要像美国的熔炉那样,熔铸一个“大中华民族”。1921年3月在国民党本部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他又特别强调“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因五族其他四族无“自卫能力”,要“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38]。可见,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和当时许多人一样,还自觉或不自觉地还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甚至以汉人为中心借助宗族发扬“民族主义”的“宗族民族主义”思想观念。然而,随着“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逐渐广为传播,成为人们熟悉的名词,将中国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观念,已然初步成为共识。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观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凝聚的意识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现代国家和民族观念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体现中国国民整体观念的“中华民族”一词,从中原到边疆几乎人人皆知,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复兴等观念,亦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信念支撑。各族人士对中华民族的理解,都是从中国全体国民的角度出发,强调国内各个民族有着紧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华民族是各个民族结合而成的“国族”。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获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建设富强的国家,各族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抗战建国。[39]这些认识,充分体现了各民族民众对中华民族观念的深入理解和认同。[59]
1939年2月2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中国的民族经过几千年混合,血缘的分界已经不可寻,而无种族之见的中国文化也非一元,而是各民族文化混合而成。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历史学需要研究这一个整体的历史,而现实政治中也不应把国内各族都称为“民族”[40]。这一观点引起费孝通等民族学研究者的质疑,他认为,中国是由众多“文化、语言、体质”不同的民族而结成的“政治的统一”,民族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民族问题的解决要靠平等来解决,而不是靠取消“民族”这个名词。[41]由此引发一场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这场讨论因为当时抗日战争的大环境而没有继续下去,但以民族国家的理论去理解顾颉刚先生的“一个”或“整个”的“中华民族”,指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层面的国家民族(state nation);基与此,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自决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在这个层面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就这一点而言,顾颉刚的理解是正确的。[42]
不过,正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在当时所指出的那样,以历史上的汉族“同化”过程,来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不仅在实践上未具有效性,而且在理论上也非常不“科学”。因为这样的民族历史实际上是脱离具体历史阶段和现实斗争的历史观,是为“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如果要正确地理解和说明中国的民族历史和民族问题,对于民族学者而言,其任务“不在于回忆过去大汉族主义的光荣,不在于制造一些欺蒙的理论,而在于以最大的真诚,以兄弟的友爱,以现实的利益,用革命与战斗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把国内各民族真真的团结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43]。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生发出来的。1938年,在中国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44]1938年10月召开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报告通过的决议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主张。[45]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46]至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中华民族观。[47]这一中华民族观,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着完整的内涵。在国家民族层面,体现了代表中华民族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任务的自觉,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对于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在国内民族问题层面,则承认和保证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建立平等联合的统一国家;在体制层面,则不再以苏联模式为教条,在统一人民共和国内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48]为目标,延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心。在这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明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在制度、法律和政策方面,把少数民族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49]并且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安排,既体现各民族的平等地位,更把全国各民族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家庭”,这个“民族大家庭”,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体。[50]
四、结 语
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演进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和自觉,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凝聚在一起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萌芽和壮大,又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国家统一和分裂交替,以统一的不断扩大为趋势,其结果不仅是王朝统治区域、统治力量的不断扩大,也使得中华民族的地理、文化空间进一步整合,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融合得以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凝聚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传统中国在差序格局和天下一统观念下构建的社会认同和政治体系遭到了严峻挑战,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华民族意识开始自觉和逐渐强化,各民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中华民族凝聚力在血与火的锤炼中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从一个古老的多元自在的聚合体,逐步向一个现代的一体自觉的共同体转变。在被迫纳入西方殖民主义所构造的世界体系过程中,清朝国家保持了其整体性。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自觉,因此具有了与之前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之间的连续性,也具备了在近代条件下建立现代国家的主体性。此后,中华民族的基本内涵,及其与现代国家构造的关系,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的新国家和新社会”的革命探索中,获得完满认识和制度上的解决,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