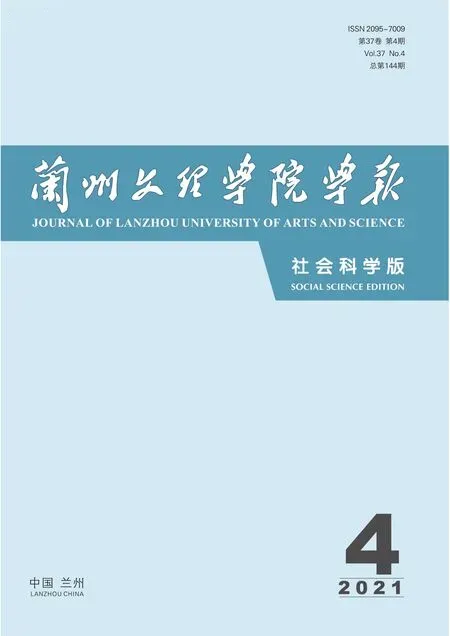转喻、隐喻、对照:城市形象片的视觉修辞策略探析
陈 睿 姣,万 应 圆
(兰州文理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当今,城市形象已成为城市诸多发展脉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各级政府在推进城镇化战略,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魅力城市。因此,制作出能反映城市特点、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形象片就成为刚需。
在学术界城市形象片有多种定义。胡玲娜认为,城市形象片是通过影视文本的传播来宣传城市形象的影片,包括城市景观、市容市貌、历史文化等方面。它能够帮助观众感受城市的外部景观和内部文化属性,从而有效地塑造和提升城市形象[1]。单文盛、甘甜从符号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城市形象片是以城市实体为直接来源,对其进行提取和加工的一套符号系统[2]。路金辉、韩晓冰认为,虽然城市形象片的称谓稍有差异:广告界称之为“城市形象广告”,政府宣传部门称之为“城市形象宣传片”,但都指向以建构城市形象为主要目的的视听文本[3]。本文所讨论的“城市形象片”是指以建构城市形象为主要目的,以城市形象为表现内容的影视作品。强调的是影视片的表现内容,而非广告属性。
我国第一部城市形象片是199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宣传片《威海,CHINA》,该片对威海城市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由此,其他城市开始把城市形象片作为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的有效手段。2002年上海申办世博会时,张艺谋担任世博申博片导演,拍摄了5分57秒的申博片《茉莉花开》,短片将上海的历史变迁、独特的多元文化和色彩融入其中。在申博现场播出时,观众爆发了多次热烈的掌声,显示了影片的巨大感染力。2003年张艺谋再次执导《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反响甚好,提升了成都的知名度。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市推出了《魅力北京》影像作品,全方位展现了北京的风采,让全世界都领略到北京的独特魅力。由此,城市形象片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4]。
目前,学界对于城市形象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内容创新、城市营销、推介与宣传、艺术文化[5]。本文试图将视觉修辞理论引入城市形象片,并对修辞过程进行细化、拆解,从修辞对象、修辞方法及修辞目标等几个层面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这些优秀城市形象片的视觉表征、修辞策略,解析修辞背后的文化内涵,以便对城市形象片的制作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视觉修辞,指以视觉化的媒介、空间、事件文本为主要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设计与使用、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以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6]。视觉修辞的话语实践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最开始的修辞学一直是在语言学领域展开研究的。新修辞学派诞生后,以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为首,提出视觉形象作为一种表征符号可以传递意义,具有象征、说理的目的,隐含着修辞的功能[7]。新修辞派的上述理念,催生出20世纪80年代的“视觉转向”[8]。它的表现有两点:其一是语言学逐渐被超越,被视觉所替代,特点是以语言为中心逐渐向以视觉为中心转变[8];其二是以罗兰巴特为代表,将符号学引入了修辞学,主要探讨非语言符号的表征特点及其内涵意义。视觉修辞通常采用的手法包括隐喻、转喻、象征、夸张、对照等。2017年,刘涛提出视觉符号的“修辞结构”对应于隐喻、转喻、越位、反讽、寓言、象征等修辞性的意义装置[6]。与语言的修辞相比它是诉诸于视觉的,是通过图像、符号文本实现意义生产的。这种表现方式和城市形象片不谋而合,城市形象的传播只有找到其自身文化的可识别性符号,并进行个性化、差别化的包装,才能避免大众化、同质化,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通常成功的城市形象片所建构的文化符号系统是独特而唯一的。纵观近年来优秀的城市形象片,大多用到了以下几种视觉修辞策略。
一、视觉转喻的象征
在修辞结构中,转喻 (metonymy) 和隐喻(metaphor) 是两种最基础的修辞方式,视觉转喻和视觉隐喻也成为修辞中最基本的传播方向[9]。然而,二者在西方修辞史上的地位却大不一样,可以说,隐喻长时间压制了转喻[10]。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诞生,转喻才渐渐得到了重视——它从一种古老的修辞方式逐渐变成认知与思维联想的方法[11]。它不光是一种指代手法,更是一种认知和联想的方式。至此,转喻作为一种更普遍,更基本的认知方式而被人们熟知[11]。
1956年,雅各布森在《语言的基本原则》这本书中,对转喻和隐喻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指出转喻和隐喻具有二元对立思想[12],在雅各布森看来,符号横组合过程表现为邻近性(将一个词放置在另一词旁边),因而其方式是转喻的,因为转喻是以自然界中的实在物体和“邻近的”指代词之间进行的联想[12]。一些较为抽象的事物难以用视觉语言呈现,我们需要用其他事物去“象征”,从而“取而代之”。这一过程所对应的修辞问题就是视觉的转喻[13]。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还将转喻等同于借代[14]。在语言学中,我们经常用“红领巾”这种较为具象的实物,去指代较为抽象的“少先队员”。同样在非语言的图像中,也需要通过一种“邻近性关系”去完成抽象物体的指涉。在著名导演姜文执导的影片《让子弹飞》中,周润发饰演的黄四郎用一顶“礼帽”迎接新县长上任。“礼帽”指代“礼貌”,既做足了面子,也给了张麻子这个假县长一个下马威。
在视觉转喻中,本体与喻体的关联方法有两种:指示转喻和概念转喻。就指示转喻而言,因为要“看到原本难以呈现的事物”,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借用有限的视觉对象来再现无限的、完整的、系统的视觉对象。因此,作为本体的视觉图像与作为喻体的视觉图像存在“邻近性”关系。上文中提到的著名电影《让子弹飞》中,“礼帽”和“礼貌”,两词读音相同,具有声音层面的邻近性,即声音意义上的指涉关系,故为指示转喻。再比如:2019年深圳环境宣传片《我在深圳等你》,第13秒出现了著名的平安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是深圳市最高的建筑物,建成后总高度达到599.1米,是深圳最高的摩天大厦,高耸入云,导演让一人站于金融中心的塔顶“一览众山小”。本体“高楼大厦”和喻体“城市”之间存在着空间邻近性。这种视觉转喻的手段暗示着深圳的文化自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其商务形象,商业实力都是顶尖的,属中国之翘楚。第二,就概念转喻而言,由于要表达较为抽象的事物,“理解原来难以表明的意义”,因此需要我们在具体的、可见的、可以感知的视觉符号基础上编织相对抽象的意义内涵。比如“环境”这个概念较为抽象,想直白的表现比较困难。这时只能求助于视觉转喻,我们可以用图像“树木”“河流”表示环境,用“运动的人们”去转喻“活力”这个概念。用这样的方式,使得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生动,使人们可轻易感知,难以忘记。在《4K上海城市形象宣传片》中,为了表达上海的快节奏、高效率,导演多次将镜头停留在各个地方不断出现的“时钟”上,钟是计时的器具,经常象征、指代时间。影片想通过时钟的快速转动,表现上海的效率、速度、与时间赛跑的特质。这便是用一个具体实物,去指代相对模糊、抽象的概念。同样的例子出现在2016年上海纪实卫视联合制作的新版上海城市形象片《上海,创新之城》中,影片第19秒,导演用航拍将镜头定格在一个用斑马线组成的“X”形岔路口,上海的岔路口很多,为何选用了X形状的?联系上下镜头段落,可以明白其意图。“X”代表了未知、不确定、一切皆有可能,持续3秒的“X”镜头,意指上海这座城市的新奇和未知性,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综上所述,指示转喻的使用,需要本体和喻体具有邻近性;而概念转喻的使用,需要本体和喻体,有某种文化语境上约定俗成的联系,具有从抽象到具象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符号是否具有代表性、通俗性。观众的文化背景、认知水平是否可以理解制作者所传递出的精神内涵。
二、视觉隐喻的映射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研究给予了隐喻极高的位置和分量。维克托·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在对隐喻修辞的文献梳理后,指出隐喻已然成为比喻中最为核心的一种修辞格,并且超过了日常生活和艺术领域的语言学范畴,最后成为视觉艺术中最关键的修辞手法[15]。乔治·莱考夫与马克·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给了隐喻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隐喻从本质上来说,是借助于一种事物去认识、解读和体验当前的事物。”[16]也就是说,当一个符号系统的解读过程出现困难时,常有的思维方式是征用一种具备普遍认知基础特点的符号系统,从而顺着后者的意义系统来靠近并把握前者的意义系统,这个过程所对应的修辞实践即是隐喻[16]。通俗来说,隐喻,其实是用一种认知的体系或概念系统去替代另一种认知体系或概念系统。
视觉隐喻可以根据本体与喻体的“在场”方式差异,生成两种不同的意义生产机制,即构成性视觉修辞隐喻与概念性视觉修辞隐喻[17]。构成性视觉隐喻指的是本体与喻体中同时“在场”于视觉结构中,观者能够借助一定的类比和逻辑联想提炼出“A 是 B”的隐喻结构[18]。视觉隐喻的基础是画面中存在着的各种元素,假设元素 A 与元素 B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类比或联想关系,我们就可提炼出“A 是 B”这样的隐喻思维。例如,对于静态图片而言,如果画面中同时出现了花朵和小孩这两个视觉元素时,观众很快能借助既定认知形成“小孩是祖国的花朵”这样的隐喻结构。对于动态图像而言,隐喻体现为两个镜头拼接所产生出的新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视听语言层面的隐喻蒙太奇。在著名导演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中,三头石狮子的镜头顺次快速切换:沉睡的狮子,睁开眼的狮子,站立起的狮子。导演利用三个镜头的拼接,含蓄且有力地表达出战舰波将金号和人民的觉醒。在2007年版上海城市形象片《上海协奏曲》中,前一个镜头是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后一个镜头是一群年轻人悠然地骑着自行车。两个镜头的拼贴让我们轻易读出“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如清晨升起的太阳”。当然,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联想,首先是源于A与B之间语境相融,性质相似,其次离不开我们格式塔完型心理学的认知机制。
相比构成性视觉隐喻的原理,概念性视觉隐喻具有较为复杂的意义机制。概念性视觉隐喻最明显的特点是本体“离场”但喻体“在场”:喻体体现为“在场”的视觉元素与内容,本体指向较为抽象的概念图式[18]。换句话说,就概念性视觉隐喻结构而言,本体通常是想象的产物,而想象的依据是“在场”的视觉符号所构建的概念图式[18]。在最著名的百岁山广告中,笛卡尔对公主的深厚感情太过于抽象,无法直接用视觉语言明确表达,这时隐喻出场,将这份情真意切的爱情置换成了百岁山的纯净水,清澈透明,纯粹美好,意喻“经典、浪漫 、难忘 、瞩目”。本体是较为抽象的概念“爱情”,喻体是百岁山纯净水,隐喻爱情像水一般纯净。2016年上海纪实卫视联合制作的新版上海城市形象片《上海,创新之城》1分40秒,科技少年制作的机器人跌倒、站起,继续行走,隐喻着上海年轻人不畏失败,勇往直前的性格特征。这里本体是较为庞杂和抽象的概念“上海青年”,喻体是跌倒后不断尝试站起,继续向前的机器人,隐喻上海年轻人不怕失败,勇敢尝试的精神,更暗示着上海是一座年轻,敢于冒险的城市。2017年潮州15秒的城市形象宣传片中,潮州著名的陶瓷和一位端庄贤惠的女子一同出现在荧幕上。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关的符号组合代表什么意思呢?直到看到片尾字幕“中国瓷都·潮州——潮人故里,瓷祠相传”,观众才恍然大悟:潮州是“中国瓷都”,故陶瓷是潮州文化得以延续的炉火。在这里,陶瓷隐喻祠堂里延续的炉火,而女子的出现,隐喻生命的传承。生命延续,炉火相传,生命的象征和未来的寄托相得益彰。影片用简单的视觉语言勾勒出了潮州的美好愿景。
三、视觉对照的呈现
在信息的呈现方式上,将两种相反、相差、相关的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相反、相差、相对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加以比照,使之相反相成,以便更生动鲜活地表现事物特征[19]。这种对照的方式常用在形象片的叙事之中,通过这种对照,借彼显此,互比互衬,以此全面而深刻地突出主体。在2019年推出的《世警会:8K宣传片畅游魅力成都》宣传片中,画面常以对半分屏的形式进行鲜明的对照,比如:1分56秒的画面中,左边是极具东方色彩的京剧花旦,右边是古典优雅的芭蕾舞者;2分25秒的画面中左侧是高科技的产物——机器人,右边是古老的民俗文化——皮影小人;2分34秒,中国男子喝咖啡和外国友人品茉莉花茶的画面形成鲜明的比照。这些对比鲜活地展现了成都这座城市的魅力:中西艺术交融,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并存,舶来品与本土特产同样畅销。想突出对照效果,创作者除了使用对半分屏的方式外,还可以利用移动镜头实现。在《中国名片·上海篇》中,一个纵深移动的镜头格外引人注目:镜头起于一位老大爷身穿蓝色的秧歌服装,极具传统文化特色。由上摇下来,大爷脚下登着的时尚轮滑鞋赫然出现在了观众的视野中。秧歌服和轮滑鞋,两种格格不入的混搭模式让人忍俊不禁,细细琢磨,导演意欲用这样的对比方式来显示上海人民既传承传统的文化活动,也用一种积极阳光的心态去拥抱新鲜的事物,即便是耄耋老人,也有着一颗年轻的心。
对照还有另一种情况,即镜头与镜头剪辑的对照,在视听语言系统中称为“对比蒙太奇”,通常指镜头或场面之间在内容或形式上的强对比,产生相互冲突的作用,以表达创作者的某种寓意或强化所表现的内容和思想[20]。同样在《世警会:8K宣传片畅游魅力成都》中,2分07秒出现西方女子穿旗袍打油纸伞,下一个镜头组接的是中国女子穿西式小黑裙礼服,打开一把油画伞。“旗袍”“油纸伞”作为极具东方魅力的符号与“礼服”“油画”这种西方符号相撞,对比意义马上浮现于人们脑中。同时,导演让西方女子出现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而将中国女子融入到西方文化语境中,“中西合璧”“文化交融”,更加能体现成都这座城市的多元化与包容性。
视觉是传达创意和表达意图最快速、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一幅看似简单的图像,不止是对事物或人物瞬间的捕捉,更是其背后文化渊源、意识形态,历史背景、思想观念的融合。视觉符号蕴藏着城市的历史记忆,是一个现实与想象交融的共同体,它们与人们的认知相契合,可触发人们的想象空间,最终具有“瞬间的认同力量”。城市形象片则是通过这些视觉符号的组合运用,系统的架构起城市的文化意义系统。因此,将视觉修辞手法:转喻、隐喻、对照等置入到城市形象片中,不仅可以帮助建构人们的观念与思想,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同时可以把握当前文化语境下城市的发展规律,城市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当然,视觉修辞中所选取的符号应当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并应顾及到观众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年代、地域、民族的观众对文化符号的理解会有偏差[21]。只有考虑到这些,才能最终实现观影者对影片含义的准确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