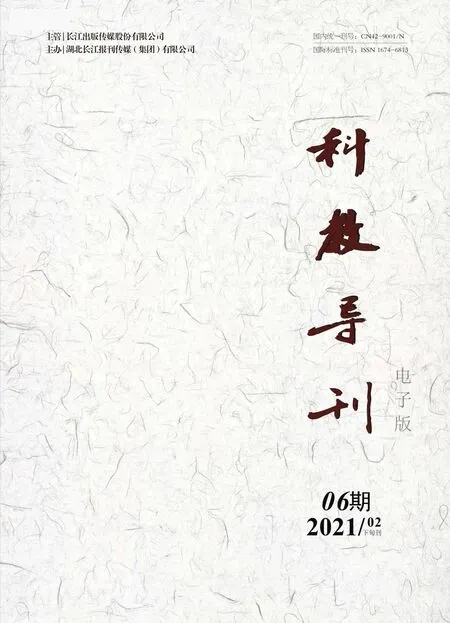《阿尔巴尼亚圣女》叙事及审美价值探析
肖 雯 卢 敏 张嘉容 宋佳静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44)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是加拿大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和“当代契诃夫”。自1968年出版发表首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即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项——总督文学奖后,声名鹊起,其后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也佳作频出,于加拿大和国际上所获奖项不计其数,受到了广泛读者的好评和评论界的关注。通过梳理门罗作品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发现,国内外学者对门罗作品的研究集中在以下类别:第一类是女性主义研究,关注女性形象、两性关系、自我意识与身份建构等问题。赵慧珍(2002)在《论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中对门罗几部代表作中的女性人物进行了分析总结。第二类是地域书写研究,致力于加拿大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学特色。刘小梅(2014)在《艾丽丝·门罗作品的南安大略哥特风格》中,采用传统哥特研究方法对门罗的故事文本进行系统分析,挖掘门罗文学作品中的“南安大略哥特”的特点。第三类是叙事艺术研究,聚焦灵活多变的叙事手法。钟丹,杨忠勇(2019)的《论艾丽丝·门罗<湖景在望>的叙事空间》,基于加布里尔·佐伦的叙事空间理论从地志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三个层次讨论小说《湖景在望》中建构的叙事空间。综上,学界对门罗作品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一领域,缺少多维度、综合性研究。而此文将结合叙事艺术和审美艺术,对门罗的短篇作品《阿尔巴尼亚圣女》进行双维度的研究。
门罗是短篇小说大师,其小说多取材于加拿大小镇里普通女性的平常生活,其文风表面简约质朴,实则结构精妙复杂,在过去与现在间来回穿梭,在虚幻与现实间不断转换。门罗用“传统的方式”述说小说主人公生平经历和日常琐碎之事,但复杂的叙事结构安排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因此,平稳单调叙事中的惊人之处便是门罗叙事的独特艺术所在。在众多门罗的短篇小说集中,1994年出版的《公开的秘密》以波澜不惊的话语、独特灵巧的叙事结构,透视小镇平常女子生活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曾获加拿大总督奖提名,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好书,并为门罗斩获了W.H.史密斯文学奖。自此,门罗作品日益受到国际文坛广泛关注。《阿尔巴尼亚圣女》是收录于此短篇小说集的第三篇故事,讲述受病痛折磨的女人夏洛特对“我”述说自编的阿尔巴尼亚圣女洛塔尔的故事。故事内容简单平淡,但该篇小说并非以传统的单线模式展开故事,而是运用嵌套式叙事结构穿梭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游走在回忆与现实之间,将三个女人的经历和命运抽丝剥茧般展现在读者面前。
1 嵌套式双线叙事结构及其审美价值
根据学者申丹(2010)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的论述,情节是对事件的安排,是对故事结构的构建。传统情节观强调情节结构的完整性,认为事件的安排必须包括开端、中段和结尾三个部分,且各个过程存在有机联系。这种单线且前后有序的传统叙事结构也被称为“线性叙事”。而现代小说家在对故事结构重新安排时,朝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叙事结构发展,打破呈线性、因果性的故事情节时序,呈现“非线性叙事”的情节安排结构模式。艾丽丝·门罗透彻洞悉短篇小说叙事艺术,开垦复杂多样的叙事结构,多采用时空倒错、拼贴嵌套、双线叙事、视角转换等非线性叙事手段,带给读者别具一格的阅读体验。短篇小说《阿尔巴尼亚圣女》以夏洛特讲述阿尔巴尼亚圣女这一虚构故事核心,铺展现实故事中夏洛特和“我”的生平故事,构成层次丰富的双线嵌套式叙事结构。两条看似不相交的线索并行,三个不同女人的故事沿着叙事话层徐徐展开,又通过框架和现实故事叙述线相互交织,连接三个女人的人生共通之处。小说叙事话语如下开展:
事件A(1):部族人枪杀向导,洛塔尔从岩石跌落陷入昏迷,被带到库拉部落。
事件A(2):洛塔尔在库拉受到照料,恢复意识;牧师叙述向导被杀原因。
事件B(1):洛塔尔独身到达意大利,和向导去往黑山的首府。
事件B(2):洛塔尔被带去库拉的途中。
事件C:“我”初次去医院探望夏洛特,她向“我”讲述自己在构思的一部电影,主角是洛塔尔。
事件D:库拉部落男男女女的劳作与生活;部落妇女准备将洛塔尔卖给穆斯林男人;牧师决定让洛塔尔成为圣女以阻止这一行径。
事件E(1):“我”第二次探望夏洛特,夏洛特继续向我讲述故事。
事件E(2):不到一周前的一个早晨,夏洛特丈夫戈迪汗找我卖书遭拒;“我”询问夏洛特近况,得知她住院了。
事件F:洛塔尔成为圣女后的生活;牧师带着洛塔尔逃离去往意大利斯库台的主教家。
事件G:1964年,“我”来到维多利亚开设书店;独居展开新生活,认识了一些朋友。
事件H:洛塔尔和牧师到达主教家;洛塔尔被送上船去领事馆。
事件(I1):“我”因婚外情决定逃离前往维多利亚。
事件(I2):“我”在书店结识了夏洛特夫妻;未多时,两人邀请“我”参加周日的晚餐,期间,戈迪汗向我推销旧书遭拒。
事件J:“我”第三次探夏洛特;第二天夏洛特已经被丈夫带走。
事件K:夏洛特夫妇的彻底消失使“我”陷入失落;“我”走在街头想象和尼尔森共度生活;尼尔森在书店等待;两人幸福生活。
事件L:夏洛特的船只驶入迪利亚特斯,牧师等候在码头。
初读《阿尔巴尼亚圣女》,读者可以领略到该小说新颖奇特的叙事艺术、体验到超越传统审美的阅读过程。门罗在叙事安排方面运用嵌套式结构,开展双线交织叙事。双线交织过程并未体现一定的规律性、逻辑性,三位女主人公人生故事的叙述呈现零散、无序拼贴连接,情节结构上并未体现戏剧性高潮。因而,面对作者构建文本时产生的时间倒错和空白等,读者需要主动地参与小说进行文本的构建,以实现小说情节的积极意义。因此,作品意义的实现需要读者的挖掘,而作品独特的写作艺术恰能调动读者的能动作用进行文本建构。
发掘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建树。接受美学批评家伊瑟尔(1991)认为,在作者、作品和大众三者关系中,大众绝不是被动的存在。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它的历史生命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能动地参与和解读,作品才算真正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他同时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调动读者的能动作用,促使其对作品进行个性化加工,是因为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为这样的加工活动提供一种“预结构”,其包含“不确定的点”、“空白”和“否定性”。文本中不确定的隐含意义使阅读的过程会遇到许多空白,空白是“存在于文本之中,受到文本悬置的可联结性”。一方面,空白造成文本句子结构和意向性关联物的非连续性,非连续性可以不断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然后再打破它,让读者获得新的视域。(赵灿,2017)另一方面,空白是文本召唤读者的阅读的动力机制,读者以“游移视点”——联结诸多空白的动态结构响应文本的召唤。读者的游移视点在文本各部分之间穿行,并在阅读的连续不断的转化里,产生“由视野组成的网络”展现着相互联系的不同视野的多重性和流贯性。(仇睿,2009)因此,“文本的召唤结构”使文本成为了有待阅读的对象并召唤读者在阅读过程运用“游移视点”积极思考,以消除文本的不确定性、填充文本的空白、获取文本的意义。阅读活动的审美响应也便在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之间得以具体实现。
再读《阿尔巴尼亚圣女》,读者会用“游移视点”响应文本的空白。小说故事以框架故事为叙事起点,一位被称作洛塔尔的女子从岩石跌落陷入昏迷,进而被部落人带回库拉部落照料直至苏醒。文本的信息的不完全叙述使读者产生疑虑:向导为何被射杀?洛塔尔为何出现在荒野?为何跌落?这些疑虑在叙事中得以消除:洛塔尔只身前往意大利旅游,因向导与库拉部落人有仇恨,库拉人枪杀向导致马受惊,洛塔尔跌落昏迷。而后,故事转而叙述“我”初次探望夏洛特,正听她讲述洛塔尔的故事。此处,读者才能发现叙事结构是以洛塔尔故事为核心的框架故事结构。叙述第二次进入框架故事,部落妇女准备将洛塔尔卖给穆斯林男人,牧师及时出现阻止了这一行径,而代价是洛塔尔要成为圣女,过上男人般的生活。故事第二次转入现实故事叙事:“我”第二次探望夏洛特,继续听她讲述洛塔尔的故事。此处叙事时间被打破,转向我从夏洛特丈夫戈迪亚口中得知夏洛特住院的实情。故事第三次进入框架故事,洛塔尔成为圣女一年左右后,牧师担心她可能再次被卖掉,便带她逃离前往意大利斯库台的主教家。故事再中断,第三次转入现实故事叙事:1964年,“我”来到维多利亚展开新生活,开设了一家书店并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此处作者仍然留白,并未告知读者“我”逃离旧生活的原因。故事叙述第四次进入框架故事,洛塔尔和牧师顺利到达主教家,且洛塔尔被送往大使馆。“他们尽快把她送上了船。夏洛特停下来,说:‘这部分没什么意思。’”故事和现实交错,将读者带回“我”第二次探望夏洛特时的场景。随后,进入第四次现实故事叙事:“我”讲述自己到达维多利亚的原因,之后便是对书店几个常客的叙述,进而讲述“我”与夏洛特的结识。未多时,夏洛特与丈夫邀请“我”参加周日的晚餐。此处,读者通过动态的空白联结结构梳理“我”的人生故事线,并以“我”和夏洛特的结识展开梳理夏洛特的人生线。叙事场景转向书店,店员向“我”谈论夏洛特,但我们尚未获知谈论的内容,叙事便在此戛然而止。转而承接“这部分没什么意思”部分,时间随即跳跃到“我”第三次探望夏洛特,第二天夏洛特和丈夫便彻底消失不见。“我”由此陷入沮丧,感觉生活失去了支撑。“我”便开始期待新的依靠出现,那便是情夫尼尔森。在“我”幻想与他度过美满生活后,转角,他便出现在了“我”的世界,和“我”共度了余生。现实故事幸福结局,框架故事也迎来剧终:洛塔尔的船只驶入迪利亚特斯,牧师出现在码头。
门罗以独具一格的叙述方法和结构技巧展开双线嵌套结构叙事,现实故事的讲述者“我”在医院听框架故事的讲述者夏洛特讲述洛塔尔的故事。而洛塔尔的故事是根据夏洛特亲身经历改编的,其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是夏洛特未曾公开的秘密。小说的框架故事线和现实故事线出现多次交错,而这叙事线交织,揭露洛塔尔、夏洛特和“我”的人生历程故事的面纱,将看似平行的故事放在一张联系网络中,再经由时空错乱使不同的故事进行了重叠,正如现实叙事线和框架故事结尾,引人无限遐想,“我”发现“我”的内心依靠在书店门前等待;洛塔尔发现她的精神支柱在灯火阑珊处等候。由此,文本的召唤结构引入读者参与阅读活动与审美的再创造,在思考文本建构的过程中不断否定期待、建立期待,通过想象和经验来联结空白、填补空间,以达成阅读建构的完整性、连贯性和逻辑性。因此,读者运用“游移视点”对文本的积极建构如下:
框架故事的故事话语:B(1)—A(1)—B(2)—A(2)—D—F—H—L。
现实故事的故事话语:I(1)—G—I(2)—C—E(1)—J—K。
小说故事话语:I(1)—G—I(2)—E(2)—C【AB】—E(1)【D】—J【FHL】—K。
2 叙述视角转换及其审美价值
《阿尔巴尼亚圣女》采取了全知视角、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和选择性全知视角。框架故事叙事整体采用了全知视角,即上帝视角,展开对洛塔尔独身前往意大利后的人生历程的讲述。但在全知模式中,出现多次向选择性全知视角的转变,叙述者选择限制自己的观察范围,仅仅揭示一位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想。“她能闻到松木的气味。他们还坐了一会儿小船,她那时醒过来,看到了天上的星星,明暗闪烁,位置变幻一簇一簇摇移着,令她很不舒服。后来,她才想到,他们那时肯定是在湖上。斯库台湖,或叫施罗德湖,或叫斯坎德湖。他们扯着芦苇爬上岸边。毯子里满是水中的小虫,都爬在她腿上裹着的碎布上。在旅途的终点——尽管她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终点。”在洛塔尔陷入昏迷时,这种含混的状态使一切都模糊不清,叙述者此处选择将全知视角转换为选择性全知视角,将叙述的范围缩小至与人物的视角一致,给予读者亲身体验洛达尔意识不清晰状态下的代入感。同时,申丹指出,“这种转换可产生短暂的悬念,增加作品的戏剧性。”也就是说叙述者明明知晓真相,却故意引而不发,为情节的递进增加了一丝神秘,也给读者带了一丝求知的诱惑。
框架故事叙事向现实故事叙事的转变整体上使视角从全知视角转向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由夏洛特的叙述转变为“我”的叙述。“我”向读者讲述“我”如何逃离、如何开启新生活、如何结识神秘的夏洛特夫妇、如何从夏洛特处听闻阿尔巴尼亚圣女的故事。结尾处,尼尔森突然出现在书店的门口,“我”会做出如何选择?当作者将现实故事里的叙述视角限定在“我”的亲身经历之上,读者便能更好地站在叙述者的视角下感受、观察、思考叙述者的情感状态等。“我们一直非常幸福。我经常感到彻骨的孤独。人生中我们总会有所发现。日日月月年年都会模糊地飞逝而过。总的来说,我很满足。”诚然,“我”忘记曾经想要摆脱一切的逃离,只是选择再次陷入爱的漩涡,体验着关系的“疏远、亲近——疏远、亲近——周而复始”。
根据伊瑟尔的审美反映理论,整个本文永远不可能被读者一次感知,因而,在读者的记忆和期望的交汇点上,存在“游移视点”,由于游移视点并不唯一地处在任何一个视野之中,所以读者的整体性感知只有通过联合这些视野才能建立起来。(赵红妹,2007)事件H叙述洛塔尔和牧师到达主教家,随后洛塔尔被送上船去领事馆。“他们尽快把她送上了船。夏洛特停下来,说:这部分没什么意思。”此处,虚构故事和现实故事交错,叙述视角由全知视角转为第一人称有限视角。读者的视野由此被带回“我”去医院探望夏洛特并听她讲述事件H。而因为现实故事叙事在回忆和现在来回跳跃,读者无法将上述视野与某部分联合,只能将其保留,等待互相联系的视野出现。当将读者读至事件I(2)和事件J部分,第一人称有限视角下保留的视野便可与之产生逻辑联结,完成该视角下构筑文本的不可或缺的集合活动。“‘我得告诉你一点儿关于那个女人的事。’夏洛特走后,店员对我说。”“‘这部分没什么意思。’‘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说,在医院的第三个下,我在走神。”过去和现在的视野在读者的游移视点下产生积极作用,将不同的小视野连接成大视野,即“我”第二次探望夏洛特时听她讲述事件H。
因此,由于文本的叙事结构模式复杂,叙事视角在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有限视角之间交替变化,读者在阅读活动中需要运用阅读的自我调节机制,使游移视点在文本视野中不断穿行,并将已经实现了的过去视野与有待于读者占领的视野融为一体,使读者在其时间流里,不停调动相应视角下的过去视野,连续不断地汇集在现在的视野下,最终将不同视角下的视野有机地构筑为一体,完成读者接受下地整体性、一致性构筑。
3 结语
门罗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能达成复杂深邃的审美体验,得益于其独出心裁的叙述艺术。门罗本人对于创作最著名的比喻是:“小说不像一条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你走进里面,待一小会儿,这边走走,那边转转,观察房间和走廊间的关联,然后再望向窗外,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周怡,2014)也就是说,作者在进行文本构建时,常常避免平铺直叙,而是利用时序错乱、双线交织、视角转换等叙事手法增加读者阅读的难度、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读者则积极响应文本的召唤结构,运用游移视点在文本中穿梭,反复填补文本的空白、拼接叙事的片段、探寻文本的意义、体验阅读的审美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