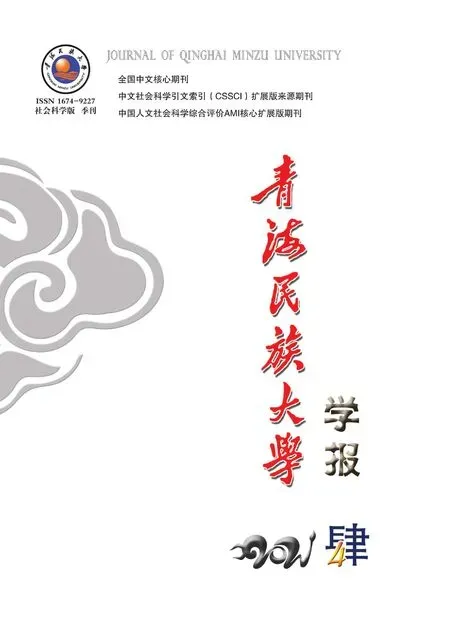“记忆之场”:凉山彝族的历史心性
——《鸡鸣之年》的文本进路
谷家荣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50500)
奴隶制是凉山彝族研究难以绕开的大题,以林耀华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均以不平等的阶级关系为起笔元点。在从事大小凉山彝区研究的多年时间里,林先生“格外关注等级问题”,[1]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深入四川大凉山腹地历时近三个月调查写成的《凉山彝家》,充分论述了彝族群体之间极不平等的血缘等级关系:黑彝为彝中统治阶级,黑白彝分别甚严,彼此之间无流动的可能性,绝无平等可言,而作为财产的锅庄娃子,主子可以随时将其变卖转让。[2]凉山彝家出生的潘蛟告诉我们,这种等级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具有族籍血统认辨特点的阶级压迫制度,最初起源于族际之间的征服奴役,[3]等级之间的出生血统认辩实质上也是一种阶级认辩。[4]由于奴隶主完全占有奴隶的权力关系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进行民主改革时,国家便“依靠百分之七十的奴隶和半奴隶,团结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者,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户数不过百分之五的奴隶主阶级”。[5]
嘉日姆几的研究当然不会脱离奴隶制这一大命题,他甚至认为“奴隶制对小凉山及周边地区社会结构的影响应该是深刻而全面的,它既是社会动荡的结果也是社会动荡的开始。”[6]但先辈学人都基本遵循群体导向(黑彝、白彝、娃子)视角研究凉山彝族,嘉日姆几则以民主改革时期安置家奴的“农场”为“记忆之场”,改道从“农场人”单位个体的生活真实去读写小凉山。在他看来,“小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发展与时势有着紧密联系”,[7]民主改革恰恰是中国多数少数民族当代史与近代史的分水岭,所以小凉山彝族社会文化研究无法绕开对民主改革这一重大事件的考察。[8]农场彝人的研究恰恰是学界最为短板的题域,他关心的问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改革后被集中安置在农场的彝人的“业态”究竟何为?这正是他花费十余年心血调查写就的新著《鸡鸣之年:云南小凉山家奴安置的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鸡》)的发问点。在《鸡》著里,嘉日姆几想要告诉我们,作为汉根彝人的“农场人”,民主改革之前所经历的一切“生命之场”皆成为其历久刻骨的集体记忆,它是农场人集体心智的最强塑动力。从此意义看,他笔下关于“农场”“农场人”的历史心性的陈述,与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研究法国历史时发明创造的“记忆之场”有着某种共通之义。诺拉的“记忆之场”犹如叙事的百货店,“既简单又含糊,既自然又人为,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它是一个“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9]回到云南小凉山,诸多远去的历史遗迹始终纠缠着农场人的记忆,“农场”是无法绕开的研究场域,《鸡》著精准锁定“农场人”,基于其口述叙事来识解凉山彝人的历史心性,可谓开了凉山彝族研究的新章。
一、“农场”:凉山彝族奴隶“鸡鸣之年”的后场
云南小凉山彝族奴隶制根深蒂固,作为奴隶群体的噶加、呷西长期从事繁重劳役,难有自由可言。1955年小凉山彝区开启民主改革试点工作,1956年全面推开,1957年新建“农场”,历时17个月,至1958年2月,17000名分居奴和14500名家奴全部交叉安置到51个农场,彝族奴隶的生活从此得到彻底改变。嘉日姆几于是把奴隶群体真正走出不平等阶级社会的1957年称为小凉山彝族奴隶的“鸡鸣之年”。
“鸡鸣之年”创建的“农场”让家奴真正告别了不平等社会。民主改革时期为了解决家奴基本生活问题,国家政策明确规定:“安置家内奴隶时,如有可归的应帮助其归家;无家可归、无亲属团圆者,应以自愿结合原则,安置其生产生活。”“除奴隶本人私房外,不从主家带出任何东西,所需生产生活资料,由政府给予适当补助。”[10]当时,记得亲人和愿意归宗的共有2488人,占家奴总数的27.2%,实在没地方可去的人就安置在农场。其实,如嘉日姆几所言,就是选择归宗的人也并非一去不复返,不少人由于无法适应汉区生活又回到小凉山,多数人都需要政府给予救助。考虑到实际情况,新成立的宁蒗县(小凉山)人民政府对家奴的住房、簸箕、筛子、茶罐、针线等均做了救济,工作可谓事无巨细。但家奴没有自己的家庭,过去在主子屋檐下都从事单一性的劳役,获得解放后难得自主生活,单独的物资补给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生计,所以当地政府才组建“农场”,把他们拢在一起集体生活。当年参与民主改革的老领导普贵忠说:“我门设想了一种形式,奴隶解放时分得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统一地办理伙食,由国家派干部进行领导,大力加以扶持。民主选举成立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实行统一留下生产成本、公共积累、口粮后,所余按劳分配。”这种“农场”既适应组织大家生产生活的需要,又解决了管理能力缺乏和老小残痴的赡养问题,可谓是小凉山的特色道路。
“鸡鸣之年”创建的“农场”开启了凉山彝人的新生活。1957年在小凉山调查的英国学者阿兰·惠宁顿曾见证了这样的场景:“一个干冷的早上,他们沿着木板坡道上上下下匆忙运土来修建农场主要建筑的围墙。妇女们在男人的另一侧工作,背着箩筐在富有弹性的坡道上飞奔,冒着齐地的百褶裙将他们绊倒的危险。我从来没有见过小凉山的奴隶们展现出如此富有激情和幽默的画面。”云南本土作家李乔在《小凉山漫步》里写到“一个站起来的奴隶”沙玛大姐一天的生活:“她干劲冲天,连日连夜同群众在一起,不停的干。开荒,积肥,挖地,什么都干,每天从天亮出去,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才回来,还要开会,布置第二天的工作,难怪平常许多人找她,难找得到。”[11]农场带来的新气象是全方位的,“‘农场模式’成为一汪引发历史意义的山泉。”[12]《鸡》著摒弃传统的“正负”影响抑或“对错”判断的研究进路,把作为线索、动力或轨迹的“农场”作为最为深刻而本真的表达,“农场”在他的笔下,也因此升华为最具特色的视角、内容与方法。[13]嘉日姆几把农场作为“记忆之场”,基于农场人的口述记忆,层层剥开民主改革之后小凉山彝族社会结构。他眼里,每个农场所采用的适合自己发展的组织“部件”发挥着不同齿轮的作用,他们既不同于彼此,也通过将自己联结成更大的小凉山彝族社会而成为一个整体,[14]所以在进行田野寻访的过程中,他尤其注重从不同角度切入农场人的生活,并自信满满地说:“尽管大家对农场的记忆和表述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并未让我们看到一个客观、完整和同一的农场,但恰恰是这些不同的视角和体验构成理解农场生活史的不同经验。 ”[15]
二、“农场”内外:凉山彝族民主改革后的“阶序”
小凉山彝族(诺、曲诺、噶加、呷西)奴隶制等级之间的世袭关系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占人口5%的诺(黑彝)和小部分富有的曲诺(农民)占据80%以上的耕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以上的家奴,而人口占大多数的奴隶,除嘎加(分居奴)占有少量土地外,呷西(家奴)根本没有任何生计资源,就连自己的身体都属于奴隶主的财产,甚至连家奴婚配后所生子女都是主子的财产。“绝大多数家奴来自小凉山周边的汉族地区,多数也是被掠夺而来的汉人。”[16]奴隶主通过掠夺、买卖和继承获得奴隶,其间的野蛮暴力根本就是凉山奴隶的一部血泪史。当然,如此遭遇也曾引起部分奴隶反抗。民主改革前夕,人们对“解放”、“改革”等概念所蕴含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也随着人们的议论而不断放大,其效果经舆论的传导淤积成不同程度的焦虑,一些人听说“解放”快要到了,还以为“解放”是一个人。但不管怎样,自“解放”这一概念上了山,彝人的心性便被彻底打乱。1950年大年三十夜,小凉山干海子坝家奴约甫和约戛邀约先后砍掉主子阿西热卡和阿西聂卡夫妇四人的头颅,逃跑未果,随后遭酷刑处死。不过,他俩从此成为奴隶心中的大英雄,一些人效仿其行为,铤而走险杀死自己主子,一时间凉山彝区闹得人心惶惶,奴隶主越发严酷看管家奴,一些不服管教的人直接被打残废,但残酷管教又进一步加剧家奴的恐惧和仇恨,几乎所有人都想逃跑。如此双重矛盾心理,牢牢困扰着每个凉山彝人的心。
民主改革终于打破传统的血缘等级“阶序”。1957年“农场”的出现真正挑破了凉山彝族血缘等级的第一道口子,彝族奴隶从此有了“农场村”观念。如此,也可以把这一年说成是小凉山彝族奴隶村落史的“开元之年”。就此话题,嘉日姆几发现,中国人类学的村落研究存在一个奇怪现象,即“历史问题一直以某种奇特的方式被回避”,[17]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研究的一大缺憾,所以在《鸡》著中,他“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历史、族群、区域、社会联系起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行走在历史中的凉山彝族社会。”嘉日姆几自谦说,这样的研究“似乎超越了村落研究本身”。[18]奴隶开启农场村历史,那些被解放的“新贵”彝人注定会与非农场村的“旧贵”彝人形成对立群体,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权力的出场骤然改变和抬高了彝族奴隶的身份和地位,过去处于高阶序的贵族群体一下子反倒成了被管教、改造及至后来被批斗的对象,小凉山彝族社会发生如此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农场人、非农场人、农场人与非农场人之间到底如何构造“我群”和“他群”意识便成了嘉日姆几所谓的“似乎超越村落研究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清楚地看到,民主改革之后,“农场村与非农场村空间形式上的依附关系变得更加明朗,农场村因国家权力的附着与高密化而象征着国家政权,使得其他非农场村在政治上依附于农场村。”[19]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嘉日姆几在后文提出凉山彝族“蛋形构造”社会结构模型的直接促动力。
首先,农场人与非农场人拒绝婚姻结合。民主改革后,农场与非农场的划分成为彝人最为重要的政治生活,农场村由此具有了阶级与等级的另一种象征标识,其间的阶级界限与彝人原有的等级界限重合,由此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凉山彝族。不过,今天的小凉山彝人,人们还是习惯将农场村定义为奴隶村,90%左右的彝族都选择生活在农场之外,他们都不愿意与农场人有血缘关系。“农场村既有黑彝,也有众多娃子的后代,还有几户曲诺,由于彝族社会固有的等级观念,他们虽然都住在一个村,但往来并不密切,特别是黑彝家,一般人都不会去,说是‘黑彝的鬼大,不敢去,去了会晕倒’。虽说不是绝对的老死不相往来,但也确实是‘不是一家人,不说一家话’。”[20]婚姻上,可谓是,“各走各的道”。黑彝(诺)有着强烈的血缘自豪感,始终觉得自己是整个小凉山彝区社会等级最高的人,但他们人数最少(沙力坪农场,黑彝只有1户,曲诺有20户,村落主体由“娃子”的后代构成),要想在当地真正立稳脚跟,还得迁就和依附百姓(曲诺)。
其次,农场人内部发展出一套新的婚姻形式。小凉山彝区的村落布局因农场人与非农场人各自的婚姻取向而得到全县范围内的整合,象征的异化引导农场人与非农场人在文化实践上有着各自的价值追求,最充分的表现就是他们的择偶行为有着门当户对的趋势,而这些导向性的择偶行为却无意中构成了小凉山彝区村落布局可以追踪的地理关系。[21]农场人并非全是家奴,许多分居奴、穷百姓和自由民也安置在农场里,群体内部的强烈认同关系,使得“农场人跨地域婚配,跨农场结合,结果将全县51个农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全新的彝区村落体系。”[22]农场村被赋予了治理、管理彝人与彝人谋求自我发展的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含义之后,农场、农场人、非农场人、等级、婚姻等问题依然在农场村的时空中继续被构筑与体验。随着彝人的流动,农场的记忆仍然以某种方式在脱域,在蔓延,而他们依然构成彝族人的历史、认同、尊严与情感。[23]但有些吊诡的是,在沙力坪农场,“有些农场人认为自己是黑彝的私生子,加上相对于周边加日、阿鲁等大家族的强势,有时这户黑彝和几户他们家过去的家奴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他们经常会相互帮工,彼此支援,‘各走各的道’的同时依然有着某种超越等级观念的认同。”[24]农场人对经济有着更为敏锐的感觉,也更加灵活,越来越理性的经济行为影响到他们的教育观,只要孩子愿意,非农场人则似乎更看重教育,由于人口流动所产生的经济理性意识,随着农场人的婚姻观念改变,其通婚范围跨出更广地域。十多年前,沙力坪农场的一位19岁的彝族姑娘就外嫁到了江苏省,只是由于诸多原因,最终该女子以悲剧收场。时下,除未跨越小凉山当地的传统婚姻界线外,农场村青年男女的通婚地域和对象都有了很大变化。
三、“凉山人”:作为“蛋形构造”的彝人共同体
小凉山彝族的阶级性在民主改革前后两个时段有着实质性差别。清末民国初年,最早进入小凉山彝区的阿鲁基足和足足克博正是抓住了权力,才得以成为小凉山的合法头目。嘉日姆几认为,“真正让阿鲁基足、足足克博在沙力坪成功立足和发展的原因……是清政府的嘉奖和扶持。”[25]从最开始的观望到最终痛下决心联合蒋宗汉镇压回民起义,阿鲁基足根本是看准了起义回民大势已去才决定投靠清政府。阿鲁基足根本就是靠着在各种势力中间投机而发家的。甚至可以说,“奴隶制度不仅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彝族统治阶级斗争、共谋的结果。”[26]直到民主改革前的三四十年代,川滇军阀混战使得彝区多股势力混存,小凉山彝族奴隶制仍处于高速发展期。凭着实力和正统性差别,黑彝、白彝和汉根彝人之间明确区分出两个完全不平等的阶层,血缘成为凉山彝人等级高低贵贱最根深蒂固的界分标准。但民主改革之后,凉山彝族内在的血缘等级意识与后入的权力阶级意识出现某种融合,其明确的表现是:“诺-曲诺-汉根彝人”之间的界线膜化为农场人与非农场人之间的界线,彝族群体的文化实践也出现真假彝人的价值判断,而这种观念根本就是“诺—曲诺”与“汉根彝人”界线脱胎而来的。嘉日姆几感叹说:彝人的族属认同又回到改革前,“血缘—等级”的边界虽然失去了原先的冰冷属性,却依然还承担着区分诺、曲诺与农场人的功能。在他看来,民主改革以来国家在凉山所实践的各种政策只是“膜”化了彝人观念中的血缘政治图式,凉山彝人的族属认同则因此呈现出某种“蛋形化”构造。[27]
如他所言,关于“蛋形”的灵感取形于“诺-曲诺-汉根彝人”之间的膜化特征,彝人群体彼此依存的三层构造使人联想到所有的卵生生命,故而嘉日姆几用“蛋形构造”来指称凉山彝人特有的族属认同所形构的社会特征。他认为,凉山彝人族属认同的蛋形特征在民主改革前就开始发育,诺(伙)群体是整个凉山彝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核心,曲伙群体围绕诺伙群体形成中间结构,汉根彝人则处在最外围。诺伙与曲伙,曲伙与汉根彝人之间界线分明,但民主改革使凉山政治格局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作为汉根彝人的“农场人”,其政治地位突起为中心,诺伙和部分曲伙则成为被改革对象,尽管有多数上层参加了新政府,但他们原有的经济实力和统治特权几乎被取消,他们只能夹在大多数曲伙和汉根彝人中间成为斗争的对象。如此,由外而内的阶级因素的切入,自汉根彝人成为政治中心之后,凉山彝人的整个族属认同被阶级认同暂时取代,其构造依然朝单核蛋形结构方向转换。[28]农场人“我是彝人,但不是真正彝人”的表述已经型塑了又一新主体,这个主体恰好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存在于彝族族属认同的蛋形构造中。其原因是,“民主改革后的阶级斗争提高了奴隶和贫农的政治地位,限制奴隶主和富农的人身自由,提倡政治婚姻,禁止跨阶级婚配,这与彝族社会原来的等级内婚重合并强化了等级婚姻在意识形态上的力量。由此,人为产生了另外一种‘阶级分治’的话语,而这些话语的政治实践却无形中强化了农场人与非农场人的‘他者’意识。”[29]于是,小凉山彝族社会某种程度上转变成了三个单核中心的结构状态,诺伙、曲伙、汉根彝人独自有着族群本有的结构圈,但整体又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蛋形社会结构,共同创构着小凉山的当下实践。
四、一种契合时宜的书写:对话口述叙事的“志”与“术”
经历过长时段的黑暗时代,小凉山彝族奴隶群体对民主改革前的遭遇有着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即便“鸡鸣之年”后过上“自我做主”的生活,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仍然是犹新的,特别是过去长期处于繁重劳役和遭遇主子野蛮对待的家奴,代际间话语相传和生活惯习培养的心性,终其一两代人的生命都难以清除心理阴霾。但正如杨·阿斯曼所言,集体记忆在空间、时间以及认同上都是具体的,集体记忆完全是站在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群体立场上的。[30]《鸡》著的最大亮点恰恰就是要让这些特殊人群拥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基于“农场人”的口述话语和生活行为借以分析研究民主改革之后小凉山农场彝人的真实生活。诚然,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所言,“对过去的知识在一切时代里都只是在服务于未来和现在时才被渴求的。”[31]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也认为“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即人们所有记忆的背后存在一个“社会框架”,“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32]照哈氏的看法,任何植根于特定情境中的个体,都是利用当下的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所以即便没有任何文化的家奴,当他们获得解放并以农场人的身份出场的时候,他们关于苦难史的个体抑或群体记忆都不可能摆脱民主改革所创造的客观生境,其口述话语都会附带上浓浓的“农场”色料,重提过去时,“农场”所隐射和象征的政治权力便会使他们安全地放大曾经的苦难,巧妙地收藏起一些内心深处的说辞,借以巩固难能可贵的当下身份。群体都拥有“修订”话语的心性,农场人的集体记忆和话语表述时都试图找到一个“志”与“术”的理想平衡点,心之所想,经由自我语言术的处理,其口述话语未必能将他们最真实的心志传递出来。观察对象此种心理的存在,大大挑战了研究者的田野工作能力,某种程度上说,此一环节的处理是直接决定研究文本质量好坏的至上标杆。
如何走好这关键一步,嘉日姆几对自己的要求是尽可能地寻回群体的自然本心。作为土生在小凉山的本地彝人,他这种“我看我”式的本族中心主义写作,何以本心,即何才能先清除掉“先见之明”本身又是一个挑战,倘若研究者自己不能拥有“白板”心理,那他目之所及、耳之所闻便皆是自我预先设置好的社会事象,奈你何能,也难写得出经得住大众目光检视的作品。对于这一点,嘉日姆几是非常谨慎的。第一代关注凉山彝族的学人主要走的是“由外而内”的学术理路,作为小凉山彝族,他天生具备“由内而内”的学术优势,但他的进路是暂且搁置下自己的熟悉耳目。2005年7月,他在云南大学组织起18位来自全国不同地方且毫无任何凉山经验的青年学生入场,全景敞视小凉山,想要借用这些“第三者”的自然目光去捕捉牵制农场内外彝人的敏感脉搏。效果是极为明显的,田野作业中,嘉日姆几如是说:“每天晚上的讨论都让人期待,因为学生们都会提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雁过留痕,“他们留下的问题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正是这诸多的“意想不到”逐渐让他拥有了重新审视过往事事的“第三只”眼睛,不再牢固坚守熟悉的地方知识,而是以一个“新来客”的身份再度审视田野。
凉山彝族奴隶的心性是复杂的,嘉日姆几在回访中再提过去,似乎又让一些人重新回到了曾经的“农场”,让他们在那幕挥之不去的记忆场景中再次相遇。1956年英国学者阿兰·惠宁顿在小凉山调查访问一位自杀未遂而从奴隶主家中成功逃跑的女奴隶阿硕乌嘎时这样写道:“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奴,不可思议地缺乏知识,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让她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1958年初我打电话约她见面时,她是宁蒗县缝纫社的一个纺织工人。阿硕乌嘎对她的出身并没有清晰的概念,一开始她说她是一个自小被遗弃的汉族,然后她又更正说她的父母才是被遗弃的,自己生下来就是奴隶。她作为陪嫁丫头来到女主人的丈夫家,她的主人是补余体日,拥有三十个奴隶。”民主改革后,阿硕乌嘎的经历,事后与自己曾经的主人补余体日同在县政府工作,但一个尴尬的巧合是她每一天吃饭的时候都在政府的食堂里碰到过去的主人,但两人“从来不说话”。带着“第二心性”去接触对象,嘉日姆几也像一个“外来者”,行走在小凉山这村那寨,他总是有许多意外发现和收获,故而他的笔触每每都能摸到了“农场人”的最深内心。他接触到的一个典型对象是巴嘎热。此人是当年《烂泥箐农场史》中唯一健在的口述报道人,世事多变,他早年随时势做过许多“大事”,所以在风平浪静的当代社会主动退隐深山。此人并不主动说话,与他面对面攀谈,几乎都是一问一答,嘉日姆几称他为“蜂子岩的隐士”。巴嘎热沉默寡言当然有原因,青年时不服主子管教,他独自跑到烂泥箐黑彝热柯家做娃子。1955年前后,多数娃子都知道解放军要彻底解放娃子,他于是主动接触工作队,及后参与了民主改革时期大小凉山彝区平息叛乱的军事斗争。嘉日姆几认为,当时的情形相当惨烈,无论是否打死过人,但他至少目睹和经历了别人被打死,闭口不谈过去,正是深谙彝族文化和习惯法精神,不愿意为这些“真相”的负面效果而承担不必要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年轻时勇敢的巴嘎热,老来势单力薄而不得不“隐居”,因为参加叛乱的人往往都是当地的大家庭,至今依旧根深叶茂。巴嘎热内心充满矛盾,行将就木的高龄老人,沉默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不同历史时岁,小凉山彝族的心性都会“应时势”而发生很大改变。就其姓氏选择一项而言,嘉日姆几就发现了许多趣点:农场彝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血缘并非彝族,但在融入彝族社会时,他们巧妙激活奴生子的传统理念解决了姓氏选择的问题,从而成为小凉山彝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场彝人姓氏选择应用了迁就、协商、投机等策略,其动机是追求各种利益与社会声誉。在血缘拟想的文化实践中,农场彝人精心选择的血缘纽显现出世俗与神圣的不平衡性。他们的姓氏选择得到了传统与现实的有力支持。[33]所以,想要最大限度地通达凉山彝人的心智,研究者自身也得巧妙地处理好自己的“志”与研究“术”,而在这个取向上,嘉日姆几恰恰有着别人不可多得的基质:不问英雄何路,结识了,他便毫无理由给予对方快意真诚。此其一。其二,不管生活风吹雨打,他唯恋在学术上“尽性子”。每每一篇新成的刊稿到手,甚或脑袋里新冒一个点子,他都会友好地约一壶茶,邀一帮听粉在某个街角大叙大谈,若有新著脱手,那经由他搭台的这种共赏仪式会变得更为隆重,不光赴约者成群,一些个学术上熬出成就的大脑袋也乐于与他叙谈,可越是有如此善谈能辩的名角出场,便越能挑逗起他言理说词的认真。《鸡》著中的很多“不解”,除精心求教于凉山彝人,更多疑点是在昆明街角找到的满意答案。
结 语
《鸡》著仅只提供了云南小凉山彝族奴隶的一个特殊个案。其实,民主改革之前不平等的奴隶制在四川大凉山彝区和西藏藏族聚居地区更为透彻,嘉日姆几也认为,“凉山奴隶制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部分,是鸦片战争在彝区的后果及历史表现。”[6]348如此,个案便有了一般性意义,云南小凉山“农场现象”的学术意义并非只有安置家奴那么简单,它暗含着理解近代以来彝汉关系的特殊命题,也意味着凉山彝族近代史有着中国汉人社会的贡献与基因。[6]24但不可否定的是,任何制度都有它的生命时势。嘉日姆几十分清楚地看到,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运动,民主改革尽管已采用协商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变革,但其作为外力切入凉山彝族社会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凉山彝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安置家奴的农场,其生产单位和组织模式的功能已取得成功,但如何整合农场与非农场社会的文化策略却没有得到重视,相反,以阶级组合为起点的农场村的政治实践强化了凉山彝族族内婚与等级婚姻的意识形态,致使民主改革的全部努力只停留在改革生产关系的层面而无法改变凉山彝族的文化结构,因此导致了今天的农场现象。[12]106从此一角度看,《鸡》著在完成小凉山“农场时段”的研究同时,又明确点破出新题,这更是此书的难能可贵之处。
——宁蒗彝族自治县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