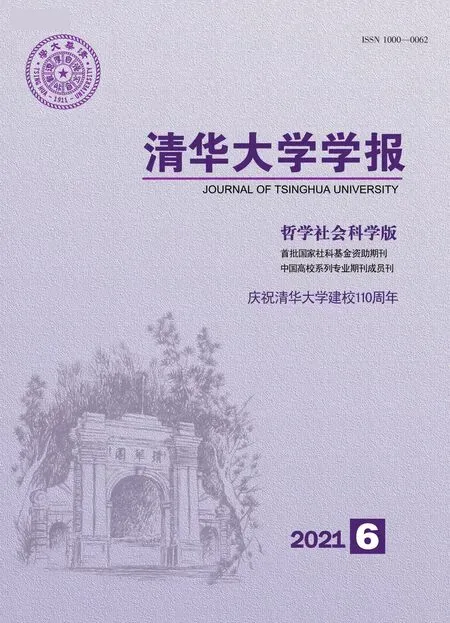外亦是内:护国战争前后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合离
徐君玉
晚清以来,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任何对既有权势结构的挑战,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列强的利益,产生列强干预的可能。外国人对中国事务参与之深,其观听甚至可以直接影响中国的政局。①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94、195页。面对中国已不断被卷入世界的事实,中外各方力量常常通过结纳或自设外文报纸来扩张自己的舆论阵地。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Thomas Ming-heng Chao(赵敏恒),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Preliminar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Four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o be Held in Hangchow,from October 21st to November 4th,1931;李瞻:《外人在华创办的报纸》,见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第125—190页;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冯悦曾研究过日本在华创办的英文《华北正报》,对北洋政府时期京津地区英文报刊的情况做过一些分析。见冯悦:《日本在华官方报:英文〈华北正报〉(1919—1930)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不过,这些研究较少展现外文报纸具体是如何影响中外舆论的。意识到需要向外人表述自己的中国各政治势力,也力图在外文报上发声。故外报上的言论虽多言外交,实关涉内政,对中外的舆论、政局走向有很大影响力。
英文《京报》(Peking Gazette)就是一份曾发挥过重要的舆论作用,被各方争夺,至今却较少得到关注的外文报纸。护国战争前后,梁启超的信件中屡言及英文《京报》,这份报纸不仅刊登了不少梁启超的文章,且一度被视作梁启超的机关报。然而正当旁人皆视《京报》为梁氏喉舌之时,双方的合作却戛然而止。以至既往学者研究梁启超的言论活动时,多未关注到梁启超与该报馆的关系。③曾业英和李德芳先后注意到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首先刊登于英文《京报》,但并未涉及梁启超与该报馆之间的关系。见曾业英:《云南护国起义的酝酿与发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德芳:《梁启超〈异哉〉一文的公开发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本文梳理护国战争前后英文《京报》与梁启超及其同人关系的转变,尝试再现梁启超言论活动中被忽视的面相;并通过考察这一时期《京报》对中外舆论的影响,展现民国初年英文报刊在政争中的特殊地位及护国战争前后外交与外论对国内政争的重要影响。
一、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联合
报纸是近代中国新兴的传播媒体,一些读书人也逐渐认识到其重要的政治作用。陈衍就注意到,公法不能“折强邻”,报馆却能“张国势”。在他看来,报馆的作用“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故中国宜开设洋文报馆,“散布五大洲”。①陈衍:《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求是报》第9册,1897年12月18日。王韬更主张:“中国之所宜自设者,不在乎华字日报,而在乎西字日报。盖日报而系华字,而传而诵之者,只华人而已,西人则无从辨其文义也。”②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04页。
孙中山后来曾列举在华设英文报刊的三点优势:一为“直接参加于世界舆论”;二为“生外交上积极的作用”,期得物质、精神援助;三为“生外交上消极作用”,排斥各种侵略主义。③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8页。可见英文报刊发行量虽小,意义却不小。对于深感有必要“张国势”的中国人来说,在华设立的外文报纸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仅外侨大多选择阅读外文报纸,驻华的外国记者或通讯员也常通过阅读外文报来获取新闻材料,以馈其国读者。④Thomas Ming-heng Chao(赵敏恒),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pp.2,3.
1913年9月20日,英文《京报》在京创刊,由德华银行的驻京代理人鄂葛岭(Alfred J.Eggeling,?-1946)出资,著名英国报人伍德海(Henry G.W.Woodhead,1883-1959)主办。据伍德海回忆,在英文《京报》创刊之前,北京的英文报纸仅有由朱淇主办的英文《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一家。由于《京报》能够全面、迅速、准确地翻译公文,很快成为了当时中国境内所有公使馆、领事馆和海关必备的报纸。直到一战爆发,伍德海与鄂葛岭出于各自的国家立场,在报纸刊载内容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1914年10月下旬,被伍德海请来帮忙办报的英籍华人陈友仁(Eugene Chen,1875-1944)趁机从鄂葛岭手中买下《京报》并自任主编,直到1917年该报停办。鄂葛岭将《京报》出售给陈友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该报能在英、德间保持“中立”,而陈友仁又有意不公开《京报》所有权变更的情况,因此当时不少人认为《京报》是一份反映德国利益的报纸。⑤H.G.W.Woodhead,A Journalist in China,London:Hurst&Blackett Ltd.,1934,pp.53-61.据日本外务省1915年1月之前的调查,《京报》表面上纯然由中国人所有,背后则仍由德国当局掌控。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の資料「支那ニ於ケル新聞紙ニ関スル調査」を引用する場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40676700、2支那ニ於ケル新聞紙ニ関スル調査2(1-3-1-17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该调查截止于1915年1月。日方当时对该报馆的实情可能并无把握,甚至在报告中错把陈友仁的中文名写成了“陈友琴”。到同年7月,《顺天时报》还指斥德国人经营的英文《京报》在离间日英同盟。⑦鲲:《〈京报〉离间日英同盟之蜚语》,《顺天时报》,1915年7月20日,第2版。
这位买下英文《京报》的陈友仁出生在中美洲的一个英属岛屿上,早年在当地做律师。辛亥革命爆发后,不通中文的陈友仁只身来到中国,通过主编英文《京报》为时人所重视,并与当时政界诸多重要人士都有往来。后来陈友仁跻身政界,多次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以推行“革命外交”政策著称于世。⑧Wu Lien-Teh(伍连德),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Cambridge:W.Heffer&Sons Ltd.,1959,pp.309-310;钱玉莉:《陈友仁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101页。但这位后来的国民党要人主办《京报》期间却一度在言论上批评、反对国民党人,反与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
梁、陈二人何时相识待考。1914年12月1日,英文《京报》增刊汉文部,梁启超特撰祝词,⑨梁启超:《〈京报〉增刊国文祝辞》,《京报》汉文部,1914年12月1日,第3版。代为宣传,表明双方关系已较亲近。此后梁启超便频频在《京报》上发表文章,大多关涉对日外交问题。这些文章不仅刊登在汉文部,还常常由其女梁思顺、女婿周希哲等人转译为英文刊登在英文部中。当时驻德公使颜惠庆就注意到:“截止1月底(1915年)的《京报》满篇都是评论日本的文章,主要是梁启超的文章。”①《颜惠庆日记》,1915年3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184页。不仅如此,《京报》馆中还有不少梁启超同人。英文《京报》初设汉文部时其主笔是梁门“三少年”之一的蓝公武,②“英文《京报》附设中文《京报》,今日出版,蓝公武为主任”。见《专电》,《申报》,1914年12月2日,第2版。蓝公武离开后,继任主笔梁秋水则是康有为受业弟子。③蒋贵麟:《康南海先生弟子考略》,见李方名辑:《蒋贵麟文存》,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1、142页。时人回忆说,梁秋水熟习英文,好谈政治,民国初年来京办报,和梁启超、汤化龙等人有往还,经常到汤化龙处接谈,后来成了“研究系”中之一员。华觉明:《解放前北京的著名新闻记者》,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25、226页。1915年2月27日,梁启超致信梁思顺时特别嘱咐道:“《京报》事易孙姓者决不可别聘,林亮功专译英文则可。”④梁启超:《致梁思顺》,1915年2月27日,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18页。这里提到的“孙姓者”指《京报》翻译员孙几伊,1915年他因事离开北京,所以辞去了《京报》馆的翻译工作。孙几伊后来又在《大中华》杂志、《国民公报》《时事新报》几家报馆“帮办报稿”或“充当访员”,⑤1919年因《国民公报》违反出版法,京师警察厅将报馆编辑孙几伊扣留,孙几伊在供词中说:“民国三年,我在英文《京报》当翻译。民国四年,我回南。”《京师警察厅为将孙几伊送厅讯办致京师地方检察厅函(稿)》(1919年11月4日)、《附抄:孙几伊供词》(1919年10月28日),见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中的北京五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61、262页。这些报刊那时都与梁启超同人关系密切,可见孙氏属于这一松散的事业团体。而梁启超的嘱托也暗示着此时梁氏对《京报》报馆的人事安排颇有话语权。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特别注意旁人如何看待他与《京报》之间的关系。1915年2月间,他在给张一麐的信中谈到他与《京报》曾订立契约:
英文《京报》初约弟作文时,弟与严订契约,谓言论须完全独立,若有他人授意彼报,强我作者,我即立刻与彼报断关系,且穷诘其资本所自来,彼言绝无外资,弟乃应其聘。⑥梁启超:《致张仲仁》,1915年2月,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10页。
当时外界对《京报》已多有由德国资助的猜疑,从梁启超这封回信中可推测,时任总统府秘书的张一麐对《京报》就有所顾虑。实际上梁启超的态度也有保留,他在为《京报》作《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一文后,要求刊登时“篇首仍作数语,云本报请某人赐文一篇,幸得许可,为此不胜荣幸云云”,以“示偶作,非常作”,⑦梁启超:《致梁思顺书》,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第390页。此笺书信在《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被排在1915年8月23日任公致梁思顺信之后,实际时间当在1914年12月19日以前。徐君玉:《梁启超两封书信的系年问题(上)》,《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2期,第302页。似不愿将契约关系公之于众。“仍”字则透露出梁启超已非第一次要求在读者前隐去那频繁的文稿之约。
梁启超对《京报》既欲避嫌实又倚重的态度,反能说明当时英语报纸在争取外交与外论上的重要意义。既往研究已多注意到,“二十一条”期间袁政府曾积极利用外文报纸影响国内外舆论以牵制日本。⑧如王芸生、李毓澍等人的著作皆有提及。李永春专文讨论过“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政府的“新闻策略”,但他把英文《京报》和英文《北京日报》误认是英人所办报纸了。见李永春:《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实际上,袁政府不仅向端纳、莫理循等外国驻华记者透露消息,也积极利用英文《京报》和英文《北京日报》这两份由华人所办的外文报,只是当时知情的官员和办报人都有意隐去了报馆由华人经营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实情。1915年2月22日中日交涉第三次会议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就曾因英文《京报》和英文《北京日报》“登载交涉内容甚详”,向中方抗议,要求公布两报与外交部之关系及是否为中国人所办。当时日置益已经知道英文《北京日报》为朱淇所办,对英文《京报》则知之尚少。①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115页。
英文《京报》自创办初与袁政府的关系就非同寻常。鄂葛岭聘请伍德海时曾向对方承诺无须为德国服务,只须伍德海“遵循支持袁世凯的总方针及其政府的集权化政策”。且伍德海是该报唯一的外籍编辑,其助手中就有候补的中国官员。②H.G.W.Woodhead,A Journalist in China,pp.54-56.陈友仁初到中国时,经伍连德(1879—1960)推荐被交通总长施肇基聘为交通部法律顾问,不久又被总统府秘书处聘为秘书,专门从事对外宣传。③钱玉莉:《陈友仁传》,第18页。后来伍连德更坦言陈友仁办《京报》得到过政府的资助。④Wu Lien-Teh(伍连德),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310.早年在北京从政、与汤化龙过从甚密的华觉明也回忆说,那时“政府当局为博得外国人的同情,很重视这种英文报,不惜重资援助它们”,陈友仁主办下的英文《京报》就是外交当局拨款7万元授意创办的。⑤林华(华觉明):《忆北洋政府后期的北京新闻界》,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昔年文教追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3页。可知《京报》当时就是政府有意结纳或主动培植的对外舆论机关。
英文《京报》实际由英籍华人陈友仁“独资”经营,但在名义上是外国人创办的外文报纸,这使该报在言论上获得了不小的自由。那时梁启超的女婿周希哲在外交部供职,与陈友仁熟识,很可能了解到一些报馆的情况,进而促成了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合作,梁启超也积极利用英文《京报》影响外交和中外舆论。作为当时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势必吸引国内读者的目光,英文《京报》因此一度走向国内舆论界的中心。
二、《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
梁启超与《京报》的稿约虽然是从对日外交问题开始,但双方最著名的一次合作却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以下简称《异哉》)。该文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不仅仅是对国体问题的学理探讨,更是一次代表集体的政治行动。选择在英文《京报》上发表《异哉》,是梁启超与同人谋定而后动的结果。
由于《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八期曾刊载此文,并注明出版时间为“民国四年八月二十日”,致使不少学者认为该文首先刊于上海的《大中华》杂志。其实《大中华》并未在1915年8月20日如期出版,《异哉》首先发表于英文《京报》。⑥已有学者关注到《异哉》发表时间问题,见曾业英:《云南护国起义的酝酿与发动》;李德芳:《梁启超〈异哉〉一文的公开发表问题》。直至9月3日《异哉》已由《京报》刊出,《申报》才有消息称梁启超欲对国体问题发表意见,表示对于“任公之煌煌大文”,“吾人拭目俟之”。⑦《筹安会之最近消息》,《申报》,1915年9月3日,第6版。可见当时《申报》馆员还未读到《异哉》一文。而《申报》的消息和评论完全摘自8月30日的《京报》汉文部,一字未改。《京报》已明言这是“本报英文部访员所得消息”,并称,任公“此文撰就,方欲邮寄沪上,刊诸《大中华》杂志。事为某某要人探知,即由京电致任公,请勿将此文公布”。⑧《国体问题与梁任公之言论》,《京报》汉文部,1915年8月30日,第3版。可知梁启超欲对国体问题发表意见的消息最初就是从《京报》传播出去的,这也是《异哉》一文要“刊诸《大中华》”的最早消息。
其实梁启超早有将《异哉》登于《京报》的想法。1915年8月21、22两日筹安会开会宣告成立,23日梁启超给梁思顺的信中写道:“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①梁启超:《致梁思顺》,1915年8月23日,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第388、389页。可见文章刚刚写成,梁启超就已托人带入京中寻求同人意见、准备登载,而译登英文自然是登在《京报》上。
从上引23日梁启超的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撰文时相当愤慨,下笔作文及入京登报的决定不免受到情绪的影响。据吴贯因回忆,当时他在北京,“闻任公此文草成,出天津索观之(时任公居天津)。原稿比后所发表者较为激烈……后有人语以袁氏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乃将此段删去,其余各段比原稿亦改就和平”。②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1页。吴贯因所言应该代表了京中同人对原稿的态度,所以梁启超延缓了在北京发表的计划,对文章多有修改,甚至一度考虑改为发表在上海的《大中华》杂志上,相对减少几分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意味。
前引8月30日《京报》消息中曾特意指出:“筹安会之发起曾自声明对于国体问题以讨论学理为范围,该会且极欢迎。然则任公之煌煌大文,不独为筹安会所欢迎,并将为我言论界欢迎者矣。”③《国体问题与梁任公之言论》,《京报》汉文部,1915年8月30日,第3版。有意将筹安会的活动约束在“学理范围”内。次日《京报》英汉双版登载“本报访员”与梁启超关于国体问题的谈话,并称这是“梁先生首次公开发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④The Monarchic Question:Views of Mr.Liang Chi-Ch'iao,Peking Gazette,No.6,Aug.31,1915.这篇访谈与随后发表的《异哉》一文相比,前者重在批判主张中国不适合共和的“外国博士”古德诺,后者则屡次将矛头直指筹安会诸人。可见这段时间梁启超曾反复调整自己的表述,一度为筹安会诸人留有余地,仍寄望于袁世凯能够维持共和。
最终《异哉》一文维持了梁启超最初的想法,在北京率先发表并译成英文。9月3日,《京报》汉文部几乎以全部版面刊登《异哉》,英文部因来不及翻译全文,先以“生死问题”为主标题对文章观点进行了概述,随后两日英文部又转译全文,⑤The Life and Death Issue:Mr.Liang Chi-Ch'iao on the Monarchic Movement,Peking Gazette,No.6,Sep.3,1915;Liang Ch'i-Ch'iao:Republic to Monarchy!Peking Gazette,No.6,Sep.4,1915.轰动一时。《京报》也因此“即日售罄无余”,一时间洛阳纸贵,“售至三角,而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⑥《国体声中之见见闻闻》,《神州日报》,1915年9月11日,第3张第2版,见曾业英:《云南护国起义的酝酿与发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82页。
《异哉》一文公开发表时间和地点的变换,恰说明梁启超及其同人在文章刊登问题上的反复琢磨。最终选定由英文《京报》首刊,应有特别的考虑。盖《异哉》如果仅发在《大中华》《国民公报》,就等于主动放弃了一次“直接参加于世界舆论”的机会,不易争取外人舆论的同情。而在袁世凯称帝前如果能通过外交压力,或更能迫使其放弃帝制。文章首刊于英文《京报》,显示出梁启超对《异哉》一文在外交与外论方面产生作用的重视和期待。
《京报》名义上是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其言论活动往往享有比本国报纸更多的自由,可见当时外文报纸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盖外报更能够刊登一些国内报纸不便刊登的消息和评论,这些文字经外报登载,又可以“出口转内销”,以转载的形式亮相于中文世界。姚公鹤就注意到,那时的中文报纸经常大量译载外报内容,因为“转登外报,既得灵便之消息,又不负法律之责任”。⑦姚公鹤:《上海闲话》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113页。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驻华公使日置益就曾抗议说,交涉内容一经《京报》登载,“其他之汉文报纸即转而译载之,于是喧传于外”,激起中国人的反日情绪。那些消息显然是中方有意透露的,但外交部却称《京报》为外国报纸,暗示其不受管辖。⑧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115页。
有意思的是,《京报》当时很可能受到袁政府的津贴赞助,却在帝制运动声势浩荡的北京率先刊发梁启超反对帝制的文章,足以说明《京报》曾是梁启超在舆论界重要的伙伴。而梁启超发表《异哉》的计划从预告到最终刊载,消息、谈话、文章无一不由《京报》率先刊登,随后又被《申报》《新闻报》等中文大报转载。可见外文报纸的读者实已蔓延至各转译报刊的读者群,不可因其发行量小而低估其舆论活动对内的影响力。
言论家通过外文报向外国人表述自己,进而影响外国舆论、获取外交上的有利地位,但当外国舆论本身成为一种权势后,它所关涉的就不仅是外交了。《异哉》一文译登英文部后,《京报》汉文部曾特别向读者介绍“西人钦佩梁任公之议论”,这位“西人”说道:“鄙人近于北京《京报》得读梁任公先生所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篇,深叹先生之胆识为不可及,所有谬误之点无不经先生道出。至论墨西哥爹亚士一节,尤为透辟。彼一般中西人士学识简陋,道德薄弱,贸然引以为中国之殷鉴,几陷中国于危险,宁不羞煞?”①《西人钦佩梁任公之议论》,《京报》汉文部,1915年9月8日,第3版。由于古德诺曾举墨西哥等国之覆辙以证中国适合帝制,且国体问题本因古德诺的谈话才引起广泛的讨论,所以这位“西人”攻击的首要对象自然也是古德诺。但此番议论未见刊载于当日的英文部,可见编辑心中所想反而是中国读者。
以近代中国尊西之盛,即使是反对西人的话,从西人口中说出也能更具威慑力,何况是反对国内的政治力量。作为一份“外报”,《京报》不仅可能影响外国人的观听,自身也部分扮演着“西人”的角色,使它的赞同者、反对者都有意予以重视、回应。②护国战争期间,反袁的《民信日报》论证中外一致倒袁时,“外人之舆论”即以英文《京报》劝告袁世凯退位为例。诚哉:《国民之责任》,《民信日报》,1916年4月9日,第1张第3版。而对方的回应,又使《京报》深入地参与到国内政争之中。
三、国内外共指的“机关报”
一如梁启超从联袁到反袁,护国战争时期《京报》的言论立场逐渐由北移南,从劝袁世凯缓行帝制,到公然主张袁世凯退位,可谓和梁启超步调相近。1916年1月12日,外交部曾致电驻美公使顾维钧说:“陈友仁近日借报反抗帝制,此次滇乱,妄登谣言,故政府信用与前大异,现正严嘱注意,姑观其后。李亚(Rea)处现若接收所寄消息,嘱勿轻于宣布,嗣后宜由执事处直接探取。”③《发驻美顾公使电》,1916年1月12日,《外交档案》03-13-043-02-001,见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46页。按,李亚(Geor ge B.Rea)是美国人,在上海办有《远东时报》(Far East er n Revi ew)。当时北京与日本方面的外交关系已十分紧张,袁政府正极力挽回各国对帝制及云南起事的态度。《京报》显然登载了一些不利于袁政府的消息,外交部的电令恰表明那时英文《京报》对外交和舆论有相当的影响力。
直至护国战争接近尾声,在上海居丧的梁启超依然重视《京报》这一言论机关。袁世凯去世后,时局亟待各方协商解决。1916年6月26日,见梁启超托子女们转告陈友仁“英文《京报》文日内当赶成”,并解释说,因为自己不轻易发言,“故全国各报皆无文字发表,《国民公报》所登告白,不过一种虚约耳”。④梁启超:《致梁思成、梁思永》,1916年6月26日,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第444页。此信似是梁启超致梁思顺,或由思顺转交思成、思永。梁启超以往均嘱托梁思顺帮办《京报》事务,不可能让尚未成年的思成、思永去转告陈友仁。信中虽有“汝等学业近何如”及“成、永何久无禀报”两句,但此信并无起首语,信末也没有写明“示某某”,梁思顺作为长女有教导幼弟的责任,这两句话同样可能是问梁思顺的。以梁启超维护共和的功绩,可想而知那时他的发言会受到各界关注。梁启超不打算将文章发表在和同人关系密切又刚刚复刊的《国民公报》上,反而答应为英文《京报》作文,可见梁启超对《京报》相当看重,且对陈友仁极为客气。又如由梁启超代拟的军务院撤销布告,系致英文《京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中华新报》四家报馆,将英文《京报》排在首位。①《唐继尧等宣布撤销军务院通电》,1916年7月1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4页。此函由梁氏拟定,参见梁启超:《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1916年7月1日,见氏著:《盾鼻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54页。这四家报馆中,《国民公报》《时事新报》那时与梁启超同人关系密切,《中华新报》则被认为是护国军的机关报纸。②梁启超:《致蔡松坡第二书》,1916年1月,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43页。《京报》得与上述三家中文报馆齐名,可见梁启超将之引为同路。
双方展现出的亲密关系,致使《京报》后来批评旧国民党人时多被视作是梁启超的发言。由于袁世凯突然离世,新局势一方面加速了全国性战争的结束和黎元洪继任、段祺瑞组阁的达成,同时又造成各方合作的基础(反袁)不复存在,各派间的政治分歧逐渐浮现。梁启超稍后就坦言“自身既有首尾未清(如军务院及松、循交涉等)之事”,同人“又非能同时尽闭门避地,其言论行动,旁观咸认为有连带责任,而以着色眼镜之眼光观察之”,行止间往往进退两难。③梁启超:《致季常七兄书》,1916年7月27日,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93页。梁启超提到的“军务院及松、循交涉”之事,《京报》都发表过时评,对梁启超多有溢美之词,难免令旁人视《京报》为梁氏“机关报”。
护国军军务院是具备临时政府性质的机构,成立前蔡锷就曾担心军务院将“启南北分裂之渐”,故不赞同。④蔡锷:《致陈宦电》,1916年5月7日,见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2页。袁死后龙济光立即宣布取消独立,与李烈钧等人再起战事,南北冲突不断。梁启超力促唐继尧撤销军务院时,军务院从成立到取消为时不过两月,护国军向北京政府提出的要求还未全部达成,有人批评梁启超此举是“急欲与段祺瑞接近,思以撤销军务院为功”,“列名电中之抚军,多有事前未及备知”,“所以奉梁氏以阴谋家之徽号”。⑤《军务院撤销之内幕》,《护国军纪事》第5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20、21页。《京报》反将梁启超促成军务院撤销之举与李烈钧等人“掠取地盘”对比,称这些“南方领袖”忙于为自己猎取官位,而置身政坛外的梁启超是“真正捍卫中国自由”的人。⑥Abolition of Military Council,Peking Gazette,No.6,July 18,1916.
由于湖南督军兼民政长汤芗铭被护国军逐出湖南,造成督军、省长职位空缺,“争湘督者”就“闻有七、八”。熊希龄等人提出戴戡督湘,立即遭到黄兴一派的反对。旧国民党人劝说黎元洪任命谭延闿为省长,梁启超明知“某派苦无地盘,争湘甚力”,自言最好“李烈钧督湘,组安(谭延闿)为省长”,不必“徒增恶感”,旋即又转变态度,向段祺瑞提出由蔡锷任湘督兼省长。⑦《上海梁任公来电》,1916年7月7日到,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5页;《上海梁任公来电》,1916年7月21日到,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册,第538页;《请允蔡入主湘政致大总统段总理电》,1916年7月25日,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册,第543页。以至李书城向曾继梧抱怨:“湘事波折甚多,皆因中央别有用意,兼之熊、梁弄鬼。”⑧《李书城复曾继梧电》,1916年8月1日,见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9页。
不同于梁启超游移的态度,与梁启超同人关系密切的《时事新报》自始就对旧国民党人在政治上积极活动抱有批评,林昶在《时事新报》上斥责黄兴一派争湘督为“暴民政治之动机”,不过他并未归罪于黄兴、谭延闿本人,而将之归罪于黄、谭周围的“策士派”。⑨覆瓿(林昶):《敬勖革命家》,《时事新报》,1916年7月13日,第1张第2版。而《京报》的言论比《时事新报》更加激烈。《京报》汉文部主笔梁秋水将矛头直指“党人”,认为他们“除有一二躬临前敌或暗中运动联合者外,其余碌碌,因人成事,非发表一二无责任之宣言,即拍发一二不相干之通电,如斯而已。苟竟以此居功,施施然自海外返国,自命为伟人,为政客,或竟运动为总长,为总理,为督军,为省长,岂不惑耶”。①秋水:《正告党人》,《京报》汉文部,1916年7月18日,第3版。此文发表时间距离黄兴归国(7月6日)相差不过数日,无疑极具指向性。②后来黄兴致电《京报》馆:“希望世界之和平与进步,并切望中华民国同循此轨道,惟言论界诸公实主张之。”言语间不乏自辩与责备“言论界诸公”之意。见黄兴:《致北京英文〈京报〉电》,1916年7月29日,见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第24页。由陈友仁主笔的《京报》英文部同样在猛烈地抨击旧国民党人。传闻唐绍仪电荐李烈钧为广东督军,于是《京报》英文部指责唐绍仪暗中与孙、黄结盟,并认为“这种新的结盟是危险的,因为那些和唐绍仪结盟的人无论是气质还是方法上,无不是革命的、破坏的……他们被认为是无法胜任现代国家建设、没有长远眼光的人”。③A New Triumvirate?Peking Gazette,No.6,July 31,1916.
在此政治形势波云诡谲之时,新任司法总长张耀曾(1885—1938)又卷入私土案中。张耀曾是云南大理人,又是旧国民党人。当时段祺瑞为表南北融洽,内阁成员多选用“南方”的新派人物,任命张耀曾为新内阁的司法总长。张氏由云南入京赴任时,被查出他乘坐的火车上携有大宗私贩烟土。英文《京报》随后屡次刊文怀疑张耀曾以官员身份犯法,有损国家颜面。八月底张耀曾同某报记者谈话时,说最近“梁启超一派与国民党有反目之事”,他计划“从事调停”,④《张耀曾氏谈话之内容》,《顺天时报》,1916年8月27日,第2版。又谈及英文《京报》“前月已不受梁氏指挥”,说《京报》“有叛梁之志”,言下之意,数月前《京报》曾受梁启超“指挥”,使梁秋水不得不在《京报》上为梁启超辩白。⑤秋水:《正告张镕西氏》,《京报》汉文部,1916年8月28日,第3版。
这并非《京报》第一次澄清该报言论的独立性。计划“从事调停”的张耀曾有意将那时的《京报》与梁启超区分开,旁人却不一定赞同。《京报》的激烈言论为梁启超引来了不少敌意。1916年7月25日,《神州日报》“揭露”同为广东梁姓的梁秋水为梁启超之兄弟,而《京报》“攻击国民党首要甚力,闻系梁秋水受乃兄意”。⑥《专电》,《神州日报》,1916年7月25日,第1版。7月26日,《民国日报》以“吾为英文《京报》惜”为题,称:“近日该报攻击前国民党各要人及国会议员不遗余力”,“总主笔李心灵本某派人物”,此举是“某某授意”。⑦《吾为英文〈京报〉惜》,《民国日报》,1916年7月26日,第2版。“李心灵”虽然不是《京报》总主笔,但他是广东新会人,同样可能在暗指《京报》为“梁派”。7月29日,梁秋水即在汉文部澄清。⑧秋水:《本报宣言》,《京报》汉文部,1916年7月29日,第3版。随后数日,英汉两部又反复强调机关报纸一说是国民党人“为夺取护国运动真正的领导人地位”而造的谣言,《京报》“纯由陈友仁君主持一切,陈君非某政党或他种政党之党员,亦非某政党领袖或他个人之党与”。⑨The“Kuo Min Tang”:the“Peking Gazette”and Mr.Tang Shao-Yi,Peking Gazette,No.6,Aug.4,1916;“The Peking Gazette”:What Has Been Said of It,Peking Gazette,No.6,Aug.11,1916;《本报与国民党》,《京报》汉文部,1916年8月7日,第3版。
在对日问题上,《京报》的态度同样给梁启超带来麻烦。《京报》自“二十一条”交涉以来,一直持反对日本的言论态度。大阪《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日本报纸每日译载《京报》社论,恒指其“为梁任公之机关”,梁秋水为“梁任公之兄弟”。梁启超在上海演讲,有日本人私下向梁启超同人质问梁氏主张中日亲善,何故其机关报纸《京报》连日反对日本。⑩秋水:《释日本人之误解》,《京报》汉文部,1916年9月16日,第3版。可见,这一时期英文《京报》一度成了国内外共指的梁氏机关报。
四、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殊途
当他人还以“机关报”一词攻击《京报》时,陈友仁主持下的《京报》英文部却逐步出现了与“机关”身份不相一致的言论。实际上,陈友仁并非梁启超的追随者,《京报》反复澄清与梁启超的关系,也表明双方不是亲密无间。在国内政争中,陈友仁与梁启超同人在政见上产生矛盾,最终导致双方走向殊途。
共和再造,国会重开,《临时约法》的恢复意味着中华民国的政体回到了内阁制,然而也埋下了府院权限模糊不明的隐患。国务院中,段祺瑞的得力助手徐树铮“事事以己意为段意,指挥黎氏画诺”,①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页。总统府里,黎元洪又有意在政治上有所表现,最终酿成府院之间互不相容。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及其同人政治立场趋近段祺瑞,陈友仁则选择为黎元洪抱不平,双方政治主张多见分歧。华觉明回忆,当时《京报》汉文部主笔梁秋水“与进步党有关系”,陈友仁“与国民党也有接洽”,“并与黎元洪方面亦有相当默契”,陈氏对段祺瑞“常有尖锐批评”。②华觉明:《解放前北京的著名新闻记者》,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226页。因此,《京报》不仅与《时事新报》观点不同,《京报》英文部和汉文部也难以保持步调一致。
1916年8月,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丁世峄起草《府院办事手续意见书》,提出总统参加国务会议的要求,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抗议此举干涉内阁行政,双方争执愈演愈烈。8月18日,《时事新报》有电文称丁世峄“到处鼓吹”,主张恢复总统制。③《丁世峄主张恢复总统制》,《时事新报》,1916年8月18日,第1张第2版。随后连日批评,谓徐树铮擅权,丁世峄复以总统为傀儡,企图通过总统制把持政权。④《丁秘书长与徐秘书长》,《时事新报》,1916年9月1日,第2张第2版;《某政客之大政策》,《时事新报》,1916年9月2日,第1张第3版、第2张第2版;《评府院办事手续意见书》,《时事新报》,1916年9月3日,第2张第2版。与之相反,《京报》英文部刊文认为在现行《约法》下,并非内阁,而是“执政总统的行政部门”对议会负责。⑤General Tuan Chi-Jui,Peking Gazette,No.6,Aug.26,1916.《京报》称其“坚信今日与中国现行有机的法律相符合之唯一制度,即以黎总统为首领之政府。总统依据《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及第四十四条,有权选任特别一部之文武官吏(称为国务员)以为己助”。故府院间的风潮“系由国务总理之策士,谋将总统在《临时约法》中规定之权限汇聚于总理掌握而来”。⑥《论中国之内阁制度(其一)》,《京报》汉文部,1916年8月30日,第3版。译自The Chi nese Cabi net Sys t em,Peki ng Gaz et t e,No.6,Aug.29,1916。在这次府院冲突中,陈友仁无疑倾向于批评国务院一方。
陈友仁与梁启超同人相左的态度,在第二次徐州会议召开后更加明显。9月22日,张勋联络十三省代表在徐州开会,通电反对外交总长唐绍仪、司法总长张耀曾。面对督军团公然以军人身份干涉政治,梁秋水在《京报》汉文部发表时评,认为“徐州会议无论果结若何,其惟一可惧者在甲派势力与乙派势力不相容,卷起政界万丈波澜”,主张“民党”对徐州会议“负消极责任”,“应从大局起见,一言一行务须格外慎重,不可稍形偏激,酿成其他变端”。⑦秋水:《评徐州会议》,《京报》汉文部,1916年9月29日,第3版。当日,《时事新报》也有短评“劝民党阁员勿相率引去,重演元年唐内阁之故事”,“劝国会数百议员勿自相惊扰,致牵动国会本身”,“劝国中舆论界认清范围,向要害处用力”。⑧《内阁风潮》,《时事新报》,1916年9月29日,第2张第2版。但陈友仁主持下的《京报》英文部对梁启超同人的调和论视若无睹,很快就站出来指责徐树铮参与徐州会议。《京报》英文部刊文揭露徐树铮“利用徐州会议以钳制国会,威吓民党”,计划“使段氏得代黄陂而为元首”,①The Chief Secretary of the Cabinet,Peking Gazette,No.6,Oct.3,1916.主张将徐树铮撤职、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以防总统不测。②The Vice-Presidency,Peking Gazette,No.6,Oct.2,1916.
10月4日,《京报》英文部载辛博森(Bertram L.Simpson,1877-1930)与段祺瑞的谈话,文末刊登了一篇《京报》记者的长评,将“七月间总理反对恢复约法;八月间府院冲突,总理涉嫌侵占宪法赋予总统之职权;九月间更为危险的徐州会议还有据传的南苑事变阴谋”与徐树铮、段祺瑞贪权联系起来。③Putnam Weale:General Tuan Chi-Jui on the Situation,Peking Gazette,No.6,Oct.4,1916;An Explanation and Some Comments:the Premier,His Cabinet and the Hsuchow Conference,Peking Gazette,No.6&7,Oct.4,1916.按:Putnam Weale是辛博森的笔名。辛博森的访谈发表后广受关注,多家报馆争相转载。有趣的是,转载的报纸中《时事新报》仅载有访谈,并以大字重点标出段祺瑞的意见:“总统不独具有宪法上之权力,须得内阁之绝对赞助以谋良善政府。”④《段总理与辛博森之谈话》,《时事新报》,1916年10月8日,第1张第3版、第1张第2版。态度恰与《京报》针锋相对。国民党系的《民国日报》反倒不惜以三日分载长评。⑤《英文〈京报〉之中国政局论》,《民国日报》,1916年10月5日,第6版;《英文〈京报〉之中国政局论》,《民国日报》,1916年10月8日,第6版;《英文〈京报〉之中国政局论》,《民国日报》,1916年10月9日,第8版。
双方的矛盾最终导致梁秋水从《京报》辞职。10月5日《京报》中文部刊登了梁秋水辞职的告示,次日中英双版都刊登了《京报》的回应,称《京报》社长(陈友仁)认为“有必要辞退现在中文部的编辑”,且不友好地补充说明:
本报向以维持国家之利益,增进国民之幸福为宗旨,不存党见,不徇私情。如前次对于倡议抗袁之人,本报不问其为进步党抑国民党,皆一律赞助不遗余力。又如国民党攻击段祺瑞氏时,本报亦曾拥护段氏。即今日本报反对一部分军人之专横,亦悉本斯旨。盖此为今日国家最重要之问题,凡独立之报纸,对于此事,皆当尽其天职,不得袖手旁观,缄默不言也。梁秋水君对于时局所持之意见,与本报根本上之宗旨不合,故不得不与本报脱离关系。⑥“The Peking Gazette”,Peking Gazette,No.6,Oct.6,1916;《本报启事》,《京报》中文部,1916年10月6日,第3张。
言下之意,梁秋水对于“一部分军人之专横”缄默不言是“存党见”“徇私情”。当日《时事新报》就有“梁秋水因与英文《京报》英文部意见不合,已脱离该报关系”的专电。⑦《北京专电》,《时事新报》,1916年10月6日,第1张第2版。可见梁启超同人同样注重梁秋水与陈友仁的“意见不合”。
10月11日,梁启超致信梁启勋,谈及英文《京报》事:
《京报》近日论调太离奇,据此间所闻,确已受府中五万。且友仁就顾问职月,八百元云。虽未敢具信,然其态度实不能不予人以可议。即使仅为一群流氓所利用,则亦危险已甚。荐柳隅未尝不可,但柳隅安能支配友仁之意思?若仅为彼作写字机器,则又何必。且前此国内外共指《京报》为我机关,而我之意见实不能支配彼,从前受累已不少。柳隅与我关系之深,天下共闻;若就此席,机关报纸之说愈征实,则代人受过无已时,不如其已也。此意已属溯初面告,弟谓何如?友仁处或令希哲稍忠告之,若彼诚干净,则劝其勿为人利用也(吾辈初非袒徐树铮,然流氓之可厌更甚。友仁若受欺,则宜以友谊忠告之,彼若悟,尚可议携手耳)。⑧梁启超:《致梁启勋书》,1916年10月11日,见中华书局编辑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32、333页。此信原件未标示日期,具体考证见徐君玉:《梁启超两封书信的系年问题(下)》,《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2期,第336页。
由该信可知,梁启勋可能不希望放弃《京报》这个舆论机关,故建议由吴贯因(柳隅)代梁秋水继续担任《京报》汉文部编辑。而梁启超认为《京报》被视为他的机关报纸已是“代人受过”,由吴贯因担任编辑,不仅不能改变《京报》的态度,且可能使《京报》再度被视作“机关报”,故不同意。
梁启超说《京报》“受府中五万”,指报馆得到黎元洪方面的津贴资助。顾问一职则指陈友仁可能受聘为总统府顾问。那时报馆记者在外兼职或收受津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经常为《京报》撰文的辛博森就被聘为总统府顾问。后来王新命回忆说,段祺瑞“在他所主管的国务院设置一些顾问咨询的员额,供收买报人之用,此风一开,北京各机关都有这类领干薪的恶例,因此有些报社通讯社的老板便借此实行了又要聘编辑又不给薪水的怪制度”。①曹聚仁著,曹雷编:《听涛室人物谭·上一代的报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5页。此风未必为段祺瑞所开,不过聘编辑可以不给薪水,可知此现象已成为当时报界的常态。陈友仁办《京报》之初就有交通部法律顾问、总统府秘书等挂名闲职,《京报》也领过袁政府的津贴。相较于受聘为顾问,陈友仁的态度令梁启超感到“可议”,更是黎段府院之争进一步激化的结果。②关于黎段府院之争,见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51—65页。
由于府院间“无事无时不冲突”,③张国淦:《北洋从政实录·中华民国内阁篇》,见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43页。黎段双方愈发不可调和。黎元洪在国会内外引旧国民党系政治势力为己援,促使梁启超及其同人拥段的政治立场更加鲜明。梁启超称“吾辈初非袒徐树铮”,恰恰表明现在已经有意袒护,“流氓之可厌更甚”,则不免将一己之见凌驾于公论之上。督军团以武人干政,攻击国会和旧国民党人,已逾出正常的议会政治轨道,梁启超同人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参与其中的徐树铮保持缄默,无怪旁人有“存党见”“徇私情”之感。
通过主办《京报》,陈友仁、梁秋水一时成为政治家眼中值得笼络的人物。梁秋水曾提及,1916年5月15日审计院股长杨汝梅到《京报》馆拜访他,又到黎元洪处鼓吹“英文《京报》颇有势力,宜与联络”,并自任可介绍其记者梁秋水来见,④秋水:《述不佞与杨汝梅之关系》,《京报》中文部,1916年7月5日,第3版。杨汝梅是湖北人,武昌起义后担任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的审计院审计官,称得上黎元洪的旧僚。有意充当梁秋水与黎元洪间的介绍人。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里,陈友仁经人介绍拜访了孙中山,据说两人相谈甚欢。⑤陈丕士(陈友仁之子)曾回忆说:“大概在1916—1917年的某个时候,我父亲就被介绍同孙中山先生认识了……(宋庆龄)告诉我,郭泰祺博士在1916年领我父亲到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孙宅去见孙先生的。”见陈丕士:《中国召唤我——我参加中国革命的历程》,郭济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1页。盖两人都讲英语,当时都对段祺瑞、张勋等北洋武人持以批评态度。这次会面成为陈友仁走向革命的萌蘖。1917年5月,《京报》刊文披露段祺瑞与日本磋商军械合同,达成后需将陆军管辖权交付日本,陈友仁因此被捕入狱。⑥《外电》,《申报》,1917年5月21日,第2版。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后,6月4日,由曾经受《京报》攻击的司法总长张耀曾呈请,陈友仁得大总统令特赦。⑦“司法总长张耀曾呈北京英文《京报》记者陈友仁因案判处徒刑,其情不无可原,请予特赦等语。本大总统依照约法第四十条,将陈友仁原判徒刑特赦,免其执行。此令。”见《申报》,1917年6月7日,第2版。陈友仁出狱后离开北京,南下追随孙中山,成为革命党人,不仅疏远了梁启超,也疏远了北京政府。而梁启超留存的书信中,也再无与陈友仁来往的痕迹。
五、结语:尝试影响“外人观听”的努力
护国战争前后,梁启超和英文《京报》合作密切,由于相近的政治主张,英文《京报》一度成为时人眼中梁启超的机关报纸。这段合作将英文《京报》推向国内舆论界的中心,成为当时国内外政治力量都无法忽视的一个舆论机关。双方因对日外交问题产生合作,最终在黎段府院之争中走向分离。英文《京报》与梁启超的这段合作过往,展现出外交和外论对中国政治的重要影响力。
英文《京报》受到梁启超的重视,因为它是一份能够影响外交的英文报纸。1917年12月梁启超等人发起创办英文《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大概就有失去英文《京报》这块舆论阵地的影响。当时不仅中国各政治势力需要通过在华设立外文报争夺外交主动权,欲在华谋取特殊权益的日本同样寄望于办外文报纸缓解国际舆论压力。1919年,日本创办英文《华北正报》(The North China Standard),①冯悦:《日本在华官方报:英文〈华北正报〉(1919—1930)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26页。也是为了在京津地区抵制他方外文报纸对日本在华主张的负面影响。
由于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为近代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在华设立的外文报纸不仅具有外交意义,也同样关涉内政。当中国还未有一份自己的外文报时,熊希龄曾痛心于各国控制下的外文报捕风捉影,煽动是非,“吾国政府应办之内政,亦多受其影响,几不能出各国势力范围之外”。②熊希龄:《拟设环球通报社呈赵尔巽文》,1907年5月14日,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1册,第290页。但各国可以通过舆论将中国的内政问题牵连外交,国内的政治力量同样可以利用外文报纸主动把内政问题诉诸世界舆论。这些谈政治和干政治的中国人未必情愿列强干涉内政,却又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主动寻求“世界”的支持。孙中山后来想要在上海设一英文杂志时指出,设立英文机关不仅可以在“言论上得与外国周旋”,同时可以“为吾党政治上之主张、建设上之计划宣传于世界”。③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8页。梁启超发表《异哉》时要求译成英文,也正是希望通过外人可读的舆论工具影响外交,以转变国内政治。
英文《京报》是一份读者以外国侨民为主的英文报纸,而驻华外交人员本身就是外侨的一个组成部分,读报的外侨以及能读英文报刊的中国人又是他们关于中国和各国讯息的重要来源。当时频繁出现的“外人之观听”一语,既可以是真正外国侨民的“观听”,也可能指向侨民背后的外国,反映其国家意旨。④关于“外人之观听”的影响,见罗志田:《国家目标的外倾——近代民族复兴思潮中的一个背景》,《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这类“观听”不必意味着直接的干涉,却仍可影响中国的政局。一些中国人显然认识到了这样内外纠缠的格局,故试图通过英文舆论参与或影响“外人之观听”,进而改变中国的内政。在陈友仁主办期间的《京报》,就是这样有意识地参与到国内政争之中。而梁启超的所作所为,也表现出同样的意图。
梁秋水从英文《京报》辞职后,熊希龄曾专为此事致电梁启超,谈及《京报》“宗旨忽变”,他与梁秋水“欲另办一中英文报,以维持外交、舆论”,并强调办一份外文报纸“实属目前要图”。⑤熊希龄:《请筹措办报经费致香港梁任公电》,1916年10月30日,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册,第635页。当时《京报》对外秉持着国家主义的立场抨击日本,论调与一年多前几无差异,这“宗旨忽变”的观感,显然来自国内政争中《京报》的立场不再和梁启超同人保持一致。
反过来,中国人在一份英文报纸上反对本国的内阁总理,不仅赋予了内政问题参与世界舆论的机会,也使熊希龄等人不得不考虑外交上的影响。可见民初内政与外交不可复分已成为时人的共识,即使没有外国势力的“在场”,各派政治力量也常有把“中国问题”当作“世界问题”来处理的倾向。熊希龄所说中国内政“几不能出各国势力范围之外”一语,最能揭示出当时内外因素的关联互动。这种内中有外,外亦是内的格局,在此后的时代里仍在继续发展,牵动着中国政局的走向。梁启超与英文《京报》这段向被忽视的合作经历,展现出中国人有意参与和影响“外人观听”的努力,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这一长期存在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