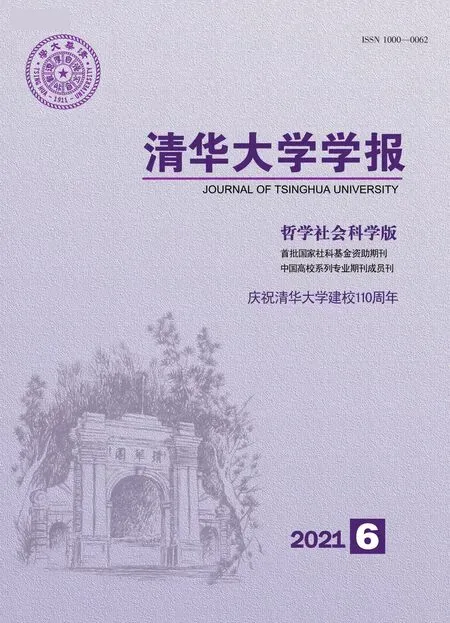全球分裂与世界文化新生态
高小康
一、“全球分裂”到文化多元主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他的另一本书《全球分裂》,标题更有冲击力,内容也更有特色,影响却远不及《全球通史》。《全球通史》初版是1970年,因为视野开阔、结构恢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正处于启蒙时期,这样的宏论更受人喜爱,在中国多次再版。《全球分裂》1981年初版,1993年才有了中文译本。这本书虽然标题有冲击力,内容主题和观点尖锐深刻,但在中国的影响却很有限。往往在中文网上搜索“斯塔夫里阿诺斯”时会直接导向《全球通史》而不及《全球分裂》。这两本书的不同遭遇,实际上是20世纪后期的时代变迁中,中国看世界和世界图景的演变所留下的一个轨迹。
《全球分裂》有个副标题“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该书的话语背景是“三个世界”语境。作者指出:“‘第三世界’一词起源于最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刚刚开始使用。”①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页。本文简称《全球分裂》。把世界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美苏两大阵营中的其他发达或中等发达国家,第三个是由南斯拉夫、埃及、印度、印尼等国发起独立于两个世界的不结盟运动,而后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这是个起于冷战时期的概念。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三个世界”话语作为处理国际政治关系的根据,在改革开放后这个概念逐渐淡化,而到90年代冷战结束后对于世界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个时期更引人注目的话语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托夫勒(Alvin Toffler)等人的未来学和全球化概念的流行。在这个时代话语背景下进入中国的“全球分裂”观念显然不合时宜,受到冷遇也是正常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000年之际,学术界关于世界关系的认识又产生了反转,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理论受到重视。但这时候“全球分裂”的“三个世界”话语背景已经消失,被更新的亨廷顿“文明断层线”理论取代了。
虽然《全球分裂》这本书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书中对“全球分裂”观念的论证仍然值得注意。作者所定义的“三个世界”形态不是从冷战开始,而是从新大陆殖民主义时代就开始了。书中第一编“第三世界的出现”是从1400年到1770年商业资本主义走向全球的殖民化进程;其后的三编依序论述的是“全球性体系”形成的三个阶段:1.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770—1870),2.垄断资本主义和全球殖民主义时代(1870—1914),3.第三世界为独立而斗争的时代。①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目录页。书中作者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形成是和殖民主义以来“全球性体系”的形成相联系的概念。“全球分裂”的背景是工业资本主义以来的“全球性体系”形成的三个阶段及其冲突。“全球性体系”与“第三世界”发展的三个阶段实际上就是作者关于全球化进程的理论,揭示了现代世界整个大的国际关系不断体系化整合又不断冲突分裂的反复振荡趋势——当下人们如同世界末日来临般惊恐地哀叹全球化走向结束,但放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现代世界视野中看,不过是一再反复出现的又一个分化周期而已。
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描述的全球分裂的最后形态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天下大乱”和全球性对抗的社会革命爆发期,冲突对抗的主要力量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及其联合体,主要由超级大国、华约、北约和“第三世界”构成。但在《全球分裂》出版后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冲突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和“三个世界”关系的重构。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把这个巨变解读为世界文明和价值观最终趋向统一的走势。未来学派对未来的大趋势提出了充满想象力的乐观期待,如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2000年大趋势》中提出的90年代到2000年世界发展的十大趋势:世界经济繁荣、艺术复兴、自由市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全球化、福利国家私有化、环太平洋崛起、妇女跻身领导阶层、生物学时代来临、宗教复活和个人的胜利……②奈斯比特:《2000年大趋势》,夏冠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目录页。福山和奈斯比特这种乐观主义全球化想象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一个典型的标识就是亨廷顿所说的“达沃斯文化”的出现:
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③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44—45页。
这种“达沃斯文化”是影响全球化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文化圈,但亨廷顿认为这个文化圈只是许多文化中的精英层次,社会基础很浅。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影响多数情况下只是表现为一些技术和消费需要而不是真正的全球文明共享。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全球流行的“大麦克”(Magna Mac,巨无霸汉堡)。然而很多非西方的文化对西方文明是选择性的:只要“大麦克”而不要大宪章。他把当代这种选择性倾向称之为“第二代本土化现象”。④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90页。显然他对这种“本土化”持消极看法,认为这种对西方的选择性吸收并不会带来世界文明的融合。
本土化的发展意味着在“达沃斯文化”的全球化浮沫下面,文化多元主义开始崛起。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包含着民族、地域、宗教、历史文化等多重关系的更复杂的冲突开始了,而以2001年的“9·11”事件成为一个顶点标志。斯塔夫里阿诺斯描述的“全球分裂”是以“三个世界”区分的民族国家集团冲突为核心,而自20世纪末进一步分化为多层次、多元化的族群文化冲突。这个时期引起人们更多重视的不再是福山和奈斯比特,而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化社会的西方化……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①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5页。
亨廷顿关于多极、多文明全球政治冲突的观点是对冷战后全球化想象的批判,他把新世纪产生的这种多文明全球政治定义为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冲突”。他认为文明是比民族国家概念更大的“终极的人类部落”,断层线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②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28页。在全球化观念影响甚大的20世纪末,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极具震撼性,有的学者专门著文反驳他的理论。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冲突又使得人们似乎发现了他的先见之明,“断层线冲突”几乎成为全球新冷战的理论根据。
然而,亨廷顿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能证明文明“断层线”在强化。他指出西方文明并没有因为全球精英即“达沃斯人”的传播而普泛化,当代经济和文化消费的全球化也没有使得西方文明影响到其他文明,“大麦克”的消费没有推进“大宪章”精神的传播。但这种悖离的真正意义并不是断层线的强化而是文明发展趋势的多样化。“达沃斯人”和“大麦克”促进了全球不同文化既交流又分化的趋势。
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谈到新几内亚的恩加人在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和掠夺之后,正在反转过来利用现代文化促进本土建设、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谈论这一反转趋势时萨林斯使用了“本土化”这个概念,他称之为“现代性的本土化”。③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22页。他提到恩加人在自己的歌中表达了以一种蜂鸟吸取花蜜的态度对待现代文明的成果,“变西方人的好东西为他们自身生存发展的好东西”。④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第12页。这就是他所说的“现代性的本土化”的范例。
地方的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本土化”两种相对趋势的冲突与互动,成为20世纪末到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复杂性特征。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在日益走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中,必须确保属于多元的、不同的和发展的文化特性的个人和群体的和睦关系和共处。主张所有公民的融入和参与的政策是增强社会凝聚力、民间社会活力及维护和平的可靠保障”。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ht t p://por t al.unesco.or g/en/ev.php-URL_ID=13179&URL_DO =DO_TOPIC&URL_SECTION=201.ht ml。提出这个宣言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保护文化多样性来消弭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分裂与冲突。
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全球分裂”,政治基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及其政治诉求,用政治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来说,就是基于“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⑥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而形成的现代国家政治冲突。然而二战后的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人口流动、移动传播瓦解了传统的空间和社区,通过种种分形组织的社会形态构建出多维多层次的社会关系。这些新兴的流动空间社区和社群关系冲击、解构着传统空间基于民族、宗教历史延续性和地理关系构成的文明“断层线”,形成了更复杂的当代文化关系及其边界。
近年来,瑞士文化学者霍伦施泰因(Elmar Holenstein)在关于当代世界文化差异及其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跨文化差异经常小于文化内差异。他以“克劳西斯代际悖论”(Croces Paradox der Gernerationen)为例说明“每种文化不仅是传承序列的最终一环,而且也是波形展开的跨文化转达的结果”。①霍伦施泰因:《人的自我理解》,徐献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69页。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看,全球分裂的文化差异基础不一定是以历史传承为核心的“想象的共同体”,可能更多的是当代跨文化传播形成的新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关系。
二、熔炉、马赛克与“流动空间的草根化”
霍伦施泰因在谈到陌生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时理出了四条文化影响的支线:阿拉伯、中国、印度和“原始”文化,“它们或多或少地轮流主导着跨文化转借的阶段”。②霍伦施泰因:《人的自我理解》,第177页。他的关于几种文明影响的说法,源自启蒙主义以来西方关于世界文明差异的认知和走向世界文化共同体想象的发展。但真正在当代社会管理实践的意义上寻求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建设,与其说是理论思辨的成果,不如说是当代社会组织形态的演进实践。例如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社会文化冲突中形成的多元文化权利保护就是这样的实践。关于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起源,有学者认为应溯源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知识界谈论的“大熔炉”(melting pot)观念:
社会学家使用了一部关于犹太移民话剧的题目“赞格威尔”,构想了一个大熔炉的图像,在这个大熔炉中形形色色的文化、信仰、肤色将会融合,最后产生空前的全新的事物。这个熔炉的构思,为充满种族和族群冲突张力的美国移民社会提供了团结的新希望。③陈国贲:《城市的内在混合性:一项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美国自建国以来通过各种法律和公共政策努力构建不分来源、族群和宗教的“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身份。“大熔炉”是一种从美国建国的原则和纲领开始逐渐生成的社会价值观,基于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为核心共识的国族价值理念。20世纪中期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政策承认了族群的多元性,但仍然坚持着“大熔炉”的国族统一性观念。二战后形成的所谓“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④“美式和平”是套用“罗马和平”(Pax Romana)的一个借喻,指超级帝国统治和安排的国际和平秩序。的世界秩序,把这种美式价值观作为人类共识向全球推广,并成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关于人类普遍史构想的根据。⑤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然而“大熔炉”价值观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个人的自由选择与社会认同、族群归属之间的矛盾。拓荒时期的美国,以个人为中心和对自由的高度重视形成了“西部牛仔”式人格的刻板印象和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红脖子”农民形象。这种好莱坞化的“美国”形象,既是欧洲移民带来的文化传统,也是特定生态环境选择的结果。而大工业城市化之后社会关系改变了,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大熔炉”遇到了危机。
20世纪50年代,专门从事现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发现,在现代化都市中的社会关系不是那种熔炉式的融合一体的关系,而是“生态”关系——这种关系由每个人各自的文化归属、经济地位、职业等诸多条件构造起来的生态环境生成,相互之间是分立并置而不是相互融合的关系。生态社会学代表人物帕克(Robert Ezra Park)在研究城市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时指出,城市人口分隔的过程“使城市分裂成许多小世界,这些小世界互相毗连,但却不互相渗透”。⑥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2页。这里描述的城市社会不再是大熔炉,而成为许多“小世界”拼嵌而成的马赛克结构。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在追求赋予黑人平等权利的同时,再次促进了美国作为种族“大熔炉”的理想。但是,随着70年代美国各大城市中心区的衰落和郊区的兴起,美国的种族关系发生了“从熔炉到马赛克”的转变:白人和黑人基本上在不同的“马赛克”里聚居,成为事实上的种族隔离。①黄湘:《弗格森骚乱与美国黑人发展困境》,《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4年8月30日。都市社会学家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
在1960和1970年代,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及特殊的都市议题,已经与芝加哥学派那时所要处理的问题很不一样了。社会/文化的整合不再那么重要。关于都市—工业社会的控制与取向的斗争变成都市问题中最重要的课题。此外,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对发展与工业化的概念提出挑战,也需要关于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新形式以及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每件事都在剧烈地争夺、论辩、相互斗争,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团体间就互相冲突的利益和选择性计划(alternative projects)进行协商,彻底扬弃了在一个共享的文化底下得到整合的概念。②卡斯特:《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刘益诚译,《国外城市规划》2006年第5期。
熔炉与马赛克的差异是从殖民拓荒时代到都市化之间的变迁产生的矛盾与转换。在殖民化进程中产生的启蒙主义与进化论史学、人类学相信人性的共同性和由此产生的历史发展前景的总体化:文明走向统一的世界性是人类进步的大趋势,从相对独立发展的“轴心期”到相互接触,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必然趋向融合——或者是“涵化”(acculturation):大鱼吃小鱼、先进吃掉落后;或者是“调适”(adaption):相互妥协融合。大熔炉的文化根据就在于这种世界文明走向大一统的想象。
与这种进化论世界史观相反,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是较早意识到共生文化之间不相融关系的学者。他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假晶现象”(pseudomorphosis):
一种矿石的结晶埋藏在岩层中。罅隙发生了,裂缝出现了……随之是震撼山岳的火山爆发;熔化了的物质依次倾泻、凝聚、结晶……这样就出现了歪曲的形状,出现了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的结晶,出现了一种石头呈现另种石头形状的情况。矿物学家把这种现象叫作假晶现象。③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30页。
在貌似统一的形态内部存在着不同结构共生而不相融的并置乃至冲突状态就是“假晶现象”。在“大熔炉”内部存在着“互相毗连却不互相渗透”的马赛克“小世界”也可以说是一种假晶现象。斯宾格勒对假晶现象的分析是基于传统的分层,如他在分析俄罗斯文化的内在矛盾时以两位文化伟人作为分层的表征:“托尔斯泰是过去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未来的俄罗斯”,④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338页。就是指俄罗斯文化传统的不同历史层次并置在现代俄罗斯共同体中。芝加哥学派在分析都市社会结构的马赛克构造时采用的是文化生态的“区位”(position)划分,他们认为这些区位之间是分隔的生态单元:“社会是由许多在空间上彼此分隔,在布局上却有统一的地区联系、而且能以独立移动的个人所组成的。”⑤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第64页。他们从生活资料、商业、工业、文化服务业、交通、邻里以及社群身份等多方面分析每个马赛克“小世界”的生态根据。
21世纪的世界与芝加哥学派所研究的20世纪中期大都市社会生态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也可以说是后全球化的生态变异。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社会学家曾把加拿大社会不同群体共生的马赛克结构描述为“垂直镶嵌”的图像,⑥陈国贲:《城市的内在混合性:一项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就是说每个拼嵌的“小世界”都是通过集体记忆垂直传承的文化群落。然而在霍伦施泰因的文化影响理论中,每个文化群落的生成发展不必是垂直传承,而更可能是跨文化转借与文化内传承纵横交错的结果。多元化不仅仅是种族历史的多样性,而且是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相互影响生成的多维性特征。
亨廷顿描述的“达沃斯文化”或“达沃斯人”是当代全球文化传播中形成的跨越国家、民族和文化群落的全球商业、文化、政治精英群,也是典型的横向文化分层——“达沃斯人”与各自归属的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远远弱于这个群体所介入的当代全球化联系及其所产生的全球影响力圈层。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与“达沃斯人”相对立的另外一种文化圈层——由不同学历、身份的年轻人以不同方式聚合成相互之间虽不相连却具有突出相似性的自组织分形群体,通过广场或网络空间表达文化政治身份和意向,对抗那些操控全球化的“达沃斯人”精英阶层。“占领华尔街”“占领伦敦”等等广场抗议活动就是这些人的标志性行为。他们因此而被称作“广场人”。①弗里德曼:《“广场人”让“达沃斯人”靠边站》,《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5月15日。这个文化圈的特征不在于历史文化、宗教和民族归属,他们在社会分层的意义上大多属于中产及以下阶层,与达沃斯文化形成了社会阶层的纵向分层差异;但同时又与达沃斯人一样是跨文化传播和文化转借的产物。
2008年之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开始出现反全球化或者说后全球化的趋势,从文化圈层的关系来看,“达沃斯人”和“广场人”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比亨廷顿警告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对立更强烈而直接。“新城市社会学”代表人物卡斯特把“广场人”在网络和整个当代移动空间中的产生称作“流动空间的草根化”:
“流动空间的草根化”(the grass rooting of the space of flows),也就是以互联网作为社会动员与应对社会挑战的网络。这不只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因为它还关乎组织、可及范围以及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许多“在线”社会运动都是这样先串连起来以地方为基础的运动,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实际的聚合。1999年12月在西雅图举行的反对WTO会议的动员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次事件确立了草根群众对抗不受控制的全球化的新趋势,并重新界定了对新经济的目标和程序的争议内容。②卡斯特:《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
“流动空间的草根化”意味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全球文化生态已无法用“断层线”来描述:传统世界格局中的文明断层线通过社区交叉互渗逐渐失去了“断层线”概念原有的文化界定性。不同国家、族群、社区之间的分界正在变成相互交错反转、无法确定维度和方向的“莫比乌斯带”(Mobius Band)③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发现的一种几何现象:把带状双曲面的两端反转对接后会形成失去边界和方向的单一不规则曲面,即貌似有边界而实际上无界限分隔的空间形态。形态。
三、帝国的黄昏:世界文化新生态
近年来被人们常常使用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这个概念派生自“罗马和平”(Pax Romana),原是指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在帝国治下形成的和平时代。“美式和平”是用罗马帝国治世来借喻,意指二战后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主导和安排构建的“帝国治下”的世界秩序。全球化的危机,实际上是主导这个世界秩序的美国面临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危机。主导全球化的帝国走入了黄昏时代。
美式全球化的危机对世界来说是整个世界文化生态的演化与重构问题。
文明断层线和想象共同体理论以“历史形态/空间延续”为核心区分出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固化了当代文化群体的传统归属,结果是忽视了全球化过程中生成的复杂维度生态关系。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城市社会学在分析文化差异时使用的生态区分概念是“区位”。城市文化生态的分隔是把区位之间理解为相互分离的状态。然而从生态学意义上来看,生态系统既有相互分立的多样性,也有系统的总体关联性。每个作为“马赛克”嵌片的区位其实都被嵌入了一个整体的生态框架背景。所以在生态学上对每一个小生态系统进行区分的时候所使用的生态位的概念通常不是“区位”,而是另外一个概念“生态壁龛”(ecological niche),指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中,一个特定种群满足生存繁衍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生态关系条件。
“区位”是个空间概念,而“壁龛”既是空间概念同时又是关系概念,意味着相对的独立和联系:既有生态的自足性,同时又有对总的生态系统的依附性——生态壁龛不是孤立分隔的空间,而是特定种群与其他种群之间生态关系的最小阈值,既包括有机体对环境的需求,也包括有机体的活动如何塑造环境。换句话说,与马赛克嵌片不同,生态壁龛的分隔性是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多样关联性并存的。
大都市具有生态分隔特征区位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社会学家们常常会谈及的纽约哈莱姆区。这个社区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是贫穷、失业、枪击和毒品的聚集地,是与大都市文明形成强烈冲突的充满社会问题的特殊社区。但是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这里同时也是具有文化生长活力的社区。帕克说“哈莱姆这个名称的含义,先后经过了荷兰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和黑人四个阶段”。①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第7页。这里是历史上一代代移民进入纽约开枝散叶的一处生态发源地,可以说是大都市的生命活力之源。所以有“我们都是哈莱姆人”的说法。
20世纪后期,以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为代表的文化多元主义强调的是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对抗,或者说是“为承认而斗争”。②霍耐特(Axel Honneth):《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但生态多样性存在的基础不是对抗而是多样性的共生。生态多样性共生的前提是每个生态单位的自足性——能够满足该种群生存繁衍最小阈值的生存条件,这是生态壁龛的基本意义;同时又需要更大的生态环境来支撑,也就是生态系统的关联性。以生态壁龛为特征的新生态所构建的文化多样性是从多元生态相互分隔的区位转向生态群的自组织,形成具有社会归属与心灵归宿感的生态关系。法国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和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先后用“场所依恋”(topophilia)这个概念来表达这种属于个人和小群体空间的心灵体验价值。
从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把全球文化发展史区分为三大轴心文明至今,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同文明日益走向全球性联系,走向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的“地球村”。但同时全球的文化形态及其生态界限又在不断分化中:从文明类型到民族国家、地域族群、社区、代沟、粉丝圈……一层层分化和裂变。当代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多样性,更重要的是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而产生的多维和多质性演化。从芝加哥学派的区位空间生态到移动互联时代的信息生态之间是一个世纪文化生态发展演化的历史——从“全球分裂”到全球分形(fractal),即趋向不规则多维化自组织的发展。
但这些显性的群落分化还不是当代文化生态复杂性的全部,更复杂的是隐性的生态关系。比如在近年来中国文化群落研究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概念“小镇青年”:
“小镇青年”作为文化消费现象进入大众视界,可追溯到2013年,由前两部《小时代》所引发的巨大争议……
争议背后,《小时代》的观众画像揭露了其票房制胜的商业秘密:1.观影人群平均年龄20.3岁;2.在地域分布上,湖北、四川、浙江、江苏、江西、湖南、辽宁、广西、重庆、河南、贵州等地的观众舆情参与度指数排在前10位,北京、上海、广东的参与度指数垫底。这组数据意味着一、二线城市之外的年轻用户成为中国电影市场重要增量群体……就2014—2015上半年电影票房的同比增长率来看,三、四线城市票房增速明显高于一、二线城市;从用户画像看,90后和95后观影群体占比在迅速增加。地域和年龄的交叉人群正是小镇青年。①Mugesong:《大数据告诉我们:〈小时代〉是属于谁的小时代?》,虎嗅网,https://www.huxiu.com/article/18172.html,2013年8月3日。
从大数据给出的信息看,特定的“地域和年龄的交叉人群”表明这是个空间界限、身份归属与人格特征都很明确的群落。这里对“小镇青年”生态的研究结论是基于地理社区和身份归属,即芝加哥学派所说的“区位”。然而实际上这是个隐性的复杂社会生态群。当代已进入“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的张力”②卡斯特:《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重构群落生态的时代。大批所谓的“小镇青年”被从小城镇中“挖出来”(lift out)进入了大都市,而且他们很可能并不在固定的社区中生活,唯一维系群落关系的是社交媒体构建的移动空间。
活跃在形形色色社交媒体中的这些人群,他们的选择和表达往往充满了个性化的叛逆色彩,但这种个性和叛逆往往又被不同社交软件构建的群落封闭性所限制,进入“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③桑斯坦(Cass R.Sunstein):《信息乌托邦》,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而作茧自缚。从形态看,信息茧房也属于一种信息系统的生态壁龛——都是相对独立的小生态圈。但与一般生态壁龛的生态机制不同的是:生态壁龛依附于大的生态系统,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并不是同质化的整体,而是由不同种群和种群簇的集合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壁龛,再通过相互联系构造的整体生态。“信息茧房”则具有不断强化的自我封闭性,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封闭化的生态壁龛。这种自我封闭性有可能导致“群体极化”现象:
在群体极化现象中,协商群体的成员典型地选择与协商开始前他们的倾向一致的更为极端的立场……群体极化为极端主义甚至盲从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生长提供了线索。通过协商,所有这些都可能被煽动,而不是减弱。④桑斯坦:《信息乌托邦》,第99—100页。
在特定情形中,群体极化导致“信息茧房”内外的文化冲突甚至会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层线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
无论是生态壁龛还是信息茧房,都是全球化之后世界文化生态演变生成的复杂形态和趋势,意味着从“帝国治下”的总体主义生态转向多元生态。
当代文化冲突的现实是全球化造成了横向意义上的全球资源共享的同时,又在不断生成着特定文化群落垂直层面的剥夺。文化多元主义则把文化生态共享变成了对抗和生态关系的破坏。历史终结论与文明断层线冲突论都无法解释当下全球文化的复杂冲突关系,“大熔炉”和“马赛克”也不能完美阐释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生态状况。当代世界文化正在形成的新的共生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小生态壁龛与大生态系统的交互共生。全球文化关系也因此从涵化、对抗走向多维的共生关系。
这种文化新生态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对小生态自足性的保护,防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剥夺;另一方面通过大的生态关联来消解断层线对抗的危机——每一个特定的文化生态群落既需要保持自己的群体归属感和内在活力,同时又要构建与整个生态环境的相互性开放关系,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说,需要内外双循环机制的文化生态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