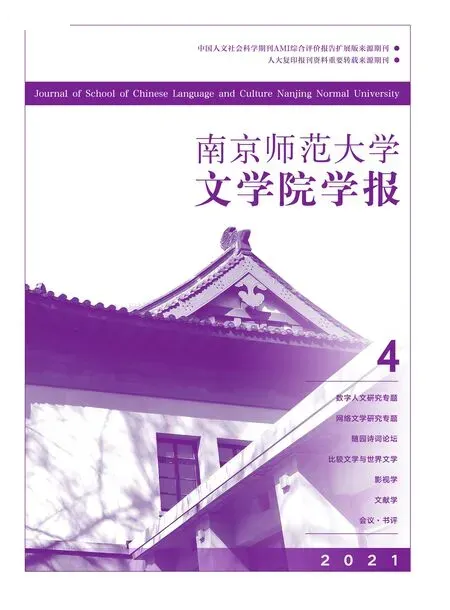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其书示人
—— 在《全清小说》研讨会上的讲话
欧阳健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起步于1997年的《全清小说》,得文物出版社担当支持,于二十四年之后熠然问世,不由得令人感慨万千。
《全清小说》第一次研讨会,为什么选择南京师大文学院?除了高峰院长的大力支持,还有热心朋友江庆柏、田俊先生的精心安排。江庆柏先生是江苏古代文献学的领军人物,为本次会议尽心尽力,十分期待他的指导,可惜因常州会议不能光临。此外,还有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全清小说》项目起步于南京。1997年10月17日,在侯忠义先生主持下,在江苏教育学院百草园,召开了全国文言小说研讨会,确定了从文学角度、根据古今结合的原则,以“叙事性”为区分小说与非小说的标准。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学术上是一个创新。编纂《全清小说》的二十年,就是履行新“标准”的学术实践的二十年。
第二,《全清小说》两位年高德劭的顾问李灵年、王立兴教授在南京。李灵年先生是南京师大文献学专家,著有《清人别集总目》等。王立兴先生是南京大学古代小说专家,著有《中国近代文学考论》等。我和两位先生结有四十年的深厚友谊: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创建,就挂靠在南京师大古籍所。在刘冬会长的领导下,我们通力协作,组织了一系列活动,留下许多美好回忆。《全清小说》重新启动以后,我们每隔三五天就通一次电话,他们是《全清小说》名副其实的顾问。
第三,《全清小说·顺治卷》顺利出版,江苏学人功不可没。20年前完成的书稿,有王立兴先生校点的《云间杂志》三卷,陆林先生校点的《玉剑尊闻》十卷。王先生和女儿火青,是最早参与《全清小说》的校点者,校点16种共120万字。才华横溢的陆林先生,热情支持了《全清小说》。他的夫人杨辉,今天也到会了。他的学生张小芳,帮老师整理文稿,深厚的师生情谊,值得赞扬。《全清小说》重新激活后,在紧迫形势下完成的,有韩石先生校点的《女世说》四卷。现在出了“续修四库全书”“丛书集成新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等,都没收《女世说》的任何版本。马晴博士校点的《藏山稿外编》二十四卷,连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也未收录;此书是1997年我得到徐忆农主任支持,在南京图书馆清凉山古籍部目验的。常州王振军、华云刚、于士倬三位博士,赶校了《虞山妖乱志》《岛居随录》《冥报录》,使得顺治卷得以完稿,顺利出版。
第四,促成《全清小说》与文物出版社联姻的红娘——杨志刚同志,也在南京。2018年6月,杨志刚给我发来微信,说他是古代小说爱好者,在我的博客中得知《全清小说》编纂与出版种种,问文物出版社的编辑想认识我,不知是否可以。由于他的热心,让我与刘永海同志建立了联系。经过半年沟通,达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共识。夏允彝说:“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多以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也。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其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岳起堂稿〉序》)《全清小说》不是国家级的,也不是省部级的项目;它的成立,是“操之在下”的,是“以同声相引重”的,是“以其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的,是靠自我成就取得话语权的。
今天,文物出版社张自成社长致新书发布词,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赠书,令人鼓舞。时逢小满,“小满三天遍地黄,再过三天麦上场”。《全清小说》是百位校点者参与的大工程,有500种3000万字的体量,顺治卷六册只占二十分之一,我们的工作刚刚启步。初次聚会,讨论《全清小说》校点的学术问题与技术问题,报告《全清小说》的新发现与新收获,为的是交流体会,总结经验,保证《全清小说》的学术质量。今天来了许多见过面的老朋友(如沈新林、王欲祥),也来了未曾见过面的老朋友(如杨俊、吴家驹)。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请大家畅所欲言,开成务实高效的会议。
本次会议的第一议题,是《全清小说》校点的学术问题与技术问题。
中国向有编纂一代总集的传统,诸如《全汉赋》《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曲》等,都是典型的范例。《全清小说》的编纂仿佛与此相类,实则大有不同。盖编纂赋、诗、词、曲总集,只要材料充分,断代明晰,将寻觅到的赋、诗、词、曲,统统收罗进来就行。而《全清小说》的编纂,却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小说的鉴别,从外观与形式上,是无法立刻辨识确认的。
首先,小说概念的界定,古今中外,歧义百出。而中国传统的小说,又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
第一个出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其所著录,有诸子十家,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家中最后一家,就是小说家。班固以为,儒、道等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而小说家,“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班固的意思非常清楚:小说家与其他九家,虽各有出处,各有内涵,但作为“诸子”的地位,却是对等的。诸子十家之间的差别,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文体而在实体。换句话说,儒家、道家之间的区别,《孟子》与《庄子》的差异,不是文体的差异,而是实体的差异。它们的差别,从形式或文体上,是看不出来的。同样,诸子九家与小说家的差别,也不是文体的差异,而是实体的差异。它们的差别,从形式或文体上,也同样是看不出来的。要之,小说家的著作,既列入四库中的子部,应称之为“子部小说”。既然诸子九家不是文体,小说就不是属于形式范畴的文体,而是荷载中华文化的实体,这里的道理,没有诞生“诸子”的西方文化是难以明白的。就其内涵而言,“小说”与“大道”,不在一个等级线上;而就其形式而言,“小说”“短书”,不是“宏论”“钜制”。正是这种自觉的“谦退”,反而能出入任意,转圜自如,让小说家成了最有生命力、最为恒久的一家。他们写的是自己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读所悟,所思所触,上至理政方略,下至人生智慧,举凡朝野秘闻、名人轶事、里巷传闻、风土人情、异闻怪谈,无不奔走笔下,成了小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这恰是“子部小说”生命力之所在。
第二个出自宋元“说话”四家中的小说(与讲史、说经、合生并列),包括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元明后出现的长篇说部,《水浒传》是“小说”的集合,如“朴刀”《青面兽》,“杆棒”《花和尚》、《武行者》等,所谓“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是也。而《三国演义》在宋元“说话”四家中属于“讲史”,《西游记》属于“说经”,原本都不曾看作是“小说”。
以上两种小说的统序,原本是非常清楚的。晚清民国以来,随着西方观念的输入,“小说”概念出现了新的歧义。《牛津英文辞典》小说要义有三:虚构的故事、具有相当的长度、以某种复杂程度的情节建构而成,而将虚构居于首位。但中国的小说,却无虚构之意。在这种背景之下,“子部小说”被大大地低估,给研究工作造成无穷困惑。加之推行“白话文”的同时,还提出了“废除文言文”的极端主张,使“子部小说”受到重创。在所谓“小说演进论”指引下,“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的模式被建立起来,明清两代的小说,是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白话小说。所谓“文言小说”,只剩下《聊斋志异》等可怜的几部了。
如今的文科教科书,充斥着“文言小说”“白话小说”、“文言小说”“笔记小说”之类的名目。讲惯了,听多了,成了不假思索的“当然常识”。其实,所谓“文言”,本义乃“华美之言”。如《韩非子·说疑》:“文言多,实行寡。”马总《意林》:“文言华世,不中利民。”刘知几《史通·补注》:“文言美辞,列于章句。”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尤其强调“文笔之辨”,所谓“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是也。以有文采者为文,无文采者为笔,其区别乃修饰与不修饰耳。“文言小说”之名,落在“文”上;“笔记小说”之名,落在“笔”上,等量视之,混为一谈,岂非南辕北辙?故“笔记小说”之名,应断然废弃。
文言又指文章。《北史·元伟传》:“书檄文言,皆伟所为。”梁肃《修禅道场碑》:“盍纪于文言,刻诸金石。”将“文言”释为“有别于白话的古汉语书面语”云云,实出于近代提倡白话文、尤其在鼓吹废除文言文之后。林纾发表于1917年2月之《论古文之不宜废》,题目用的尚是“古文”而非“文言文”。将“文言文”三字连用,最早见于夏丏尊、叶圣陶《文心》:“大概是文言文罢,你们在小学里是只读白话文的。”此书初版于1933年6月。可见“文言文”一词,纯是现代人的杜撰。
我们《全清小说》所要编纂的,正是有清一代“子部小说”的总集。从学术地位看,自汉代迄清,“子部小说”代有所作,数量众多,且得到正宗目录学版本学的认可。会议印发的程毅中先生的文章提出:
《全清小说》的命名,可能会引出一些不同的议论和质疑,如“小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全”字号的标准从宽或从严的选择。关于这一点,同门学友李灵年兄的序言已经作了详细的解释。但根本问题是文言小说的特点就是杂而广,具有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和多种文献价值的不同取向,确实需要深入的研究和界定,还需要文献目录学的支撑。《全清小说》的出版,正好提出了一个可供分析探讨的案例。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进行一次广泛的讨论。
“子部小说”的存在问题,在于范围过宽。胡应麟将小说分为六类: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全清小说》的编纂亮点,在于运用叙事的标准,对传统目录进行亦减亦增的工作:将一部分子部小说著录的如丛谈、辩订、箴规之作剔除;又将一部分杂家、甚至史部的作品列入。这一运作的最大特点,不是以目录学为出发点,而是以作品的客观存在为出发点。本书与《全唐五代小说》《全宋文》《全明诗》编纂的最大不同,是经过鉴定、筛选、编次的清代“古体小说”总集,体现了新的学术成就,是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工程。
至于《全清小说》校点的技术问题,包括编次、校点与文字处理。而文字处理又包括异体字的统一与简繁字的转化。凡例规定:“除人名、地名或涉及训诂等,异体字一般应改为通行正体字,如‘銕’改‘鐵’、‘皁’改‘皂’、‘帀’改‘匝’、‘菴’改‘庵’、‘葢’改‘蓋’、‘歬’改‘前’、‘隣’改‘鄰’等。不硬性将古时的俗字,改成繁体字。对少数民族含侮辱性的字一律改正,如‘猓’‘猺’‘獞’,改為‘倮’‘瑤’‘僮’等。部分讳字,如元(玄)、宏(弘),一仍其旧,以保留原生状态。”会上印了一个《统改及易错易混字》。原先以为比较简单,但实践下来,才发现问题相当复杂。如异体字,在古籍中大量并存的状态。孔乙己讲“回”字有四种写法,就是典型的例子。有校点者提出,对于古籍应予体认和尊重。这个意见,值得考虑。
至于简繁字的转化,存在问题就更多了。有的字原本上已是简体,如“于”“栖”,就不要回改成“於”“棲”;给文字增添偏旁,是后世的事,如“卓”(“桌”)、“快”(“筷”)、“段”(“缎”)、“分付”(“吩咐”),也不要回改。至于将“他”改“她”,就更不对了。简化字的最大问题,在自身原本就是正字,而又兼作了简化字。如“干”(干预,干系,河干,干城,干戈,一干人,干姓),一不小心,成了“幹”“乾”,问题就严重了。在处理时,须要万分小心才是。
《全清小说》整理校点只是工作的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使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全清小说》收有五百种小说,我们是校点者,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要处理好第一个与第一千零一个的关系。
我整理了一份《顺治时期古体小说整理研究》,归纳出《全清小说·顺治卷》31种的基本数据,其中:
宁稼雨先生《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未著录7种:《虞山妖乱志》、《无名氏笔记》、《书事七则》、《快园道古》、《原李耳载》、《馀生录》、《瘿史》、《花间谈往》、《藏山稿外编》(称未见),占22.58%。
未正式校点出版25种:《虞山妖乱志》、《无名氏笔记》、《女世说》、《书事七则》、《原李耳载》、《馀生录》、《瘿史》、《说铃》、《美人判》、《筇竹杖》、《岛居随录》、《书叶氏女事》、《王氏复仇记》、《物感》、《冥报录》、《云间杂志》、《花间谈往》、《麈馀》、《妇人集》、《妇人集补》、《诺皋广志》、《藏山稿外编》,占80.64%。
知网无研究论文20种:《虞山妖乱志》、《无名氏笔记》、《书事七则》、《原李耳载》、《馀生录》、《瘿史》、《说铃》、《美人判》、《岛居随录》、《书叶氏女事》、《王氏复仇记》、《物感》、《冥报录》、《花间谈往》、《续太平广记》、《麈馀》、《妇人集补》、《诺皋广志》、《藏山稿外编》,占64.51%。
至于研究成果,已经出版的如《玉剑尊闻》十卷,有知网论文3篇;《快园道古》二十卷(残存九卷),有知网论文5篇;《影梅庵忆语》一卷,有知网论文31篇;《因树屋书影》十卷,有知网论文1篇;《南吴旧话录》二十四卷,有知网论文3篇;《女才子书》十二卷,有知网论文4篇。未正式校点出版的,如《女世说》四卷,有知网论文5篇;《云间杂志》三卷,有知网论文1篇;《妇人集》一卷,有知网论文4篇。论文数量都不多,皆有极大的开掘余地。
人们都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被视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全清小说》占了“明清小说”的四分之一,却是最有待开发的四分之一。除了《聊斋》《阅微》《子不语》外,大多没有进入研究的视野。这里的原因很多,近代鼓吹的“白话正宗”论,将文言文贬为毫无价值的“死文学”,是重要原因。我赠送大家的《百年微澜》一书,曾从三方面约略言之:
一、使小说研究失却厚实根基。知文学而不知非文学,知小说而不知非小说,知名著而不知非名著,眼界狭隘,底气不足。
二、漠视文言小说,使小说研究长期处于“跛足状态”。研究者只强调宋元“平话”为“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却不正视文言小说实际上滋养了它,是他们所取材所学习的典范。但知文言小说的名著如《聊斋志异》,进入研究视野的文言小说寥寥无几;不曾读几本文言小说,就摇头说“没有价值”。
三、过分拔高一二名著,尤以《红楼梦》为甚。“拥挤的红学世界”人是越聚越多,《红楼梦》也越说越玄。俞平伯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233-234页)
从古代小说研究角度看,《全清小说》的整理出版,将扩大我们的视野。无论是作家论,小说史,文献与版本,综合研究,鉴赏,可做的文章实在太多。筹备中的《〈全清小说〉论丛》,将本着发现、开拓、深化的方针,出人才,出成果。我们的前景,无限远大。
2021年5月22日于南京师范大学南山专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