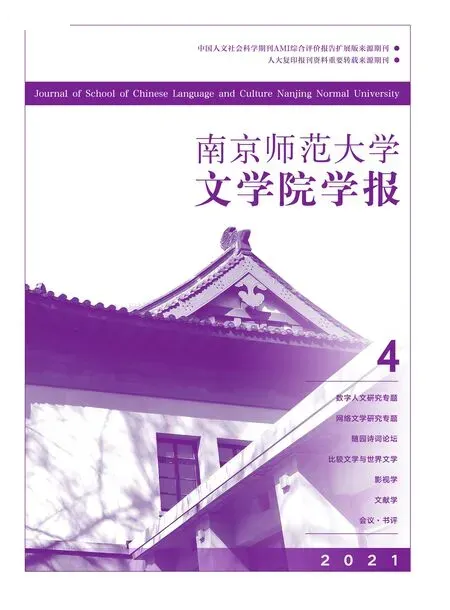易代之际周密的南郊礼制书写
谢雨情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宋史·礼志》云:“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谷,孟夏大雩,皆于圜丘或别立坛;季秋大飨明堂;惟冬至之郊,则三岁一举,合祭天地焉。”[1](P2456)宋代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祭天活动称为“大礼”,南宋依制每三年举行一次冬至南郊大礼,这是都城政治生活中最为隆重的一项典礼。学界多探讨宋代郊祀制度、典礼所用郊祀诗(1)参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赵嗣胤:《南宋临安研究——礼法视野下的古代都城》,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江云:《北宋郊祀研究》,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杨晓霭:《试论礼乐诗歌的多重情境——以宋代郊祀诗为范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杨晓霭:《试论唐、宋郊祀声诗所呈现的时代特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但对文人观看南郊礼的书写及其内心感受未予足够关注。度宗咸淳三年(1267)正月的南郊礼,距此前理宗宝庆三年(1227)的举办相隔四十年之久,是南宋最后一次南郊大礼。对此,周密在亡国前作诗《南郊庆成口号二十首》,亡国后作笔记《武林旧事·大礼》。本文旨在立足具体历史语境,探究这两次书写在文体形态、结构重心、情感指向等层面的差异性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周密南郊礼制书写的历史语境
周密的生活与创作以宋元易代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其南郊礼制书写即发生于易代前后两个不同的创作时期。
宋亡前,周密虽仕途不显,多任掌管钱粮或礼仪的低级官职,但世代为官的优渥家世让他有条件悠游自在地生活。自宝祐五年(1257)加入西湖吟社,周密“风月交游,山川怀抱”[2](P102),作品多描摹西湖风光,记录研讨声律的吟社活动,展现文人雅士的逸致闲情。
宋亡后,吴兴家宅被战火焚毁,周密搬迁至杭,选择不仕,闭门著述。他自幼深受家中祖父、外祖父、父亲的影响,把保存史料作为重要治学追求:“台阁之旧章,官府之故事,泛滥淹注,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图,恐遂废轶。”[3](P2)亡国后更是致力于以笔记记录宋季历史。在当时杭州、吴兴、会稽的文人结社集会和往来唱和中,形成了一个以周密为中心,包括王沂孙、张炎、戴表元等人的遗民群体。此时周密“所著书中拳拳于景炎祥兴君相”[4](P3800),多抒发亡国之痛。作为政治参与度较低的基层官吏,周密未似文天祥或者其他官员一样殉国,但他“二十年自惟平生大节不悖先训,不叛官常,俯仰初终,似无慊怍”[5](P306),选择以文人的特殊方式记录时代变迁,反映了亡国后未出仕遗民文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
南郊礼制是周密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与政治有关,且在亡国前后均有书写的题材内容。度宗咸淳三年南郊礼作为南宋最后一次南郊大礼,它的发生在宋末又具有典型的政治意义。
“皇帝即位之三年,当咸淳柔兆摄提格之岁,内外治谧,文物熙畅。普天观万化之新,昌运际三登之泰……前此之所未睹,实为我皇家开亿万年太平无疆之休。……盖自宝历丁亥以至今日,四十年希阔之典,一旦克举,仪章文物,有光于前,无靡丽以炫俗,无科配以及民。[6](P36)”由周密诗序可知此次南郊礼是“四十年希阔之典”。宋代本实行“三岁一亲郊”制度,但理宗宝庆三年(1227)后的四十年都未遵守这一制度,这与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局势密切相关。具体而言,端平元年(1234)入洛失败,宋蒙战争胶着二十多年,蒙军攻过长江,南宋朝廷一度面临迁都危机;朝政相继为史弥远、贾似道所把持,以致理宗后期怠于政事,沉溺享乐。[1](P13782)正是由于上述消耗,加之连年灾害和公田法的盘剥,国家财政几近崩溃。而国力疲敝时朝廷根本无力举行南郊礼。自南渡以来,朝廷便常因费用不足,而改行费用较少、仪式较简的明堂礼。《文献通考·明堂》:“中兴以来,国势偏安,三岁亲祀,多遵皇祐明堂之礼。”[7](P2332)南宋南郊礼凡19次,明堂礼凡30次。(2)高宗在位36年,南郊礼7次,明堂礼5次。孝宗在位27年,南郊礼6次,明堂礼3次。光宗在位5年,南郊礼1次。宁宗在位30年,南郊礼3次,明堂礼7次。宋理宗在位40年,南郊礼1次,明堂礼12次。宋度宗在位10年,明堂礼2次,南郊礼1次。宋恭帝在位2年,举行明堂礼1次。具体参见杨高凡《宋代明堂礼制研究》,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直至开庆元年(1259)蒙哥汗去世,南宋得以修生养息,其后理宗于景定五年(1264)逝世,度宗即位,搁置四十年之久的南郊大礼才提上议程。
咸淳二年(1266)工部尚书赵汝暨奏请南郊礼,时值南郊礼、先帝新丧大祥祭礼之年,但因冬至前日有月蚀,因此改期至次年正月初一。[1](P2446)随后度宗颁布《行郊祀礼诏》,由诏书可知行南郊礼的两个主要目的如下:
第一,南郊大礼是嫡长子继承制下确证皇位正统延续性的重要手段。《诏》曰:“礼修肆类,大舜所以致嗣位之恭;祀秩肇称,成王所以昭受命之敬”[8](第359册P372-373)王应麟《咸淳三年郊祀大礼赦文首词》:“朕嗣受丕基,遹求彝宪。正月上日类于帝,率惟虞帝之初;昊天成命殚厥心,祗若周郊之始。”[8](第354册P137)南宋皇帝子息凋零,理宗为太祖赵匡胤次子赵德昭的九世孙,与宁宗血缘疏远,且家族社会政治地位较低,宝庆元年(1225)由权相史弥远扶持登基,因此宝庆三年(1227)行南郊大礼。度宗同样面临身份合法性问题,作为宁宗八弟赵与苪庶子,身份低微且资质不高“七岁始言”(《宋史·度宗本纪》)[1](P891),曾受左丞相吴潜质疑(3)《宋史·吴潜传》:属将立度宗为太子,潜密奏云:“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忠王即度宗,意即吴潜无法像史弥远扶持理宗一般扶持度宗。[1](P12519),后由权相贾似道扶持即位。可见举办南郊大礼是度宗通过礼法秩序确立统治合法性的手段,也是度宗受天承命、延续正朔的象征。
第二,南郊大礼是度宗治国理政的自我勉励和公开宣示。《诏》曰:“式克勤劳王家,惟既增修国政。加璧以聘老,侧席以待贤。杜群枉以为明,令四方毋来献。我其夙夜,允怀济时之思;心之忧危,每轸奉诏之虑。疆埸曷繇而庶定?年谷奚自以屡丰?罔知于兹,其何能淑?惟天惟祖宗之界付,在上在左右之鉴观,曷揭虔于始郊,以答贶于初服?念其难其慎,曾微可告神明之功;而有报有祈,盍为大芘黎元之地?”[8](第359册P372-373)依南郊礼制,帝王只有做到勤勉政事、广纳贤臣,国家边疆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才有资格举行南郊大礼,即祭告上天、祖先,汇报治国政绩,为长治久安、万世太平祈福。度宗甫一登基,便减免赋税、赈济百姓,南郊大礼举办也象征着他要在上天、先祖的监督见证下对官僚阶层和普通百姓做出励精图治的承诺。
在理宗四十年没有举行南郊大礼、统治不力的基础上,咸淳南郊大礼的成功举办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皇登基后气象为之一新的印象,为时局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士人纷纷上表庆贺,如王应麟《拟贺郊祀礼成进诗表》、俞德邻《贺郊祀庆成表》。但必须要认识到当时的宋廷仍旧处于国力日渐衰颓的阶段。虽然大礼举办时宋军取得小胜“是日广安之捷适至”[6](P38),但军事、政治、经济上的诸多问题并没有从根源上得到解决。
以度宗咸淳南郊礼为书写对象,周密亡国前创作《南郊庆成口号二十首》,是作为小官观看典礼的盛世感怀书写,表现南郊大礼的盛大恢弘;亡国后创作笔记《武林旧事·大礼》,是作为遗民追忆故国的正朔认同书写,表现南宋的礼乐文明之治。从中可窥见随时代变迁,文人身份转换对其作品文体形态、结构重心、情感指向的具体影响。
二、《南郊庆成口号》与盛事记录
咸淳三年南郊礼后,周密紧扣现实政治,作《南郊庆成口号二十首》,着重记录南郊典礼的历时过程,突显参与希阔盛典的自豪之感。他通过细节刻画和创新意象使得诗歌与以往的南郊诗相比表现出了叙事性和纪实性的特点。
南郊礼毕后作庆成诗是宋代传统,一般有奉和、献诗两种情况。其一,宰相、礼官等人的奉和。如真宗天禧三年(1019)礼官杨亿《奉和御制南郊七言六韵诗》、徽宗宣和元年(1119)太师蔡京《恭和御制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斋宫即事赐诗四首》等。其二,官员礼成献诗,多为讨皇帝欢心。如仁宗嘉佑五年(1060)翰林词臣曾巩作《郊祀庆成并进状》颂美仁宗功德,曰:“……福合于天且不违之圣,宜有歌颂,被于声律。臣与在馆阁,以文字为职,不敢以菲薄自止,谨作五言郊祀庆成诗一首”[9](P79)。哲宗元祐七年(1092)门下侍郎苏辙作《进郊祀庆成》诗并状,诗下自注哲宗功绩,后“以郊祀恩特加护军进开国伯、食实封二百户。”。[10](P1394)又如太宗淳化四年(993),王禹偁作《南郊大礼诗十首》:“肠断商于左迁客,圜丘无分得荣观”(其二),“年来不见祀圜丘,谪宦携亲叹白头”(其十)[11](第2册P727),歌颂南郊大礼盛况。他自淳化二年被贬商州团练副使,又量移解州,在作诗表达无法参加南郊大礼的悔恨和早日回京的期盼后,当年即“召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1](P9794)。
观察周密《南郊庆成口号二十首》序中的用语可知此诗应为献诗:“陪台贱臣,虽不获骏奔于百执事之列,然快睹盛举,自庆遭逢。既不能效杜甫献三赋以希望恩泽,又不能效马第伯记封禅以夸示后世。恭惟熙朝,钜典煊赫,照映耳目,讵可以芜陋自书,无所纪载?”[6](P37)咸淳三年,周密时任两浙运司掾,虽未居大礼执事之列,自觉官微言轻,但深感生逢盛世、亲见盛事,于是作诗二十首详细记录此次盛事。他在组诗的结尾再次强调这种心情:
子云无分从甘泉,留滞犹胜叙史迁。瑞应可书郊祀志,熙功宜被奉常絃。(十七)
曾闻宝庆老人言,不见亲郊四十年。何幸圣时瞻盛举,咏歌留作画图传。(十八)
我将清庙周诗颂,泰畤汾阴汉史书。献赋可无徐穆伯,贡谀何取马相如。(十九)
太平寰海扇皇风,千载风云喜际逢。行见版图恢旧宇,泰山父老徯东封。(二十)[6](P38)
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受颂圣功能的支配, 以庆祝南郊大礼举行为主题的南郊诗形成了其独有的结构模式,多为排律或由律绝构成的组诗。开头直接歌颂大礼的举办,中间记叙大礼过程,结尾歌颂帝王功德。对于皇帝的歌颂语汇多固定为“圣君、圣主、圣寿、圣旦、圣时、圣代、圣嗣、圣瑞、圣德、馨德、灵德、明德、勤德”。对于大礼场面的描绘则多固定为祥瑞动物意象“天鸡、仙鹤、丹凤、龙、鸾”等。情感呈现出普遍化、空泛化的特点,程式化写作痕迹明显,适用于应制唱和场合。而本身即为颂圣而生的口号诗表现得尤为程式化。“口号”本是一种随口吟成、篇幅短小的诗体,在宋代发展为教坊乐工创作的乐语。后翰林学士钱惟演的上书让乐语的创作特质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成为舍人院撰写的正式文本。此后翰林词臣多在典礼、圣寿、节日以庆祝、颂德为旨创作口号诗,如苏轼《斋日致语口号》、秦观《中秋口号并引》等。这些诗歌为应制而多谀辞,缺乏生动个性的思想情感。周密的《南郊庆成口号》则在细节刻画和意象使用上都做出了创新,突破了以往南郊诗程式化的特点,显得较为生动。
现将周密《南郊庆成口号二十首》与其他南宋南郊诗的相似段落进行对比:
第一,描写皇帝登上郊坛的场景之别。周密诗曰:“和气排冬午夜春,列星呈瑞午阶明。千官执玉萧芗远,静听登歌奏六成”(其五)。先渲染整体环境的温暖明亮,再通过描写郊坛上下执事官的安静,侧面烘托仪式的肃穆庄严。而前人诗曰:“登歌已奏迎神曲,天步雍容上午阶” (周紫芝《郊祀纪事十首其八》)[11](第26册P17353)、“合奏谐纯绎,登歌美缉熙”(陈宗远《郊祀庆成诗》)[11](第72册P45180)仅言其盛大庄严。
第二,描写皇帝车驾回朝场景之别。他人多将目光投向仪仗形制,如“宝仗朝回物采鲜”(任希夷《郊祀庆成三首其三》)[11](第51册P32091)、“玉路旂常龙十二,绣衣卤簿虎三千”(杨万里《拟乙巳南郊庆成》)[12](P985);或队伍行进过程,如“招摇回左翿,阊阖敞南离。侍仗朝绅拥,升楼禁跸随”(陈宗远《郊祀庆成诗》)[11](第72册P45180)。周密则以四首绝句叙述完整过程:
衙前口号奏谐和,日映龙颜喜气多。六辔暂停鸾辂稳,凤韶新奏庆成歌。(其十)
锦幕千家尽贵豪,万花呈晓翠帘高。数声掣电惊清跸,一点红云认御袍。(其十一)
喜看回仗自青城,十里东风五色云。露布西来天一笑,舆图新复广安军。(其十二)
万骑云从簇锦围,内官排办马如飞。九重阊阖开清晓,太母登楼望驾归。(其十三)[6](P38)
他不仅正面铺陈描绘仪仗的音乐、形制、随从、天气,还以街边观礼市民的反应侧面烘托热烈氛围。王炎“一声传入跸,万目望华芝”(王炎《郊祀庆成诗》 )[11](第48册P29776)以清路之声引出皇帝的万众瞩目,形容皇帝在仪仗队伍中的位置。但周密不仅以远处驰来的骏马引出皇帝出场,而且以御袍的引人注目和独一无二强调皇权的至高无上。
第三,描写登门肆赦(皇帝登上丽正门进行大赦活动)场景之别。前人仅描绘了丽正门前树立金鸡竿这一标志性流程:“丹凤端门耸,金鸡涣号施”(王炎《郊祀庆成诗》)[11](第48册P29776)、“日丽鸡竿矗,天旋凤律新”(范成大《次韵郊祀庆成》)[13](P112)而周密“换辇登门捲御帘,侍中承制舍人宣。凤书乍脱金鸡口,一派欢声下九天”(其十四)[6](P38)则详细叙写了皇帝登门经过、侍中承制舍人诏书宣告、丽正门前金鸡争夺以及百姓反应。
由上可见,周密在描绘与前人诗作相同的场景时,虽然继承了一些固定语汇,如“鸾辂”“凤韶”“凤书”“金鸡”等;但更重要的是,他紧紧抓住了前人不曾关注的大礼细节,使诗歌从程式化的套语中脱出,落到了实处。以往的南郊诗多想象、代拟、套作,皇帝的出行和大礼过程只简单交代步骤,其盛大淹没在固定语汇和辞藻、意象的组合中。周密不再套用传统的写作模式,而是关注仪式主体之外的天气、观众、街景,为大礼的进行营造了一个个真实具体的场景。使得大礼完整过程以 “郊坛行礼图”“郊毕驾回图”“登门肆赦图”等一幅幅图景的形式连续动态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诗歌表现出了极强的纪实性。
在这些细节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天气意象的使用。周密将南郊诗的书写重点从都城的建筑和吉祥天象转向了天气。以往南郊诗继承了唐代都城诗以长安城建筑奠定基调核心,侧重表现都城空间特征的写法(4)关于唐代都城诗的特征可参康震:《唐代诗歌与长安城建筑文化——以“北阙—南山”的意象解读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但大多数不是以实地建筑为描写对象,而是套用一种意象传承陈陈相因的都城空间话语系统。例如,吕陶“彩城齐北阙”(《郊祀礼成诗》)[11](第12册P7782)、秦观“海岳朝双阙”(《次韵蒋颖叔南郊祭告上清储祥宫》)[14](P280)、王安中“喜色生春临魏阙”(进和御制南郊礼成喜雪诗)[11](第24册P15981)、周紫芝“九重和气满宫城”(《郊祀纪事十首其二》)[11](第26册P17353)、刘攽“旂幡径九门”(《郊祀庆成诗》)[11](第11册P7281)、杨万里“星沈析木天街北”(拟乙巳南郊庆成二首其二)[12](P985)等。而在周密的南郊诗中类似于“北阙”“九街”“九门”的空间意象基本是缺位的。诗歌中对于空间的描绘只有两处。一处为化自王维“九天阊阖开宫殿”的“九重阊阖开清晓”,另一处为对南郊圜坛高度的描写“圜坛八陛际云高”。这种缺位与现实的空间基础有关。临安城并未遵照传统的都城规划原则进行建造,不如长安城宏伟富丽、平整宽阔。南宋宫城以杭州官署为基础依傍凤凰山麓改建,中兴以来为求俭省,宫室十分狭小,如大庆殿在不同场合会因需要改换殿名充作他用(5)吴自牧《梦粱录》:“丽正门内正衙,即大庆殿,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俱御之。如六参起居,百官听麻,改殿牌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改名紫宸;进士唱名,易牌集英;明禋为明堂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如果直接继承以往都城话语系统中对于高大城阙的描写,虚构南郊礼中的临安,这与周密在南郊诗中所追求的叙事性和纪实性不符。而如果选择实写临安狭小的宫苑殿宇,又与他颂圣的初衷相悖。于是他将目光投向真实却依然具有虚幻夸饰空间的天气,作为新的都城话语。
描写天气意象并不是周密的突发奇想,在南郊诗中以天象预兆吉祥十分常见:王禹偁“宝图高大北辰星”(《南郊大礼诗》)[11](第2册P727),秦观“云行博山气,风卷步虚声”(《次韵蒋颖叔南郊祭告上清储祥宫》)[14](P280),王珪“星拱低宸幄,云回护帝辕。祥辉新日月,佳气浃乾坤”(《郊祀庆成诗》)[11](第9册P5949)。但这些描写完全忽略了冬至日实际的天气特征,只留下了理想化的吉兆天象。而周密所书写的南郊大礼在正月初一举办,此时天气渐渐回暖,因此祥和天气成为了他刻画的重点:“和气排冬午夜春,列星呈瑞午阶明”“瑞霭烘春夜不寒”“万点明星簇紫皇”“一夜东风斗柄回,紫坛葱茜若春台。熙熙万宇风光暖,尽入君王饮福杯”“衙前口号奏谐和,日映龙颜喜气多”“万花呈晓翠帘高”“十里东风五色云”“新元颁赦又颁春”[6](P37-38)。“和”“明”“春”“暖”成为了大礼举办的底色,与之相伴的是“列星呈瑞”“瑞霭”“五色云”的天象。可见周密诗中的天象虽然继承了以往南郊诗中的理想化成分,但它建立于春夜东风和煦、群星闪烁的现实天气基础。虽然天象为虚,但天气和南郊礼皆为写实,三者共同形成政通人和、与民同乐的盛世气象。
总体而言,以往南郊诗虽堆砌辞藻、极力颂扬,南郊大礼形象仍显笼统虚无。周密南郊诗虽然写作目的依旧是颂圣,但从典型场景的营建、环境细节的把握和意象的创新来看,显然更具有叙事性和纪实性。这与他对自己南郊大礼写作性质的认识有很大关系。首先,他对南宋朝廷满怀热爱和期待,有通过自己书写使度宗南郊礼流芳后世的写作自觉,其次,他有继承《史记》纪实传统的写作追求。因此他的写作自然要区别于以往的应制颂圣南郊诗。
三、《武林旧事·大礼》与正朔认同
端宗景炎二年(1276)元军破临安城,南宋灭亡。距离咸淳南郊大礼十年后,现实与周密在诗里所期待的“亿万年太平无疆”“版图恢旧宇”截然相反。遗民周密作叙事性笔记《武林旧事·大礼》聚焦历史记忆,侧重追怀典章文物的盛大恢弘和南宋正朔的礼乐之治。

第一,周密注重营造与民同乐的氛围。这主要体现在三个细节:
一是描绘向皇帝出行的仪仗队伍献礼。《武林旧事》注重队伍与民众的双向互动。《东京梦华录》中北宋民众因大象高超技艺而打赏:“诸戚里、宗室、贵族之家,勾呼就私第观看,赠之银彩无虚日。”而《武林旧事》中南宋民众则因队伍向民众致意而犒劳:“每队各有‘歌头’,以彩旗为号,唱和《杵歌》等曲,以相两街。”这种官民的双向互动,营造出普天同庆、吉祥和乐的氛围,体现皇帝与民同乐的政治精神。
二是描绘仪仗队伍出行场面。《武林旧事》注重描绘民众。《东京梦华录》民众仅作为背景来烘托热闹场面:“御路数十里之间起居幕次,贵家看棚,花彩鳞砌,略无空闲去处。”主要描写对象是参与大礼队伍之人的服饰和情态:“执旗人紫衫、帽子。每一象则一人裹交脚幞头紫衫人跨其颈,手执短柄铜钁,尖其刃,象有不驯,击之。”相较《东京梦华录》对大象队伍的穷形尽相,刻画如生,《武林旧事》则略写大象,重点刻画都人:“及驾出前一日,缚大彩屋于太庙前,置辂其中,许都人观瞻……宰执亲王,贵家巨室,列幕栉比,皆不远千里,不惮重费,预定于数月之前,而至期犹有为有力所夺者。珠翠锦绣,绚烂于二十里间,虽寸地不容闲也。歌舞游遨,工艺百物,辐辏争售,通宵骈阗。至五鼓则先驱,所至皆灭灯火,盖清道祓除之义。”综上,就观礼者身份看,临安城中不论身份阶级,官、商、手工艺人皆可观看大礼;就大礼重要性看,人们以观礼为荣,不计距离、金钱、时间,甚至与他人争抢观礼位置;就宋廷宽松的统治氛围看,皇帝仪仗置于太庙以供观瞻,官兵直至皇帝正式驾出才对观礼者进行清道和约束。
三是描绘“登门肆赦”活动。《武林旧事》十分注重描写皇帝大赦后百姓对此的反应。《东京梦华录》侧重描绘犯人和官吏的服饰细节:“罪人皆绯缝黄布衫,狱吏皆簪花鲜洁。”《梦粱录》则主要描写皇帝:“上登楼临轩,立金鸡竿放赦,如明禋礼同。”在周密的笔下,“登门肆赦”表达着皇帝对于太平万寿的期望:“即先发太平州、万州、寿春府,取‘太平万寿’之语。”也是大礼最直接积极作用于百姓的举措:“罪囚应喏,三呼万岁,歌呼而出……满道都人竞观。”。皇帝大赦天下,百姓感谢皇恩,极大增强社会认同感、巩固国家统治。
第二,周密注重描绘大礼祭祀的盛况。
一方面,周密对大礼的人数使用了一定程度的夸张手法。在关于“驾诣青城斋宫”的描述中,周密将大礼形容为十倍于“四孟驾出”的人数:“盖十倍孟飨之数”。“四孟驾出”条载:“殿步三司,分拨统制将官军兵六千二百人摆龊诸巷”,与“大礼”条记载的“仪仗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相比,可以发现大礼与孟飨的人数仅相差689人,周密却夸张为十倍。在记叙登坛祭祀仪式开始前的准备活动时,他写到参与典礼的执事官每人都手提一灯,“万灯辉耀,灿若列星”。灯上以不同图案区分标记,由于图案太多,“亦有好奇可笑者”。以图案多形容灯多,以灯多形容人多,虽未直言人多,却造成了人数众多,气势非凡的宏大场面。
另一方面,周密对大礼场面进行一定程度的夸饰。在描绘百姓观看君王登坛祭祀、奏响郊祀乐曲场面时,《东京梦华录》形容为“外内数十万众肃然,惟闻轻风环佩之声”,《武林旧事》则描绘为:“时壝坛内外,凡数万众,皆肃然无哗。天风时送佩环韶濩之音,真如九天吹下也”。虽然南宋的观看人数“数万众”不如北宋的“数十万众”多,但气势更为恢弘。这归功于周密将“轻风”形容为“天风”从“九天”吹下。同时这种形容又强调了天人合一,君主的合法性。在关于大礼结束后皇帝车驾回朝的描述中,孟元老以“诸军队伍鼓吹皆动,声震天地”形容,而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只是简单叙述事情经过:“天明,仪仗卤簿甲骑卷班回丽正门”。相比于孟元老和吴自牧的平铺直叙,周密的夸张和比喻使得场面更为宏大,他首先形容了仪仗人数“千乘万骑”,再形容其情态“如云奔潮涌”,又以俯瞰视角形容观看典礼的“四方万姓,如鳞次蚁聚,迤逦入丽正门。”以人们的渺小烘托出了礼乐场面的庄严宏大。
值得关注的是,周密在《武林旧事·大礼》结尾引用了《南郊庆成口号》中的两首:“弁阳老人有诗云:‘黄道宫罗瑞脑香,衮龙升降佩锵锵。大安辇奏乾安曲,万点明星簇紫皇。’又曰:‘万骑云从簇锦围,内官排办马如飞。九重阊阖开清晓,太母登楼望驾归。’”引用内容避开当初对南宋国运的期待之语,特别选择了描绘大礼盛大场面、烘托南宋礼乐文明形象的内容。
第三,从笔记结构布局与重点内容可见周密对典章文物重要性的强调。从笔记结构布局看,《武林旧事》将皇家几项最为重要的仪式典礼放于卷首,包括 “庆寿册宝”“四孟驾出”“大礼(南郊·明堂)”“登门肆赦”“恭谢”“圣节”等几项皇家最为重要的仪式典礼。反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首记录都城空间,卷十记录郊礼;吴自牧《梦粱录》从卷首开始记录时令习俗,郊礼则依附于九月明堂礼之下置于卷五。从笔记反复强调的内容看,他多次强调面对华夏文明首次被异族文明统治,衣冠文物被大量破坏自己的痛心。他记录所知的文物旧规,希望后人能够恢复:“成均旧规,后来不复可见矣。谩言所知者数则于此,亦可想见当时学校文物之盛,庶异日复古或有取焉。”[20](P23)并对所载的宋帝孝行、宋廷德治产生向往,从而对世教民风产生积极作用:“又皆乾、淳奉亲之事,其一时承颜养志之娱,燕间文物之盛,使观之者锡类之心,油然而生,其于世教民彝,岂小补哉。因辑为一卷,以为此书之重。”[19](P195)
周密在笔记中注重营造与民同乐的氛围、描绘祭祀的盛况、强调典章文物的重要性。这些特点都是为展现中原文化的优越性而服务的。究其原因,周密对正朔文明和礼乐的重视与礼官经历有关:“余为国局,尝祠蜡,充奉礼郎兼大祝。”[20](P25)奉礼郎和太祝属太常寺管辖,负责设置皇帝祭祀板位,管理玉册、献酒等事务。(6)《宋史·职官志》:“奉礼郎,掌奉币帛授初献官,大礼则设亲祠板位。太祝,掌读册辞,授搏黍以嘏告,饮福则进爵,酌酒受其虚爵。”(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根据周密“陪台贱臣,虽不获骏奔于百执事之列”之语可知他并未参与咸淳南郊礼,只是观礼者。但礼官的经历使得他对南郊礼制的书写更为纯熟,也产生了一种潜在的职务暗示和写作自觉。再加上之前在参与和写作南郊礼过程中所体会到的盛大国礼的象征意义。这使得南宋南郊大礼在周密《武林旧事》中呈现出一种理想的礼乐文明形象,并且成为儒家文明、正朔文明和中原文化的象征。强化南宋南郊礼制形象,是他作为遗民对帝都的理念性诉求,也是唤起遗民群体南宋故都临安集体记忆与认同的重要手段。
结 语
周密在宋元易代之际对南宋度宗咸淳南郊礼两度进行书写,虽然历史语境和写作身份不同,表达目的和表达手法相异,但其思想脉络和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都来自于周密对于南宋王朝的无限热爱与眷恋。诗歌《南郊庆成口号》作于南宋江河日下之时,周密通过营建典型场景、把握环境细节和使用天气意象,对现实盛典进行了纪实性的史实书写,渴望以诗歌永久的留住这神圣的一刻。笔记《武林旧事》则作于南宋亡国之后,在情感落差巨大、集体记忆消逝和文化离异感强烈时,渴望通过对盛典万众欢腾、万民齐乐的夸张书写,来呈现南郊礼无与伦比的凝聚力、感召力,以此来追忆中原王朝神圣的文化体验,并以此潜在对照蒙元文化。
宋度宗咸淳三年的南郊大礼作为南宋末年中原盛世模式的最后一次残照,留影在周密亡国前后的两次文学书写中。通过比较周密两次南郊大礼书写,我们能看到南宋礼制文化对于宋末士人心态、都城文学和遗民文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