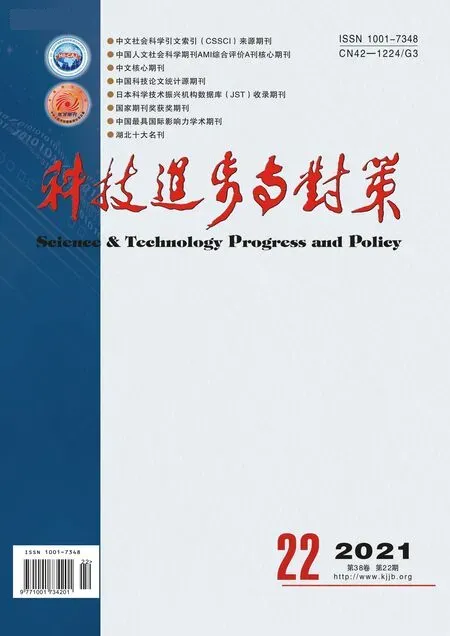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制度:流变、适用与启示
单 娟
(1.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510)
0 引言
专利权通常被认为是所有知识产权中最具有领土性的[1]。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市场的出现给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带来了独特的挑战,然而,专利保护国际化的发展并未突破其地域性属性,专利权人原则上仍以享有特定国家赋予的专利权为前提寻求权利保护。发达国家的专利权人认为专利权的地域性导致放纵境外市场的“侵权”行为,因此,美国在立法、执法上不断突破专利地域性,对境外行为予以规制以保护美国专利权人利益。同时,美国国会通过修改美国专利法确立了具有域外效力的规则,美国专利权人也不断寻求美国法院解释立法对境外行为及损失予以救济[2]。
2020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要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有关法律规定域外适用,完善跨境司法协作安排”[3]。未来15~20年,新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扩散应用将处于持续加速期[4],专利跨国保护的重要性与专利权地域性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正逐渐向技术先进国、技术输出国转变,如何充分保护本国发明创新、保护国家和私人利益,必须仔细衡量法律政策,其中,如何构建中国专利法域外适用规则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中国立法是否可以借鉴美国模式,在保持专利权地域性的基础上赋予专利法部分条款域外效力?对于美国专利领域的“301调查”和“337调查”等执法研究,中国学界取得了一定成果,而对于美国专利法立法本身的域外效力规则及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国学者研究相对较少。
专利法的域外适用是指国家将具有域外效力的本国专利法规制适用于其管辖领土范围以外的人、财产和行为的过程;一国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实现专利法域外效力的过程就是专利法的域外适用[5]。本文讨论的专利法域外适用,区别于传统国际私法上一国法院在处理涉外专利纠纷中对他国专利法的适用。同时,专利权是专利法范围内的权利,因此,立法确立的专利法规则的域外效力意味着专利权在此规则范围内享有域外效力。本文将聚焦美国专利法,介绍其专利法域外效力规则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和美国法院的实践并予以评析,一方面为我国构建专利法域外效力规则,积极利用司法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供借鉴,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企业知己知彼,防范在美国法院以侵犯美国专利权为由被诉,并为可能的被诉提供合理应对依据。
1 专利权的地域性与美国专利法域外效力规则确立
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以及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等带来了法律领域巨大变化,专利法领域被认为是美国近代法律发展中最不稳定的领域之一。
1.1 专利权的地域性与专利保护国际化
所谓专利权的地域性是指在一国境内根据该国法律所取得的专利权,只能在该国境内有效,受该国法律保护,不能得到其它国家当然的承认和保护,在没有取得专利权的国家,人们可以随意利用已知的智力成果,而不受法律追究[6]。关于专利权地域性之成因的经典理论解释认为,专利权脱胎于封建特权,封建割据的地域性使得其只能在产生的地域内有效,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追逐经济目标的驱动下,这一性质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最基本的属性之一[7]。一般认为地域性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在形式上限制了创造者享有权益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实质上它又是创造者享有权益的切实保障。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承担着英国制造业的半成品原料如木材、生铁、羊毛等供应商的角色。这一切随着美国独立战争而发生变化,大规模地“盗窃”外国技术、机器设备和相关知识为美国工业化服务成为美国社会的常态,这一时期的美国法律和政策也为工业领域知识产权的“盗取”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虽然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赋予发明专利一定期限内的独占权,但1790年第一部美国专利法并没有确保发明专利原创性的实质性条款,这也意味着一些进口商可以相对容易地将他人已在外国获得专利的“专利”转化为自己所有而获得美国专利。甚至,马萨塞斯州还专门为此类行为提供购买贷款,宾夕法尼亚州为从欧洲“盗取”技术的人发奖金[8]。同时,专利法否认外国人可以在美国获得专利保护[9]。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已从专利的净“接受者”转变为净“制造者”。基于此,美国对专利保护的态度也随之慢慢转变。
1836年,美国国会开始要求专利申请人证明他们寻求美国权利的发明的新颖性,并创建了美国专利局审查申请。虽然旨在削弱从欧洲“盗取”技术的行为,但申请审查制无疑使得专利申请变得繁杂,同时,申请人往往需要付出高昂费用,使专利持有越来越成为“富人的运动”。在许多行业,专利被用作吸引资本的商业资产,进一步集中于大公司的创新活动[10]。与此同时,大国之间更加注重贸易往来,各国也逐渐意识到剥夺外国公民的知识产权成为阻碍自由贸易的重要因素。19世纪70年代,大国开始寻找避免专利等工业产权被“盗取”的方法。1883年《保护工业产业的巴黎公约》拉开了专利保护国际化的大幕,美国也在1886年加入该公约。巴黎公约确立了以互惠为基础的国民待遇原则,以各国国内立法为基础,坚守了专利权严格的地域性[11]。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基本处于搁置状态。二战后,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西方世界无可争议的领导者。随着专利产品占出口产品比重逐年上升,美国实体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知识产权国际协调的重要性[12]。但是,美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合作过程并未达到其原本意图,美国支持创建的WIPO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发展中国家请求经济发达国家给予知识产权优惠待遇的主要场所,此外,1975年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巴黎公约以满足发展需要。当然,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努力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美国企业开始利用私人诉讼将司法域外管辖作为跨国保护其专利权的可能途径。
1.2 美国法院对专利法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的坚守
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是美国法院在解释联邦制定法域外适用问题时运用的一项法律适用规制,即“除非出现相反的意图,否则国会的立法只适用于美国的领土管辖范围[13]”。相较于商标领域,美国法院对专利领域法的域外适用是较为保守的。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在专利法领域的运用可以追溯到1857年,自此美国法院和国会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将专利权保护限制在“美国领土范围内”,这在早期的案例Brown v. Duchesne案和Dowagiac Manufacturing Co. v. Minnesota Moline Plow Co.案中都有所体现。
20世纪70年代的Deepsouth Packing Co.v.Laitram Corp.案(以下简称Deepsouth案)被认为是美国法院适用反域外推定原则的典型案例。Laitram公司起诉Deepsouth公司未经同意制造其拥有专利的去除虾线设备的零部件并出口,然后在境外组装成一台完整的设备,该设备侵犯了其专利权。上诉人Deepsouth公司辩称美国专利法并不禁止在美国国内生产专利产品的组成部分,将这些部分出口到国外进行组装并使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同意了上诉人的主张。在John Mohr & Sons v. Vacudyne Corp.案中,美国伊利诺伊州北部东区地方法院同样否认了对未经授权使用方法专利的美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该案中,美国专利持有人拥有在卷烟制造过程中用于再存储烟草的蒸汽工艺,Vacudyne公司未经其授权在美国境内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生产,组装和测试了一台机器并销往境外。尽管如此,法院裁定没有发生任何侵权行为,因为制造与销售的全过程并不是完全在美国境内发生的。在此期间,美国联邦法院在涉及侵犯美国专利的设备在美国领土上的临时存在案件中也反对域外适用美国专利法。在 Cali v. Japan Airlines, Inc.案中,美国喷气发动机专利持有人起诉日本航空公司侵权,主要争议问题是外国飞机在运送乘客和往返美国时是否需要支付美国的专利特许权使用费。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决定支持外国航空公司,理由是根据1944年《芝加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27条,允许在另一国领空内临时使用专利装置。
总体而言,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法院仍坚持专利法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维持这一立场的关键是美国法院确立的在美国境内界定受保护专利应满足“全要件原则”,即要求生产、组装、销售等各阶段行为都在美国境内发生。
1.3 美国国会专利法域外适用立法的例外突破
美国国会于1952年制定的专利法第271(a)明确规定,发明专利侵权除另有规定外,以属地主义原则为限。此外,1948年的《司法及司法程序法》(Judiciary and Judicial Procedure)第1498(a)条和第1498(c)条从政府责任承担角度也进一步明确规定,凡未经授权而使用或制造美国发明专利,该使用或制造是美国联邦政府所为或为其需要而提供,专利权人可向美国联邦法院对美国联邦政府提起诉讼并请求赔偿;若引起起诉理由的行为发生于国外则不适用该法。
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增速下降,企业研发投资率持续下降。出于对美国经济竞争力下降的担忧,1974年美国国会先后修改关税法第337条和贸易法第301条,并于1982年设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简称CAFC),专门审理专利、海关和政府合同相关索赔。
Deepsouth案对专利法域外效力的否定引发了广泛热议,美国国会在强大且高度协调的美国专利权人的压力下于1984年修正了专利法,增加了第271(f)条。首先,第271(f)(1)条适用于“全部或基本部件”在美国制造并出口以进行境外组装的情况。其次,国会通过第271(f)(2)条进一步超越了Deepsouth案,该规定将某部件打算在国外组装成专利发明时没有实质性非侵权使用的部件的出口定义为侵权。立法突破性地将境外组装行为视为侵权,尽管存在国内联系,但目标是针对从事零部件组装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最终结果是规范专利的国外市场,因此,其被认为是美国专利法立法首次例外肯定域外效力的情形。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报告指出,“当为外国提供部件以避开美国专利时,情况与在美国制造或出售创新产品是一样的;该法案对于维护创新和投资环境是必要的”[14]。
1988年美国国会专利法修正案为管辖域外专利侵权又增添新基础第271(g)条。虽然该条表面上是排除根据方法专利制造的产品进口到美国,实际上是保护美国的方法专利免于在境外被“使用”,在该条的约束下,当事人在美国境外使用该方法专利制造产品,然后出口到美国的行为须承担侵权责任。在立法推动下,涉及域外主张的专利诉讼案件不断增加。除上述条款外,专利法第105条关于外太空活动的规定,第271(b)条关于境外诱导侵权规定和第271(a)条中关于许诺销售规定是否具有域外效力也在实践上引起争议。此外,第284条是否可以包含域外损害赔偿也是一直以来存在争议的问题。
总体上,美国国会对专利法的修正赋予部分规则以域外效力,这些修正案试图弥补由于专利权地域性引发的漏洞。整体上这一时期的美国法院虽然积极参与跨国知识产权诉讼,但是,他们并不太积极主动地将本国专利法适用于域外。这一点与保护自身权利的“经济民族主义者”的期望相违背,因此,美国企业再次游说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如今,可以看到美国以“301调查”和“337调查”为代表的国内行政手段,以Trips为代表的国际条约机制,以及与专利法域外适用制度相结合的美国专利权保护制度,都以维护美国利益为前提。
2 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司法实践的限制与扩张
法院司法实践是国家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重要保障,这一趋势在美国法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5]。随着立法的变革,美国专利权人不断作为原告出现在美国法院,测试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的界限,但美国地方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在评估此问题上存在不一致。鉴于篇幅限制,本文重点围绕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实践展开分析。
2.1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限制专利法域外适用的实践
首先,尽管专利法第271(f)条被认为赋予域外效力,但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多起案件解释其适用范围时仍然比较保守。在Waymark Corp. v. Porta Systems Corp.、Pellegrini v. Analog Devices Inc.、Cardiac Pacemakers Inc. v. St. Jude Med. Inc.等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均认为第271(f)节禁止出口专利发明的部件,以部件实际从美国运出为责任承担前提,不包含方法专利索赔情况。例如,Cardiac Pacemakers案明确“鉴于国会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打算根据第271(f)节保护专利方法,而且国会明确打算推翻深南案的问题,反域外适用推定迫使我们不要将第271(f)节的范围扩大到方法专利”。
其次,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还狭义地解释了第271(g)款的规定。例如,在Bayer AG v. Housey Pharmaceuticals案中,法院确定该条文仅适用于通过方法专利获得的有形产品进口,排除了根据方法专利产生的无形产品进口构成侵权的情形。根据Eli Lilly v. Cyanamid案解释,方法专利的实质性变更不构成侵权。此外,法院明确指出,侵犯方法专利需要侵权人在美国境内履行该方法的所有步骤。在历经7年的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案中,法院最终认为Akamai & Limelight作为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商,由位于美国和全球各地数百或数千个服务器组成,在互联网上执行的方法专利的各个步骤可以在不同地方执行,美国专利法无权对此予以管辖。
再次,对于“销售”和“许诺销售”,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般认为专利持有人必须能够证明侵权实体出售或许诺出售“专利产品”,同时,专利产品的实际“销售”必须在美国进行,单独进行谈判和执行销售合同并不是根据第271(a)条构成侵权行为的销售。此外,法院在一些案例中裁定,许诺销售仅适用于在美国要约并实际在美国销售的情形。如美国Rotec公司起诉Mitsubish公司在中国制造的塔式起重机侵犯其美国专利权,美国联邦巡回法院认为,被控侵权者的合同签订等活动都是在中国进行的,根据美国法律,专利使用范围仅限于美国及其领土,并且不能以国外行动为由认定侵权,其结论表明在美国提出要约是侵权的先决条件。
此外,禁令救济是用于侵权补救的关键手段,禁令通常直接规制侵权行为。美国法院可以利用其权力授予禁令规范外国行为,但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早先的案例中持谨慎态度[16]。在Spindelfabrik案中,法院指出由于机器都是在德国制造的,美国专利法是在美国防止侵权,因此,禁令不允许将美国专利法的范围扩大到美国边界之外,将其禁令适用于这些机器。在Int'l Rectifier Corp. v. Samsung Elecs. Co.案中,法院认为三星的行为并非在美国发生,因此,不受禁令限制。
最后,一直以来损害赔偿的标准是一个争议性话题。除因境外行为造成的境外损失外,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侵权行为可能影响海外市场,对于这些海外损失是否应该赔偿也是现实问题。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对两种情形下境外损害赔偿的态度一直遵循否定观点,严格遵守专利权的地域性。在Power Integrations Inc. v.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Inc.案中,被告境外的行为无疑影响了原告的海外销售,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否定了专利权人追回境外利润损失的诉求。在随后的Carnegie Mellon Univ. v. Marvell Tech. Grp案中,被告侵犯了原告专利并向第三方收取特许使用费,原告主张该部分海外特许使用费损失,法院认为此行为发生在境外并不构成专利法第271(a)条规定的侵权,而损害赔偿应以构成法律上的侵权为前提,因此,损害赔偿不成立。在WesternGeco LLC v. ION Geophysical Corp.案(以下简称WesternGeco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态度也保持一贯性。
2.2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扩张专利法域外适用的实践
首先,联邦巡回法院在部分案件中对第217(f)条作出宽泛的解释。在Waymark Corp. v. Porta Sys. Corp.案中,法院裁定即使在境内未组装,仅为境外组装而运输关键部件并打算组装也构成侵权;在Eolas Technologies Inc. v. Microsoft Corp.案(以下简称Eolas案)、AT&T v. Microsoft案(以下简称AT&T案)中,均裁定指出部件可以包括无形软件,软件复制可以构成软件的“提供”;此外,在Life Techs. Corp. v. Promega Corp.案(以下简称Life Techs案)中,法院还裁定即使只有一个部件也引起构成实质部分而侵权。
其次,第271(g)条明确依据方法专利在境外制造产品并出口到美国的行为构成侵权。一般而言,美国法院关于专利纠纷的举证责任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在Creative Compounds v. Starmark案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指出,在此种案件中,被告较原告更具有确定真实制造方法的优势,基于公平原则,被告应揭示其制造方法,否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再次,第271(a)条是关于在美国境内直接侵权责任的规定。一直以来,美国法院对该条款的理解一直坚持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1994年的专利法修正案对第271(a)条增加了关于专利发明“进口”和“许诺销售”也构成侵权的规定。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Transocean Offshore Deepwater Drilling Inc v. Maersk Contractors USA.Inc 案中突破性裁判认为,无论要约在何处发生,即使在世界各地进行谈判,只要潜在的销售可能在美国进行,就可能构成侵权。此外,特拉华州地方法院曾裁定只要要约在美国境内,即使销售目的地不在美国也构成侵权。
此外,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在美国境外发生的诱导行为可能引发专利侵权责任。在Merial Ltd. v. Cipla Ltd.案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指出,如果外国当事方具有必要的知识和意图,利用域外手段积极诱使在美国境内发生直接侵权行为,则该行为属于第217(b)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在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A.案中,法院进一步认为,被告关于专利有效性的认识并非引起侵权抗辩的理由。
最后,在1998年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v. CellPro Inc.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改以往对境外行为发出禁令的谨慎态度,指出只要是为了阻止美国专利权被侵犯,对于一些本身并不构成直接侵权的境外行为,法院也可发出禁令予以规制。在随后的涉外专利诉讼中,美国法院常常毫不吝啬颁发域外禁令[17]。专利权人通过向法院申请域外禁令阻止境外侵权产品出口至美国,同时,美国法院发出的域外禁令不仅包含消极性禁令,也包括要求被告在域外积极履行特定行为的禁令。如在Micro International Ltd.v. Beyo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Co.案中,被告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家公司,其将产品出口至美国销售,侵犯了原告关于转换器的两项美国专利,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此颁发的永久禁令不仅包括消极的禁止即禁止生产、使用、销售、许诺销售或出口至美国,也包括积极的禁止即要求被告在其境外生产的涉案产品贴上标签,显著地注明“不在美国销售、使用,不出口至美国”。
2.3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专利法域外适用实践
近20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尤为关注专利案件,同时,最高法院也开始解决制定法的反域外适用推定问题。鉴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专利法域外适用问题上的不一致,美国最高法院在几起相关案件中着力解决此问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前期案件中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在AT&T案中,最高法院审查了两个关键问题,计算机软件是否构成第271(f)条的“部件”以及该软件的复制是否构成“提供”,法院最终判定抽象意义的“软件”不构成第271(f)条的部件;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即使第271(f)条是具有域外效力的条款,但反域外适用推定仍然适用。Life Techs案提出一个问题即单个商品成分是否构成第271(f)条的实质部分,法院驳回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解释,认为对“实质部分”作定量解释更符合立法原意和条文逻辑,仅提供Taq聚合酶一个组成部分,因在数量上仅占总体组成元素的1/5,与法条规定的情形相去甚远,故Life Tech公司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该案中法院并未提及反域外适用推定问题。此外,在2014年的Limelight Networks Inc. v. Akamai Technologies Inc.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若无他人完成系争方法专利中所有步骤以构成专利法第217(a)条的直接侵权行为,则被告并未构成同法第217(b)条的诱导侵权。
WesternGeco案是美国最高法院在过去30年里首次审理涉及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该案颠覆了最高法院在专利法领域对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一贯的谨慎传统。2018年6月22日最高法院以7∶2裁定这个历经近10年的案件,判决被告ION公司补偿原告WesternGeco公司海外利润损失9 340万美元。最高法院在分析该案时,适用了RJR Nabisco案确定的判断制定法域外效力的两步走方法,但是,跳过第一步(判断是否存在美国立法机关的明确表述),直接进行第二步,通过制定法规范的焦点判断是否属于该规范的域内使用。法院认为美国专利法第271(f)(2)条是原告提出专利侵权损害之诉和利润损害赔偿的法律基础,本案必须将第271(f)条和第284条相结合,美国专利法第284条关注的焦点是“侵权损害结果”,最主要目的是使专利权人获得基于损害的完全赔偿,被告在美国境内制造零部件,故本案的焦点是被告的境内行为,因此,判给原告的利润损失是对第284条的国内应用。戈萨奇和布雷耶两位大法官共同撰写了详尽的反对意见,其中,布雷耶法官认为,因在美国境外使用发明而判决损害赔偿,“可能会默许美国专利权人利用美国法院将自己的垄断扩大到国外市场”。该案引发了美国学界的广泛讨论,反对观点认为专利的过度赔偿将导致非专利实体的兴起,从而给创新带来负面作用,而且,专利所有人本身不一定具有境外利润的预期。支持的观点则认为,此判决为美国专利权人的境外求偿打开了大门,是对过去美国专利政策的反思和重整[18]。特拉华州地方法院认为,此案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推翻了之前的判决。
3 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制度评析
在美国宪法框架下,美国立法、行政与司法在国内法域外效力的事项上,逐渐发展出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借力和支撑关系,共同推动美国对外制裁法律机制的形成与强化[19]。美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以尊重专利权的地域性为前提,以效果原则为基础,仅对部分类型的个别规则赋予域外效力,是一种有限度的域外适用。
3.1 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的谨慎与扩张
美国法的域外适用充满了不确定性,行为类型、主体、经济背景、社会因素、监管环境、法官背景等都会产生影响,这种不确定性自身反复变化。鉴于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分歧,美国国会不断根据司法实践和经济发展状况等调整立法,这一点在专利领域表现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对专利法的不断修正,逐渐从立法上扩大其域外管辖的基础。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美国在立法上仍以尊重专利权的地域性为基础,仅针对境外组装和境外依方法专利制造商品并出口到美国等行为,确立部分规则的域外效力。
同时,美国司法界在限制与扩张之间表现出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美国司法界谨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传统上对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担忧外[20],还有几个因素影响美国法院的决定。首先,美国对专利权地域性特征的尊重,体现在对直接侵权的地域性遵守上;其次,专利权人可以通过国外专利注册寻求国外专利保护救济;再者,专利法的域外适用可能对专利的国际合作带来障碍,如果其它国家也予以相同的反制,势必对自由贸易造成障碍[21];最后,美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可能在一定范围内由于仅约束美国公司的境外组装和境外投资制造等,而最终对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利益产生影响,其并不约束不出口到美国的境外侵权的外国企业,在长期竞争中这势必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22]。但是可以看到,美国法院对专利法的域外适用建立在“效果原则”的基础上,并不断尝试突破,逐渐对在境外组装、境外诱导、境外制造并出口到美国的境外行为予以本国法的适用,在域外禁令救济和域外损害赔偿方面也不断扩张边界,甚至部分法院在一直仅适用于美国境内直接侵权领域的“许诺销售”问题上有所突破。对此,美国理论界认为,首先,在美国经济优势下滑、国际知识产权合作乏力的情况下,扩张域外适用范围与专利法促进科技创新的目的相一致,这种扩张将使美国能够继续在全球市场上制定专利保护与竞争规则而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23];其次,扩张不一定违反礼让原则,美国专利法域外的有限使用可以防止对美国法的规避,也不会对外国创新造成影响;再次,其与外国的法律冲突也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在巴黎公约等国际条约的努力下,各国国内专利法越来越趋于协调一致;此外,美国国会对第271条的系列修订填补了跨国监管空白[24]。
3.2 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的维权功能与竞争功能
现代社会,单纯地通过胜诉来实现维护自身权益、弥补损失的维权功能已经不再是许多企业参与诉讼的最主要目的,打击竞争对手、争夺市场份额才是其真实目的[25]。专利诉讼是富有公司的游戏[26]。近年来,美国专利权人常常采用申请“337调查”和法院专利侵权诉讼相结合的方法,双管齐下开展专利诉讼活动。
如果被裁定违反“337”条款,则被申请人的产品将被禁止进入美国,但申请人无法获得侵权赔偿。相较而言,采用侵权诉讼的模式,可以既主张就侵权行为颁发禁令以禁止侵权产品的制造、使用、出售或加工,还可请求经济赔偿。相对于“337调查”一年左右的周期,联邦地区法院审理专利案件的平均周期达25个月,加之美国专利诉讼的高额代理费、复杂的证据举证规则等使得很多企业迫于压力而转向和解赔偿。在NTP Inc. v. Research In Motion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方面判决RIM公司作为加拿大企业不应适用美国相关法律,另一方面却支持了NTP的权利主张。对于这一矛盾的判决,RIM向最高法院提起调卷令请求,但随后案件以RIM支付6.125亿美元作为补偿和解结案。“337调查”与专利侵权诉讼并举的策略,使得企业可以将竞争对手永久性地从国内市场排除并获得丰厚的赔偿金,即使企业在专利诉讼中不能胜诉,也能暂时性地限制竞争对手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为抢占新市场创造有利时机[27]。
3.3 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对专利创新与维护国家利益并重的作用
林肯有一句非常形象的概括:“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为了鼓励积极创新,政府必须对市场竞争行为加以调节,从法律上给予创新者市场垄断权,使其能从创新中获利,从本质上讲是对私权利的维护。美国通过立法确立具有域外效力的专利法规则,并通过司法强制力实现域外适用,进一步扩大了美国专利权保护的地域范围,实现了更大程度上对美国专利创新的保护。
知识产权的商业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法律。随着全球化及互联网的“无国界”,一些美国企业为了躲避美国专利制度而在外国设立子公司。美国的法律制度和专利政策逐渐认识到全球经济的现实,通过建立具有域外影响的新框架,试图保护专利政策最基本的前提即激励创新,进而达到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的目的。对此,有美国学者总结道:“美国法的效力止于国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美国乐见这一趋势。如果可以通过单边立法并动用执行资源规制其它国家的人,超级大国无须征服更多土地,就可以扩大其利益”[28]。
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与其它领域的法的域外适用一样,专利法的域外适用也难免带来他国对本国主权利益的担忧,在NTP案中,加拿大政府就表达了对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的不满,认为这会对加拿大与美国间的礼让原则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美国法律体系不得不努力平衡国内经济利益与对外关系,以及宪法规定公平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29]。但总体而言,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仍是美国法院最主要的衡量标准。
4 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当前发展背景下,有必要采取防御和建设共进的举措,在防范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不良影响的同时,加快推进中国专利法域外适用制度建设。
4.1 积极防范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的不良影响
首先,在企业层面,应充分利用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制度的自限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对专利维权竞争功能的认识,面对境外专利诉讼时缺乏思想准备和具体应对措施,时常处于被动局面。鉴于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立法的相对模糊性以及诉讼带来的竞争利益,美国法院在众多专利诉讼中表现出不确定性较大的现象,相关案件为中国企业应诉抗辩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企业在美国专利法域外效力扩张到自身时,应适时利用美国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充分联系要求、国际礼让原则及正当程序要求等制度,主张美国专利法对中国企业不具有域外适用效力。此外,我国企业应审慎选择合作伙伴,提高专利权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尤其是代工企业应尽量避免代工产品系非美国专利持有人的境外组织、方法专利制造等带来的风险。
其次,在政府层面,应全方位设置相关专利风险防范与应对“安全阀”。知识产权规则竞争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美国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呈现出从多边向单边发展的趋势[30]。要应对美国法域外适用,必须先了解美国法律制度及其实际运作,做好必要的风险预警。目前,中国企业普遍不具备风险信息掌握能力,政府应积极引导中国企业提高对外合作中的专利风险防范意识,并主导构建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专利风险预警机制[31]。2020年初中美达成《中美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第一部分内容主要是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对等化,其中,在司法协助方面提到“双方应确保其法院最终判决的任何罚款、处罚、经济赔偿支付、禁令或其它侵犯知识产权的救济措施,得到迅速执行”。美国特别善用禁令救济,并且通过司法确认实现对域外经济损害赔偿的救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必然面临相关的美国专利判决执行问题。对此,中国人民法院应综合运用公共政策保留等制度,对于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重大私人利益的外国判决、裁定,采取拒绝或谨慎提供司法协助的行为。
最后,在非政府层面,应多主体联动,加强相关研究,协助政府和企业做好风险预警与保障工作。专利法域外适用体现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互动使得专利保障制度更为复杂,相关行业协会应积极配合政府和企业做好风险预警,同时,学界也应积极推进相关研究,为中国立法和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高昂的诉讼费用是中国中小企业海外应诉最主要的障碍,一方面应建立知识产权诉讼费用保障,由行业协会采用企业互助发展的模式,根据企业出口额统计数据,设置一定比例提取作为知识产权应诉基金,发生相关诉讼时由行业协会从基金中提取一定金额予以扶持[32];另一方面,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险等业务,将海外侵权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并利用其海外服务网络和专业渠道的法律资源应对侵权诉讼[33]。
4.2 适度推进中国专利法域外适用制度构建
首先,法律移植是近现代各国知识产权立法活动的重要路径,同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水平应以尊重国家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为前提[34]。中国目前正处于专利引进大国和专利输出起步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一方面要应对因专利引发的美国制裁与诉讼,另一方面,在专利数量和质量飞跃发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存在专利保护意识薄弱的问题。美国在专利法域外适用问题上也是谨慎的,立法仅在境外组装、境外制造、境外引诱等行为上确立有限的域外规则,在司法上由于对专利法域外适用的担忧至今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中国专利法域外效力规制的确立应在体现中国理念和尊重专利权地域性的前提下,适度、有限地确立具有一定弹性空间的规则。当然,除实体规则外,也应重视禁令等程序规则的设计[35]。
其次,立法确立域外效力后,如何适用尤其是如何有效适用是关键。在私人专利法的域外适用中,私人发挥着重要作用。私人促进立法变革,并积极利用司法途径实现维权和竞争双重功能。当专利诉讼具有跨国特征时,谁赢谁输可能会对某个经济领域产生国际影响,尤其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如涉及公共卫生的药品、通讯等方面,甚至会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产生影响。因此,应积极调动中国专利权人的能动作用。
最后,司法具有填补立法漏洞、细化法律规定、适度扩张适用等积极作用[36],应对全球风险,离不开国内法院的积极作为。美国法院从最初对专利法反域外适用的坚守,到逐步谨慎的域外适用,这种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谦抑性做法也体现了对国际法的尊重。中国自2014年以来陆续在多地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和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尽管法院和法官不具有直接造法功能,但在法律的解释和适用上具有一定的能动空间。因此,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应鼓励法院结合具体案情,技术性地扩张专利法的域外适用。
5 结语
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工业产品的系统化、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但知识产权仍然具有地域性特性,赋予专利权以域外效力成为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平衡专利权地域性与全球保护间矛盾的重要手段。美国专利法的突破始于专利权人的利益诉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立法、执法和司法共同作用的域外适用体系,以维护美国专利人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适度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有助于保护本国企业利益,也是一个国家影响国际法规则创设的有力工具。现阶段,中国努力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应谨慎防范走出去的知识产权风险。一方面中国企业应提高专利意识,同时,在美国专利法域外效力扩展到自身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多样化、碎片化、单边化等特点,中国作为新兴专利创新国家,应借鉴美国等国专利保护模式,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利保护规则,保护中国专利权人利益,增强中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并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应认识到单边法律域外适用会对国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不能忽视知识资源在全球的公平分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正义。
——兼评专利法第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