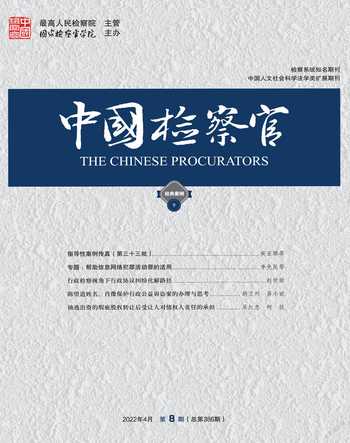美国法院商业贿赂引渡案的实体和程序
胡城军
摘 要:美国法院审理引渡案件,一般由美国政府代表引渡请求国政府,而美国政府则具体由联邦检察官代表出庭,它的常规审理事项为“可引渡犯罪”“双重犯罪”和“合理根据”问题,法院适用的法律为引渡国内法和条约,法庭论证的主要依据是判例和学说。我国可根据国情吸收其合理因素,如重视检察官的诉讼定位、加强合理根据的立法和司法等。
关键词:美国法院 海尔布隆 引渡
美国法院审判引渡案件的实体和程序对我国来说还比较陌生,本文以一个涉及腐败和欺诈犯罪的引渡案件——海尔布隆(Heilbronn)引渡案[1]来剖析,此案对我国的司法系统审理引渡案件有一定的启示。
一、基本案情
本案被请求引渡人(在本案中是人身保护令的申请者,所以也称“请求人”)海尔布隆是居住在美国的以色列人,且是美国永久性居民(美国绿卡拥有者)。他于1986年至1987年期间,在以色列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的教学医院贝林森(Beilinson)医院担任神经外科主任。作为科室主任,他有权指定哪个医生进行手术和安排手术顺序。
贝林森医院是普通病人基金(Kupat Holim Clalit)医院,是复杂的社会保健网络的一部分。普通病人基金是普通劳工联合会(Histadrut)的一个附属机构,是以色列四个保健基金中最大的一个,为以色列75%以上的人口服务。这个基金和其他三个主要的医疗基金的资金主要来自会员费、雇主费和政府资金。普通病人基金得到了政府的大量补贴和监管。
海尔布隆于1988年6月12日以贿赂和欺诈的罪名在以色列被捕,违反了《以色列刑法》第290条和第415条。他交了保释金,并获准赴美参加医学会议而离开以色列。审判定于1989年11月28日在以色列进行,但他未能出庭。起诉书第1至10项和第12项指控说,病人的亲属向请求人支付金钱,以确保他有权在医院为接受免费治疗的疾病基金成员进行手术。第8项和第9项指称,请求人接受了金钱,他承诺将亲自进行手术,而事实上他并没有。
1990年12月17日左右,以色列正式要求从美国引渡海尔布隆回去受审,依据是《以色列刑法》第290条的11项贿赂和第415条的2项加重欺诈。该项请求是根据1962年12月10日在华盛顿签署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之间的引渡条约》(以下简称《美以引渡条约》提出的,该条约于1963年12月5日生效。
美国联邦检察官遂代表以色列政府向密歇根州地区法院提出引渡海尔布隆的申诉。根据《美国法典》第3184条的要求,引渡听证会由治安法官布雷内曼(Hugh W.Brenneman)主持,于1991年3月27日举行。1991年5月9日,该治安法官签发了可引渡证书,证明引渡罪名1至10中的贿赂指控和罪名8中的欺诈指控。[2]海尔布隆随后根据《美国法典》第2241条在该地区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请求,以挑战该法院的治安法官对其提出的引渡证书,此时被告是联邦检察官约翰·肯德尔(John Kendall)。
请求人认为,被指控的犯罪并不属于引渡条约条款范围内的可引渡犯罪;构成被指控犯罪的行为根据美国法律并不构成刑事犯罪;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美国法典》第3184条和引渡条约第5条意义范围内可以作为审判的行为;引渡请求所依据的加重欺诈指控在以色列并没有受到起诉。
但法院在审理中发现,以色列对其指控的犯罪就是引渡条约中规定的犯罪,构成可引渡的罪行。首先,对于“贿赂罪”的理解,法院认为,条约使用的术语“贿赂”不仅限于对公共官员的贿赂,可以解释为包括对以私人的能力开展活动的个人的贿赂。其次,海尔布隆被指控的犯罪在两个国家都认定为犯罪,因此构成引渡的双重犯罪原则。贿赂的共同因素,即通过行贿或收受贿赂来影响其所承担的义务,这在《以色列刑法》和《美国法典》第666条和第1320a-7b条中都有相同的规定。再次,有充分的证据来保证引渡的合理根据。最后,法院认为,请求人利用病人的优势地位就足以构成加重欺诈,符合条约的可引渡犯罪。法院因此拒绝了海尔布隆的人身保护令请求,确认予以引渡。
二、法院论证过程
由于可引渡证明不是最终命令,因此不能直接对证明引渡的命令提出上诉,唯一的救济方法是在本地区法院内提出附带人身保护令程序。人身保护令不是纠错令,也不是对认证法官或治安法官已经作出的决定进行复审的手段,对治安法官引渡命令的人身保护令的审查范围是很窄的。以下是法院对人身保护令审查的要点及论证过程。
(一)可引渡的犯罪
法院指明,请求人被指控犯有11项贿赂罪,列在《美以引渡条约》第2条第15款。请求人争辩说,起诉书中所述的罪行不属于条约签署时对“贿赂”一词的理解范围:从历史上看,“贿賂”被理解为贿赂公职人员,以影响公职人员行为的执行,《美国法典》第201(c)条证明了这一点。请求人声称,由于他不是一名公共官员,外科手术不是一种“官方行为”,且所指控的行为没有“破坏”监管决定,因此所指控的罪行不在条约条款的范围。法院认为,条约本身并没有对“贿赂”下定义,也没有将其局限于公职人员,因此,确定无疑的是,不应对引渡条约作狭义或限制性的解释;相反,条约义务应该被自由地解释为有利于引渡。
审判期间,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律师顾问贝克(Baker)在他的声明中说,要求引渡请求人的罪行适用《美以引渡条约》第2条。法院认为,国务院对条约的解释有权得到相当大的尊重 ;虽然政府的政治部门的一项条约解释对于以条约解释为根本任务的法院来说不是决定性的,但它仍须得到很大的重视。
法院驳回了请求人对“贿赂”的狭义理解。法院列举了联邦和许多州的法律,这些法律涉及很具体使用“贿赂”这个词的情况,都有指向私人支付(金钱或货物)以影响他们的行为的意思。总体来说,在1961年以前,“贿赂”的共同理解和意思就已经超出它早期普通法的定义。在42个州和联邦立法中,“贿赂”包括了对以私人能力行为的个人的贿赂。
法院的结论是,条约中使用的“贿赂”一词不限于贿赂公职人员,对请求人的指控属于可引渡罪行的范围。
(二)双重犯罪问题
请求人的第二个主张是,对被指控犯罪有关的引渡违反了双重犯罪原则。
法院认为,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请求人违反了以色列的刑法,即《以色列刑法》第 290条。该条的规定是:“1.公职人员因与其职务有关的行为而收受贿赂,可处7年监禁或7年监禁和1万英镑罚款。2.在本节中,‘公务员’包括向公众提供服务的法人团体的雇员。”
为适用双重犯罪原则而确定在美国的犯罪,法院的通常做法是必须查看联邦法中类似条款的规定;或者,假如联邦法没有的话,则参考请求人发现地的州法;或也没有的话,则参考多数州法。
法院认为,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贿赂也是违法的。然而,请求人的论点是,脑外科医生在美国可以收取“市场能够承受的任何费用”,他被指控的特定行为在美国不构成犯罪,在以色列属于犯罪行为,因为“独特的经济结构把医生变成了公务员,并谴责向医生支付法律不要求他们提供的服务”。
法院援引判例的观点是:对双重犯罪原则应进行扩张解释,不要求两国法律所描述的罪行的名称相同,也不要求两国的责任范围相同,或在其他方面相同;如果被指控的特定行为在两个司法管辖区都是犯罪行为,这就足够了;如果请求国指控所依据的行为也被请求国法律所禁止,则双重犯罪的要求就得到满足;一项特定行为的分类不同,或两国适用不同的证明要求,都不妨碍引渡。
法院认为,以色列对贿赂罪的指控相当于《美国法典》第666条,该条规定,每年接受联邦援助超过1万美元的组织的雇员接受贿赂属于犯罪。它也可与《美国法典》第1320a-7b条相提并论,该条规定,任何人因安排或订购医疗保险支付的服务而接受贿赂都是犯罪。
法院援引判例的观点是:两个法律没有必要完全等同;如果每个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相同,并且两种法律“基本上相似”,则存在双重犯罪;当法规惩罚属于同一“普遍承认的犯罪”的广泛范围内的行为时,它们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如果“每一法规所惩罚的实质行为在功能上相同”,就满足了双重犯罪的要求。
对此,法院援引了布劳赫(Brauch)案[3]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布劳赫案中,引渡上诉人辩称,尽管英国的货币指控是违反该国的《盗窃法》,但它们完全是基于违反《外汇管控法》的指控,该法案是为了进一步推行英国特有的货币政策而制定的,在美国法律中没有类似的规定。该案上诉人辩称,若不是英国独特的外汇管制体系,他会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该案法院驳回了他的观点。该法院重点关注和比较了两项盗窃法规中欺骗的共同要素后,认为,双重犯罪要件的规定延伸到要求特定行为构成欺骗的理由并不是两个司法管辖区共同的實体法。
法院认为,本案情况基本相似。不管是根据《以色列刑法》第290条,还是《美国法典》第666条和第1320a-7b条,贿赂的共同要素是通过行贿或收受贿赂来影响所负义务,即这些法规对“贿赂”的定性本质上是相似的。双重犯罪并不要求请求人的行为构成贿赂的理由,在两个司法管辖区的实体法中是相同的。因此,法院的结论是:对请求人的引渡不违反双重犯罪原则。
(三)合理根据问题
引渡审判中合理根据问题的分析基本来自于引渡条约中“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被告有罪”的规定的要求。
引渡请求人声称,由于没有贿赂指控的基本要素——腐败的证据,因此没有合理的根据支持贿赂指控。他声称,这些指控只表明,他得到的报酬是因其技能而获得,而不是他的地位或影响力。
法院认为,以色列起诉书指控请求人滥用职权,与请求人的主张相反,这一法律结论并不是腐败的唯一证据。除了指控滥用权力之外,以色列政府还提供了那些付钱给请愿者以确保他为其亲属进行手术的人的口供。引渡材料还包括埃南(Einan)博士的宣誓书,他作证说,请求人作为神经外科主任,有能力决定由谁来执行手术以及执行手术的顺序。埃南医生在他的证词中说,请求人对一些病人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他们的病情不相称,而且有传闻说那些病人付钱给了请求人。他作证说,有两次请求人的病人的手术被奇怪地安排在其他有更大医疗紧急情况的病人之前。他还作证说,尽管请求人通常只做最困难的手术,但有时他做的手术是其他医生可以轻松完成的。综上所述,这些宣誓书构成合理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请求人滥用职权,收受金钱,并不是基于医疗需要,而是基于对自己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将手术等情况的安排或排期作交换。
请求人还声称,没有合理根据支持第8项欺诈指控,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海尔布隆没有按照医学上的理解“执行”该手术,或者他本人无意执行该手术。
法院认为,埃南博士和珍妮特·卡尔库利(Janet Karkukli)的证词支持第8项罪名中的欺诈指控。珍妮特·卡尔库利作证说,为了回报请求人说他是给她丈夫做手术的人,请求人要求她捐赠一台复印机。她进一步作证,在手术后,请求人告诉她,他已经切除了赘生物,并在随后的对话中表示自己是实施手术的人。埃南在证词中作证说,在有关卡尔库利手术的医疗记录中,埃南博士是外科医生,波夫兹纳(Povzner)博士是助理外科医生,海尔布隆医生根本没有参加手术。因此,根据适用于合理根据认定的宽松标准,法院确信有一些证据保证治安法官的裁定,即有合理根据相信请求人犯有在第8项指控的欺诈罪。
基于上述分析,法院拒绝了请求人的人身保护令。
三、对我国司法系统审理引渡案件的启示
(一)我国引渡法院应把握的三个基本环节
1.可引渡犯罪的判定。“可引渡的犯罪”条款是引渡条约的基本条款,一般在引渡条约的首部都有规定,采取列举式、概括式或综合式三种立法模式。[4]在美国法庭中的“可引渡犯罪”实际指犯罪的列举式。列举式最大特点是明确具体,在法院适用中可以直接对号入座”。《美以引渡条约》采列举式,该条约第2条列举了31项犯罪类别,其中第15项就是贿赂罪,第18项是欺诈罪,本案就涉及这两项犯罪。该“贿赂罪”没有区分公职人员贿赂与商务人员贿赂,因此当然包括商业贿赂。商业贿赂在《以色列刑法》中明确规定为犯罪,按照条约规定可以构成条约“贿赂罪”的要求,而“加重欺诈”问题在条约中没有区分欺诈的“轻”与“重”,被请求引渡人被证实足以在以色列犯有加重欺诈,因此也符合条约“欺诈罪”要求。
我国引渡条约目前很少有这类条款,但与莱索托引渡条约[5]以及我国香港与美国的引渡条约[6]采取了以上的列举式,法院可以“对号入座”式地适用。
2.双重犯罪的判定。双重犯罪原则条款相当于可引渡犯罪条款的概括式,一般会在引渡条约的首部得到规定,即被请求引渡人在请求国指控的犯罪,在被请求国也应被认为是犯罪,且两国对此规定的刑期都在1年以上或未执行刑期6个月以上才能准予引渡。概括式的优点是可周延囊括所有较严重犯罪。《美以引渡条约》第2条只规定对其列举的第27-31项犯罪进行双重犯罪审查。但是作为美国引渡法院的常规动作,美国法院在本案中仍然进行了双重犯罪的审查。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条约都采概括式,我国所签双边引渡条约大都采该立法模式。
根据美国的经验,我国法院在进行双重犯罪审查时要注意和认知以下问题:(1)被请求国法院对于“是否构成本国犯罪”的审查实际是对被请求犯罪人在请求国的行为进行本国法律的虚拟适法,而不是实在适法,即将该行为假设为是在本国发生是否构成犯罪,且犯罪的名称可以与请求国同一行为构罪的名称有所差别——不必名称完全相同。(2)被请求国为联邦国家时,则涉及到该国法院适用法律的选择问题,即到底是适用联邦法还是适用州法?本案法院给出的顺序是:先是联邦法律,再是发现地州法律,最后是多数州的法律。我国缔结引渡条约的伙伴国有联邦国家,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巴西等,我国向这些国家提出引渡时,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3.合理根据的判定。合理根据问题是美国双边引渡条约的立法特色,会以专条加以规定。《美以引渡条约》第5条规定,“只有在根据被请求方法律,有足够证据证明,假若被请求引渡人受到指控的罪行发生在该国,而将其羁押提审是合法的,或证明他就是请求方法院所宣判的人时,方可准予引渡”。该条的核心要素就是证据问题,即必须证据充分。其次是判断的法律依据,即按照被请求国法或请求国法。总体而言,判定被请求人有罪是引渡的重要前提,在美国引渡判例中称之为“引渡的合理根据(probable causes)”,为美国引渡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在本案中,对于被请求引渡人受指控的贿赂罪,有证据表明,其收受病人亲属金钱,为病人作特殊的手术顺序安排;对于其受指控的欺诈罪,有证据表明,其向病人作出了虚假的亲自手术的承诺。因此,证据确凿,引渡犯罪成立。就此而言,所谓“合理根据”,实质就是打证据。
笔者以为,我国引渡条约和《引渡法》都没有合理根据的规定,这是我国法律的一大缺失。合理根据是确定罪与非罪的重要依据和方法,在以后的引渡法或条约中可以加入这样的元素,并在引渡司法审查中将其作为核心的审判事项来看待,为说理性裁判书打下基础。
(二)应让检察官在引渡程序中承担重要角色
美国法院系统的司法审查程序大概是,首先由美国政府代表引渡请求国向被请求引渡人所在的州地区法院提起引渡申请,而美国政府具体又是由联邦检察官代表;然后地区治安法官举行引渡听证会,并做出是否准予引渡的初步结论;如果治安法官做出准予引渡的结论,被请求引渡人可以向地区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此时被告是联邦检察官;如果地区法院拒绝人身保护令请求,被请求引渡人可以向联邦巡回法院提起上诉,此时被上诉人一般是联邦检察官。中间可以穿插保释程序。[7]上诉决定做出后,由法院将判决意见及材料交联邦检察官,由联邦检察官送美国司法部。[8]美国国务院收到其司法部的材料后完成行政审查,做出最终引渡决定。因此,联邦检察官的角色在引渡司法审查程序中不可或缺。
我国检察官在引渡中的角色仅由《引渡法》第21条规定,即如果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引渡请求所指的犯罪或其他犯罪应由我国司法机关追诉,应将此意见告知最高人民法院和外交部。但我国检察官缺乏如同美国引渡司法系统中的角色地位,其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目前我国的引渡司法审查程序类似于行政审查,因为只有法官与被引渡人两方。笔者以为,尽管引渡司法审查不是类似于刑事公诉的程序,但也类似于民事诉讼程序,需要三方当事人才能更好地完成质证和辩论的诉讼过程,因此,在我国引渡司法审查程序中引入检察官代表请求国很有必要。
(三)形成说理性强的判决书
美国引渡判决书的写作一般说理性较强,论证比较充分。在引渡论证过程中,采用引渡有关的案例、条约、国内成文法和民间法律重述等,并非常重视证据的质证和采用。其中通常做法是采用案例来说明问题,以体现判例法国家的特色。相比我国法院的判决书说理性方面欠缺,亟待加强。
我国法院与美国法院国情有较大差别,但其判决也可以作为我国法院的参考。我国法院在审理引渡案件时,可将有些事项列为必须参考范畴,如“可引渡犯罪”“双重犯罪”和“合理根据”的认定问题以及善意解释方法等;有些可列为任意参考范畴,如判例和学说的论证方法等。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项目“美国引渡判例法研究”(20A291)的阶段性成果。
[1] Heilbronn v.Kendall.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Michigan, Southern Division.June 5,1991,Decided;June 5,1991, Filed.File No.1:91-CV-428.from:775 F.Supp.1020;1991 U.S.Dist.LEXIS 7846.
[2] In re Extradition of Heilbronn,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Michigan,May 9, 1991, Decided ; May 9, 1991, Filed,from:773 F. Supp. 1558 ; 1991 U.S. Dist. LEXIS 19442.
[3] Brauch v. Raiche, 618 F.2d 843, 851 (1st Cir. 1980).
[4] 参见马德才:《国际法中的引渡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5页。
[5] 该条约第2条“可引渡犯罪”没有采取列举式,但是第3條“应当拒绝引渡的理由”中列举了政治犯罪的排除情形(8种),属于可引渡的范围。
[6] 该条约在第2条“犯罪类型”中列举了36种犯罪类别。
[7] In re Extradition of Heilbronn,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Michigan,May 9, 1991, Decided ; May 9, 1991, Filed,from:773 F. Supp. 1576 ; 1991 U.S. Dist. LEXIS 19450.该裁决为地区法院针对海尔布隆的保释申请作出。
[8] 参见黄芳:《美国引渡制度研究》,《法律适用》2019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