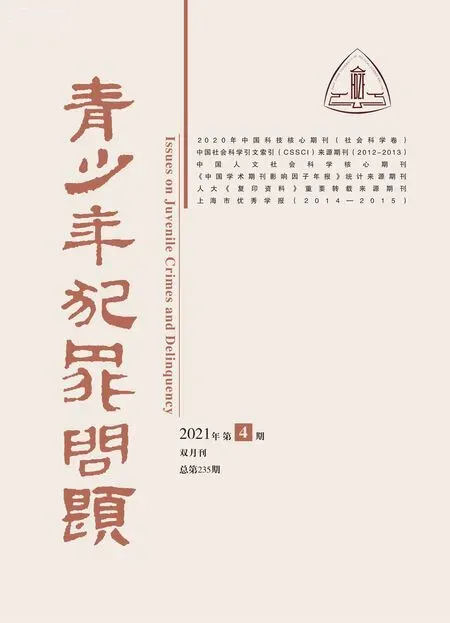实现全民守法的路径转变:从强制到法治教育
雷槟硕
守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旧法治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新法治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标志我国法治建设的升级,同时也表明党和国家对法治建设有新的理解,是新法治理论对原有法治理论的升华与发展。(1)参见范进学:《“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载《法学》2018年第3期。其中一个重大变化便是强调“全面守法”,一方面,这表明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心转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法治建设中的难点、问题与重心应转向包括守法在内的法律实施。另一方面,也表明法治社会的建成主要不是依靠执法、司法。尽管人们对法律的认知主要来自于他们对执法与司法活动的直观印象与间接经验,但有序的社会秩序表明,社会总体符合法律秩序的框架安排,呈现为整体守法的状态。社会中的大部分主体都选择守法,只有少部分主体会进入到执法或司法视野。若大部分主体选择违法,则法治建设可能面临溃败的风险。因此,防患于未然,探究人们守法或违法的原因以及如何改进守法环境、推进法治教育,比描述社会整体守法的实然状态更重要。只有更多主体选择主动守法,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纠纷,减少法律资源的事后投入,保证法治建设在社会治理的末端实现。
守法的重点在于人们为何守法。只有明确人们为何守法或违法,激发人们积极守法的动机,才能使上述守法对法治建设的作用得到落实。关于该问题,已有的理论提出了契约性守法、功利主义守法、游戏性守法、成本效益守法等观点。(2)参见王凌皞、葛岩、秦裕林:《多学科视角下的守法行为研究——兼论自动守法中的高效认知界面优化》,载《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吴亚辉:《论守法的逻辑——基于法经济学分析范式》,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不同观点对人们为何守法作出了不同的说明,但这些观点却未回答后述问题,即为何人们持有这些理由以及为何这些理由能够对人们的守法行为提供证成。而且,不同守法理由论仅为分析人们守法提供了“真理的片段”,无论是简单的功利主义判断,还是成熟的成本效益考量,都将守法塑造为工具主义的范式,增加了守法环境维持的外部成本。因此,为促使人们更积极守法,降低守法的外部成本,更可行的方式是“由外而内”促使人们内化守法理由,培育人们的规范认知,融贯主体的价值观与社会价值,在具体情形中践行守法行为,最终在宏观上实现法治社会的终端建设。
一、外在强制性模式的短板
传统的守法理论多主张采用外在强制性模式。该模式注重提高违法成本、加大违法控制等方式减少违法,进而实现社会与公民守法的目标。但是,外在强制性模式的守法观无法解释许多情形,在许多论证中都被证明是短板。
(一)外在强制性模式的短板表现
首先,外在强制性模式错误理解了“守法”的“法”的涵义。通过外在强制性模式促使人们守法的观点对法律本质存在错误认识。该模式将法律本质设定为一种强制性手段,最具典型代表性的理论就是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该理论指出,法律乃是一种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命令预设一个不利后果,作为制裁或强制服从。(3)参见[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一方面,法律是否都具有不利后果是存疑的,因为法律规定中不仅存在义务性规定,还存在权利性规定,不行使权利并不会带来制裁或强制服从。即使放弃权利意味着一种不利益,但不利益不等于强力制裁。反对者可能提出两种反对意见。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权利仅是义务的条件语句,将授权性规则理解为“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的片段。该种观点扭曲了不同社会规则的社会功能。(4)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88-91页。并非所有规则都必须以威胁方式存在才能发挥社会功能,而且社会实体——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或法律规则并非都需要对社会施加威胁。另一种反对意见以阿尔夫·罗斯的道义逻辑还原理论为论据,认为权利的可为道义模态可被还原为义务的应为/勿为道义模态。(5)参见[丹麦]阿尔夫·罗斯:《指令与规范》,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因此,法律本质仍是义务性,进而是强制性的。但还原是可逆的,可为道义模态可被还原为应为或勿为道义模态,意味着反之也能成立。并且,道义模态是道义逻辑问题,关注法律的规范性问题,即“为什么遵守法律”而不是“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再者,即使忽略规范性与性质问题的区别,在规范语义转向的背景下,将法律等同于威胁为后盾的命令,实质是将规范性等同于强规范性,忽略了更为基础的隐规范性,进而使得以规范性来源为核心命题的守法探究陷入还原主义困境。(6)参见郭贵春、赵晓聃:《规范性问题的语义转向与语用进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即是说,法律被理解为刑罚、行政处罚、惩罚性赔偿等要素为必备条件的硬性惩罚规则,任何“规则”都需要设定惩罚才被视为规则。相应的,只有违法才被视为法律的实施,而守法只是法律实施以外的活动。(7)参见[奥地利]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7页。因此,指出强制性模式短板,首先需要指出强制性模式误将守法的“法”等同于强制性规则,不仅不当地将法律范围过分缩小,还忽略了强规范的显性与弱规范的隐性不同。
其次,外在强制性模式无力解释诸多情形。强制性模式主张外部惩戒构造守法环境,使得主体实施行为时考虑违法成本。但实践中却存在诸多不考虑违法成本,或者即使考虑了违法收益与成本仍选择守法的情形,如在没有警察与监控摄像的红灯路口,且是深夜无其他车辆,仍有驾驶员选择守法。即在守法收益很低或为零且无违法成本时,行为主体选择守法,无法为外在强制性模式所解释。而且,生活中普遍存在如下情形,人们在守法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守法,或言之,人们不仅没考量守法成本与收益,甚至都未对守法行为进行考量。基于认知心理学上的人类信息加工机制可以得知,人们的很多行为是在无觉知状态下做出的,该类行为与外在因素是惩戒性还是奖励性的,甚或是否存在守法理由不存在直接关系。因为隐性记忆的存在会激活人们的自动加工机制,促使人们自动做出无觉知行为(既可能是守法行为,也可能是违法行为)。(8)参见葛岩、秦裕林、林喜芬:《为什么自愿守法——自动化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研究》,载苏力主编:《法律与社会科学》,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而且,生活中还存在大量积极守法行为,行为人也并未考虑外在强制或威慑。因为如前述法律规则不等于强制性规则论证指出的,承认法律包括授权性规则,意味着人们可以依据授权性规则实施行为。尽管人们行使权利可能是因为外在激励的引导,但外在激励不等于狭义上的强制。同时,还存在放弃权利的场合,如债权人基于亲情放弃部分或全部对债务人的债权。在该类情形中,不仅不存在外在威慑,也不存在被包含于广义威慑的收益。相反,放弃权利对权利人意味着不利益。此时,权利人仍在积极守法,却并非基于外在强制。
最后,外在强制性模式的维持成本过于高昂且收效甚微,以至于缺乏长期维持的必要性、可行性。不可否认,强制性模式对人们实施守法行为是有效的,但其成本过于高昂且收效甚微。(9)See Tom R.Tyler,Rick Trinkner.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34,42,132,201.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强制性模式发挥作用的范围与限度由维持强制性模式投入的资源决定,若不能持续维持资源投入以及投入的深度,会导致外在强制性模式作用衰微。如热点监管(Hot-Spot Policing)策略,即分析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人群的违法可能性,对该类情形集中投入大量外部威慑资源,实现减少违法行为的目的。但热点监管的成功,即在高压状态下维持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人群守法,依赖相关主体在热点领域持续投入高度集中的资源。对特定时间、地点、人群的资源高度集中投入,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使得原有的违法行为短暂潜伏或分散化分布,在资源投入减少时出现高度反弹。如2005-2007年,我国开展过三次“环评风暴”,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集中整治,但专项活动结束之后很快出现反弹。(10)参见何香柏:《我国威慑型环境执法困境的破解——基于观念和机制的分析》,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而且,外在强制性模式的效果也可堪质疑,如美国曾开展所谓“恐吓从善”(Scared Straight)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方面包括组织那些青少年违法者或者那些被学校或其他方式认定为存在危险的儿童参观监狱。在参观期间,孩子们将被狱警以及犯人训斥,以展示如果他们犯罪被抓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11)Tom R. Tyler & Rick Trinkner, 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 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p.201-202.但实践中的情况是,以外在强制性模式为核心的“恐吓从善”不仅没能促使青少年从善,相反,给“他们上了一课”,(12)Elizabeth S. Scott & Laurence Steinberg,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the Regulation of Youth Crime,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008, 18(2):26.使青少年掌握了更多的违法技能,形成了错误的价值观。该项目并未减少青少年的违法行为,而是使得青少年违法行为增多。(13)See Anthony Petrosino, Carolyn Turpin-Petrosino, Meghan E. Hollis-Peel, Julia G. Lavenberg, Scared Straight and Other Juvenile Awareness Programs for Prevent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andomized Experimental Evidenc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2003, 589(2):31.因此,尽管强制性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构造出成本高于收益的外部违法环境,促使行为人根据成本效益的理性考量实施守法行为。但从整体的成本效益角度分析,维持成本过于高昂且收效甚微,甚至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因而缺乏长期维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二)外在强制性模式缘何存在短板?
外在强制性模式无法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守法行为,尽管对于一部分违法行为有管制效果,但效果不甚明显,且在成本存量不增的情形下,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特定领域,会减少其他领域的资源投入,不仅无法解决特定领域违法行为的长期性问题,还可能导致“按下葫芦又起了瓢”,使得其他领域规制不足。即外部强制可以成为行为人守法的外部理由,但其效果为何不佳需要认真分析,这涉及人们为何选择守法的认知特点。因此,在指出外部强制性模式不足的同时,还需要分析强制性模式缘何存在短板。
第一,并非所有领域都适合外部强制模式介入。“权威染指这些范围的程度要受到限制,如果权威执意要管理恰当范围以外的行为,权威的引导可能被拒绝。”(14)Tom R. Tyler & Rick Trinkner, 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 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1.即任何主体都会认为特定领域是自主的空间,或言之,人们认为权威的活动存在的限度。如家庭中的孩子一般会将行为分为三个领域:道德领域、习惯领域与私人领域。在前两个领域中,行为可能涉及同其它人的活动与交往,也可能产生损及其他人的权利或者社会秩序的效果,因此孩子更易于接受外部权威对他们行为的介入。但在私人领域中,孩子更坚持自己的自主性,如果外部权威强行介入孩子的私人领域,会导致两者之间的冲突。尤其随着孩子年龄的成长,自主性认识逐渐提高,冲突会进一步加剧,通过外部强制力量保证外部主体的权威并不会提高外部主体的正当性,相反会削弱其正当性,将权威形象转化为威权形象。(15)See Tom R. Tyler & Rick Trinkner, 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 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46.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外在强制性模式需要供给更多的外部控制资源,却无法保证较佳的效果。因为个体“若相信有外在力量的控制……个体的自主控制感会减弱,内在动机也随之降低。”(16)冯竹青、葛岩:《物质奖励对内在动机的侵蚀效应》,载《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4期。为此,需要持续供给外部控制资源,而外在控制的增强会进一步削弱内在动机,进而需要供给更多的外部控制,使得资源供给不断增多,但实质效果越来越差,陷入恶性循环,一旦供给减少便引发反弹。
第二,人类是规范性的动物,而不仅是理性经济人假设驱动下的工具理性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感受性(sentience),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的是人拥有智识性,这种智识性就在于人的态度和行为展示出一种可理解的内容。”(17)韩东晖:《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一种规范性哲学的说明》,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或言之,人们具备的理性不仅有工具理性,还具有规范理性,能根据法律规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规范采取特定行为。即使人们的日常行为更多的是自动化行为,但该类自动化行为依赖于隐性记忆。隐性记忆来自人们于公共生活理性或规范理性处获得的认知,经过长期的生活操演与实践训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出现了人们遵守法律或者践行守法行为而不自知或者未进行反思的情形。但不存在前期的公共理性或规范理性实践训练,便会形成其他类型隐性记忆,引发其他类型行为——如违法行为,即自动化行为也存在实践差异命题。基于此,过于强调工具理性,关注人们与其他动物共通的感受性,而忽略了智识之中的规范性。而且,工具理性会导致人们一味地采取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违法成本低于收益时,守法便不再可能。尤其是对于市场经济主体而言,更是如此。但复杂的社会关系、复合的社会系统内,行为主体不仅单纯地进行成本效益考量。即使是市场经济主体,亦会采用社会的视角去评估其社会角色与责任。
第三,现有外部规制模式具有正当性溢出效应,在外观上具有覆盖甚至逐渐取代外在强制模式的特点。即使所有的法律规则都是强制性的义务规则,违法成本高于收益,外部环境能够持续维持资源供给,也不意味着强制性模式的施加是任意的或混乱的。在现代法治社会语境下,不利效果的施加以程序化的方式作出。在符合程序正义的情形下,即使外在强制模式会施加一个不利后果,相对于不正义方式,人们更倾向于接受程序正义保证的结果。“即使在特别小的时候,孩子就已经将程序正义纳入到他们关于公平竞争的观念中。”(18)Tom R.Tyler & Rick Trinkner, 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 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42.而程序正义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协助合法性强制,保证结果的可接受性,更在于程序正义形成了独立的可接受性外观,产生正当性外溢之效果,覆盖甚至取代外在强制性模式效果的特点。即是说,尽管在一些情形中,外部强制性模式似乎在发挥作用,但实质上并非强制性模式发挥作用,而是程序正义保证其发挥作用。尽管强制模式具有很强的外在控制,且外在控制对主体的自动遵循具有侵蚀效应,剥夺了行为主体一定的自主感,但因为程序正义提高了行为主体的参与感,在程序参与中使其了解和明确自身胜任该过程,获得正面反馈,抵消甚至超过控制阙如带来的正当性流失。(19)参见冯竹青、葛岩:《物质奖励对内在动机的侵蚀效应》,载《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4期。因此,外部强制模式发挥作用得益于程序正义,也正因为程序正义的功用,使得强制性模式本身功能阙如,为程序正义的正当性溢出效应所覆盖。
因此,一方面,作为规范性动物的人,能够但通常并不需要借助强制性模式便能实施守法行为;另一方面,强制性模式发挥作用的领域以及在特定领域内发挥作用存在限度,超过必要限度会侵蚀人们守法的动机,导致人们实施更多的违法行为。同时,即使强制性模式似乎在特定场合发挥作用,但可能仅仅是因为通过程序正义保障下的正当性溢出效应,实质发挥作用的是程序正义,而非强制性模式。
二、通过内在认可推进自觉守法
相较于强制性模式——将法律作为一种外在约束,并依据成本效益考量选择遵守与否——内化模式更具有可行性。两者的重大区别在于,前者接近于哈特所说的“外部观点”,而后者接近于“内部观点”。(20)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页。内部观点之下的主体具有较强的义务感与极高的主动性,(21)参见魏治勋、刘一泽:《法治的根基在于培育具有“内在观点”的公民》,载《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7期。不仅将法律规范作为外在约束,更多的是将法律规则作为二阶理由。即行为主体经过前期的批判性反思,学习并认可法律规则或其背后的法律价值,在行动时将其作为行动理由,即使该理由在内容说服力上未必强于其他理由,如道德、习惯、宗教规范等,但法律规范作为二阶理由依其性质排除其他内容说服力更强的一阶理由,在法治的末端实现守法。因此,通过内在认可推进人们形成规范认可,最终促进人们守法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从内在视角构建规范性;培育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需要区分不同阶段的法治教育。
(一)从内在视角构建规范性
守法是一种客观状态描述,探究为何守法是对守法主体行为理由的探寻。探究为何守法就是追问法律为何具有规范性,尽管法律规范是外在规范环境,但其之所以能够为人们遵循,则是因为其被内在化为一种行为理由。即使是强制性模式,也是通过外在压力刺激人们实施守法行为。因此,此处所指内在视角不仅是指法律规范内在化的过程,更不是人们因为外在压力被动采取行为,而是指法律规范内嵌于人们的主观认知,形成内在视角下的规范性认知,激发人们主动守法。之所以主张从内在视角构建规范性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遵守规则先于理解规则,要保持言行一致,需要将实践的理念转化为行动的理由。“遵守一条规则……人们是被训练着做这事的。”(22)[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45页。即“能动者的行动往往是在规则的指引下进行的,但在试图说明遵守规则的行动时,就会发现,我们恰恰是通过行动而理解和诠释了规则”。(23)赵晓聃、郭贵春:《规则遵循和意义的规范性》,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年第6期。即主体守法之“法”先于主体理解,特定主体对“法”的理解生成于守法之实践。守法主体通过践行“法”来理解其含义,即使守法主体借助隐规范性理解“法”,也需要守法主体在隐规范性实践中理解隐规范性,而隐规范性存在于共同体语境中。因此,规则与规则之理解相对分离,守法/遵守规则并不等于守法主体理解“法”;并且,作为共同体语境的隐规范性体现为共同体的行为实践理念,决定个体对显规范性的理解,而显规范性于守法实践中存在。若守法主体欲理解规范必须具备实践理念的观点,同时,守法主体也无法脱离隐规范性理解规则,因为“人不是未经教化,脱离规范且沉湎于个别性的动物”。(24)韩东晖:《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一种规范性哲学的说明》,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否则,守法行为仅是无自主意识的机械操作,犹如技术规范。尽管行为为行为主体作出,若与主体意识无关,无异于机器操作。相反,在规范语境中,守法主体对实践理念进行必要的批判性反思,并根据其内容的正确性或其性质预设将之作为行为理由,为守法提供实践辩护。否则,便不存在守法主体,仅是观察主体对守法活动进行外在的观察描述。因此,若使守法成立,必须要求主体处身于守法实践中,并在实践中理解“法”,将理解转化为行为理由,做到守法行为与守法主体自主意识的结合,实现主体自主的守法。
第二,即使是无觉知行为,已经存在的隐规范性使得自动化守法成为可能。自动信息加工仰赖于隐性记忆存在,尽管此时守法具有无觉知特点,但无觉知不等于“无知”。人类无法想象不存在的事物,即使神话、幻想、小说,也都以人的生活经验与规范实践为基础。对于法律活动而言,法律具有建构性特点,若要形成触发自动守法的隐性记忆,便需要在日常实践中建构隐规范性与显规范性活动。并且,“长期训练不但会改变神经功能,也可能改变神经结构……通过社会规范的建构,道德观念的普遍提升也是推动自愿守规的必要途径”。(25)葛岩、秦裕林、林喜芬:《为什么自愿守法——自动化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研究》,载苏力主编:《法律与社会科学》,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若要通过自动化守法降低社会守法成本,减少执法、司法环节的资源投入,应在日常实践中形成隐规范性,通过显规范性与隐规范性的双重训练,形成守法主体的隐性记忆,提升自动化守法的可能性。因此,即使是自动化守法,也需要在内在视角通过共同体实践形成规范语境。
(二)培育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
守法行为依赖守法主体之规范认知,但这不等于主体存在规范认知就会选择实施守法行为。规范认知可能是支持性的,也可能是反对性的。工具主义的守法存在成本高昂、收效甚微甚至负面作用等问题,而反对性规范认知可能导致行为主体采取违法行为,且在规范认知层面赋予违法行为以正当性,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因此,为增多成本更低、质量更高的守法行为,不仅要促使人们形成规范性认知,还需要规范性认知的内容为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
首先,人类具有规范认知塑造的可能性。“即使是小婴儿也能对道德与不道德行为进行可靠的区分。这些对道德行为的内在理解通过与外在世界打交道得到磨炼与发展,最终形成一个人对正义的理解。”(26)Tom R. Tyler & Rick Trinkner, 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 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42.一方面,“人非生而知之者”,规范性认知并非自始具备,而是在由简单到复杂的生活实践中逐渐习得;另一方面,规范性认知之路径并非固定的,而是可改变的,即使是实践中习得某种规范认知,通过改变外在环境、转换交互活动,也可以转变已有之规范认知。
其次,基于规范认知的可塑性与守法目的的考量,需要培育人们对法律的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即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社会形成权威正当的规范语境,构造共同体的一致规范,塑造后来者对特定问题的规范认知。守法构成社会整体实践,守法实践蕴含着人们对“法”的支持,无论是外显的态度还是内含的价值观,整体之实践形成隐规范性。在具体守法活动中,宏观上,隐规范性会对具体守法活动形成规范引导;微观上,其他主体的具体实践能为后来者提供遵循路径。人们在形成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之前,借助惯习遵循、行为模仿参与具体守法实践,也可能基于父母、学校、执法主体之强力践行守法活动。与此同时,人们在具体守法实践中理解守法之内容,形成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以价值观为纽带逐渐形成主动守法的反思性认知。与惯习遵循或强力维持不同,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是价值层面的社会纽带,将人们连接在一起。此时,人们具有主动向价值靠拢的倾向,而不是被动接受强力推行作为价值表征的规则。一旦联结形成,“这些价值观成为一个人的品质,当他们不能够遵守这些规则之后,他们自己会产生内疚或羞愧的消极情感”。(27)Tom R. Tyler & Rick Trinkner, 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 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72.
因此,为实现前述守法之目的,需要培育公民形成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在守法主体、规范语境之间形成连接中介,实现隐规范性到显规范性的传递与守法与守法理解的统一。
(三)区分不同阶段的法治教育
通过培育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促使公民形成对守法的认同,借助价值观与价值的融通实现规范认知的转换。在这里必须指出,并非任何一个阶段的价值观培育都是一样的,人在不同阶段的情况并不一样,因此,在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方式的法治教育。
首先,在家庭培育阶段(入学前阶段)注重简单奖惩引导,促使儿童形成具身体验。该一阶段的儿童缺乏必要的规范认知能力,自控能力弱,规范环境主要为家庭与玩伴,其规范认识主要来自身身体的感知。(28)参见雷槟硕:《教育惩戒权行使的目标:培育规则意识》,载《复旦教育论坛》2019年第4期。即该阶段儿童通过身体体验理解规范,理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做了会产生什么后果。在该阶段,儿童面对的最大权威便是父母,面对的规范主要是父母的命令与引导。规范认知的内容便是“如果这么做,不能吃零食”“如果那么做,妈妈会打我”,将饥饿感、爱的剥夺感等身体体验理解为规范后果,形成规范性认知的基础。因此,在该阶段,进行较高难度的认知控制并不可行,更多的是需要通过身体体验式奖惩促使儿童形成规范认知。
其次,初等教育阶段侧重于价值灌输与协商辩论。进入学校的儿童在前期更接近于学龄前儿童,但随着儿童入学时间变长,其同教师的接触增多,儿童开始面对不同系统的权威与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权威与规范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而面对冲突,儿童会依据前期形成的规范认知进行权衡判断,根据已有知识、经验与认知体验进行选择。因此,对进入该阶段的学生,不应再机械地采用类似爱的剥夺、身体惩戒的教育方式,而应进行价值灌输,进行规范辩护,并就价值辩护进行协商辩论,提升儿童的控制感、参与感与胜任感,可以促进儿童对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的深化赞同。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该阶段的儿童逐渐进入青春期,在生物学意义上,孩子社会情感系统与认知控制系统不断发育。但相对于社会情感系统,认知控制系统发育较为滞后,因此,青少年在青春期容易出现情绪失控、情感反应过度等问题,因为认知控制系统并未并轨发育,不能在生理意义上形成有效制约,引发青少年的冲动行为,忽略规范认知的内在约束作用。(29)See Tom R. Tyler & Rick Trinkner, 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 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11-114.因此,该阶段应采用必要的奖惩深化初期规范认知的效果,但奖惩应结合价值观,尤其是基本社会公德、基础法律价值等内容,将基础规范认知同法律价值进行链接,形成更牢固的规范认知观念,强化规范认知与支持性态度和价值观的约束力。
再次,对于高等教育阶段到步入社会时期的青少年或年轻人,要更加注重塑造他们同社会的联结,加强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的连接,通过协商合作、公平对待等方式,将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固定化。随年龄成长与教育阶段的深入,青少年更多接触不同规范,规范的正式性不断增强,规范之间的龃龉也不断增多。但该阶段的青少年认知控制能力不断增强,情感冲动受到更强的约束,行为背后具有更强的理由支撑。因此,采用协商合作的方式,公平对待青少年,可以借助认知控制能力强化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的效用,通过不同规范系统之间的辩论与过程公开实现价值融通,嵌套于青少年的规范认知系统。而且,通过青少年个体价值观与社会、法律价值的联结,可以构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纽带,能够保证非熟人社会关系领域的稳定,保证缺乏亲密联系的主体基于价值的向心力主动连接到内容性纽带之上,强化个体与法律之间的粘连性。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教育方式的阶段性,并且,还需要强调从儿童阶段就着手进行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的培育。一方面,诚如前文论证,不同阶段的主体具有不同特点,认知能力、自主意识、情绪控制能力等方面表现出生物能力的差别,采取无差别的方式并不能取得理想效果;另一方面,必须强调培育工作从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开始,尤其着重青少年阶段的培育工作。因为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并非在人成年那一刻突然获得,相反,这仰赖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的法律社会化过程,而且在青少年阶段已经基本形成。(30)See Tom R. Tyler & Rick Trinkner, 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 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不能将守法限缩为成年人的活动,忽略内在态度的奠基阶段。
三、达成个体价值观与法律规范的规范一致性
通过培育人们对法律的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可以促使人们在规范性上实现价值观与法律价值的一致,即在内在价值观与外在规范之间达成规范一致性。(31)See Tom R. Tyler & Jonathan Jackson, Popular Legitimacy and the Exercise of Legal Authority: Motivating Compliance, Cooperation, and Engagement,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2014, 20(1):79-81.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激发人们守法的内在动机,减少守法的外部成本。而且,通过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教育,规范意识不仅得以内化,还实现了规范意识同社会价值、法律价值的融贯。不仅通过更低社会成本方式实现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内化,还降低执法与司法在规范性认知上的成本投入。但这不意味着内化规范认知是独立的活动,相反,规范认知内化需要必要的外在条件,因为“守法不仅仅是对思想和观念的灌输,还包括……条件的供给和环境的塑造”。(32)李娜:《守法社会的建设:内涵、机理与路径探讨》,载《法学家》2018年第5期。因此,实现“由外而内”的规范认同,需要外部条件与内在观点形成合致。
(一)内在规范认知需要外在条件协调
规范认知并非形式逻辑推导的产物。并非给定前提,便能演绎地推导出人们获得与法律价值具有一致性的规范认知。以法律社会化的过程视角来观察,规范认知存在内化过程。首先存在外在规范可以内化,包括作为共同体实践的守法语境,作为隐规范性存在;还有具体的法律规范,对人们的行为提出具体的作为、不作为要求,作为显规范性存在。并且,隐规范性构成显规范性的基础,使得人们能够在守法实践的语境中实施守法行为,并通过守法行为理解具体守法行为的含义。
第一,现代社会并非扁平化的原始社会,具有体系化的系统语境,共同体守法实践属于系统语境的子系统之一。不可否认,法律以及规范的起源缺乏确定的考古证据,无法在实证上予以确认,使得人们无法确定规范语境的生成时期。作为替代解释方案,社会契约论、公平游戏论等理论假设依其理论说服力获得人们的认同。除此之外,人类学的考察、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证明与证伪,不断丰富人们对规范起源的认知。但现代社会不同于扁平化的原始社会,最重要的并非能否确定规范环境的形成时期,而是谈及培育人们的规范认知,现代社会确实存在相对体系化的系统语境。法律系统是社会系统(规范语境)的子系统之一,该系统在日常法律实践与法律规则的制定、实施的交互影响中不断发展完善。一方面,调整性规则宣告人们的生活,建构性规则塑造人们的生活,在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之间不断向前发展。以至于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淡忘法律的经验价值,加之思维经济原则的影响,规则成为节省时间的装置,(33)参见[英]约瑟夫·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朱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最终法律被人们作为建构性规范来设定、引导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并非一经确定便不再发展,现实生活往往会在特定领域、特定情形中出现生活与规范的对冲、融合,或冲击规范的封闭性,或结合规范塑造社会生活。尤其是面对生活的冲击,规范并非需要一味地妥协、更定,而是需要强调柔性开放的同时,不断重申“法治是被定义的生活”,共同体守法实践是“被法律定义的生活秩序”。(34)参见陈金钊:《法治是被定义的生活——关于法治逻辑的意义探寻》,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7期。在此类互动中,规范与实践形成了相对分离却又内在统一的互动语境,构成社会整体之规范语境,形成个体守法的隐规范性存在。
第二,规则体系构成具体外在条件,形成守法主体的行动理由集。守法作为一个统合性概念,不仅仅指社会呈现的守法状态,同时还指抽象意义上的人类守法行为。但守法活动并非抽象的,只有在具体情境中谈论守法才有意义。因此,守法理由论就需要具体到细致的行为理由上。如张三不杀人是守法,但张三在某个具体时间不杀杀父仇人的理由是《刑法》第232条规定了故意杀人罪,实施杀人行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在此,《刑法》第232条构成具体的行为理由。而体系化的法律秩序包括大量的法律规则,内容庞杂但有序的行动理由集。行动理由集是外在于人们的现行规范体系,若要促使其内在化,必须使规范能够转化为内在行为理由。外在理由集的转化依赖于两个条件:其一是共同体实践存在相对稳定统一的隐规范性,使得人们能够理解守法规范的基础含义;其二是能实现规范一致性,即理由集体现的规范价值能与主体内心的价值观合致。需要指出的是,规范性一致的达成是一个互动过程的结果,而且该过程是动态发展的。规范性语境与儿童阶段的身体体验互动形成基础规范性认知,基础规范性认知又结合校园与社会规范发展为更为复杂的社会规范认知。这种认知更多的是生活维度的,而非法律意义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未遇到正式意义的法律问题。(35)See Tom R. Tyler & Rick Trinkner, 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 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1.但日常生活的守法实践与隐规范性环境,以及前期体验形成的规范认知不断交互影响,在具身体验中训练获得隐性记忆或行为理由,作为实施下次守法行为的动力。
第三,守法主体将具体规范作为行为理由不等于其能够认知全部行动理由集,人们对作为行动理由的规范认知,更多的来自于朴素认知。“无法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法律专家”,并且,即使是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也无法知悉全部行动理由集。一方面,因为法律自身的复杂性,使得了解、认知、认可外在行动理由集需要巨大的信息成本、机会成本以及认知能力,法律的庞杂使得人们不可能获知全部行动理由集;(36)参见李娜:《守法社会的建设:内涵、机理与路径探讨》,载《法学家》2018年第5期。另一方面,守法主体对具体规范的认知,更多的是朴素的“正确性”认知,掺杂着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的认知,往往并不具体到法律条文层面,更多的是停留在规则与规范语境之间的原则/基本价值层面。这个法律近似于伯尔曼“‘法律’信仰论”中的“法律”,被信仰的“法律”并非是规则意义上的法律条文,而是自然法,即价值层面的原则,关乎法律背后的正义理念。(37)参见范进学:《“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解误解的深化——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2期。对于普通主体而言,无需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具体规则转化为行为理由,人们只需将自身的价值观同具体规则背后的法律原则/基本法律价值达成规范性一致即可,这便意味着人们具有将外在规则转化为行为理由的能力与可能。即使在涉及具体行为规则的情形中,规范一致性依赖的也是原则的价值性实现中介传递。相反,单纯传递具体法律规范,并不能直接引起人们的认同,也不能形成规范一致性,一方面这是因为已有价值理念与显性规范可能存在错位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原则在价值层面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规则的具体性、复杂性、可转化性等方面阙如,使得作为受众的公民无法理解或有效将具体规则同其背后的价值联结起来,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普法的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
第四,规范一致性是实现规范内化的前提条件,但规范一致性并非当然形成,其需要外在权威具有合法性外观,能在规范性上符合内在认知或体验。即是说,规范一致性以符合论为判断方法,以内在认知或体验为判断标准,符合标准的,则在认知上实现规范一致。因此,由外而内的内化需要权威是合法的,若外在权威不能以符合内在规范认知或体验标准的方式行为,或者外在显性规范不符合内在认知的,会出规范性冲突,进而引发违法行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间或发生的规范冲突便是例证,典型的就是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情形,如饥饿难耐偷面包、偷药品救生命垂危的亲属等。尽管该类情形属于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冲突,但也能揭示规范冲突的特征以及由此引发的违法问题。即是说,显性规范因其复杂性、具体性或可转化性问题导致规范性认知效果欠佳,是规范转化的形式问题;而显性规范不符合公民的内在认知则是因为规范转化的内容存在问题,两者共同构成规范性认可的障碍。
因此,通过法律价值内化实现守法之目标依赖外在价值内化的过程,而内化过程仰赖外在价值与内在体验达成规范一致,这使得规范认知依赖于共同体实践形成的宏观规范语境与具体情形中的微观规范转化。后者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形式上的“可转化”,其二是内容上的“能符合”。
(二)通过协商性模式解决如何促进守法问题
由外而内的内化模式具有外在强制模式所不具备的优势,能更好地促进人们守法,但“内源性研究路径有一个较大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很难回答一个实用性问题,即‘如何促进人们守法’”。(38)吴云梅:《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一个经验性守法研究的新路径》,载《西部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尽管由外而内的内化模式并非简单的内源性研究路径,但到目前的论证都未给出如何促进守法的方案建议。因此,为避免类似诘难,需要指出,由外而内的内化模式如何促进守法。
首先,该模式相较于强制性模式具有优势,因为规范一致性可以形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结,将个体嵌套于隐性规范语境,并将显性规范转化为行动理由,通过规范一致性促进行为主体采取守法行为。因此,解决“如何促进人们守法”的问题不在于该模式能否促进人们守法,而在于该模式需要借助何种方式实现。即由外而内的内化模式能够促进人们守法,问题在于应采取何种方式实现该模式,通过规范一致性实现促进人们守法的目标。
其次,在常规领域,规范一致容易达成,因为多数人都生活在隐规范性语境中,对法律持整体支持态度,往往采取守法行为。但对于非常规领域,存在规范冲突的情形或显性规范较为专业的领域,因不同规范指引的指向不同,或因为显性规范缺乏必要的可转化性,使得个体无法有效借助隐规范性语境理解显性规范,最终无法实现规范一致性的要求。因此,实现由外而内的内化的重心在于非常规领域。
最后,对于非常规领域的规范一致性目标,应采取协商性模式来达成。协商性模式强调三个要素。第一,提供商谈机会。因为规范认知的形成受自主感、控制感较大影响,在规范冲突的领域或无法理解的领域,通过强制实现规范控制,会减损权威的合法性以及规范的正当性基础。“强制好比将沙子投进齿轮中,系统会运转地更慢和更不流畅,结果就是成本更高昂——有时会成本高的失去了竞争力。”(39)Jane Mansbridge, What Is Political Science Fo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4, 12(01):11.相反,通过给守法主体提供机会进行规范认知商谈,可以提高守法主体的胜任感、控制感,尽管结果不一定符合守法主体的目标期待,但胜任感可以抵消不利后果带来的冲击。(40)See Tom R. Tyler & Rick Trinkner, 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 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7.并且,通过提供商谈机会,可以形成守法主体与权威以及显性规范之间的交流机会,提升几者之间的隐性联系,在规范性暂时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形中,形成约束力较弱的纽带,而不至于使行为主体脱离隐规范性语境的框架。第二,进行理由说明。在规范冲突与显性规范转化困难的领域,显性规范不符合行为主体自身的规范认知,或者显性规范因其抽象性、封闭性无法为行为主体所理解,进而无法实现规范一致性的目标。类似情形出现时,法律实施主体不能放任问题存在,相反,应化解规范冲突或提升规范的可理解性,融贯显性规范与基本法律价值,进而达成规范一致性的目标。因此,法律实施主体不仅要给行为主体提供商谈参与的机会,还需要为显性规范提供理由。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价值选择与观念变化的加速,使得冲突不可避免,只有进行必要的理由供给才能缓解多元与易变带来的冲击。第三,阶段协调。尤其是在生命历程的视角下,规范认知是在法律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认知在成年早期才逐渐定型,而在此前的几个阶段存在阶段转换的问题:学龄前—初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完全步入社会阶段。在不同阶段,规范认知教育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产生的结果可能并不一致。因前述不一致,在阶段转化中会出现认知冲突。如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可能采取强制性模式,学校则可能采取协商性模式;或父母采取协商性模式,学校可能采取强制性模式,这会导致孩子的认知冲突。或者,规范认知的培育并非仅是某一个阶段、一个领域的任务,需要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协调培育。不能将规范认知培育交给某个特定阶段,形成其他阶段的培育空白或真空,这样很容易导致规范认知偏差,使得错误的规范认知介入。如学校通常将自己定位为技能教育场所,培养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41)See Tom R. Tyler & Rick Trinkne, Why Children Follow Rules: Leg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59.但学校还应承担规范认知培育的责任,否则诸如不良同龄人团体、低俗亚文化圈等外在环境很容易侵染成长阶段的行为主体的规范认知。所以,规范认知的协商性模式还需要注意阶段协调。
结 语
法治社会建设不仅需要有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严格公正的执法司法活动,更需要全体行为主体积极守法。保证全民守法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外在强制性模式与由外而内的内化模式。采取强制性模式不仅需要持续投入高昂的社会成本,而且收效甚微,甚至可能导致负面效果。相反,促使人们形成内在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可以降低社会成本,同时促进人们更加自愿、积极、主动守法。为此,需要注重培育内在支持态度与价值观形成的条件,即促进共同体实践构成的宏观隐规范性语境与微观显性规范同行为主体价值观达成规范一致。通过规范一致性将个体(价值观)与法律(价值)联结在一切,形成法律与个人之间的纽带,促使人们认同法律。进而促使人们将法律体现的价值作为内在动机,在具体情境中,将规则形成的外在理由集转化为内在行为理由,培育自动化守法的隐性记忆与基于批判性反思的显性记忆,提升规范激发人们守法的效果,在法治社会建设的终端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