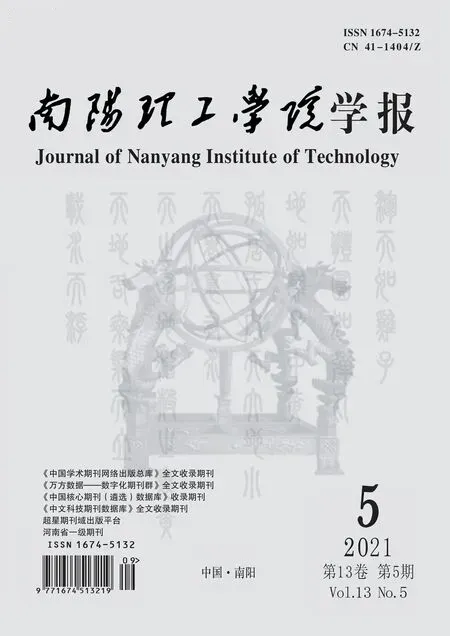《宣室志》的佛道文化探析
常智慧
(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宣室志》因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问鬼怪神异之事而命名。鲁迅先生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著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新的阶段,虽观念上仍不离搜奇记逸,但写法已基本上是出于作者的构想,更加讲究技巧和文采,是“始有意为小说”。唐代思想活跃,佛道观念盛行,文人普遍倾心佛道,因此出现了众多与佛道相关的作品。晚唐小说发展到后期,小说技巧日益成熟,出现了专集类作品。《宣室志》便是在小说技巧成熟和晚唐佛道思想活跃的两相作用下出现的。
一 晚唐佛家思想影响下的小说世界
汉末魏晋时期,佛教文化渗透到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表现出佛教影响文学的特征。到了隋唐时期,文人创作延续这一特征,出现了一系列与佛教相关的作品,以佛教为主题的唐人传奇便是如此。
(一)晚唐佛家思想熏陶下的创作动机
唐代社会思想文化高度繁荣,从整体态势看,佛教在唐王朝大致可与儒、道并举。但又因统治者对佛教的喜好不同,其对佛教的政策也会有所差异。唐敬宗时,曾大力倡导佛教,寺庙僧侣日益增多。文宗以佛教对政治教化无益,而下令铲除佛教,之后又转变态度,“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之像,以彰感应”[2]96。唐武宗即位后崇尚道教,故“诏除天下佛寺”[2]53,令“沙汰归俗”[2]110,抑制佛教发展。到了宣宗朝,佛教的颓靡态势才有所改变。这些在《宣室志》中都有涉及。
在《宣室志·迎光王(一)》中,太子宾客卢尚书在梦中向自己为僧时的师傅详细讲述了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反复无常的境况。其中“会昌中,沙汰僧徒,斥归家,以荫补光王府参军”[2]33以及“无几,宣宗自光邸践祚……自是稍稍兴复释教,寺宇僧尼如旧制”[2]34都是对唐武宗会昌灭佛及宣宗稍兴佛教的真实再现。
张读不但在小说中表述了其出生之后的武宗灭佛和宣宗兴佛事件,就连敬宗和文宗朝的佛教政策也有涉及。究其原因大致如下:据史书载,张读的祖父张荐写有《灵怪集》,而其外祖父是当时家世显赫的牛僧孺即《玄怪录》的作者,其从小就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除此之外,《宣室志》中也有张读学过佛法的例证,如《宣室志·求人心遇猿僧》讲述了宗素为父求心却遭猿猴化为胡僧戏耍的故事。这一故事中出现的“割体饲虎”原是佛教“本生”故事,猿猴所说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3]亦是出自佛家经典《金刚经》。由此知,张读是学过佛的。张读本就不满武宗灭佛的过激行为,再加上小说世家的多元文化影响,在灭佛压力减弱时便将有关佛教的重要事件表现出来。
唐朝是一个高度开放和包容的时代,文人创作和学习的热情高涨,他们渴求从儒家之外的其他宗教中汲取营养,融入中土的佛家思想便是他们的首选。统治者对佛教态度的反反复复更是招致推崇与学习佛教的文人的不满,因此他们便用创作的形式将心中不平表达出来。张读所作《宣室志》就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为小说披上了一层宗教外衣。
(二)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营造的小说氛围
佛说:“天地之间,五道分明,恢廓窈冥,浩浩荡荡,善恶报应,福祸相承。”[4]佛家认为,每个个体都是前生、今生和来生三世不断轮回的过程,这提醒着人们善恶有报,要多做善事。我国自古就有关于因果报应的记载,如《说苑·敬慎》云:“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也。”[5]但相较而言,佛教对因果报应观念的阐释更为全面。这种观念经过晚唐的沧桑巨变与佛法在中土发展的双重作用而表现得更为明显,各阶层文人大多把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反映到创作当中。据笔者统计,《宣室志》中有关因果报应的篇目多达23篇,大概是全集的1/7,这个数目是相当可观的。下面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如《宣室志·贪官变牛》中说,崔君“为河内守”[2]26时贪婪刻薄,“尝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值”[2]26,死后变成牛来承受自己作恶多端的后果。这一故事是佛家观念中恶有恶报之典型;又如《宣室志·犬报德(二)》中赵叟常把行乞得来的食物分给群犬,因此,在大雪冰封的天寒时节,群犬为无衣的赵叟驱寒,当赵叟最终因寒致死后,“群犬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2]29,这个故事即为善有善报。作者列举这些,实际是对晚唐社会风气的一种警示。晚唐社会处于政治黑暗、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混乱时期,各级官员只顾个人利益,压榨百姓;百姓的赋税沉重,苦不堪言。唐后期民风不再淳朴,人们相互猜忌与欺骗,身为官僚的张读对此感到尤为痛心。因此他希望通过这些故事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丝善良。即使身为动物都懂得善报,(比如小说中为赵叟驱寒的群犬),更何况是我们人类自己呢?这不得不引起当时社会的反思。
在PLL合成频率源的设计中,为得到高精度的输出信号,一般由高精度的有源温补晶振提供高稳定性的输入信号。若在VCO与数字N分频器之间接入前置倍频器,PLL合成频率源的输出频率便可达到GHz数量级。
不仅如此,《宣室志·董观死而复生》中的“死而复生”[2]51、《宣室志·竹季贞借尸还魂》中的“借尸还魂”[2]83等,都表现了佛家的轮回观。虽然死而复生类故事是佛教文化在小说中的常见反映,是小说虚构的手法,但也是佛家因果报应的另类体现,是晚唐无望社会中作者寄希望于佛家普度众生的现实反映。
小说作者将佛家因果报应观念运用到我国的叙事文学创作中,对我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后来许多章回小说的构思都不能超越因果报应的结构模式。在这类小说中作者往往会将这一价值观具象化,再将其主人公设为真人,以加强故事的真实感,起到了教化人心的作用。
(三)晚唐时期人们对特异佛僧的精神寄托
晚唐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当时政治黑暗、赋税繁重,百姓不堪重负。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到公元884年黄巢起义被平息时,唐王朝已元气大伤。张读此时在朝为官,目睹着民生疾苦,但他并不甘心昔日辉煌就此没落,他渴望出现能人异士来拯救国家。由此,他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一批奇异佛僧。这一方面迎合了当时社会修习佛法的热潮,另一方面也符合当时百姓渴望被解救于水火的强烈愿望。
如《宣室志·三宝村》中胡僧不仅知道村里所埋是何宝物,就连宝物的来历以及开启的确切时刻都可以预测。作者虚构出这样的村子,首先表现出佛教中认知过去和预知未来的特异功能,契合了当时人们希望出现真正的活菩萨给他们指引明路的心理;其次,文中还说宝物是一名男子因躲避祸乱埋在此地的。由此可见,三宝村是一个可以避难的理想之地。笔者认为,对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来说,急需此类地方来护佑自己的安全。作者虚构出这一理想桃花源,表达了人们对安定生活的美好向往。
《宣室志·诸葛重生》中说,韦皋满月时因遇一胡僧前来拜访而面带喜色,胡僧解释前世俩人是好友,并预言韦皋“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蜀人当受其福”[2]120。而后韦皋的经历果然如此。韦皋是中唐名臣,传言他曾“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作者注:古同擒)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6]在动乱不安的晚唐更是急需这样的名将来护佑百姓。张读这样写不仅表现出佛法的转世轮回观念,更反映出晚唐百姓对英雄的渴求,希望他们能够为其带来安宁。作者刻画特异佛僧,不仅是对佛法无边的赞颂,更是对奇能异士的渴望。在当时那个动乱年代,能救百姓于水深火热的大多是能人异士,笔者认为这一思想和当时社会的豪侠观念也有些契合。如《虬髯客传》中对豪侠的渴求和《宣室志·诸葛重生》故事中对特异佛僧的期望大体相同。
晚唐佛家思想影响下的小说世界不仅是作者本人学习佛家思想的有力佐证,也是当时社会众生普遍修习佛法的真实再现,体现出当时百姓渴望出现英豪来改变现状的心态。作者在小说中对佛家世界的虚构,也加深了我们对佛教影响文学的理解。
二 乱世求仙思想及对道士的讽刺与批判
道教是唯一植根于中国土壤、产生于东汉末年的本土宗教,它从古代的巫术、神仙传说、谶纬神学以及黄老思想中发展而来。道教产生之后,就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传奇小说中仙道题材的重要来源。
(一)乱世中的求仙思想
传说道教的始祖是老子。因老子和唐王室同为李姓,故唐自称为老子之后,道教是其信仰的重要宗教。《旧唐书·玄宗本纪》中的“辛卯,享玄元皇帝于新庙。甲午,亲享太庙”[7]133,“二年春正月丙辰,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7]134,“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宫为太微宫”[7]134,皆为王室重视道教的反映。唐代公主妃嫔多入道受封,朝臣如贺知章等,亦弃官为道士。道教在唐代尊崇至极,至唐武宗时,更是勒僧还俗,暴虐至极。晚唐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使唐王朝难以再现开元盛世。因动荡不休,大多数文人无法通过科举走向仕途,深感自己报国无望,故转而信道求仙。《宣室志》中就有表现乱世求仙思想的作品。
如《宣室志·李贺成仙》说的是,房建因心慕道教而常随道士修习道术,后来遇见一位道士送他发簪,并被告知此簪来历。房建去往南海后,见一泥塑道士如此前所遇道士却未有簪。后与其交谈,果是同一人,房建“因以玉簪归道士”[2]162。南海观中泥塑道士竟可以跨越千里来和房建谈论道术,不能不令人称奇。作者通过对这样的奇异事件的虚构,表现了道教的神奇,符合当时社会的求仙心理。求仙访道不一定非要到遥远的蓬莱仙山,只要潜心求道,无论在哪都能得到仙人指点。作者赋予此类故事真实的主人公,更加激发人们对长生不老的渴求。唐朝本就标榜得道长生,晚唐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世家子弟将报国无望的社会心理安放于求仙访道之中。再如《宣室志·章全素》说,蒋生因不识章全素为真正的仙人,未听从全素的建议,最后导致求仙失败。这是对盲目求仙者的讽刺,也是乱世求仙思想的另类体现。面对唐末乱世,人们大多选择将灵魂放逐在求仙中,去找寻精神的蓬莱仙岛。他们急于求成,为了得道修仙不择手段。而笔者认为这正是当时世人对求仙急躁冒进的体现。
晚唐时期的求仙思想是当时社会状况下的必然产物,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这一求仙思想不仅是当时社会思潮下人们的精神桃花源,促进了晚唐文人的精神升华与文学创作,如《宣室志》就是很好的例证;它也可能会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海洛因,促使他们感性求仙,急于得道升天以求解脱,导致其因炼制和服食丹药而丧命。
(二)兆应类故事的天命无力感
中国占卜问事历史悠久,“此则古之巫、祝、史,秦汉之方士,今日之巫觋,皆为本等之行业,而今之道士,亦似舍此而外,无谋食之方耳”[8]99。那些占卜之士认为,凡是大事必定会在一些物象方面有所预警,而占卜之术可以解释这些奇异现象。志怪传奇中大多有此类故事,这反映出浓重的天命观。关于天命,《论衡·命义篇》中说:“命当夭折,虽秉异行,终不得长;禄当贫贱,虽有善行,终不得终。”[9]天命不可违抗,一切都是注定。晚唐时期,社会走向没落,对晚唐百姓来说,往昔的开元盛世一方面提醒着他们此前的繁华,一方面又暗示着繁华难再,让人对此感到无力。这些让作品蒙上了一层悲凉灰暗的情绪。
《宣室志》中有许多兆应类故事。这些故事中的谶兆现象虽然大多反映的是贬谪、疾病以及生死,但内容丰富,值得注意。如《宣室志·李揆》中李揆见到蛤蟆而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君梦到蜘蛛却数日命绝;《宣室志·王缙贬兆》中王缙见一老鼠后不久果然获罪被贬。这些征兆都与动物有关。又如《宣室志·娄师德》说,娄师德在梦中进入一个叫作“地府院”[2]32的地方,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一生,“后入仕,立官咸如所载者”[2]33,又因误杀无辜而被降寿,“自是卧疾,后三日乃薨也”[2]33。这篇小说的谶兆涉及了预言和梦境,典型地体现出天命观,深刻地透露出一种浓重的晦暗色彩,恰恰吻合了当时世人无力改变自己及国家命运的心态。
《宣室志》中有很多反映天命观的兆应类故事,据笔者统计有21篇之多,使小说集周围萦绕着一层幽寂冷清之感。此类小说大多透露出一种无力改变命运的宿命观,这和此一时期的文人心态有很大关系。晚唐时期,政治黑暗、经济低迷,处于当时社会的人们看不到自己和国家的未来方向,深感唐帝国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之境地。因此人们对个人和国家都失去信心,既不争取,也不退缩,只是漠然地接受着上天关于自己命运的审判。这些心理体现到作品中就是通过兆应类故事来表现世人对命运的被动接受。
(三)对虚伪道士的讽刺与批判
唐王朝视老子为祖先,将道教奉为国教,“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立玄学博士”[8]137。唐朝帝王为巩固地位,鼓吹得道成仙、长生不老,无所不用其极。唐代帝王多好道家之术,他们将道士宣入宫中,命其炼丹制药,以求长生。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均是因服金丹而丧命。张读就生活在这种社会里。他深知自己身为官员之使命,但仅凭他一己之力难以扭转颓势,故产生的愤懑和郁结表现在小说中就变成了对虚伪道士的强烈讽刺与批判。
如《宣室志·三狐治病》中,裴君的儿子因病入膏肓,药石无效,转而求助道术,依次来了高氏子、王生以及另一位无名道士,这三位治病救人之士皆相互指责对方是狐狸,以至于“闭户相斗殴”[2]133,最后裴君“开户视之,见三狐卧地而喘,不动摇矣”[2]133。原来这三位道士均为狐狸所化,结局可谓令人啼笑皆非。作者用狐狸化道士骗人来讽刺唐末那些假道士,批判了道士故弄玄虚、欺骗世人的伎俩,揭发道术害人,警醒世人分辨真假是非,希望信道的普通人擦亮眼睛,不要被某些虚假道术欺骗。最后三只狐狸被杀的结局,意在揭示残害世人的虚假道术和虚伪道士必定受到严惩。又如《宣室志·长行子骰子怪》中叙述了一位张秀才因肄业而借居空宅时的所见,夜里相互搏斗的道士和僧徒原来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博戏中的物品——长行子所化。还如《宣室志·侯道华窃药升仙》描述了道士们对供给者侯道华的恶劣态度:“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2]112这些都表现了一些道士的虚伪行径,表达了作者对唐末道士为谋取个人利益而不顾世人性命之行为的不满。
晚唐时期,求仙问道热潮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退,反而愈演愈烈。笔者认为这些可能与当时动乱不堪的社会现状有很大关系。处于乱世的人们将精神寄托在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身上,希冀能够得道升天。这一渴望成仙的心理被一些“有心人”利用,就出现了大力鼓吹道家无所不能的现象。而这又恰好契合当时世人“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因此在当时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深受其害。作者希望以上故事能够警醒世人。
三 佛道文化在小说中的对立与融合
佛道二教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主要宗教,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用道家文化解释自己,另一方面还对道教加以攻击,道教发展起来后各朝代统治者们对待佛道二教的态度不同,两教为了发展自身在历史上出现了对立;当然二教之间也有相辅相成、相互汲取的现象。《宣室志》中对这两种现象均有所反映。
(一)佛道文化在小说中的对立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为了争夺信徒,佛教一边对道教加以利用,一边又加以诋毁。至于道教,看到佛教传入中国后信徒增多,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故与佛教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东汉开始,佛道二教就互相争位。到了唐朝,统治者定道教为国教,佛道之争更甚以往。武德四年,佛道两家针对定位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武德八年,统治者决定其位次顺序为道、儒、佛。唐高宗曾三次召集僧道进行问难,佛道争论事件多年未得结果。而唐敬宗、文宗、武宗以及宣宗朝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出现了反复。故在唐王朝,佛道两教的排序一直没有准确定论,佛道之争一直在持续。这些社会现状反映在《宣室志》中,就表现出一种佛道文化的对立。
如《宣室志·尹君》中严绶倾慕尹君得道,常去拜访他,等其升官之后便迎尹君入府,“日与同席”[2]11。严公之妹学佛而“怒其兄与道士游”[2]11,并以堇汁害尹君,尹君假死脱身。严公之妹因学佛就残害与兄长交往的道士,这一行为充分证明唐时佛道两教已经到了视同水火的地步。《宣室志·赤水神》中袁生罢官游巴川时遇到赤水神,赤水神告诉袁生他所在祠堂因数月下雨而被毁,却未得到及时修缮。故希望袁生来年调补新明县令时,能帮其重修。后袁生果为县令,却无银两为其修缮祠堂。此时袁生发现赤水神把一个老和尚的魂魄拘禁鞭打,就想让老和尚出钱修祠,并劝说赤水神放了老和尚。袁生向老和尚说明了缘由,让他修祠。老和尚应允后魂被放回,病也痊愈了,但他并未修祠,而是领着弟子去毁坏赤水神像和祠堂。赤水神便将灾祸降至袁生,后来袁生竟忧郁而死。笔者认为先不论袁生的自作自受,单论赤水神将老和尚的魂魄拘禁鞭打,而老和尚病愈之后却毁神像和祠堂,这些都表明佛道两家并不是都能和谐共处,反而有时到了相看两厌的地步。
以上便是佛道两家对立的典型例证。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受到唐高宗时佛道之争余波的影响,而后来统治者对佛道两教的不同态度,对当时社会上分别学习佛道两教的人也有很大影响,故出现了佛道对立的社会风气。张读因其自身学佛,也受到此风气的影响,故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佛道文化的相互对立。
(二)佛道文化在小说中的融合
佛道两教信仰中都提倡出世,都讲求修行,故双方有相通之处也并不能视为抄袭。佛教刚入中国时以天竺文写成,为拉拢信徒,便出现了用道家字句解释佛教经典的现象,比如“妙”字就是由《老子》中“故常‘无’,欲以观其妙”[10]转化而来。久而久之,佛道两教难免会有相似之处。唐代是一个高度包容的时代,有着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世人各自学习佛、道,兼学两者的也有之。即使到了中晚唐时期,佛道两教经历几次浮沉,在社会上也各自有着追捧者。为了扬长避短,佛道文化相互吸收与融合也就不奇怪了,这些在张读小说中也有体现。
如《宣室志·游仙都稚川》中有一和尚契虚为躲避“安史之乱”而遁入太白山。后有一道士来拜见,他告诉契虚应到仙都稚川看一看,契虚请乔君为其指路,乔君告诉他,在途中他会遇到一位樵夫当向导。随后,契虚被指引着去了稚川,拜见稚川真君,被告知道教“绝其三尸”[2]14的修炼方法。这里讲述的是道士指引和尚学习道术,这样的故事可谓是罕见。作者认为佛可以学道,道也可以学佛,二者可以相互学习,共同促进各自教派的发展。《宣室志·护佛寺地神》讲的是佛道两家互帮互助的过程,有一神者以背承受世人留在佛祠之地的唾液,“由是背有疮,渍吾肌且甚”[2]124,却毫无怨言,僧人道严听了他的遭遇就“使画工图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2]125,希望以此减轻他的痛苦。佛祠之地本不应出现道家的一切,作者不仅让它出现了,还为这些与道家相关之物的出现给予了合理的解释,使人读之毫无违和感。
以上这些都是佛道文化在《宣室志》中的融合。无论是佛可以学道,道也可以学佛,还是佛道两家相互帮助,这不仅仅是作者自身多元文化背景的反映,更是唐代社会政策开放、思想高度活跃与自由的结果,这些即使到了晚唐也依然有增无减。
佛道文化的对立与融合在小说中的体现,一方面是晚唐时期文化思想高度活跃与繁荣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对佛道两教政策不同的结果。这些对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风气习俗和政策制度都有很大的帮助。
处于社会动乱前夜的晚唐时代,宗教可以成为世人暂时麻醉精神的良药,因此在宗教的虚幻世界里,人们都寄希望于佛道两教,企图从中寻找精神的安放之地,但无论是对因果报应的虔诚信奉和对特异佛僧的深切期盼,还是对求仙访道的执着追求和对道术害人的强烈讽刺,这些都透露出一种无力扭转命运的宿命感,作者通过这些表达了晚唐社会颓势下士人明显的晦暗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