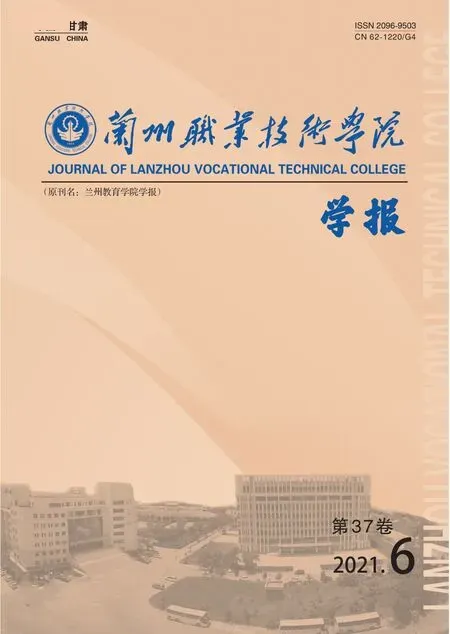从乐器琴瑟翻译看理雅各的《诗经》跨文化阐释
庞 清,唐海艳
(重庆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重庆 400074)
一、《诗经》中的“琴”“瑟”及其文化内涵
(一)《诗经》中的“琴”“瑟”
“琴瑟”这两种乐器一般以合奏的形式出现。《诗经》中一共有七首诗同时出现了“琴瑟”,他们分别是:《关雎》《定之方中》《女曰鸡鸣》《鹿鸣》《常棣》《鼓钟》《甫田》。通过分析《诗经》中琴瑟合奏的具体场合,我们可以发现琴瑟的使用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1.婚礼用乐
《关雎》诗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传统《诗经》学认为此诗为祝贺新婚之诗,认为“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对周朝贵族男女结婚典礼的描写,琴瑟合奏可视为“娶女”仪式上演奏之弦乐。[1]
2.家庭用乐
《女曰鸡鸣》诗云:“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常棣》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这些诗句都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夫妻恩爱和谐、琴瑟和鸣的美好生活景象,因此琴瑟合奏也常常蕴含着夫妻和谐美好、家庭美满幸福之意。
3.宴饮用乐
有关宴饮用乐,《鹿鸣》中的描写最为典型。诗中写道:“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诗句描绘了主人宴请嘉宾,客人们弹琴弹瑟的欢乐场景。另外,《鼓钟》也有琴瑟合奏的场景,“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可见,周朝上层贵族宴请嘉宾常用琴瑟。
4.祭祀用乐
《甫田》诗云:“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2]周王在琴瑟和鼓乐的音乐声中虔诚地举行了祭神仪式,也就是农神——田祖。这种古老的祭祀方式,生动的体现了周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也体现了琴瑟等乐器在古人与神的交流中是重要的媒介。
《诗经》中还有一处单独用“琴”的诗章,即《车舝》的“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觏尔新婚,以慰我心”。诗歌主要描写了男子在娶妻途中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如琴弦的六辔包含着诗人对婚后和谐生活的美好想象。
此外,单独用“瑟”的情况,在《诗经》出现了两次,即《山有枢》的“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和《车邻》的“既见君子,并坐鼓瑟”。这两首诗歌都描写了友人欢聚作乐的情形,从中也表达出人生易老,时光易逝,享乐也要及时的观念。[2]
(二)“琴”“瑟”的文化内涵
琴瑟古已有之。关于琴瑟的发明与创造,主要有伏羲造琴、神农造琴、黄帝作琴等说法。而无论哪种说法,都可见琴瑟的历史悠久。瑟和琴不仅仅只是两件古老的乐器,它们就像镌刻着民族文化烙印的种子,让我们能从中读出历史的厚重与积淀。
1.琴瑟与周代的祭祀文化
祭祀是先秦人们生活中一项极为庄重的内容。在中国整个漫长的农业时代中,人们一直通过祭祀来传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祖先的崇拜。作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音乐和乐器在周人的祭祀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前文提到的描写祭祀场景的诗歌《小雅·甫田》,就有琴瑟和钟鼓这样的祭祀乐器。在进入农耕时代以后,出于对于农业的重视,社稷崇拜是上古汉族先民最为重视的祭祀活动,先民通过钟鼓琴瑟这些祭祀乐器取悦神明,向神明和祖先祈求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
2.琴瑟与周代的礼乐文化
周人的“礼”与“乐”保持密切的关系。《乐记》中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建设与礼乐的兴盛关系十分密切。《定之方中》写到“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诗歌记载了狄人侵袭卫国并占据了卫国的都朝漕邑,卫文公于危亡之际,率领臣民迁于楚丘重建卫国都城。在楚丘重建宫室之后,卫文公首先在楚丘宫室之外种植了“椅桐梓漆”这些树木,这些树木的种植都是为了日后制作琴瑟。由此可见,重建国都之时,百废待兴,礼乐建设却与政治建设一样成为了首要议程,“琴瑟”作为主要的乐器也在政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诗经》同时也具有“和谐合德”的礼乐象征意义。这点我们可以从《诗经》中的很多诗歌得到论证,如《关雎》诗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男子用琴瑟弹奏乐歌巧讨姑娘的欢心。再如《女曰鸡鸣》和《常棣》之“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和“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表达了夫妻之间的相处宛如琴瑟合奏。这些诗篇中的琴瑟合奏的场景描写,蕴含着和谐合德的乐教内涵,蕴藏着诗人对夫妇关系和睦、家庭和谐的礼乐精神的积极追寻,也诠释出了周人对礼乐文化教育的深刻理解。[3]
3.琴瑟与周代的宴饮文化
琴瑟不仅出现在祭祀和礼乐文化之中,在宴饮文化中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鹿鸣》和《鼓钟》是两首典型描写宴饮场景的乐歌,琴瑟是宴请宾客时的重要乐器。宴饮诗歌不止是为了表达贵族礼节,也从一定的层面上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的繁荣。
总之,从《诗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无论是作为祭祀神明的媒介,还是代表礼乐文化的家庭日常用乐,或是在宴饮文化时的社交用乐,“琴瑟”作为主要的乐器都向我们展现了在礼乐文化制度熏陶下的周人的美好祝愿,即期待通过琴瑟合奏获得个体家庭的幸福美满,希望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二、理雅各英译本《诗经》对“琴”“瑟”的翻译
在理雅各英译本《诗经》中,一共出现了七处关于“琴瑟”的翻译,三处关于“瑟”的翻译,一处关于“琴”的翻译。以下为具体情况。
在理雅各的译文中,“琴瑟”更多时候代表的是一种乐器。他对“琴瑟”的翻译有两种,lute(中文翻译:鲁特琴)和lute,small and large(中文翻译:大的和小的鲁特琴)。在《关雎》《定之方中》《鹿鸣》这三首诗歌中,理雅各把“琴瑟”译为lutes, small and large;在《女曰鸡鸣》《常棣》《鼓钟》《甫田》这四首诗歌中,理雅各把“琴瑟”翻译为“lute”;“琴”的译文只出现了一次,即《车舝》中的“琴”翻译为lute;在《车邻》《山有枢》《鹿鸣》这三首单独出现乐器“瑟”的诗歌中,理雅各把“瑟”译为lute。[4]总体来说,理雅各对琴瑟翻译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在理雅各的译本中,“lute”是对《诗经》中的“琴”“瑟”这两种乐器最多的一种翻译。在《牛津高阶词典第9版》中“lute”的解释为鲁特琴,是一种早期的弦拨乐器,最开始只有两根弦,后面发展到6至10根弦。[5]理雅各选择了一个西方已经存在的乐器“鲁特琴”,去解释中文中存在的“琴瑟”,“琴瑟”简单地变成了西方的乐器。其次,在理雅各的译诗中,西方读者很可能把“鲁特琴”理解成一种乐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代表着琴和瑟这两种乐器,理雅各对于“琴瑟”还有一种翻译:lutes, small and large,这种译法表面上区分了琴瑟两种乐器,但其实仍是把它们混为一谈,琴与瑟的区分绝不仅仅是形状大小的区别,在中国古代,琴与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乐器。哪怕是琴瑟合奏,仍是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总之,通过汉文本《诗经》与理雅各英译本《诗经》的乐器词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理雅各的翻译切合了西方读者的理解,有利于把中华的传统典籍带到西方。但是在译文中却失去了“琴瑟”这两种古老的中国乐器身上所散发出的独特的魅力。跨文化交际中,这种情况十分常见。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这次的乐器词汇对比研究,去看待理雅各在跨文化诠释中的得失呢?
三、理雅各翻译的跨文化诠释得失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他的著作《琴道》中说到:“我们选择对应翻译词语时,首先考虑的问题并不是一件东方乐器的形状,而是应该考虑这件乐器所奏出的音乐的精神和它在自己国家文化中占据的位置。”[6]毫无疑问,鲁特琴开始是贵族阶级使用的乐器,和高雅的志趣相联系,理雅各选择用鲁特琴翻译琴瑟,也是因为鲁特琴与中国琴瑟一样,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乐器,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理雅各看来,西方的鲁特琴与中国的“琴瑟”有着相似的文化内涵,那么,他们是否真的具有相同的文化含义呢?下面,我们从以下三点来分析理雅各在关于乐器词汇的翻译中出现了哪些跨文化之误。
(一)理雅各的乐器词汇翻译使读者产生了文化错位
《诗经》中提到的乐器都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他们的出现让诗歌充满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诗中的主人公也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文化身份。[7]在理雅各的译文中,诗中主人公在面对喜欢的姑娘弹奏的乐器是鲁特琴,自然他在读者的心中也变成了西洋人的形象,诗中所发生的故事在读者的脑海中也变成了西方的场景。如果译诗不标明这些乐器词汇的具体属性,西方读者在阅读这些诗歌时,就会发生严重的文化错位。这样反而不利于外国读者深刻的理解中华文化。[8]
(二)理雅各的译文没有阐释中国诗歌内涵的意象
中国古代诗歌表意含蓄,《诗经》更是如此。[9]《诗经》中出现的意象并不是简单的意象,是被中国诗人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和特殊意义的。《诗经》中出现的“琴”和“瑟”两种文化器物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或与祭祀相关,或与礼乐相关,或与宴饮文化相关,并不是单纯指乐器[10]。但是,理雅各译文中对琴瑟的翻译都无法翻译出“琴瑟”这个名物所代表的文化意象。由于《诗经》中的乐器词汇常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读者虽然可以理解到原诗大概所要传递的意思,却并不能真正懂得去挖掘原诗中“琴瑟”这些名物所代表的真正意象,这会引起读者的文化误读。
(三)西方的鲁特琴更多的代表着一种变化之美,而中国的乐器琴瑟更多的代表着一种求同之美
鲁特琴这类古代欧洲乐器,前期更多的为贵族和宗教所使用。但发展到后期,开始从宗教音乐中脱离出来,与世俗音乐开始逐步融合变成一种全民乐器,而不再隶属于哪一个特有的阶层。而中国的琴瑟从诞生开始就充满了文人气息,琴瑟从开始的祭祀发展到之后的礼乐文化,它们是文人阶层的专属之物。[11]从鲁特琴和琴瑟不同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西方音乐总是在不断地否定自身,然后继续在这种否定中前进发展。这一特点造就了鲁特琴追求的是一种变化之美。而在充满礼乐制度的周朝,音乐与礼教互为表里,士大夫在演奏琴瑟时,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求同之美。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跨文化传播中,《诗经》中乐器词汇的翻译绝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理雅各的《诗经》译本,客观上影响了西方汉学之发展,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其中西融通的理念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理雅各的翻译并没有完全传达出中国诗歌中内涵的意象,对潜在的文化内涵也有一定的误读,这启示我们应该把中华文化因素有机融入西方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