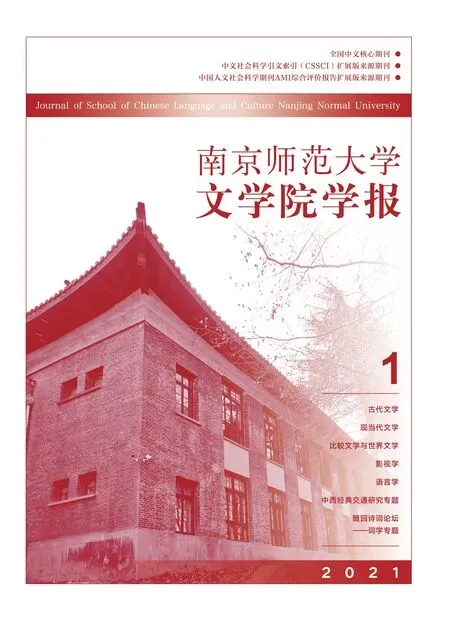民族的显影与历史的追溯
——阿来影视创作的非虚构叙事
欧阳一菲
(常州工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自小说《尘埃落定》发表以来,大家对阿来的关注日益增多,并从其作品中洞悉社会变迁、家国民族、宗教信仰以及个性人性等诸多主题意旨。同时,阿来在人物塑造、语言风格、印记符码以及叙事结构等方面的巧思匠心,也逐渐为受众所熟悉。小说《格萨尔王》中的民族民间文学力量、长篇纪实作品《瞻对》中的“非虚构”地方志式叙述、长篇小说《空山》的藏地诗意语言,以及《尘埃落定》中的“傻子”边缘视角,都饱含了作家对康巴地区的深情,同时赋予其作品冷静、理性的叙事姿态。“阿来的这种以‘边缘’‘现代化之后的后发优势’视角冷眼看世界,看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与外族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居高临下、以后视前的独到视角”[1](P106),这种叙事姿态赋予其小说历史长度、文化深度和传播广度,使小说兼具智慧的源泉和思想的启迪,成为阿来作品为人青睐的重要法门。
从2014年的电影《西藏的天空》到2019年的电影《攀登者》,阿来将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经验和风格融入影视领域,以往作品中的藏地文化追溯、自然理念探寻和非虚构叙事,又出现在电影观众的眼前,编剧阿来为他的忠实读者和新生观众带来了更多期待,同时也为中国新主流电影注入了新鲜血液。
一、中国眼:“非虚构”的跨界新尝试
电影《攀登者》由阿来编剧,再现了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故事,实现了讲述中国故事的一次整合和尝试。影片将家国情怀与个人夙愿相结合、将当代历史与现代视角相结合、将非虚构叙事与商业片结构相结合,实现了影片在精神诉求、文化价值和传播渠道等方面的交流共赢。基于“登山”这一题材,编剧阿来尝试用“非虚构”方式,在中国登山队真人故事的基础上,对主要人物、细节部件和情景场景进行适当改编,进而实现从文学到影视的一次“非虚构”探索。
(一)缝合个体与国家的“小叙事”
从2014年的《西藏的天空》到2019年的《攀登者》,这两部影片都与阿来有着天然的亲近性,“藏地”“登山”“民族”“宗教”,已然成为阿来的标签。从文学创作者到电影编剧,这些标签犹如文化烙印一般,印刻在阿来的文字中。阿来是一名登山爱好者,在六七年前他对中国登山队的老一代“攀登者”们进行过一次抢救式采访,其中包括1960年登顶成功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刘连满以及 1975 年冲顶的夏伯渝和女登山队员潘多。这些真实人物的口述素材,及其和藏地民俗宗教的亲缘性,成为阿来担任藏地题材影片编剧的重要契机。
无论是2014年的文学作品《瞻对》,还是影视作品《西藏的天空》和《攀登者》,阿来都尝试用“非虚构”方式建构故事。这种“非虚构”叙事得以“凸显个人、亲历、揭秘、故事等要素,以极具个人化视角的充满密布细节的‘小叙事’,而不是以宏大叙事映射大问题、诠释社会与人生。”[2]电影《西藏的天空》采用藏族演员,以藏语为主要台词对白语言,讲述藏族地区平凡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情感纠葛和心理诉求。阿来从故乡亲人的视角出发,试图用零距离的写实手法,描绘双主角普布和丹增迥异的人生轨迹,并将社会变迁与藏地文化演变隐藏在人物的生活轨迹中。阿来的这种“亲人视角”和“故乡叙事”在影片内外都形成了个体的多重情感交流,使得影片充满了温情与能量,同时又自然地注入了忧虑和关怀。无论是对人物命运的叙述还是宏大主题的阐述,阿来都试图避开使用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像符码,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人物个体的情感体验,并通过普布与丹增之间的朋友情谊、多哲活佛与普布的师长关系、丹增与央金之间的主仆爱情等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展开剧情叙述,将个体诉求和人物命运的讲述自然地放置于宏大叙事前面。这一尝试,成为阿来“非虚构”创作的个人化视角“小叙事”的一次探索,同时也为缝合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奠定了基础。
在《攀登者》中,阿来又一次实践了这种个人叙事对家国情怀的诉说,在宏大历史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插入了一条情感线索。影片中第一次登顶时,方五洲为了抢救深陷雪崩中的曲松林,而放弃了保护摄像机,并导致了二人长达15年“不被承认”的心理阴影。1975年,方、曲二人因再次攀登珠峰而重逢,曲松林质问方五洲:“为什么要保住我的命,而舍弃摄像机?”面对曲松林的质问和夺门而去的背影,方五洲唯有苦笑,而一旁的杰布则用藏语呼喊着“兄弟”。在曲松林看来,他们之间横亘着的是一桩事关民族荣誉的大事;在杰布眼中,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兄弟情谊;而在方五洲看来,这是一次个人选择与历史演进之间的抉择。当今社会,人们的阅读习惯逐渐发生变化,读者群体愈发需要多元化的信息刺激,单纯的宏大叙事较难满足受众的多维情感诉求。因此,这个场景设计,巧妙地将平凡个体的苦闷无奈、愤恨哀怨和真挚情谊融为一体,在个人叙事中不着痕迹地抒发了家国情怀,完成了“接地气”的中国故事的讲述。此外,影片中杰布的藏语使用,不仅使其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同时也传达了一种文化乃至文明样态之间的对话,为影片的历史叙事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
(二)缝合真事与写实的人物形象塑造
关注社会变迁、关注藏地文化、关注人的生活和命运,似乎已经成为阿来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就如阿来自己所说,“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3](P1-2)因此,他的笔下呈现出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或是疯癫、痴傻、孤苦、不幸,譬如“傻子”二少爷(《尘埃落定》)、失足少年拉加泽里(《空山》),又或是勤奋、理智、奋发,例如一生勤勤恳恳的王木匠(《河上柏影》)、独立自强的斯烱(《蘑菇圈》)。这些性格、命运迥异的人,呈现给受众不同的人生体验,同时也承载着作者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藏地文化的追溯。阿来这种塑造人的能力,很自然地被其带入到影视编剧作品当中,进而赋予了影视人物更多元的性格色彩。
影片《攀登者》由中国登山队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来,影片中人物众多且性格突出,每一个人物都有各自的符号属性和叙事使命。阿来巧妙地将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影片主题相结合,实现了人物与叙事的有机整合,用现代视角叙述“当年故事”,缝合了叙事疏离感,进而拉近了观影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使人物更具典型性、真实性和艺术性,赋予人物民族属性和家国情怀。影片中围绕“攀登精神”塑造了一批性格各异的人物:具有耐力和实力的登山队长方五洲(原型为王富洲);对爱情忠贞、对事业尽心的气象学家徐缨;勇于奉献却又执拗冲动的曲松林(原型为屈银华);阳光乐观却又有些粗心马虎的李国梁(原型为邬宗岳);果断勇敢且具有自我超越精神的杨光(原型为夏伯渝);美丽善良又果敢机灵的女性攀登者黑珍珠(原型为潘多);还有天真单纯又乐观坚韧的藏族登山者杰布(原型为贡布)。这些人物是有各自性格优势的攀登者,同时也是有着弱点的普通人,譬如性格执拗甚至有些偏激的曲松林。因自己第一次登山遇险时方五洲的“错误”选择,他怨恨了挚友方五洲15年,直到第二次登山时,眼见着队友李国梁因保护相机而牺牲,他才真正明白方五洲15年前选择的意义,他抱着李国梁遗体痛哭时,既是在追忆不舍这位年轻的队友,更是在痛诉自己15年来的冷漠和自私。编剧通过这一个个鲜活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保证情节演进真实性的基础上,又赋予影片戏剧张力,同时,照应了“攀登者”共同的精神追求——坚毅勇敢、执着登攀、誓登高峰。当这种精神共性反射到个体身上时,又会散发出炽热的情感力量。电影中的英雄们各自实践着具有个性化色彩的人物属性,英雄群像也更像一个组群集合,他们共同印证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普世价值,更彰显了艺术的包容性、创造性和无限张力、魅力。
(三)缝合真情与实感的弹性细节设置
《攀登者》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一段往事,而影片受众的生活经历则与那段历史相隔较远。影片的叙事在过往历史视野与当下审美期待之间展开,这便需要编剧对历史史实做出一定戏剧化改编,进而缝合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间隙。“在把真实历史原型转化为当代观众爱看的影像故事时,需要妥善掌握‘度’:一方面‘大事不虚’,在总体上尊重史实;一方面‘小事不拘’,在若干局部或细节上不拘一格地虚构或想象。”[4]如何找寻史料史实和细节改编之间的平衡点,成为影片创作的一个难点。编剧阿来聚焦个人叙事,关注个人选择的创作特质,成为解决真实事件与戏剧改编之间审美平衡的重要契机。1960年,随队记者郭超人在新华社发表长篇通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其中写道:“5月25日清晨北京时间4点20分,三位登山英雄经受了重重困难的考验,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的顶峰,为中国体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由于当时天黑,不能拍照,他们在顶峰上停留了大约一刻钟,就决定返回征途。他们看到自己攀登顶峰时在雪上留下的脚印,二十五岁的四川林业工人屈银华立即把它摄入了电影镜头——这将是纪录这次伟大登山事迹的影片中,最宝贵的画面之一。”这是有关1960年登山的真实记录。在影片中,编剧加入了遭遇雪崩的情节和摄影机这一细节,并且设置了方五洲放弃相机、抢救队友的经典段落。“摄影机”这个叙事符号是记录史实的有力物件,更是传承攀登者精神的重要纽带。在影片中,不同的队员面对挽救生命还是抢救摄影机的抉择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摄影机”也因此成为历史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的一条情感通道,亦是我们一直在找寻的平衡点。摄影机第一次出现是在1960年的攀登行动中,它的“牺牲”成为横亘在方五洲与曲松林之间的一座“山”,摄影机此时已经被赋予了叙事使命,它是“个人对时代的记录以及时代对个人的记录”[5](P32)。1975年,登山队再次向珠峰进军,当方五洲因伤病不能完成任务时,青年摄影师李国梁主动请战,此时,“摄影机”的叙事作用再次显现,这位没有登山经验的登山队长,此刻已经和“摄影机”一起肩负起了符号叙事的使命。李国梁在坠落的前一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保护摄影机,他与“摄影机”一起再次尝试了方五洲当年的选择题,也一起给予曲松林一个迟到的答案。“摄影机”串联了突击队长徐浩天、方五洲和李国梁“誓攀高峰”的执着信念和历史使命,同时也给观众留下了一道选择题——你会选择什么?
对于人性的描摹刻画,《西藏的天空》中也使用了一些细节。普布在幼年时期,因受刑而在脑中留下了一个“血块”,这个血块让他饱受头痛的折磨。在遇到解放军杨医生之前,他一直将“血块”等同于果报和惩戒。在这里,“血块”具有细节隐喻的作用,它暗示着宗教信仰对人性、思想的压迫。后来,在解放军杨医生(杨医生隐喻着现代文明,也是思想解放的主要途径)的帮助下,血块被取出,预示着长期存在于普布脑海中的桎梏被拆除,普布实现了自我解放和救赎。
二、中国梯:中国精神的延续和传承
(一)个体叙事下的家国情怀书写
在影片《攀登者》的开头,有这样一段文字:“1960 年,国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珠穆朗玛峰,归属的边界谈判正在关键时刻/邻国登山队筹划从南坡抢登珠峰”。影片开头的字幕,直观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国际局势,同时也明确了中国登山队肩负的使命和职责,冲顶珠峰也因此更具政治意味。影片通过非虚构的创作手法,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关于国家形象的史实,用影像的方式展现,这一方式方法既能够赋予国家荣誉和历史记忆以具象化的呈现,同时,在影像建构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个人认知、集体意识和家国情怀的凝聚和升华。影片将个体意旨寓于国家意志之中,赋予个人理想、愿景和情感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对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叙述和延展,都与家国情怀紧密相连,使“国家”与“个人”形成包容、交织和反刍的关联。
这种别样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的书写方式,是阿来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特色,也是饱含着阿来独特异域视角下的家国情怀,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我们的文学不可能不写英雄,我们的文学不可能没有国家意识,只是说我们一定要遵从文学本身的、艺术本身的规律来写,而且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写。”[6]当我们看到方五洲面对曲松林离开背影的落寞无奈神情,看到李国梁牺牲时割断绳索的义无反顾,看到徐缨为爱人、为祖国舍身忘我的执着,我们便能够从这些个体身上感受到他们无私、果敢和坚毅的爱国情怀。这些凡人英雄所散发的个人魅力,让观众更容易理解、更容易相信、也更容易产生共鸣,攀登精神也因此更为深刻与真实,进而构建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
(二)艺术修辞语境下的宏大史诗叙事
阿来善于将艺术修辞语境与史诗叙事相结合,通过意象符码、人物性格和历史事件,传递爱国、无私、奉献和团结等抽象的民族精神。正如黑格尔所说,“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必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联系上,必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7](P107)对于史诗的叙事,或是具有深厚的文化溯源,或是具有特定的历史规律,在阿来编剧的两部作品中,艺术、历史、文化与民族在碰撞中实现了交融、互通。
“叙事的目的就在于把一个社群中每个具体的个人故事组织起来,让每个具体的人和存在都具有这个社群的意义,在这个社群中,任何单个的事件,都事出有因,都是这个抽象的、理性的社群的感性体现(黑格尔)。”[8](P9)主旋律电影《攀登者》无疑承载着家国情怀的叙事诉求与史诗叙事的主旨表达的使命。阿来将文学创作中的“发愿”(1)佛教用语,谓普度众生的广大愿心。后亦泛指许下愿心。在藏族文化中,作者在写书的时候会在前面写一首诗,表达作者对这本书所寄托的愿景。运用到影片当中,赋予史诗叙事多样性和生动性。影片伊始是一只蓑羽鹤在天空飞翔的镜头,这种具有牺牲精神和坚韧毅力的鸟类便被赋予隐喻作用,成为影片中的叙事符号,同时也奠定了影片励志又悲壮的史诗基调。另一个叙事符号——珠穆朗玛峰,更是作为渲染影片史诗基调的关键元素,高频出现在影片台词中。“我们自己的山,要自己登上去”,这是攀登珠峰的意义所在;“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登上自己的峰顶”,这是攀登珠峰的目的所在;“要测量珠峰准确的高度,中国的高度”,这是攀登珠峰的职责所在。这些意象符码的使用,分解又重构了史诗叙事的宏大属性,使影片中表达的家国情怀“高能震人心,低能接地气”。
(三)情感认同下的中华美学精神建构
阿来曾经说过,他在作品中试图展现“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9],他关注的不仅仅是民族与文化,更多的是隐藏于文化中的理念、观念和信念,因此,在这位具有双重文化视角的作家作品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独特地域、民族文化背后的普世文化,将西藏文化、传统习俗放置在汉文化和现代文化场域之中,用具有现代性的眼光去回溯、反思、填写不同文化之间的沟壑,进而实现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
影片《西藏的天空》呈现出三种话语形式:“一种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是现代性的、启蒙的、个性解放的或关于传统与现代文明碰撞的;还有一种是挖掘人性自身的,表现人性的觉醒和对人性的追问。”[10]影片在表现启蒙性和现代性时,巧妙地用人物之间启蒙思想的传播进行言说,例如杨军医便是一个传播平等启蒙意识的现代性符号。影片当中有中西思想的碰撞,有现代与传统思想的交织,对于这种碰撞和交织,主创采用了一种包容的叙事姿态,展现其冲突,同时又赋予其缓冲的空间。因为接受了西方教育,丹增在文化、宗教和理念等方面与父亲、活佛等产生了分歧,甚至在自己的去留问题上也开始疑惑。在这个问题上,主创的构思也非常精巧,丹增的离开是因为受伤而导致的被动行为,之后他的回归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文化认同、文化回归的一个标识,这种回归和认同也被赋予了主动性和自觉性。创作者认为,西藏文化不应该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反例存在、延续,而应该是一种文化的同构和认同,甚至是情感的共鸣。这种观点渗透在阿来的诸多作品中,《攀登者》亦不例外。
影片《攀登者》围绕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展开探讨,进而彰显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意蕴。登山运动员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完成了国家赋予的使命,诠释了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联,突显了爱国主义精神,这便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体现。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他们面对雪崩、苦寒和烈风,也看到了珠峰的巍峨雄壮,影片在这里借物抒情,珠峰之高隐喻了攀登者们的境界至高,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体现。个体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穿梭交错,实现了多种关系的串联,同时拉近了观众与登山者之间的情感关系。珠峰的雄伟、英雄的伟岸、中国精神的坚韧以及中国力量的博大精深,都在诉说着“崇高美”这一重要的中华美学精神。借助情感认同实现文化共通,似乎已经成为阿来习惯又擅长的叙事手法,也成为观众对阿来的一种期待。
三、中国故事:新主流电影的突围与重生
伴随着融媒时代到来,人们对于信息创造、接收和反馈的途径都愈发多元化,这种传播途径的变革为电影发展带来了机遇。数字技术的使用在电影制作中频现,“新主流电影”亦尝试吸收、使用曾经属于艺术电影“秘诀”。在“国庆档”呈现的《攀登者》,将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进行了巧妙的组合,完成了一次跨域对话,影片在民族文化、思想意蕴,以及类型化元素的言说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既传递了新主流电影的共性特征,又彰显了影片个性化的处理手段,为今后同类型影片的创作提供了参照和依据。
2010年以来,随着电影市场发展的逐渐稳定和产业链的日益成熟,新主流电影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土壤,其中,类型化的叙事模式成为此类影片发展成型、成熟的重要助推,这也是主旋律电影在弘扬主流价值观方面做出的一次有力探索和转变。影片《攀登者》将灾难片、体育片和剧情片提炼、整合并重构,成为影片抢占商业市场的有力武器。《攀登者》可以说是国产“重工业”(2)为了争抢时间进度,《攀登者》的特效制作早在影片正式启动拍摄之前就已经率先启动,这种操作流程,保证了影片能够在计划范围内制作完成,并不影响影片的排期上映。这也成为影片的亮点之一。电影的代表作,影片在特效制作、后期制作和类型叙事等方面的运化能力,都可见一斑。影片中对极限生存环境的再现,精准、逼真又自然。在零下20摄氏度的恶劣环境中攀爬而导致脚掌冻伤发紫的情景,营地帐篷被十级飓风顷刻拔起的瞬间,以及雪崩、风暴等恶劣自然气象的袭击,通过后期特效的处理,显得真实又具有冲击力。同时,这些场景的存在,也建构了影片类型叙事的基本图谱。相比于这些极端恶劣的自然现象,人类命运则更显渺小。灾难片中的“不可抗力”和片中人类的艰苦卓绝两相组合,便为灾难中的人性、人情辟出了一抹关怀和情怀。《攀登者》中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形象,人物性格的张力在类型化叙事和快节奏的情节发展中得到了突显,更具感染力。影片遵循电影市场的运行规律,将类型叙事元素与艺术创作手法相结合,潜移默化中向观众诠释了国民英雄在不可抗力和大是大非面前的执着坚守和奉献精神。同时,影片借助体育片的励志情节、灾难片的自然理念,在新类型架构下,实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置换,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人类更多了一份坚守、奉献与超越,这既是新主流电影在类型创作上的突围,同时也是其在主题精神上的一次升华。
除去对主流价值情感的升华,影片也注重情感的包容性传递。将主流精神缝合进影片情节的针脚中,以细腻自然的艺术表现手法呈现影片主题,是新主流电影的叙事诉求。意象符号,便是传递宏大精神的微小注脚。《攀登者》中高频出现的摄影机、三叶虫化石和冰镐,寓意着使命、爱情和生命;皑皑雪山等场景,则营造出一种冷峻、崇高的巍峨气势。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蒙太奇剪辑手法的使用,影片将观众带入到类型电影的感召模式当中,形成了一个“浓与淡”“情与理”“大与小”相结合的情感传递模式。“情”“景”“物”的交融,缝合了类型片与主旋律电影之间的文化裂隙。
写出人物的深度、时代的高度,是阿来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定位,这种定位在影片《攀登者》中依然有迹可循。当片中人物高声呐喊“登上去,找回我自己”时,观众会不由自主的与登山队员们齐呼“我们都是攀登者”,这便是“共同体美学”的建立,主创与受众在精神、思想和情感等方面都实现了共情、共鸣。这种有深度、有高度、更有温度的艺术表达,注重创作者与受众情感的共鸣、注重国家情怀与个人情怀的统一、注重年代情绪与社会情绪的交流,赋予了新主流电影创作的新启示。
如何找寻“家国叙事”与“个人叙事”之间的平衡点,《攀登者》似乎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主旋律与类型化、非虚构的融合,既满足了家国叙事中更深层次的精神表达,同时又赋予类型元素、商业化视听特效发展空间,加之细腻、接地气的情感渗入和凡人英雄群像的塑造,使得主旋律意旨的表达更加自然、真切,更具感染力。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现实主义的再现和商业命脉的把控,都在《攀登者》身上寻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