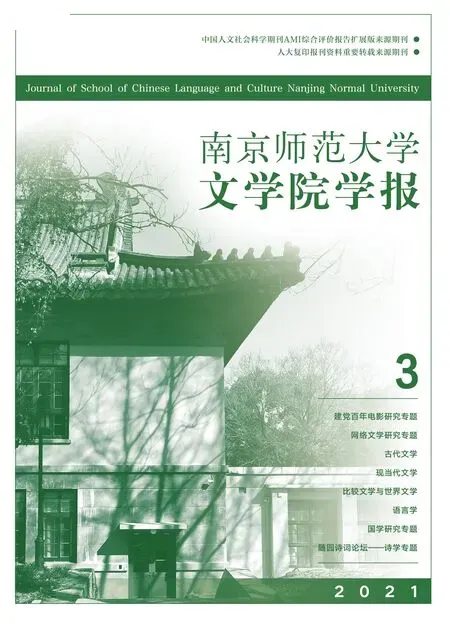“观棋烂柯”:视野的变换与意义的衍生
韩 斐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烂柯”故事产生于两晋时期,而“观仙对弈——斧柯烂尽”这一基本情节架构在唐代基本定型,并在众多异文中成为主流,实现了宗教逻辑到文学逻辑的转化。[1](P205)这个故事在接受视野的变换中不断衍生出新的意义,重新合理化,主要是通过“烂柯”作为文学典故和文学题材被反复使用和加工而实现的。本文就“观棋烂柯”故事在古代诗文中的文学接受情况略作梳理和阐述,以探求其丰富的文学意蕴是在什么样的接受视野中产生的,又融入了怎样的文学传统和时代精神。
“烂柯”故事主要通过樵夫王质观棋或服食后斧柄腐烂(即生命的延长),表现出类似“天上一天,地下一年”的宗教超凡时间尺度。这是生命永恒在道教中的一种特别形式,道教思想认为“人应当超越世俗的时间系统而进入道教想象中的神仙的时间系统,……如果他能得到神鬼的助佑,在道士的冥助幽赞下,人可以在另一时间系统中获得更长的生命”[2](P370),此为烂柯故事产生之初的意蕴。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故事情节分解为时间、空间二端。从时间上来看,有神仙的时间系统和世俗的时间系统;从空间上看,有仙境的空间(或围棋游戏空间)与世俗的空间(或棋外空间)。文学接受所能提供的理解与阐释的多种可能性,都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在烂柯故事的接受史中,可以发现原本在故事中并行不悖的两个时间系统逐渐受到质疑而被改造,原本彼此隔绝的两个空间逐渐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对应的象征关系。在视野的变换中,我们对烂柯故事中时间和空间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从而衍生出世幻浮促、世事如棋等等象征意义。随着固定象征意义形成,“烂柯”也就逐渐符号化,进而被纳入“隐逸”的艺术母题与主题谱系之中,作为一个因子与其他故事发生联系。
一、道教语境下的仙境想象
由于故事在道教语境下产生,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烂柯故事还在表现仙药的神奇作用,所以最初烂柯典故的文学书写主要强调时间上的长生久视,对山中灵境的向往构成了烂柯最基本的内涵。
从南朝到唐代,烂柯被普遍地视为神仙故事,王质的游仙经历仍然是诗人们关注的重点,烂柯寄寓着人们对于仙境的想象,如大历(766-779)前后,刘迥、李幼卿、谢勮、羊滔、李深、薛戎等6人的《游烂柯山·仙人棋》,就强调其仙境的意义。另外,在很多唐代诗歌中,把道士或隐者游历隐居的经历比作烂柯。王质观棋这种脱离现实世界的方式使唐人把隐居经历与烂柯联系了起来,山中围棋也就成为隐者山林生活的标志,如崔涂《樵者》“莫看棋终局,溪风晚待归”[3](卷六七九),许浑《送宋处士归山》“世间甲子须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3](卷五三八)。可以看出,烂柯典故不仅给这些诗歌带来一种虚无缥缈的神仙意境,而且在表现出世意境时,空间的隔绝是建立在时间系统不同的基础上的,所以此时对于烂柯故事的书写集中于对道教超凡时间尺度的表现上。
唐人也用烂柯典故来表现生命的短暂,比如元稹《春分日投简阳明洞天作》“菌生悲局促,柯烂觉须臾”[3](卷四二三),崔致远《下元斋词》“听烂柯翁之说,则倍惜光阴”[4](P502),这其实也是对故事中道教时间观的一种解读方式。明确现实时间的短暂以后,宋人就由此质疑王质是否突破了神仙与人世两种空间的界限,如晏殊《棋盘石》“干雹声中闻子响,不知还许采樵观”[5](P1963),徐积《棋仙》“一局闲棋犹未了,坐中老却采樵人”[5](P7554),以此来表达山中仙境与世隔绝。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把“烂柯”放在道教的语境中表达长生久视,宗教超凡时间尺度都是烂柯典故的基本内涵。最初对于烂柯故事的咏写都围绕时间展开,建立在承认这种奇幻的时间观的基础上。
二、时间观的置换与生命体验
中唐出现了两个对于“烂柯”的意蕴非常重要的作品,一是孟郊的《烂柯石》,一是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孟郊《烂柯石》:
仙界一日内,人间千岁穷。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唯余石桥在,犹自凌丹虹。[3](卷三八〇)
从时间变化这一故事情节出发,点出了“万物皆为空”,以仙棋的短暂消解了现世时间和人生社会的意义。这种新的阐释来源于佛教对烂柯故事的解读。《华严经》卷六四讲到:“时毗目仙人即伸右手摩善财顶,执善财手,即时善财自见其身往十方十佛刹微尘数世界中”,经历了很长时间“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劫”[6](P1136)。“劫”是一种极长的时间单位。即善财童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前往十方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经历了无法计数的劫的时间。中唐时期释澄观《华严大疏钞》引入了烂柯故事解读这种佛教时间观念:“是以善财一生能办多劫之行者……何得一生不经多劫,仙人之力长短自在故。如世王质遇仙之棋,才看斧柯烂已经三岁,尚谓食顷。既能以长为短,亦能以短为长。”[7](卷八六)毗目仙人可以做到“念劫圆融”,时间“长短自在”,无量劫可以现于一念,也就消解了时间的意义,这显然为烂柯故事在时间层面上注入了一种新的理解方式。须知,时间意义的瓦解,也就把整个宇宙、存在、人生、社会都归为幻妄,因为这些可能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把佛教时间观纳入烂柯故事这种写作思路在宋人手里得到更大的发挥。如苏轼《停云》:
对奕未终,摧然斧柯。再游兰亭,默数永和。梦幻去来,谁少谁多。弹指太息,浮云几何。[5](P9548)
他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看待人生和万事万物,而是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这个世界的。“观棋烂柯”典故的特殊性在于,烂柯人超越时间的经历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因为他超越生死,没有变老,所以更可以“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这恰恰引发了古人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既有浮世盛衰无常、沧海桑田须臾改换的深沉感叹,又充分展现出个人身处宇宙中的迷惘、空漠、幻灭之思。
取消现世的意义,也为故事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撇开故事本身而提取王质归家后的情感。名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到乡翻似烂柯人”,截取了烂柯人归家后生疏而怅惘的心情,把樵夫王质的生命体验扩大,消解了原本的游仙意义,使得烂柯故事拥有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情感意蕴。这种因生命思考而引起的怀疑人生意义、无所希翼、无所寄托的伤感情绪,在文学对“烂柯”故事前赴后继的使用、加工和转述中不断强化,以至这样一种无常之恸几乎伴随着“烂柯”文学书写的始终。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烂柯故事原本的一个核心思路——道教时间观被悄悄地置换为佛家的一种哲理化解读。中晚唐以后,文学家也就艺术性地转换了对“烂柯”的表现重点,不同于道教语境下对于现实的超越与漠视,转而表现现实人生中“世幻浮促”的感受。南宋陈与义《夜雨》总结棋局的象征意义“棋局可观浮世理”[5](P19473),到了明代,陆树声《清暑笔谈》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观点,“棋罢局而人换世,黄粱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清世累,营营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近达生之旨”[8](P9)。“世幻浮促”,“幻”即虚幻,人生如梦幻泡影;“浮”,老庄学派认为,人生在世虚浮无定,所以称人生为浮生;“促”,即生命的短暂。在中唐以后烂柯故事的接受中,人生虚幻无定成为它的主要内涵。随着故事中神秘因素的逐渐消解,在两宋时期,唐人所开掘的新思路得到了进一步发挥。观棋烂柯故事本身所带有的一种如梦似幻的美感特质在宋诗中也被发掘出来,这正是一种“幻”、“浮”、“促”的美感。宋诗名篇欧阳修《梦中作》: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5](P3691)
这首诗带有梦的非理性的色彩,四句诗分别描写了四种不同的意境,而这四种意境中人生恍惚迷离的感觉和情随事迁的无奈情绪又是相通的。“棋罢不知人换世”,以棋写梦,只抽取烂柯故事的梦幻、迷惘与伤感,来写梦境的葱茏迷离。黄庭坚《记梦》也同欧阳修的诗歌一样,以众多意象描述了梦境,其中的“烂柯”意象显然也是抽取了它的美感,写实的成分很有限。烂柯典故在此已经彻底抽象化,从故事本身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审美符号。
当道教时间观被置换以后,“观棋烂柯”故事被哲理化了。佛教的思维方式是通过烂柯故事中两个时间系统地相互转换,来说明空间的虚幻。从而为“烂柯”赋予了空幻的哲理化生命体验,而且凝结了无常之恸的情感意蕴和如梦似幻的美感特质。
三、理性的反思与游戏书写
南宋士人开始对道教“天上一天,地下一年”的时间观予以彻底的辨证与否定。烂柯故事最初被收录在《东阳记》等地理类著作中,在中古时期的知识体系中当属于博物知识。而宋人将博物、格物作为体察“道”的工具与手段,将宗教的虚幻世界心性哲理化,用一种对待外物相对理性的态度重新对烂柯故事进行审视。事实上,这是整个宋代知识世界的转变,“逐步由方域、奇幻与现实世界并存的多重知识图景,内转为历史、现实经验世界的单重图景,由鲜活生动的感受想象,转化为人文常识理性的辨析反思”[9](P185)。例如洪咨夔诗题中“见壁间虞仲易《观棋诗》有‘天上人间元一气,如何顷刻烂樵柯’”[10](P78),可以看出虞刚简诗以常理对神仙时间观念提出了质疑,天上人间不可能产生两套时间系统。又如李季可《松窗百说》“仙家”:
《世说》有误到仙家者,时不顷刻,及反乡闾,人已死亡,世事改易。至于观棋,局未云终,斧柯已烂,觅路还家,海变桑田。人间所以贵慕神仙者,以其快乐无恼,长生久视耳!今斯须便过百年,朝夕已经千载,不知自天地开判以来,终得几局棋,凡过几旦暮,大较不至数岁事,亦何谓寿考邪?俚俗相戏,骂云:“愿你活一百二十岁,则教一日过了。”正好相喻,可为大笑。[11](P14)
他提出了如果神仙时间观成立的话,那么“斯须便过百年”,神仙所体会到的时间仅仅是“斯须”而已,反而不能称为长生久视了。这种对于神仙时间观的彻底否定昭示着方术灵异的落幕和日常经验的回归,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理学家所追求的“理”。王十朋认为“仙家不寿考”条“大有益于风教”[11](P43),说明这种看法符合当时普遍的价值观。到明代出现了更多否定神仙长生久视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理性的声音在后世的延续。比如张以宁《衢州咏烂柯山効宋体》:
人说仙家日月迟,仙家日月转堪悲。谁将百岁人间乐,只换山中一局棋。[12](P90)
很多作品都是从质疑神仙时间观来立意的。又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九“仙亦不久”,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七一,顾起元《说略》卷二四“谐志”,这方面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了。
在神仙时间观本身崩塌的同时,文学创作也就试图从新的方向寻求故事的合理化。比如试图挖掘观棋时不为外界所扰的游戏的迷狂,描写时间感的丧失,把写作的重心转到游戏本身,如刘敞《围棋调邻几》“樵柯烂尽忘归时”[5](P5704),韩信同《棋盘仙迹》“贪看柯烂不知时”[5](P44645),顾逢《王质观棋》“弈边忘日月,况复遇神仙”[5](P40014)等等。尽管如此,烂柯故事从时间上继续发挥想象仍然受到了限制。从仙境的空间(或围棋游戏空间)与世俗的空间(或棋外空间)的关系来阐释故事的作品也就随之增多。比如把棋局和人间胜负、尘世兴亡对照起来,在王质观棋的过程中,世事如棋局争斗,他与仙人观览了人间胜负、古今兴亡,突出仙境对人间的超越。化用烂柯典故表达“世事如棋”的意味在宋诗中非常多见,把世事比喻为棋成为一种常用的诗歌语言。如:
局上闲争战,人间任是非。空教采樵客,柯烂不知归。(朱熹《题烂柯山》)[13](P568)
偶尔观棋忽烂柯,岂知胜负是如何。归来笑问人间事,恰是人间胜负多。(陈岩《斧柯岭》)[5](P43281)
都是从世事如棋的意义上来处理这个题材的。原本故事中围棋游戏的空间在文学创作中被展开,并且与现实对应,成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变化的隐喻。
由于宋人在围棋的文学书写中对于“忘机”的强调,所以在烂柯故事的诠释中,不仅要超脱于人间胜负,更要实现对神仙游戏胜负的超越。至此,原本烂柯故事的叙事空间被分离为三个层次:一是现实生活的空间,故事本就选取了斧柄来象征这个空间;二是仙境的空间,包括仙人对弈的棋局空间;三是王质的心理空间。当王质全身心投入游戏的时候,心理空间和仙境的空间是融合的;而有时宋人会刻意搁置对于王质长生、神仙时间观的解释,将王质的心理空间与仙境空间分离开来。例如:
山中一枰棋,尘世底事无。若复计胜负,与彼亦何殊。(陆游《郭氏山林十六咏·小烂柯》)[5](P25740)
玉行敲断欲生尘,翻手那知局面新。到了不妨饶一着,旁观自有识机人。(方岳《次韵宋尚书山居十五咏·烂柯台》)[14](P175)
秉烛随者明,奕棋观者精。观者未必高于奕,只是不与黑白同死生。天上神仙何所争,亦复于此未忘情。樵夫柯烂忽猛省,却与棋仙作机警。……(许及之《观奕篇》)[5](P28328)
不仅因观棋而摆脱了尘世的束缚,而且旁观者的身份使他比在游戏中忘情的神仙更加清醒,把世事、棋局、神仙都归为无意义。可以从“小烂柯”“烂柯台”等名目的诗歌中看出,这也是后世文人园林中烂柯造景的主要寓意。世事如棋,而王质作为旁观者,成为诗人们寄托理想的对象,完成了对于世事与棋局中争斗的超越,从而再一次对原本的烂柯故事作出了全面颠覆的解读。
明初朱善《题观奕图序》中,出现了更加理性化的批评:
余览晋樵者观奕柯烂事,好事者复画图摹刻以传于世,心窃疑焉。夫亘古此一天地而谓洞中别有天,信乎?亘古此一日月而谓山中别有日月,信乎?神仙者,流盗窥玄命之秘,偃仰屈伸,呼吸吞吐,以增益其寿命,理或有之,而欲移晷换刻,返轮迂辔,以岁为日,以世为年,有是理哉?……烂柯之说,盖亦好异者之寓言耳。而昧者不知,遂从而实之,只见其察理之不精,而听言之不审也。吾意创是说者,特借弈棋之胜负以喻一时之战争耳。何以言之?晋氏自武帝之后,骨肉之残贼,胡羯之践蹂,生民之焚溺,极矣。……当是时,士失其学,农失其畊,工商举失其业。譬之樵者之观弈,不惟斧烂其柯,比其还家,则身且无归矣。岂不可闷之甚乎。[15](P185)
首先否定了烂柯故事的时间观,然后强调它的“寓言”性质,从世事如棋的角度生发出新的解读,认为弈棋是现实中战争的象征,联系故事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论述。以王质观棋象征西晋人民的战争经历,从而把原本具有神秘色彩的、抽象的烂柯故事历史化、写实化了。
文人的游历也有助于理性的解读。元明清时期烂柯文学数量的增加与这一时期的游历风气有所关联。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文人游历的规模、地域范围都是空前的。文人游记的激增极大地促进了人文地理的发展,不仅为我们客观记录了各个时期各地的烂柯景观以及相关传说的情况,而且明代文人创作游记有游历、考察的性质[16](P289),给烂柯的解读带来了一种理性的视角,例如田艺蘅《烂柯游览纪行》:
……即王质遇仙处。……石梁上覆好事者为塑看奕图,宛有生气。时闻山禽剥啄,樵斧丁丁,犹疑落子声。所惜尘缘未断,不能睥睨半局耳。凌风登石桥,绝顶羽士指北望隐隐者,西安城也。村墅星罗俨如布子,而峰岫云绕东去,又如斜飞联络,势不可断。谷口九折,如双关防入而奔泉激石,又如冲坚击虚汹莫能御。呜呼!此山川自然之奕也。若夫以方舆为枰,江河为界,泰华衡为子,四裔为边,中原为腹,秦楚燕越为布位,常山蛇首尾为势,争胜负于一着间,则又天下之大奕矣。古今敌手雌雄几较哉。[17](P33)
俯瞰西安城(今浙江衢州)而联想到烂柯故事,进而将眼前所见之景比喻成“山川自然之弈”,再进一步把整个中国喻为棋盘,谓之“天下之大弈”。在这篇游记中,仙棋与世事变幻的联系更加具体,包括枰、界、子、边、腹、势等喻体都有了相对应的本体,我们能进一步联想到王质所观“山川自然之弈”、“天下之大弈”局势变幻的情形,这也是一种烂柯故事历史化的表现。
可以发现,烂柯故事逐渐集中在围棋的书写上,棋局可观浮世理、世事如棋,甚至连围棋的游戏心理都得到表现,故事中棋局文学意蕴的发掘至此已经非常深入。这显然是故事的时间观逐渐颠覆、在时间角度难以做出进一步发挥之后的一种文学创作的自然转向。在理性反思的历史过程中,这种转向不仅仅使得世事如棋与旁观者清的意蕴得到充分发挥,而且造就了“观棋烂柯”的一种历史化解读方式。
四、“题画时代”烂柯书写的符号化与世俗化
“烂柯”的核心情节在于观棋,我们在唐宋时代看到的“烂柯”题材作品,大抵是对烂柯山或石棋盘景观的书写,是基于自然景观审美的;而后随着文人园林的发展,逐渐出现对于园林造景中所谓“小烂柯”的描绘;从宋末以后,开始出现题弈棋图诗。虽然都是烂柯题材,但是作者的审美对象发生了变化,烂柯的书写开始进入一个“题画时代”。在唐代,衢州刺史游烂柯山寻王质观棋所,写下作品刻于碑上,才得以流传;到了近古“题画时代”,不仅登临烂柯山逐渐变得容易了,而且游览的门槛已经降低到所谓的“卧游”,只要拥有一幅弈棋图,任何人都可以吟咏烂柯仙境。王演畴《题烂柯山图》就描写了题画创作的情境:“五岳年来但卧游,向平有债未曾酬。客持一幅烂柯景,叩户邀予翰墨留。生绡写就笔遒劲,展轴知为载文进。恍然置我三衢山,便乏诗才动诗兴。”[18](卷七)文学接受方式的变化,为吟咏烂柯提供了契机,大大激发了文人对烂柯故事进行言说和议论的兴趣,过去烂柯故事所凝结的意蕴被进一步强化。在此基础之上,“烂柯”的文学接受也出现一些新时代的特点。
(一)围棋的符号化
围棋题材是唐代就已出现的重要绘画题材。在元明清时期题画诗对于围棋题材画作的咏写呈现出一种主题趋同的倾向,作家倾向于把主题不明显的弈棋图解读为仙弈,从而与烂柯发生联系。故而虽然弈棋图内容并不一定是观棋烂柯,但题弈棋图诗却成为烂柯故事的一种全新的文学接受方式。
在题画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围绕围棋所形成的母题系统:围棋、樵夫、烂柯、橘中戏、商山四皓、松、山林……这些元素全部混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叙事的混融与整合,无论是否与烂柯故事相关,他们都共享了在长期文学书写中所积累的烂柯故事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意蕴。例如元代成廷珪《题刘商观弈图》:
……松荫对弈者谁子,岂非甪里园公乎?云绡雾毅古冠佩,童颜雪顶沧溟枯。野樵旁立太痴绝,归来始觉仙凡殊。斧柯竟化作尘土,世间甲子真须臾。……[19](P27)
表现出明显的橘中戏与烂柯故事的混合,对弈仙人为商山四老,观弈者为樵夫,王冕《刘商观奕图石刻本》、许有壬《题钱舜举三仙奕棋图·其二》、张翥《刘商观棋图》、顾瑛《题刘商观弈图》、贝琼《题刘商观奕图·其二》均有这种倾向。事实上,无论绘画题材是“高士弈棋”“三教弈棋”“蓬莱仙弈”“仙姑对弈”,题画诗都会引入烂柯故事,这种情况在非题画的作品中也存在,尤其是把“仙棋一局世上千年”的时间观念混融在橘中戏的故事中。如明代周拱辰《小游仙》:
橘中输却熊盈袜,又向松间赌玉箫。花影覆棋阴未转,误人柯烂不成樵。[20](P460)
没有图画依托,而把两个故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重新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围绕棋产生的故事彼此之间的混融,说明围棋的符号意义不仅止于绘画领域,而是向着其他艺术领域拓展。
元明两代的题画诗还致力于引入烂柯故事,构建一个“樵夫”的隐士形象,如元代陈樵《吕氏樵隐图》、岑安卿《题黄中立樵云卷》等。观棋烂柯成为“樵夫”的经历之一,以突出樵夫出世的形象。此类画作与题画诗的立意,延续了烂柯文学书写中樵夫旁观者清及对世事的超越,观棋被认为是“樵隐”。赫云在对中国古代艺术史中“隐逸”的母题谱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山水——渔樵的一套谱系,并重点对“渔父”母题谱系进行过分析[21](P128)。而“樵夫”母题就属于这个大的艺术母题与主题谱系之中,烂柯已经被纳入了山水林泉的叙事空间。董纪《题画》:
罢钓归来不汝期,无心说起烂柯时。仙家岁月真如许,也向山中看奕棋。[22](P771)
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渔父”与“樵夫”形象的融合。而我们以围棋为核心的全部母题都可以纳入到这个大的谱系之中。
围绕围棋所形成的母题谱系,包括烂柯、橘中戏等等故事的嫁接组合,正是围棋以及烂柯故事符号化的表现。它们不再指代具体的、实际的物或者故事,而是代表共同的抽象化、概念化的意蕴,因此可以突破彼此叙事的界限,实现混融。文人画是一种综合性艺术,题画诗中这种母题的符号化,正是绘画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这种符号化从文人园林的烂柯造景,如“小烂柯”“樵隐堂”“橘隐”等等类似名目的造型艺术就开始了。首先,诗歌是时间性的艺术,而绘画是空间性的艺术。无论是《述异记》等等烂柯故事的文本,还是烂柯题材的诗歌,都是描述王质的经历来叙述故事;而烂柯造景和绘画则是以“决定性瞬间”叙事,选取“观棋”的画面,甚至只有围棋盘本身,来引发对于烂柯故事的想象。而图像表意本就具有不确定性,选取一个画面,尤其是一个虚构的画面,就意味着拥有一个开放性的想象空间,由围棋所触发的联想都可以在诗画的对话互文中融为一体。其次,中国画在语图结合的过程中,逐渐朝向语言靠拢,文人画尤其如此,北宋画家李公麟认为“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情性而已”[23](P76)。而绘画要吟咏性情,试图传达和表现语言,“则必须朝向抽象化的方向发展。绘画超越自身内容层面就是视觉图像的程式化、符号化并逐渐形成具有特定文化寓意的原型化母题”[24](P127)。这也是中国绘画艺术中出现众多母题与主题谱系的一个原因。所以图像本身的符号化、谱系化,也就导致了围棋的符号化,以及以围棋为核心的一个母题系统的形成。而烂柯故事则为这个母题系统提供了最重要的时空两方面的隐喻。
(二)烂柯的世俗化
围棋与烂柯故事的符号化,使得人人拥有自己的“烂柯”成为可能,这不仅使得创作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在烂柯故事中增添了更多个性化的自我表达。如果说唐宋文人以烂柯故事来表现神仙境界、世幻浮促、超越世事的理想人格,那么进入元明清时代,烂柯故事更多表现的是一种个人化的世俗生活体验。
文人画的一大特点就是“吟咏性情”,而题画诗更是观画者与画家心灵的沟通。所以作为文人画的弈棋图和题弈棋图诗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表达。从宋末开始,烂柯题材作品中除了充满尘视名利、雅好山林的志趣之外,特别致力于书写王质或对弈仙人的游戏心理空间。如方一夔《古意六首·其一》演绎烂柯故事,其中写道:“神仙在何处,只与人世同。眼净偶自见,心到遥相通。”[5](P42223)神仙与人都是相同的,只要“眼净”、“心到”,就可以达到神仙的境界,这是一种禅宗、心学思考的理路,强调内心的自我启发与觉悟。在元代题画诗中,除了强调对世俗的超越,作家常常把这种“眼净”、“心到”等同于文人在围棋游戏中所体会到的闲适,比如:
三衢仙人石桥奕,隅坐野樵心自适。(岑安卿《题黄中立樵云卷》)[25](P475)
尘世清闲从古少,山林岁月自来多。(释善住《题刘商所作观奕图》)[26](P731)
神仙闲日无处消,借棋对着聊逍遥。(刘将孙《烂柯图为福宁州尹殷周卿作》)[27](P38)
与其说是在写神仙,不如说是在以围棋游戏的闲适体验来表现自己的心境。无论是元代异族统治下的消极反抗,还是真实的生活体察,元人将对“闲快活”的追求渗入到了烂柯故事的写作中。以题烂柯图写闲情的思路在明代延续了下来。如解缙(1369-1415)《观弈图》二首:
去年曾到烂柯山,看著残棋不肯还。自是太平舒化日,神仙都只在人间。
尘中车马如流水,每遇闲时日似年。只在人间已如此,何须日讶看棋仙。[19](P28)
可见明代也出现了一些通过烂柯故事来讨论理想神仙境界的声音,不再强调提升超越,而是排除机心桎梏而追求人伦日用,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彼此打通,神仙境界即是游戏中所体会到的闲适。
除了文人画的自我表达之外,绘画本身的叙事方式决定了烂柯题材更加注重空间上的表现。我们从很多题画诗中可以看出,很多烂柯图所表现的都是拈子思量的画面,这也为神仙时间观增添了新奇的解释:
碧玉花冠素锦裳,对拈棋子费思量。经年不下神仙着,想是蓬莱日月长。(黄庚《仙姑对弈图》)[28](P817)
如何一局成千载?应是仙翁下子迟。(高启《观弈图》)[29](卷一七)
小年长日正迟迟,算是樵柯欲烂时。大抵人情多好胜,偶逄仙敌亦争棋。(查慎行《虞山钱劬谷属题采药图二首》)[30](卷一八)
神仙时间长是因为“费思量”、“下子迟”、“人情多好胜”,这既是对于图画的描绘,也是诗人对围棋游戏本身的体察。以围棋棋手的长考来解释故事中的神仙时间观,包含了丰富而美好的生活情趣,更是一种世俗化生活体验的表达。
综上,烂柯故事的接受史就是在古代主流文化逐渐倾向于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的过程中,突破其本来长生久视的内涵,用文学的方式衍生出历史化、哲理化的意义,同时又凝结了丰富的情感意蕴与美感特质。首先,受到佛教时间观的影响,烂柯开始表现一种物是人非的无常之恸,乃至于世幻浮促的意蕴,呈现出一种哲理化的倾向。其次,在不断的理性怀疑中,故事的时间观被彻底否定,仙人弈棋对世事的隐喻得到表现,赞美旁观者清的超越精神的作品增多,将烂柯故事历史化也成为一种新的解读思路。第三,到元明清时期,题画诗的兴起、综合性艺术的发展、文学艺术的通俗化趋向,使得观棋烂柯逐渐符号化,成为“隐逸”艺术母题与主题谱系之中的一个因子,烂柯故事的文学接受也就朝着更加个性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