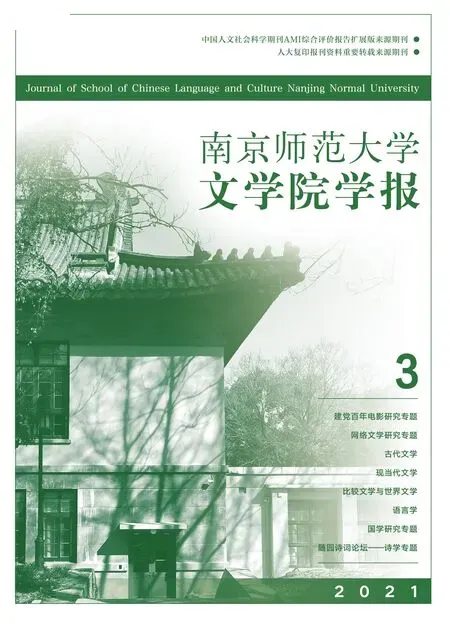30年代左翼电影的抒情面向
乔洁琼
(青岛科技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影戏”被认为是“概括整个中国传统电影观念的基本概念”,“影戏理论”“是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1]“是由一个双层结构的理论框架构成,在外一层是一个带有浓厚戏剧色彩的技巧理论体系,影戏理论的深层结构则孕育着一种从功能目的论出发的电影叙事本体论。”[2](P303)。“中国电影本体论基于两个核心——叙事结构和教育功能,这其中又以教育功能为首。”[3]关于30年代左翼电影(1)1993年,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经夏衍等人确认,指定了74部左翼电影,本文采用此权威指定,对概念不做进一步辨析。,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政治武器、道德教化等论说占据主流地位,成为我们认识这一电影族群的惯性思考。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情感转向,中国文艺的“抒情”面向浮出水面。王德威提出“抒情”与“革命”和“启蒙”共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4]李海燕考察五四前后的文学现象,提出“儒家感觉结构”“启蒙的感觉结构”和“革命的感觉结构”,试图从情感史视野构建中国现代性的动态“感觉结构”。具体到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电影,将反帝、反封建等政治诉求传递给大众,引导大众实现文化和情感转向,需要一个抒情的面向。俄国形式主义丹尼尔·格劳尔德认为情感是情节剧的目的所在:“情节剧的所有要素——主题、技术、原则、结构和风格,都从属于一个最为重要的审美目标:纯净、生动的情感呼唤。”[5]抒情让乏味的政治议题变成了具有审美观感的感性体验,塑造了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左翼电影如果缺乏了“抒情”这一面向,不可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左翼电影运动”,也不可能号召起千万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阶级情感,更不可能实现共产党力图传达的政治理念和文化观念。近年来,中国学者从传统文化资源寻找线索,力图将“抒情传统”纳入到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框架中,“中国电影学派之中必然包容有中国文化基因传承的抒情性”[6],“在中国电影里,一种天道世运的宇宙观念和生生不息的生命体验,蕴蓄着旷远超凡诗意和深深的忧患意识,在天人合一,物我同一,主客归一的浑融境域中,同化最大多数受众的情感,试图导向所有人的心灵,这是中国电影美学面向未来的精神旨归。”[7]
回到左翼电影的历史情境,我们则应进一步追问,属于古典的抒情传统如何与现代性的电影结合,进一步形成中国电影的“抒情传统”?30年代左翼电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与现代媒介电影的结合,是“无产阶级欧化文艺”[8]与西方科技结合的产物,具有十足的“现代性”。左翼影人大多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传统与现代是他们必然要处理和面对的主题。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重新形塑了左翼电影的抒情面向,主要表现在左翼电影的抒情摆脱了古典的抒情传统“集中在精英阶级吟风弄月、闲情偶寄的形式”,[9](P137)进入到一个属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实践中。从左翼电影这里开始,“人民情感”成为电影书写的核心,也构成了百年中国电影的主线。
一、有“情”的主体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一种感时忧国的情结,所谓“诗言志”“诗缘情”“兴观群怨”都蕴含了个人情感与家国政治之间的关系。“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用于祭祀或者宗教仪式,以达到与神沟通的政治目的。因此“诗言志”自提出起便具有了群体性与功能性特征。汉代以后,儒学将“志”与“道”相联系,发展出“文以载道”传统,事实上窄化了“诗言志”的原始含义。魏晋时期,文学自觉与诗人主体精神的觉醒,催生了“诗缘情”理论,“标志着诗歌开始从书写‘群体’之情转向‘自我性灵’的歌唱”[10]。实际上,中国抒情传统中的抒情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和表达,还包含了对政治、历史的理解与想象。“外在的物事和有情的主体相触碰,引发了诗情,而也唯有借诗情的发挥,历史的义理才能澄明”。[11](P57)这一概念与雷蒙·威廉斯提出“情感结构”形成呼应,“情感结构代表一个历史情境里,主体经由公私生活的律动、对现实赋予意义,并将此意义体现于感官与感性形式的过程”。[12]抒情主体通过一种感性形式表达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左翼电影是中国共产党表达个体忧思与民族生存的文化载体。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电影的重要性,但面对20年代中国电影完全受商业驱使的现状,态度是审慎的。“从‘九·一八’直到‘一·二八’的炮声一响,中国的电影就开始转变了。”[13]时代呼唤新的文艺,“要创造新的抒情诗,诗人自己必须以新的方式来感受世界。”[14](P37)有识之士在寻找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时,首先观照的是主体意识的重建,这一重建包含“情感”的重塑。
在1932年“文艺大众化”讨论的热潮中,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人瞿秋白发表了《“我们”是谁》一文,文章指出,要解决文艺大众化的问题,首先应当摆脱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将“我们”从小资产阶级意识中摆脱出来,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15](P100)。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是个人的、主观的、眈美的;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则是忧患的、斗争的、呐喊的。中国电影人应该改变20年代“游戏观念”和“消遣主义”趣味,用劳动大众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去感受世界,创造新的抒情诗。1933年3月(2)对于“电影小组”成立时间,有不同说法,本文引用夏衍《新的跋涉》见《中国左翼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认为电影小组成立的时间是1932年秋。,在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成员有: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随后团结进步人士,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3)1933年2月9日,由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领导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于上海成立。会议选出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黄子布(夏衍)、陈瑜(田汉)、洪深、郑正秋、聂耳、蔡楚生、史东山、孙瑜、任光、金焰、张石川、唐槐秋、胡蝶、应云卫、沈西苓、姚苏凤、程步高、周剑云、黎民伟、卜万苍、李萍倩、周克、查瑞龙等三十一人。其中郑正秋、周剑云、姚苏凤、孙瑜、卜万苍五人为常务,该协会组织如下:郑正秋为总务部长,程步高为秘书;周剑云为组织部长,聂耳为秘书;姚苏凤为宣传部长,沈西苓为秘书;孙瑜为文学部长,夏衍为秘书;卜万苍为技术部长,金焰为秘书。。“左翼电影人”作为一个具有相近理念的“抒情主体”开始形成。
在群体氛围的感染下,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影人首先实现了“情感”转向。蔡楚生1932年编导了《粉红色的梦》,该片讲述了一个青年作家受到交际花诱惑,同妻子离婚,后来幡然悔悟回归家庭的故事。9月6日,《每日电影》发表了席耐芳、凤苏、鲁思的一组评论文章,席耐芳(郑伯奇)批评电影受了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充满了豪华、舒适、享受、腐败的舶来味[16]。苏凤敏锐地指出,影片中的主人公罗文是一个平凡的、资产阶级用以消遣的、那种谈情说爱的小说作家。[17]聂耳发表了《下流》的文章,认为编导应站在劳苦群众也就是“下流”人群的立场上,描写大众。左翼影人的批评对蔡楚生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1935年《会客厅中》一文,对自己的创作历程进行了反思。“由于数千年来传统的封建社会思想所支配,中国的国民性,无疑地是在固步自封的状态中生活着,……无形中养成了一种奴性(我自己也是一个),所以对于一切感觉上的迟钝、麻木,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他认为1931年创作的《南国之春》中,“掺进自己一些小资产阶级趣味的优美的抒情诗般的梦幻以外,一切只是找一个固有的既成的规模”,“《粉红色的梦》从开拍第一天起,就懊悔她的完成。”“我决定我以后的作品,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而尽可能地使她和广大群众接触。”[18](P139)
蔡楚生的反思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创作者如何从一种自上而下的麻木情感苏醒过来,转向鲜活的时代情感,成为一个“有情”的主体;二是创作者如何从沉迷于自我,顾影自怜的情感单体摆脱出来,转向劳苦大众的群体情感。这也是当时左翼影人情感重构的重要内容。吴永刚在参与拍摄了田汉的《三个摩登的女性》《母性之光》,参加了几次金焰亭子间的电影小组组织的活动后,开始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衷芑香导演在拍摄了《兰谷萍踪》后,鲁思、洪深、席耐芳等影评人批评该片“脱离经济而独立的超然的高级的爱是开历史的倒车”[19](P192)。 衷芑香接受批评,1933年拍摄了具有鲜明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挣扎》。洪深在总结《1933年的中国电影》时指出:1932年后期,中国电影已经明显从颓废的、色情的、浪漫的、乃至一切反进化的羁绊中挣脱出来,勇敢地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左翼电影人的 “诗言志”“诗缘情”既继承了古典知识分子的抒情表现,又将这一抒情面向嵌入到启蒙、爱国的时代背景下,将“志”与“情”与救国、唤醒国民相结合,重塑了现代的抒情主体。“电影诗人”孙瑜疾呼,“电影救国,至于舞台剧或影剧,并非我辈自负,中华将来命运,与之关系甚深。我辈在现时制剧,何不向救国方面做去,国耻之羞,穷恶之惨,气节沉沦之悲,何处不能痛与告众。即以军人而论,给他们点国耻戏和理想中之模范军人看看,看了之后,总可有点感效吧。”[20]孙瑜的电影都与“救国”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小玩意》提出的“实业救国”,还是《体育皇后》中的“体育救国”,还是《大路》中建筑工人的救国行为,都将个人之情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起来。通过电影唤起人民的爱国情感,抒情与爱国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主体的情感最终落脚在国家兴亡上,历史的义理终得彰显。这种情感超越了创作者个人的情感体验,重塑了一个具有群体特征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抒情诗人”。
二、“抒情”的叙事
软性电影论者黄嘉谟批评左翼电影“全是灾难病死虐待等社会黑暗面的压迫,或是失业贫乏等难题,却硬要交这辈神经衰弱的观众去解决,要他们陪着剧中人共同受尽压迫与困难,这种影片也未免太残暴了。”[21]黄嘉谟否定电影揭露现实、描写苦难的意义,认为电影是一种供人娱乐的“软片”。这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揭示了左翼电影的诗性核心:生死苦难。综观74部左翼电影,书写苦难占据了绝对的比例。《新女性》中的知识女性韦明遭受情感失败,在生活苦难和流言蜚语中自杀;《桃李劫》中知识青年陶建平的妻子黎丽琳产后因无钱治病死去,陶建平为救妻子犯罪被判处死刑;《渔光曲》中穷困的小猴在小猫的怀中死去;《神女》中的阮嫂被判死刑;《天明》中的菱菱为救表哥英勇赴死;《小玩意》中的叶大嫂由于女儿死去,家破人亡而发疯;《船家女》中玲子被逼为娼,铁儿发疯……死亡、发疯、入狱成为人物的主要结局,“生死”是左翼电影表述的一大主题。
情感在本质上与“生命体验”紧密相连。左翼电影常常触及到的“死亡”主题在中国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蕴涵了中国传统抒情结构。“死亡”成为一种抒情意象可追溯至屈原。屈原选择了对世俗的不妥协来追求他心中的真理,是以“我的存在即将消失的‘无’,抗衡、询问、诅咒那一切存在的‘有’”[22](P130)。后世知识分子将“死亡”视作一种精神,锤炼出一种面对困难虽痛苦、压抑、悲伤,却能够忍辱负重、寻找生命此在意义的心理情感。这种情感形式在显露和参与人生深度上,获得了空前的悲剧性的沉积意义和冲击力量。这种由死亡而带来的感情的抒发,“总是与对人生—生死—存在的意向、探寻、疑惑交织在一起,进而上升到一种哲理的高度”[23](P130),形成一种“情理结构”存在于中国诗学传统中。
左翼电影的生死主题融入了现代性话语,构成了新的抒情传统。所谓现代性话语就是在革命与启蒙背景下的民族观念和爱国主义。30年代,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尚不明朗,中国文艺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焦虑和彷徨。一方面,在革命与启蒙的语境下,传统成为现代的对立物,它不是民族未来的选项;另一方面,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还未扎稳脚跟的马克思主义屡遭重击,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左翼进步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出路未免感到迷茫。这种焦虑体现在电影的“整体叙事”中。列维·斯特劳斯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提出“神话原型”这一概念,认为“如果神话有意义的话,该意义不可能存在于那些构成神话的孤立的元素中,而只能存在于这些元素的组合方式中”[24](P286)。74部“左翼电影”虽然题材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但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被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压榨的劳动阶级,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女性,觉醒又被现实吞噬的青年,无果的未来,影片通过“死亡”来呈现这一沉痛体验,蕴涵了个人与国家未来之路的想象。左翼电影中普遍存在的“消极情绪”深层次上来讲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相关。“消极情绪同为明天奋斗相连,通过把消极情绪同疾病、死亡等联系在一起,强化了把它们作为努力目标的重要性”。[25](P81)电影的苦难常常伴随着觉醒和坚韧不拔的生存意志。《自由神》中的陈行素历经苦难,依然坚韧地生活下去;《大路》中筑路工人被敌人机枪扫射而死,但他们又在想象中“起死回生”,延续着抗敌的神话……,从这一意义上讲,左翼电影将“生死苦难”放置在民族解放与国家未来的现代性话语中,激起了观众的民族情感,号召出千百万人义无反顾的精神或力量,号召出对未来的向往。传统的抒情核心与现代性话语重构了左翼的抒情传统。
饶曙光认为,“中国电影的诗性气质更为明显,所谓的诗不单指叙事的抒情功能和意义,也包括了叙事的抒情风格和形成。”[26]左翼电影在叙事上借鉴了中国传统的传奇叙事(4)虞吉认为中国电影叙事的建构是一个涉及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问题。“传奇性叙事”则在中国电影叙事中提供了“叙事范式”,具有普遍参照功用。传奇性叙事“要求情节的整一性,故事必须有头有尾,追求事件的曲折离奇和缝合照应的构思技巧,讲究叙事的规定程序。……它的人物必须充满情感,但不必具有意志,不必把情感化为动作,它的情节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作者的意愿,而非剧中人物的意志。的特征,讲究故事的完整性,追求故事的曲折离奇和缝合照应,情节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创作者而非剧中人物等等。在叙事上又带有“说书人”的痕迹,在呈现故事的同时又跳出来进行评价,将与情节无关的抒情插入剧中。有的影片叙事结构比较松散,常常不是以一个强烈的戏剧性需求来推动情节发展,而是由若干没有因果关系的情绪段落组成。如《大路》,前半段由群像人物和劳动场面撑起,工人劳动、饭铺抢茶杯、小六子偷东西、男人洗澡、月夜谈情等段落。这些段落在情节上无因果关系,剧中人物也没有一个强烈的戏剧性需求,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之间关联性较弱。但该片依然具有饱满的抒情色彩,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总之,左翼电影将生死这一“抒情”核心包裹在一个传统叙事结构中,尽最大可能发挥电影的情感媒介属性,将一个私人的情感体验转化为一个集体经验的话语演习,从而召唤出中国人集体的情感。
三、人民情感共同体
建构主义观点认为,情感是社会、文化的建构物。在文化更迭的历史时期,个体生命会被新的文化结构所模塑和打造。[27](P4)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儒家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撬动和改变着儒家的思想、情感、文化结构。新的文化结构的出现逐渐建构了人民这一历史主体。人民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将工农兵作为主体身份凝聚在一起的不仅有政治理念和文化认同,还需要一种情感和价值认同。个体是如何从儒家感觉结构中摆脱出来,获得“人民情感”的认同,并能够以“人民”的感觉体验痛苦、压迫、绝望,这一过程与中国共产党的一整套情感建设机制密切关联。30年代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的文艺思想在“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尤其在文艺为什么人、作家的世界观改造以及工农相结合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毛泽东文艺观点惊人的一致”。[28](P116)瞿秋白在《普罗大众文艺现实问题》指出,“普罗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29](P464)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左翼电影构建了“人民情感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是以民族情感为基础,以“人民性”为旨归的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情感共同体。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种以“三纲五常体系”为情感纽带将中国人连接在一起的“伦理共同体”[30](P121)。李海燕提出“‘儒家的感觉结构’即儒家礼教表达情感的维度,主要以‘三纲’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两条为核心。在每一‘纲’中,情绪的灌注或投入在理论上都是互惠的,作为忠诚的回报,君会施以仁或恩,作为对孝的回报,父则会施以恩或慈,构成正统儒家礼教基础性道德情感的是‘忠’与‘孝’。”[31](P26)在儒家礼教情感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对情的表达依附于“礼”这一目的。延伸到文艺作品中,诗歌与道德情感之间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发乎情,止乎礼”。由于长期受到“礼”的压制,造成了中国人缺乏一种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更缺乏一种民族同情之心。鲁迅一生致力于唤醒“麻木的国民的灵魂”。一个看着自己同胞被残杀,不仅没有感到痛苦和憎恶,反而抱着欣赏和欢呼的态度来观看这一景象,在鲁迅看来,这种人活着是毫无意义的。启蒙运动就是唤醒国人的灵魂。国人只有认同了民族的情感逻辑,才能从民族情感构成出发去体验他们的痛苦。
五四知识分子力图构建一个“民族情感共同体”的逻辑,“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不会把自己视作另一部分的外来人;他们能感受到彼此属于一个族类,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命运凝铸在一起……,民族总是被设想成一种平等的、深刻的同志之爱……,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32](P6)五四知识分子将“文学视为一种情感工程,力图通过普世性的、基于情感的身份认同替换掉亲族关系和基于地域的身份认同,从而让中国人对彼此形成感觉,并互相以民族的身份相认。”[33](P236)左翼电影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自觉承担起构建“民族情感共同体”的责任。
左翼电影在叙事上通过追寻、唤起、再造情感的方式来唤醒民族情感。惨痛的集体记忆促成了情感共同体的形成。左翼电影常常对主人公的苦难身世加以“回溯”来强化集体记忆,如《三个摩登的女性》《大路》《马路天使》《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民族生存》等多部影片都有东北沦陷的社会背景。东北沦陷引起了国人普遍的愤怒的民族情绪,通过电影修辞将民族情感加以强化。观影过程促使民族情感移情到观众身上。人们在获得民族认同的同时也感受同胞的痛苦,获得感受他人情感的能力和对弱者的认同,“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
在启蒙和革命的语境下,“人民情感”不再是伦理情感,而是由阶级、妇女、青年、国家等意识规定下的现代情感。《春蚕》《挣扎》《丰年》《天明》《渔光曲》等影片讲述了农村的破产,农民在丰收之年依然走投无路,将劳动人民的悲苦命运指向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神女》《新女性》《小玲子》《脂粉市场》《船家女》等影片讲述了各类女性的悲剧。《桃李劫》《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夜半歌声》《十字街头》等影片指向青年的觉醒和选择。这些“现代的情感逻辑”通过电影的传播,极易被大众模仿。人们通过电影能够感觉到他们正在紧随潮流,电影把个人与共同体连在了一起。同时,左翼电影中所宣扬的自由恋爱、阶级斗争、妇女解放等主题在小市民的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日常体验,而是一种“理想的”“想象的”情感体验。想象的体验借由电影媒体被扩大并神圣化,最终形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情感,人民情感共同体由此得以形成。
左翼电影深刻反映了文艺的政治性、集体伦理以及人民性之间的关系。从瞿秋白、夏衍所主张的“艺术,为着工人农民而存在”,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34](P866),再到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明确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35](P211)再到2014年,习近平主持文艺座谈会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36](P13-14)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情感”的传承和延续。人民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是30年代左翼电影抒情面向的立足点和艺术旨归。
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对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进行了评价:“这些影片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它不仅深深感动了观众,而且促使他们汲取政治信息;在一个为不平现象所折磨而没有正义的社会中,残余的人性内核没有例外地总是体现在下层人民身上。”[37](P488)左翼电影通过重塑抒情主体创造了时代的“抒情诗人”,他们围绕着生死苦难的抒情内核,将个体与民族情感联结在一起,重新建构起人民情感共同体,这一人民情感和精神延续至今,成为共产党文艺政策的起点和落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