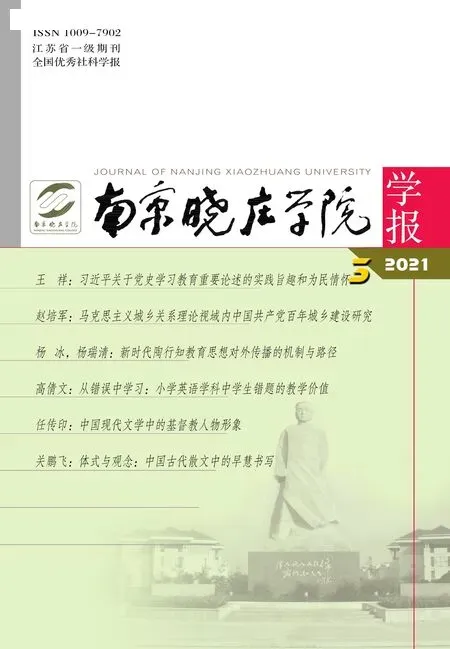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督教人物形象
任传印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作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有神论宗教,基督教(1)本文所指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参见卓新平主编:《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58-63页。在唐代已传入中国,但其传播与影响在很长时间内非常有限。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华民族殖民统治加剧,中国被迫开启现代化,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体系面临解体,新的信仰与价值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此时基督教再次强势东进,产生了相当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民族历史文化、现代社会转型、文学革命、基督教传播等共同促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督教人物形象,涉及宗教界与文学界两方面作者,涵盖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塑造耶稣、牧师、神父、平信徒等多种人物。学界对此有所论及(2)学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督教人物形象主要是专题或个案研究,主要有:倪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小说中的基督徒形象——以巴金、路翎和张爱玲为中心》,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学富《中国文学中的耶稣形象》,《金陵神学志》1995年第Z1期;洪玲《肩负起民族和人类的十字架——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耶稣形象》,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祝宇红《“本色化”耶稣——谈中国现代重写〈圣经〉故事及耶稣形象的重塑》,《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梁工《中国现代作家对耶稣形象的重塑》,《东方丛刊》2008年第4期;郭晓霞《十字架上的女性基督:析五四女性文学中的耶稣形象》,《圣经文学研究》2010年;伍茂国《“耶稣之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几种解读》,《晋阳学刊》2005年第5期。学界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研究方面亦有著述,有些章节或个案涉及基督教人物形象,但非重心。参见:[美]路易斯·罗宾逊著,傅光明、梁刚译《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唐小林《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华龄出版社2004年版;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总体而言,学界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不断推进,学界与教界都有参与,论著注重历史与文献,具有现代性视角、文学自觉与宗教学养,多侧重作家作品专论,特别是耶稣形象的研究较多。以上著述对基督教人物形象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笔者认为,该论题有必要从现代文学转型视角开展综合研究以及某些比较研究。,但尚未见系统性考察。笔者基于现代社会转型与价值重构视角,探讨现代文学中基督教人物形象的价值导向、文化意蕴,兼及形式特征,在文学史视域中总结其特征、规律与得失,以资镜鉴。
一、宗教性书写
宗教性书写源于对基督教有信仰倾向及情感认同的作家作品,其塑造的基督教人物传达了宗教教义、情感体验与精神特质。宗教哲学家保罗·蒂里希认为,人们不能在终极的严肃意义上拒斥宗教,因为终极的严肃,或者终极关切的那种状态,本身就是宗教。(3)终极关切是对世界本源、存在意义、人性、生死、命运等问题的探索与解答,它以超越任何具体、初步和有限的方式趋近或达到生命整全意义上的和谐。参见[美]保罗·蒂里希著,何光沪选编:《蒂里希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82-383、1140-1141页。基督教人物形象的宗教性书写注重终极关切的体验与价值,包括在世罪感与精神超越两个层面,后者主要体现为信、望、爱三个方面。(4)卓新平主编:《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第114-157页。同样是导向信仰,宗教界的文学性作品与文学界的创作有所不同,前者抱持“文以载道”的思想,注重对宗教体验的审美传达,亦有与时代共患难的担当;后者亦有信仰心理,但相对比较开放丰富,注重表现现实人生与基督信仰的对话,虽然这种对话比较复杂艰深,但获得的启示往往质实深刻,在传统神学的现代启示与反思现代性方面具有独特且重要的价值。两者在信仰心理与价值重心上的差异导致人物形象的表现形式亦有不同。
基督教作家中,神学家、教育家、诗人赵紫宸比较典型。他说:“我常觉得诗与宗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却愿把我自己的宗教经验,在诗的生活中,透露出一点,分给尚未向巴力屈膝的同道们。这是我将诗出版的最大的理由。”(5)赵紫宸:《赵紫宸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32页。他基于耶稣的生平故事材料、自由主义和本色化的神学立场与信仰体验创作《耶稣传》(6)此处受到前贤的启发。参见祝宇红:《“本色化”耶稣——谈中国现代重写〈圣经〉故事及耶稣形象的重塑》,《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第31-39页。,作品以时间顺序描述耶稣的生命成长与信仰历程,表现耶稣对上帝的信靠、期盼以及博爱、勇毅、牺牲等信德。作者的神学立场与神学研究使耶稣形象具有创造性阐释的意味。例如以现代文化运动和心灵解放界定基督教的本质,以人本主义的精神永存阐释复活,将《圣经》中的神迹理解为现代集体主义精神的结果,强化博爱救世中的民族观念,以圣贤比附耶稣(7)祝宇红:《“本色化”耶稣——谈中国现代重写〈圣经〉故事及耶稣形象的重塑》,第31-39页。,体现出作者以其神学立场对现代转型中时代社会的回应。之所以选择传记形式,或许是因为这种较少艺术成规的文体可以充分容纳宗教内涵。除了传记,赵紫宸的新诗亦值得注意,如《客西玛尼》运用比兴手法,以抒情主人公的想象渲染受难牺牲的耶稣形象。《伯利恒》借鉴古典绝句艺术,围绕地名赞颂和论议耶稣的意义,传达抒情主人公强烈的信仰意志。《破碎的国旗》表达基督徒将上帝与民族国家融合的情感。《弟兄,你为何不信》以对话方式叙说信仰对人生的价值。《牧师经》以日常场景、朴素的语言塑造乡村牧师形象,他们不是超凡脱俗的神使,而是平凡地传播福音,既有精神追求,也有丰富的人性,显示出圆形人物的真实性与富有张力的情感蕴藉。
文学界富有宗教意蕴的作家作品相对多元。首先,作家对基督教的体验与认同的角度及其程度有所不同;其次,作家创作相对专精,审美诉求普遍高于教界,基督教人物形象内涵也有不同,故总体有简约与复杂之别。简约者又约略有两类:或偏理性演示,或偏情感传达。前者如深具宗教学背景的许地山,将现代学术理性与宗教思想结合(8)许地山说:“我想宗教当使人对于社会、个人,负归善、精进的责任,纵使没有天堂地狱,也要力行;即使有天堂地狱,信者也不是为避掉地狱的刑罚而行善,为贪天堂的福乐而不敢作恶才对。”他认为当下的宗教应当易行、普及、道德情操强、有科学精神、富有感情、具有世界性、注重当下生活、合于情理。参见方锡德编:《许地山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页;陈平原编:《许地山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366页。,小说《缀网劳蛛》塑造了女主人公尚洁,她以博爱与庄重调伏恶人,颇有玛利亚色彩,悔改的长孙可望则反衬着她的虔诚与圣洁。夏志清认为,《缀网劳蛛》近似中古基督教的传奇,尚洁近乎圣徒。(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路易斯·罗宾逊认为尚洁作为基督徒的模范人物,颇有摩西在西奈山传道的意思,人格过于神圣完美,很难令人信服。(10)[美]路易斯·罗宾逊著,傅光明、梁刚译:《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西方人文主义扬弃中世纪神学,建构现代人性与价值,对人的丰富性、矛盾性、真实性有深入发现,有学者亦从文学角度阐发人类内心的矛盾与深广(11)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08页。。比较而言,尚洁接近神性意义上的人,性格不够丰富,不同侧面的组合有失自然(12)譬如尚洁开始的忍辱负重与坚毅静定颇有刻意自持的意味,后来面对女儿失声痛哭,前后似不够协调。。不过,作为基督精神的象征(13)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扁平的尚洁非虚假功利的说教符号,而有宗教之真实,是信仰实践的结果。许地山依托较深的宗教学养,表现其理解的神性美,但这种特殊的美难以与众多读者相适应。苏雪林皈依天主教(14)苏雪林留学法国时,爱情之殇、兄长之死、母亲之病、远离故土等因素造成的困境使之皈依天主教。参见陈国恩主编:《苏雪林面面观——2010年海峡两岸苏雪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43页。,富有自传意味的小说《棘心》塑造的修女马沙,舍弃世间享受而致力于主的事业,对浸淫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科学理性的女主人公杜醒秋而言,马沙显得陌生神秘,作者从杜醒秋视角写来,较多理性观照。天主教作家张秀亚(15)张秀亚自幼受天主教影响,1941年受洗,该年出版小说《皈依》《幸福的泉源》,融入自己接受天主教的思想转变与信仰体验。参见包兆会:《历史文化名人信仰系列之二十四:张秀亚》,《天风》2015年第12期,第52页。的小说《皈依》《幸福的泉源》彰显天主的崇高伟大(16)张秀亚:《张秀亚全集》(第10卷),国家台湾文学馆2005年版,第170页。。两部小说皆有青年“爱情+信仰”的情节模式,重点写超凡入圣的信仰心路及其与爱情的冲突,最终共同走向信仰,或在信仰背景下建立爱情,叙事艺术较多承袭了古典文学的故事性、含蓄美、象征性、抒情性、大团圆以及比兴手法。其中《皈依》中的男女主人公华、珍以及次要人物神父,《幸福的泉源》中的次要人物考伦医生、蓝衣修女、讲道的神父与院长、同学湘,其形象性格与文化意蕴普遍比较简洁鲜明,主要表现主的力量与信、望、爱的信德,有较为明显的传声筒特点与教化意味。
同样是简约人物,基督教作家冰心与苏雪林、许地山又有不同,她更多地寄托于情感抒发,具有较强的皈依意志和情感认同,笔下的基督教人物主要是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如《迎神曲》的主人公膜拜上帝,思考何去何从,冥悟自语。《送神曲》确证神的启示,虔心膜拜。人与神的交互体现出主人公从困惑到超越的动态心迹。《晚祷(一)》的祈祷表现了主人公的宗教情感,信仰意志的生发、扩充、净化与坚固。《晚祷(二)》的主人公在仰望繁星宇宙的终极体验中聆听秋风、落叶,表达对造物主之恩威的崇仰与皈依。冰心根据《圣经》故事创作《傍晚》《黄昏》《生命》等十余首诗,以人神对话方式塑造出祈祷上帝、崇仰启示、感受慈爱从而实现“我心安定,我心安定”(17)冰心:《冰心诗选》,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的信仰者形象;《他是谁》《客西马尼花园》《骷髅地》塑造了悲壮受难的耶稣形象、先知形象,博爱与牺牲精神尤其明显(18)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第67-68页;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另外,朱雯的《逾越节》与端木蕻良的《复活》(19)这部小说直接受到赵紫宸《耶稣传》的启发。参见祝宇红:《“本色化”耶稣——谈中国现代重写〈圣经〉故事及耶稣形象的重塑》,第31-39页。这两部小说将基督教文化与作者的宗教修养、审美情感融合,前者通过生动细腻的言行心理描写与情景交融手法,截取和塑造了在客西马尼花园临危不惧而又不乏忧患踟蹰的耶稣形象,表现虔信上帝、心系黎民、毅然受难的基督精神,对门徒也有简略刻画;后者主要截取耶稣被捕、受难及复活的故事,注重情景交融与人物比较,写耶稣在客西马尼花园的心理与祈祷,在十字架上的心理,表现其忧伤、孤独、痛苦、勇毅的性格,最后指出耶稣的复活唤醒了人类的良知,蕴含对现代新道德的期冀。两部小说都依托《圣经》改编,耶稣形象有所趋同,但在审美表现上各有特点。
与扁平人物相对的,是复杂的圆形人物。例如许地山的《商人妇》《玉官》塑造的女性基督徒,具有从凡俗到神性的动态复杂过程,呈现传记式的信仰心路,表现了更丰富的宗教体验与艺术真实。《商人妇》的主人公惜官被丈夫抛弃,逃难流离之际,睹明星而获启示,在基督徒朋友以利沙伯的引导下皈信上帝。《玉官》中玉官的皈依历程更为曲折,体现了乡村底层妇女摆脱困境、争取自由的心理需求。玉官开始入教时着眼于人身安全,后来为了薪水和儿子读书而学习教理,无论是以《圣经》驱除恐惧、震慑军人,还是期盼神主保佑儿子的功名与自己的牌坊,都是生存层面的功利追求。后来玉官经历了与儿媳妇的矛盾,疏离家庭,又见证了小叔子李慕宁的信仰,在旌表节妇已过去的时代,此前抱持的期待落空,心理失衡激发其寻求新价值的自救意识(20)宗教心理调研显示,生命紧张或失衡是多数教徒接纳信仰的内因,而且存在从契约式交换关系到逐渐内在化、纯真化的转变。参见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她认识到以前的自私与虚伪,反思现在的遭遇,其忏悔与皈依心理比较生动、强烈、真切,此后投身乡间的宗教与公益事业,趋近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21)路易斯·罗宾逊认为,《玉官》描述一个妇女在个性化进程中完成自己的故事。参见[美]路易斯·罗宾逊著,傅光明、梁刚译:《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75页。,表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平民主体性、信仰逻辑与女性经验。张秀亚《幸福的泉源》中的三位主要人物也较为丰富,冯士琦在坚守信仰中探索信仰与爱情的关系,信仰是爱情的基础,但又不是爱情的必要条件,其动态的矛盾的心理丰富真实且有深度;知性女青年方文菁从热爱诗书、信仰自我的朴拙状态逐渐认识到天主教的牺牲精神,进而与冯士琦实现信仰与爱情的圆满结合,虽然蜕变过程较多情感思维与浪漫色彩,但仍展现了信教过程;徐美仑信仰天主教,促成冯士琦与方文菁相识,后来两者相恋,她喜欢冯士琦,遂陷入爱情失落与嫉妒怨恨,最后通过信仰实现觉悟与超脱,虽然其有机性不够强,但心理比较丰富真实。三个人物都蕴含遭遇困厄、成长蜕变、人神对话的特殊性与丰富性。
林语堂与许地山颇有不同,与张秀亚比较相似,《林语堂自传》以线性结构和优美文笔建构自我形象,表现曲折的信仰历程与个体经验。少年林语堂热爱自然,受到作为传教士的家父的影响,也学习儒家文化。在以科学理性、道家道教的人文主义否定神学的青年时期(22)何建明:《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史研究》(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0页。,宗教意识仍深刻影响其对意义世界的解释,蕴含着人文理性与基督教的冲突。基于终极关切的心理,晚年林语堂面对哥特建筑,在对神的审美感悟中确认价值:“那种在大马色路上炫花了圣保罗的眼的光,现在仍在世世代代中照耀,没有晦暗,而且也永不会晦暗。这样,人的灵修藉赖耶稣基督而接近上帝的心灵。”(23)林语堂著,工爻、谢绮霞、张振玉译:《林语堂自传》,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神启织就了沉静绚烂的晚霞,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道家与神学、科学与信仰等不同价值中自求慰藉的宗教心理,其形象内蕴非西方神学传统的直接延伸,而是涉及多方面思想资源对话的现代探索。(24)林语堂晚年的基督教信仰具有耶道对话的特点,是灵性与理性的重新整合与提升。参见何建明:《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史研究》(下),第726-727页。
从社会转型与价值重构的角度说,基督教人物形象的宗教性书写增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性及艺术价值,人神对话的紧张(25)在基督教视域中,人是有罪与欠然的,这为超越世俗提供强大的动力。参见戴立勇:《现代性与中国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8页。与终极关切虽然没有诸如《红字》《悲惨世界》《罪与罚》《复活》以及颇有传统的《忏悔录》系列等国外基督教文学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色鲜明且震撼心灵的思想与艺术境界,但可以刺激传统农耕文明之重和谐的思想与审美心理,为中国现代人学思想与实践带来破与立的动力,为文学的超验书写提供文体选择与艺术手法方面的经验,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后发现代化语境下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学与文化、建构基督教人物形象的特点。如与同期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其他类别的宗教人物形象比较,愈加能见出其特质。(26)就宗教性书写而言,因信仰之思想与情感差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督教人物、佛教人物、道教人物、伊斯兰教人物各有其文化意蕴与价值关切;艺术表现方面,基督教人物相对出色。可参考:任传印《形象·意义·审美——中国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研究》,浙江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任传印《论民国武侠小说中的宗教人物形象》,《武陵学刊》2015年第2期,第97-102页;任传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佛教人物形象塑造》,《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99-106页。
二、批判式塑造
在西学东进、文学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对基督教人物形象的批判式塑造有其历史必然性,其思想资源是以科学理性、人文理性、民族独立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亦不同程度地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视角、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等。就批判的具体内容而言,有的侧重人物的宗教修养与个体道德,有的针对人物内心世界展开人性与神性的观照,有的抨击基督教人物对中华民族国家利益的侵害,有的兼有多重意蕴。就作家投射的价值判断而言,多数侧重否定,这源于启蒙思想对传统神学的解构、民族独立对西方殖民的反抗;另外有的从现代视角予以肯定,有的则呈现现代理性、道德意识、宗教思想文化彼此交织的复调式的矛盾状态。
首先是否定式塑造。基于现代人文与科学理性、道德意识的基督教人物批判比较广泛,相关作家各有切入点。以有教会学校经历的张资平为例,自然主义文学的情欲主题使他笔下的基督教人物普遍受到情欲与功利的支配(27)自然主义文艺思想造成张资平小说中性爱与信仰的矛盾,但实际上基督教并不反对灵肉和谐。参见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210页;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181页。,既对人物的信仰真实性表达了批判(28)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121页。,也暗含当时自然科学对人性的解释。小说《上帝的儿女们》通过富有荷尔蒙气息的言行心理描写表现教会人员的道德混乱,诸如眉目传情、私通怀孕、《圣经》与《金瓶梅》并置,女性迫于现实困境入教,学生迫于金钱或洋教势力信教,等等。《冲积期化石》中的申牧师攀求势力,造成女儿被逼死,是并无宗教人格的“单洗杯盘外面的法利赛人”(29)张资平:《冲积期化石 飞絮 苔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中的牧师贪鄙庸俗,《梅岭之春》中在教会任职的吉叔父违背诫命而通奸,《公债委员》中混迹于教会的陈仲章抛妻弃子,《蔲拉梭》中的宗礼江迫于贫穷入教,等等。这些欲望化、扁平化的人物既有对应市民感性欲望的俗文学特征,也不乏对社会与人性的严肃思考。沈从文通过边地美好人性视角批判现代都市的病态生活,这比较直露的批判也涉及基督徒,如小说《蜜柑》中的S教授,用圣恩大学的经费办聚会,看似座谈校务,实则娱乐。无名氏的《无名书》源于整合东西方文化重建新文明的宏愿,主人公印蒂曾皈依天主教,发现梅神父道德败坏后离开,但作者的批判集中于形而下的道德实践而未达到对教理的批判(30)无名氏:《〈无名书〉精粹·代序:试论〈无名书〉》,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徐玉诺的散文诗《与现代的基督徒》基于虔诚纯粹的信仰心理,以对话方式逼视基督徒,说“基督徒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31)刘济献编:《徐玉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自私自利代替美好信德。臧克家的诗歌《罪恶的黑手》批判基督徒的险恶、虚伪与功利,表达道德批评与社会革命思想(32)王本朝分析了作者的反帝意识与批判的主观性。参见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41-42页。。
基于民族国家视角的否定式塑造比较鲜明。萧乾对基督教的强迫性与殖民性深有体会(33)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15页。,例如小说《昙》中的约翰牧师,以感化中国人自命,但面对中外民族矛盾与教会学生的游行抗议,遂愤然驱逐与事者启昌和他的母亲(34)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167-168页。,深刻揭露民教冲突。郭沫若的自传体小说《双簧》对武汉基督教青年会司会者施以犀利风趣的批判,指出基督教与国民革命势不两立,“吃教”的骗子胡说八道。(35)杨剑龙指出小说对基督教的批判,但其论述重心非人物形象。参见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136页。老舍的《四世同堂》探索抗战背景下几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命运,作品对英国传教士窦神父和本土世袭基督徒丁约翰的塑造寄托了民族独立意志与现代人道思想。窦神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基督博爱精神,西方中心立场与文化偏好使他更像普通人;丁约翰崇洋媚外,是典型的“吃教”,他对英国人富善先生崇敬顺从,为了赚钱而制作伪劣军服,不惜背弃上帝和民族情感。田汉的话剧《午饭之前》讲述底层工人与女性贫病交加的生活,看似博爱的牧师却私心自用,表现了虚伪人格与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36)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39-40页。将此与其他类别的宗教人物形象比较,会发现上述问题具有普遍性,可见现代启蒙思想与文学主潮对宗教的批判具有整体性与趋同性。
其次是肯定式塑造。作家将基督教信德如虔诚、博爱、牺牲、勇毅、革新等纳入现代文明与道德视野,使之成为现代价值重构的支撑性资源,属于对神学的现代阐释与借鉴。碧野的小说《被凌辱了的十字架》通过倒叙塑造了为保护中国难民而被日军暗杀的伊兰神父形象,小说没有深入表现其神学内蕴,而是通过场景与行动的白描表现神父与日军抗争的正义、博爱、勇敢等品质,基于民族国家现代性和人文理性的价值立场,肯定了神父的崇高人格。茅盾在国民党严密文网中创作小说《耶稣之死》,突出耶稣与法利赛人之间的矛盾,肯定了耶稣作为革命者的悲剧、正义、进步,影射当时的政治斗争与社会批判。(37)[美]路易斯·罗宾逊著,傅光明、梁刚译:《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262页。朱湘在诗歌《哭孙中山》中以耶稣意象表现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与民族情怀:“救主耶稣走出了坟墓,华夏之魂已到复活的时光!”(38)朱湘著,梦辰编选:《等了许久的春天》,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受时代思潮影响,此类人物塑造占少数。
比较复杂的是兼有上述两种价值内涵的复调式塑造。作者基于现代科学知识与信仰情感体验,对基督教及其人物形象既非彻底肯定,亦非彻底否定,而是趋于神学感悟与科学理性的对话交锋,是文化转型时期对生命真实与价值的探索,也是内心无以解决的矛盾与困惑的深刻表现,折射出作者复杂的文化立场与微妙的精神状态。例如苏雪林的《棘心》,女主角杜醒秋在信仰问题上最终未臻精诚专注。她开始皈依神源于抗婚与对家庭危机的畏惧,后来生病住院时受到无神论的影响,转而反对神学,对世界与人生的思考并不透彻和成熟。在法国乡村,她受到马沙修女的熏陶,敏于人生的虚无,颇有深度,试图将宗教作为生活标准。杜醒秋发现科学有限、宇宙无限以及生命意义的创造性,但理性精神使她难以接受神学的真实,陷入科学与神学的矛盾状态。虽然后来因为母亲病重与婚姻危机,她再次皈依,但并未解决思想的不彻底性:“那是她的老脾气,平时将天主撇在一边,一到忧惶无措的时候,又抓住他不放,她又热心地来奉事天主了。”(39)苏雪林:《绿天·棘心》,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页。与民间女性玉官的嬗变不同,杜醒秋的理性精神、爱欲需求、神学依赖相混合,最终未达到纯粹之境(40)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105-108页。,而是保持着凡圣杂糅、人神对话的复杂信仰心理。从现代化造成的价值分化而言,这种“一人多信”(41)傅有德:《信仰而不皈依:“一人多信”现象解析》,《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第9-12页。的文化心理既有时代性,也有民族性。
杜醒秋的复调意蕴源自苏雪林的经历,巴金小说《田惠世》中的基督徒田惠世则是现代知识分子自觉开展心理分析与真理探索的结果,作者说:“我想写一个宗教者的生与死,我还想写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间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42)巴金:《巴金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4页。小说源自巴金的基督徒朋友林憾庐的生平(43)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178页。,熟悉的素材使田惠世表现出较强的宗教意蕴,他将基督教的优良信德与家国情怀、刚毅进取等中国文化精神相结合,可谓有鲜明的本土色彩的基督徒。但表现宗教非巴金的目的(44)巴金特别提醒读者不要因此将他视为基督徒。参见巴金:《巴金全集》(第7卷),第614页。,除了塑造该人物,他基于科学立场与人文理性对神教表示了比较明显的质疑和批判,主要体现为知识青年冯文淑与田惠世之间思想论辩式的对话(45)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181页。,最终神学话语与启蒙话语无法沟通而僵持,因此整体而言,小说表达了对基督教人物的矛盾心理。
综上所述,从文学史角度看,基督教人物的批判式塑造展开了科学话语、启蒙思想、道德理性、文学审美对基督教的认识及其再创造,拓展了文学的题材、思想与艺术经验,此类人物塑造注重信德的时代化与本土化,有利于发挥文学的思想教化功能。但无论否定、肯定还是矛盾,无论科学抑或人文,作者的宗教素养都不够精深,对神学缺乏鞭辟入里的认识与体会,复调式塑造可谓此心理之真切表现。艺术方面,较多存在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语言直白而少蕴藉,主要是作者对宗教理解有限,且批判意志较强,不能将之含濡转化为思想情感与艺术形象。
三、审美化运用
较之于宗教性书写和批判式塑造,基督教人物形象的审美化运用主要体现出文学的审美自觉,以此建构作品独特的审美价值,多见于小说。特征主要有三:第一,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所用笔墨不多,宗教性与思想性明显降低,凸显其作为能指符的形式特征,但其潜隐的宗教心理之触发与暗示功能可以有效激发读者的审美想象。第二,比较而言,参与审美建构的人物有强势与弱势之分,前者积极发挥审美功能,后者则消极建构文本。第三,审美参与弱化了人物形象的思想性,作品的审美价值是整体性存在,故此类人物形象的审美意蕴要密切结合文本方可呈现。
就强势参与类型而言,有的是基督教题材与人物形象兼备,有的则以人物形象兴发审美体验。前者如梁宗岱的诗歌《晚祷》,诗人以作为祈祷者的抒情主人公与上帝展开心灵对话,超越苦恼,趋向宁静辽阔、天人相谐的审美境界,在此诗的意象组合与情感空间中,“主”成为外在宇宙与心灵本质的人格化表现。孙玉石说:“‘主’与‘晚祷’只是一种宗教的外壳,以情理与思绪织成的失落的感喟才是此诗的真意。”(46)孙玉石:《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但抒情者如果没有基督教背景与人神对话思维,情感流动与意象创造恐难获致深广的审美想象、宇宙意识与终极意味。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其二)》塑造了背十字架的耶稣形象,为启蒙者表达基于苦难的审美创造充任能指符号。(47)任传印:《鲁迅笔下的宗教人物形象塑造》,《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97-103页。艾青的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通过耶稣形象传达了富有时代感与反思自己革命经历而来的理想信念与情感。(48)前贤对此有所论及。参见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321-322页;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第148-150页。夏莱蒂的小说《基督与猪》叙述耶稣不断投胎救赎人类,但最终绝望而去,寓含了对人性之丑的感喟与反思。(49)祝宇红:《“本色化”耶稣——谈中国现代重写〈圣经〉故事及耶稣形象的重塑》,第31-39页。冰心除了宗教蕴藉比较深的创作,也会以审美眼光塑造基督教人物,小说《相片》写施女士早年到中国教会学校工作,收养的女孩长大后转向爱情,颇感落寞的施女士在中西文化的交融撞击中回眸人生,体验到深重的虚无、悲伤以及对往昔恋情的追怀。小说旨在对施女士特定年龄段复杂惶惑的女性心理进行审美透视,基督徒身份与教会环境没有强烈的神学意味,而是为人物的审美内蕴提供了鲜明和陌生化的叙事元素。
未涉及题材的基督教人物形象以曹禺的《雷雨》为代表。剧作在序幕和结尾设置天主教教堂、修女与音乐,结合曹禺对宇宙神秘性的憧憬(50)曹禺:《雷雨·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4页。,人物的情欲苦闷、悲剧命运、罪感等文化母题的审美呈现,会发现天主教背景与尼姑绝非仅在故事层面制造陌生化情节,而是通过“上帝”视角兴发终极关切之感悟,提升读者的审美境界,在换位观照中获得净化(51)曹禺说:“‘序幕’和‘尾声’在这种用意下,仿佛有希腊悲剧Chorus一部分的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因为事理变动太吓人,里面那些隐秘不可知的东西对于现在一般聪明的观众情感上也仿佛不易明了,我乃罩上一层纱。那‘序幕’和‘尾声’的纱幕便给了所谓的‘欣赏的距离’。这样,看戏的人们可以处在适中的地位来看戏,而不致于使情感或者理解受了惊吓。”参见曹禺:《雷雨·序》,第13页。。如果说《雷雨》的悲剧使人感受命运的强大、神秘与可怖,天主教尼姑形象的沉静和谐则开启了超凡入圣的审美体验。再如徐訏的小说《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采用浪漫传奇手法叙述“我”作为心理医生对女主人公白蒂的治疗,侍女海兰为此牺牲,白蒂恢复正常后悲恸于海兰之死,进入修道院成为修女。白蒂的皈依看似具有神学意味的价值追求,但小说未表现她的心理嬗变与神性体验,着力渲染的是海兰的自杀及其遗书造成的悲剧与崇高,因此白蒂的皈依很大程度上是对海兰圣洁人格的向往,最终成为借助神学想象兴发的审美体验。还有鹿桥的青春题材小说《未央歌》,蔺燕梅的姑姑、神父等天主教人物从侧面烘托蔺燕梅单纯美好的性格与大学生热情迷茫的生活;蔺燕梅在“接吻事件”之后到教堂忏悔,在教堂工作,既缓和了激烈的感情冲突,亦启示读者想象蔺燕梅与小童后续情感发展的可能性,故天主教文化元素旨在建构小说的叙事艺术。
与强势参与相对的是弱势参与,此类基督教人物基本上只有附属价值,自身意蕴非常有限,故几乎不会影响作品的整体审美意蕴。例如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以近现代民族抗战为背景,通过蒋家儿女不同的思想与命运探索现代青年的人生道路,其中蒋秀菊与王伦是夫妻,都毕业于教会学校,但基督徒身份既没有体现为人物的性格心理与生活方式,也没有与整个作品密切相关。钱钟书的《围城》提及鲍小姐的未婚夫李医生是基督徒;张爱玲的《年青的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亦提及基督教人物,但皆为一笔带过,没有特别的形式与意味。
综上,基督教人物形象的强势审美参与体现了文学自身的终极关切意蕴,多传达罪感、悲剧、崇高、神秘、永恒等美感(52)参见张世英:《基督教与审美》,《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第13页;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36页;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第174页。,较之佛教人物形象审美参与所蕴含的苦惑、空灵、朴拙、神秘等审美体验,可谓特质明显,是现代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创造性运用,其含蓄与意境体现了对古典文学经验的接续,弱势参与则提供了富有文学史意味的人物形式。较之西方文学,上述审美化运用还不够丰富,文体形式涉及不够广泛,如通俗文学中有很多佛道人物,但少见基督教人物。这主要与文化积淀、时代思潮、作者的基督教修养、审美创造力有关,基督教文化元素作为能指符尚未普遍进入作家视野,至今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有较多创造性与艰巨性的课题。
将上述三种类型(53)文学形象是比较微妙和具有掺杂性特征的直观之物,笔者的价值分类着眼于作家的宗教文化背景与人物形象的核心意蕴,如果具体考察某个人物、作品或作家,则可能存在多种意蕴不同程度的混合,这与文本的复杂性、作家创作心理的复杂性及其动态演变有关,研究者文学接受中的视域融合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理解亦有影响。比较,可知宗教性书写普遍内蕴比较深沉,但体量不大,影响有限,缺乏与现代社会的深入广泛互动;批判式塑造虽然思想情感较为激切直白,对世界、人生与心灵的理解失之于简单,但比较契合时代主潮与民族文化心理;审美化运用体量较小,审美意蕴多元发散,受众较多。如与其他类别的宗教人物形象比较,会发现上述特点具有普遍性。需要指出,宗教性书写与审美化运用都倾向于无限之思悟,在文艺想象与宗教体验之合成以促进现代人解脱现世苦痛方面(54)王国维指出,文艺与宗教都可使人解脱现世之苦痛,故宗教人物形象可以成为这两种价值的有机融合。参见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有重要探索价值,更契合文学表现人之自由意志与超越精神的现代价值定位。时至今日,在扬弃传统宗教文化价值的新时代,它们各有其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