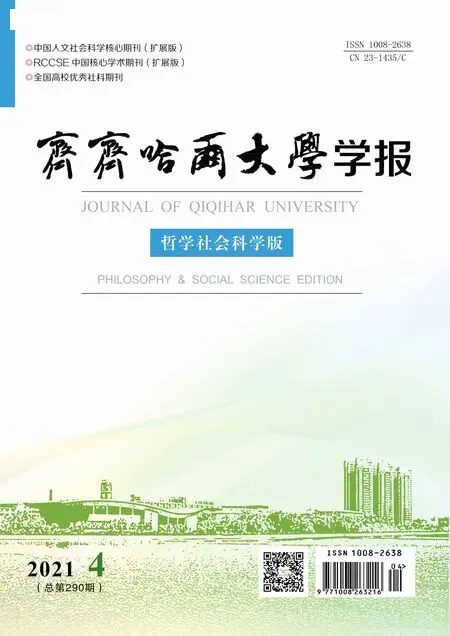《唇典》:立足俗世展现东北历史文化风貌
孙志伟,赵宪臣,刘省非
(1.齐齐哈尔大学 a.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b.教师教育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2.齐齐哈尔市新闻传媒中心,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5)
任何长篇小说的创作最初都有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决定着小说的走向,规划着小说的构思,也影响着小说的呈现方式。对最初发表在《收获》,后来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庆长篇小说《唇典》(2017)来说,它的立足点就是通过对俗世的书写来展现东北的历史和文化。
“唇典”一词在小说前“注”中解释为萨满传讲的家族和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便成为唇典,作者以“唇典”命题意为作品所描写的是在东北口口相传的民族史、民间史。正是这种史诗风格,小说问世以来,就显示出了巨大的影响力,即写出了一部活着的东北历史。细心阅读会发现,在反映东北历史方面,这部长篇小说可说是走出了一条独异的道路,它把有关东北的历史和文化完全融汇在了对俗世生活的再现和表现中,聚焦的始终是人物这个核心。书写历史中人物的命运、人物的关系、人物的纠扯,建立起一个复杂的人物谱系,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个显见特色。如果再辅以历史和文化的渲染,把人物置于激荡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之下,这就是一部充满了时代演变、内容厚实的长篇小说。对这样的长篇小说进行深入分析,有必要把在俗世中紧密纠缠的人物与历史与文化的关系做出剥离,区别之后的条分缕析,将更有助于认准并看清小说的面目。
一、俗世中的人物载沉载浮
写出俗世中人物命运的载沉载浮,对《唇典》来说做到了一番苦心孤诣的经营,这样的经营首先就在表现在了小说的结构上,这就是一部以人物结构起来的小说。这样认定的理由首先就体现在了小说的章节结构上,小说的章节以满语“腓凌”来命名,在满语中“腓凌”是“回”、章节的意思。十个“腓凌”就是小说的十个回目,这些回目的醒目所在就是人物,回目确定了哪个人物,这一回目就会以这个人物为小说叙事对象,交待出这个人物的来龙去脉、所经历之事,构成小说人物的人生之种种。譬如“头腓凌”的郎乌春,就是开篇以郎乌春这个人物为主体,开始了小说的讲述。
(一)“非常态”的人物关系
就俗世中写人物来说,小说把人物置于生活的变化之中进行了曲折呈现。小说虽然人物众多,但主要人物集中在了郎乌春、柳枝、满斗等人身上,围绕着这三个主要人物衍生出的李良、王良、苏念、韩淑英、娥子等人也是构成小说不可分割的人物,其中的关系既相互缠绕又有着各自的命运走向。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一户之家的郎乌春、柳枝、满斗串联起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如果说这是一部以家庭人事为主线的家庭小说也是成立的,只不过这个家庭有别于其他家庭的地方过于复杂也过于疏离。这个在小说中松散的家庭,对应着时局的混乱,是一个家庭在时代大背景下的随波逐流。
以家庭之变折射时代之变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并不鲜见,鲜见的是写出了这个家庭人物关系的复杂,写出了俗世生活中的“非常态”,这种“非常态”就是人物在情感上的彼此伤害、彼此隔阂又彼此走近、彼此相融。这种“非常态”就是人物对自身命运的无法掌控,只能在时代的洪流中载沉载浮。小说中郎乌春与柳枝的关系就经历着这样“非常态”的曲折,柳枝本来是郎乌春追慕的对象,为得到她还曾求母亲去柳枝家提亲,可就是因为柳枝遭受了自己的人生不幸,被土匪王良强暴未婚先孕,郎乌春在娶了柳枝后就开始冷落她,形成了他们之间有名无实的婚姻关系。情感上的不冷不热,让彼此很长一段时间若即若离,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经历上的复杂多变,才让这对夫妻最后消泯了恩怨真正地相亲相融。
在“非常态”的曲折中,一家之主的郎乌春还牵扯到与革命者韩淑英的关系,这也是郎乌春加入保乡队开始从军经历之后发生的另一段情感故事。在这个情感故事里,女革命者韩淑英对郎乌春的解救,以至二人在革命遇挫后的逃亡生涯,为他们情感交往提供了机遇。正是在逃亡生活中,这对男女有了女儿娥子,并出于继续投身奋斗生涯的需要,把娥子送给柳枝抚养。这样一来,事实上这个家庭在养育子女上两个主要当事人的恩怨已经扯平,儿子满斗与女儿娥子在血缘上分别为异父和异母的关系。这个家庭的复杂,为小说展开了多条叙事线索,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身上都有各自的故事,小说也是在家庭成员的故事讲述中丰满起来的。
(二)模糊的人生面相
这些故事包括郎乌春的从军经历,柳枝与组织的关联,满斗的萨满学徒史、抗联活动以及后来在政治运动中的命运遭际,娥子短暂的革命生涯。在郎乌春的从军经历中虽有着诸多偶然,但他作为抗联师长转战山林、坚持东北抗战却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书写,这也是郎乌春从军经历中最重要最浓重的一笔。这个从旧军阀的军队里走上抗日战场的旧军人,在日军铁蹄蹂躏东北的岁月里经历了抗战的洗礼,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苦。小说特别从满斗的视角写出了郎乌春转战山林的非凡经历,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与凶残的敌人殊死抗争,抗联当年所经受的困苦都在小说里得以披露。按说这样的郎乌春应该是以英雄的姿态跃入人们眼帘,但吊诡的命运却让这个英雄落入了耻辱之中,在最后的战斗中这个曾经的抗联英雄被迫放下武器,归顺了日本人,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尽管这种归顺并非真正的归顺,只是一种表面的应付,但仍有损于这个英雄的名誉,他后来的命运遭际也由此被改写。
柳枝的命运波折在小说中也有自己的运行曲线,与他的丈夫郎乌春相比其悲苦程度并没减轻。且不说在郎乌春离去的那些日子里她独自一人在马滴达为抚养满斗独撑生活的艰辛,就是在后来为救满斗卷入了争斗之中,她也是随着风雨飘摇,无法安身立命。就说她奉组织之命,暗杀自己丈夫郎乌春的举动,就已经让这个俗世中的平常妇女力有不逮,面临着心理的煎熬。她的命运在当初被土匪王良强暴时就已铸下,后来所生发的一切关联不过起着印证作用。不过这个人确是个称职的母亲,在叙述者满斗的眼里,柳枝要比郎乌春高大得多。从满斗身陷匪巢柳枝的四处求救,到满斗空降摔傻柳枝的寻找及精心呵护,都能看出母爱的非同寻常。
俗世里的满斗所走过的道路与其父其母紧密相联,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举足轻重,即是作为叙述者出现,也是作为小说人物出现。这个人物从出生起就有通灵的一面,有迥异于他人的视物功能,这一特异功能也影响着满斗的命运,先是被大萨满李良收为徒弟,后来又与花瓶姑娘苏念身陷匪巢,再后来又做了抗联的战士,直至经历了解放后种种磨难。作家把这个人物是作为清醒者来塑造的,满斗的清醒在于他知道自己的有所承担,正是有所承担他才走上了寻找花瓶姑娘的曲折路途,也正是有所承担,他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抗联炸毁飞机场的任务,以及在为他人蒙冤受过时能坦然处之。这样的人直到最后还保持着清醒,满斗毅然踏上寻找灵魂树之举,再次说明他对现世的洞悉,一个丢失了灵魂的世界,最需要的就是找回灵魂、妥善安放。
小说里的俗世充满混乱,与这个混乱的世界相对应,俗世里的人生也是混乱、动荡和不安定,这种混乱不仅体现在了人物关系上,也体现在了各自的人生上。每个主要人物都经历了载沉载浮的命运变迁,在这种变迁中,人物的面目无法真正的认清,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面相。就历史上郎乌春、柳枝、满斗都曾参与了抗联活动而言,他们都是英雄,但在小说里他们又都没有享受到这种英雄感,从来没有以英雄的面目出现,相反却磨难重重,被误解被打击被整肃,始终处于混沌、模糊状态。评论家张晓琴在《在历史中溯源--“70后”小说隐秘路径》一文中曾谈到:“大的历史书写往往造成了对个人的遮蔽,个人的重要性在其中被弱化。”[1]《唇典》在大历史的书写中,并没有造成对个人的遮蔽,个人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弱化,但也没有明朗化,整部小说就主要人物来说还在给人分不清道不明之感。
二、俗世中的历史变幻起伏
《唇典》有一条在线性发展中贯穿其中的历史脉络,这个历史脉络从民国初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如果划分出阶段,则可看到军阀混战、日军侵华、抗联血拼、国共开战、文革动荡、改革初期等一幕幕历史的上演。伴随着历史的变幻起伏,人物也在历史中随波逐流,呈现出各自的命运走向。
(一)动荡人生演绎动荡历史
在小说中,历史是无法从故事情节中抽离出来的,它总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存在,动荡的历史也只有通过人物的生活动荡来体现。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历史动荡最明显地表现在了郎乌春的身上,这个本分的农家子弟就是受到动荡历史的裹挟,卷入了一场场争斗之中,历史的阶段性通过这个人物的出现,而有了清晰的彰显。其中的深刻历史印记都集中了他的从军经历上,从一开始的保乡队员到驻军团长再到抗联师长,郎乌春完成了自己的从军史,这个从军史恰好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他的从军实属身不由己,是那个阶段的历史推着他走向战场,这些战场包括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他也在军阀的混战中身份一变再变,与多个军阀人物扯上了关系,如果说军阀混战史是一部民国社会的荒诞史,那么这样的荒诞史也是由郎乌春的从军史体现出来的。这些战场也包括郎乌春作为抗日救国军的一员,转战白山黑水的那段历史,这段历史应该属于郎乌春个人的光辉历史,构成了中国抗战史的一部分,历史的起伏也在这一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郎乌春个人的这段抗战岁月,可看成是整个东北抗联活动史的浓缩,尤其是在冰天雪地里的转战,那种艰辛备尝、那种身陷绝境,与我们所知悉的那段抗战历史构成了重叠。这个人物活在了历史中,也活出了自己的本色,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小说中的历史变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物的贯穿,投身于历史的大潮中也是小说人物不可避免的宿命。这一点在柳枝、满斗这些人物身上也有体现,尤其在满斗身上体现出的历史变幻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已经切近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生活,属于当代史的范畴。历史的这种巨大跨度,通过对人物的叙述而成为可能,小人物与历史在小说里形成了同构,认识人物同时也是在认识历史。
(二)变幻事件映射变幻历史
在历史的变幻方面,小说除了通过人物演绎这种变幻,还通过一些事物或者某一物件来映射着历史的某个节点,譬如以火车在小镇的出现指涉世事的变化。就东北来说有一条最著名的铁路就是中东铁路,这条铁路的修建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时代特征,小说开头火车开进白瓦镇,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描述,还鲜明地将人们的视线引入了当时历史情境。白瓦镇人最早的火车印象来自朝鲜人拎着的猪皮匣子,里面装着的放映机让乡民在电影屏幕上认识了这个庞然大物,当初屏幕上呼啸而出的火车还惊吓到了现场观众。这种曲笔写历史的方式,有点像收藏家收藏逝去年代的小物件,每个小物件都能让人联想到历史。
就历史本身来说,有着多种多样的呈现方式,从哪个角度进入历史,也取决于作家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从小物件入手来认识和进入历史,折射出历史的变幻,可起到更为生动地呈现历史的效果。
(三)复杂的环境展现复杂历史
在小说的环境描述上,也能看出与历史的互动。《唇典》中的环境描写是结构小说的重要一环,这种重要就是把环境描写与小说的情节叙述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起到了共同推动情节的作用。这一点颇为类似于著名作家阎连科所提到的“自然情景”说,他在谈到风景描写时曾做过分类,说过这样的话:“我把小说中那些华丽、多余、累赘的关于环境与自然的描绘称为风景描写或风光描写,而把那些与人物、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甚至说没有那样环境描写,就没有那样的人物与某种思考的对小说中必不可少的环境与自然的描绘,称其为‘自然情景’。”[2]按照这种“自然情景”说索解《唇典》中的历史变幻,每当写历史陷于混乱动荡之中,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也紧随着这段混乱而得到了混乱的渲染。写到街景是如此,写到田园也是如此,在写到抗联的那段历史时更是如此,严酷的环境与严酷的历史相关连,营造出了一片肃杀和荒冷。就是写到江水开江时的暴怒也预示着时局的即将变化,郎乌春与江水的搏斗也是他后来在动荡的历史中翻滚的提前预演。所说的“自然情景”在《唇典》里,景就是环境描写,情就是历史的变幻。
凡是有着历史纵深的小说,都要在如何呈现历史上有所作为,不拘泥于已有的历史呈现方法,以多种手段来呈现历史这也是《唇典》这部小说的引人注目之处,这样的呈现也使僵硬的历史更显活泛,从而为小说人物提供了行动和命运演进的舞台。
三、俗世中的文化有灵失灵
东北的文化一向有着自己独有的组成和特色,这个塞外的荒寒之地在漫长岁月中所形成的民族文化,是与他们的生活密切关联的,是从生活中来又回到生活中去的产物。《唇典》里所涉文化是世代生存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满族文化,在这个民族的文化里相信万物有灵,围绕着万物有灵催生出来的萨满文化是这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正如有学者所说:“萨满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白山黑水间各民族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其对世界独具个性的诗意认知,在这个充溢着神秘色彩的世界,宿命和神祗真实存在,神谕通过萨满之口实现对人世的评判和仲裁。”[3]
(一)具有民间共识背景的萨满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唇典》,这部小说也是一部有关萨满的小说,其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李良和满斗,一个是真正的萨满,一个是命定的萨满。作为真正萨满的李良是一个神性存在,这种神性一方面表现在他的“不死”,一方面则表现在他的“救人”。他的不死不仅是承继了铁匠家族的萨满衣钵,而且是死过了的人所以不死,他的家族浴火经历,已经为他注入了坚不可摧的魂魄。这就有了李良即使在为伪满皇帝溥仪做家祭时因窥破奥秘而招来杀身之祸,但仍然游走于世间,即使后来被文革中的革命小将从坟墓里掘出来,也能说显形就显形,说无踪就无踪来去自由。
萨满文化中有灵的体现,都是由李良萨满来完成的,这个真正的萨满作为灵魂附体的存在在小说中肩负着重大的使命,这个使命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小说藉助‘幽灵’的神秘性、非常规性,展现了被‘现代’‘历史’遮盖的无限的奇异性和丰富性。”[4]李良萨满的救人也是这种奇异性和丰富性的表征,他的救人主要是在柳枝面临绝望境地时施以援手,以一个萨满的无边法力瞒天过海,解除了柳枝失身于人又难言于人的苦楚。这时的李良萨满是悲天悯人的化身,他的良善举动包蕴着萨满文化的救赎意义。此后的救人举动一再延续,在满斗的成长过程里他也多次现身,做出了唯有一个真正的萨满才会做出的拯救之举。
小说中的满斗之所以是命定的萨满,是因为在他出生之后就被李良萨满所倚重被收为弟子,他自身也有过人之处,天生就有能辨出鬼魂、夜能视物的能力。他的这种特异能力,助他看出了许多真相,也助他完成了抗联交给的、在别人看来无法完成的任务。但这个命定的萨满,却不想成为真正的萨满,尽管有机会摇身一变就能传承起萨满遗失的精髓,但满斗仍然选择了抗拒。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有些人想打萨满文化的主意赚个盆满钵满请他出山,也被满斗断然推拒。但他骨子里仍然依循着李良萨满的悲悯之心,代人受过、替别人担当罪名即使吃尽了苦头,也独自默默承受,有关萨满的深层认知依旧了然于心,以不是萨满的萨满存在,行走于漫漫红尘。
萨满文化是东北民间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有着相当深厚的民间共识,《唇典》在立足俗世回看历史时,不可能绕过这一重要的萨满文化,事实上,作家刘庆一开始就把萨满文化当成了小说的重点经营,因而在他笔下呈现出的萨满文化既有隐秘的揭示,也有着不同于他人的书写,对丰富人们对萨满文化的了解及洞悉,可谓别有洞天。
(二)具有民俗风情画意义的满族文化
《唇典》在萨满文化之外,对东北的节庆文化也做了融入故事情节的展示,那些东北的传统节日风俗,几乎都在小说中被提及,有些是作为推进情节的需要而着重渲染的,有些则是简单描述或一笔带过。小说中得到重点渲染的节庆文化是灯官节,也就是正月十五的闹元宵。小说里两次提到了灯官节之变,第一次灯官节选出的灯官老爷还是郎乌春,也是在灯官节游行中,郎乌春遭遇了土匪抢劫,才有了他后来的命运遭际。第二次灯官节之变也与第一次灯官节有内在联系,第一次灯官节的抢劫就是当过灯官娘娘的王良一手策划,第二次灯官节则是为了消灭王良的先遣军,其中郎乌春的策划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两次灯官节虽然并非这个节日风俗的全面再现,但有关灯官节的大致情景都有所披露,浓浓的节日文化气息在文字里流淌。
小说中的树文化也是作家刻意突出的东北文化之一,在满族人的认知里,每一棵树都有灵魂,都承载着生命的今昔过往。所以种树就成了老年满斗甘愿付出的日常劳作,他为每个逝去的亲人,及那些与自己有过关联的人都种了一棵灵魂树,并日夜陪伴着这些灵魂树过着安闲的日子,直到这些灵魂树被盗伐。也是在灵魂树被盗伐之后,满斗才踏上了寻找灵魂树的漫漫长途。在失灵的年代里寻找灵魂树,也成了小说最意味深长的隐喻。
小说中的文化意含往往规约着小说的高度和深度,就《唇典》来说,萨满文化以及对灵魂树的寻找,构成了小说有灵与失灵的冲突,而这个有灵和失灵,绝对不是向神秘文化表达敬意或者惋惜,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反观。处于失魂状态下,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是一种病态、一场悲剧,只有重新找回失落的灵魂,社会和个人才能健全健康地向着光明的前景进发。
综上,在分别从俗世中的人、俗世中的历史、俗世中的文化等方面对刘庆的长篇小说《唇典》进行了分析之后,还有必要重申,这三个方面在小说中是紧紧融合在一起,也是在小说情节中共同推进的,这样分别孤立起来,并有所侧重的拆分,也是为了更清晰地阐释小说的需要。正是建立在这三者的融合书写之上,才使《唇典》成为了“近年来中国长篇叙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是奉献给中国文坛的沉甸甸的具有史诗品格的力作。”[5]所谓的作品大格局,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对人物、历史、文化的把握,在作品中把握的精当恰切,作品就会立得住、传得开,刘庆的《唇典》在问世之后能引发热议,已经以自身的实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有了人物命运的载沉载浮、历史和文化的含量,《唇典》还会持续地在读者中口口相传。
——现代牙刷的由来
——以吉林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