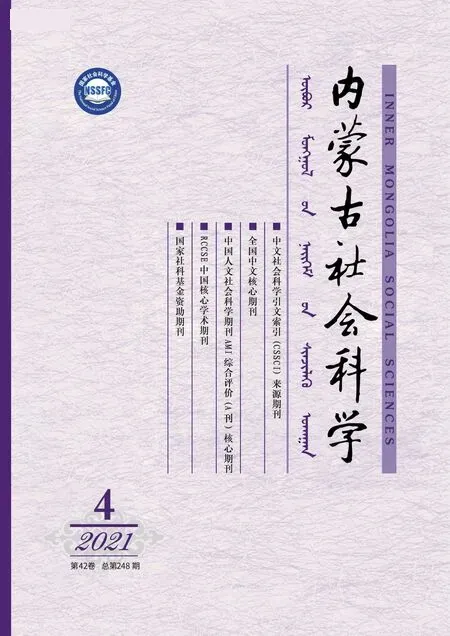未成年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反思及其实践路径
刘小庆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4)
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该部法律以“未成年人福利的实现”为立法宗旨(1)参见姚建龙《〈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述评与完善》,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0年第2期。,意图通过细化监护人责任、增设网络保护、强化学校保护、引入强制报告制度、明确政府职责以及特定人员从业禁止、司法保护全覆盖等内容的完善,形成“国家、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全方位保护格局,提升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水平。然而,该部法律只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纲领性文件,无论立法者考虑多么周详、条文内容如何细化,也不足以应对社会生活中复杂多样的侵害未成年人事件,尤其是严重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益的刑事案件,该法虽对未成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有所涉及,但从整体而言仍难以做到司法保护的全覆盖。鉴于刑事案件程序与未成年被害人的实体性权利、程序性权利紧密相关,因而“司法保护全覆盖”目标的实现亟须《刑事诉讼法》的及时介入和专门保障。
在刑事司法领域,由于长期受到“以客观真实为本”的理念指导,我国刑事诉讼一直遵循着“强职权主义”的发展理念。无论是被追诉人还是被害人,均被误认为是服务于打击犯罪的手段和工具,其诉讼权利和人格尊严长期被办案机关所忽视,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被害人的诉讼权益往往被认为其蕴含于国家追诉的利益之中,因而没有得到立法和司法部门应有的重视。为切实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确立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从而使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工作于法有据。(2)参考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82条的解释可以发现,将被害人纳入“当事人”范畴的唯一目的就是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力度。参见胡康生、李福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95页。被害人从“参与人”到“当事人”身份转变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其诉讼境遇、保障其诉讼权利,因而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需要“当事人”的地位为其提供法律依据,“当事人”地位的真正实现也需要通过诉讼权利的全面落实加以体现,二者互为“充要条件”。因此,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工作可以从其诉讼地位的角度予以考虑。基于上述理由,笔者从文本和实践入手考察未成年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落实情况,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未成年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新理论,进而就该理论的实施提出具体举措。(3)本文讨论的对象仅限自然人被害人,范畴仅限于公诉案件,本文中的未成年人与国际公约的儿童是同一概念。
一、未成年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实践审视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并未进行单独考量,只是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作了统一性规定,且被害人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仅被视为“诉讼参与人”,直到1996年修法时才将其纳入“当事人”范畴,2012年、2018年《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也延续了上述规定的做法。未成年被害人这一群体在司法实践中的“当事人”地位是否得到了充分体现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一)司法实务:未成年被害人异化为“工具人”
未成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属于“当事人”,理应享有《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长期受实用主义的影响,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实际上处于“工具人”的地位,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围绕着探究案件事实真相这一预设目标而展开的。
一方面,侦查取证工作成为第一要务,而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权被忽视。面对我国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频发,公安机关在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与发案规律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加强了与检察机关的密切配合,意图在此基础上形成办案合力,尤其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公安机关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了“一站式取证”的试点工作,从接到警情的第一时间起,公安刑侦部门、技术部门与检察机关同时到场开展相关证据的固定和提取工作,有力地提升了案件的办理质量。但由于“一站式取证”尚处于试点阶段,且在试点地区的选择上也经过了深思熟虑,所以在这些地区办案的规范性相对有保障。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个别偏远落后地区,难免会受到人力、物力、财力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同时,办案机关迫于相关考核指标的压力,“破案”往往成为基层办案人员的第一要务,致使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被忽视的情况屡见不鲜。据实务部门反映,一些办案人员在未成年被害人所在的村庄、社区、学校开展物证提取、案件调查等工作时,经常会开警车、鸣警笛、穿警服、闪警灯,毫不避讳众人,在无意中泄露了被害人的隐私。[1]另外,虽早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就要求“询问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但部分基层派出所由于女性工作人员较少,难以进行合理调配,而由男性工作人员代劳的情况也较为常见。(4)有实务工作者通过调研发现,部分地区女性工作人员参与询问女性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比率只有10%左右。参见王春风、李凯、赵晓敏《我国未成年被害人询问工作机制构建》,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5期。尤其是在一些性侵害案件当中,询问内容比较敏感,男性工作人员的参与极易加重被害人家属的顾虑、徒增未成年被害人内心的恐惧。尽管存在各种客观上的制约因素,但办案机关对未成年被害人人格尊严权保障的主观意识不强仍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定罪量刑工作摆在优先位置,未成年被害人的参与性诉求被剥夺。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被害人有权出席法庭审理活动,但基于司法实践所形成的“职权文化”,法官通常认为刑事庭审是决定被告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公益活动”,与被害者个人并无直接关系,因而法庭忽视乃至阻碍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情况并不少见。即便被害人参与了庭审,实际上也是作为控方证人发表证人证言,而其作为“当事人”所享有的报应诉求和参与性权利通常会被剥夺。尤其考虑到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认知能力、接受质证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等与成年人相比尚处于弱势地位,其无论是作为被害人或是证人出庭,均可能会增加庭审的不可控性,妨碍审判程序的顺利推进,甚至有可能削弱控方证据的证明力,进而动摇控方的有罪证明体系。出于上述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18条明确将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出庭的条件限定为“确有必要”。在立法谨慎态度的明示与法官对于是否“确有必要”的自由裁量权相结合的情况下,未成年被害人是否作为证人出庭尚且受到了严格限制,其“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现便更加困难了。
(二)立法内容:未成年被害人成为“被遗忘”的人
未成年被害人作为未成年人,在法律知识、诉讼行为能力以及心智成熟度等方面与成年人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因而理应得到立法机关的特殊体恤和充分关爱。然而,由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长期被忽视,进而造成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呈现严重失衡的状态,“未成年被害人”成了“被遗忘”的人。
首先,关于“未成年被害人”的立法内容呈“碎片化”分布,缺乏权益保护的专门性法规。目前,未成年人权利的保障工作已经受到我国立法与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并在《刑事诉讼法》《刑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反家庭暴力法》《义务教育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得到了明确体现。但上述法律法规中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条文明显呈现碎片化分布,即均有所涉及但却规定不多且内容相对粗浅,可操作性较差。西方国家高度重视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工作,并大多通过颁布单行性法规的方式对被害人权利进行专门保护。例如,新西兰于1963年制定颁布了世界上首部针对被害人保护的专门法规——《刑事被害人补偿法》;美国国会于1982年、1984年、1990年颁布了《被害人及证人保护法》《犯罪被害人法》《被害人权利与复原法》等专门法规;德国于1986年、2004年通过了《被害人保护法》《被害人权利改革法》。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尚未出台专门针对被害人保护及补偿的法律法规,因此,“未成年被害人保护法”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被害人的权利设置多以“成年人”为视角,缺乏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单独考量。《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因而在应然层面,被害人拥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如报案或控告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知情权,等等。但仔细考察上述权利的内容后发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往往以针对“成年人”式的法律条文加以保护,未能体现出其具有的特殊性。由于缺乏针对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障的专门规定,司法实务中仅凭办案人员自我权衡,其随意性较大。以隐私权为例,虽然《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个人隐私”尚无具体解释,通常仅从被害人是否遭到性侵、被告人是否成年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57条),对于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是否应当或可以不公开审理尚无明确规定。由于法官对“个人隐私”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司法实务中将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进行公开审理的情况也较为常见,由此可见,我国立法尚缺乏对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专门考虑。
再次,当前的未成年人权利保障以“加害人”为中心,“未成年被害人”成为被“遗忘”的人。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实践呈现出强职权主义的发展趋势,被追诉人实际上成了刑事诉讼的“客体”,致使对其人权保障不足。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被追诉人的诉讼境遇,《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借鉴对抗制诉讼因素开始,就始终致力于打造一部“被追诉人权利法”,从而使被追诉人成为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的中心。受这一理念的影响,2012年和2018年《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但该部分内容并未突出“被害人”的价值取向,几乎所有的权利架构均是围绕“加害人”展开的,如第277条中对案件承办人员的特殊安排、第278条中对法律援助权的保障以及第285条中对不公开审理范围的划定、第286条中对犯罪记录封存等隐私权的保障,等等。关于未成年被害人,仅有第281条中关于“询问未成年被害人”的规定。继续梳理《〈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可以发现,目前对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如其中第558条要求对未成年被害人出庭履行作证义务提供特别保护,第559条要求对未成年被害人个人信息进行保密,等等。但总体而言,其保护力度仍有所欠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获得法律援助方面存在严重失衡的情况,前者适用强制辩护规则(第564条),而后者则需要满足“经济困难”的条件(第565条)才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无论是司法实务中将未成年被害人异化为“工具”,还是在立法内容中无意识地将其“遗忘”,都在一定程度上降格了未成年被害人的主体地位,稀释了其“当事人”的权利内涵,矮化了刑事诉讼“善”的内在品质。未成年被害人在实务与立法层面的境遇进一步表明,一般“当事人”地位的简单套用无助于提升其诉讼地位、落实其诉讼权利。
二、未成年被害人“特殊当事人”地位理论的提出
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理论探讨最终应当落脚于其合法权益的具体实现上[2],但立法赋予的“当事人”地位未能改变一般被害人诉讼权利被虚置的局面,因而更不可能对改善未成年被害人“工具人”的现实定位和“被遗忘”的立法境遇有所助益。因此,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具体实现应当在充分考量其身心特点和案件具体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关于未成年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理论。
(一)主体特殊性:未成年人的“被害性”较高
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方面与成年人相比均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而其容易遭受外界的侵害,即“被害性”相对较高。对此,奥地利学者琼·格雷文提出:“被害性是指根据内在、外在两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使人能成为被害人的那种特性。”[3](P.31)就内在因素而言,未成年人的“被害性”可以从生理、心理两方面结合具体的年龄阶段(5)按照发展心理学理论,未成年人根据其年龄跨度可以分为婴儿时期(2岁以前)、学步儿时期(18个月~3岁)、学前期(2~5岁)、童年中期(5~12岁)以及青春期(12~18岁)。参见大卫·R.谢弗、凯瑟琳·基普《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5页。对其进行分析。
一方面,未成年人的身体尚未发育成熟,其犯罪抵御能力和危险自救能力相对较弱。在婴儿时期(2岁以前)和学步儿时期(18个月~3岁),婴幼儿只具备简单的抓握、咀嚼、爬行、啼哭等行为能力,其并不具备主观上诱导他人实施犯罪的可能,但也不排除某些偶发性因素导致其遭遇犯罪的侵害,如实践中发生的盗抢、遗弃婴幼儿的案件。学前期(2~5岁)的儿童生性活泼好动,其活动空间由家庭扩展至外界,但其仍不具备抵御犯罪和危险自救的能力。童年中期(5~12岁)的儿童虽然具备了一定辨识危险的能力,但与成年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其抵抗侵害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外界的侵害。青春期(12~18岁)的男生,由于其骨骼硬度与肌肉力量逐渐增强,因而具备了一定的犯罪抵御能力和自救能力,但这一年龄段的女生仍然较易受到侵害。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犯罪认知能力和自身的心理调节能力相对较差。在婴儿时期和学步儿时期,婴幼儿的大脑和神经细胞尚处于发育初期,只能通过嗅觉、味觉、触觉初步感知外界,还不具备记忆、思维、复杂情绪的表达能力,因而完全不具备犯罪认知能力。学前期儿童大脑的生理结构日渐成熟,但尚不能正确区分潜意识与意识、想象与现实,其对犯罪的认知能力也处于初步形成期。在童年中期,儿童的机械记忆能力胜于其逻辑分析能力,因而对犯罪的认知能力相对较弱,极易受好奇心的驱使而相信陌生人,在受害以后不能正确面对并及时告知老师或家长,导致其重复被害性较高。青春期也被称为“第二心理诞生期”,这一阶段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逻辑分析能力、情绪控制能力逐渐趋于成熟,具备了一定的犯罪辨别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但青春期的未成年人由于其独立观念逐渐形成、自我意识逐步觉醒、自尊心显著增强,由此导致男生的性格容易冲动、叛逆、偏激,做事不计后果,容易诱发被害事件的发生;而女生的内心相对比较脆弱,在受到侵害之后不能自我疏导和调节,在形成心理创伤之后所需要的恢复时间较长。
(二)案件特殊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类别较为集中
目前,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治理工作形势较为严峻。2017至2019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犯罪嫌疑人12.14万人,起诉16.11万人。其中,2019年批捕4.76万人,起诉6.29万人,较2017年分别上升了40.76%和32.62%。[4]通过对上述数据的深入剖析可以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不仅在数量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具有异于普通刑事案件的显著特征。
第一,强奸、强制猥亵、猥亵儿童三类案件占比较高,发案的类别相对比较集中。与普通刑事案件中侵财类案件占比较大有所不同的是,未成年人被害案件的发案类别中,强奸、强制猥亵等性犯罪案件占有较大比重。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至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奸未成年人,猥亵儿童,强制猥亵、侮辱未成年人三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总数分别为10603人、13445人、19338人,2018年、2019年同比上升了26.8%、43.83%。其中,起诉的强奸未成年人的犯罪嫌疑人分别为7550人、9267人、12912人,2018年、2019年同比上升了22.74%、39.33%。检察机关起诉这三类犯罪的人数占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人数的比例也由2017年的22.34%上升到了2019年的30.72%。[4]从地方的情况看,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数据为例,其全省侵害未成年犯罪的案件中,发生在农村和乡镇的案件占比接近70%,其中,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占比高达67.7%。[5]
第二,教师、亲朋、邻居等熟人作案的占比较高,很多案件的加害人与被害人的社会关系相对比较亲密。与普通刑事案件发案的随机性相比,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犯罪分子主要是利用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师生关系等接近被害人,且未成年被害人由于自身对犯罪的认知能力不足,某些情况下不能正确区分正常的关爱行为和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在加害人的威逼利诱下,受害人通常不会及时向家长或老师告知其受害的事实,若没有留下明显的外伤或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在家人、老师未能觉察的情况下,其存在多次被侵害的可能。据中国少儿文艺基金会女童保护专项基金会对典型案例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性侵害女童案件中熟人作案占比达到70.43%,且该比例在2014年一度高达87.87%。(6)参见《“女童保护”2019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011202459057937,2020年5月18日,2020年10月2日。再如福建省惠安检察院通过对2016年以来受理的审查起诉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数据统计后发现,性侵害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比例高达77.42%。[6]
第三,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概率偏低,致使办案机关对间接证据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以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为例,此类案件的证据存在“两少”的情况。一是涉案的关键物证较少。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中熟人的占比较大,导致其作案的隐蔽性较高,加之部分未成年人的年龄偏小,对犯罪的认知能力较弱,被害后未能在第一时间告知家人或老师,致使物证灭失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北京市发生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有超过半数的被害人在初次遭受性侵害后,并未及时告知监护人,导致涉案的关键证据未能及时被办案人员固定和提取,进而增加了案件办理的难度。[7]二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嫌疑人数量较少。在大量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很多犯罪嫌疑人利用未成年人第一时间固定证据能力不强的弱点,尤其是在其选取的侵害地点较为隐蔽时,则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拒不如实供述的情况较为突出,因此,办案人员不得不加强对间接证据的提取力度。例如,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至2016年,北京市发生的802件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的案件多达205件,占总数的25.5%。[8](P.24)
(三)维权特殊性:对未成年人进行专门保护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意义重大,但由于部分家庭和学校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不强、在资源投入和安全教育等方面有所欠缺,同时受生活环境、教育环境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未成年人保护现状还不甚理想。对此,国际社会包括我国均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作出了专门规定。
对未成年人权利进行特别保护是国际社会已经达成的广泛共识。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第25号决议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目前,其已成为缔约国最多的国际性公约,其前身可追溯至1924年国际联盟通过的《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该宣言的通过使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第一次成为世界性的议题,且主要从五个方面要求缔约国保障未成年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这意味着未成年人的权利保障工作成了一项国际性的义务。总之,《儿童权利公约》第一次全面规定了未成年人的权利类别,并细化了相关内容以增强公约的可操作性,标志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保障已经引起我国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后备力量,对于国家的繁荣发展与家庭的和谐稳定意义重大。为此,我国分别于1991年、1999年专门制定并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法律。同时,《宪法》《义务教育法》《劳动法》《刑法》《民法典》《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等司法解释均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布局已经初步形成。
综上所述,由于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与成年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其极易遭到外界甚至是熟人的侵害,加之未成年人在遭受侵害之后固定证据的意识较为薄弱,导致此类案件中加害人的认罪率远低于普通刑事案件,案件性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此外,鉴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和我国立法机关的高度认同。因此,赋予未成年被害人“特殊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必然性。然而,由于司法机关并未认识到未成年被害人作为“特殊当事人”在主体、案件、维权等方面的特殊性,导致对该群体在司法实务中知情权的保障相对滞后,其隐私权也尚未得到完全的落实,人格尊严权常常被忽视。同时,未成年被害人参加法庭审理的权限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刑事和解的自主决定权也通常由监护人代为行使。因此,当前的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障工作应当严格贯彻“特殊当事人”理论,从而兼顾其权利内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三、未成年被害人“特殊当事人”地位的实践路径
未成年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的“特殊当事人”,具有不同于一般“当事人”的特征。一方面,未成年被害人作为“案件当事人”理应享有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当得到公安司法机关应有的尊重和切实保障。另一方面,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相比,在维权意识、维权能力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应对其权利加以优先和特殊保护。因此,未成年被害人“特殊当事人”地位的实现需要在充分照顾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与案件特点的基础上,从对其所涉及的诉讼内的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充分尊重,以及对其进行特殊保障的视角进行落实。
(一)对未成年被害人实体性权利的充分尊重和特殊保障
首先,对未成年被害人知情权的优先落实。未成年被害人作为犯罪手段与结果的直接承受者,是刑事追诉程序发动的始源性要素,具有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当事性”,其权利的保障理应得到优先落实。当然,在所有被害人诉讼权利中最基础的当属被害人的知情权。被害人知情权是指被害人有权知悉其本身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应当通过何种程序参与诉讼、案件的进展过程及处理结果如何等情况的权利,而负有提供信息义务的一方应以合理的方式为其提供信息并对这项权利加以保障。[9]“知情权不是一项一般性的子权利,而是其他权利得以正确行使的先决性权利。”[10]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被害人的知情权却难以得到保障,如在2008年发生的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习水公职人员性侵幼女案”中,被害人李某的母亲在得知女儿被侵害后的第一时间便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但由于一直未获知案件的办理情况,又担心受到加害人的报复,不得不全家移居外地。(7)参见《莫让花季再流泪 专家谈未成年人如何免受性侵害》,http://edu.china.com.cn/txt/2009-04/13/content_17593182.htm,2009年4月13日,2020年10月2日。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的立案、拘留、逮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开庭等各个关键节点上,都应当优先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知情权,并强化案件承办人员告知义务的履行。
其次,对未成年被害人隐私权的全面保护。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11]隐私权保障的意义在于,其本身具有“实现个人尊严和维护与他人良好关系的双重价值”。[12]隐私权的实现不仅是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体现,也是彰显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情绪控制能力较弱,在受到侵害后往往对自身的遭遇不能够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极易做出自杀、自残等极端选择,且其心理修复的过程相对比较漫长。因此,为避免未成年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应当对其个人隐私实行审前、审中、审后的全面保护。[13]具体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科学选取询问场所。在司法实践中,有条件的地区,其办案人员应当选择在配备有心理医生且私密性较好的医院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询问,并允许被害人的监护人全程陪同;条件受限的地方,也可以在被害人的家中进行询问,但办案人员在调查时间、衣着、交通工具的选择方面均应进行特别的考虑。二是立法应当对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是否公开审理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法院在网上公布判决书时,应当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特别是对其生活半径信息的公布,应尽可能地避免将信息细化到街道、社区这类有可能让人推断出被害人居住地的程度。三是针对可能造成未成年被害人严重心理创伤的案件,办案机关可以借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遭受严重心理创伤的未成年被害人建设独立的“个人信息系统”,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加密存储。
最后,对未成年被害人人格尊严权的充分落实。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由生命尊严和社会尊严两部分组成,是公民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的有别于其他客观存在物的高贵和庄严。[14]人格尊严权是一项“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具有高度的社会实践性,未成年被害人作为“特殊当事人”理应充分享有人格尊严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被害人在遭到侵害后通常伴有情绪激动、内心恐惧,不能清楚表述案发的经过,或者需要办案人员多次做工作才能使其消除顾虑,因而这类案件更加考验办案人员的耐心。因此,广大办案人员应当调整工作思路,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人格尊严予以充分的落实。一方面,针对此类案件应当配置专门的办案人员。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从诉讼程序启动后,各部门就应当安排熟悉受害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和案件特点的办案人员来办理。另一方面,对办案的方式进行适度优化。办案人员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应当注意询问语气是否得当、取证方式是否合理,最好提前拟定询问大纲,对于心理创伤较为严重的被害人,要尽可能地在心理医生的协助下开展取证工作。
(二)对未成年被害人程序性权利的充分尊重和特殊保障
第一,应当尽量满足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从狭义上讲,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是指被害人参与法庭审理活动的权利,其主要强调被害人享有的庭审时“在场的权利”。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通常具有表达内心诉求的欲望,而保障其诉讼参与权尤其是庭审参与权有助于改善当前“被害人权利保障弱化”“当事人地位虚化”的局面,同时也是推进庭审实质化、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应有之义。未成年被害人有效参与庭审可以适度消解其作为被害人的不满情绪,同时也能通过其证人作用的发挥实现案件的客观公正。法庭审判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是彰显正义良知、惩恶扬善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场域,具有特殊的涵义,而一律禁止未成年被害人参与法庭活动相当于变相剥夺了其作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因此,可以考虑在结合心理医生与被害人家属意见的基础上,充分尊重未成年被害人的个人意愿,满足其参与庭审的合理诉求。具体而言,当未成年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活动时,应由合适的成年人或心理医生陪同其参与庭审,并由法院工作人员提前带其熟悉法庭环境、为其讲解法庭规则;当未成年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原则上应采取不暴露其身体外貌、真实声音的技术进行相关的环节,并在法庭内建立专门的证人休息室供其休息。
第二,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意见权的充分关照。未成年被害人作为诉讼的当事人除了“形式化”地出席庭审和“工具化”地扮演证人角色外,相关部门应当推动其“当事人”地位的“实质化”,充分尊重其享有的陈述意见权。所谓陈述意见权,是指被害人就其所关切的事项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案件情况及其处理意见的权利。[15]对此,《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在经审判长许可的前提下,可以向被告人发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第2款中规定,儿童在影响自身权益的诉讼中,应享有直接或间接陈述其意见的权利。由于未成年被害人是犯罪手段与结果的直接承受者,其对加害人往往怀有复仇心理,因而其陈述意见权尤其是求刑权理应得到充分重视。一方面,对于参加庭审意愿强烈的未成年被害人,应尽量保障其在诉讼代理人的协助下开展案情陈述、当庭质证、量刑意见发表等诉讼活动。另一方面,对于不愿参加庭审或身体、精神状况不适宜出庭的未成年被害人,可在征求个人与法定代理人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录制音视频、书面陈述、远程音视频连线等方式进行诉讼活动。
第三,对未成年被害人刑事和解权的适当尊重。近年来,受“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影响,各国开始在刑事司法中搭建平台以促成被害人与加害人进行协商对话,以便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专门设置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并将是否达成和解协议作为被追诉人能否获得从轻处罚的法定条件之一,这一做法充分尊重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影响力。而针对未成年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第1款要求各国应当在科学考虑儿童年龄与认知能力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其对关涉自己切身权益事件发表意见的权利。此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也要求,在涉及未成年人事项的时候应当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可根据案件性质、被害人受侵害程度、加害人自身因素以及被害人是否清楚和解协议法律意义的前提下,适当尊重未成年被害人刑事和解的自主决定权。在此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有必要、也有义务对相关法律条款及其具体内涵进行释明,务必确保和解协议不违背法律法规与被害人个人意愿。当然,对于被追诉人具有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屡教不改等情况的案件,不仅要限制双方和解,而且应当严肃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