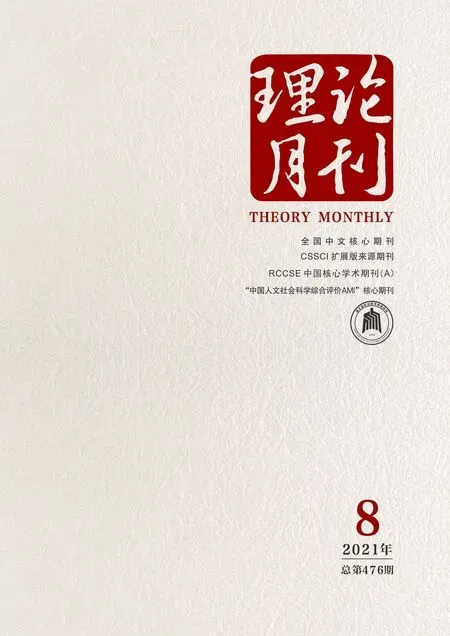短暂的瞬间与永恒的本质
——波德莱尔从时间维度开启的现代性之思
□杨 柳,何光顺
(1.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420)
法国文学正如法国社会,当行进到19世纪中叶之时,已进入一种空前的困境。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进程,古典主义的理性和严格教条早已被打碎,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热情同样不复存在,人们倦怠于现实的破碎和丑恶,在这时代的节点,波德莱尔发出“你无权蔑视现实!”的呐喊,在污浊的现实中孕育美丽的花朵,在过渡、短暂和偶然中隐藏着永恒和不变,两个极端相互冲突和交叉,形成“现代性—缘域”的思想:“仅用‘现代性’描述波德莱尔所开启的文学范式,已显得过于笼统和模糊。‘现代性’概念虽由波德莱尔提出,但概念思维的相对薄弱让其无法更好地呈现这种写作的丰富性。实际上,波德莱尔逆反形而上学本体论主宰的西方古典文学,深入到现代文明的血脉和骨骼处,创造出一种充满内部差异、矛盾的新型文学样态,已有近于东方文学注重内部阴阳共生、自他互转的缘域化境。”[1](p302)当然,在这种相近中又有着较大的差异,即中国古典文学的缘域主要是指文学作为一种非疆域的人文现象所强调的物性、神性、人性的和谐状态及其对感性生命的直观。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现代性—缘域”则是在看到物—人—神关系被工业资本摧毁时去进行重建的创造,它烙印着法国和西方现时代的独特印记,即注重对都市之恶的发现,对都市大众之无名和隐匿状态的展现以及一种象征性写作的实践。
波德莱尔“现代性—缘域”文学思想就是指一切都在因缘之场中变幻又聚集,破碎又重组,在短暂感性的肉身里有着永恒和不变的精神应和,在空间里开展着的世界又向着神圣和神秘跃进。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缘域”思想也弥合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文艺美学思想所存在的两对对立的鸿沟,它意味着瞬间的、偶然的现象与永恒的、不变的本质不再呈现其尖锐的对立,而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现象即本质,瞬间即永恒。这无疑是现代性文学思想对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重大突破。正是这种充满矛盾性、复杂性、隐秘性又具有弥合性、统一性的时间之思及其文学思想,构成了波德莱尔从时间维度开启的现代性之思,它不是线性的时间,也不是物理的时间,而是耦合中的混沌的时间,是让空间变得不再清晰而隐藏着幽暗和混沌的深渊性存在。文艺复兴时期曾经坚持的人文主义理想,古典主义时期关于规则和秩序的强调,伴随着工业革命到来后的冷冰冰的机器而搅得混乱。人们在这种仓促的改变中惶惑又伤感,在机器的隆隆巨响中,一切都变得太匆忙,时间是变幻的时间,将一切搅得粉碎,一切都显得那么偶然和易逝,但这偶然和易逝中又隐藏着永恒和不变。作为新时代精神的开启者,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是打开这新时代精神的一把钥匙,是从时间的维度上重新认识和体验生命和存在。
一、现代性:短暂又永恒的时间重启生命的因缘
何谓“现代性”?现代性概念的创始人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他刻画了有关现代性的特征,即一半是“过渡、短暂、偶然”,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本人虽然不是哲学家,但这个说法是充满哲学深度的,并很大程度上表明一种思想的巨大分野,那就是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过渡、短暂、偶然是现象界的,是表明肉身和万物的有限的,即一切现象都只是过渡性和短暂性的存在,不具有真实性,也当然是偶然性的,不具有必然性,而本体是理念、神、上帝,是灵性的和无限的,它是实体性的存在,也是永恒的、不变的,是万物或世界的绝对本质。永恒是对实体、本体、本质的肯定性描述,不变则是对实体、本体、本质相对于现象和万物的否定性描述,即作为实体、本体、绝对本质的理念和上帝,就不是万物和现象那样的变化,而呈现为瞬间、短暂和偶然性存在。这样,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现象/万物的瞬间、短暂和偶然与实体/本体/本质的永恒和不变,就分属两个世界。如果说永恒、不变的本质是属阳,是正,短暂、偶然的瞬间是属阴,是反,那古代哲学就是阴阳分割的,是正反互不相容的。但在波德莱尔这里,短暂偶然的瞬间与永恒不变的本质却同属于“现代性”本身,成为一个阴阳共生、正反相成的相互共依的内在性存在。由此“现代性”也成为描述现代文明的一个关键性概念。
这里我们就要追问,波德莱尔提出的“现代性”是否有更早的渊源?“现代性”都拥有哪些特质?在人们描述和诠释“现代性”概念歧义百出之际,我们中国学者是否可以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视角重新界定这样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而让其具有中国性。为深化该问题,我们这里仅从历史传统、当下语境和波德莱尔眼中的现代性三部分来探讨现代性这一概念。
(一)现代性从历史中开启的新变:不断跃进中的断裂
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兼作名词和形容词的“modernus”(现代)是中世纪根据“modo”(最近、刚才)一词创造出来的,其词义是指“我们时代的,新的,当前的”,它的反义词是“古的,老的,旧的”。值得注意的是,更早的拉丁语没有“现代/古代”这种对立,在拉丁语中,“古典”(classicus)的反义词是“粗俗”,而不是“新”或“最近”。“古代”越是年迈,人们越是需要表达“现代”的词,直到公元六世纪,“新的、恰当的”(medernus)才出现。“现代”这个词,是晚期拉丁世界留给世界的遗产之一。这也是卡林内斯库在追溯现代性观念时所说的,现代性是“源于基督教正在死亡观念的现代性感情”[2](p60),认为“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2](p18)。这就把特定的时间意识,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可逆的历史性,那种加速度式的跃进所产生的断裂凸显了出来,而这也就从历史中开启出现代性的新变,它令诗人好奇和震惊,而开始专注于新与旧裂变中的冲突。
福柯更将在康德启蒙哲学诞生之前关于“现代性”时期的说法归纳为三种主要形式:“第一,将‘现在’理解为世界的一个时期,它因自身的特点而不同于其他时期,或是因一些悲剧事件而有别于其他时期。在柏拉图的《政治家》里,对话者认识到他们身在一个世界剧变的时期,一切会颠倒,随之而来的都是消极后果。第二,思考‘现在’,并从中发现未来事件的征兆。这是赫尔墨斯式的历史解释学原则,奥古斯丁对此以身示范。第三,将‘现在’看作向新世界黎明的过渡,维柯在《历史哲学原理》的最后一章有过阐述,他以之为‘今天’的,实际上是‘在多数民众臣服于伟大君主的民族间传播最完善的文明’,或是‘文明程度无与伦比的欧洲’,‘她具备实现尘世福祉的一切条件’。”[3](p184)
福柯认为,到了康德这里,“现代”的概念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康德“不以之为世界的一个时期,不是一个包含未来征兆的事件,也不是完美世界的黎明。康德几乎是以完全消极的态度定义启蒙,‘一个结束’,或‘一条出路’”[3](p184)。如果说康德的否定性的现代性是哲学的,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则是文学和艺术的,也同样是否定性,或在否定中以颠倒的形式呈现的,在波德莱尔那里,“希望与绝望,黑暗与光明,善良与罪恶,都以理性化合法化的操作形式呈现出来”[1](p303)。现代性就在从古典乡村文明向着现代工业文明跃进中产生急剧裂变,就是工业文明进程中的碎片化、短暂性所隐藏的永恒的生命时间的凸显,它也是万物看似被机器大工业生产搅碎的偶然性中开显出一种决定现代文明生产的不变法则,即充满乐观精神的资本家和科学家似乎掌握了神之创世的规则,人成为神。这就如歌德《浮士德》所写的浮士德博士在与魔鬼梅菲斯特订立赌约出卖灵魂以赢得肉身暂时性的青春美丽之时,他所赢得的这些享乐及其奋斗都看似偶然和易逝,但当他最后时刻感叹:“‘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预感到这样崇高的幸会,我现在正把绝妙的瞬间品味。”[4](p434)这时,浮士德就赢得了瞬间与永恒,偶然与不变的统一。魔鬼希望拿走浮士德已经出卖给他的灵魂,却未能成功,因为现世的生命的劳动已经与灵魂的永恒不再分离,看似偶然性、短暂性的尘世生活,却因为人的勤奋和努力而与永恒和不变的灵魂同在。
(二)从现代性切入的当代社会文化语境:新时代的诞生
对于福柯来说,康德阐释“结束或出路”的方式极为模糊,而这就需要重新予以阐释。“康德开篇就说,人要为他的不成熟状态负责。这意味着他若想走出那个状态,就只能借助于自我改造。在象征意义上,康德以为这样的启蒙进程里包含着一个口号,这个口号的独特性让人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这个口号又是一个命令,是一个人施加于自己的命令,也是施加于他人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敢于思考(aude sa per),‘有勇气、有胆量去认识’。”[3](p185)某种程度上说,波德莱尔喊出“你无权蔑视现实!”就是康德的启蒙口号的另一种表达,一种否定性的形式,却同样呼唤人要有勇气去认识去介入现实世界。每个人必须决定自己是否作为演员参与这个现代性进程,而这个进程也在每个人的参与中逐渐完善。
哈贝马斯引用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思考:“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的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短暂中抽取永恒。”而后指出:“现代已整个地成了暂时现象,但它又必须从这种偶然性中替自己赢得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雅明采用了波德莱尔的上述主题。波德莱尔满足于认为,时代性和永恒性在真正的艺术作品中达到了统一,而本雅明则想把这种审美的基本经验回转到历史语境当中。”[5](p12)在哈贝马斯看来,从暂时性中抽取出永恒,也就是从偶然性中替自己赢得标准,这标准实际也就是一种人发现上帝或神之创世的存在法则,也即将永恒性的本质寓于短暂性、瞬间性现象的艺术创造法则。这种法则的发现,是植根于启蒙运动对未来的理性设计,以“理性”和“进步”来建立其合法的根基,以“革命”和“反叛”来确立其话语的主导地位。齐美尔则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世界。”[6](p62)现代性就是与理性、进步为其内在性维度,又强调一种心理主义的现代生活体验,在现代工业机器语境下,人们通过技术机械算计一切,但精神和心理又产生着巨大分裂。
(三)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缘域”之思:短暂又永恒的生命时间
现代性从历史中开启的新变,一种不断跃进中的断裂,或者现代性切入当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以及哈贝马斯所看到的贯穿其中的“主体性原则”,它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5](p21),这其中的短暂与永恒的矛盾统一,偶然与不变的悖论共生,现象与本质的表里如一,都在波德莱尔的重视都市与大众生活的写作中被呈现出来,并因着大众和都市的变化的生活而发现了人作为其中主角,一种“崭新的英雄形象”所造成的被中国学者所命名的“现代性—缘域”思想。于是,波德莱尔关于都市之恶的写作,就“预示了某种无可挽回的历史断裂感,但却也意外地开启了现代文学的自他互转、矛盾相共的他化缘域”[1](p304),这种思想的他化缘域就是康德“有勇气、有胆量去认识”和波德莱尔“你无权蔑视现实”的合题,是对于现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洞见,它表明“诗人在解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文学同一性的想象中,又不完全停滞于现实生活的破碎和分裂,而又渴望往更高处或它处寻求超越的冲动,这就是我(同一性)—非我(他化、异质性)—再转向我(非同一性、缘域化)的现代性文学内在丰富性的生成”[1](p305)。这种同一性与差异性冲突又共生的关系,是对于“短暂/偶然/瞬间/现象”与“永恒/不变/绝对/本质”关系的思考,也是摆脱了物理时间而进入生命时间的新“现代性—缘域”之思。
这种“现代性—缘域”思想在波德莱尔1863年《现代生活的画家》中评论同时代的画家康斯坦丁·居伊(Constantin Guys)时有明确表达:“他就这样走啊,跑啊,寻找啊,他寻找什么?肯定,如我所描写的这个人,这个富有活泼的想象力的孤独者,有一个比纯粹的漫游者的目的更高些的目的,有一个与一时的短暂的愉快不同的更普遍的目的,他寻找我们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也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6](p21)波德莱尔评论的居伊,是为一些英国报刊工作的插图画家,当时被称为“风俗速写的大师”,也被波德莱尔称为“现代生活的画家”,同时也是“巴黎生活的画家”,“正是在接触居伊的过程中,波德莱尔逐渐形成了他后期的美学思想,这是一种删繁就简的即景速写美学,就是要通过快速而准确的勾勒将瞬间的印象捕捉下来”[7](p162)。
正是在和居伊等描绘现代生活的艺术家的交往中,波德莱尔确认了其进入现代都市和大众内部展开写作的自觉。在波德莱尔笔下,“现代”也逐渐从一个区别于“古代”的时间概念中跳脱出来,开始具备更为深刻和丰满的内容。它是“暂时的、不易捉摸的、变化的”,也是“离奇的、神秘的、不愉快的”。由此,从历史分期中解脱出来的“现代性”概念,就宛如一个会变化的精灵,在丛林中忽隐忽现,某个角度看如此美丽,某些角度看却又丑陋不堪。尽管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描述仍显粗疏,但必须承认的是,“他是第一个触摸到它(现代性)的人”。这种偶然、变化、神秘、离奇,蕴含着丑陋和美丽、粗疏又精致的生命关系,就呈现为“短暂”与“永恒”、“偶然”与“不变”、“差异”与“同一”的裂变与平衡,就是学者所说的“现代性—缘域”关系的表达,这种“现代性—缘域”是一个跨越了哲学和文学、东方与西方界限的概念,它开启了新的思想与艺术的世界。
二、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之思:矛盾和悖论中的文学缘域的重构
一切都在矛盾和悖论中生成,是瞬间、偶然和变灭的,但又似乎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本质,是不变和恒常的存在,这也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工业文明所开创的一种思想的缘域,而波德莱尔立足于巴黎的城市文学的写作就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文学缘域思想:“文学缘域就是指文学既有其暂时的自性自觉,却又是缘他在而来又缘他在而去的缘起式的人文存在样态。”[8](p115)这种“文学缘域”在波德莱尔那里就体现为“都市之恶”与“大众”的关系,就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和都市广场的嘈杂大众中,一种去中心化丛林化的状态,让每个人感觉到无所依傍,一种焦灼和恐惧困扰着每个人。从这种过渡、瞬间、偶然、短暂与永恒、不变的矛盾性写作出发,就有了波德莱尔的矛盾修辞的运用,也就是刘波所指出的,矛盾修辞就是使决然不同的事物的性质互渗互溶,从而营造出一种全新的境界[9](p22)。下文我们对波德莱尔矛盾修辞运用中所开启的文学缘域境界试作论述。
(一)在臭腐的土壤上开出美丽的花朵
波德莱尔是一位高超的矛盾和悖论思维的思想者和艺术家,他的写作中既让各种矛盾同时出场,却又让这些矛盾组合成了美妙的音符与和谐的乐章。“善”与“恶”,“美”与“丑”,“高”与“低”,“上”与“下”,既互为矛盾,又互为共生,它超越了“正题”与“反题”的对立,而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合题”。梁宗岱在《象征主义》中就对其进行了再次阐发:
在那里,腐朽化为神奇了;卑微变为崇高了;矛盾的,一致了;枯涩的,协调了;不美满的,完成了;不可言喻的,实行了。[10](p83)
腐朽和神奇、卑微和崇高,矛盾双方并不相互割裂和排斥,而是共同构筑成一个对立又共生的互依性的因缘结构。它让矛盾呈现出一致性,枯涩的呈现出协调性,不美满的变得完满,不可能的得以实现。矛盾修辞就以违反矛盾律的方式,将一种神圣和神秘经验表达出来,它仿佛是用自己的方法,“使思想挣脱日益残酷的奴役,使它重新走上全面理解的大道,并恢复它那原始的纯洁”[11](p290)。而这种矛盾修辞就打破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超验、永恒和静止之美,而呈现出矛盾双方的缘起共生之美,它就不同于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关于“美是超验的、永恒的、静止不变的”的美的教条和准则。自启蒙时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古典的静态的社会和静止的理念美就被打破了,一种新型的审美意识诞生了。
人们的审美意识在改变,而作为敏锐的具有极强感受力的艺术家波德莱尔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并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将其呈现了出来。当古典主义诗人还停留于格律规范,当浪漫主义诗人还在追忆往昔美好的时候,波德莱尔把注意力放在了现实生活的美中。具有现代性精神的艺术家,已经无法依据柏拉图的传统美学思想来观照这个社会,新兴科技已严重或完全摧毁了古老文明及其思想观念,人们追名逐利,生活紧张,然而,正是在这个污浊的现实中,波德莱尔发现了美的新的形态,也即一种“现代性—缘域”之美:“如同任何可能的现象一样,任何美都会包含着某种永恒的东西和某种过渡的东西,即绝对的美和特殊的美。”[12](p495)“绝对美”和“特殊美”、“永恒的东西”与“过渡的东西”、“不变的”和“偶然的”的互依共生性质无疑是高度契合的。那种稳靠的实体的世界坍塌了,而一切都只是在急速变化的缘起之场中重组、跨界,并发出混杂的声音。这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相互的关系。”[13](p69)马克思与波德莱尔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抵达现代性,都看到了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的碎片、偶然、短暂和瞬间,而用冷静的眼光审查这种变动、偶然化的关系,也就是都市中的大众的不稳定关系,就需要启蒙主体确立其内在的生命法则,那就是康德所强调的先验法则,是福柯所指出的“关心自己”。
正是从这种跨界、缘起、杂语的“现代性—缘域”出发,波德莱尔对现代性所具有的美的认同便非常容易被理解,“过渡、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这一半是丑陋和肮脏,动荡和罪恶,是瞬间现象的变灭,但按照雨果提出的“美丑对照”原则,极致的丑陋必将与极致的美丽共存:“基督教把诗引向真理。近代的诗艺也会如同基督教一样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事物。它会感觉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波德莱尔是“美丑对照”原则的忠实推崇者,并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波德莱尔主张“从恶中挖掘出美”,美和丑成为一种对立依存中的矛盾共生体,在看似对立中消解,在消解中又新生。
(二)在瞬间和偶然里绽放永恒之花
汪民安指出:“对波德莱尔来说,关注现在是因为要关注现代生活。现代生活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风俗,也即一种全新之‘美’,一种同古代文化和古代生活截然不同的美。因此,关注现在,就是要关注现代生活本身特殊之美。”[14](p12)这种全新之“美”或“特殊之美”,也即一种“现代性—缘域”之美,就是“完全打通了内—外、善—恶、美—丑、物—我的彼此应和的象征关系,这已然构成了文学是文学而又非文学的他化向度和缘域境界”[1](p311)。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们没有自己的土地,远离了家园,古典主义的永恒已不在,浪漫主义的纯净理想已消失。相遇如此短暂,美丽仅有一瞬,作为与传统美相对应的“艺术的其中一半”,现代性的美,必然带有浓重而强烈的时间性。美在当下、美在瞬间、美在偶然。我们所有的独特性几乎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烙印,被不幸或痛苦折磨着的人比那些生活在欢乐和幸福中的人更容易从生活的时间之流中游离出来,现代艺术家致力于寻找“现实生活短暂的、瞬间的美”,悉心体察生活,以渴望创造新的美的艺术。
波德莱尔把握到了“现代性—缘域”艺术所特有的时间意识的美感,就是对瞬间和偶然的充分展现,在其中发现某种永恒和不变,如《给一个过路的女子》:
电光一闪,复归黑暗!——美人已去,
你的目光一瞥突然使我复活,
难道我从此只能会你于来世?
远远地走了!晚了!也许是永诀!
我不知你何往,你不知我何去,
啊我可能爱上你,啊你该知悉!
刘波认为:“这位交臂而过的女子之所以让诗人兴奋不已,是因为诗人在她身上看到了他所能构想出来的关于美和幸福的最完美的观念。诗人表达的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慕之情令人印象至深。”[7](p162)刘波的看法还是相对古典化了,相对较注重偶然路遇的女子所映现在诗人心中的永恒和不变的理式美,实际上,波德莱尔这首诗表达的更是一种瞬间美、偶然美、短暂美,而后才是这瞬间和偶然里的永恒和不变的本质获得实现。这永恒和不变的纯粹本质,或刘波说的“完美”不是观念化的,而是具体化的,是都市和大众的偶然短暂的相遇中就即刻闪现和顿悟的永恒和不变,这有如佛家所言的“一花一天国,一叶一菩提”。永恒、不变之美,不在彼岸,而就在当下偶然和瞬间的因缘聚散中,在那缘发式的觉悟中。
因此,一位过路女子,虽然只是波德莱尔记下的匆匆一瞬,但在这一瞬中,相逢的快乐和永诀的伤感同生,一种交融着短暂/偶然与永恒/不变的审美体验也在这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心理活动中生成。这种现代性的美感是因缘而起又因缘而散的,没有稳靠的实质,故难免让诗人产生若许感伤,一种无法把握的现代性瞬间里的偶然的印痕。正因为其是一种特殊美,故现代艺术家并不需要沿袭传统的绝对美的标准,而只是忘情地沉浸于现实生活,并将之表达出来。也正因为没有对过往的沿袭,现代艺术家才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表达现代美的方式进行了创新,从一种“特殊的激情”中表达出现代性的差异性,“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诗学可作为现时反对过去——转瞬即逝的瞬间反对稳定的记忆,差异反对重复——的例证”[2](p59)。在这种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中,波德莱尔尽情体味着现代生活充满瞬间和偶然的美。生命的爱就在这种瞬间里瞥见永恒美之中实现,要去把握和体验短暂,去把握今生和书写来世,要看到世界的缘起和跨界中的和谐的美。
(三)在碎片和断裂中开出完整之花
在波德莱尔之前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中,诗歌中的事件多是连绵不断的景象,并且诞生了很多长诗。但波德莱尔却很少写作长诗,他反对浪漫主义诗人冗长杂沓的写作,在事件的选取和描写上,波德莱尔也没有沿袭前人的方式。波德莱尔擅长写断片和残景。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碎片、残景、街头漫游等充满“惊奇”的事件屡次出现,没有绵延的叙事,寥寥几句便描绘出了事件的全部内容,然而,在这些只言片语中,现代生活的断裂感和偶然感却得到了深刻的展现。以波德莱尔的《天鹅》为例:
卢浮宫前面的景象压迫着我,
我想起那只大天鹅,动作呆痴,
仿佛又可笑又崇高的流亡者,
被无限的希望噬咬!然后是你,
安德洛玛刻,从一伟丈夫的怀中,
归于英俊的庇吕斯,成了贱畜,
在一座空坟前面弯着腰出神;
赫克托的遗孀,艾勒努的新妇
《天鹅》这首诗是波德莱尔题献给雨果的,它是感慨失去家园的流浪者的哀歌,其时雨果正在泽西岛流亡,“在全诗整体上,‘逃离’主题同与之相关的‘流亡’主题交相呼应”[7](p134)。在连同《天鹅》诗稿寄给雨果的信中,波德莱尔谈到他的创作手法:“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一下子说出一个偶然事件、一个画面所包含的具有暗示性的一切,说出所看到的一个动物苦苦挣扎的景象如何驱使心灵去贴近所有那些我们热爱的、被抛弃和受苦受难的生灵,去贴近所有那些被剥夺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人们。”[16](p134-135)安德洛玛刻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的遗孀,特洛伊城陷落后,被庇吕斯虏为女奴,后又赏给了奴隶艾勒努斯为妻。安德洛玛刻的命运,实际是“现代人漂泊不居,仿佛过着流亡生活”的写照。波德莱尔以“偶然事件”来描述这种逃离和流亡的命运,看起来这种强烈的具有画面感的事件是出人意料的偶然性的发生,但它又隐藏着命运的必然和无法改变的神意法则,这就如现代人的漂泊和流浪,也同样是城市文明和大众的注定的必然的无法改变的命运,它只是显现出偶然性的景观。
在这首诗中,传统诗歌的连贯而绵延的叙事模式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断裂感的跳跃。卢浮宫是现实,天鹅是记忆,安德洛玛刻是神话,黑女人、孤儿、水手、囚徒和俘虏则又是记忆,全诗虽然不乏对事件的细腻描写,却没有连贯性的叙述,一个又一个场景不断闪现,更迭变异,但似乎又有着内在的联系。片段的叠加就构成了全诗看似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碎片却契合了新时代的匆忙和人们无法改变的命运:任何地方都不是故乡,都只是短暂的、偶然的驻足。在精神的漫游和漂泊中,碎片和断裂被重组,偶然瞬间的尘世场景和必然不变的命运法则交织,并成长出了完整的艺术之花。
三、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艺术的问题:对抗性矛盾仍未完全消解
作为一位具有开拓性和先锋性的诗人,波德莱尔的贡献就在于摧毁了“欧洲自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以来那种精神—肉体、天堂—地狱、神圣—世俗的简单二元对立结构和深层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开启了西方现代性文学注重差异性耦合的缘域”[1](p310),但这种开创性仍旧受到其二元对立文化语境的严重局限,并体现出三个方面的不足:
(一)震惊体验源于矛盾的难以调和
现代艺术的特点是“震惊”,但短暂的震惊让人感觉新奇并可能激发创造力,持续而强烈的震惊却可能让人开始变得麻木而失落于震惊所造成的现实混乱之中。《恶之花》对过渡、短暂、偶然、瞬间的美的追求固然反映了时代剧烈变化中的震惊体验和趋向于异态和下坠的审美感受,但这种不断地沉落、下坠、创伤、毁灭也让人心容易变得悲观且缺乏信念和敬畏,缺乏执着追求的意念。这里以《音乐》为例:
音乐常像大海一样将我卷去!
朝着苍白的星,
背负多雾的穹顶,浩渺的天宇,
我正扬帆启程;
我挺起胸膛,像打开所有的帆
鼓起我的肺叶,
在聚集的波浪的脊背上登攀,
眼前一片黑夜;
我感到一条受难之船的痛楚
在我身上震颤,
顺风,暴风和它的一切的抽搐
在深渊的上面
把我摇晃。有时候又安详平静
如绝望之大镜
现代艺术的特点则是“震惊”,是对于碎片、偶然、瞬间的不可把捉的好奇和惊讶。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探讨了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灵韵”消逝和“震惊”体验的问题,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就写出了“灵韵”消失时代中的“震惊”体验,这种“震惊”体验是对剧烈变化时代的一种特别表达,也就是说,对于充满瞬间、偶然、过渡、短暂的令人震惊的时代,艺术必然有与之相伴而生的明晰的“震惊”体验,这种对于震惊的描写也是一个“现代的现象”,是“与世俗历史生产力的伴随现象,并从消逝之物中感受到一种新的美”[17](p26),焦虑和骚动,心理的晕眩和混乱,各种经验可能性的扩展及道德界限与个人约束的破坏,自我放大和自我混乱,大街上及灵魂中的幻象等,就诞生出了现代的感受能力,也就是一种复杂的“现代性—缘域”艺术。
在波德莱尔的笔下,音乐不再是古典音乐的纯净和优美,而是“像大海一样将我卷去”,一种令人“震惊”的力量,又有着令人哀伤的色调,“朝着苍白的星”,主体性的我,与暗淡的世界形成尖锐的冲突与对立,“我挺起胸膛”“鼓起我的肺叶”“在聚集的波浪的脊背上登攀,/眼前一片黑夜”,世界的背景是黑色或苍白的,“我”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不断动荡的背景或舞台上,“震颤”,“在深渊的上面/把我摇晃”,这个世界简直令人难以承受,不曾有欢乐,只有各种令人震惊或震颤的情景,令人感到绝望,诗人感到憔悴,诗人心中充斥着一种漆黑的没有未来的忧郁。当一种来自外界的过剩的能量造成人心的强烈震惊之时,人的自我意识也会产生本能或走向自觉的防御。但震惊的持续,却可能让意识在不断遭受冲击中变得疲软而难以抵抗冲击。在波德莱尔那里,大量表现“震惊”体验的诗歌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心理防线,使人恐慌、狂躁、自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可谓现代性震惊体验的不朽之作,波德莱尔的震惊体验的强烈和难以缓解,实际就是源于短暂/偶然与永恒/不变的矛盾难以克服,波德莱尔难以将其真正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生命的缘域之场,故而,这种现代性体验就往往形成对于生命的过度刺激,而难以让人得到安顿。
(二)生活的妥协源于对抗性冲突的缓和
现代性或现代艺术的本质在于现代世界的对抗性冲突所造成的痛苦,正如刘波所指出的,波德莱尔缺少家庭温暖,与他母亲和继父关系紧张。因此,“诗人便毅然转身到家庭‘外部’去勇敢地拥抱艰难和险阻,把那里看作是自己夺取荣耀的领地”[7](p61)。蒋永国也认为:“在《巴黎的图画》中,波德莱尔歌唱大街上的乞丐、老人、病人、妓女、赌徒、罪犯,把他们视为‘家人’。《老妇人的绝望》和《窗》也是此延长线的作品。”[18](p79)对这种现代艺术源于生存的痛苦和紧张的本质,何光顺则对其进行了揭示:“现代艺术的感性抗争及这种抗争最终难以实现的痛苦使其区别于原始艺术的感性释放及这种释放的无阻碍的自由。”[19](p77)波德莱尔的诗歌写作就可以看作是其对自己所处生存状态的激烈抗争以及这种抗争最终难以实现的痛苦的表达。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描摹了“老妇人”被小孩嫌弃后,“向隅而泣,喃喃自语”,这也表现了一种生活中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生存的痛苦。
然而,无论生存的冲突多么激烈,诗人的写作终究是一种生存的矛盾冲突的缓和,或者说将矛盾引向了倾诉和艺术化的释放,这正如波德莱尔在《通功》中所写的:“快活的天使啊,你可认识焦灼、/羞愧、悔恨、哭泣、无聊,还有种种/可怕的夜里压迫人心的惊恐,/模模糊糊却像把一张纸揉搓?/快活的天使啊,你可认识焦灼?”[15](p81)随后,诗人又写到了“天使”与“怨恨”“发热”“皱纹”,这一切与天使构成矛盾的衰朽或颓废的存在,在这首诗中,波德莱尔把传统艺术的“韵味”和现代艺术的“震惊”相结合,写出了冲突和矛盾的尖锐。波德莱尔看清了现代性的短暂、瞬间、偶然、破碎,以及现代生活的种种罪恶,但是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却没能找到更好的出路,而仍旧只好向传统求助,如在这首诗的结尾,诗人诉说:“然而我只求你为我祈祷,天使,/充满幸福、喜悦和光明的天使!”这也表明波德莱尔淡化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他无法看到现代性的光明的未来,他的诗歌精神还在现代性刚刚起步之时,不免要回到传统的天使或女神的怀抱,去缓解痛苦和祈求福乐。
(三)梦幻化的想象表明精神的无所皈依
波德莱尔擅长暴露平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但也在大的社会环境等宏观层面有所缺失,其落脚点始终是在具体的生活,而缺乏对大环境的反思。诗人写的“乞丐”“白头老父”“七个老头子”“一位过路的女子”,都是现实而具体的人物及其生活百态,但对于造就这种生存状况的大环境,波德莱尔的关注度则严重不足。当然,波德莱尔也有描述大环境的作品,如《无可救药》:“一个不幸的中邪人,/为逃出爬虫的栖地,/在他徒劳的摸索里/寻找钥匙,寻找光明;”,“/——画面完美,象征明确,/这无可救药的命运/让人想到,魔鬼之君/无论做啥总是出色!”[15](p152-153)这让人看到了一个遭难者,在生存的大环境的难以改变中,自己个体的命运也终究难以改变。
对于这种大环境的恶劣,诗人很少去揭示原因,也很少指出反抗、逃离或拯救的道路,他的写作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虚幻感或观念化指向,如《无可救药》开篇所写的“一个观念,一个形式,一个存在,始于蓝天”,这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观念化的意味。又比如《巴黎的梦》开篇所写的:“这一片可怖的风光,/从未经世人的俗眼,/朦胧遥远,它的形象,/今晨又令我醺醺然”[15](p201),诗人随后又写“品味大理石、水、金属/组成醉人的色调”“无尽的宫殿”“金盘”“水晶帘”,都表现出对于失去的乐园的梦幻式的追忆和怀想。这些幻想或观念化的书写,也表明了诗人的精神皈依的困难,在一个碎片、短暂、偶然、过渡、瞬间的现代世界,另一半的永恒和不变始终隐藏着,或者说纯粹的美的本质和精神隐藏着,并徒然表现为一种艺术形式和观念的呓语。
波德莱尔以他的直觉把握到了现实生活的偶然和瞬间,借助文学实现了对偶然、瞬间的生活与都市之景的书写,并在其中发现了不变和永恒的本质,但在理论上却仍旧难以对这个问题进行透彻理解。西方现代先锋派理论家克勒在谈到从“报纸剪辑”诗到最现代的事件时曾经指出:“对物质性的狂热服从并非是一种社会状态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这一社会状态中,只有偶然所揭示的东西才能免于虚假的意识,摆脱意识形态,不被打上人类生活状况的完全具体化的烙印。”[20](p138)现实生活是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汇集,文学书写偶然性、瞬间性,就是要从看似偶然中寻找一种必然性和本质性,也就是偶然和不变的统一,是短暂和永恒的统一。波德莱尔在他的作品中写到了很多偶然、短暂、瞬间和不变、永恒的冲突与统一,但因其理论上还未做出透彻深入的诠释,这导致其写作相对缺少文学所应当抵达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维度,从而导致他的作品在裸露巴黎的肮脏和丑陋方面较多,这也是波德莱尔被当时批评家称为“腐尸诗人”,而波德莱尔不愿意接受却又很难真正予以回击的原因。
四、结语
我们看到,在19世纪的人们倦怠于现实的破碎和丑恶中,当波德莱尔喊出“你无权蔑视现实!”这无疑是一次强烈的震动和一种唤醒。波德莱尔通过直面现实的写作,让人们重新认识现实,将现实的丑恶、粗糙、破碎、偶然、短暂、瞬间、易逝之物予以重组,以在其中发现永恒不变的精神维度和本质存在,而这也就是学者所看到的一种“现代性—缘域”的思想。这种缘域化思想是因着一种不可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线性时间所造成的不断跃进中的断裂而产生,从而产生另外一种心理时间,即在短暂与偶然中对永恒与不变的渴望,并在艺术家那里呈现为以矛盾和悖论的写作,以象征的手法实现艺术与现实的张力和弹性创造。这样,工业进程的线性时间和艺术家感受到的断裂时间就共同作用,形成一种耦合中的混沌的时间,并让现实生活的空间变得不再清晰而成为隐藏着幽暗和混沌的深渊性存在。但因为波德莱尔终究是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刚刚走出的诗人,他还难免会流连于古典女神或浪漫主义精神的某些幻影和虚像,他还难以提出走出其时代困境的出路和方案。作为一个诗人,一位个体化的写作者,波德莱尔无疑是优秀的,但他自己还未来得及投入到他所同情的那些受苦者或穷困的阶层,这就让他的写作显出一种旁观者的态度,而无法实现自我生命的真正救赎,当然也不可能带来或引发社会的真正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