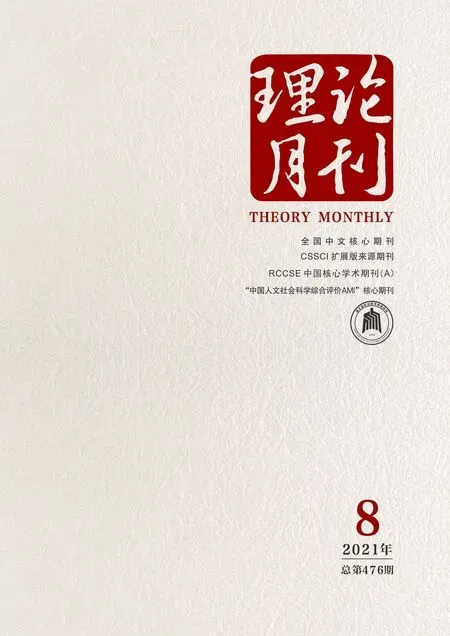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的相遇
——基于词源、内涵与逻辑的理论考察
□赵睿夫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作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两股思潮,“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与“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活跃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洞见与话语资源。自其建构伊始,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就有天然的理论关联,二者共同面对着“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两大问题,却迈向了迥然相异的研究路径。尽管国内外学界对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的专门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但对二者理论关系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具有多维的理论联系,二者都批判戕害自然生命、将人与自然工具化、割裂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政治模式,力图实现人类生命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和解,前者侧重人类生命存续中的“内在自然”向度,后者侧重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外在自然”向度。要具体分析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在何种程度上相遇,一个涉及概念、谱系与逻辑的总体考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之上,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的关联将清晰可见。
一、对“生命政治学”词源、内涵与逻辑的考察
(一)对“生命政治学”概念的词源与谱系的考察
从词源学上看,“Biopolitics”一词的词根指向古希腊的“βίος”(生命)与“πολις”(政治),二者均系古希腊哲学最为原初的构成概念。一方面,“βίος”表示人的生命、生活世界、生活方式等意象[1](p152),强调具有社会性、合法性、组织性的生命形式,与纯自然的、动物性的、官能性的生命形式有所区分。在生命伦理学的视域中,“当生命以人的形式表达出来时,便呈现出新的神秘意义和价值”[2](p42),换而言之,人的生命的社会性与自然性之间存在先天的区别与张力,这就为生命政治学的出场埋下了伏笔。除“βίος”外,生命政治学还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示生命的概念——“ζωή”,与“βίος”不同,“ζωή”意表纯粹的自然生命,指代最为一般和原初的生命形式,它没有任何风格特质,不关涉任何政治等社会生活命题,因而也被理解为“动物性的生命”或“生物学生命”,与“βίος”构成一对矛盾范畴[3](p88)。另一方面,“πολις”原表城邦、社团、栖息地等人类聚居空间单位[4](p3),衍生出“πολιτικoς”用以表示“政治的、政治家的、城邦的、公民的”[5](p191),经由《荷马史诗》《政治学》《政治家篇》等著述的阐释而表统治、管理、争斗、分配等意。及至现代语词中的politics/politik/politique等形式,政治普遍被理解为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其实质是上层建筑层面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
最早的完整名词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概念的可能①这里使用“可能”有两重原因:一是Lemke在Biopolitics:An Advanced Introduction一书中的原文处使用may表达出了他对这个说法的不充分认定;二是福柯在《性经验史》一书中有过生命政治概念是“18世纪所发明”的说法,但这个命题也同样缺少具体论据。参见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1.使用者是瑞典地缘政治学者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6](p9)。19世纪后半期,斯宾塞、狄尔泰、柏格森、齐美尔、尼采等思想家使人的生命过程与机体规律问题重新受到欧陆思想界的关注,彼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现“生命体隐喻”风潮。拉采尔于20世纪初提出民族与国家有机体说,深刻影响了契伦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契伦将“生命体隐喻”纳入自身国家学说,将国家与公共社会类比为一个庞大的有机生命体,从有机主义的角度重叙了人类历史中的政治斗争,并通过《政治体系原理》(Grundriss zu einem System der Politik)等著作将“生命政治”概念带入了学界视野[7](p73)。真正首次使得“生命政治学”成为理论专题的学者无疑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6](p4),他基于对权力的统治权力、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三分法,分析了人类政治文明中生命政治化的生成机制与历史表现,揭示出自由主义现代政治对生命过程的窥秘与干预实质。在福柯之后,经由阿甘本、埃斯波西托、巴特勒、哈特、奈格里、维尔诺等人的阐释,生命政治学开始与欧陆左翼激进哲学发生交互,逐渐成为现代性反思、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思潮。
(二)对“生命政治学”理论内涵的考察
生命政治学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种“国家对生命施行治理的政治模式”。在兰克(Thomas Lemke)的理解中,“生命政治学不能简单地被称为一种特定的政治活动或政治学的一个子领域,它涉及生命过程的调控和治理”[6](p31),同样,福柯也表达过“不能把生命政治简单视为‘国家所进行的一种对生命的调节’”[8](p338)。换而言之,生命政治学的理论主体不是施政者,其理论主题也并非是使治理技法完善化、合理化、高效化。与其说生命政治学是一种建构性、技术性、策略性的政治实践指南,毋宁说其是一种以历史政治实践为分析样本的政治经验反思,它并不完全赞成或彻底否定某种政治模式,而侧重于对人类历史中“处理生命的政治”[6](p2)的现象及其本质的研究与思考,即如阿甘本所言:“只有一种反思能使政治之域摆脱它遮蔽状态,同时使思想回归其实践性的召唤,那就是:追随福柯和本雅明的建议,对赤裸生命与政治之间的关联进行主题性的拷问。”[9](p8)
福柯将生命政治的基本范畴设定为“人口”,强调“自由主义框架”对于生命政治诞生的重大影响。在福柯的理解下,生命政治是“西方自18世纪起试图使人口特有的现象向治理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得合理化的某种方式”[10](p3),是“一种从总体上调节人口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11](p77),其根本目的即以最小的经济政治成本取得最大的社会治理与控制成效。即是说,生命政治的本质是对人的自然存在状态的政治化,随着原本作为自然生命的人被人口化、符号化、手段化,政治自身也就转化为生命政治,这个过程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政治权力统治,同时也使得整个公共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性有所提升,但却意味着对部分群体生命权利的剥削与压迫,充满着反自然、反主体的工具理性意味。
与福柯的自由主义反思路径不同,阿甘本不认为生命政治是纯粹的现代政治产物,他指出,生命政治作为一种统治逻辑始终在场,造成自然生命被剥离现状的绝不仅是福柯所指摘的自由主义政治,整个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都是生命政治化的过程。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并不像福柯那般关注微观的社会权力结构与日常生活规训,而是从宏观视角出发分析整个国家至高权力作用机制的转变,揭示出“紧急状态”或曰“例外状态”的常态化对于人的生命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剥离,以此批判西方生命政治化的“赤裸生命”生产实质。与福柯和阿甘本不同,埃斯波西托立足于“免疫学”(immunology)范式,以一种“阐释学途径”[12](p235)来观测生命政治。与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βίος”/“ζωή”区分不同,埃斯波西托认为“生命政治的目的并不是要以将生命的一部分牺牲给另一部分的暴力统治的原则来区分生命——虽然这种可能性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恰恰相反的是,它是为了拯救、保护、发展作为一个整体(as a whole)的生命”[13](p139)。这种对生命政治的积极考量揭示出福柯与阿甘本批判路径之外的新理论可能:以其协调与保护意义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生命政治研究。
(三)对“生命政治”逻辑基础的考察
在生命政治学的意义上,现代国家的构造离不开对权力与生命的规范化计数,如个人信息与特征的编码化、职能部门运转的效率报告、人口再生产状况的宏观调控、选票与社群认可度的数字化统计、社会生活空间的容积规划等,这种以计数为集中表现形式的理性模式以服从多数群体作为对少数群体的规约理由,把具体的、具有丰富内涵与独立诉求的人抽象化为工具性的形式符号,从而实现对人的自然生命的政治化控制。在阿甘本等人处,这种计数理性被概括为“排斥—纳入”(exclusion-inclusion)逻辑,对于这种逻辑的分析即构成了现代生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使命。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敌友政治观”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具有内在近似性,但将“排斥—纳入”关系直接理解为政治学传统意义上的“敌—友”关系显然是武断的。如阿甘本所言:“西方政治的基本范畴不是朋友/敌人,而是赤裸生命/政治生存、zoe(‘ζωή’)/bios(‘βίος’)、排斥/纳入。”[14](p140)在这几对基本范畴中,最具抽象性者即是“排斥—纳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关于城邦与个人关系的论述极有可能是政治意义上“排斥—纳入”逻辑的最早外显:“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4](p9)亚氏揭示出城邦政治文明运作的基础在于有所选择地将一部分服从公共权力秩序与约束的人纳入日常生活中,而另一部分反对世俗秩序或不被世俗秩序所需要的人则被“鄙弃”出了“人”的范畴——这与阿甘本所强调的“神圣人”(Homo Sacer)范畴高度近似:在古罗马法中,神圣人是由于犯罪而被审判的人,人们可以任意将之杀死而免受惩罚,且其不能作为给神的贡品被祭祀。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试图通过分析神圣人的概念以“揭示一种原始的政治结构”[9](p8),这种政治结构即是“排斥—纳入”逻辑的产物。
“排斥—纳入”是生命政治的逻辑基础,亦是生命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关注对象,它不是一维的,其逻辑内部充满着复杂张力。排斥与纳入不是决然对立的,在阿甘本看来,“将一部分人的生命还原为赤裸生命,是整个共同体人口安全的基石”[15](p51),因此排斥一部分人的生命形式本身也是纳入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即所谓的“纳入性的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正是在这样的逻辑链条之下,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突、赤裸生命与政治主权的对立、“现代民主的内在矛盾”[9](p170)诞生了。
二、对“生态政治学”词源、内涵与逻辑的考察
(一)对“生态政治学”词源与谱系的考察
从词源学上看,Ecological Politics的词根包括古希腊语词“πολις”(政治)与“οίκος”(生态)。在古希腊的原初语境中,“οίκος”有“房间”(room)、“房屋”(house)、“住所”(dwelling)、“本地”(native land)、“家庭”(household)等含义,同时也指代“诸多事物构成的集合”[16](p1055)。1865年,德国学者汉斯·雷 特 尔(Hanns Reiter)由 希 腊 文“οίκος”与“λόγος”(原因,理由,逻辑)构出德语词汇“ökologie”,用以表示“自然的原理”①部分学者也对这一说法作出了“错印说”或“笔误说”的勘误,但这些勘误本身也未完全确证。参见:马振兴,等.中、外文“生态学”一词之最初起源及定义考证[J].生物学通报,2017(11):10.。从原初内涵上讲,“ecology”指代“研究房屋的学问”,后经外延发散,逐步转变为“研究栖息地与聚落的学问”,并最终表示“生态,生态学”。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其《生物一般形态学》中将“生态学”(此著中写作为Oecologie)的基本内涵界定为“针对有机体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整体科学”,其研究范式强调关注周遭世界诸经验现象间的系统性与总体性。
“生态政治”这一命题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对“生物界”与“政治”二者内在关联性的认识,如其所言:“就生物界的现象说,我们可以见到——也可以说,在这一方面方始可以确切地见到——专制和共和(宪政)两种体制。”[4](p14)1935年,生物学研究者弗兰克·索恩(Frank Thone)首次使用了“political ecology”概念[17](p1-16),但真正使“生态政治”命题得到广泛关注的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揭开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绿色思潮的序幕,如为其书作序的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所言:“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共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18](p9-10)
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揭示出西方工业文明的能源与环境限度,各色生态政治思潮开始活跃于欧美政治舞台,生态思潮与绿色运动的矛头逐步转向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活方式。这一时期的生态政治思潮可以被划分为“深绿、浅绿与红绿”——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为核心的“深绿”运动、以经济技术手段革新为核心的“浅绿”运动和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替代为核心的“红绿”运动[19](p2)。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对于生态意识的要求日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逐渐成为西方绿色革命运动及其理论代言人[20](p8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里约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文件和条约的相继出台,生态政治理论在实践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当代,“生态政治”被界定为“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政治性理解与应对”[21],“对如何构建人类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间的适当关系的政治理论探索与实践应对”[22](p1)。需要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生态政治与当今社会流行的其他术语如环境政治、绿色政治等,基本上是具有相同内涵的不同表述方式”[23](p67),在理解不同学者的理论时,必须明确其话语具体所指。总之,生态政治学可被理解为“以生态政治现象及其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也可以称为环境政治学、绿色政治学”[23](p67)。
(二)对“生态政治学”邻近概念的辨析性考察
由于生态政治学具有较为宽广的范畴外延,对其理论内涵的阐释将以邻近概念辨析的形式展开。
首先,“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之辨析。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的关系高度复杂,截至目前,学界对于二者关系大致有两种看法:持“同一论”的学者认为“在概念上,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环境政治学、绿色政治学是相当的”[24](p21),有所区别的只是二者的研究范式;持“差异论”的学者则认为,政治生态学侧重以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生态政治学则侧重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生态问题,二者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能一概而论[25](p121)。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二者的范畴差异决定了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同一概念。政治生态本身并非一个环境面向的语词,它是以生态学系统性方法论范式审视一定范围内政治状态的产物,强调政治系统内部存在着如自然生态系统一般复杂的关系,它与生态政治表意交叉,但侧重点明显不同。对此,刘京希教授主张用更具综合性的“生态政治理论”来整合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将之界定为“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运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26](p77),使得围绕政治学与生态学所产生的交叉学科呈现出更强的内在话语融通性。总之,生态政治学强调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思考生态问题,而政治生态学则强调用生态学系统论的眼光审视政治问题,本文所讨论的生态政治学更倾向于前者。
其次,“生态政治”与“生态文明”之辨析。费切尔(Iring Fetscher)发表于1978年的《论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被视为是“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这一专有理论范畴的出场之作。卢风教授将“生态文明”理解为“用生态学指导建设的文明,指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文明”[27](p14);郇庆治教授则从四个维度出发界定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即“哲学理论层面上的弱生态中心主义关系价值和伦理道德”“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性范式的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建设与实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创建中适当生态关系的部分”“现代化发展语境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向度”[28](p50)。从范畴的层面来讲,生态文明是高于生态政治的,它强调从各个维度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和谐精神,是生态政治的最高追求目标与最终价值归宿。这同时也意味着推进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进程,必须考虑生态政治这个重要维度,“理想的生态环境需借助政府的力量营造,高度的生态文明需依靠政治的支持才能建成”[29](p54)。
最后,“生态政治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之辨析。生态马克思主义亦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旨在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探讨摆脱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由美国学者本·阿格尔于1979年首次提出[30](p414-415),但其实质性的理论发轫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7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人与自然双重解放问题的研究,即如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所言:“除非造成污染的制度和政治力量被消灭,否则我们就不能指望为人类解放创造一个清洁的环境。”[31](p350)20世纪70—80年代,阿格尔、莱斯、高兹等学者以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关系为切入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奥康纳、福斯特、佩珀、布兰德等欧美学者的引领下,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的提升与研究进路的丰富化清晰可见[32](p86)。生态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诸多生态政治理念,可以将之理解为生态政治阵营中极具影响力的一派,对其研究也必然是生态政治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但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三)对“生态政治学”逻辑基础的考察
尽管按照“浅绿”“深绿”与“红绿”的思潮划分方法,生态政治的内部逻辑是杂冗纷繁的,但从宏观而论,生态政治学仍然有一个较为明确的逻辑基础,即以“规范”(Norm)与“超越”(Transcend)为主要矛盾范畴的政治哲学逻辑。“规范”与“超越”同为政治哲学基础范畴,“规范”强调对应然逻辑与形式原则的政治遵循,而“超越”则意指在实际反思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传统理念与信条的政治批判,也即是说,“规范”侧重于原则、限度,“超越”侧重于批判、求变。完善的政治哲学应是规范性与现实性、理念性与实践性的统一[33](p23),“哲学被自己缺乏的东西所规定,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种逃离它,却以某种方式在它自己内部所拥有的超越的规范”[34](p44)。规范与超越之间存在着张力:一方面,规范性表征着政治哲学的政治性,缺失了话语规范与原则依据的政治哲学也就意味着缺失了投身现实政治指导的可能,将倒向纯粹的思辨哲学或乌托邦主义;另一方面,超越性表征着政治哲学的哲学性,要求其内蕴批判力与否定力,不寻求超越的政治哲学将流为单纯的“治理术指南”,而无法提供击破现存桎梏的理论洞见。
首先,生态政治学的“规范”逻辑表现在其人学导向的价值追求。作为诞生伊始就包含着人类理性精神的政治考量,生态政治学在本质上必然是服务于现实社会的政治实践的——政治性的理论基质决定了生态政治学必然要以现实社会生活作为价值依归。生态政治学始终带有人学的价值痕迹,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的栖居场所存在,人类作为生态系统诸要素中的一环存在,人类需要调整政治策略以适应生态变化,解决生态问题是走向更成熟的人类政治形态的必经之路。承认人的立场与价值为生态政治学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框架,否则将陷入反人类主义的自然拜物教。生态政治不是一种固定的政治模式,它是一种从政治角度出发理解生态问题的政治考量集群,一切的考量目标均指向对生态环境危机的解决,对生态良好环境的建设,对生态友好型政治体制的构想,这个考量集群的主体必然是承认自然价值与自身价值同时存在的具有生态关怀与政治眼光的现实的人,对于人类主体的价值承认始终是生态政治学的规范性边界。
其次,生态政治学的“超越”逻辑表现在其内蕴的自律反思精神。生态政治学通常包含“政治哲学理论”“绿色运动”“绿党政治”“公共政策”四方面内容[28](p46),从政治哲学上看,生态政治学是人类超越自我中心主义、超越经济与计数理性的思想产物,它以约束人的资源耗费本能与自然控制欲望作为超越旧的政治文明的手段,从诞生之初就包含有“通过自我否定实现自我肯定、通过自我约束实现自我超越”的理论目的;从绿色运动上看,生态政治学不排斥绿色运动的出现与发展,但始终强调适度、适宜、适当的运动精神,始终对绿色运动本身进行反思改进;从绿党政治上看,生态政治学并不试图为绿党政治提供一个贯穿始终的教条式规范,它接受多种形态的绿党政治议题;从公共政策上看,生态政治学包含有一个“求变大于守成”的隐在前提,对于现有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发展是生态政治区别于某种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特质,它不断试图超越现有的政策体制以谋求更好的生态发展前景,始终具有不同一般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活力。
最后,在生态政治学的境域中,“规范”与“超越”的双轨逻辑存在交互可能。无论是以接受合法性框架与承认人学价值为核心精神的规范逻辑,还是以谋求改进与自律反思为核心精神的超越逻辑,在本质上都是人类政治文明自我升华过程中的智慧产物。提供一个承认人类主体价值的理念性前提使得生态政治学成为一种合理的政治考量集群而非自然崇拜宗教,提供一个超越思维定式的自律机制使得生态政治学成为一种包含创新动力的政治哲学反思而非特定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规范”与“超越”逻辑指向了共同的目标,即一种立足未来的更具生态关怀精神与社会规范能力的生态文明政治。
三、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在何种意义上相遇
(一)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相遇在对“自然生命”的共同关注
前文已述,无论是生命政治学还是生态政治学,都十分重视对人的生命的自然属性的研究,二者在词源上都脱胎于“人的生活场域”这一基本意向,在内涵上都关涉人的生命权利及其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逻辑上都试图破解割裂生命自然性与社会性、以政治权力倾轧自然系统、将统治阶级意志强加于人与自然的极端政治模式。回溯亚里士多德关于生命的命题:“至于‘工具’有些无生命,有些有生命……一切从属的人们都可算作优先于其他无生命工具的有生命工具。”[4](p11)如果将人类政治文明的根基设定在生命可以被政治化、人与自然都可以被视作工具、自然生命可以被非自然手段控制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类似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极端惨剧终将再次发生。在政治文明已经普遍承认人的生命权利的现代,重估“自然生命”或“生命的自然属性”的价值,成为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需要共同面对的理论问题。
兰克在《生命政治学导论》中多次使用了“生态生命政治学”(Ecological Biopolitics)的概念,揭示了生命政治学的自然关涉潜能。一方面,生命的生物学第一属性就是自然性,任何生命都是构成生态系统的要素之一;另一方面,生命政治学研究的旨归是让人获得更好的生存状态,而生态问题的存在从本质上与人的生存相冲突,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学必然是生态的。如兰克所言:“生命政治学的概念与生态考量相关,并成为各种意识形态、政治和宗教利益的参照点。”[6](p24)基于“βίος”与“ζωή”的生命划分方法,生命政治学已经表现出“生命必然存在去政治的自然状态”的隐在命题。在如何摆脱现代政治文明的生命控摄的核心问题上,生命政治学给出的可能性回答是通过主体性的生产,恢复生命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只有在肯定自然生命的先在价值的基础上,生命的去政治化才是可能的。
同样,生态政治学必然是关注生命的。从出发点上看,如果放弃人类生命的存在价值,那么追求良序公共生活的政治就无从谈起。从理论内容上看,对于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关注贯穿着生态政治学的始终,如果说生命政治学更侧重于强调人类生命本身的价值,那么生态政治学则普遍关注生态系统中一切具有关联性的生命要素——维护生命多样性本身也构成了实现生态和谐的重要环节。从理论目标上看,生态政治学指向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政治局面,其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解,这种和解绝不仅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更意味着社会化、政治化的人类与自身自然性的和解,意味着生命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和解。从特定议题上看,对于灾害与病疫的防护治理同样也是生态政治学的重要内容,拯救生命显然作为生态政治学的重要价值追求存在,这既是由其生态保护的意旨决定的,也是由生态学范式的系统关涉决定的,“自然(地球和宇宙)、生命、人、社会此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35](p3)。
(二)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相遇在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前文已述,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在范畴上都产生于西方现代政治所面临的治理危机,在内涵上都强调对现代性政治模式的反思与批判,在逻辑上都主张对技术理性、计数理性的人与自然的割裂实质的超越。现代性是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共同的理论标靶,是二者得以存在与发展的矛盾性动力源泉。“在马克思和康德那里,批判的目的都是为了阐明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含糊不清的东西,为了把一些被埋藏着的、规定我们思维方式的假定发掘出来,为了对这些假定进行公开检验”[36](p415)。批判反思现代性,不意味着彻底放弃现代性或陷入某种“反对一切”的虚无主义境地,用“虚无”去反击“存有”的错位批判并不适用于一种以“政治”作为主体话语的理论,只有通过批判反思,我们才不至于在现代性之中丧失自身一切非现代性的“灵韵”(瓦尔特·本雅明语),进而真正理解现代性的复杂意涵。
从词源上讲,“现代性”一词来自拉丁词汇“modernus”(现在、现在时),德国学者姚斯(Hans Robert Jauss)认为“modernus”一词出现于约公元5世纪,其原初意旨在于将基督教社会同旧的异教社会区分开来;在现实历史上,现代性的萌芽出现于15世纪后期[37](p1)。现代性不等于纯粹的“新”,它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必须与传统性、古代性、原始性等范畴形成对立才可能存在。因此,现代性对于非现代性而言,总是先天就带有启蒙者的优越性与主动性,这使得现代性总是站在传统与自然的对立面。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定目前尚缺乏共识,詹姆逊(Fredric R.Jameson)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其他的,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因而也就得出了“我们希望放弃对现代性进行概念陈述的徒劳努力”的结论[38](p31)。从其表征来看,现代性意味着经济重心由传统农牧业转向工业与信息产业,政治重心由神权与皇权统治走向以自由主义民主制为主导的权力分散化的政治制度,文化重心由约束性与控制性的传统教庙习俗走向强调主体解放与理性能力的个人主义文化氛围,社会结构重心由传统大家庭单位转向精密分工的多元化社会单位等。
生命政治对于人口的批量化管制,对于具体个人丰富属性的抽象化,对于部分社会群体的排斥与纳入,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现代性治理思维的体现。没有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思维模式,也就没有生命政治的高度专业化发展;而没有生命政治提供的人口与社群控制方法,现代性政治也不会走向空前高效的成熟运作状态。由此,部分学者将生命政治学定性为“与现代性逻辑一致”“服务于资本主义”[39]固然有其理由,但生命政治学不是为生命政治服务的指南术,其在分析生命政治化进程的同时也客观揭示出自然生命存在的可能性,这种隐性表达决定了生命政治学研究必然能够比一般的政治哲学反思更容易触动到现代性的某些逻辑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学的诞生即是现代性及其治理模式衰落的体现——“生命政治对自然性的回归,意味着关于现代性逻辑的单一化叙事的式微,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终结”[40](p62)。
同样,生态政治学也包含某些现代性的特质——它始终强调政治文明与生态境况的演进发展,强调诸政治经济因素间的效率配置与成果计量,呼吁以理性精神节制自然资源消耗。但与现代性不可逆转的进步史观,鼓吹个体理性与社会结构细化的观念体系不同,生态政治学体现出超越性的理论自觉:它直面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博弈,正视政治哲学与社会治理术之间的话语差异,接受不同历史观对待生态问题的态度差异。总之,生态政治学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矛盾性源于其多元的思想来源,一方面,现代性的确为生态政治学的诞生提供了进步性的历史观念,但另一方面,生物学、马克思主义等各色理论的介入使得生态政治学并不完全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治理术。
(三)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相遇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发展
前文已述,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都以生命的二重性,即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同时存在作为自身理论展布的前提,二者共同面对着人类内部与外部自然解放的理论问题。如福柯所言:“如今在写历史的时候,不可能不运用到直接地或间接地与马克思思想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也不可能不置身于一个马克思曾描述、定义过的境域中。”[41](p281)作为一门追求“人与自然双重协调和谐”[42](p27)的人类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从自然性与社会性两方面出发理解人的生命,力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迷雾中探索出一条通向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共同完成的解放之路,与生命政治学、生态政治学存在问题范式与文明愿景上的张力。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贸然作出“生命政治学/生态政治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粗粝论断,但亦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在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二者间的枢纽性意义。
生命政治学经常被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具有强烈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意味的后马克思主义、欧陆左翼激进理论等)思潮,其主要代表思想家福柯、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等人也都热衷于阐释马克思经典论述,如福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与控制时,援引了马克思的“用对生产的分析来代替对掠夺的谴责”[43](p37)方法,并在讨论规训与人口问题时大量论述马克思的相关思想;阿甘本并不像朗西埃等人那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反倒力图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当下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以生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更为深刻的批判性透视”[44](p114);埃斯波西托高度重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这种影响整个现代社会的剥削的一般过程,都是由马克思在其每一个步骤中重建的”[45](p82)……生命政治学者们普遍有“必须使用马克思主义范畴武器与思想工具”的理论认识,这也使得生命政治学研究决然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相断裂,更毋言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治理术指南”。
生态政治学包含一条清晰的马克思主义进路——以“红绿”为主要体现形式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力图将生态学思维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以此弥补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生态问题阐释的相对性的“理论空场”[28](p82)。如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中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解释与完善,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生态唯物主义”延展,布兰德在《全球环境政治与帝国式生活方式》中对“绿色资本主义”与“社会生态转型”问题的深入讨论等。生态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是成功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生态政治的“红绿”派提供了一个经典性的问题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以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主要代表的生态政治学者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欧美思想界中焕发出新的理论活力。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已经构成了一个互构互益的“生态系统”。
必须认识到的是,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也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性。在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主流之外,也存在着一些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者,如生命政治学者朗西埃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与阶级意识理论的否定[46](p118),生态政治学者柯布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与妄断[47](p175)等。这种理论局限一方面产生于当代欧美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理解的不系统、不全面、不客观,另一方面也源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对于思想界的浸染,为马克思主义贴上了负面标签。在思想界泥沙俱下、波诡云谲的今天,辨明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限度,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思潮良性交互的必然要求。
四、结语
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的相遇既是理论必然,也是现实要求。在理论逻辑层面,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同属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入思考的产物,二者都从强调“间性”、反对“孤立”、寻求“总体解放”的理论立场出发,凸显了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双重价值,表现出现代性反思与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兴味。在现实逻辑层面,疫情发生后的世界思想界普遍讨论生命作为一种生态系统要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此理论背景之下,生命政治学与生态政治学都将脱离原初的“技治主义”[48](p175)囹圄,共同向一种推动生命与生态伦理完善化,促进现代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寻索人与自然矛盾解决道路的积极政治哲学迈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的话语联动,将成为可以预见的未来理论趋势。基于对生命政治学、生态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三者理论关系的辨明,摆脱了视野局限的、超越了资本主义话语囹圄的、洞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生命政治学、生态政治学必将成为“为实现自由个性而开辟道路的鲜活的现实版本”[48](p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