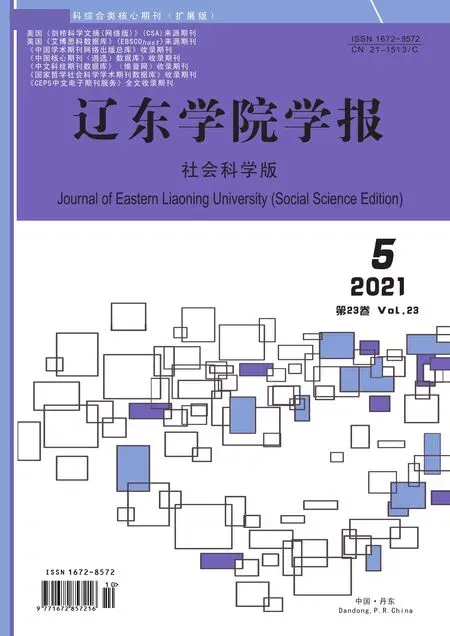再谈“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相关例证的考证讹误
——敬复胡铁岩先生
张 志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基础部,四川 成都 611130)
“我皇上”是清代官方规定的称谓当朝皇帝的专门术语,是判断清代作品写作年代的“时间坐标”[1]。在研究《春柳堂诗稿》时,张宜泉自序“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2]中使用的“我皇上”,即成为“证明张宜泉《春柳堂诗稿》自序写于乾隆朝的时间坐标”[1]。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所普遍认可。但胡铁岩先生不这样认为,在多篇文章中要么“回避”“我皇上”的“时间坐标”意义,要么举证“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这些观点能否成立,正如胡铁岩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尚待学界评价”[3]的。故前有张书才先生针对胡铁岩先生文中“忽略回避了‘我皇上’三字”[1]发文,重点辨析了“我皇上”三字的“时间坐标意义”:“综上所述,清宫档案、官修书籍、私人著述等历史资料皆可证明,古人都是用‘我皇上’、‘我皇’或‘今上’指称当朝皇帝,而不是也不能用来指称已经去世或已经退位的前朝皇帝。这是历史常识,且典制攸关,古人是不能也不会混称混用的。”[1]后有笔者对胡铁岩先生随后提出的“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的八个例证的质疑,认为这八个例证均为考证讹误,不能成立:“故我们就不应把古人偶然出现的错用、误用之例当成符合官方典制的可以正常使用之‘常例’,并用它去作为评判的标准,而应该是对文献作‘整体把握和理解’。”[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胡铁岩先生并不认同,近来又有《“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一文,一一为之辩护,且还提出“我皇上”已“具备了在辞书‘我皇上’词条下单独立项使用义项的条件”[5]的新观点。不过,“单独立项使用义项”的目标能否实现,恐怕同样“尚待学界评价”吧。坦率地讲,胡铁岩先生的回复并不令人信服。笔者虽才疏学浅,但也愿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就“复文”再提出拙见,就教于胡铁岩先生及各位方家。
一、关于《御制平定青海碑文》和《重建廉泉亭敬祀龙王记》中的“我皇上”
这两例都是误用、错用的显例,因胡铁岩先生回应的理由有相似处,故一并讨论。
(一)《御制平定青海碑文》中的“我皇上”
《御制平定青海碑文》由雍正皇帝于雍正二年亲撰,文中“我皇考圣祖仁皇帝睿虑深远”句,是对其父康熙功业的赞颂。胡铁岩先生主张“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举出的第一个例证即傅恒纂修的四库全书本文字,此本文字中“我皇考”作“我皇上”。窃以为此例不足以为证,是明显的误用,正确的符合官方规定的称谓是“我皇考”。为此,拙文举出故宫博物院编印的故宫珍本丛刊第047册中的《御制平定青海碑文》及现存于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碑文拓片(包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和江苏溧阳学宫遗址发现的同题碑文),均不是四库全书本的“我皇上”而是“我皇考”予以证明。这些例证既有底本出自“乾隆三十五年”的故宫珍本丛刊(编纂此书的正总裁也是傅恒)[6]7,又有最早出的雍正三年立石的碑文,应该说雍正原文是“我皇考”证据确凿,“我皇上”为误用是客观事实:“文献、碑石两相印证,事实确凿无疑。”[4]但遗憾的是,胡铁岩先生不予认同:
对于张志先生这一指责,笔者颇难理解。确实,《四库全书》本与《故宫珍本丛刊》本存在词语差异,但是用今人所编纂的《故宫珍本丛刊》中的稿本来否定《四库全书》本是不恰当的。雍正皇帝《御制平定青海碑文》作于雍正二年。根据检索,雍正皇帝撰写的《御制平定青海碑文》不仅在北京国子监刻碑树立,在全国其他地方也都有树立,其文字版本也不只有一种。到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时,相隔已有50年,而到《四库全书》编成时,时间更是超过了一甲子。也就是说,《四库全书》本的《御制平定青海碑文》是最晚的版本。众所周知,《四库全书》的编纂和审核是有极为严格程序的,最终以朝廷名义正式刊布。张志先生拿一个并未经过严格审核、也没有正式刊发的故宫保存稿本来否定《四库全书》正式刊本,是否合适,还望张志先生细酌。[5]
事实是《御制平定青海碑文》中的“我皇考”文字不是“今人”编纂,“故宫珍本丛刊”也不是“今人”编纂。该书的“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是:“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清)温达等纂.-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6(故宫珍本丛刊),本书与‘御制亲征朔漠纪略/(清)圣祖撰’等13种书合订。”[6]“圣祖”“温达”(1715年卒,曾随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官至大学士)“等”人都不是“今人”。故宫博物院只是使用了这个原就“珍藏”于故宫的版本近年“影印”出版而已。“珍本”者,珍贵重要的版本也。认定这个版本是“并未经过严格审核、也没有正式刊发”的,没有证据。如果这些“珍本”没有正式刊发,那么,它又如何被珍藏下来的呢?最让人遗憾的是,胡铁岩先生竟然说它是“稿本”。“稿本”不就是作者著作的底稿吗?如果这“珍本”真是雍正的“稿本”,那么,胡铁岩先生举出的四库全书本“我皇上”是误用、错用之词,不就明明白白、一清二楚了吗?哪还需要如今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拙文有图片显示,“珍本”是影印本文字,不是稿本。即便如此,这也丝毫不会影响到“珍本”中“我皇考”称谓用法的正确性。
另外,以“《四库全书》的编纂和审核是有极为严格程序的”为由,也不能证明此处的“我皇上”称谓符合官方的规定。《四库全书》的编纂和审核固然极为严格,但也不能说书中就没有讹误。乾隆皇帝自己“信手抽阅”就曾在书中发现“即有讹舛,其未经指出者,尚不知凡几”,故有乾隆皇帝“既有校对专员,复有总校、总裁,重重覆勘,一书经数人手眼,不为不详,何竟漫不经意,必待朕之遍览乎?若朕不加检阅,将听其讹误乎”[7]的指责。近年来,对《四库全书》讹误的研究就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某些卷首首行误出“荟要”考》[8]《〈四库全书·皮子文薮〉提要指误》[9]《四库全书〈诚斋集·诗集〉勘误》[10]《四库本〈牧庵集〉所收〈唐诗鼓吹注序〉辨误》[11]《论〈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的误辑问题》[12]等多篇文章。如果再算上《四库全书总目》的话,这样的研究文章更是不下数十篇(1)近日有消息称:“新订《四库全书》项目——《四库全书丛编》文化工程项目,在《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晓岚的故里河北省沧州正式启动。该工程集编纂、整理、勘误、缮录于一体,力图对《四库全书》存在的问题进行勘误修正,并增加了近世以来对库书文献研究的新成果。”可见,《四库全书》中存在讹误是客观事实。见张杰《问世230多年来首次〈四库全书〉正被“一个字一个字重抄”》,《华西都市报》,2021年4月9日,第13版。,可见,上述理由不能证明“我皇上”不是编纂过程中出现的讹误,更不能确认它就是雍正的原文。
同样,以《四库全书》本是“最终以朝廷名义正式刊布”的“最晚的版本”为理由,也不能说明此处的“我皇上”是正确的用法。因为,保存至今的文字作“我皇考”的雍正三年“勒石国学”的《御制平定青海碑文》石碑,也是以“朝廷名义正式”立碑的,为“雍正皇帝撰文并正书,碑阳满汉文合璧”[13],只是文字勒于石碑上而已。而且,辨析“我皇上”是否符合官方规定的正确用法,是否为雍正的原文,正确的做法是应考察其最早出现的文献,怎么会以“最晚”为标准呢?再说,这里不同的称谓用语既然都出自为立碑而撰写的“碑文”(《御制平定青海碑文》),而“碑文除皇帝御笔外,均为清代官方馆阁体”[14],那么,考察太学碑上的文字不就是一种最优先的选择吗?胡铁岩先生无视这最早且为“皇帝御笔”的石碑文字,却以“今人”编纂为由质疑“故宫珍本丛刊”文字(2)何况编纂此书的正总裁也是傅恒,且从《平定准噶尔方略序》的序言落款“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仲春月吉御笔”来看,此书的编纂时间也是很早的。有乾隆“御笔”作序,则知审核也应严格。故胡铁岩先生所谓“未经过严格审核”云云不符合实际。见故宫博物院编《平定准噶尔方略》(第一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这样的回应是否合适,也望胡铁岩先生细酌。
至于胡铁岩先生的“张志先生若能根据其所发现的词语差异,来对‘我皇上’的不同文本加以比较,探讨版本上存在的差异及其造成的原因,倒不失为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但张志先生却未能如此做,这是很令人遗憾的”[5]一段话,笔者已有所比较,故不再回应。
这里,再从语境和行文对象上多说一句,既然此碑文是雍正皇帝本人所撰写,那么,雍正作为当朝皇帝,会使用称谓当朝皇帝的专用词语“我皇上”去称谓他已故的父亲前朝皇帝康熙吗?雍正会出现这种既违背现实又违背朝廷有关规定的低级错误吗?何况文中“圣祖仁皇帝”明确指向康熙,此文也是写给天下人看的!雍正此处行文、用词完全不具有误用、错用的可能性,“我皇考圣祖仁皇帝”才是文中唯一正确的用法。
(二)《重建廉泉亭敬祀龙王记》中的“我皇上”
《重建廉泉亭敬祀龙王记》是同治本《安远县志》中收入的何光的一篇文章,文中的“我皇上”是何光在借鉴、抄录《时应宫记》原文时出现的错误书写,它显然是不符合官方规定的一例错用称谓,胡先生文中存在考证讹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胡铁岩先生同样也不认同:
张志先生对这段文字中出现的“我皇上”用于称谓前朝皇帝的事例,在无法直接否定的情况下,又质疑其用词的正确性:“这段文字颇为奇怪:在‘康熙五年’与‘越乾隆之七年夏’之间,插入的一段文字中有‘雍正二年,我皇上于丰泽园北,建时应宫以享之’之句,着实让人费解。”也就是说,又和对“例一”的态度一样,既然无法否定,那就说是误用,所以不算数。
对于张志先生这样的质疑,笔者实感无奈。因为问题讨论的是有没有将“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的事例,而不是用“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对不对的问题。张志先生以该文用词不妥为由来否认《重建廉泉亭敬祀龙王记》中“我皇上”是称谓前朝皇帝例子的做法,显然已经偏出了问题的讨论范围。[5]
这样的回应也是让人“实感无奈”的。
段玉裁曾谈到“校书难”问题:“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14]365这种观点应该对我们的讨论有所启示。胡铁岩先生说“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这就是“立说”,“立说”则需要“定其是非”。显然,胡铁岩先生的“立说”要成立,就不仅仅只是找到一些所谓的“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的事例来这样的简单,其事例本身就需要经得起质疑,需要“定其是非”。
实际上,胡铁岩先生在文章中也是要问“是非”的,这是其写作目的:
拙文举隅之目的,只是想说明:虽然“我皇上”等词语作为官方术语,其含义的确是专指当朝皇帝的,但不是绝对的,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特别是非官方场合和非官方文章中,还是存在着不规范使用情况的。张宜泉长期“隐下僚”,其《春柳堂诗稿》自序亦非官方正式文书,故《春柳堂诗稿》自序中的“我皇上”一词亦存在不规范使用之可能。诚望学界在今后使用《春柳堂诗稿》自序中“我皇上”一词作为该书写于乾隆时期证据时充分考虑到存在例外这一因素。[15]
这里,从那些错用、误用的“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的“举隅”中推断出《春柳堂诗稿》自序中“亦存在不规范使用之可能”,不仅也偏出了胡铁岩先生所声称的讨论只限于“有没有”的范围不说,而且更在其“诚望”中隐含了“是非”,即暗示着“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的“立论”是对的。这些事例是可以作为依据去推断《春柳堂诗稿》亦存在着这种“不规范使用之可能”的——《春柳堂诗稿》中的“我皇上”是称谓前朝皇帝,进而得出胡铁岩先生想要的答案:“我皇上”“并不具备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证明力”[5]。所以,胡铁岩先生不是不问“是非”,不是不知道要对“立说”本身“定其是非”,相反是知道的。故胡铁岩先生的回应不能成立,且让人遗憾,因为张宜泉自序中“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中的“我皇上”是清楚无误地指向着当朝皇帝乾隆的,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二、关于《康熙侠义传》和《马贼讨俄之檄文》中的“我皇上”
《康熙侠义传》是通俗小说,《马贼讨俄之檄文》一文来自报纸。
(一)《康熙侠义传》中的“我皇上”
关于此例,拙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里,要么把“我皇上自定鼎以来”视为一个“固定语句”,则此语专指顺治皇帝,要么把其中的“我皇上”一词看成是称谓当朝皇帝的官方专门术语,指康熙皇帝,二者必居其一。但无论选哪一种用法,其结果都显示出《康熙侠义传》的上述用语是符合官方对“我皇上”或“我皇上自定鼎以来”的规定和社会习惯用法的。[4]
胡铁岩先生认为这是“机辩”:“看了张志先生的这些机辩,笔者只能付之无奈。既然可以做二选一的逻辑选择,就说明张志先生的主张本身具有或然性,如果真有人选择是指顺治皇帝,岂不令张志先生尴尬?”[5]如果真的令人尴尬,那也是胡铁岩先生尴尬在先。说“我皇上自定鼎以来”是固定语句专指顺治皇帝的是胡铁岩先生,说此语又是指当朝皇帝康熙的也是胡铁岩先生,有其文字为证:
此处出现的“我皇上自定鼎以来”一语,本是清初的一个固定语句,专门用来指称顺治皇帝。然根据小说的故事背景,及此段文字的前后关联,显然又是指康熙年间的当朝皇帝。[15]
把这段文字再简化一下,不就是说“我皇上自定鼎以来”一语,本是“专门用来指称顺治皇帝”的,现在“根据”“关联”,“显然又是指康熙年间的当朝皇帝”,这“当朝皇帝”不就是康熙吗?只是胡铁岩先生又据此进一步认为“我皇上”一词“其使用含义已经泛化,是指自定鼎以来的皇帝们,是属泛指”[15]而已。坦率地说,拙文的上述表述受到了胡铁岩先生文章的影响。即便如此,此例也不支持胡铁岩先生的观点,因为“我皇上”的“泛指”也只是限于这个特殊的“固定语句”之中。
至于拙文说“我皇上”似乎存在着“我国的皇上”省写的可能性,也是因为它出自通俗小说,口语性强,文中也有“请我国圣人入关”等用语。这不是关键性理由,即便抛开此说,也并不影响拙文的说服力。
(二)《马贼讨俄之檄文》中的“我皇上”
此例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它“译”自日文(胡铁岩先生文中缺失此信息),不是中文原文。用译自日文的事例来举证是不可靠的,因为不是一手材料。但胡铁岩先生却回应说:
就一般情况而言,确实存在翻译不一定准确的可能性,但在这个具体事例中,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随便翻翻光绪年间的各种报刊文牍,“我皇上”“圣天子”触目皆是,是使用频率极高的常用词语,而且属于不允许用错的词语。说常驻中国的日本记者不知道“我皇上”一词的准确使用含义,张志先生您自己相信吗?[5]
胡铁岩先生一会儿说“我皇上”一词“属于不允许用错的词语”,一会儿又极力举证“我皇上”“还是存在着不规范使用情况的”,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可信的?再者,光绪年间的各种报刊文牍不会用错,并不意味着“译”自日文的此文就不会用错,这里没有必然的联系。至于说“常驻中国的日本记者”就知道“我皇上”的“准确使用含义”,则更是一种主观的愿望。胡铁岩先生问我信不信,我当然不信。于此例来说,我更愿意相信这位日本记者不一定知道“我皇上”的“准确使用含义”。不要说外国人了,就连中国人也未必都知道:
当然,诚如朋友所指出,曾有学者认为,假定张宜泉出生于乾隆末年,嘉庆二十四年中举,用“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如何如何,也还是恰当的;“我皇上”三个字,充其量只能表明张宜泉是乾隆年间出生的,而不能“规定”他的整个一生都在“乾隆年间”度过,更不能成为《诗稿自序》也必定作于“乾隆年间”的“坐标”。毋庸讳言,这样的认识和理解,有违历史实际,是确实错了的。[1]
连中国的一些学者都对“我皇上”的使用有错误认识,何况是位外国人呢?哪怕他是所谓的“常驻中国的日本记者”(但不知胡铁岩先生何以断定是“常驻”)。所以,即便把日本记者想得太好了,也是否认不了这个事例本身的缺陷的。
至于这里的“我皇上”是不是“我国皇上”的省写,从“凌辱我皇上,蹂躏我邦土,戕害我生民”的排比句式来看,从它翻译自日文来看,省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这也不是关键性证据,即便抛开它不论,也不会影响到拙文对此例本身局限性的辨析。不过,在此段文字的最后,胡铁岩先生以“同一质疑方法不该重复使用的”话来回应,却让人诧异、困惑。
三、关于《宋元经解删要序》中的“我皇上”
张廷玉文《宋元经解删要序》中的“我皇上”确指当朝皇帝雍正,惟因此文就作于雍正朝,而非胡铁岩先生主张的乾隆朝,胡铁岩先生的观点是对张廷玉文的曲解。但胡铁岩先生不这样认为:
故张廷玉《宋元经解删要序》写于乾隆初年本不应成为问题,但张志先生在解读这段话时,误将“又十余年”解为张廷玉写序的时间,从而导致对《宋元经解删要序》中“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的质疑。[5]
这个回应不符合事实。拙文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一句话是把“又十余年”“误解”为张廷玉写序的时间。胡铁岩先生为了把张廷玉写序的时间拖入到乾隆年间,从而造成“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的假象,把张廷玉文中的一处表述时间的文字摘取出来,又与另一篇文中提到的另一件事的时序强行连接在一起,这才是误解。请看张廷玉文:
康熙癸巳,望溪蒙诏入南书房,与共晨夕,叩其删取大指,颇与余同志,盖十余年间,虽舟车奔迫,未尝有一日之辍焉。其取之慎,凡注疏大全,皆数周而后及此。首《诗》《书》,次《易》,次《春秋》,皆毕于辛卯之秋。其冬,以牵连赴诏狱,在狱始治《三礼》,而苦其书之难致。及出狱未兼旬,荷圣祖仁皇帝搜扬,置诸禁近,俾校文史,赐以第宅,资粮、饮食、衣服,一取给于内府。我皇上嗣大历,服推先帝遗德,赦其子孙宗族并归田里,其心益宽然,一无所累。公事之暇,日有孜孜,又十余年,而后诸经之说续备。其所删取,又再遍焉。望溪向余每言两朝圣天子覆帱之恩,未尝不流涕也。[16]501-502
张廷玉文时序清楚,先说到康熙,再说到雍正,根本没有提到乾隆。这里引录一段拙文的相关分析:
“荷圣祖仁皇帝搜扬,置诸禁近,俾校文史,赐以第宅,资粮、饮食、衣服一取给于内府”,这是康熙的“覆帱之恩”。“我皇上嗣大历,服推先帝遗德,赦其子孙宗族并归田里,其心益宽然,一无所累”,这是雍正的“覆帱之恩”。故把康熙和雍正两朝皇帝合称为“两朝圣天子”,表意清楚,指向明白。
至于胡先生将在《清史稿》列传七十七中摘出关于方苞“三年还京师”的记载与张廷玉本文中“又十余年”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时间纪年连在一起,说“从雍正三年到雍正十三年正好是十年”,进而推算出张文的写作“应该已经进入乾隆初年”的观点,更是不符合文本实际的推论,难以成立。从张廷玉文来看,“又十余年”应上接“赦其子孙宗族并归田里”的那一年算起,此事正是雍正元年的事。另外,《清史稿》说“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而后才是“雍正二年,苞乞归里葬母,三年还京师”。所以,从“世宗即位”的雍正元年算起,到“又十余年”,这样前后时间算下来,恰好是雍正十二三年左右。故胡先生所谓“该序文的写作时间应该已经进入乾隆时期”的观点无法成立。(着重号原有)[4]
拙文的这段分析存在所谓的“误将‘又十余年’解为张廷玉写序的时间”的错误吗?将“三年还京师”与“又十余年”连在一起来推断时间,才是真正的误解。
让人诧异的是,胡铁岩先生在“复文”中,竟然又把与“又十余年”相连的时间换成了更靠后的“雍正四年”,说“从雍正四年开始的‘又十余年’本身就已经进入乾隆年间了”[5],看到这里笔者也实感无奈。因“又十余年”上接的时间是“赦其子孙宗族并归田里”的那一年,而这一年正是雍正元年。从雍正元年到“又十余年”,不正好是十一二年或十二三年吗?怎么会进入乾隆年间了?对张廷玉文作这样的解读,是帮不到胡铁岩先生观点的,即使找出再多的材料来作推论,似也无济于事。
“两朝圣天子”同样指意明确,文中确指康熙和雍正。如果胡铁岩先生主张的张廷玉序已进入到乾隆朝,那为何张廷玉会说是“两朝”?加上乾隆明明是三朝,为何偏偏不提乾隆当朝?因乾隆皇帝对方苞也是有“覆帱之恩”的。为何方苞不言、张廷玉不写?有合理的解释吗?再者,方苞和张廷玉都是皇帝的亲近大臣,“我皇上”称谓使用在其各篇文章中皆清楚无误、丝毫不爽。关于此点,张书才先生和笔者分别已有论述,不赘。
值得一说的还有胡铁岩先生文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笔者之所以在《举隅》中要选张廷玉《宋元经解删要序》为例,除了该例本身的“我皇上”一词确实是指称前朝皇帝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序文中出现“两朝圣天子”之用语,作为与“我皇上”性质相同的用于称谓皇帝的特定用语,虽然不能对“我皇上”的称谓含义起到直接证明作用,但至少可以起到佐证作用。这一点,张志先生似乎也意识到了:“毋庸讳言,张廷玉文中的‘望溪向余每言两朝圣天子覆帱之恩’之语,义指当朝和前朝的两朝皇帝无疑。但即便如此,要想得出胡先生所希望的‘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的结论来,也是颇有难度的。”[5]
在这段文字中,胡铁岩先生提到了我的“意识”,但却不是我的意思。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如今再明确一下:“两朝圣天子”“义指当朝和前朝的两朝皇帝无疑”,指康熙和雍正;但是即便如此,也无法得出“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的结论来。拙文的表述是清楚明白的。但在胡铁岩先生的文中,我的意思已经变成不是这样的了。因有文前“除了该例本身的‘我皇上’一词确实是指称前朝皇帝外”一句的限定,也就是说,在已然认定“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的情况下,胡铁岩先生通过“‘两朝圣天子’之用语,作为与‘我皇上’性质相同的用于称谓皇帝的特定用语,虽然不能对‘我皇上’的称谓含义起到直接证明作用,但至少可以起到佐证作用”的连接,就把原本不是我的“意识”,硬是非常巧妙地转换成了我的意思,即:“我皇上”如同“两朝圣天子”一样都是可称谓前朝皇帝的。这里需要郑重申明:我没有这样的“意识”。拙文的上述表述不能对胡先生的观点起到佐证作用。故胡铁岩先生又提出的“‘圣天子’可以用于称谓前朝皇帝”[5]的说法,则既“不能对‘我皇上’的称谓含义起到直接证明作用”,也不能起到相应的佐证作用,何况还属于“偏出了问题的讨论范围”之话题,故恕不再论。
四、乾嘉交替时期文稿中的“我皇上”
“此三例都非常特殊,处于退位皇帝和继位皇帝交替的时段里。”[4](3)其实“例六”不能成例,“此三例”实只两例。因伊秉绶诗中并无“我皇上”用语,且虽有“六十一年岁丙辰”句写嘉庆元年事,但诗中“于维太上恩高厚,皇帝大孝作元后”句,却是用“太上”称谓前朝皇帝乾隆的,称谓无误,符合官方规定。今借此机会对拙文作出修正,特此说明。这是拙文的观点。也就是说,“既是特殊情况,‘我皇上’一词称谓前朝皇帝也就只能限于乾隆、嘉庆两朝间的交替时期,且应是极个别大臣的私意所为,而不能进一步将其视为清代的通例准则。否则,如果以乾隆朝纪年一直可到‘乾隆六十四年’为依据的话,则胡先生举出的‘例四’‘例五’‘例六’三例,不是也都符合‘我皇上’称谓当朝皇帝的规定了吗?”[4]胡铁岩先生如果要否定这些看法,就应该对拙文中关键性的“只能限于乾隆、嘉庆两朝间的交替时期”的观点予以批评,证明它是清代的普遍现象。但胡铁岩先生却不是这样,而是转移了话题,把回应放在了“嘉庆四年,宫中宪书为乾隆六十四年”这类时宪书“适用范围”的大小上:
张志先生试图将这类事例的适用范围尽量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其所提出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行为人只是个别人,“且应是极个别大臣的私意所为,而不能进一步将其视为清代的通例准则”,“且只限于乾隆嘉庆两朝之间极少数大臣的文字中”;二是只限于宫内,“而且,从‘内外奏章’的用语看,也就包括了官方民间的一切文章奏折,它们都要‘另书新元’没有例外”。但张志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得到相关史料的支持(例略不引)。[5]
这里,胡铁岩先生的回应其实都是误解。
第一,拙文认为在乾嘉交替时期称谓乾隆皇帝为“我皇上”的是“极个别大臣的私意所为”,但胡铁岩先生的认识正好相反,认为“不是极少数大臣私下所为,而是按照嘉庆皇帝的明确指示、全国统一行事的”[5]。那么,依据何在呢?胡铁岩先生在“复文”中举出了《春冰室野乘》和《清稗类钞》中的两条材料,其内容大致相同:“高宗内禅后,已颁行嘉庆元年宪书。嗣仁宗面谕枢臣,命除民间通行专用嘉庆元年一种外,其内廷进御,及中外各衙门,与外藩各国颁朔,皆别刊乾隆六十一年之本,与嘉庆本并行,以彰孝敬之诚。自是两本并行者历四岁,至高宗升遐后始已。”原来胡铁岩先生是把嘉庆皇帝命两种“宪书”并行当成了依据。这两条材料明明是说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四年,时宪书可“两本并行”,这才是“嘉庆皇帝的明确指示”。嘉庆哪有对“我皇上”称谓的“适用范围”问题做了什么“明确指示”、需要“全国统一行事”?能把两本宪书的并行使用与“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不是极少数大臣私下所为,而是按照嘉庆皇帝的明确指示、全国统一行事的”等同看待吗?即便能得到乾隆本宪书的人数再多(材料显示是二品以上大臣),也不一定意味着用“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的人数就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亦即乾隆纪年的时宪书“适用范围”再大,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用“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的大臣就多,更谈不上这“是按照嘉庆皇帝的明确指示、全国统一行事的”,它们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回应否定不了拙文的称谓乾隆皇帝为“我皇上”“是极个别大臣的私意所为”的观点。
第二,拙文“从‘内外奏章’的用语来看,也就包括了官方、民间的一切文章和奏折,它们都要‘另书新元’,没有例外”[4]这段文字,是针对乾隆皇帝之语作出的分析,是说乾隆维护“我皇上”一词作为当朝皇帝称谓用语的态度,并非针对这类时宪书“适用范围”的大小。请看原文:
而乾隆的意思是:
朕亦只令于宫廷陈设,及颁亲近王大臣。而各省颁行,仍俱系嘉庆年号,内外章奏,亦一体令书新元。
可见,乾隆皇帝维护“我皇上”一词作为当朝皇帝特定术语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从“内外章奏”的用语来看,也就包括了官方、民间的一切文章和奏折,它们都要“令书新元”,没有例外。故“令书新元”也就根本不只是针对官方而言的朕“令”了。(着重号原有)[4]
乾隆要求“仍俱系嘉庆年号,内外章奏,亦一体令书新元”,当然是希望宫内、民间从嘉庆纪年角度来使用符合官方规定的皇帝称谓用语“没有例外”了。不过,乾隆的愿望没能实现,还是有一些宫内、民间的“章奏”没有做到“令书新元”。拙文的这段分析应是符合乾隆朕令实行的实际的。乾隆希望“令书新元”,但嘉庆另有想法、官方衙门不遵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皇上”用来称谓乾隆皇帝就是嘉庆的“明确指示”和全国的“统一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嘉庆面谕中有“命除民间通行专用嘉庆元年一种”的表述,即为命令在“民间通行专用”的是嘉庆纪年的时宪书,也就是说,是嘉庆皇帝试图将这类时宪书的“适应范围尽量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在“内廷进御,及中外各衙门,与外藩各国颁朔”之中,哪里是所谓的“全国统一行事”?胡铁岩先生说《春冰室野乘》和《清稗类钞》这两条材料常见,问我“为什么没引”[5],原因就是这些关涉时宪书“适应范围”的材料与“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的讨论没有直接的关系,故不引也罢,何况引了,不正好说明乾隆纪年的时宪书“适应范围”只在“内廷”“衙门”“外藩各国颁朔”中这些“最小的限度之内”吗?
最为重要的是,时宪书的“适应范围”大小与“我皇上”的称谓问题不能画上等号,胡铁岩先生在“复文”中举出的两条乾隆纪年的材料,就算可以证明“以乾隆年号纪历是通行做法”“各类方志在记载外地官员的任职、‘恤荫’时,也都有用例”[5],但这些“用例”有“我皇上”一词使用吗?能证明“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是嘉庆皇帝的“明确指示”、是“全国统一行事的”吗?拙文一再强调,在乾嘉交替时期存在着一些“我皇上”称谓前朝退位皇帝的事例是属于特例,更不是“清代的通例准则”。如果仅仅因为它的存在,就把特定时期的、也是个别现象的特例作为清代的通例准则,创立新说,不是仍需要“定其是非”吗?把“特殊”当成“一般”,把“个例”当成“通例”,把“偶然”当成“必然”,是不能使“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的观点成立的。所以,不管胡铁岩先生再找出多少这些“我皇上”称谓乾隆皇帝的事例来,也仍然改变不了它们属于特例的性质,其“立论”不能成立。
要之,胡铁岩先生所举出的相关例证确实都存在考证讹误,也是客观事实,它们不能支持“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的观点。
五、增补的两例“我皇上”和一例“我皇帝”考辨
(一)《皇清诰封资政大夫一等侍卫内务府总管加一级保公碑记》中的“我皇上”
《皇清诰封资政大夫一等侍卫内务府总管加一级保公碑记》是《雪屐寻碑录》中收录的一篇碑文,有一段文字涉及“我皇上”:
甫十一岁,恭值我世祖宪皇帝选拔侍卫从人员,因公动合礼法,遂擢为执御,由谨慎勤劳迁二等侍卫。于康熙三十五年从征中路,奋勉前驱,迨平定沙漠,奏凯旋师,屡迁为一等侍卫。于雍正元年兼养心殿总管,督理圆明园工程事务,兼总管。于雍正二年为协理崇文门税课副使。于雍正三年升为管理崇文门税课正使。于乾隆二年十月初九日,公以疾卒。十月十三日,奏事郎中张文彬代为转奏。本日奉旨:保德患病淹逝,深属恻然,著锡予内务府总管职衔,钦此钦遵。内大臣户部尚书兼内务府总管海望,亲至柩前,口传谕旨,吊恤存问,礼遇之隆,人臣蔑以加矣。计公年六十三岁,身受我皇上天恩,生荷教养,卒叨追嘉,凡出入用委四十余年,一应公务,未尝遗误,而悉称得宜,则公生平之节俭、正直、谨恪、公忠,概可知矣。[17]9-10
由于保德生于康熙十二年,卒于乾隆二年,且从十一岁开始当差,故胡铁岩先生说:“‘身受我皇上天恩,生荷教养,卒叨追嘉,凡出入用委四十余年’的‘我皇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单指乾隆皇帝,而是包括前朝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5]
其实,此例证作为证据本身仍需要“定其是非”。
第一,惟因碑文中有对皇帝称谓的错误用法,故可合理怀疑文中的“我皇上”称谓属于误用、错用之例。保德生于康熙十二年,满十一岁当差时,是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的庙号是“圣祖”,可碑文却是“我世祖宪皇帝”,称谓错误。“世祖”是顺治皇帝的庙号,而“宪皇帝”又是雍正皇帝的谥号,“我世祖宪皇帝”均非康熙皇帝的庙号、谥号,称谓全错。由于文中有对皇帝称谓的错误用语,则在此语境中同样是称谓皇帝的“我皇上”一词也极可能是一处错误用语。故此例硬要作为证据也是有先天不足之处的,其本身的正确性就让人怀疑。
第二,退一步说,此例按照胡铁岩先生的观点“不可能是单指乾隆皇帝”,那也就意味着此例是基于在称谓当朝皇帝的基础上又可能包括了前朝皇帝的特殊使用情况,是个特例。这个可能的既称谓了当朝皇帝又包含了前朝皇帝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性意义:那种不加任何条件限制的所谓“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反过来说,也就表明不存在“我皇上”具有跳过当朝皇帝而只称谓前朝皇帝的所谓普遍用法,且此用法更不具有“时间坐标”意义。因此,不能以这个特例作为标准去分析、推断“我皇上”在古籍中的“时间坐标”。
要之,由于此例本身就需要“定其是非”,故作为证据同样存在着先天不足。
(二)《大清搢绅全书》序中的“我皇上”
乾隆丁酉本(四十二年)《大清搢绅全书》序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我皇上统一函夏,澄叙官方,法度整齐,既慎简于尔庶司百执事,定位分职,咸有攸宜,宵旰持衡。其间升降黜陟。新命之下铨部者,无日无之。[18](4)此材料由任职于国家图书馆的好友于鹏先生代为查找,谨致谢忱。
胡铁岩先生把这里的“我皇上统一函夏”解释为“‘统一函夏’是指大清定鼎”[5],再以《日下旧闻考》中“我国家统一函夏,定鼎建都”一段文字为依据,得出结论说“与‘统一函夏’并用的是‘定鼎建都’,显然,序里所说‘我皇上’不是指当朝皇帝,而是指开国之君”[5]。而这个开国之君是谁呢?胡铁岩先生又据《国朝传宝记》中有“文皇帝之臣服函夏”[5]一句,认为即是“文皇帝”皇太极。这样,此处的“我皇上”就称谓前朝皇帝皇太极了。
这恐怕又是胡铁岩先生的误读。
第一,按照胡铁岩先生的逻辑,如果“‘统一函夏’是指大清定鼎”,那么,“我皇上统一函夏”即与“我皇上定鼎建都”同义,亦即与“我皇上自定鼎以来”同义——都在说“定鼎”,而这里的“我皇上”是指皇太极。然而胡铁岩先生不是曾说过“‘我皇上自定鼎以来’一语,本是清初的一个固定语句,专门用来指称顺治皇帝”的话吗?那么,“统一函夏”或曰“定鼎以来”的“我皇上”到底是指“开国之君”皇太极呢,还是指顺治皇帝?显然,两种看法相互抵触。故将此处的“我皇上”解释为称谓前朝皇帝皇太极,没有说服力。
第二,大清缙绅录的版本演进过程证明此“序”中的“我皇上”应指当朝皇帝乾隆。“有清一代,缙绅录广为刊刻,有官刻、坊刻两途,数量甚多,具体书名则有《爵秩全览》、《大清缙绅全书》、《大清中枢备览》、《爵秩新本》、《爵秩全函》、《缙绅新书》、《大清日新职官录》、《大清最新百官录》、《职官录》等等不同称呼。”[19]302《大清搢绅全书》是最通行的书名,序中有“我皇上统一函夏”文字者,出现在乾隆朝。现能查到的叶一栋序于乾隆戊辰春(十三年)的《满汉缙绅全本》(5)此材料由任职于国家图书馆的好友于鹏先生代为查找,谨致谢忱。序无“我皇上”文字,可知有“我皇上统一函夏”文字的“序”应写于此后的乾隆年间。于鹏先生代为查得的乾隆丁酉本(四十二年)《大清搢绅全书》,包括胡铁岩先生查到的乾隆五十八年本及至晚清的众多版本皆已有此文字之“序”。可见序者在此“序”中始提及的“我皇上”指当朝皇帝乾隆无疑。
第三,史实证明此“序”中的“我皇上”是指当朝皇帝乾隆。完成清朝统一大业的正是乾隆皇帝。1644年清顺治帝虽定都北京,清朝建立,但社会动荡,边疆不稳,战事频繁。“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连续向西北等地用兵,最后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一个空前盛大的王朝。”[20]286故清朝真正实现国家统一是在乾隆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随着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完成了天下一统,乾隆四十二年本《大清搢绅全书》“序”中就有了“我皇上统一函夏”的文字,这显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序者对当朝皇帝乾隆“统一函夏”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如果说此序中的“我皇上”是指皇太极或别的什么皇帝,那么,明显与史实不符。故此处的“我皇上”定是称谓当朝皇帝。
要之,“我皇上统一函夏”中的“我皇上”称谓的是当朝皇帝乾隆,说它是指前朝皇帝皇太极亦属考证讹误。
(三)《重修缸窑岭伯灵庙碑记并序》中的“我皇帝”
《重修缸窑岭伯灵庙碑记并序》由侯廷弼作于咸丰元年,序中有“迨我皇帝定鼎以来”[21]句,胡铁岩先生认为“我皇帝”指“历代皇帝”[5],符合实际。不过,此句式虽与“我皇上自定鼎以来”大致相似,但“我皇帝”似不可“与前述例七《康熙侠义传》中‘我皇上’用法对看”[5],因为摘出的“我皇帝”一词与“我皇上”的称谓含义是有所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
“我皇帝”指“历代皇帝”,但“我皇上”则指当朝皇帝。罗国俊作于嘉庆三年的《圣驾释菜临雍讲学礼成恭记连珠九首》一文中,“我皇帝”与“我皇上”是分别使用的,所指不同,且文中对清朝各皇帝的称谓用语皆清楚无误:
中曰彝伦堂,有圣祖御书赐额,御制祭酒箴。世宗御书文行忠信额。至我太上皇帝于乾隆二年大成殿易盖黄瓦,三十年钦颁周笵彝器,凡十五年建辟雍宫于集贤门内,以复古制。是年二月亲行释菜,御制《临雍讲学诗》《三老五更说》,堂哉皇哉,诚千载之盛举也。迨我皇帝践祚以来,凡郊、社、宗庙以及经筵诸大典,罔不恪遵庭训,次第举行。今陬二月之吉,圣驾释菜临雍讲学,典至隆也。惟我皇上聪明天亶,仁孝性成,尊养兼隆迈舜文之大孝,英贤并育绍孔孟之心传……[22]1421
文中“圣祖”为康熙,“世宗”为雍正,“我太上皇帝”为乾隆,“我皇帝”泛指清代历任皇帝。惟因文中已称乾隆皇帝为“太上皇帝”(当时还健在),则“我皇上”必称谓当朝皇帝嘉庆。且嘉庆皇帝又恰于“嘉庆三年即举临雍之典”[23]29,与文中“今陬二月之吉,圣驾释菜临雍讲学,典至隆也”之句正好印证,而这正是罗国俊去世的前一年。故文中“我皇上”必称谓当朝皇帝嘉庆无疑。在此语境中,针对不同对象,罗文表述分明,用语准确。这是“我皇上”与“我皇帝”称谓内涵不同的力证。可见用此序中的“我皇帝”来支撑其说,不具说服力。更何况它还存在于所谓的“固定语句”之中呢!
要之,将“我皇帝”与“我皇上”混为一谈,亦属考证讹误。
综上所述,胡铁岩先生所举出的例证,都存在着各种不足,皆不能支持“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的观点,其间存在着考证讹误是客观事实。对胡铁岩先生“立论”最为有利的材料是“我皇上自定鼎以来”句式中的“我皇上”以及乾嘉交替时期的个别用例,而这些例子要么恰恰是出自“固定语句”,要么是在特定时期,都属于特例。特例是无力支撑“立论”的。至于个别的错用、误用之例就更不足以“立论”成说了。所以,“我皇上”的“时间坐标意义”能够将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限定在乾隆朝,曹雪芹与他晚年在北京西郊结识的朋友张宜泉确实生活在同一时空。
最后,顺便说一句,我的基本观点已如上述,如没有全新的材料出现,恕不再回应,还请胡铁岩先生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