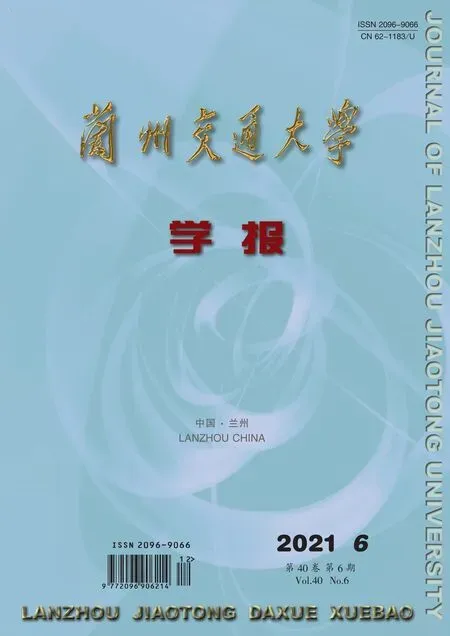随物化嫌隙,明时续故谊
——苏轼惠州致程之才书札探论
张小花
(兰州交通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
苏轼在被贬谪惠州期间与断交四十二年之久的表兄兼姐夫程之才冰释前嫌、重修旧好,在短短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书信往来频繁,写给对方的书札今存七十五通,所占比例为苏轼惠州所存书信的三分之一,是与他来往的亲友中书信存留最多的一位。这些信札全部写于绍圣二年正月至绍圣三年三月,即程之才任广东提刑期间。书札内容丰富,涉及苏轼谪居惠州时期生活和精神的各个层面。考察其中的细节,可知苏程二人对亲情的珍视不仅化解了两家四十多年的仇怨,而且消除了政治斗争投射在彼此身上的阴影。程之才对苏轼的关怀和暗中保护不仅改善了苏轼的贬居生活,也为他提供了可贵的情感支持和心灵慰籍,支撑他度过了内外交困的人生逆境。信札的内容对于了解苏轼在惠州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态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既勇于为义又小心畏惧的行为局促,既渴望北归又不得不处处为家的矛盾心理在书简中交替出现,仔细分析其中的缘由,可知苏轼在亲情、友情的支持下应对政敌打击和生活困境的生存智慧。
一、苏程两家结怨缘起与释憾经过
程之才,字正辅,苏轼表兄、姐夫。有关苏程两家的恩怨和释憾经过,《齐东野语》卷十三记载详细:
老泉《族谱亭记》,言乡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盖苏与其妻党程氏大不咸,所谓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诗,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辞甚哀,其怨隙不平久矣。其后东坡兄弟以念母故,欲相与释憾……坡之南迁,时宰闻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辅为本路宪,将使之甘心焉。而正辅反笃中外之义,相与周旋之者甚至。坡诗往复唱和中,亦可概见矣。[1]
苏程两家交恶缘于苏洵幼女嫁与表兄程之才,在程家备受虐待,两年后郁郁而死,年仅十八岁。苏洵作《苏氏族谱亭记》,痛斥程之才之父程浚:“大乱吾族”,[2]视其为“州里之大盗,私以戒族人焉:仿佛于斯人之一节者,愿无过吾门也。”[2]八年之后的嘉佑四年,苏洵又作《自尤》诗详尽叙述女儿死于程家之事,悲愤的序言和诗句流露出对程浚夫妻和女婿程之才的不满,可见苏洵对女儿的死一直耿耿于怀,苏轼兄弟也因此与程之才断交四十二年。
宋哲宗亲政后,以“绍述”为名,恢复神宗时的新法政策,新党人物纷纷还朝,开始了对元祐党人的打击。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曰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3]苏轼于绍圣元年十月抵达惠州,时为宰相的章惇派遣程之才为广南路提点刑狱公事,巡按广州。程之才于绍圣二年正月“巡视广州,因侯晋叔来惠,致简。(苏轼)答简以一唔为幸。”[4]苏轼与程之才的第一封信只有短短七十余字:“近闻使斾少留番禺,方欲上问。侯长官来,伏承传诲,意旨甚厚,感怍深矣……知车骑不久东按,倘获一见,慰幸可量。”[5]程之才给苏轼的书信惜无存留,根据苏轼此信的内容推知程之才托侯晋叔(程乡县令)致意,问候苏轼,并承诺前往惠州看望苏轼,这一举动透露出他期望与苏氏兄弟化解多年恩怨的急切心情。
绍圣二年三月五日,程之才抵达惠州,苏轼先一日派幼子苏过前往舟中迎接,程之才在惠州逗留十日,与苏轼携子登山临水,造访惠州胜境,诗篇往来,以记其事。苏轼在《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诗中感叹:“此身如线自萦绕,左旋右转如缫车……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6]感叹自身命运漂泊无定的同时更凸显出程之才对自己的深情厚谊。此后二人交往频繁,书信往还不断,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和当地政事的处理,程之才频繁给苏轼寄去食物医药等物品,苏轼回寄诗词书画。半年之后,广州风灾,程之才巡视灾情再次经过惠州并看望苏轼。绍圣三年二月底,程之才因处理苏轼之事不附执政之意,被调离广州,召还朝廷后,山川阻隔,二人书信来往自此而止。
二、亲情化解了两家宿怨和党争阴影
苏轼兄弟与程之才在患难之中重修旧好,看似权宜之计,实则根源于双方自始至终无法割断的血脉亲情。中国社会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基础之上,注重人伦,以情为贵的文化在心理上形成了“血浓于水”的价值取向,在偏重家族血缘亲情关系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家族成员之间、族亲姻亲之间往往呈现出很强的凝聚力和渗透力,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则是对家庭、亲情异乎寻常的重视。对于形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梁漱溟先生解释为:
吾人亲切相关之人,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人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7]
因此,苏轼兄弟 “其后以念母故,欲相与(程家)释憾”,必然在情理之中。程浚有子五人:之才、之元(字德孺)、之邵(字懿叔)、之详、之仪。苏轼兄弟与程之元、程之邵来往密切。元祐初年,程之元出知楚州,苏轼写有《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诗中回忆儿时的欢乐情景:“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6]同时夸赞之元、之邵兄弟二人的才学品德如“炯炯明珠照双壁”。[6]
在注重人情的社会生活中,宗族亲友,邻里乡党之间往往会形成错综复杂的人迹关系网络,姻亲家族之间相互影响、俱荣俱损的情况极为普遍。元祐八年,黄庆基弹劾苏轼苏辙“援引党羽,朋党亲戚,布在要路。”[8]在列举的“亲戚党羽”中有程之邵之名,苏轼赶赴惠州途中与程之元的信中对被贬一事牵连亲友深感不安,“老兄罪大责薄,未塞公议,再有此命,兄弟俱窜,家属流离,汙辱亲旧。然也亦如此,但随缘委命而已。”[5]可见苏程两家的关系远非一般的亲戚之情,而是涉及到政治主张等更加深层次的内容。苏轼、苏辙与程之才虽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实则通过两家其他人的来往早已有了潜在的联系,这为苏程二人在惠州的释憾奠定了感情基础。
“人际关系的核心是情感关系。”[9]其中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当属亲情,它可以决定并改变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苏洵与程俊父子绝交是缘于对女儿的爱和愧疚,苏轼兄弟与程氏兄弟先后重续旧谊同样是出于对母亲家族的亲情延续。苏轼在与程之才的第二通书简中道出了这一事实:
某窜逐海上,诸况可知。闻老兄来,颇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若以骨肉之爱,不责末礼而屈临之,余生之幸,非所敢望也。[5]
苏轼在信中通篇谈论两家往昔的骨肉亲情,以“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感叹与程之才断交时间之久,期望对方念及“骨肉之爱”,而“不责末礼屈临之”。苏轼同样希望与对方见面,解开两家多年的旧怨。苏轼在信的末尾以家人的口吻问候程之才兄弟及诸外甥的近况,提到苏辙在湖口见到程之才的儿媳,从其口中得知对方对自己的深厚情谊,遂“感服不可言”。由此可见,苏辙与程之才的家人之间早已有了交往,家族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网实质上是一张巨大的情感关系网,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正是通过这种联系得以实现,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中的每一个人。
程之才特意绕行惠州拜访苏轼的举动足以表明他愿意与之和解的诚意和决心。此次见面,令苏轼“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能解也。”[5]对于抛开旧怨、重修旧好,苏轼称为:“永辞角上两蛮触,一洗胸中九云梦。”(《同正辅表兄同游白水山》)[6]放下仇怨对苏程二人都是一种心理上的解脱。
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不难理解为何程之才的举动能够赢得苏轼的感情和信任。苏过在《书漳南李安正防御碑阴》中写道:“绍圣初,先君谪罗浮。是时,法令峻急,州县望风旨,不敢与迁客游。”[10]程之才被派往广州,是由于“绍圣执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宪节,皆使之甘心焉。”[11]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家庭始终以其较强的内在凝聚力在某些方面排斥国家政治因素的渗透。”[12]因此,章惇等人想借程之才之手打击苏轼的阴谋落空了。苏轼在给程之才的信札中也说:“谪居穷寂,谁复顾者。兄不惜数舍之劳,以成十日之会,惟此恩意,如何可忘。”[5]程之才不顾朝廷禁令与自己的前途,主动与苏轼重修旧好的情谊令他动容。
程之才在与苏轼的交往中同样获得了情感慰藉,他巡按广州只是新党执政者打击苏轼的又一手段,并非本人所愿。他在《次东坡碧落洞韵》诗中写出了内心的伤感:“粤从度岭来,日见乱山横。触目皆荒凉,宁复乐事并。”[13]于他而言,赴任广东并不是一桩乐事。离乡万里来到蛮荒之地,触目凄凉,且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因执政者的旨意去迫害自己的表弟,对程之才而言,这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是对他的政治才干和人品操守的忽视。
北宋中后期日趋严重的党争和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使中下层官员的处境更加艰难,坚持个人操守和维持仕宦生涯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出他们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力感,程之才在夹缝中的生存危机实则是当时众多官员的缩影。但是,亲情消除了政治上的对立和仇恨,消解了党争投射在二人心灵中的阴影,使他们在宦海沉浮中体味到了可贵的真情,获得了心灵的安慰,减轻了内心的苦闷与无奈。
三、亲情是苏轼惠州生活的心灵慰籍
亲情不仅使苏程两家化解了旧日的恩怨和政治仇恨,更是苏轼在惠州度过谪居生涯的心灵慰籍和情感支持。由于党争被逐出朝廷,在触目凄凉的惠州,离乡万里,昔日亲旧纷纷避之惟恐不及,苏过在《赠王子直》诗中写道:“南行几万里,亲旧书亦绝。……未著绝交书,已叹交游绝。”[10]并且发出了“管鲍久已死,交情云雨翻。”(《和叔宽赠李方叔》)[10]的感叹。这些尚且能够忍受,而亲人离散所带来的凄凉孤独感则是心中无法排遣的痛苦。苏轼在《书〈归去来词〉赠契顺》中写道:“余谪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随,余分寓许昌、宜兴,岭海隔绝。诸子不闻余耗,忧愁无聊。”[14]家人对自己的担忧反衬出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谪居生活的孤寂,亲情的慰籍对于抚平心灵的焦灼无依和孤独感至关重要,是疗治精神打击和心理创伤的良药。因为“居家自有天伦乐,而因其有更深意味之可求,几千年中国人就向此走去而不回头了……与我有亲如一体的人,形骸上日夕相依,神魂间尤相以为安慰。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此所谓‘亲人’,人互喜以所亲者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悲,悲而不伤。盖得心理共鸣,衷情发舒合于生命交融活泼之理。”[7]此言道出了人们渴望亲情关怀的内在原因。
程之才的照顾对于身处困境的苏轼显得弥足珍贵,他在给对方书简中写道:“漂泊海上,一笑之乐固不易得,况义兼亲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过厚,惭悚不已。”[5]程之才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苏轼的生活提供种种便利,利用官员邮递系统为其传递家书,安排士卒为其提供各种服务,并使他从偏僻的嘉祐寺搬到官员往来驻跸之所合江楼,改善了他的居住环境。苏轼在与广东提举大夫萧世京的信中提及:“始寓僧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辅至郡,许假馆行衙。”[5]程之才调离广州后,苏轼担心“兄此去后,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计,意欲结茅水东山上,但未有佳处,当徐择尔。”[5]可知苏轼买地筑屋,修建白鹤峰新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程之才的照顾,无法继续在合江楼住下去,实属无奈之举。苏轼在《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中把程之才对自己的照拂称之为:“人言得汉吏,天遣活楚囚。”[6]
对苏轼而言,生活上的困窘固然难过,但心灵的愁闷和情感的孤独则是急亟待决的问题。苏轼被贬惠州期间,族中亲人相继去世,他在与侄婿王庠的信中伤感地写道:“自十九郎仙逝,家门无空岁。三叔翁、大嫂继住,近日又闻柳家小姑凶讣,流落海隅,日有哀痛,此怀可知。”[15]程之才对苏轼的关怀,让他感受到了来自家乡亲情的温暖,缓解了内心的哀痛和苦闷。
情感的交流是相互的,苏轼对程之才同样表现出亲人之间的关心和挂念。程之才夫人去世后,苏轼“限以谪居,莫缘奔诣吊问,愧恨万千。”[5]遂先后写了九封信安慰他:“吾侪老矣,不宜久郁,时以诗酒自娱为佳。亡者俯仰之间,知在何方世界,而吾方悲恋不已,岂非系风捕影之流哉!”[5]如果“家居悒悒,触物增怀,不如且徜徉山水间散此抑郁也。”[5]并邀请他来罗浮山一游。
苏程二人的交往自始至终贯穿着浓浓的亲情,亲人的关怀和支持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是帮助他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支柱。二人重修旧好是面对现实,思归故乡,思考人生,既而产生情感逆转之后的必然回归。是对家乡故土、亲人的怀念,也是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重新反思。苏程二人羁旅官场,厌倦感和恐惧感与日剧增,二人的释憾含有某种精神超脱的意识,同时,也透露出他们对当时政治生态的不满和反抗。
四、苏轼贬居生活在程之才书信中的反映
惠州时期是苏轼晚期心态和哲学思想的成熟期,也是他作为一位生活的智者,运用自己的生存智慧超脱苦难,成为“坡仙”的重要阶段。苏轼与程之才的信札多角度呈现了他在惠州真实的生活情状及复杂心态:既不拒义行又忧谗畏讥的行为局促,时刻期盼北归又随遇而安的矛盾心理。宋代文人是一个对个体生命和精神格外珍惜的群体,“苏轼的旷达源于时代理性精神的浸润和对传统思想的超越。”[16]“无论穷达,都能在内心精神领域保持主体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这是中国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苏轼是第一人。”[17]
苏轼一向倡导实学,四库馆臣评论《苏轼书传》时云:“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18]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称赞其兄:“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19]为学期于有用,为政利国利民,这是贯穿他一生的主导思想,即使在贬谪期间也不例外。苏程二人交往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协助程之才实施了许多惠民之举。费衮《梁溪漫志》卷四记载:
东坡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东提刑,东坡与之中表,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诸军缺营房,散居市井,窘急作过,坡欲令作营屋三百间,又荐都监王约,指使蓝生同干,惠州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漕符乃令五万以上折纳现钱,坡以岭南钱荒,乞令人户纳钱与米,各从其便。博罗大火,坡以林令在式假,不当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专牒令修复公宇仓库,仍约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桥,坡以为吏孱而胥横,必四六分了钱;造成一座河楼桥,乞选一干吏来了此事……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而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生死祸福动之哉?[20]
苏轼给程之才的书札共有九通是为当地的政事出谋划策,涉及建造营房、修桥通路、火灾后重建民居、税米积压、掩埋骸骨等当地长期积留的难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其中并不排除程之才向苏轼征求意见的可能。
在线教育(E-Learning)可细化为同步在线教育和异步在线教育。同步在线教育即在在线教学平台支持下,教师根据教学内容作教学过程设计后,在同一时间内不同空间下进行师生在线教学。反之,异步在线教育则是教学平台支持下的不同时间内不同空间下进行的师生教学活动。在线教育课程的大量涌现且备受关注,加之Coursera、ed X、Udacity等国外成熟在线教育平台的激励,催生了很多国内在线教育平台,如MOOC中文网、微课网、传课网、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等[2]。
为解决惠州官军缺少营房之事,苏轼给程之才写了一封一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分析利害,不无担忧地告诫对方:“如惠州兵卫单寡,了无城郭,奸盗所窥,又若营房不立,军政堕坏,安知无大奸生心乎?”[5]为此事精心谋划,从所需木料砖瓦、人工钱数、注意事项、派遣官吏等大小事宜无不思虑周详。他在信中解释自己此举的原因是:“此事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及悔无及也。兄弟之情不可隐……此数十年积弊,难以责俗吏,非老兄才气,常欲追配古人,即劣弟亦不轻发也。”[5]惠州军备不肃,苏轼为之担忧并提出解决对策,既是因为此事关系重大,处理不当会生出事端,更因程之才的才气胸襟使苏轼愿意协助其解决当地的一系列积弊。
在帮助程之才解决难题的过程中,苏轼也获得了精神上满足并怡然自得。他与程之才的信中写道:“轼入冬,眠食甚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鸥鹭翔集,鱼虾出没,有足乐者。又时走湖上,观作新桥。掩骼之事,亦有条理,皆粗慰人意。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之,免忧。”[5]他将事情的顺利进展视作谪居生活的乐事。根据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论,物质生活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会自觉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使人生更有价值,在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成就感。苏轼帮助程之才实施惠民之举正是这种精神需求的外在表现,程之才为其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在不拒义行的同时,苏轼也不得不有所顾虑。他在信中不断第叮嘱程之才不可把信息透露出去,更不可让别人知道是自己的主张。“深不欲言,恐误老兄事,故冒言,千万密之。与才元言,但只作兄意也。至恳,至恳。”[5]“千万密之。若少漏泄,即劣弟居此不安矣……此本乞一详览,便付火,虽二外甥,亦勿令见。若人知其自劣弟出,大不可,不可。”[5]“甚密之”、“看迄,便付火”等字眼在书简中不断出现。
苏轼之所以如此小心谨慎,一则自己在贬官期间“不得签署公事”,越职言事被政敌知晓,不仅会给自己增加一项罪名,也会牵连程之才及身边亲友;二则由于自身的经历使他对言语文字心有余悸。苏轼与王巩的信中就慨叹:“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纷也。”[5]因此,尽管他对程之才信任有加,但还是不忘在每一封提及公事的信中反复叮咛,告诫对方,可知他忧谗畏讥的戒惧心理。
苏轼不拒义行的善举和小心忧惧的心理是他应对生存困境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东坡易传》对坎卦的解释为:
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伤……所遇有难易,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则中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惟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刚中。[21]
随物赋形只是水的形态,“未尝不志于行”才是水的本心,柔外刚中既是水的特性,也体现了苏轼在惠州的生存智慧,对外部的挫折和打击既不畏缩逃避,也不奋起抗争;而是采取“随物赋形”的方式积极应对,坚持自我又随时权变。阮堂明认为正是水赋予苏轼完整的精神人格和生命智慧。[22]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与参寥子二十二首之十七》)[15]
然而,回归是中国历代逐臣心中永恒的希望,苏轼也不例外。绍圣二年九月十九日,哲宗大饗明堂,赦天下。得知朝廷大赦的消息后,苏轼不无欣喜地给程之才写信:“某今日伏读赦书,有责降官量移指挥,自惟无状,恐可该此恩命,庶几复得生见岭北江山矣。幸甚。”[5]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提及哲宗在赦书中的政令,亦不乏溢美之词:“得北方故人书,皆云仁圣日跻,兼有昭、裕二陵德美。某虽废弃,曾忝侍从,大恩未报,死不敢忘,闻此美政,不胜踊跃。”[5]苏轼期望哲宗继承仁宗、神宗的“德美”,念及往日“曾忝侍从”的君臣之义,令他量移稍北之地。同时就赦书中涉及到的岭南税役之事,给程之才写了两封千字以上的长信,陈述岭南税役折纳掊剋害民,建议与萧世京、傅才元(广东转运使)集议,“权利害之轻重,取舍从宜。”[5]这不能不说是得知北归有望时喜悦心情的另一种反映。之后他又两次写信给程之才打听大赦消息:“赦后痴望量移稍北,不知可望否?兄闻众议如何,有所闻批示也?报言者论寿州配买茶一事,已施行仁圣之意,亦可仰测万一也。”[5]从朝廷发布的政令中猜测皇帝的意图,可知他期盼大赦消息的急切心情。
然而,“章惇先期言,此数十人(元祐党人),当终身勿徙。”[23]当苏轼从苏辙信中得知确切消息后,以失落的心情给程之才写信:“轼近得子由书报,近有旨,去岁贬逐十五人,永不叙复,恐赦书量移指麾,亦未该也。行止孰非命者?譬如元是惠州人,累举不第,虽欲不老于此邦,岂可得哉!”[5]北归无望,营建新居打算终老惠州,看似旷达,实则透露出深深的失望与无奈。之后苏轼痔疮发作,本年冬至与程之才的信中说自己“自至日便杜门不见客,不看书,凡事皆废。”[5]苏轼把自己闭门谢客,心灰意冷的举动解释为疾病所致,但实际上不能不说是受到“终身勿徙”这一消息的打击。程之才离开广州回到朝廷后,苏轼给他的信中写还不忘询问:“兄北归,别得近秏否?”[5]苏轼探听朝廷的消息,不仅因为时局的任何变化可能都会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命运,更是源于内心期盼北归的希望。
从苏轼与程之才的书札中纵观苏程二人重续旧谊的始末缘由,可知亲情不仅是他们化解多年恩怨、重归旧好的情感基础,也是消除政治恩怨的重要因素。程之才对苏轼的关怀照顾帮助他度过了孤寂的贬谪生涯,是他惠州生活的心灵慰藉和情感支持。对程之才的信任使苏轼勇于为义,助其实施了许多惠民之举,苏轼也从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升华。但迫于严酷的政治环境和对言语文字的忧惧,又反复叮嘱对方不可泄露书札内容。随遇而安的超然之举与期盼北归的希望交织在一起,正是苏轼随物赋形、外柔内刚的生存智慧在逆境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