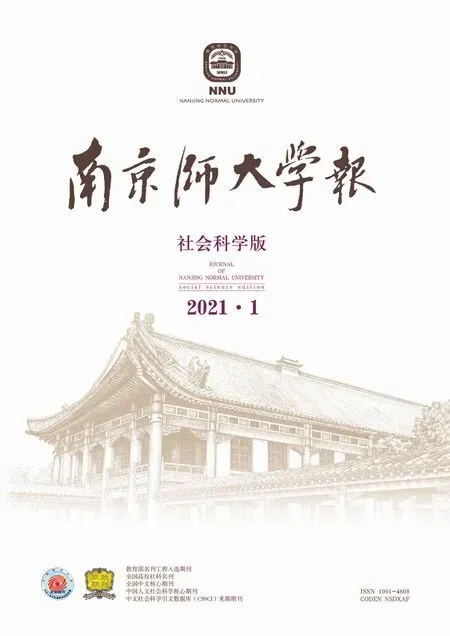试论体认语言学的中国认知哲学向度
张智义
体认语言学是近年来由我国学者创立的语言学理论(王寅,2014;王寅,2019),自提出以来,逐渐形成相当的影响,陆续有学者结合体认语言学的思想对语言哲学、语言思维、语言本体、隐喻语言乃至语言教学进行了分析(魏在江,2019;廖光蓉,2019;王寅、王天翼,2019)。随着体认语言学的发展,其有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但既往体认语言学研究较重同西方哲学的承继关系。实际上,体认语言学的核心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中国认知哲学中的若干核心命题。结合中国认知哲学向度,分析体认语言学和这些核心命题间的联系和承继,可以进一步彰显体认语言学的本土特色,也能为体认语言学今后的勃兴提供一些思路,使其真正植根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屹立世界语言理论之林。
一、 体认语言学的核心理论和学术承继
体认语言学是我国学者王寅于近年提出的一整套语言研究理论,涵盖本体、方法和应用。体认语言学(英文译作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为ECL),是在西方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为CL)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如果说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语言研究是对形式语言研究的反动,那么体认语言研究就是对目下流行的认知语言研究的扬弃。在认知语言研究兴起之前,形式语言研究大行其道。针对形式语言研究在“天赋观”“自治观”基础上所提出的语言普遍性观点和形式化研究方法(Chomsky,1988),认知语言研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语言的“体验观”和“象征观”,认为语言是人们在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本质上是象征性的(Langacker,1991)。这就实现了对形式语言研究的反动。而体认语言研究认为单纯强调语言的认知基础是不完整的,进一步强调语言的体验基础,实现了对认知语言研究的扬弃。
从本体看,体认语言学强调“体”和“认”,embodied一词借自心理学,是具身之意,心理学上指生理体验对心理感知的影响(Lawrence,2014,p.11),因此这里的“体”即指“体验”,而“认”则指传统的“认知”。实际上,体认语言学对“体”和“认”的界定,也有过变化。前期研究中偏重从哲学角度,将“体”和“认”分别界定为“存在”和“思维”,认为除了有一种凭借“看见”(SEE)现实来认识世界的“体”方式,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似”(SEE AS)概念隐喻式的“认”机制(王寅,2014,第36页)。综合看,SEE起到的是“体”(存在)作用,AS起到的是“认(思维)”功能。近期研究更加注重语言本体的视角,认为“体”重在“身体力行”,凸显“互动体验”之义,“认”强调“认知加工”,两者结合,既强调了“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论立场,也凸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辩证法原则,这样就将客观与主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可更好地解释语言之本质(王寅,2019,第54页)。因此,体认语言学在本体论上对语言研究的贡献是在既有认知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体”的因素,以分析语言背后除主观认知之外的客观实践因素。
从方法论看,体认语言学奉行“现实-认知-语言”的原则。从左向右为“决定作用”: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语言和知识是人们基于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体认观完全符合唯物论和人本观的基本原理。从右向左为“影响作用”:语言影响认知,认知影响现实。前半句与“弱式语言世界观”相吻合;后半句与辩证法相一致,即人们一旦获得正确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理论,便可改变世界。
从应用看,体认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原则,在语言研究中,具备综合性、层次性和实践性的特征。综合性在于体认语言学有助于实现语言分支学科的融合;层次性在于语言研究的各个层面,如语音、词汇、语义、词法、句法、篇章都可以结合实践、认知分析语言现象的理据;反过来也可以思考各个层次语言现象对认知和实践的影响;实践性在于通过挖掘语言背后的认知、实践理据,促进语言的教和学。
体认语言学在本体、方法以及应用层面已蔚然成形。但其前期研究偏重同西方语言哲学的承继关系,有多篇文献系统梳理了体认语言学同西方语言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及后现代哲学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学理传承。如王寅明确指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体验哲学及认知语言学之上建立起来的体认语言学,当视为西语哲之延续”(王寅,2018,第132页)。而彭志斌(2019,第30页)的研究在对体认语言学进行哲学溯源时,也明确了体认语言学的西方哲学立场。
迄今为止,尚无一篇体认语言学的研究文献挖掘体认语言学的中国认知哲学源流,这和体认语言学建构本土理论的初衷并不一致。本文即尝试讨论体认语言学的中国认知哲学向度,一方面希冀找到体认语言学的中国认知哲学渊源,进一步确立体认语言学的本土性;另一方面也希冀体认语言学能从中国认知哲学中获得启发,丰富和发展理论体系,实现“立民族之林”的目标。
二、 名实、言意、知行——体认语言学的本体溯源
中国哲学历经几千年演变,形成了丰富的认识论思想,汇聚成为中国认知哲学。中国哲学所谓的认知,注重探讨名实、言意、知行等重要概念,这和体认语言学确立的现实、认知、语言三个本体高度契合。
首先,体认语言学“现实-语言”的本体维度契合中国认知哲学中的名实观。“名”就是语言,“实”就是现实。中国认知哲学认为,名有谓实的功能,如《墨子·小取》说“以名举实”;《经上》也说“举,拟实也”;《经说上》又说“告以文名,举彼实也”(张永祥、肖霞,2015,第87、131页)。“名谓实”就是说语言对现实的反应关系。这里的“实”可以指个别事物或事件,可以指类别的事物或事件,也可以指抽象的事理。抽象事理由于其特殊性,引起了古哲先贤额外的兴趣,如《经上说》举例说,“信,不以其言之当也,使人视诚得金”(张永祥、肖霞,2015,第134页),诚、金各有所指,以金喻诚,即以隐喻思维反应抽象事理。这就引出了名实关系的另一面,“名”虽依“实”而有,但并不等同于“实”,如《尹文·大道上》说,“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这里就是强调名实有别(厉时熙,1977,第94页)。综合这些认知观点看,“实”是认识的对象,或对象的本质;“名”则是认识的结果,或认识结果的表达。在这中间,认知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对于抽象事理往往依赖隐喻机制实现。凡此种种,都和体认语言学“现实-语言”的本体互动以及体认语言学对隐喻机制的高度关注相吻合。
其次,体认语言学的“认知-语言”维度契合中国认知哲学中的言意观,“言”就是语言,“意”就是认知。中国认知哲学向来关注言意间的关系。墨家很早就提出“以辞抒意”的思想,就是指用语言表达认知层面的心思意念。如王弼从《周易》解读出发,提出了“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王晓毅,1996)。表面看,王弼似乎在强调意重而言轻,否定语言的流播价值。但正如夏甄陶(1996)的分析,王弼所强调的重点是认知对语言的决定作用。与王弼相反,欧阳建提出“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这就是强调语言对认知乃至于对现实的反向影响(李才远,1979,第16页)。综上可见,中国认知哲学的言意辩证观也和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本体互动一致。
最后,体认语言学的“现实-认知”维度契合中国认知哲学中的知行观,“知”就是认知,“行”就是现实。知行观是中国认知哲学的重要理念,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在“知行”上下功夫(刘大钧,2007,第27页)。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宋代以来的认知哲学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看法,王船山和颜习斋认为习是知的基础,离行则无知,有行则有知;程朱理学则认为知是行的基础,有知则能行,无知则不能行;阳明心学则认为知行无别,知行合一(方克立,1982)。抛却上述观点的违心成分,在知行辩证关系上,体认语言学强调体认结合的论述和知行观一脉相承。
综上,体认语言学在本体论层面对中国传统认知哲学的名实、言意、知行观进行了整合,并在整合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以语言研究为核心,对语言、认知和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厘清。在一定意义上,可谓集传统认知哲学之大成。本研究认为,这恰恰是体认语言学本土特色最鲜明的体现,也将成为其发展活力的不竭源泉。而体认语言学应更注重挖掘认知哲学本体观资源,进一步拓展“实(行)-意(知)-名(言)”或“现实-认知-语言”辩证逻辑内涵,为构建中国特色语言研究话语体系努力。
三、 五官、心征、说表——体认语言学的右向决定论溯源
中国认知哲学向来重视对于认识来源和性质问题的思考。在体认语言学奉行的从现实到认知再到语言的原则中,右向的为决定作用。讨论认识来源和性质在本质上体现为现实如何决定认知,继而决定语言。因此,两者存在契合。
在认识来源和性质问题上,中国认知哲学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些观点持外在说,即认识的来源和性质均取决于外。有代表性的如荀子,如《荀子·正名》篇中说,“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表,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荀况,2018,第36页)。这里的论述和体认语言学的观点决然类似,强调“五官”的外感对形成认知的决定作用,然后通过“心征”的认知对语言的“说表”形成决定作用。体认语言学涉及语言本体研究的诸多应用层面,实际就是发掘感官对认知,再对语言所起的作用。如体认语言学认为汉语常按动作顺序组句,体现的就是视觉形成的认知和表达效果(王寅,2015)。还有些观点持内在说,如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观,朱熹认为,人心本有知,这种知与外物相接(格物)之后才能求物之理(致知),而穷万物之理(穷理)之后,方得大用。朱熹的学说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语言,但其基本思想颇类形式语言学研究的思想,也和体认语言学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本文将在第五小节进一步深入分析。另有一类观点是对内外观点的综合,即认为从来源和性质看,认识既有外在,也有内在来源。如王船山在《正蒙注》里说,“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故由性生知,由知知性”,这里“三相遇而知觉乃发”的观点实际表明,认知包括语言都是内外兼修的结果,王船山认为,大部分知识有赖外在格物,也有很多知识是“吾心固有而无待与格物”的(萧萐父、许苏民,2002,第64、75、97页)。内外交互的思想同体认语言学体认结合的原则在辩证、联系的思想内核上一致。
上述分析表明,从方法论看,体认语言学重视“现实-认知-语言”右向决定原则和中国认知哲学中有关认知来源和性质的论述血脉相承,其和荀子的认知论观点非常契合;而朱熹的学说虽然和体认语言学的右向决定论有所不同,但存在会通的可能(下文详述);王船山的学说在内在逻辑上和体认结合的思想一致。体认语言学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从这些观点中汲取营养,丰富自身。中国认知哲学有关认知来源和性质的理论表明,可以更加辩证地看待所谓的决定作用,即在“现实-认知-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在肯定前者对后者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认知和语言中的一些自主能动因素。以语言的构词为例,比如英文“unicorn”(独角兽)一词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全赖认知中的想象因素构造(Lemmens,2016,p.275)。实际上,基于想象的文学语言能提供大量体现认知和语言自主能动性的实例。
四、 毕同毕异和白马非马——体认语言学的左向影响论溯源
上文分析中国认知哲学对认知来源和性质的论述,重点强调来源即现实,强调现实对认知、认知对语言的决定作用。那么,中国认知哲学中还有一些观点,侧重分析认识的方式和过程,这就把重点切换到了认知和语言上,即语言如何反过来影响认知,认知如何反过来影响现实,也就是体认语言学的左向影响论。我们发现,体认语言学的左向影响论和中国古代的哲学智慧也颇多契合。
先看认知对现实的影响,在中国认知哲学看来,认知的实现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对现实的构建。如惠施认为,就认知对现实的构建而言,任何现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认知通过在现实中找到共通的性质,发现“同”“异”两大共通性,就完成了对现实的构建。在“同”“异”的探寻中,认知深刻地影响了现实。惠施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小同异”与“大同异”中其实包含了丰富的认知联系论和辩证法。“小同异”的要义在于用分级的方式,以大类小类逐级明确概念;“大同异”观则肯定一切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相同和相异(钱穆,1992,第63页)。
体认语言学中认识对现实的影响向度深刻反应了“毕同毕异”中的“大小同异”观点。体认语言学十分注重的隐喻机制实际就是以“同”求知,以“同”影响认知;而作为体认语言学发端的认知语言学强调以任何语言表达的差异反观认知、现实差异,实际上也是以“毕异”观构建、影响现实的具体体现。而体认语言学中语音、语义、句法、语篇层面通过层级分类方法还原认知、现实的方式,也体现了“小同异”的思想。
再看语言对认知的影响。在中国认知哲学看来,语言的表达方式也会深刻影响认知的构建。这里,最有代表性的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观。白马非马看似诡辩,夸大“个别”与“一般”的差异。但如果结合认知和语言的关系看,白马非马的观点反应了语言对认知的影响。体认语言学在结合分析哲学探讨哲学基础时,专门强调了罗素“摹状语理论”对体认语言学的影响。罗素区分了“限摹vs专名”“语法形式vs逻辑形式”这两对概念,前者对应认知,后者对应语言。专名可被亲知,为直接知识;限摹为摹状性描写,为间接知识(苑莉均,1996,第621页)。因此语言上通过在体现专名的逻辑式前加限定成分的语法形式,深刻反应了语言对认知的影响,即通过语言增加认知的丰富度。尽管体认语言学再三强调罗素哲学观在体认语言学“语言加工”观点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这一观点在中国早期认知哲学观中的白马非马观中已经发端,足见体认语言学与中国认知哲学的内在联系。在语言对认知的影响研究上,体认语言学大有可为。体认语言学注重不同民族的体认方式如何决定了语言的差异。实际上,不同民族语言的差别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人们体认的方式。如过去认知语义对动词框架和卫星框架的区分,实际深刻反应了语言对认知的影响(Talmy,2000)。
综上,从体认语言学的左向影响论看,其主要观点也都能在中国认知哲学中见到端倪,传统认知哲学的若干理念也能为丰富和发展体认语言学的左向影响论提供有益借鉴。
五、 理学和心学的砥砺与会通——体认语言学之于形式语言学
众所周知,在中国认知哲学的数千年发展史中,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是重要的代表性流派。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存在重要的差别,但也存在交流融通的可能,此所谓两者的砥砺与会通。本研究发现,程朱理学关于认知的若干重要观点和形式语言学的基本架构颇有几分相似;而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知行合一观,在本质上同体认语言学相通。这里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一是进一步明确体认语言学的中国认知哲学向度;二是希冀体认语言学能够进一步发扬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传统,更有效地将现实、认知、语言进行融合。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存在深刻而复杂的差异,简言之,程朱理学的认识论认为认识就是天理,天理是不植根于内心的一整套普遍的道德规范,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之意。因此朱熹的思想被认为带有强烈的客观唯心主义色彩。而阳明心学的认识论认为认识就是人心,需要用心体悟,方能成就人格完善和自我实现。所以王阳明的思想被认为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如何用心体悟?阳明心学认为知行合一是实现体悟的重要修为。在行的基础上获得知,以知来丰富、完善、指导行,形成知行相互补益和交替上升是用心体悟的要义(郭美华,2002)。综上,“格穷天理”还是“用心体认”是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在认知论上的本质差异。但两者也有会通的可能。理学和心学会通的基础在于两者同属认识论范畴,会通的途径是在知行合一,用心体认的基础上趋近对真理的认识(刘艳,2019,第32页)。
回归语言研究,理学和形式语言研究相类;心学和体认语言研究相类。众所周知,以体认语言学为代表的认知语言研究是在批判形式语言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言研究,核心的观点是大脑先天就有自治的“句法模块”,且存在一套普遍的句法原则(universal grammar)(李曙光,2020)。这两个核心观点深刻影响了形式语言学对语言结构、语言认知和语言习得的分析,在形式语言那里,现实和认知的互动是缺失的,语言就是作为一套自治句法原则的认知机制作用的结果(Chomsky,2000)。这和朱熹对天理的看法很相近。而体认语言学则明确反对句法的自治性和普遍性,明确不存在先天的句法模块,语言都是在现实和认知的互动体验中形成的,语言的差异反映了认知的差异,也反映了现实的差异。语言的互动体验观十分接近阳明心学的用心体悟、知行合一观点。但是形式和体认的会通也是可能的,会通的前提是两者均在现代认知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形式属于第一代认知科学,体认属于第二代认知科学),会通的方法和途径是:在对先天自治“句法模块”扬弃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挖掘现实、认知、语言的互动关系,从细微的差异入手,逐渐探寻有一定普适意义的语言规律。
以上研究表明,体认语言学之于形式语言学的破立关系在传统认知哲学中也有本可源。在当下语言学亟待确立本土特色、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体认语言学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应该将知行合一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应该进一步融合现实、认知和语言,在现实层面强调“互动体验”,在认知层面强调“认知加工”,在语言层面强调“语言体认”,以语言反观认知,反观现实;以现实丰富认知,丰富语言。三者充分的融合互动,既做体认细微差异的小文章,又做体认宏观规律的大文章。
六、 结论
体认语言学代表了我国学者尝试构建本土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努力,经过多年的发展,体认语言学理论逐渐成熟,在本体论、方法论和针对语言分析的实践应用层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研究则进行了一次系统挖掘体认语言研究的中国认知哲学向度的尝试,希冀构建体认语言学的本土之壤和中华之根,以进一步确立这一理论体系的传承性和开创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希冀体认语言学能够进一步从中国传统认知哲学中吸收有益成分,开拓研究视野,挑战理论难题,为繁荣我国的语言研究做进一步的贡献。本研究属于尝试,且由于企盼面面俱到,终不免挂一漏万,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还有待体认语言学者和所有有志构建中国特色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学者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