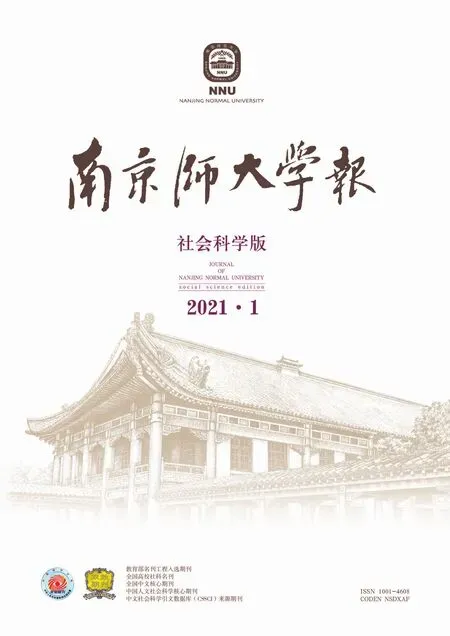课程“泛化”: 面相、过程及价值
吴晓玲
课程泛化——“人人皆谈课程”“人人皆做课程”“事事皆可成课程”“事事皆需课程化”——是指我国近20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所出现的课程理解和课程开发多而杂以至缺乏共识、边界和规范的现象。研究者们大都是在一个反省和批判的角度下认识课程的泛化:“课程概念的泛化及其危害”(1)王娟娟:《课程概念的泛化及其危害》,《江西教育科研》2007年第7期。“课程概念泛化现象之省思”(2)陈莉:《课程概念泛化现象之省思》,《全球教育展望》2015年第12期。“校本课程开发的‘泛化’问题及其对策”(3)张诗晗、郑鑫:《我国发达地区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泛化”问题及对策》,《基础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笔者以为与其把“课程泛化”视为错误或危害,不如悬置消极判断,视“泛化”为“中性”现象,保持对该现象的关注和开放,努力在看到的有限与实在性中去探寻未被感知到的实在性与可能性;不把课程泛化看作结果或结论,而视其为向诸多可能敞开,既产生新问题、新矛盾,也生成新结构、新现实、新思想的过程。
课程泛化现象演进大致经过以下4个阶段:课程概念泛化,课程权责泛化,课程资源泛化,课程技术泛化。如果把20年看作为一个时间单元,这4个渐次产生、相互勾连的阶段也可被视为泛化现象构成的4个紧密关联、相互交叠的维度。这4个不同阶段或维度既呈现出泛化现象的共同特质:观点或行动在量上的突增和质上的转变,使过去的课程认知与实践的边界和结构被突破、跨越甚至重构;又各自在历史文化土壤和时代发展背景、社会运作体制下生发出不同的过程性价值。
一、 课程概念泛化
课程泛化的思想前提是课程概念的泛化:内涵越来越抽象,外延越来越宽泛,什么都可以是课程……对课程泛化的批判也肇始于此:不利于课程论学科的发展,导致课程实践混乱、学校功能缺失、教师作用迷失,凡此危害等等。笔者以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课程概念“一与多”的问题。在“多”添“乱”之前,课程大致被界定为学校教学内容及其进程的安排、组织或计划,或者稍许做一些改变:把教学内容替换为学科或学业、课业内容。此界定体现的是工程学思维,把课程当作为一种脱离人、脱离历史文化情境的实体,采用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追求确定性和决定性。(4)李定仁、徐继存:《课程论研究二十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页。如果把课程论学科的发展类比为机械工程,把概念看作是理论大厦的基石,那么这样的概念界定的确稳当安全,但问题的关键是,课程论是社会学科,课程是“人为”并“为人”的,固化本质、固化概念的做法只会扼制这个学科的生命力,使学科发展固步自封,从而导致实践发展陷入僵滞。从某种意义来讲,对“课程是什么”的追问本身比获得某一固定的答案更有意义和价值。因此对课程本质的追问以及课程概念的多元化恰恰是课程论研究得以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动力,也是赋予课程实践者以主体思想力、判断力和拓展其专业空间的基本前提。
在肯定课程概念泛化之积极价值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多”对认识的干扰。笔者以为面对诸多或以概念形式来表述,或用观念或理念方式来提炼的课程本质见解,我们可以通过文化的理解、历史的还原、学科的廓清来梳理多种见解之间的关系,合理安放它们的位置,建构它们之间的秩序,而不必在“概念”和“理念”之间,此概念彼概念,此理念彼理念之间争个高下,更不能囫囵吞枣、含糊笼统地当和事佬。
在对课程概念泛化的批判性研究中,有一个危害常被揭示,即我国课程论研究大量移植欧美课程学术观念和话语,从而导致本土课程研究失语。笔者以为除去学术态度浮躁和能力尚弱等原因外,一个主要的客观原因就是我国的课程实践比较单调。一个国家本土课程理论的发展水平和其实践水平一定是大致相当的,贫瘠的实践必定会导致理论的贫乏,单一的实践中长不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因此,是本土课程实践和研究贫乏在先,才需要引进外域思想。当外域思想几乎不分历史阶段,瞬间一齐涌入之后,丰富和单调反差鲜明,本土研究暂时失语是必然的,整个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基本都经历了此阶段。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有兼容并蓄、善整合的文化基因,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又是多种文明状态并存和跨越式压缩式发展的进程,课程作为教育的重要载体和谋划必然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多种需求,所以多元课程概念的存在既体现了文化的张力也贴切于国情。
我们还需要从历史的维度来解读被以共时性的方式罗列出来的课程概念。当课程被看作“学科知识”时,往往意味着某种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延续,相信世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原理和真理,并体现出精英主义教育的倾向。因为学科知识是过往探究的结果,是人类理性文明的智慧结晶,是确定的,可以被预先计划和组织。而用“经验”来界定课程,则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酝酿和建立,譬如杜威的经验课程思想所诞生的时代背景正是美国需要拓殖边疆、需要冒险,需要创新求生,需要在非固定、非永恒的环境和信念中面对新事物、提出新见解,从而建造新世界和新文明的年代。原先从欧洲传过去的理性主义传统(包括学科知识)难以胜任当时美国的发展需求,转而寄希望于“经验”。在认识途径中诉诸经验,意味着要突破权威,打破刻板僵化的秩序。(5)吴晓玲:《走近教学想象力——基于对以自然为法之教学观的理解》,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用“经验”来界定课程,还体现出一种教育大众化的趋向,譬如现代课程理论之父泰勒就是用教育经验、学习经验来表述课程原理,其在从学科角度来探讨教育目标问题时反复向学科专家强调不是为了培养像他们那样的学科专家而是为了培养一般公民,应该让孩子学些什么以及怎么学。泰勒的课程思想产生于美国的“八年研究”(1933—1940),而八年研究的一个深刻历史背景就是在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如何让尽可能多的孩子在学校里待尽可能长的时间。若学生过早结束学业离开学校,而社会缺少就业机会,势必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学校课程要从过去培养和选拔精英的思路,转变为适合绝大多数学生学习的思路,即大众化思路。我国当下课程改革中,被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频繁强调的“学科素养”和“儿童(学生)立场”大致就是“课程即学科知识”与“课程即学习经验”这两种课程概念本土化的时代演绎。“学科素养”立足于学科知识来育人,“儿童立场”则是倡议直接经验的育人价值,体现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诉求和路径的复合性。
“课程即学科”与“课程即目标”虽被看作同一类属的课程概念界定,都强调预设和控制,但也隐含着明显的差异。后者相对于前者,对教师而言,意味着更大的专业自主空间。前者规定着教师就是知识的传递者和传声筒,教育就是教知识,知识内容本身就是目标;后者则给予教师以教学内容的选择权和采纳权,但为了保证一定水平的教育质量,则从基准化目标的规定上进行控制。之所以最近考试大纲的取消要比课改之初课程标准的颁布给一线教师带来更多实质性的影响(慌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许多老师们驾轻就熟的是教知识点,只要有确切的知识点范围,就不会也不必劳神费心地去研究课程性质和目标,尤其在高利害考试的学段,课标基本是“说起来重要、用起来不要”。取消考试大纲正是为了让课程标准真正成为“标准”,老师们没有了考试大纲可依赖、遵照,方才有可能真正重视和研读课程标准,也才有可能实现其课程标准引领和规范的价值。
除了历史——文化的解读视角,我们还可以从学科的维度来进一步理解课程概念的多元性。譬如,“课程即社会文化再生产”和“课程即社会改造”,体现的是教育自我传承和变革的双重属性,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课程的实然和应然本质。这与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课程本质不是一个话语体系,但的确能够拓展和加深我们对课程的认识,无论对课程理论研究还是对课程实践改革,都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和建构思路。我国当前努力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走向新时代的发展愿景必然会让“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社会改造”这两种本质功能同时并举。
综上,当我们用文化的视角、历史的眼光、学科的视野来认识和理解课程概念泛化之“多”时,会减少多而杂乱迷失的嫌恶和痛苦,增加多而洞察明辨的智识。
二、 课程权责泛化
如果说课程概念泛化是课程观念和思想解放的理论启蒙,那么作为课程管理体制民主化产物的三级课程管理制度则是泛化现象得以在实践中出现的真正撬动之点。没有课程权责的结构性变化,没有课程开发主体的普遍增多,不可能出现课程泛化现象。
在课程集权体制下,课程预先法定,是教与学的不容置疑的前提,教师要做的就是“以教护课程”:让学生接受、记住课程承载的法定知识。当知识授受过程与知识创造、选择过程全然分离,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就都是被动的接受知识结论的客体。我们从“教”和“学”两汉字的篆体结构都能显然地看到指代课程的“爻”与教授者、学习者之间上下位以及服从和膜拜的关系。历史文化积习和惯性在很大程度上让老师们对“课程”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这种课程体制再配合以考试选拔体制,使师生被束缚在狭隘、焦虑的空间中,生存视野被禁锢,知识的生命价值、生活意蕴被遮蔽,主体的生活热情与创造能力被抑制。(6)吴晓玲:《论课程与教学的深度整合》,《教育发展研究》2014年第24期。三级课程管理制度规定“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2001-06-08,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j_kcjcgh/200106/t20010608_167343.html,2020-04-05.。其赋予学校规划、实施和开发一定课程的权责,这意味着学校教育实践者和课程之间权力结构发生了改变,预示着教的人、学的人与知识世界、生活世界的理智和精神联系所可能发生的改变:通过连接沟通知识的创造、选择与传授过程,让师生以生命主体的状态直面博大精深、复杂多变的知识世界,心灵向世界敞开,敬畏地认知世界,深刻地感悟生活;改变灌输与占有知识的动机与方式,让知识从被截断来龙去脉的考试链中解放出来,真正释放培育生命自觉、助人成长、伴人远行的价值。当然这种改变是一种理想的愿景,需要足够长的过程、足够坚定的努力、足够专业的能力。
与实践者长期无课程意识状态相伴生的是课程能力的缺失。课改初期,对绝大多数学校教育实践者来讲,课程是高高在上的专业领域,在没有相应力量承受其重、分享其权、发挥其能时,面对着这份陌生的沉甸甸的课程权力,许多教育实践者感受到的是挑战和压力。在学校教育实践者自身课程意识尚未觉醒、课程需求没有萌发之前,这种自上而下的“赋权”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享受被让渡的一些权力,毋宁说是承担指令式的“赋责”:学校须有自己的课程,要自己开发课程。权力意味着“可为”,职责则意味着“应为”,但是若没有相匹配的“愿为”和“能为”来落实,那么“可为”所带来的自由和舒展感就会被“应为”带来的任务和压抑感所遮蔽。
改革与发展是时代主旋律,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不积极投入改革,即意味着错失发展的机遇。课程改革也同样把学校推向这样的境遇。但是当许多学校、许多教育实践者还不具备相应专业实践的空间、精力、能力的时候,就必然会对课程权责有着消极的体验:在制度文本上,学校拥有了课程管理的主体权责;在具体实践中,学校却经受“上级课程行政滞后”“社会应试倾向”和“自我建构能力不足”的困扰。(8)张相学:《学校课程管理:赋权后的困惑与抉择》,《教育科学研究》2005年第11期。外力赋予的,超前于体制环境、实践认识和行动能力的权责必然会有泛化之嫌,来自实践者的抵触声音一直都存在:每所学校都须要有自己的课程吗?谁都想开发课程吗?谁都能开发课程吗?
课程改革希冀通过改变课程来“重塑”(9)钟启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与“学校文化”的重塑》,《上海教育》2001年第14期。“重建”(10)余文森:《新课程与学校文化重建》,《人民教育》2004年第3—4期。学校文化,学校课程作为学校文化建设和内涵发展的重要的新的生长点,被寄予厚望,成为是否积极实施改革的重要标签。一所学校是否有自己的课程、是否有足够多的自己的课程、课程是否富有特色成为判断一所学校是否积极发展、锐意进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行政力的推动下,能为者先为,名校示范必有课程展示;想为者也勇为,后发学校争相以课程开发成果来证明自己的办学理念和能力。只要有小部分学校积极探索和示范引领,学校开发课程就真从理论阐发和倡议的“需为”、政策引导和规定的“可为”和“须为”逐渐成为实践中的现实“能为”和“愿为”。
虽然过程自始至今充满了各种各样理解和行动上的误区、盲区,从而被反思和批判着;也充斥着多种多样的矛盾、困难和困境,被揭示和论争着,但我们的学校教育实践者的确在这摸索、探索、开拓的过程中逐渐在不同水平上提升了课程专业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课程意识和需求被不同程度地唤醒,由起初被动、应激的工作状态逐渐走向了自觉的专业的富有使命感的主体实践状态。只有当实践者内在的“需为”“想为”“能为”与“可为”“须为”相融合时,“赋权”才能转化为“享权”“行权”。
笔者在对中小学校课程规划和建设进行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学校课程建设状态与实践者思想的活力、精神生命的状态是密切关联、彼此契合的,大体经历四个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四种不同的行动与表达状态:起始是外力推动下的执行性实践和格式化表达“上级要我做”;接着是实践审议中的调适性实践和存疑性表达“我能做吗?”;行动自觉中的发展性实践和叙事性表达“我这样做”;文化自觉中的科学化实践和主体性表达“这样做才是好的”。从外显行为来看,学校教育实践者成为课程权责主体是为了课程,但是随着课程规划、开发和校本化实施过程的推进,这种向外用力的过程也在向内塑造着教育者自身的精神生命状态,由对外在物的探讨,经过意识的中介,向人本身回归,这是一段教育视野、思想和情怀的被解放和自解放、被激发和自绽放的意识和体验过程。(11)吴晓玲:《论学校课程规划的过程性——基于江苏省义务教育学校课程规划状况的调查》,《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7期。
因此用期待和守望的眼光来看待“谁都要开发课程”诸如此类的课程权责泛化现象,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研究者都能够对“赋权”过程中的蹩脚、焦虑、不适和抱怨更加包容、耐心些,不因噎废食,也不好高骛远。越来越多的教育实践者们正在这个曾经让他们敬之也畏之、无力也无暇顾及的课程园地耕耘、收获也发展着,渐渐地就会发现“丢不下”这份被赋予的权力,从而真正地享有权力。
三、 课程资源泛化
课程概念泛化是课程资源泛化的思想前奏,既然“什么都是课程”,自然“什么都能成为课程”;课程权责泛化是课程资源泛化的主体条件,“谁都要开发课程”必然带来对课程资源的旺盛需求,从而课程资源成为课程改革推进和学校课程建设十分重要的“生产资料”。没有课程资源,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规定“积极开发合理利用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各学科各学段课程标准也都专门设有“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版块。官方文本的引导力是巨大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纷纷对课程资源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
课程资源泛化现象在理论界定中就已预置伏笔。课程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课程资源是指有利于课程目标实现的各种因素,狭义的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直接因素来源。(12)吴刚平:《课程资源的理论构想》,《教育研究》2001年第9期。相对来讲研究者们大都更倾向于使用广义概念,譬如:“课程资源是课程设计、实施和评价等整个课程编制过程中可资利用的一切人力、物力以及自然资源的总和。”(13)徐继存、段兆兵、陈琼:《论课程资源及其开发与利用》,《学科教育》2002年第2期。“凡是有助于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活动所能开发和利用的物质的、精神的材料与素材。”(14)齐军、姚鑫圆:《课程资源概念的梳理与重组》,《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0期。常见的课程资源分类几乎包罗万象:条件性资源和素材性资源,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校内资源、校外资源和网络资源。
理论构想的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课程资源,对局限于也习惯于以教科书、教参、练习册等教学辅助资料为教学材料的教师来讲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课改初期,相对物质素材资源来讲,短缺的主要是精神条件资源:(1)思想教育僵化、物质利益至上、崇高理想匮乏,导致思想资源偏狭、落后;(2)本土知识创新能力不足、仰赖从国外引进输入,且往往忽略知识发现和创新过程中大量富有创造性的过程性基础内容,使得知识资源数量不足、品位不高;(3)教师普遍缺乏课程改革所需要的主体意识、目标意识和创生意识。(15)范兆雄:《论我国现代课程资源短缺问题》,《教育探索》2003年第3期。因此在课程改革初期,教师们的课程资源意识主要集中于显性的物质资源,再加上地方课程管理者以课程特色化来推进校本课程开发,具有地域特点的自然、社会物质资源(包括显性、有形的历史文化资源)被首先纳入到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契机,使得长期在学校教育中被忽略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能够进入校园,被关注、被传承、被推广甚至被创新。近20年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尤其体现在物质文明的发展上,这又进一步强化了课程资源开发“物化”的态势,这一方面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校园学习环境、学习资源、学习方式向着主题化、实物化、艺术化、活动化、功能化和网络化方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片面追求视觉化、相互攀比、不物尽其用甚至浪费的不良倾向。
虽然改革过程存在诸多误区,但是总有一些真挚的实践者用自己执着的探索亲历体验到了寻找、挖掘甚至创生课程资源所带来的未曾有过的智性幸福,譬如:“教师们在寻找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不论纸质还是电子文献关于家乡的资料都很单薄。资料短缺的困境恰恰也成为释放教师智慧的佳境。教师们的工作不再停留于信息、知识的搜集、接受与传递,而是尝试着自己去探求、发现与生成知识、思想。这样的转变虽然需要付出许多艰苦的劳动,但教师们的精神生命力得到了焕发。在开发校本课程的过程中,开发课程的教师们首先受益于这一开发过程而获得了自身的专业成长。”(16)南京市栖霞区龙潭小学:《“美丽的龙潭——我的家乡”校本课程活动指南》,2010。因此课程资源开发对教师们来讲不仅是挑战,也是解放,唤醒了他们的资源创生和利用意识,打开了他们的教育视野,把他们的工作与真实的生活世界、亲历的知识世界紧紧联结在一起。随着教师们的课程意识被唤醒,课程资源开发不再只是一种向外求之于物,也是向内求之于己、察己之心、体己之悟的过程。没有教师主体生命理智和情感的投入和融入,物只能是物,再丰富再先进,也只是外在于教育的摆设。
实践贵在持恒。前述学校的课程开发团队在对校本课程进行修订的过程中又提升了对资源开发的教育理解:“关注学校内部和外部的可用资源,合理和充分利用地域特色,不仅能够体现学校教育特色,形成教育活力,还能够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探究、合作、表达、沟通、尊重、理解等良好品质。”(17)南京市栖霞区龙潭小学:《“龙娃导览”校本课程概要》,2015。他们对课程资源的理解的变化还体现在学校门厅的廊柱上。在他们还没着手开发校本课程之前,廊柱上贴的都是我国和国际顶级知名大学的海报;校本课程开发后,他们把大学的海报全部都换成了当地名人的简介、字、画以及各种字体的学校名称;再后来,他们又把廊柱改造为给孩子们看书的围坐式书架,让孩子们一进校门就可以看到书、读到书,通过书走向生动的生活和宽广的世界。这些静悄悄的改变在无声地诠释着一所乡村小学对课程资源、对校本课程、对教育的理解。
有研究指出:过于宽泛地界定课程资源可能反而造成学校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困难。学校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资源观念,丰富的课程资源不仅指学生所处的教育环境具有许多课程资源,同时也指学生可以便捷地使用资源,为自主和合作的学习、实践、探索性活动服务。(18)张廷凯:《课程资源:观念重建与校本开发》,《教育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对理论研究者来讲,可以跨越过程、思辨地、前置地提出“科学合理”,但对实践者来讲,“科学合理”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在有了诸多过程经历后通过不断地反思而逐渐达成的,诚如前述案例学校校长所说:“在开发校本课程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成为我们理解教育、理解课程、理解儿童、理解自我的新的思考点。我们相信在校本课程从无到有、从不是到是、从不好到好的思考与行动过程中,我们的学生、教师、学校都能获得共同的进步与发展。”
课程资源泛化现象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教材的弱化和边缘化。有一句常被老师们引用,但已难查出处的话既能够诠释课程资源重建教师教学内容观的解放意义,也微妙地隐含着在课程资源系统中教材被弱化和冷落的境遇:课程改革前,教材就是“我”的世界,课程改革后,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教材。从理论推演来讲,教材一定包含在课程资源内,但是多数人在论及课程资源时,常用“超教材”或“非教材”的叙述方式。这主要是因为课程资源概念提出的一个合法性来源就是对“唯教材”“教教材”的批判,所以广大教育工作者很容易在直觉和情感上把教材排除在课程资源之外,人们总是刻意地谈非教材的课程资源。研究指出,如果课改初级阶段为了确立课程资源概念的合理性,“矫枉过正”尚可理解,但如果继续把“用教材”忽略在重要的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行为之外,则有可能犯“被它掩盖的比它所揭示的还多”的错误。(19)张亚飞、柯政:《论课程资源的两种叙述》,《全球教育展望》2006年第11期。
笔者曾经访谈过一位年近退休的特级教师,他认为课程改革不是增强了青年教师的课程专业能力,而是弱化了课程专业能力:现在青年教师不琢磨教材、不深入理解教材、不精熟于教材,怎么可能会教教材?教材都教不了,还谈什么用教材教?所以在他主持或主讲的培训,都要求教师必须带上课程标准和教科书。这位老师的观点一方面折射出老一辈教师的课程观、教材观,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在课程资源被不断强调的语境中教材却被忽略和边缘化的现象。其实在我国客观现实中,教材一直都是重要的教育教学载体和依据,大部分教师在大部分时间依赖的资源还只(能)是教材。教材经过许多专家精心研磨,非常具有再开发潜力。课程改革深化阶段学科核心素养理论体系的建构、统编教材的编订和教材研究的异军突起,都在表明课改初期阶段被边缘化的课程资源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以更成熟稳健的样态回归到教育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中。
因此,我们同样需要用过程、发展、辩证的眼光来认识课程资源泛化现象,看到它对激活学校办学活力、丰富教育内涵、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积极主动有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看到矫枉过正、急功近利的消极性、负面影响,更要看到并相信科学合理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实践智慧是在坚持不懈的教育实践探究、自觉的反省批判和追问中产生的。
四、 课程技术泛化
课程资源是课程开发的“原料和对象”,课程技术则是将原料加工为课程的“手段和方式”。课程资源泛化重建了教师们的教育内容观,也向教师们提出了掌握转化、加工资源为课程的课程技术的要求。笔者在与实践者开展合作行动研究时,发现时有教师会产生“我做的是课程吗”“我在做课程吗”诸如此类的疑惑,其实正是对课程技术的一种自觉。当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由分类别课程开发与实施走向学校课程顶层规划和整体建设阶段时,催化了课程技术泛化现象的产生。因为从课程的视角和逻辑来观照和统整学校教育活动并对之进行顶层设计,必然会运用课程技术来建构和规范学校教育各项活动,所以出现了“事事皆需课程化”的现象,譬如:社团课程化、班会课程化、仪式课程化、大课间课程化、节日课程化、劳动课程化、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化、环境教育课程化、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化、生涯规划教育课程化、学法指导课程化、研学旅行课程化……(20)杨骞:《课程化——问题探析与解决方略》,《中小学教学研究》2018年第8期。
“事事皆需课程化”现象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对“课程”的误解。“课程”原本是个集合概念,是个总称,其内在构成不必再用课程来指代。譬如构成“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不必再赘述为礼艺、乐艺……;再譬如,英国课改文件规定中小学校课程包含4个组成部分:学校生活和校风(school life and ethos)、课程领域和学科(curriculum area and subjects)、跨学科学习(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个人成就的发展机会(opportunity for personal achievement),其也没有因为想改变传统课程的构成主体“课程领域和学科”,而分别给其它三个组成部分加上“课程”以示重视。因此我们的中小学校完全没有必要把学校课程体系中的所有构成都加一个“课程”。误用“课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得已的有意为之,原因显而易见:课程的丰富表明在课程改革和建设中积极作为。我们不必总是反感、嫌恶因词误用所带来的课程词语泛化现象,而更应该去深度挖掘“事事皆需课程化”所隐含的潜在的过程性积极价值。“课程化”重在“化”,这些年其也从原先的形式主义的功利筹谋,渐渐生发出对本真的理想教育的追求:运用课程编制技术,使学校中传统学科课程外、高利害考评体系外的教育活动或教育领域,从失落、边缘恢复应有的教育位置和功能,从随意走向规范,从不稳定、临时化、权宜化走向稳定、常态化和品质化。
课程技术首先是价值选择、澄清和定位之术。无论是技术旨趣的课程开发原理第一个问题“学校教育应达成什么目标”,还是解放旨趣的概念重建主义者所要求的课程研究要形成一种基于有效理解和反思教育自身是什么的教育思维体系,都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强调课程研究都要思考价值问题。因此把某物某事某活动某育课程化,意味着要思考这些事、物、活动对特定身心发展阶段、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特定时代发展背景下的学生有着怎样的当下和未来价值。不课程化,就不思考价值,或者价值就不存在了吗?当然不是,价值潜在地存在,对价值问题的思考也可能自发产生。然而,现实中太多人忙着低头赶路做事,忘记了赶路目的,无暇对诸事进行梳理,淡漠了忙事的价值归属。凡当真、认真的课程化,就必须自觉、明确地把价值问题想明白、思通透。仅有外在的价值和目标也仍不够,还需要将其内化为富有主体性的价值感和目标感。笔者在田野研究中发现一些具有敏锐课程意识和自主课程开发能力的教育实践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具有明确、执着的价值感。“事事皆需课程化”意味着教育实践者将可能藉由课程的路径和技术去寻找失落的主体意识,培育教育价值洞察力、理解力和守护力。
择定价值、明确目标之后,接下来的课程技术就是教育经验与内容的选择、提要之术,即思考选择什么样的教育经验和学习过程能够最好地实现价值和达成目标。学校课程膨胀拥堵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肤浅的功利化追求,而是因为当下知识增长不可计量、技术迭代太快、生活方式悄然速变,世界变动不居,人、社会与自然之间不断暴露新的矛盾,各种新问题不断涌现……因为我们曾经的课程太单调,所以课程改革给人的印象是给课程做加法,但随着课程的量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就必须要做整合甚至减法。如果仅仅是把林林总总说法的课程写或画在纸上,也许唯恐不够多、不够丰富,但是一旦要考虑用具体的时间来落实这些课程的时候,就会发现“多”变成了负担,就会意识到“贪多”不是课程改革和学校课程建设的明智之举,粗放式思路须向集约化精耕细作转变。“事事皆需课程化”意味着为学生们选择和创设的教育经验需去芜存菁,要中择要、精益求精。
课程技术不只助人登高望远、俯瞰教育全景,也助人走进教育微观世界、心灵世界。构建课程十分需要化整为零的分析性思维和细节意识,否则整体大视野就只能停留于混沌含糊,价值思维流失于思辨空想。与那些在学校笃定踏实地开展课程实践的教育者交流,让人感动、给予启发的往往是他们课程专业生活中的细节,尤其是对人本身的关注。譬如,一位坚定相信“课程是学校灵魂”的校长认为:学校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些课程就好比是一粒粒种子,这些种子在不同孩子的身上萌芽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的萌芽早、有的萌芽迟,早和迟的时间也是有差异的,甚至也有可能发不出芽。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更加敬畏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21)吴晓玲:《论学校课程规划的过程性——基于江苏省义务教育学校课程规划状况的调查》。再譬如,一位曾在乡村支教、相信“儿童阅读课程化可能是最经济也最实在的改变乡村教育生态的可行之路”(22)汪琼:《迟到的阅读》,《中国教师报》2019年4月17日,第 8版。的老师这样反思:“教育不那么需要锦上添花,极需的是雪中送炭;比上课、课程建设更重要的,是对生命的理解和解困,是你要看见他,懂得他;教育的首要核心是人,永远是人!不知人,焉知教?”“对绘本课程的开发,我曾是狂热追随者和坚定行动派,但两年的支教生涯,面对那些还没有开花就伤痕累累的生命,很多想法和行动都转了弯或换了道。绘本对那些特别的小孩而言,与其说是阅读课程,还不如说是疗愈手段。”(23)吴晓玲:《班主任课程领导的阅读旨趣与生命理性——走进班主任Q老师的读写世界》,《江苏教育》2019年第47期。一所有志于为每一个儿童设计课程的学校在进入课程建设高原期时,校长问了老师们两个问题:“如何让课程更贴近孩子?”“如何让课程扎根于教育的土壤?”这些来自课程实践者的朴实又深刻的反思和追问既显现和标示出“事事皆需课程化”所带来的过程困惑、试误和拨开云雾现澄明的省察、体悟,也勾勒、预示着其未来发展方向。
结语
相对于“课程泛化”,笔者以为“泛课程探索”或许更能够整体地、妥帖地反映和解释我国21世纪开始的这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课程概念泛化、课程权责泛化、课程资源泛化、课程技术泛化现象。没有课程概念泛化,就不可能有丰富的课程思想和广阔的课程实践探索空间;没有课程权责泛化,就不可能让“需为”“应为”的课程思想和政策转变为“能为”“愿为”的生动课程实践;没有课程资源泛化,就不可能打开实践者的课程视野、解放他们的课程想象力;没有课程技术泛化,就难以让那些被忽略、被轻视的教育活动和领域,从视域之外走向规划之内,甚至作为学校教育创新的重要生长点,逐渐恢复其曾失落的教育地位和发挥其应有的育人价值。因此我们需要正视、珍视和规导、释放“泛”所蕴含的思想解放力、构建力和实践探究力、创新力,让本土课程理论研究继续保持思想的生机和张力,促进“泛课程探索”培育出释放主体活力和富有育人力量的课程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