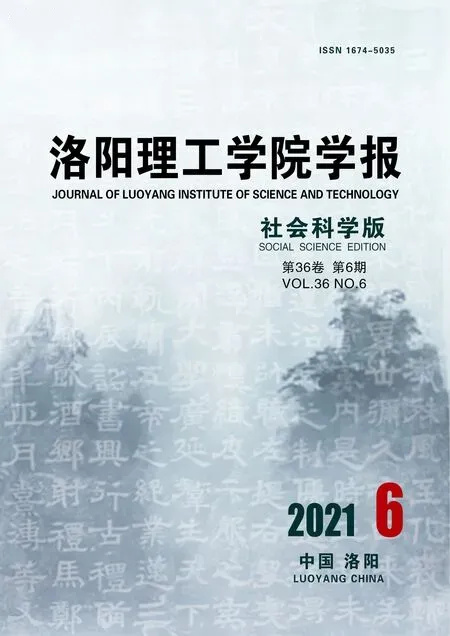东昌府木版年画体系表征研究
岳 彩 静
(河南大学 美术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东昌府木版年画产生于山东省西部的聊城市。京杭大运河与黄河在此交汇,南来北往的商业交流,不断丰富着本地域的文化载体。东昌府木版年画在本土风俗民情的基础上汲取了不同地域的艺术风格,呈现出典雅大气又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它与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平度木版年画等一起构成了山东木版年画的区域产地。“年画来路不用问,北至东昌府,南到朱仙镇,杨柳青后来夺了魁,菜园随着来打混。”从这首广为流传的民谣,可见东昌府木版年画在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中的地位。
今天人们谈及木版年画,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和中国木版年画的起源地开封朱仙镇,东昌府木版年画则较少被论及。究其原因,近代以来由于黄河改道、运河堵塞以及陆运的发展,东昌府的南北交通动脉地位消失,其城市命运也几经更迭,甚至一度变成落后封闭的区域。因为地处封闭的文化地理环境,东昌府木版年画养在深闺无人识,多在社会底层流传,极少受到上层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干扰。这使其至今仍保持着原汁原味的地域特色,有着完整且独立的发展体系。通过东昌府木版年画独立体系的研究,有望打开整个山东甚至中原地区木版年画研究的新视阈。
一、发达刻书业是东昌府木版年画自成体系的依托
木版年画因刻制于木版的制作工艺而得名。中国的木版年画制作多是先刻版后印刷。印制一张完整的木版年画,往往需要很多套木版。一套完整的木版,多以颜色为单位,一种颜色一套版。此外,还有线板或墨版等。所以,木版年画的核心环节就是刻版。刻版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木版年画的图像呈现。刻板业的发展,是促成木版年画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中国,木版年画的制作技艺与刻书业的雕版印刷技术是一脉相承的。东昌府木版年画独立体系的形成依托于东昌刻书业的发展。
东昌府木版年画并非单指东昌府辖区内的木版年画,也包括周边其他县市区的木版年画,如张秋木版年画、东阿木版年画等。他们互相影响,联系密切,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东昌府木版年画发源于聊城南部的阳谷县张秋镇。清末时期,山西移民在张秋镇开设店铺,带动了此镇的经济发展。借助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兴盛,张秋镇一度跃为“南有苏杭,北有临张”[1]93的鲁西第一大镇。山西移民带来了木版年画的手艺,最先在此开设年画店。后来几经搬迁,张秋木版年画迁至东昌府,并影响了周边地区。这些木版年画积聚,直至形成今天的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发达体系。
刻书业的繁盛直接带动了刻版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东昌府书院林立,是科举考试重地。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刺激了东昌府刻书业的发展,有“东昌作坊,书笔两行”的佳话。光绪年间,东昌府内刻印作坊琳琅,“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老字号作坊皆有据可寻。著名的海源阁藏书楼落户于此,加之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催发,东昌府的印书业盛极一时。东昌府一度成为全国刻书、印刷、制笔业的中心之一。这在《老残游记》中可以找到佐证:“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是最盛的。小号店在这里,后面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版,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2]75厚重的文风,漕运要道的地理位置,使东昌府刻书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刻书业的雕刻艺人,不单刻制书版,同时雕刻插图版画,这就孕育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的雏形。雕刻插图版画与制作木板年画在技术上一脉相承,这给东昌府木版年画独立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刻书业自成体系且发达,是东昌府木版年画体系独立性的根基。东昌府木版年画在制作工艺上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刻印分离。鲁迅曾总结中国的木版画:“地不问东西,凡木刻的图版,向来是画管画,刻管刻,印管印。”[3]230东昌府的刻书业也是如此。刻书业只负责出版、印制和发行,不刻版。刻版环节交由专门的刻版艺人来完成,刻印分家的刻书业孕育出雕版印制的木版年画,在制作工艺上自然是一脉相承的,同样也是刻印分家。其一,刻印分家的制作流程节约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制作成本。整个木版年画制作流程中,成本最高的环节就是刻板。刻制一整套木版往往耗时耗力。若有个细节刻错,整版就要弃掉重来,成本很大。东昌府木版年画在刻版选料上使用的是梨木,因梨木木质坚硬,久泡不变形。在雕刻木版之前,要将梨木在水中浸泡数月。刻版技艺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掌握。一旦有专门的刻版艺人,画店就不需要长期雇佣刻版工人。年画店按需定制木版,大大降低了年画的制作成本。其二,国内其他木版年画的艺人往往集刻印技艺为一身,而东昌府木版年画刻印分离。这既是东昌木版年画的独立之处,同时也是其局限所在。刻印分离使东昌府木版年画无法迅速调整自身以适应市场和时代的发展。
二、东昌府木版年画的表征符号
东昌府木版年画的独立体系是通过一系列表征符号彰显出来的,如题材、用色、造型、构图等。其独特性是东昌府木版年画区别于其他地域木版年画的显著特征。
(一)题 材
东昌府木版年画有着广泛的取材,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年画与群众生活紧密相连,因其淳朴率真的艺术特色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木版年画的“艺人们在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作画。他们身在天高地远的穷乡僻壤,与朝廷的文字狱全然无关。整个中国木版年画史上,少有年画由于抨击时弊而招来麻烦。它们是农民的自娱自乐,嬉笑怒骂,一任自由”[4]3。同样,东昌府木版年画也是东昌府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东昌府木版年画题材广泛,种类繁多。在东昌府木版年画中,不难看到中国木版年画中常见的门神类、神马类、故事人物类等题材。
门神是东昌府年画中最重要的一类题材。因为“过去连年灾荒、会教门多、拜庙成风”[5],门神被奉为驱邪避秽的法宝,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东昌府木版年画中的立刀门神与其他地域木版年画中的形象不同。立刀门神是各地都有的门神题材,但是在东昌府木版年画中立刀门神的形象塑造生动且简洁,被称为中国门神画之最。
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木版年画在数量上仅次于门神类年画。这类木版年画多取材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如《三国演义》小说中的“赵云救阿斗”,《白蛇传》中的“西湖借伞”等。这些题材,经过雕版刻制的再塑造,通过印制形式的图像传达,形成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独特的样式和风格。东昌府木版年画题材中对地域周边名人轶事有所侧重,这一传统在今天也有所体现。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也成为今天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创作题材。
娃娃画是木版年画中以儿童为题材的年画,东昌府娃娃画有独特之处。其年画中的人物都是儿童,用儿童的天真来表现喜庆的气氛。而其他地域娃娃画题材大多是妇女、儿童皆有。东昌府娃娃画,多采用“娃娃抱鱼”“童子花篮”“娃娃采莲”等题材。其中“童子花篮”题材为其所特有,在我国其他地域年画中没有出现。东昌府娃娃年画中的娃娃,形象圆润饱满、生动活泼。
此外,灶神、全神、财神等题材在东昌府木版年画中也较为常见,其中以灶神和财神最多。灶神形象在东昌府木版年画中有“摇钱灶”“大金灶”“大粉灶”等几十种之多。这是东昌府木版年画题材的表征。
(二)用 色
东昌府木版年画所用颜色非常鲜艳,色彩亮度很高。取色多用红黄绿紫等亮色,即使用到黑色,也只是用作帽子、头发、胡须,偶尔用作衣服上的褶皱[6]。东昌府木版年画在制作时只有“草版”,即制作年画的过程中套色刻印,只印不画。“其色彩分为丹红、粉红、黄、绿、青、黑六色。印出的画面效果,不仅色彩对比强烈、鲜艳明快,而且印刷精致、准确,整体装饰感强,具有特有的地域风貌”[7]9。其人物面部不着色,这使得年画人物形象更加醒目。东昌府木版年画因为采用套色刻印的技艺,色彩往往不能完全附着在轮廓线上,经常超出之外,不受轮廓线的制约。轮廓线和色彩相互结合又相互独立,进而收到写意的审美效果。这与周边地域木版年画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如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受传统文化习俗影响,多用暖色。杨家埠木版年画用色口诀: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画真新;红主新,黄主淡,绿色大了不好看;紫多发恶,黄多傻,用色干净画鲜艳。与这两个地域年画相比,东昌府木版年画有其独特的颜色表征。
(三)造 型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不同地域风格迥异,造型差异较大。总体来说,南方木版年画秀丽脂粉,北方木版年画粗犷饱满。东昌府木版年画在造型上有突出的特点:一是造型夸张。年画人物造型将头部突显出来,人物头大身体小,人物头部占全身比例的三分之一以上。人物眼形窄长,鼻子瘦窄平直,耳朵较为圆润,衣纹细致,整体人物形象生动。二是形象明快简洁。东昌府木版年画中人物造型简练,表现主要部位,而其他部位简略,虚实结合。年画艺人将主要人物刻于中间位置并占据较大的比例,其余的人物列在主要人物的周边。三是线条粗犷。年画人物的轮廓线较为粗犷,刀感鲜明,人物显得稳重大气,彰显出北方特有的文化风貌。
(四)构 图
东昌府木版年画构图颇具匠心。“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这是年画艺人心口相传的秘诀。“满”“全”是东昌府木版年画构图的最大特点,即在一个平面上,塞满人物或其他吉祥物,不留空白。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构图有着截然相反的特征。传统文人画讲究留白,“虚实相生”“有无相生”是其构图的审美特征,追求“无画处皆成妙境”。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则讲究“满”。东昌府木版年画的灶君画就是构图布满整个画面,几乎不留空白,把所有要传达的东西展现在受众面前,给人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6]。这种“满”“全”的构图形式不仅是装饰性绘画的需要,也营造了一种欢快、热闹的气氛。同时,这种构图也与印刷工艺有关。“东昌木版年画全靠手工印刷,在版面上若留有空白便会塌纸玷污画面。艺人为解决这个问题,尽量将画面填满,将自己心里能想到的都组织在咫尺画稿中,在剩余的空间添加一些象征吉祥、富贵之类的东西”[8]。东昌府木版年画依傍着大运河文化,乘着刻书业的大势,形成了线条刚劲、粗犷、淳朴的构图风格,此为其独特的艺术闪光点。
三、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产销体系
年画最早主要以门神的形象出现,它被赋予的用途是祈福驱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风俗习惯的需求,到了近代,年画不再局限于宗教用途,而是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寻常百姓节庆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且发挥着“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由于年画的题材内容多取材于民间传说故事,内容情节大多积极向上富于教育意义,因此,年画成为一个良好的教育途径。在年画的鼎盛时期,家家户户形成了“以画过年,无画不年”的生活习惯。
东昌府木版年画鼎盛一时,与旺盛的市场需求直接相关。聊城地区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年画市场,首先归功于地域交通与经济的发达。自明初后,聊城借助漕运的绝佳地理位置,成为“扼九省之喉”的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黄金水道上的聊城,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水路要冲。朝廷运往北京的大宗漕运物品以及全国各地货物,无不在聊城集结转运。当时的聊城运河里,北上的漕船与南下的货船,首尾相接,来往不绝。这使山东聊城成为重要的商业都会,经济的繁盛让其有“小天津”的美誉。经济的繁荣使聊城成为一个较为富裕的商业地区,百姓也有了财力去购买年画,逐渐形成规模化的年画消费市场。其次是内在的文化需求。年画这一艺术形式在东昌府地区的盛行,还得益于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聊城文风兴盛,不少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提倡风雅,大力兴办书院。明代“后七子”的盟长谢榛,创作了《渔舟唱晚》的金灼南。这些都为聊城文化的兴盛贡献了力量。文风兴盛,助推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的文化市场需求。
东昌府木版年画有着独特的销售方式。自清代以来,东昌府木版年画的销售方式沿承山西木版年画的销售方式——开设画店。据记载,清末聊城规模比较大的年画作坊有“通顺”“五福祥”“同泰”等二十多家大堂号画店。“门画是手艺,学了就得济”“穷人要想富,开个门神铺”,由此可见年画店的兴盛。民国后期,社会动荡,加之运河漕运的衰退,东昌府木版年画的销售方式随之也发生了转变,走街串巷的叫卖成为主要的售卖方式。“大寒冷,中暑热,春秋两季印正得”,年画印制具有极强的时令性。但东昌府木版年画的销售是常年进行,不分寒暑季。东昌府木版年画印制分布在聊城20多个城镇和乡村,从业者或合伙或独办,常年经营年画业务。这些画店春夏季印制扇面画,秋冬季印制年画。明清鼎盛时期,仅张秋镇的年画作坊,每年用纸2 400令。整个东昌府木版年画在鼎盛时期的销量可想而知。东昌府木版年画主要销售范围立足本省主要城市,并辐射周边省份,远至东北三省等地。独特的销售方式和销售地域,构建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独立的销售体系。
四、结 语
东昌府木版年画在中国木版年画谱系中,不是最富盛誉的。但其艺术风格鲜明,制作工艺独特,有着完善的产销体系,可以说是中国木版年画的一个历史写照。东昌府木版年画立足于鲁西大地,与其他地域的木版年画相比有其独立的表征符号和文化价值。民间文艺得到传承,文化方能自信,民族才能复兴。诚然,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如何传承与保护像东昌府木版年画这样的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