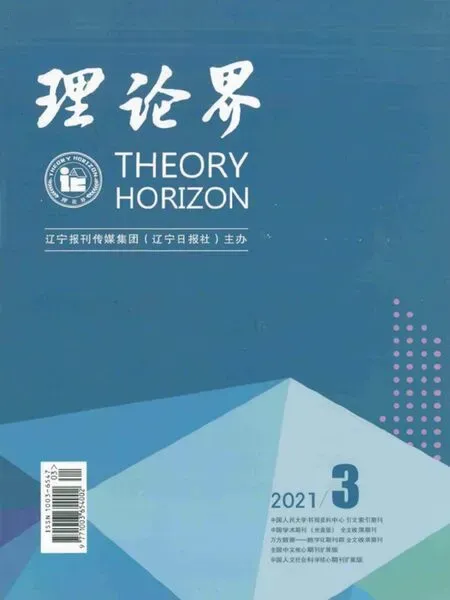个体、时间性与悲情意识
——《二十四诗品·悲慨》的精神境界
李旭阳
就中国美学中的悲感文化而言,《二十四诗品》中“悲慨”一品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在“二十四品”之中,“悲慨”一品亦有着较为独特的气质,其所奠定的基调既不华丽,又不恬淡。既非体用之分,又非风格所规。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爆发,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极悲之情。这与魏晋时期的悲情意识表达有难得的相似之处,在历来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是比较难得的。虽然《二十四诗品》的产生年代和作者目前学界有比较大的争议,但其文本所呈现的思想上的重要价值不容忽视。其中“悲慨”一品的独特的气质也是颇具吸引力的。“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悲慨”之情,大抵是诗歌之内情而外充。“悲慨”一品,不仅仅是对诗之一品的品评,更体现了一种个体情感的独立与思考,为我们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悲感文化的探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进路。
一、作为风格论的“悲慨”与作为意境论的“悲慨”
“诗品”自钟嵘始。在钟嵘《诗品》之中,品为“品第”之意,较为明显。“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1〕自汉至魏晋六朝,受政治选才影响,品藻人物是普遍现象。钟嵘《诗品》即以三品裁夺诗人与作品之高下。虽然清代便有将《二十四诗品》与钟嵘《诗品》并称之例,但此《诗品》显然非彼《诗品》。《二十四诗品》的问题复杂一些。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文本,其题为“二十四品”。〔2〕对于“品”的释义历来亦有不同观点。杨廷芝在“二十四诗品大序”中说,“诗以言志,亦以见品,则志立而品与俱立”。〔3〕这里颇有以人品立诗品的意味。祖保泉《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中,“品”解为品题、品味。当然,除此之外,更多学者持“风格论”的观点。较早研究《二十四诗品》的陈国球先生认为“品大概与文体的体字相类似,是说明分类的量词,并无实意。所以应取《广韵》的‘品,类也’的解释”。〔4〕也就是用二十四首四言诗描述不同种类的诗。就其内容而言,陈同意诗品所论述的是不同之“风格”。王润华曾论述《诗品》风格之理论基础及其基于个性、文学的风格论。〔5〕郭绍虞在《诗品集解》中亦提及“所作重在体貌诗之风格意境”。〔6〕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风格论是有别于西方文论传统的风格论的。当我们将其定义为“风格”时,无疑形成一种割裂,这是需要谨慎对待的。虽然“品”有品目之分,亦有不同类型之指向,但其所更为突出的,是一种意境的呈现。朱良志在《〈二十四诗品〉讲记》中提及,若将“品”理解为风格,此风格也非今人所说“风格”,而是一种“风神气格”,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气象”“境界”。“不是风格类型的描述,而是通过境界的创造烘托一颗‘诗心’,讲心灵境界的培养、生命体悟的超升,讲超越主观与客观的纯粹生命体验。”〔7〕清代袁枚曾仿《二十四诗品》作《续诗品》。而袁枚《续诗品》之“品”在于方法。相较之下,《二十四诗品》以二十四种诗的风格展现了二十四种诗的境界,并不侧重揭示到达此种境界的途径。因此,《二十四诗品》的写作,即是以二十四种风格呈现二十四种意境,亦完成了蕴含于其中的情感表达。
以“风格气象”论之,二十四诗品的品类之分是有其文论传承的。而“悲慨”作为其中一品亦能在其他诗论中寻求到踪迹。皎然《诗式》中便有“悲”“怨”二式,此外严羽《沧浪诗话》中说“诗之品有九”,其最后二品即为“悲壮”“凄婉”。〔8〕郭绍虞在校释此处时引陶明濬《诗说杂记》:“何谓悲壮?茄拍铙歌,酣畅猛起者是也。何谓凄婉?丝哀竹滥,恕怨如慕者是也。”〔9〕大体一悲壮一凄美。悲慨所表达的意境要比二者更完整。其所表达的悲美一方面具有悲壮之感,另一方面亦有凄凉之情,气势更外扩宏大,情感却更内向自我。悲愤出诗人,在古代中国早有传统。《诗经》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但“悲慨”一品依然在“二十四品”中较为特殊,盖因诗品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其风格更倾向于任乎自然,而悲慨与之相悖。其所表达的悲慨之情,完全是一种情感的爆发,这种纯粹的情感式的表达,亦不多见于中国古代诗论。而其所展现的意境,可以细分出许多的角度,与其他诗论相较亦更为突出。
二、悲慨中的意境表达与情感表达
“悲慨”一品充分调动了景的描写,以景写悲情。情与景,历来是文学文本中需要处理的两个重要范畴。相较于魏晋时期的诗歌作品与诗论文本,“悲慨”一品展现了更高的书写技巧,其文本更具有一种意境论的特点。意境论是到唐代才日渐成熟的中国美学理论。
魏晋时期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丽”很好地概述了其时代的诗歌美学特质,情感的表达也往往是内在情感的构建。例如阮籍咏怀诗:“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10〕末二句直抒胸臆,浓烈的悲情呈现于读者面前。这里需要注意到的是,虽然阮籍的诗歌中亦出现了“孤鸿”“翔鸟”的物象,但其更像是为了情感的抒发而构建的物象,而非实景出现。直至刘勰《文心雕龙》出现之后,“物色”作为文本的构成才真正得到理论的重视。自东晋后,“缘情”与“物色”二者融合,至唐代在借助佛家思想的基础上真正发展出了情景交融的完整意境论。意境的出现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充分,也更为完整。
“悲慨”一品起始便营造了一幅压抑而悲壮之景。“大风卷水,林木为摧。”卷水之风,必是极大,而挟水而来的狂风,所过之处林木为之所摧,大树被连根拔起,继而为狂风所卷。一幅末世之景。《诗品浅解》说“悲慨”一品“起手似有北风雨雪之意”,〔11〕其化自《诗经·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句,开篇便将凄凉悲苦之景呈于读者眼前。景往往是情的外化,景的描述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展现景物本身,而是有其自身的独特情感的。具体在这里,场景颇为雄阔,却无半点豁然之感,只有无尽之压抑,使我们很容易便置身其中,而面对此景颇生人生无常之感。故此“适苦欲死”,但却“招憩不来”。如此困苦乃至欲死,却无法得到安宁。情景相交融,更凸显其悲哀。由于情境的存在,悲慨之情的表达便有了具体的依托,情感表达之人也有了确切的形象。这是在过往的诗论中所不常见的。
而就情感而言,由文本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悲慨”一品中展现了双重之悲,一重是“适苦欲死”的人生之悲,一重是“大道日丧”的社会之悲。而这两种悲归根结底,在于个体性的凸显。个体与外界的反抗,一个是命运性的,一个是历史性的。“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是为人生之悲。如前所述,面对极悲之景与人生之困苦而欲死,却无法得到安宁。人生之无常与无奈凸显得淋漓尽致。更进一步地,人生百年尚且如白驹过隙,荣华富贵不过会败落冷灰。欢腾之后往往是萧萧落寞。再加上面对社会巨大之变故困苦欲死却无法得当安宁,人生何其悲哉。“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是为社会之悲。“大道日丧”颇为明确地点明了世事之变故,王朝之倾覆。悲天悯人的天地道义无处可排遣。大道日丧,时局动荡,却雄才不出,乃至不禁要对天长问谁是雄才。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是,时值乱世,雄才不出,唯有空悲切。而壮士拂剑,慨无用之情,却弥漫浩然之悲哀。“浩然”,极盛大之势,孟子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句,温庭筠亦有“荒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之联。而以浩然形容哀,本不为多见。故此以浩然所展现的盛大之哀气,更显其哀。
“悲慨”一品中,充分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与情感。庙堂是属于儒家的,江湖则更多划归道家层面上去。就“悲慨”一品而言,虽然每句都言景言己,但却道出了一种强烈的社会与国家层面的危局。并且,这种悲慨更多的是由此而生。以“大道日丧”最为明显。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日丧,明确点出了国家与社会之危亡。这也难免会产生儒家饱学之士“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感。并且,这已经不是先天下之忧,而是天下已忧,行将崩亡。故此所立之形象,难免会被视为儒家之士。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其背后亦体现了道家江湖之远。江湖之远离不开庙堂之上,壮士拂剑也正是因为大道日丧,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也就是庄子所谓的人间世。而在这种人间世的慨叹,如果细致考量的话,会发现其背后的悲情更深一层的悲情意识的展现。
三、个体、时间性与悲情意识
张国庆先生在《〈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中认为,“悲慨”一品所具有的是类似于西方悲剧的一种表达,〔12〕其著作中详尽分析了西方悲剧理论。在我的理解中,西方悲剧理论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自我意识的问题。在中国美学传统的表达中并没有形成关于自我意识的概念。但这种个体性在“悲”的表达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进一步而言,西方悲剧精神所强调的是自我意识觉醒后所意识到的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割裂所造成的命运性的对抗,而中国美学中的悲情意识是由个体的自我存在感所带来的生命意识的强化,在遭遇命运的对抗时所产生的悲情之感。
悲剧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剧种分类,而是涉及自我意识与主体的一种精神存在。悲剧精神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情感表达,更主要的是展现了自我意识独立的命运性与对抗性。无论是命运悲剧还是情感悲剧,其根本所呈现的,正是一种自我对外在的反抗。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苦恼意识问题的讨论似乎提供了一种思路。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个体意识到自我与外在的分裂,当为了达到外在而又无法跨越分裂时,便产生了苦恼的意识。这种苦恼的意识,在精神阶段的发展似乎可以视为悲剧的延续。其本质的问题在于,个体在面对命运时所持有的无奈。
“悲慨”一品中的人生与社会之悲,都体现出了一种命运性的困苦与无奈,这是最为悲慨之处。具体来说,“适苦欲死,招憩不来”与“壮士拂剑,浩然弥哀”最为体现了这种悲慨中的困苦与无奈之情。困苦欲死却不得,何其无奈。招憩不来,连安宁也无法得到,甚至主动去召唤竟然也不来,无能为力之虚脱与无可奈何之感慨,都集于此中。壮士拂剑,乃以例证之。剑是壮士最为得力之处,李白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但此情此景,剑却再无用武之处,因为大道日丧,若为雄才。无雄才,无宁日,无用处。只能黯然拂剑,眼见大风卷水、林木为摧却只能浩然弥哀,仿佛整个宇宙之中都充满了这种困苦与无奈之情。这种面对命运的无力感使整体的表达增添了浓郁的悲剧性。在此意义上,这一段已经不再仅仅是写诗之品了,更是融入了个体自身的情感在其中。这种情感的迸发,是颇具独特性的。而它明显体现出了作者的困苦与无奈之情。悲剧往往在于无奈,这是自我与世界相割裂造成的不可及。《二十四诗品》背后的个体生命,每一个都是一个个体,有悲慨,有旷达。而至悲慨时,一种命定的无奈缓缓展开。在这种意境中的个体已然丧失了对抗的能力,只能随之飘摇,任情感肆意奔涌。这似乎是作者自身的经历化为一品,融入其中。若从这一点来看,是能为作者的考据提供一些思路的。不过就目前的可能作者而言司空图处唐末之乱世,虞集以汉人身份处元朝廷,都具有一种自身的命运之无奈处境,这一思路还有待新的证据。
与西方悲剧有所不同的是,就中国的悲情意识而言,这种割裂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往往呈现为以“叹逝”为核心的表述,即对时间性的关注。时间是悲情意识的另一个隐喻。这种对时间性的关注是远高于西方悲剧的。对于时间的慨叹自《诗经》时便已有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时间的流逝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美学中的悲情表达,往往与时间性有关。“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我们注意到在“旷达”一品中,也有类似表述:“生者百岁,相去几何。”这些与时间性直接相关。而相类似的表达在中国古代文本中数不胜数。吉川幸次郎《推移的悲哀》曾做过论断,悲情完全是由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生存在时间之上而引起的悲哀”。〔13〕虽然这一论断是针对《古诗十九首》而言的,但推而广之,就中国美学中的悲情意识而言,这种时间性的悲哀感,是悲情发生最为核心与根本的。
时间性所带来的悲情必然是针对个体的。对群体而言,这种时间性的短暂感与命运的无奈感往往被中国文化下特有的大历史观所消融。虽然这种个体性的意识常常并不直接作为主流出现于中国古代美学之中,中国古代文人并非不具备类似于西方自我意识所达到的个体性的特质,但是,他们以生命感来体悟。时间性下的个体呈现的便是生命观。时间的往复带来个体的无奈,在这种个体与外在分裂的过程中,时间是最能展现命运之不可抗的直接表达。在逝者如斯的境遇下,中国文人往往生出的便是生命的无奈感。这是由悲剧的内核所决定的,亦是作为个体所无力抗争的。而一切的大道日丧,一切的漏雨苍苔,都是在时间的往复中一去不返的不可抗拒的命定。
困苦而无奈,只能眼见“萧萧落叶,漏雨苍苔”,心中悲慨又与谁人说。困苦与无奈往往归于命运,无法弥合的分裂造成了循环往复的悲哀。“悲慨”一品以景起,以景终,但起始尤是悲壮之景,至尾处却“萧瑟寂寥,不免令人感极而悲矣”。〔14〕以萧瑟之景束尾,其中的无奈只能化为一声长叹,最终成就为中国美学中的悲情意识的一种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