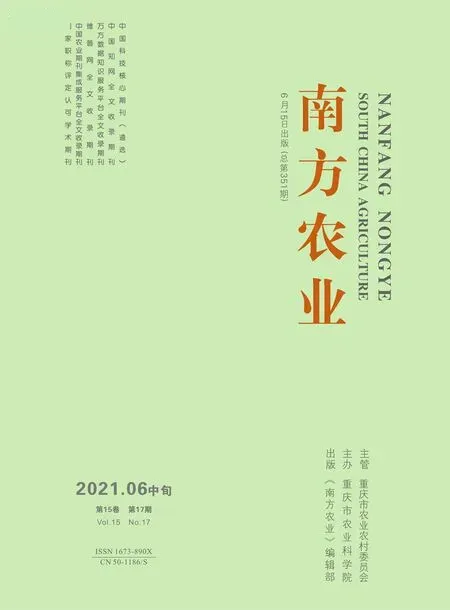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下有关农村社区建设的思考
胡子彤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
随着2020 年脱贫攻坚目标的全面顺利完成,我国农村的发展已迈向乡村振兴的重要阶段。在充分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五大任务,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及生活富裕。为了实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五大目标任务,进一步提升农村社区氛围,凝结社区情感,持续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建设,针对当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及突出性问题,期以通过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为未来中国农村社区建设找到思路、提供借鉴意义。
1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阐述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是在优势视角的引导下产生的理论,但其与优势视角较为宏观的理念不同:它比优势视角更为细致地制定了社区未来的发展道路,在优势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人们注重资产为本、聚焦内部和关系驱动,倡导社区居民一步一步地制定概念、树立信心、建立目标、操作化,使得发挥社区内在优势不仅仅是口号,而成为一套有迹可循的方案计划。
2 理论运用中可能存在的困境
相较于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处于边缘地位,同时国际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也影响着农业的发展与生产形态[1]。农民不同于城市居民居于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农民在维持生计的前提下,一时间难有条件发展自身的主体地位。“三农”问题的现实困境给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的实行造成了更多困难。
2.1 农村社区领袖缺位
社区领袖在解决有关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被反复提及,其对于农村社区结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实际上,社区领袖的培养即使是在发展历程较长的城市社区中都是十分困难的。城市社区的居民尚且因个体因素具有异质性,受到个体家庭琐事、工作要务的困扰。农村社区居民除了个人生活工作事务之外,还会受到文化知识水平的影响,部分地区还会有性别歧视的存在,这些都成为阻碍农村社区领袖形成的影响因素。
2.2 复杂权力结构设阻
随着社区的资源基础不断变化,并且依赖于大多数当地社区之外存在的实质性社会力量,社区资产必受外部结构性力量的制约[2]。社区的权力结构建立的同时必会引人产生不美好的联想,同时 社区与政府的连接若建立在对政府资源的过度依赖上,将可能降低社区的自主性,这些结果可能让外部关系成为一种“负债”[3]。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夹杂着政府职能的转化甚至下放,政府主导的社区建设自上而下,不能完全避免行政化的色彩,即使是基层的群众自治性组织,社会组织也很难在其中拥有较大的主导性,并借此建设完全由社会组织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就当前情况来看,我国当前社区建设模式更倾向于日本社区建设的混合模式。在此转换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过于行政化的社区治理体系也会造成加剧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2.3 农村代际关系日益疏离
在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中,十分重视社区关系的建立。社会学家滕尼斯也在使用“社区”这个概念来指称传统的“礼俗社会”的时候,该概念本身就具有根本的、道德统一性、亲密和亲族的意思[4]。我国农村也更加重视情感方面的联系,毕竟众多农村社区之间都存在着血缘或是宗族关系,然而社区在此方面的积累却也并非可持续的发展。个别的农村社区会因为历史先祖的缘由产生排他、排外性,其在张和清等于云南省绿寨进行的实践中就有鲜明体现[5];除此之外,代际关系的传递也会产生一定的损耗,进而破坏本以为可持续的团体凝聚力,如青年一代在社区间的交流极少,除了老一辈之间的人情往来,显得疏离冷漠。农村社区关系的建立一时之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
3 回应与对策
3.1 整合社区资源,助力社区建设
坚持社区资源整合是提升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步。农村社区的人员组成多样,既包括本地基层党建、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宗族中的大家长及乡村企业负责人,也会有部分外来进入的志愿者、专家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社会组织。针对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充分发挥社区内部重要角色作用,鉴于本地的党建负责人、政府人员、宗族家长及企业家所具有的语言和情感联系优势,可以在联络社区人员、机构和后续沟通、社区活动建设推广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外来的志愿者、专家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支教、帮扶等行动为社区带来高质量的知识培训和技能指导。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助力农村社区建设开展。
例如,在村支书和宗族家长等当地农村社区重要代表人物的支持和协助下,策划各类政策宣讲、技能培训活动,以农村社区第一书记为主要带头人,实行“固定课堂”与“流动课堂”宣讲模式[6]:“固定课堂”利用乡镇驻地、村委办公室等固定场所开展集中进行政策宣讲活动,充分利用本地党政机关人员的资源优势帮助农村社区居民认识基层政策,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和居民幸福感;“流动课堂”则利用群众会、田坎会等方便易捷的日常生活场所开展技能知识下乡宣讲活动,让本地的“田秀才”和外来的学者进行更深层次的切磋和交流,推动农村社区资源生产与发展。
3.2 聚焦内部力量,特色引擎发展
我国农村社区缺乏领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村社区中无法留住人才,结合我国农村发展现状,应充分利用中华民族乡俗文化的特点,使民族民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引擎”作用[7],刷新新一代青年人对农村社区的认识,使其看到农村社区中的新生动力,从而留于社区中,成为重要的人才领袖。在此基础上,相信在对优秀的民族及民俗文化上的充分认识和把控上,社区人才能够进一步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将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就会让诸多农村社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展现,达到将农村社区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物质创造力,最终造福一方社区居民的目的。
3.3 凝结情感,破解乡村社区“原子化”困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乡土社会由于中间组织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的个体原子化,导致人们走向人际关系疏离的未来。新时代的农村社会也面临着该种困境,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政府,导致乡村社区内部松散、组织能力差,农民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益时,往往以原子化的个人去面对政府和社会等权力机关[8]。而他们由于自身能力和社会地位相对的劣势,其利益诉求往往无法上达,而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因为中间组织力量的缺失失去了下传的管道。
为了突破这种发展困境,农村社区更应在其中承担“粘合剂”的作用,依托农村社区特有的乡土、乡情、乡愁等情感因素,充分利用基层党建、宗族凝聚力、民族信仰等力量构建乡村利益、情感共同体,不仅将基层乡村社会组建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要在此基础上将共同体建设的文化价值诉求在于培育互助精神,唤醒传统情理文化的感召力,帮助传统的农村社区居民交往摆脱更多的性别束缚、传统伦理规范约束,并由此形成守望相依、互援互助的情理法则,构建理性、团结、美好、热爱、共享及幸福的农村社区[9]。
4 总结与思考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有其在优势视角影响下的理想性偏差,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方法是一种必要但不充分的方法[10],它可能成为某种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良方,但同时存在着短板和局限性。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试图构建各方都获益的故事,有些时候发展虽不尽如人意,但任何改革和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以农村社会为背景的变革,更是掺杂着多重因素,具有强烈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