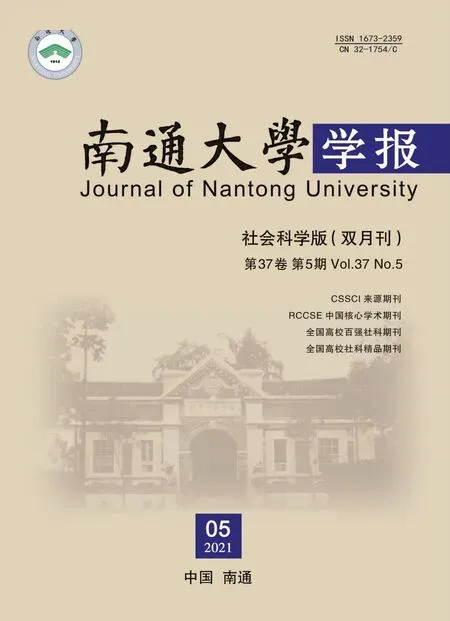从天下到国家:严复格义叙事中的“国群”伦理建构
凌 红,胡 芮
(1.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2.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社会发展到近代的产物,其特征是既具有近代国家形态的政治内涵,又含有具体民族特性的文化内涵。在晚清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历史实践中,维新派、革命派为实现民族复兴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建立近现代国家的构想。但在只知“天下”而不知“国家”的传统思想知识背景下,大多数人对近代以来“国家林立”的世界格局还难有真切的认识。加之,建构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在近代中国呈现出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的历史独特性,使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传统民族观念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在迎来具有国族象征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之前,晚清知识分子在思想界的探索对近代国族意识建构可谓有导源之功。其中,又以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构想最具典型意义。从1895 年开始,严复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其基于“群”的伦理内涵而提出的“国群”观念已经体现出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state)的意涵,在伦理认同方面具有独特的思想意义。目前,关于其“国群”伦理思想的研究,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从严复独特的“格义叙事”的思想实践中钩抉幽隐,探索严复的思想实践在近现代道德转型中的价值与作用,揭示其“国群”伦理思想深刻内涵,对于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的伦理意义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格义叙事”中的“国民”与“国群”
出于守护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保守立场,严复在翻译西学著作时,有意识地采用了一些中国文化之中固有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这种方法是区别于现代“翻译”之外的“格义叙事”①“格义”,原指中国学人以本土儒家、道家思想来解释佛学、理解佛教义理所用的比附和阐释方法,后来泛指用比较和类比的方法来解释异质文化的概念的方式。严复在翻译西学著作时,运用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中固有的概念来表达西学概念,也是一种“格义”。“叙事”最初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的呈现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模仿”(mimesis)/“叙事”(diegesis)的二分说。此言严复的“叙事”特点,是他在翻译时比较、分析了中西思想的共同特征和个体差异,并从个别的经验中揭示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而不是拘泥于狭隘的“本义”。在严复的翻译中,广泛存在比附性质的“格义”以及有目的地援引西方思想资源进行“叙事”,以契合中国的需要。例如在《天演论》中将“天演”“进化”视为“易”“天道”,将“逻各斯”和中国哲学中的“道”“太极”放在一起讨论,等等。这种独特的格义法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展现为“格义叙事”,换言之,“格义叙事”可以视为严复伦理思想的方法论基础。。严复自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足见其在会通中西方文化思想实践中的审慎心态。然而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格义叙事”的用心良苦似乎并没有得到思想界应有的肯定,甚至遭到过误解批判。围绕严复所译《社会通诠》的按语所引起的争议便是例证②严复曾因在《社会通诠》第十二章案语中的有关民族主义的“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等表述,被指责是非民族主义者。王宪明、苏中立等指明对严复民族主义思想存有“误解”,参见王宪明:《严复群学及军事政治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苏中立:《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对严复〈社会通诠〉中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辨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4 期。。究其缘由,学者们对其“民族”一词的解读存有偏差。当时严复所说的民族主义的“民族”之义,与当下学人所讲的民族主义所指并非同义。严复对“民族”“nation”“state”“国”“群”等词汇的理解与阐释,触及近代以来国族伦理建构的重大问题,也是近代伦理思想史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究。
据王宪明等人的研究,严复在《社会通诠》按语中所说的民族,“不是对应于甄克思原文中的‘nation’,而是对应于原文中的‘tribe’‘clan’‘patriarch’‘communities’等数个不同的词”,上述这些词,“其基本意思主要是指处于宗法社会阶段的‘宗族’‘家族’‘家长’‘群体’或以此为特点的社会组织,是建立近代国家过程中所必须扫除的过时之物”[1]120。苏中立指出:“‘nation’一词,按照后来通行的理解本应译作‘民族’,严复却多将之译作‘国民’……甄克思所谓的nation,是指在消灭了前述tribe 这一社会政治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代的或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政治组织,它强调领土与文化意识,它与居住于一定领土上的所有人口有关。它不等同于国家(state),但要通过国家实施政治管理,有的地方,nation 一词几乎与国家(state)同义。”[2]59
由此看来,严复将“nation”翻译为“国民”,而不是“民族”,是因为“民族”对于严复而言,是建立近代国家所需消灭的过时之物。那么严复所理解的“民族”之义是他自己的主观认定,还是有据可依呢?这一译法与我们所理解的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相距甚远。现今我们所用的“民族”一词对应于西文“nation”,这在当时主要归功于20 世纪初日译文及留日维新人士所做的贡献。那么当时日本学者对“民族”一词又作何解?其实,对于“民族”的来源地日本而言,当时对“民族”的使用也很混乱,连日本学者都感叹:“‘民族’一词,自何时、是如何开始使用的,并不十分清楚。”[3]64学界一般认为,日本学者将“nation”译为“民族”的最早例证是1872—1888 年间翻译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的《国家论》时,加藤弘之、平田东助等人将“民族”对应于“nation”。平田东助还曾对“民族”之义做了说明:“民族(Nation)与国民(Volk)虽其意义甚相类似,且相感通,然全非同一之物。德意志语所谓民族者,谓相同种族之民众。国民者,谓居住于同一国土内之民众,故有一族之民分居数国者,亦有一国包含数种民族者。”[4]239由此可见,19 世纪末日本对应“nation”的“民族”强调的是同种族的概念。很多人认为,“民族”就是日译汉字,来自日本。但现有学者已经从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找到了有关“民族”用词的语料。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族’一词,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3]63就此看来,无论“民族”是来自日本,还是中国固有,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之义起初的确具有宗法社会的特征,强调血缘、种族、家族等因素。
因此,对于一心要使中国脱离宗法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的严复而言,此种与宗法社会相系的“民族主义”必须摒弃,也就无可非议了。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来看,列强入侵,国家危亡,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兴盛,知识分子大声疾呼:“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5]485革命派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国人推翻帝制的有力武器。但严复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理性审慎的,他“改变了传统‘以夏变夷’的民族观,开始宣传‘物竞天择’竞争性民族观念”[6]45。为了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带来的国家分裂,他提出“保国”必须“合群”,合众人之心,统众人之志。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与华夷之辨相通的宗法社会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当下应该群策群力地由传统的宗法“国群”变为现代民族国家之基础的“国群”,其中过时的“民族”观念不可留存。也就是说,严复是要打破宗法性“民族”间的隔离,扫除“小己”与“国家”之间的障碍物。因此,他将“nation”译为“国民”,强调的是非同种同族但都是同一国土上的共同体成员,这明显具有现代民族国家(国族)意识,也凸显了严复的“没有‘民族主义’冠饰的民族主义者”[1]121的形象。
就中国近代的历史境遇而言,这种渴望民族一统的觉悟是在西方这个绝对的异族“他者”的刺激下萌生的。在与“他者”的抵抗过程中,近代中国有了建族自觉、国族自觉的自我意识以及走向近现代国家的要求。严复的“国群”说便是在这种语境中出现,以“群”为核心,力图以此为基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吴攀提出:“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是中国谋求生存、寻求富强的前提,也是遵循‘群’作为社会有机体不断进化的自然法则和历史规律的必然要求。”[7]137严复认同荀子的“民生有群”的观念,并结合社会进化律,提出社会是有“商工政学”的“有法之群”,国家是社会发展的“最重之义”。由于中国不存在西方“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严复对“国家”“社会”用词也没有太细致的区分,在国家社会层面上的群,严复称为“国群”。当然,也不能仅从传统的“群”的观念来理解严复的“国群”。严格意义上讲,严复的“国群”观念是传统“群”义近代发展的结果,是国家社会含义上的“群”。荀子的“群”论为严复“国群”观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基础,近代西方思想又赋予了“群”全的新内涵。
在严复看来,“国群”归于“群”。“群”不仅是人的社会性群体(social group),也是伦理道德共同体。自继承传统思想而言,严复的“群”说是建立在荀子“群”论之上。“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8]6能群之“能”,是人区别于禽兽天然本能的社会道德性象征。“人何以能群?曰:分。”(《荀子·王制》)“群”的基础是“分”,“分”主要指社会政治伦理分工。通过“分”,人们各得其所,各尽其责,构成规范有序的群体关系。“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分”的依据是“义”,“义”是礼义,道义,依据“义”,实现“明分使群”“群居和一”。可见,荀子的“群”不仅具有道德认知与价值导向,还具有社会组织性,是在礼义道义化的基础之上结成的有序的群体社会。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注重整体秩序。儒家的“礼乐之治”“和而不同”,墨家的“兼爱尚同”,法家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及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都透露出中国人追求整体和谐的价值倾向。孔孟开创了儒家注重“群”的思想传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社群伦理基调,荀子更是对孔孟“仁者,爱人”“兼善天下”人伦意义的群性思想作了开创性发展,突显出“群”的社会伦理性。
在承接传统基本“群”义的基础之上,严复吸收了先进的社会发展史观,根据英国学者甄克思(Edward Jenks)所著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他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异哉吾中国之社会也!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8]135虽然这种直线型一元进化史观具有历史狭隘性,但是近代竞争秩序的世界版图中,“国家以军制武节而立者也,以争存为精神,为域中最大之物竞,不竞则国无以立,而其种亦亡”[9]88。争存立国是时代发展所需,是近代特色。根据严复所言,“国”和“社会”虽都属“群”,但“国”与“社会”还是有所区分的。“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东学称组织)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卪,有法度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8]126“社会”可以理解为一群人有法度地在一个固定的区域生活。“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固守特定的疆域,不仅要有法度地生活,还要时刻抵御外来侵犯,所以“国”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严复的现代“国群”理念是在吸收西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伦理资源而形成的。不难看出,在援引西学资源进行“国群”理念建构中,传统伦理资源始终是作为认识的“前见”出现的。梳理其对“国民”“国族”概念进行格义叙事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出,严复孜孜以求民族国家的当代建构和传统封建伦理秩序之间是存在着不小的张力的,此过程既体现了“过渡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困顿,更折射出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存在不小的抵牾之处。可以肯定的是,严复的格义叙事背后“兼采中西、以中为主”的价值立场,既是当时面对强大西学的审慎态度,也是基于中国时代问题的理性反应。
二、“群学”观念建构中的中西汇通
“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8]560是严复追求国家富强的基本文化观。为挽救晚清中国之危局,一些先进分子提出“合群”口号,兴起一股群学、合群思潮。不同于早期康梁从传统典籍引申出“敬业乐群、会友辅仁”的群学思想,严复借用了西方社会科学原理,注意引证传统文化资源加以论述叙事,阐释以民为本的现代群治理念。《原强》一文中,严复这样写道:“有锡彭塞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8]6从英国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群学,严复看到了“民之相生相养”的民术和“兵刑礼乐”的群术的中西融通,主张以先进的西方学术之理来阐释中国人伦之事,以实现群治之效。可以看出,严复对“群学”的阐发明显受到东西方文化资源的双重影响,对荀子思想的阐释体现出鲜明的救亡倾向,是寄希望于谋求文化救国之道的时代表现,用中西会通的思想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严复把西学的社会有机体论、自由论、进化论等思想融合在建构未来民族国家的构想中。面对“国将不国,群将不群”的危难时局,严复呼吁国人“合群保种”。“合群保种”是充分发挥个体的能力,提升小己的“力”“智”“德”,实现利己利他的文明社会环境达到“合私为公”,以实现国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富强。受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思想影响,在严复看来,“群”“国”是由“小己”“民”构成的社会有机体。“所谓小己,即个人也。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么匿’,译言‘单位’。……社会之变相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是故群学谨于其分,所谓名之必可言也。”[8]126严复通过音译的方式新造了一对概念——“拓都”与“么匿”,用以表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中西伦理的差别[10]25。将“小己”置于“群”之中,将“民”置于“国”之内,以“小己”“民”为构建“群”“国”之单位,取代“王土”“王臣”的封建伦理关系,他提出保国的治本之策,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8]27鼓民力就是增强国人的身体素质,练“民之手足体力”;开民智就是“追求学问、探究事理”;新民德,就是培育“人心相通”的社会公德。其中,严复认为新民德为三者之最难。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聚民力强国力的精神。
严复借助于西学资源阐发的“以民为本”思想已然不同于传统民本思想,是与现代自由权利理念相结合的民本论。“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8]27自由是严复“合群保种”说的关键词。严复介绍斯宾塞有关群学的太平公例时说:“各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域。”他肯定了自由对于个体及群体发展的价值,是个体发展的前提。人得自由,则个体的潜能才能得以发掘与提高,群体的富强才能得以实现。同时,个人自由需以他人自由为边界,以求权利无损而共利。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8]5,严复感叹:“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8]981在近代“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国际竞争形态下,从19世纪中叶开始晚清王朝遭遇史无前例的变局与危机,救亡图存,合群保种成为举国上下至重至大的任务。严复的“群学”以“群”“己”为基本范畴,以自由为核心价值构建了新的伦理体系[11]42,其目的是企图通过思想的革新造就新兴的民族,进而建设新兴的国家,体现出温和改革的总基调。
20 世纪初,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冲突激烈,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其中源自排满情绪的“小民族主义”(梁启超语)盛行一时。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运用了大量篇幅论证满汉之分野,称满族是“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12]182,主张推翻满族统治,建立大汉族。革命领袖孙文在革命初期也坚持满汉之分,1905 年8 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其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有八字是反满。排满与严复的“合群”形成对立。严复认为“合群保种”需合众人之力,凝聚国人之心。“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遂)邃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8]10排满情绪虽然对动员民众参与反封建斗争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容易导致民族分裂主义倾向。严复的民族观点不同于狭隘的“小民族主义”思想,与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不谋而合。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提出“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亦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13]75-76。受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思想的启发,梁启超在1902 年写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了作为整体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概念,“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13]73。“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是“构建新伦理体系与民族国家的重要精神支柱”[14]174。严复说:“爱国者,民族主义之名辞也。泰西哲家谓非道德理想之至者,故世间国土并立,必其有侵小攻弱之家,夫而后其主义有所用也。”[15]265从这一理路看,严复早已超越了传统种族和地域的界限,持有一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民族整体意识。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指出:“没有某种社会制度,没有构成社会制度的有组织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就根本不可能有充分成熟的个体自我或人格。”[16]231严复的“合群保种”是从历史传统和社会制度两个维度展开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从基本的生命生存物资环境考虑,群体为个体提供了保障,所以合群一开始就是一种本能的需求。群性还具有历史性,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群性在合群的基础上,会不断容纳和增加新的社会性元素,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伦理道德规范。史密斯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17]9“民族”对应于严复思想体系中的“国群”,严复推崇“国群”,是基于伦理共同体的思考,即以民族国家为最高伦理目标。他从种群竞争的国际视角出发,超越了传统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侧重于争取民族独立,伸张领土主权和民族凝聚力,超越了传统的文化认同模式,走向了近代民族国家认同。
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是伴随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国人的思想意识中诞生的,其过程的被动性远远大于自发的主动性。王朝“天下”与近代“国家”的对抗包含了对传统家国一体观的解体和近代独立自主国家观的建立,其过程实则是要实现国家伦理观念由传统向近代的蜕变,促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费孝通语)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18]1。中国的“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建构近代民族国家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历史境遇。严复的工作,事实上找到了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伦理资源的接榫之处,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基础上,改造并有机融合了传统民族观念,为国族伦理建构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三、建构“国群”伦理实体
要理解严复建立国族伦理认同的思想谋划,需要进入近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思想时空。从16 世纪的英国开始,法、俄、美、德随之陆续建立起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在几百年中逐渐推广到亚、非诸国。这种时代现象也可以说是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席卷之下产生的。作为现代国家基本组织形态,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这一“想象”是基于历史、现实的一种建构。不单是政治理性的建构,还有集体认同的情感归依。不单是享有自由权利的个体集合,更是作为伦理道德的共同体而存在。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黑格尔有关伦理实体理论中得到启示。黑格尔在其著作《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对伦理实体的形态有不同的提法,前者以家庭和民族为伦理实体的基本结构,后者将伦理实体划分为“家庭(family)——市民社会(civil)——国家(country)”三阶段。看似不同的框架,实则本质精神是统一的。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可以看作是民族的现实精神的客观化和运动的两个环节”[19]108。在黑格尔看来,“伦理性的实体包含着同自己概念合一的自为地存在的自我意识,它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20]197。民族是天然的伦理实体,而在近代的国家中,民族和国家在近现代国家形态中不可分割。从伦理精神上说,国家是民族的伦理精神的否定之否定的运动结果;从时间值域上看,民族和国家是连接着历史和未来的一条轴线。
理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要义可以归为几点:(1)构成民族国家的要素包括:集体认同的民族,政治独立的国家身份,拥有边界的领土范围。(2)建构民族国家包括民族与国家的双重建构。既是具有统一的民族意识的民族共同体,又是以国家为最高忠诚对象且体现人民主权的国家政治共同体。(3)构建民族国家虽然是时代现象,但是因具体历史境遇的不同,又具有个体差异性。概而论之,不管是从领土,还是族类划分,民族国家都是宣扬主权自治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整体构建的民族认同。
若从建构共同体的目的论出发,严复的“国群”说充分体现了建构共同体的意蕴。“国群”首先是作为“政治-法律”共同体的实体。严复将“state”一词译作“国家”,强调了治权,将“nation”一词译作“同种国民”,强调了文化认同。他指出:“以其言语风俗之同,于是据一领土,内足自治,外可御侮,而国成焉。”[8]329就对内自治而言,国家的治权通过政府发挥公权力,政府实则是国民行使权力的机构,通过国家的政治制度来实现。就政治自由而言,严复阐述为国家主权独立自由、民主自由、民权自由等,提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认为国家是民主政治共同体。用西方自由主义观念来阐释国群的近代内涵,他说:“见世俗称用自由,大抵不出三义:一、以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制干涉为自由。此义传之最古,于史传诗歌中最多见。二、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为自由。在古有是,方今亦然。欧洲君民之争,无非为此。故曰自由如树,必流血灌溉而后长成。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由。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婚姻自由,结会自由,皆此类矣。”[8]1289-1290同时,严复认为自由是有法之自由,“夫文明之众,虽号结习自由,顾所谓自由者,亦必在法典范围之内,有或干纪违法,政府固得干涉而禁沮之”[8]300,提倡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是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如若违反法律条例,政府有权干涉。关于自由权限的界定,最具有说服力的是严复译自穆勒《论自由》的《群己权界论》。在《群己权界论》首篇,严复便明示道:“群理之自由,与节制对。今此篇所论释,群理自由也。盖国,合众民而言之曰国人(含社会国家在内),举一民而言之曰小己。今问国人范围小己,小己受制国人,以正道大法言之,彼此权力界限,定于何所?”[21]1通过对自由之群己权界论的阐释,严复为建立自治的主权意识提供了法理基础。群己自由是严复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命脉。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无论宣称主权的人实际上期盼的是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当主权成为从下由人民提出而不是从上由上层统治者提出的主张时,民族国家的现代理想就产生了。”[22]351-352
严复所言“国群”是近代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制形态,是近代社会的伦理共同体。不同于荀子所言的传统宗族组织建制形态的“国群”,而是吸收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和传统群体伦理的杰作。斯宾塞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进化原则运用于人类社会范畴,提出社会有机体进化论。他将社会类比成生物体,将社会分工类比于生物体各器官的分工,认为机能的均衡决定有机体的均衡。在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强调个体对整体的影响,认为“聚集体的特性是由各组成单位的特性决定的”。受其启发,严复提出:“斯宾塞诸公,以国群为有生之大机体,生病老死,与一切之有机体平行,为之比较,至纤至悉。”“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大小虽异,官治相准。”他透过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发现了国群作为一有机生物整体,其与群内个体之间的重要关系,并且从斯宾塞的思想中另辟蹊径地找到了中国传统群体伦理的影子,觉知到社会有机体论与我国文化的“秩序情结”的暗合。“窃以为其书(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8]126由此可见,严复的“国群”不仅是有机体,更是伦理共同体。他说:“国者有机之体也;民者,国之么匿也;道德者,其相吸力之大用也。故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基于苞桑。即使时运危险,风雨飘摇,亦将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8]342将么匿之小民凝聚成一国之机体在于道德力之维系,没有道德的向心力,一国之民则如一盘散沙,国将不成国。严复推崇的道德力是爱己、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的道德公心力,冲破传统私德蒙蔽、将中国德性主义伦理传统的“推己及人”的亲和力,以及“忠恕之道”的约束力结合起来,以此为凝聚民族国家的力量,来推进现代群治方略。于严复而言,“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8]18。“群者,人群之积”。群学要义在“人伦治化”。严复一方面宣传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另一方面,他更为用心的是强调“能群”“善群”“合群”的群道思想。
对于严复而言,近代国家应是“合群善群”的伦理共同体。借由“国群”概念,严复融通了中国传统民族观念与近现代西方的民族(nation)思想,“国群”体现出鲜明的伦理实体之寓意。严复结合传统社群主义群体文化基础,吸纳西方先进社会科学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国群”概念。其思想建构的特点一方面包含建构现代独立自治共同体的意蕴,另一方面体现出他对基于传统伦理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严复作为近代伦理启蒙的先行者,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冲突的历史境遇中,审慎地采取了学习和融会西方现代思想的立场,通过其独特的“格义叙事”为近代寻求思想自强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有益的进路,具有非凡的思想创见和文化革新的勇气。但也需要看到,严复建构“国群”的思想架构,仍停留于将中西方思想资源进行生涩拼接的阶段,没有深入挖掘出华夏民族的“历史-文化”根基。正是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做出了更深刻而合理的建构,他说:“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23]8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事实。而将这一事实自觉地表现为一个统一民族而不带任何歧视或挟私自重,含纳各个民族和谐共生而皆相忘于江湖,固然有梁启超的杰出贡献[14]174,也应该是严复的“国群”思想启迪了梁启超对“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从这个意义来说,严复开风气之功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