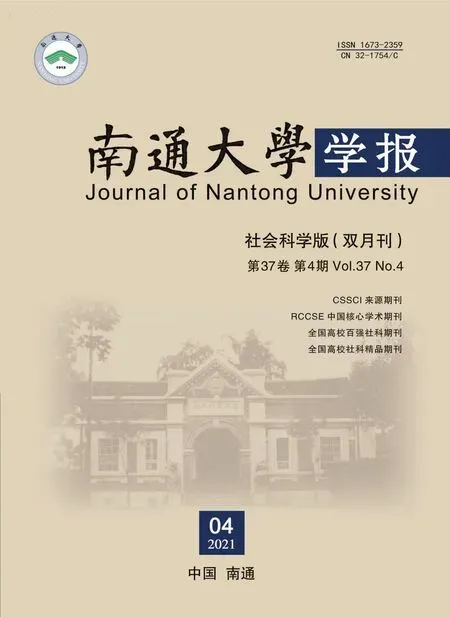论建党百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信仰的现代性探索及其效应
赵宬斐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从19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逐步确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构建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之后,立刻对东方中国采取殖民式的掠夺行动,这使中国社会传统的家国天下信仰体系及其统治秩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国知识群体随着传统秩序的逐渐解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从此,国人在直面西方现代性暴风骤雨般的洗礼时,立刻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长期在社会生活中累积与传承下来的传统也陷入困惑和危机之中。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1]7中国社会传统正是在遭遇西方现代性的直面碰撞下,引发了“一系列文化、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大变化”以及“最重要的权势转移”[2]9,导致中国知识界陷入前所未有的“知识论危机”①“知识论危机”是美国学者麦金泰尔在《谁的公正,哪一种理性》(1988)一书中提到的观点。之中。在这艰难与危机的时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传统信仰不断解体的过程中探索、选择以及建构新的信仰体系,以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其中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自身的传统进行反思,为摆脱艰难处境寻求突破,他们在信仰知识谱系与图景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导,实现信仰转向,进行信仰的现代性新建构,这也导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视野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他们自觉承担起中华民族复兴与现代国家建构的使命,开始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与大动荡中,吹响了现代性号角。
一、“知识论危机”下知识分子传统信仰的解体及其转向
“知识论危机”旨在对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某些转折和节点呈现出的一些特征进行概括。麦金泰尔认为,人类社会传统文明一般经过信仰建立、信仰质疑与信仰重构阶段的发展序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已经习惯于对“天下体系”和“天朝大国”心存信仰与崇敬,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指引下生活着;但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社会一下子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瞬间产生的民族危机、国家危机、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令国人不知所措;国人的“知识仓库”逐渐陷入“失序”状态[3]8。人们发现再按照传统的观念指引生活,不仅不能适应世界的发展,甚至无法正确辨识眼前世界的急剧变化,身边的诸多问题与事件等都得不到有效的解答。业已建立和运行的传统信仰开始遭受质疑,亟须新的信仰来替代之。在这个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困局。在这个时期,这批先进知识分子自觉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为如何更好地改造已经出现严重危机与断裂的传统社会,苦苦寻求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于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传统的羁绊,转向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想从西方现代性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去建构新的信仰及追求,从而为改造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输入新鲜血液,帮助传统摆脱危机。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遭遇西方现代性冲击带来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4]。面对西方多重冲击,中国传统社会依靠自身能力显然无法应对多重灾难与危机。如果说“一个传统反复带来灾难,或反复被证明明显不灵,那就行将灭亡了”[5]272,面对“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6]174-175的艰难困局,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已经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此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临的不仅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更是深刻的信仰危机。要有效解决这个危机必须“借助另一个有生命力的传统来帮助它度过这个危机”[7]18-19,面对现实的残酷与压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确实感到需要西方先进的现代性替代没落的传统,以一种先进科学的世界观和信仰帮助中国社会顺利地从传统转向现代,并妥善处理好新观念、新信仰与过去长期存留的旧观念和旧信仰之间的关系,重建一种有助于人们理解和适应的现代性新秩序与新生活。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救亡图存危机,不仅是一种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可以说更是一种深远意义上的信仰危机。在这场中西对比产生的鲜明强弱之势的比较与刺激中,为了寻找真信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表现出应有的勇于承担使命与责任的雄伟气魄,拯救民族危亡和热爱国家的伟大风骨,都扮演了“盗火者”和“取经者”的先驱者角色,努力寻找救亡图存的先进理论,以指导中国社会的救亡图存。20 世纪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共同表达的主题思想,先进中国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的新理念,他们由此自觉地担负起如何使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伟大责任与使命。
在现代性探索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与挑战,特别是在20 世纪初,中国被迫面向西方开放,一时间西方各种思潮迅速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到处充斥着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冲突。这个时期显然是“一个新旧决裂和分化的时刻”,这也“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进一步的伟大的分裂”[8]26-27。中国早期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逐渐认识到西方现代性所孕育的理性、科学性、主体性与先进性,试图从那里找到能够帮助传统摆脱危机的方法论与现代性方案。他们进行艰难探索,开始尝试“在认识外来文明的过程中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文明和政治、社会制度”[9]169。围绕着“如何拯救中国”“中国向何处去”等历史性问题探讨,在中国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形成了一幅政治救亡思潮蜂起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其中,以经世致用、洋务、维新、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思潮最具有代表性。如此纷杂的政治思潮在中国大地上互相激荡,交相呼应,精彩纷呈;或旧潮未落,新潮又起;或是蹒跚前进,或是急转直下,形成了嬗递多变、波澜壮阔的景观。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真信仰积极开展对各种“信仰”的“比较”“试错”与“甄别”,面对当时多样化的文化思潮和对各种主义进行综合审视多方比较,在反复试错与甄别过程中,自觉地认同和接受当时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独具的信仰现代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具体行动方面采用多种方式与方法翻译、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指导地位。这批先进知识分子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但实现了自我的政治自觉,还唤起了民众的政治自觉,并逐渐成长为主动组织、领导大众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对各种思潮试错与甄别中追求真信仰,在追求无形强大的信仰过程中,主动与拯救民族危亡、实现现代国家建构的自觉担当精神合二为一,不分彼此,如此一来,即便在最艰难时,只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精神就不会垮,就能够在对各种思潮进行综合审视与总结中完成在信仰方面的自觉选择。历史的发展也最终证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实现对信仰的现代性追求,必定在中国社会历史长河中奏响凝重而辉煌的华章。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信仰的现代性建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传播以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极大地震荡了中国社会原初的历史语境,立刻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响应与共鸣,产生一种巨大鼓舞性的力量,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指导下,逐渐由原来的个体信仰转变为集体信仰,凝练成一种新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把西方先进的现代性思想——马克思主义有效地与中国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好,对社会广大民众的信仰进行示范与引领,率领广大民众进行现代性革命以摆脱被奴役和被统治,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独立。这种信仰的现代性是从历史、现实与实践的维度中建构出来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直面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以拯救民族危亡和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为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要通过“传播—改造”“组党—革命”“组党—实践”等方式实现了信仰的现代性新建构。
(一)“传播—改造”
五四运动前后,由于逐渐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十月革命及其道路的认同,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杨匏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系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积极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活动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旦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会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来武装自己。他们不仅成为各种维护资本主义理论的彻底批判者,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批判者。由于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十月革命胜利的展望,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必将“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10]104,人类社会今后发展趋势“必是赤旗的世界”[10]117。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在了解、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完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化,使当时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获得完整的框架,被当作科学认识世界的理论,被看作有效改造中国的科学指南。如此以来,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也日益体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于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现代救亡图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逐渐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契合、一种历史性的精神期待。作为民族灵魂的知识分子,充当了挽救国运、振兴中华的先锋和桥梁,由此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拯救民族危亡和实现现代国家建构的新观念以取代原有传统中没落的“家国天下”的信仰观。陈独秀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11]17,开始尝试用它来改造社会;李大钊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讴歌十月革命并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12]260。李大钊在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指出,在中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指导下来改造整个社会,使其旧貌换新颜,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蔡和森在接受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之后也指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3]50一旦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如何使其获得民众的认可与接受赢得最大范围的支持。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仅通过报纸、书刊这些传播媒介,逐渐塑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即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仅仅为了“探究学理”和“玩弄新的词藻”,而且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把探寻的社会发展规律看作“担负革命”的“科学理论”。他们勇敢而又理智地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那就是尝试“组党—革命”,促进马克思主义真正走向劳苦大众的心里,用于指导中国的革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和国家建构等重大问题。
(二)“组党—革命”
当时,西方国家建构的先进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引领世界潮流,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混乱社会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没有任何一种组织或团体有能力承担起结束中国社会混乱局面的艰巨任务。正如张闻天指出的那样:“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14]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在这个“世界的新潮流”[15]中实现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必须在先进的信仰支持下成立一个先进组织,把全国劳苦大众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像苏联共产党一样的中国政党组织十分必要,必须按照“组党—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蔡和森就深深感到建立先进党组织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民众运动过于幼稚,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组织和俄国共产党一致的共产党,这样才能让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有力且彻底。”[16]39陈独秀身体力行,很快就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中国各地先进知识分子群策群力地积极响应建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尝试探索出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复兴民族、振兴中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织化。这个组织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完成,就是因为中国社会中已经存在着“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7]。可以说,“对‘主义’的信仰和从个人走向‘组织’,成为五四知识分子重新寻找救国路径和个人生命意义的不二法门”[18]。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创立中国共产党之后,就立刻对政党组织进行“政治训练”,期望中国共产党也能够“像1871 年法国巴黎无产阶级和1917 年10 月俄国十月革命一样,采取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直接革命’,来实现社会革命”[19]。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创立列宁主义式的先进政党之后,立即组织广泛的宣传,带领劳苦大众进行革命斗争,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最终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救国救民、复兴民族、振兴中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举措,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扫清了诸多障碍。这不仅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而且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选择“组党—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他们开始逐渐将自己的视线聚焦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和实践道路上来,并坚定了以阶级斗争和武力革命的手段来践行伟大的信仰。
(三)“组党—实践”
随着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中国爆发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的传播与阐释,而开始面向社会大众、走向社会大众、结合社会大众和引导社会大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一方面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其的坚定信仰,在国内的大力译介、传播促进广大民众对其的认同与接收;另一方面是先进知识分子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需要这种先进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引导大众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提升自身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是先进知识分子破解这一议题的关键之举。
李大钊不止一次地说自己“喜欢谈论布尔扎维主义”,更是坚定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如何分析中国实际问题,以真正解决好“中国向何处去”[20]264-266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分析当时中国实际就指出:“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21]517,伴随着国人思想政治觉悟的逐步提高,毛泽东指出“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21]517。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只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才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并能够转化为自觉的实际行动,以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完成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立新的信仰时,就成为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坚持以“具体事实”作为认识问题的基本依据,用科学的认识论看待中国具体的实际问题,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和组织工人力量,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深入到厂矿、企业组织工人,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阶级基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是立足于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思考和选择,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自己的具体经验,统筹考虑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如革命手段、革命力量等,创建了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信仰的现代性建构不仅改变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生活方式、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还进一步推动他们建立起新的思想观、文化观与理论观。这批先进知识分子从批判中国传统儒教中转向接受和传播西方各种现代性思潮,再到进一步更替为真正信仰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指导,进而掌握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武器,最终完成了信仰的真正转向。这彰显出他们矢志不渝的对信仰现代性的追求。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信仰的现代性建构不仅推动他们毫不犹豫地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家国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还推动着他们孜孜不倦地探索民族、国家在未来世界中的坐标。在新的信仰指导下,他们认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即“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22]317。这批先进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自我认知的不断升华、不断淬炼和砥砺前行的精神,才使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具备了思想变革与制度创新的意义。
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信仰建构的现代性效应
知识分子群体一旦确定新的信仰建构,必然导致其政治视野与格局都发生深刻的变动,并越来越具备高度的政治化功能,这也赋予他们在政治上的特殊使命与责任担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立刻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与大动荡中,新的信仰建构也成为呼唤知识分子政治意识苏醒的现代性号角,由此产生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自觉,现代民族与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价值与信仰体系的重建等一系列政治现代性效应。
(一)知识分子的政治自觉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的激荡,进一步促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转向。他们坚持从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技术与制度,进一步拓展延伸到文化、思想与观念,这种转向不仅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一种危机意识,而且在反思中产生了政治自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从中西文化冲突的洗礼中摆脱传统和旧学走向现代性与新知识兼备,这种时代变革面临的迫切之事就是如何再造新文明的政治觉悟。正如胡适指出的那样:“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23]409。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新政治观的实践,只有立足于对现代性追求的自觉之上与旧的传统彻底决裂,才能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架构不足以实现救国的目的,特别是经历了清末民初一系列政治体制的失败尝试,他们最终与传统的信仰决裂,开始重塑自己的信仰,秉持强烈历史责任感,去寻求客观真理,探寻中国救亡道路,并积极依靠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信仰唤醒民众、引导民众,以实际行动去推进历史的变革。总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认识到明显冲突着的每一种观念都有正确的地方……这个群体有力地推翻了极端的保守也不断阻止着激进的狂暴盲动,这个群体引领新中国走出危急的转变阶段,正呵护着她迈向伟大的未来”[24]25。中国知识分子最鲜明的政治自觉就是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新信仰引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凝聚信仰。
(二)现代性的民族与国家意识诞生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混乱时代,中国人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如何拯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与统一。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事件“都不曾达到挽救危亡的目标,都不曾做到建设一个有力的统一的国家的目标”[23]380。在内忧外患交织下,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不但自觉地提升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还有效地促进了国人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的觉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是以“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23]552。胡适在这里借用“小我”“大我”等词来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就是那个时代的“大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天下”怀有深沉责任感,才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突破了“皇权神圣”“朕即国家”的“家天下”的传统信仰观,自觉地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斗中,凝练出对民族与国家的新的信仰观并广泛和深入地传播、接受,从而使中国走上了民族解放和振兴之路。
(三)群体性信仰的凝练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坚定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能在经世致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潮中进行比较与鉴别,使自己置身于各种治世救国的舆论与思想中保持一份清醒和冷静。在当时,无论是“实业救国”、社会进化论、互助主义,还是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信仰产生过影响,但是经过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渐深入认识以及在革命斗争中锤炼,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摆脱了各种思潮的干扰,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相信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坚定走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范式才能实现救亡图存。他们因信仰的选择不约而同地承担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建构的伟大历史使命。陈独秀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就指出:“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25]17他进一步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25]10毛泽东也认为:“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6]2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才能使中国人看到自己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的新理念。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无数社会成员共同表达的主题思想。先进中国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统摄各种思想、主义和方案,并置之于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推动着救亡运动向更高的层次跃进。
(四)改造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确立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改造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都把目光投向西方发达国家,希望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取经验与借鉴来更好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由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拉开了对西方现代性方案的移植与探索的大幕。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道路的探索中,先后出现各种社会改造方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洋务派救国方案;以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代表的戊戌变法和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等,上述改造中国方案都无法经受时间的检验,一一遭受破产,这也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如何“改造中国”的现代性进行再思索与再探索。随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责任意识逐渐增强,中国思想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着重新定位与转向。如何革命、怎样救亡以及坚持什么样的阶级立场,逐渐主导了整个思想界。这样,“改良”逐渐让位于“革命”。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主要代表的革命者开始真正登场,以革命的手段书写宏大叙事,他们从无数个方案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武器,凝聚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共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改造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坚决抛弃了温和改良的方式,把武装斗争与暴力革命作为改造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五)重建价值与信仰体系
面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巨大困境,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清醒认知“一个面对知识论的危机的传统已经无法由它本身的资源再予以复苏,因此,它必须提出新的架构及理论来解决困难”[7]18-19。这个新的框架和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是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指导,才最终摆脱了遭遇传统信仰解体的“知识论危机”,焕发出革命的青春与活力。他们积极参与和领导救亡图存,重建价值与信仰体系,积极推进社会政治体制变革。这批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共产主义作为终身奋斗的理想目标,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状况构建起长远目标和眼前目标相结合的信仰体系:把始终不渝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确立为长期信仰,把用革命的手段消除内乱进而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国家建构确立为坚定信仰;同时,为了实现伟大目标,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以凝聚信仰,通过革命使中华民族彻底走向民族独立。
四、结语
正是一代又一代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不变初心和伟大使命,才有了今天的伟大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从1921 年成立以来,历经百年,正在把一个个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在革命年代,无数共产党人坚定信仰,经受住血与火、生与死的淬炼,谱写出一曲曲视死如归的英雄赞歌;在新时代他们又经受住各种名与利、得与失和各种诱惑的考验,描绘出翻天覆地的宏伟蓝图。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就是信仰的传承,不管是在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中,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困难挑战面前,共产党人都是以信仰作为自己的精神之基,以身许党,以身报国,忠心为民。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我们感受到一种力量,并吸收这种力量,使自己在面对坎坷中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