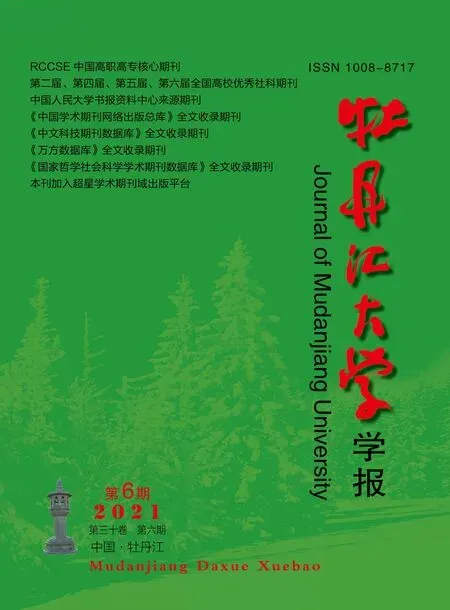现实主义美学特征的彰显
——评何顿的《幸福街》
李小红 黄小莹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汉语言文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何顿的新作《幸福街》,是成熟作家的精心之作。小说诞生后,引起批评界的关注。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幸福街》无论是在作品的表现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是作家以自己的写作经验和悲悯情怀创作出的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从小说内容来看,《幸福街》主要讲述了湘南黄家镇上一条名为幸福街的街道上,两代人在近70年的历史变迁中的生活经历。小说在书写人物性格、命运变迁的小历史中将黄家镇乃至整个湖湘地区的沧桑巨变娓娓道来,同时,小镇风景,风俗习惯、饮食、服饰文化的有机融入,使《幸福街》博彩众长的同时又能兼具个人特色,成为新世纪以来又一部全景展现市民生活与历史,彰显现实主义美学特征的力作。
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经历了异常复杂的接受和发展过程。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倡导的“写实主义”到鲁迅要求打破“瞒和骗”,以个体心灵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再到40年代胡风洋溢着“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诞生,现实主义一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的焦点论题。进入当代以来,虽然种种艺术思潮风起云涌,但是对现实主义的重视从未曾中断。90年代后期兴起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作家们始终对现实主义保持着旺盛的热情。然而,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之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应该拥有怎样的美学特征?要想把这些中外文艺理论颇多争议问题阐述清楚,可能需要专章论述。然而,普遍的一种认知是,作为一种创作原则,现实主义应该保有其“诗”与“真”的美学特征。“诗”是指其“诗性”,而“真”是指作品能够忠实地反映历史、生活本质的真实与真相的特点。从这个层面而言,何顿的《幸福街》正鲜明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
一、性格史、命运史与大历史的辉映
历史是对发生于过去事件的话语叙述,历史存在于叙述当中。然而,由于叙述历史主体的立场、方式、视野的差异,使得历史叙述出现了许多分野,历史因此有了大小之辨。“所谓‘小历史’,就是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所谓‘大历史’,就是那些‘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1]作为当今文坛上书写历史的长篇佳作,何顿《幸福街》最显著的现实主义特征之一,就在于作家摒弃了长篇小说表现历史时惯常对“大历史”“史诗性”的追求,转而关注普通人性格、命运的发展变化。小说集中书写了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后期近70年的历史变迁中,幸福街上的两代人对理想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他们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心灵的煎熬与痛苦。在细致、鲜活、丰沛的性格史、命运史的书写中,作家表达着勾陈一个国家、民族历史走向的愿景。
《幸福街》的开篇,何顿以从容纡徐的笔调,讲述幸福街改名的事:“幸福街原先叫吕家巷,1951年新政权给街巷钉门牌号时,将它改名为幸福街。”开篇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实际却包含着新中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事件。紧接着以幸福街为核心,本书的主人公1958年出生的几个孩子开始登场,住在幸福街的何勇、林阿亚、陈漫秋;住在光裕里的黄国辉,住在由义巷的张小山。紧随他们其后的是50年代走上工作岗位的上一辈的父母叔伯婶娘以及邻居。何勇的母亲是小学校长李咏梅、父亲是大米厂的厂长何天明;林阿亚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周兰、父亲是理发师林志华;陈漫秋的母亲是赵春花、父亲陈正石是个资本家,后来被打成右派,一蹶不振,死于脑溢血。黄琳的父亲黄迎春是区长,母亲是孙映山,张小山的父亲是副区长。林林总总的各式人物生活于同一个空间中,作家笔触在两代、数十个人物之间自由的腾挪转换而丝毫不显凌乱,这主要得益于作家高超的叙事手法。他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小说的每一章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主人公重点叙事,其他人物与其互为映衬,由此,每一个人物形象的性格都获得了充分的成长空间。在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中,展开了对他们人生命运、际遇的探寻,在他们看似偶然,被历史洪流所决定的人生经历中,实际上隐含了作家对他们人生走向中必然性的思考。
小说中最具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之一是张小山,小说叙述张小山的悲剧命运,将之与荒诞、风起云涌的时代相联系,写出了大时代洪流的裹挟中人的卑微与渺小,不能自己掌控自己命运的悲剧处境。小说表现人物命运与时代紧密勾连的一个典型事件就是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这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可是,对于参加高考,青梅竹马的几个人却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对于林阿亚、黄国进、陈漫秋几个好学上进,在文革中没有荒废学业的人来说,是喜事,他们都信心满满的准备参加高考;对于何勇、张小山和黄国辉而言,确是难以言喻的苦涩与伤感:
何勇叹息一声说:“要是那时也考大学,我也会读书。”张小山恨道:“就是,要是高考提前几年,我也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那现在我肯定也是个大学生。”……“唉,世上又没有后悔药呷。”何勇说,脸色就深沉,“我们被‘四人帮’害醉了,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当时生怕自己变反动”。张小山笑,附和道:“何勇说的没错,我们那时候懂个屁?受这些害人的思想影响,我读高中时连书包都不带的。那是读什么屁书?”[2]
这一段关于高考、大学的对话,会使我们自然而然的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伤痕小说”,叙述文革造成了一代人盲目无知、面对新时代无所适从的悲剧处境。然而,如果作家的笔锋就此停止,那么张小山这个人物形象充其量也就与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宋宝琦类似,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然而,何顿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笔触向更深处挺进,以独特的艺术技巧随物赋形,写出了历史流转中人物性格形成,变化的过程,以及命运与时代交织的多义性与复杂性,人物形象因此更具立体感。
“1978年底,张小山招工进了竹器厂。一进竹器厂,他又觉得没点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的思想也跟着改革开放的思路活跃起来。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不想一辈子与竹子打交道!他心大、人野,想改变自己。”[3]“脑子活”是张小山的典型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点在整部《幸福街》中具有延续性。小说的开篇写张小山,写他看到同学黄国辉因为拾金不昧被表扬,由此也想表现的微妙心理。写他在游泳时救起了林阿亚,由此成为了光荣的少先队员。塑造出一个聪明中带着狡黠,又追求上进的小男孩的形象。正是因为聪明,脑子活,让张小山成为幸福街上最先感到时代变革风向标的人。他敢于开风气之先,拿着借来的钱只身前往广州,带来了“单喇叭收录机”和邓丽君的磁带,组织小镇上的青年跳舞。后来因为跳舞他被抓进了拘留所,被厂里除名。他拿着朋友借他的钱开始创业,从广州进来的墨镜、打火机,磁带让张小山狠赚一笔。而后,他又在千年古镇上开了红玫瑰歌舞厅,短时间内积聚起了大量的钱财,感受到了金钱带来的成功和幸福。在眩目的光环中,他逐渐迷失了自己。后来,他的歌舞厅被烧,背负了巨额债务被关进监狱。出狱后,他开录像厅,放黄色影片;在农村开地下赌场,放六合彩;最后因为入室抢劫杀人,被正法。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地写出了张小山波澜起伏的人生。张小山这个人物形象,可以看作是作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像葵花》《弟弟你好》《生活无罪》等小说中人物序列的延伸,张小山与冯建军、弟弟、狗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十年文革造成了他们文化知识的空白,长期在底层生活的经验又使得他们对金钱有着强烈的热望,新时期的到来,他们在火树银花的改革开放中挖到了第一桶金,尝到了甜头。可是,知识的匮乏,法律意识的单薄,也让他们撞了南墙,吃了苦头。在失败的经历的刺激下,他们铤而走险。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何顿将被时代抛掷,苦苦挣扎的一代人得形象刻画得鲜明生动,极具代表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4]这就是说,人总是受着具体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制约,现实主义作家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总是将人物放置在复杂的、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去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复杂。何顿遵循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除了塑造出张小山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之外,还勾勒出了何勇、黄国辉、林阿亚、陈漫秋、杨琼、高晓华等人物的命运轨迹,他们的命运,既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也与他们的性格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聪明上进的林阿亚、陈漫秋、黄国进,虽然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他们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坚持学习,最后成为大学生。仗义真诚的何勇,虽然没能成为大学生,也因此与初恋情人失之交臂,但他能秉持初心,抓住机遇提升自己,最后也改变了人生境遇。而偏执僵化如高晓华,思维一直停留在“文革”时期,无法适应新的时代,也因此被时代抛弃。小说以大历史的变迁为经,以人物性格禀赋的发展的“小历史”为纬,共同谱写出人物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发展变迁的历史。幸福街的“小历史”与中国的大历史相互辉映,我们能够在他们平凡、琐碎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中感受“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代洪流。
二、以心灵、人性的描摹反映生活本相
《幸福街》表现的内容非常广博,繁花似锦的笔法将百年古镇的历史风云、古老街巷的世故人情和盘托出,在各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篇章中,作家如同话家常一般,将幸福街上的各色人物娓娓道来,既为每一位人物作传,又在交叉的叙事场景中展现他们丰富完整的社会生活与作为,在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中反映命运际遇、时代变迁;更将笔触深入内里,书写心灵、剖析人性。“以作家的善良的爱爱仇仇的人性感情,揭示了一个善恶对抗、美丑泯灭的现实世界,开掘了人物深邃的灵魂”[5],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的美学特征。在《幸福街》中,何顿忠实地描述了幸福街上各色人物的心灵史,既敏捷犀利的剖析人性之恶,又能客观公允的展示他们身上闪耀的人性之光。这种不带任何倾向性、不对人物做爱憎评价的客观书写,能够真实真切地反映出生活的本相。
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人格缺失,而这种人格缺失或者道德缺陷一旦遇到极端的历史境遇,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极大地被激发出来。小说中林阿亚的父母林志华与周兰,在50年代的运动中,因为他们家私藏枪支的事情被人举报,所以,林志华与周兰都被抓走,林志华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判了15年刑,周兰则被无罪释放。周兰是一个软弱的女子,失去了丈夫之后,她终日以泪洗面,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在严副主任的威逼利诱之下,她委身于严主任,以此获得短暂的安宁。后来,她在新的工作单位认识了彭校长,当她想与彭校长开始新生活时,嫉恨交加的严主任教唆林志华指认自己的妻子是特务,使周兰面临牢狱之灾。小说一方面描写了周兰的懦弱,正是她的软弱无助,让严副主任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也写了林志华心胸狭隘与善妒以及严副主任和刘大鼻子的卑劣恶毒。不管是唆使林志华的严主任,还是诬告自己妻子的林志华,都彰显出了人性的软弱和邪恶。陈兵的父亲,曾经是吕家的家丁,受过老东家不少的恩惠。然而,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当南下干部们收集东家的罪行时,管家高有祥诬陷东家指使他打死了大米厂好吃懒做的雇员黄豆角,他也落井下石,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使老东家含冤而死。小说真实的描写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人性之恶是如何获得了滋生的温床,最终酿成一出人间惨剧,给人的心灵蒙上了数十年无法抹去的阴影。
“每个人和每个时代都可以说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上面的、公开的、得到说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够清楚描述的表层,可以从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点并浓缩为规律;在此之下的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我们能潜入表层以下——这点小说家比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构成却是黏稠的物质:我们没有碰到石墙,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每一次前进的努力都夺去我们继续下去的愿望或能力。”[6]在上述文字中,赛亚·伯林认为,小说家比之于社会科学家,他们在表现历史时往往能够书写出历史情境中复杂的人性因素,从而使原本“骨感”的历史变得血肉丰满。在《幸福街》中,何顿忠实的描写了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之下的人性之恶,由此真实细致地表现出历史与生活残酷的本相。
然而,书写人性之恶绝非何顿的本意。在《幸福街》中,何顿将更大的篇幅,更多地笔墨投注在幸福街上平凡普通的人物身上,写出了生命应有的价值和高度。以人道主义的光辉,照进历史的深处并赋予历史应有的正义和尊严。何顿像一个辛勤的寻宝者,在历史洪流中浮沉的各式各样的小人物身上寻找人性的光辉,传递着普通人物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温暖。上文中提到的林志华,他的自私和卑劣让妻子周兰深陷囹圄,饱受折磨,让女儿林阿亚成为“孤儿”,这是一个让人可恨又可怜的人物。然而,当他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他不惜以死来表达自己的忏悔。张小山一夜暴富,财富的积累让他迷失了自我,在灯红酒绿中放任自己的欲望,致使曾经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伤心绝望。可是,当他得知自己曾经暗恋的女同学杨琼下岗,丈夫卧病在床之后,即使杨琼曾经伤害过他,他也不计前嫌,施以援手。陈漫秋的母亲赵春花,因为丈夫的历史问题饱受非议,一直在生活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后来,她在工作中结识了前任区长黄迎春,黄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她非常照顾,赵春花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小说真实的描写了黄迎春和赵春花之间“发乎情,止乎礼”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尤为珍贵。“人是有限的,有死的存在,然而,人又有渴望无限和永恒的一面;人有足够下贱和丑陋的一面,然而,人又有向往高尚和美的一面。”[7]何顿的《幸福街》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以往文学中对人片面、单一性的阐释,小说中没有一个笼罩着政治神性光环的人物,书写人性之恶,也是舒缓而克制的,人的尊严、正义、道德与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彰显。这种现实主义的笔触不但扩充了新世纪以来历史叙事的审美容量,而且也丰富了历史小说的人物形象谱系。
此外,何顿在《幸福街》中也写到了人类特殊的情感——爱情。作为一部以书写历史为主体的小说,《幸福街》中的爱情书写,既区别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爱情,爱情被淹没于狂热的革命政治话语之中而只能退守边缘;也不同于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爱情,或者阴暗而畸形,或者诗意而虚幻。何顿笔下的爱情,是充满烟火气的、是流动着的实实在在的日子中的爱情,这种爱情,充满了鸡零狗碎的平庸,但也有人间大义的担当。当我们在小说中读到何勇对林阿亚的感情,读到他对林阿亚的放手,我们在唏嘘长叹的同时也不禁会热泪盈眶。何顿以旁观者的态度,冷静而缄默的叙述着他笔下人物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他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投注在小说人物身上,以人物丰富、细腻的心灵的书写折射历史进程,以人性之光烛照生活的本相,由此彰显出现实主义书写可能抵达的深度和力度。
三、现实主义书写的叙述维度
何顿在评论家的眼中,是一位辨识度很高的作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生活无罪》《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等新写实小说独步文坛,他的小说“表现都市年轻人那亢奋、粗粝而不无鄙俗的生存搏斗,原生态的叙事与‘生活无罪’的价值逻辑,使得他的这些作品显出一种‘正而不足,邪而有余’的精神姿态”。[8]到了新世纪,何顿的写作路向发生了改变,在《幸福街》中,他“坚持了批评现实主义的精神,直面生活、直面现实、反思历史。”[9]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对社会现实与人生命运的关切思考、对人类进步与人性完善之价值追求的‘现实’精神,是与文学同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精神,是文学的生命基因之一。”[10]这种文学精神的来源,与作家在创作中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自觉无疑是对人类长期文学创作活动中最能有效地通往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方法途经的一种总结和概括。”[11]何顿在《幸福街》中追索历史、呈现历史,其所采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叙述维度:
其一,作家的叙述视点的“下沉”,对历史的发现和表达转向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呈现,由此形成了具有个性特色的日常生活叙事模式。作家将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上山下乡、文革、改革开放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件都囊括进小说之中,可是,历史在小说中退居于幕后,成为一种背景。小说的主体是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我们在小说中丝毫察觉不到“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剧烈历史变迁,反而是随着幸福街上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中逐步进入了历史,这主要得益于作家高超的细节描写的技巧。别林斯基要求现实主义应该“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12]何顿在幸福街中用绵密的细节钩织出一副湖湘市民日常生活的“清明上河图”,湖湘地区的历史文化、小城的四时风光,婚丧嫁娶、岁时节庆的习俗夹杂在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市民生活之中被他娓娓道来,在日常生活细节和历史事件的巧妙设计中,历史变迁中生活的原始面目和时光流逝中人生百态的真实表情都清晰可见,人物性格、命运与历史同构,生活之光叠影着历史之像,在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同构关联中一起抵达历史的本相,从而表达出作家重铸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情感与愿景。诚如评论家所言,何顿在《幸福街》中甘当“历史的书记”,小说“几乎在所有的细部上,都是经得住检验的。”[13]
其二,突破传统现实主义纯粹客观叙事的窠臼,在依据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基础上,驰骋主观想象,深入内部,深度描摹人物的心理现实,使作品具有广阔的现实空间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显示出作家自觉地文化批判意识和自省精神。虽然,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其非理性、荒诞性的存在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旨归,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文学就可以忽略对人的心理、精神世界的表现。恰恰相反,作家应该“从人物心理切人,描写现实社会在心理上的投影与心理对现实存在的反应,使社会现实与心理世界的丝连在艺术的聚焦镜下交辉凸现,你会听到那纷乱心音与骚动现实的交响,从而深刻地呈现出一种生存状态”。[14]《幸福街》中,何顿敏锐地捕捉人在现实环境中的感受和认知,细致入微地将这种感受叙述出来,由此体现出一种对心理现实的还原向度。诸如小说写周兰委身于严主任,当她听到严主任说女人真是个好东西之后,她微妙的反抗心理。但即使反感,她也没有办法以一己之力反抗。由此既反映出人物性格的懦弱,同时也表明那个极端专权荒谬的年代,漂亮女性的狭小的生存空间和境遇。再如写与何勇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后来成了何勇初恋情人的林阿亚,当她得知何勇与唐小月结婚,她的心理活动:“仿佛一件漫长的自己无法厘清的事情总算有了结果。……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原来人家是可以放下她的!”[15]此处寥寥数语,将林阿亚怅然若失之后如释重负的心理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出来。整部小说中,此类的心理活动、状态的描摹比比皆是,小说将时代变动中的幸福街的现实和街上各色人物的心理融合为一个整体,在对人的心理境况的摹写状绘中,裸呈历史与现实,勘察生命的本义和人性的本相,由此体现出一种还原的向度。
其三,客观写实与主观抒情有机结合,形成了风格鲜明的风景叙事。小说中的“幸福街”,不仅是人物活动的现实地理空间,也是作家寄托情感,安放乡愁的载体。这个名为黄家镇的百年古镇,与沈从文的凤凰古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秦岭山地一样,都成为一个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时空体。何顿在小说中工笔绘制出了一幅幅湖湘地区的风景图,疏影横斜的大树,光影交织的天空,或明或淡的日光与月光,桂花飘香的街道,浩浩汤汤的湘江水……何顿采用一种感性的、极具抒情意味的语言写景,色彩、形状、味道的组合,使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幸福街的立体面貌。而风景书写,往往与幸福街人事的变迁交织在一起,使小说的现实主义叙事充盈着主体意识从而带有了一种诗性特质。
雨果认为,“天才所能攀登的最高峰就是同时到达伟大和真实”[16],对于《幸福街》而言,何顿不仅准确、客观地写出了历史中的人和事,烛照人性的光辉与黑暗,而且,理性之思与感性之语的交织,使《幸福街》成为一部抵达真实,接近伟大的现实主义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