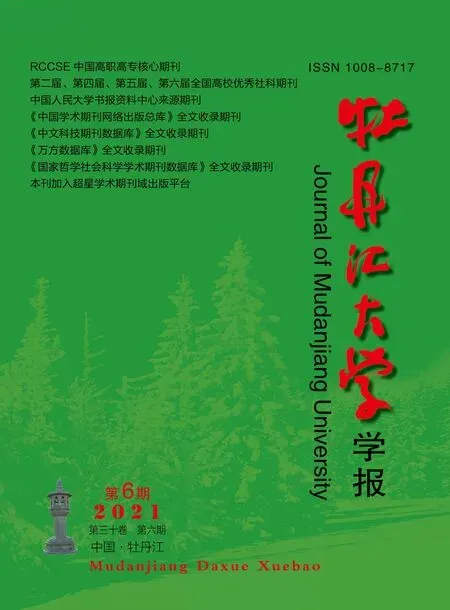当代青年的救赎与沦丧
——论《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对象主体的互动
曲美潼
(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136)
在近年来出现的文学作品中,当代青年的形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刻画当下青年群像似乎成为作家们必须肩负起的使命。2014年,石一枫发表了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随后,这部作品在图书出版界和评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品中对象主体之间的互动揭示了当下身处不同阶级青年的生存状况。其中,“对象主体”这一提法,出自刘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主要指作家在文本中创设出的人物形象。重视对文本中人物形象的解读,高扬人物的精神主体性,成为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的重要依据。《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对象主体包括故事的叙述者“我”和被讲述者,同时也是故事主人公的陈金芳,故事以两个人在生活中的交叉互动展开,讲述了“我”与陈金芳在不同时空下经历的不同人生轨迹以及在彼此生命中展开的错位交集;“我们”俩在共同经历了救赎与沦丧后,最终都走向了幻灭和失败。通过对两个人生活经历的解读,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看出当下青年存在的某些共同的精神症候。
一、叙述对象在北京城中展开的时空互动和成长
作品中的主要叙述者“我”生长于北京铁道兵部队大院,少年时期就读于部队子弟学校,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一技之长,从幼时便开始练习小提琴;陈金芳则是来自湖南农村,因为姐夫在部队食堂做饭,才得以来到北京的学校借读,偶然和“我”成为了同学。在少年的“我”和“我”身边的同伴看来,陈金芳家里条件一般,学习成绩一般,个人品味一般,但又及其“爱慕虚荣”,因此在学校里备受老师和同学排挤。这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人却因为同住一个大院开始产生了某些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从叙述的空间上看,故事以北京城作为基础进行空间的流转。“我们”年少时的经历主要发生在北京部队大院和部队子弟学校,成年后的交集则主要发生在北京上流社会的“艺术圈”。作者石一枫在《我眼中的“大院文化”》中谈到,北京大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本身就是属于青春的文化:作品描述的知识记忆中的青春,而深受它感染的人,即使臭名昭著或功成名就,却依然力图保存青春般的单纯、尊严和浪漫的个人英雄主义气息。”[1]42作品中身处于部队大院中的叙述者“我”是大院中的固定生活成员,拥有北京户口,享有院中“主人”的地位,和其他北京孩子一样,是城中的“坐地虎”;被叙述者陈金芳则是大院中的外来户,也是学校中的边缘人,“他们随家人进京,初来乍到时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好不容易熟悉了环境,却往往又要离开。”[2]42对于陈金芳这样的外来人口,“我们”也讲究交朋友的“成本”,深知她们不会在北京久留,也就没有必要深交,因此都选择对她“视而不见”。但陈金芳搬来大院后不久,“我”有一次在练习小提琴时,在窗外的树下看到了她的身影,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她经常出现在树下听“我”演奏,“我们”就这样形成了一种隐秘的演奏者与听众之间的关系,“小提琴”成为了文本中联系两个对象主体关系的意象;“我”与陈金芳的再次相遇,也是因为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的演出。此时叙述的主要地点已经发生了转换,从部队大院和子弟学校转向了更广阔的空间——所谓的上流社会“艺术圈子”。此时的陈金芳摇身一变,成为上流社会圈子的中心和焦点,叙述者“我”反倒成为了社会上的边缘人,游离于主流之外,游戏人生。叙述者与陈金芳因为艺术再一次发生联系:“我”为陈金芳在绘画评论界牵线搭桥,为她引荐B哥做艺术投资的投机生意;最后因为陈金芳试图挥金拯救“我”,帮“我”重拾小提琴梦,两人闹掰。从部队大院到上流社会的“艺术圈子”,叙述者“我”经历了从城中“坐地虎”到社会边缘人的转换,其中蕴含了当代青年人理想主义的幻灭和生活激情的退却;文本主角陈金芳虽然无学识,无背景,却经历了由大院“边缘人”到上流社会主流人的逆袭,体现出了当下主流价值观的偏颇。
回顾现当代文学中的创作,有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是围绕着北京城展开叙述,老舍和王朔都曾经是北京的书写者和代言者——老舍的小说着眼于北京的现实和底层生活,聚焦时代和社会的问题典型,《骆驼祥子》展现了城乡文化的差异对于社会中的小个体的影响,《离婚》则揭示了民族的劣根性,他用“京味”的语言和表达刻画了北京的民俗和人物。王朔作品中的北京更具现代特征,是市场化席卷下的新型都市,他更多描写的是现代化席卷下的北京新兴地界和在城中放浪形骸的青年,比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多次提到的“燕京大饭店”和《动物凶猛》中在东城、西城“泡妞、打群架”的大院共同体。北京也是石一枫创作中的一个空间和地标,他的大部分创作都以北京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红旗下的果儿》刻画了一群生长在北京城中“80后”青年的青春、爱情与成长,《恋恋北京》以北京的地点作为不同章节的标题,讲述“北京之恋”,《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了外乡青年在北京的奋斗经历,《特别能战斗》记录了一位北京大妈奋斗的生活闹剧。石一枫曾经表示过,自己对于“北京”的写作,不想继承民俗,只想继承现实;他对北京的刻画继承了老舍的现实主义倾向,又发展了王朔的现代性笔法。
从叙述的时间上看,故事以“我”和陈金芳从少年到青年成长道路上的相互交织展开。从少年到成年,叙述者“我”从最初的追求艺术的理想主义者,经历了考取中央音乐学院失败,被主考教授判定为“技巧有余而缺乏灵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演奏家,最后放弃了音乐,甘于平庸,以颓丧的态度面对生活。与此同时,故事也完成了对主角陈金芳作为外乡人的经历的打造:少年的陈金芳之于北京这座现代化大都市,是一个外乡人,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她渴望留在北京,渴望“扎根”城市,获得城市人的身份和城中人的认同,因此,即使乡下的父亲去世,全家人决定返回乡下,她也誓死抵抗,决心留在北京,发出最响亮的呼喊:“你们把领到北京,为什么又让我走?”[2]46为了留在北京,陈金芳不惜一切代价,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是身体,到了成年以后,终于跻身于所谓的“圈子”,获得了艺术界的重视,成为了圈内的红人,然而由于艺术投资的失败,最终还是落得惨淡的众叛亲离的下场,尚未“扎根”,却已被“拔根”。
纵观文本对象之间的交互关系,可以看出,从少年到青年时期,叙述者在陈金芳的故事中,扮演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最后回归旁观者的角色:少年时期,“我”冷眼旁观着其他同学对她所谓排斥和欺侮,没有因为她是“我”的“听众”而站出来为她出头;青年时期的再次相遇,“我”恰好离婚,她重新进入“我”的生活,“我”意识对她的莫名情愫,成为她这一时期生活的参与者,到最后二人关系破裂,她重新归于沉寂,“我”再次回归旁观者的身份:眼看她起高楼、宴宾客再到楼坍塌。陈金芳对于故事的叙述者“我”来说,扮演了从陌路人,到恍如初恋的倾诉者,再到生活的参与者,最后回归陌路人的角色:陈金芳本是一个来自湖南的外乡人,对于生在北京大院的叙述者来说,是完全的陌路人,但是由于对“我”的“演奏”的参与,她成为了“我”音乐上的倾诉对象,也使得我的表演多了些“人情味”;在重逢后,她对“我”的评价也让“我”惊异于她对我的认知和了解,成年后的她也成为了“我”生活中的参与者,但在她试图用金钱重造“我”旧日的理想后,终于意识到了“我”内心对她的无法解除的隔膜,在她浮华落尽后,此二人重归陌路。文本中的对象主体在相互交流中,曾经奇迹般地达成了某种奇异的默契,形成了共振和交流,但最后由于身份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还是走向了破裂。两个对象主体从时间到空间上的互动,揭示了二者在文本中的成长轨迹:陈金芳的一路畸形“成长”与“我”的拒绝“成长”,选择颓丧,都是当下青年变态发育的写照。
二、从救赎到沦丧——对象主体在行文逻辑上的交互和角色形象的最终确立
上文从作品的时空呈现角度分析了对象主体之间展开的交流与互动,展示了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角色在文本中成长的过程。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提出:“作为文学对象的人,相对于作家来说,它是被描绘的客体,但是相对于它的生活环境(社会)来说,它又是主体——它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的环境和他的生活是被他所感知的对象。”[3]15从石一枫创作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来看,叙述者“我”和主角陈金芳都是文本中有意识的主体,在文本中有各自的发展线索和逻辑,作家在行文中主要设置了“救赎”和“沦丧”两个环节,并以救赎和沦丧为线索,使得文本中的两个对象展开逻辑上的互动,完成角色的成长和最终确立,形成了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
文本中第一个逻辑互动环节的关键词是“救赎”。作品情节设置巧妙,叙述者“我”与陈金芳在成长的道路上交集虽然不多,但是文章刻意着墨于“我们”之间屈指可数的几次见面,讲述了“我们”通过对对方的解救,完成了相互的救赎,看似偶然,实则是文本刻意安排的必然。其中,第一次是陈金芳对“我”的解救:文本中时间发生在高一结束的时候,“我”在参加少年音乐联展的归途中不小心踢倒了小卖部的两个酒瓶,被“豁子”为首的一帮混混盯上,正当危机时刻,陈金芳的出现解救了窘境中即将挨打的“我”;第二次救赎的初始,是“我”对陈金芳的解救:时间流转至高中毕业,“我”在艺考中被淘汰,理想破碎,陷入无边的失败主义情绪,骑车在马路上闲逛时,恰巧看到马路对面“豁子”正对着陈金芳拳打脚踢,正值失意中的“我”在激动情绪的裹挟之下冲入人群与“豁子”对抗,为陈金芳抵挡住了部分伤害;但是在对抗结束后,陈金芳反而张开双臂将“我”拥入怀中,安慰了正处于无边失意中的“我”。在“我”与陈金芳的几次接触中,“我们”的人生轨迹虽然截然不同,但是却彼此交叉,呈现出一定程度上情绪的共情和融合。高一时的“我”向自己的梦想一路挺进,此时的陈金芳也通过各种方式在北京立足,对生活充满了“死心塌地的热情”;高中结束的“我”丧失了音乐的梦想,沦为失意的庸人,陈金芳与生活上的“靠山”分道扬镳,生活一片黯淡。作者选取了这两个时间点,勾勒出两个青年命运的奇迹般的重合,以及两个主体之间的相互救赎,使得人物角色在文本中实现了发展和成长。
文本中第二个逻辑互动环节的关键词是“沦丧”。在石一枫的创作逻辑上,成年之后的“我们”经历了身份和社会地位上的互换——“我”在经历了理想的陨灭后,逐渐沦为平庸生活的分母,践行“混子理论”,过上了吃软饭、寄生虫、不思进取的生活,呈现出一派颓废之气,也因此遭到了上进的妻子的抛弃;陈金芳用尽自己的力量拼命跻身上流社会,不断介入不同的艺术圈子,用名贵的奢侈品和上流人的样态包装自己,并试图通过投机生意来获取更多金钱和地位。结局是,“我”沦丧为犬儒主义的牺牲品,陈金芳在一次投机活动中千金散尽,重新沦为社会底层。成年以后,“我们”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多,“我”将她介绍给更多艺术人士,她则为“我”排解了生活的无聊和寂寞,虽然曾经相互取暖,最后也都并非善终,但“我们”本质上却并不类同。叙述者“我”是看穿了生活的众生本质,自主选择了做生活的逃兵,避开与他人发生实质性的利益关系,身轻如燕,落得内心的空虚寂寞;陈金芳是看不穿生活的残酷真相,试图凭借一腔孤勇和投机行为改变自身的境遇,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石一枫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塑造了这两个性格十分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让他笔下的人物在完成篇章建构中的同时也完成了角色形象的最终确立。
刘再复曾经提出作家与自己笔下人物的“二律背反”定律,认为作家在创作中越是积极主动,他在自己塑造的人物面前就越是被动。石一枫在谈及自身创作动机时,也提到自己心目中好小说的标准:“一,能不能把人物写好?二,能不能对时代发言?”[4]120他对自己笔下人物的基本定位是,用个人的命运来反映时代潮流中的众生之相,至于人物自身性格及命运的发展,则顺应自然,合乎逻辑即可。这便是作家在文本中对对象主体的极大尊重。从文本对象的角度出发,刘再复认为,导致对象主体失落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用“环境决定论”来支配人物性格、用抽象的阶级性来取代人物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用单纯的外在冲突来取代人物灵魂的塑造。石一枫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巧妙地避免了人物性格的空洞化和单一性,讲述了两个青年成长中的故事,通过时空的不断转换以及对象主体之间展开的“救赎”和“沦丧”构建出行文的逻辑,使得看似无交集的二人由此展开了文本中生命的交汇;虽然两个人物隶属于不同的阶级,但是阶级性并不是决定二人命运的唯一因素。此外,从文本意蕴来分析,作品中两位在城市中挣扎的青年代表了千万个身处城市的青年形象,二人的命运发展轨迹也揭示了文本背后作者想要表现的当代青年共同面临的时代压力和精神困境。
三、对象主体背后的意蕴:勾勒底层失败青年群像
孟繁华曾表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是一种失去了青春的文学,当下的文学尚未创造出能够代表新时代意志的青年形象。青年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支撑和力量,青年形象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朝气和未来。当代中国青年形象塑造的问题,是当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甚至是新时代文学中亟需加以重视的问题。
《世间已无陈金芳》通过文本对象之间的互动和角色的确立勾勒出叙述者“我”和陈金芳的城市青年形象。评论家李云雷认为,石一枫通过他的小说揭示了当代青年失败的命运,也向我们揭示了全球化时代资本运行的奥秘,他以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方法深入到时代的核心,也以“失败的青年”形象让我们反思当代世界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5]《世间已无陈金芳》的叙述背景是北京,故事围绕北京城中两个少年的成长展开:一个是处于城市边缘的“顽主”,一个是居于城市底层的外乡人,代表了城中不同类型的失败者;两个人身处同一地界,却身属不同的阶级,石一枫试图通过对二人不同经历的描述来展示当下底层失败青年的群体特征和差异性,从而触探到当下青年存在的某些共同精神症候。
故事的主人公陈金芳是当代底层外来青年的代表,她们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学历,被城市生活深深吸引,渴望扎根于城市,获得城市的身份和城中人的认同。陈金芳为了摆脱原生家庭、驻留于城市使出了浑身解数,不惜寄人篱下、出卖肉体,甚至忍受拳打脚踢、倾尽全部财力只为买一架钢琴,成年后的陈金芳拼命向上挣扎,摹仿“欧范儿”、用名牌包装自己、忙碌于“艺术圈”,甚至连名字也改成了陈予倩。表面上看,是她对名利和金钱的追逐,实际上她是内心渴望真正地融入城市;陈金芳渴望摆脱原生阶级的束缚,结果却是越反抗越焦虑,越反抗越绝望,最后落得飞蛾扑火的结局。
故事的叙述者“我”是游离于城市之中的边缘人的代表,这一类人出生于城市,生长于国旗之下,有着一定的家庭背景:“我”在军区部队大院长大,就读于部队子弟学校,具有从小家中便供“我”学习小提琴的资本和实力,周围的同学们也和“我”家的条件近似。年少时的“我们”便有了高人一等的意识,很少与外来借读的学生打成一片;对于陈金芳的爱慕虚荣,孩子们共同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态度,“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2]45“我们”这类人青年,在经历过轰轰烈烈的青春追梦后,逐渐看到了理想主义尽头的空虚无妄,在告别理想后展现出对生活的颓丧,无论是面对爱情和生活,都提不起拼搏的勇气。正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他们游戏人生、放浪形骸,沦为城市中的边缘人,对一切抱有无所畏、破罐子破摔的态度。
文本中“我”和陈金芳的人生失意并非是偶然的个例,而是当下底层城市青年的真实写照,他们个人命运的背后,昭示的其实是我们当下时代出现的新问题:首先是阶级原来越固化,不同阶级之间难以流动——上层用资本积累财富,用财富积累学识,用学识提升自我,从而跨向更高的层级,底层青年若是没有财富和知识的加持,仅仅通过个人盲目的实践和奋斗是很难改变出身的。其次是城市青年成长中呈现出共同的精神力量的缺失,这也是当下时代展现出的人类精神困境。
城市中的青年在迈向社会后,可能出现两种样态:一种是有理想主义的加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另一种则是理想破灭,以边缘的姿态游离于生活之外。作品中“我”代表的一类人,虽然选择以“顽主”的态度消极对抗人生,但是毕竟混迹于中产层级,有着名牌学校学历的加持,也有文学评论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有“混艺术”的朋友可以聊以慰藉,有B哥这样有钱有势的知心好友,也有父母的实力作为经济的支撑,生活不至于跌落谷底,更不要说去面对生活中真正的残忍和不堪;此外,“我”还拥有家庭和高等教育留下的基本素质,在精神方面有着自己的底线和坚守,同样是混迹于“圈子”,但却不汲汲于名利韶华,不做投机苟且之事,虽然沦为城市中的边缘人,但是始终是清醒的,“我”从骨子里认为自己与陈金芳不属于同一个阶级,也从未以平视的眼光给予她想要的认同感。城市中底层的外乡人在走向社会后,也可能呈现出两种走向:一种是对自身有清醒的认知,通过知识改变自身命运,超越自身的阶级,另一种是盲目流连于城市,渴望一蹴而就获得成功,最后少有善终。前者在当下社会之中,并非没有实例,但是拥有这样坚韧意志和能量的青年毕竟只占少数,更多的人与陈金芳一样,属于后者,本就出身底层,没有良好家庭环境的熏陶,对自我的认知和定位并不明确。偶然的机会使得他们离开农村,见识了城市的繁华,于是便渴望在城市中立足,取得与城市人相同的地位,但是他们却没有用知识为自己打下基础,只是在原有认知的基础上幻想着改变命运,他们没有原生家庭做靠山,也没有大把的财富给予他们作为实践和交往的资本,因此就不得不采用不正当的途径和方式畸形地向上生长,上流社会人们的投资和把戏对于他们来说则是倾尽一切、孤注一掷,一旦投机失败,他们就会一无所有,跌落至谷底,没有家庭朋友的支持,彻底丧失触底反弹的可能。阶级的凝固化是导致二人最后结局的重要推动力量。
此外,石一枫在这部作品中还关注了城市青年成长道路上的精神缺失,并从中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中暴露出的青年形象问题。近年来,描写城市和城市青年形象的小说不在少数,但是作品中更多展示的是当下青年面临的精神困境。从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书写的底层青年失败奋斗史,到文珍的小说集《十一味爱》青年的都市爱情故事,再到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对城市中青年互动的关注,这些作品更多关注了当代青年个人命运的失败;他们用当下社会单一的“成功学”标准要求自己,认为财富和地位是成功的唯一衡量标准。
同样是新时代青年,涂自强和陈金芳们与曾经的梁生宝、孙少平们相比,缺少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与昂扬的精神斗志。这也正是底层城市青年们展示出的时代症候:没有“新人”偶像作为精神上的指引,同时缺少理想主义的支撑和带动。
石一枫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对青年形象的塑造既承袭了已有作品中的某些青年特点也有其独特之处。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作家们对于青年形象的刻画,主要可以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以谢慧敏为代表的“伤痕式青年”,《班主任》中的谢慧敏曾经受到了错误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和行为都十分僵化,这一类青年代表了“无意识”的蒙昧和封建;二是以孙少平为代表的“奋斗式青年”,《平凡的世界》中,以孙少平为首的青年们无论是出身寒门或是高贵,都积极并且乐观,保持着纯洁的内心,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身的命运;三是以王朔笔下的“青年顽主”形象,这一类青年生于国旗下,长于物欲之中,他们的青春见证了国家经济和资本的崛起,面对周围环境的巨大变化,他们逐渐从新奇转变为无所适从,面对理想的消亡,他们选择游戏人生,对一切抱有无所畏的态度;四是80后作家们(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笔下的“新式青年”形象,作家们与他们笔下的青年在年龄上几乎同步,他们的青春是彼此重合的,都充满了孤独和伤感。石一枫对于对象主体的塑造则有着自己独特的考量: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叙述者“我”的形象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王朔“顽主”形象的延展,陈金芳的形象则是路遥笔下的“孙少平”的畸形变异;“我”继承了“顽主”的生活态度并在新时代有所发展——“我”是新的时代环境下的“顽主”,面对的不再是时代发展的初始阶段,而是财富和资本无限膨胀、时代和科技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面对更纷繁的社会环境,“我”有过顽劣,也有过沦丧,但是始终有着自身的坚守和底线;陈金芳形象的塑造则超越了已有的几类青年形象,开辟并代表了新时代逐渐形成的一类新的青年形象——渴望摆脱原生环境,跨越阶级跻身上层,幻想越过个人奋斗的步骤,通过投机的方式直接取得财富和地位。石一枫对文本中这两个人物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能力和野心,也看到了他在文本创作中的无限潜能。
四、结语
石一枫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通过两位对象主体之间的交互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底层青年彼此缠绕的成长经历,通过时空上的交错以及两个青年之间展开的救赎与沦丧完成了文本角色的塑造,并通过文本中的青年形象揭示出当下时代共同的精神症候以及青年们的精神缺失。王国维曾经说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同样,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青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感悟,针对每一时代青年们面对的具体精神困境,我们应该从具体的时代角度出发来理解。石一枫在谈及自己的文学创作态度时曾经提出,作家贯穿在写作中的对时代的总体认识,应该是一种“文学的总结”,而不是“社会学的总结”或者“经济学的总结”,这种总结是灵活多变的,千人千面的,而非单一地用某种理论对社会进行图解分析。[4]119青年形象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根基和支柱,塑造新时代的青年形象是迫切的时代话题,也是当代文学创作赋予作家的新的时代使命。新时代的文学创作者们,应该重视起自身肩负的责任,充分发挥文学的主体性意识,提出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创作出新时代需要的文学新形象,将人物的命运纳入时代发展的大潮之中,致力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文本中做出新的展望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