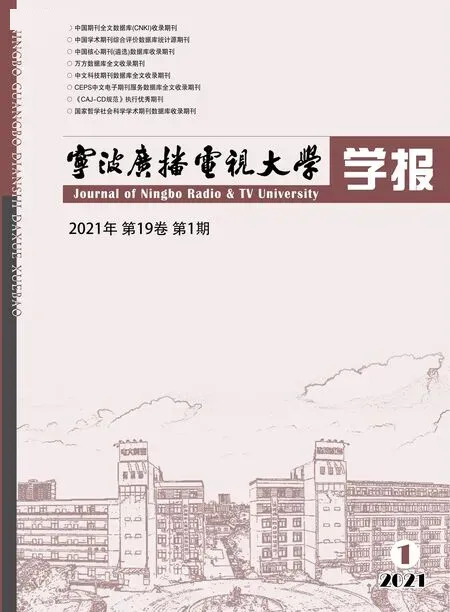张岱《快园道古》中的遗民情怀
李宇豪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明清易代之际,涌现了一大批为明朝守节的遗民,张岱就是这些遗民中的一员。张岱一名维城,“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1],号陶庵、蝶庵、古剑陶庵、古剑老人等,晚年又自号六休居士。张岱出生于通世显宦之家,是张远猷的直系后裔,又是状元张元汴的曾孙张耀芳的长子。公元1644 年甲申之乱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明朝的命运,同样也改变了张岱的命运,南明接连建立起来的政权,皆如风中残烛般转瞬即灭,张岱曾一度投身其中,但很快便大失所望地离开,从此隐遁江湖,立志以史存明。正如张岱自言:“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駭为野人。……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间。”[2]《快园道古》正是成书于张岱隐居编写其史学著作《石匮书》时期,据其小序“岁乙未九月哉生明日,陶庵老人书于龙山之渴旦庐”[3]8,可以推定《快园道古》成书于清顺治十二年即公元1655 年,此时距离甲申之变已经过去了十一年,而张岱也已即将步入耳顺之年。《快园道古》正是在张岱经历国破之变十年后追忆过去而编撰的作品。
笔记兴之所至便信手记录,篇幅短小又杂取种种生活所见所闻所感记录成册,相对古人所作的诗词等抒发性情的文学创作,笔记则大多以记叙为主,少有直接吟咏内心,抒发个人志趣情操。但这些并不意味着笔记只是单纯的短篇文章的堆砌,这些纷繁的故事,是作者生活和思想的剪影。这些故事的选取、排列和组合,如同待解开的密码一样,背后隐藏着作者在创作笔记时流露出来的内心想法。《快园道古》是张岱晚年创作的带有回忆录性质的笔记作品,它创作的初衷是“余盖欲于诙谐谑笑之中窃取其庄言法语之意,而使后生小子听之忘倦。故饴一也,伯夷见之谓可以养老,盗跖见之谓可以沃户枢。二三子听余言而能善用之,则黄叶止啼,未必非小儿之良药”[3]8。由此可知,张岱创作该笔记带有很强的教育目的,正如小序中提到的那样:“若余所道者,非坚人之志节则不道,非长人之学问则不道,非发人聪明则不道,非益人之神智则不道,非动人之鉴戒则不道,非广人之识则不道。”[3]7在这些张岱想要传递给后人的点滴笔记中,可以从单则笔记的内容乃至于全篇笔记的编排中挖掘出张岱想要传达给子孙的遗民情怀。
一、对于故国的无限追思
笔记名为《快园道古》,“道古”二字点出了该书讲述的是过去发生的故事。翻开《快园道古》,张岱并没有将时间轴向前推移到足够称之为“古”的先秦两汉,就连唐宋两朝也鲜有涉及,他恰恰把时间选择在了明代,这个对于他来说相去不过十一年历史的时间点。将相去不过数十年的历史称作“古”,这似乎有点夸大其词,况且南明朝廷依旧宣扬着明朝政权的存续。佘德余在《快园道古》的整理弁言中却提出“名为‘道古’,实为谈今”[3]3。“今”与“古”鲜明地将过去和现在分割开来,那些只能追忆的过去变成了无法挽回的历史。在张岱的心目中明王朝已经成为了故国,“道古”便是在回忆前朝发生的种种。这种对于前朝的追忆之情,成为《快园道古》编撰的暗线。
《快园道古》的门类总共有20 个,光是盛言明代风物就有“盛德”“学问”“经济”“言语”“夙慧”“机变”“志节”“识见”“小慧”“任诞”10 个门类,带有批评色彩的门类也只有“纰漏”和“诡谲”。从门类的角度分析,明显正面描写明朝旧事的门类占据了一半。张岱带着对于往昔美好的浓浓追忆,而将这些记忆一一罗列。
统观全书,张岱以一种诙谐谑笑的笔触描绘着明代的众生相。这些故事大多以明代历史中积极正面的人物作为记录的重点,突出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又或是过人的聪明才智,彰显了明代的“正能量”。在《快园道古》中,张岱还记录下自己、亲属、先世和朋友的言行故事。在记录这些笔记的过程中,作者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对于过去生活的怀念和如今沧海桑田的感慨。张岱在笔记中记录了许多自己周遭生活的点滴,包括自己幼时被称为神童,赈灾越中甚至六婶娘与钱相公家争房等事。这些对于生活点滴的记录,是张岱对于自己人生的回顾,其中不难看出张岱对于过去的不舍。曾经优渥的生活与现在贫困潦倒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张岱在念念不忘之余更有命运巨变的感慨。如夙慧部中提到张岱八岁与陈眉公对对子的故事:“陶庵年八岁,大父携之至西湖。眉公客于钱塘,出入跨一角鹿。一日,向大父曰:‘文孙善属对,吾面考之。’指纸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陶庵对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赞赏,摩予顶曰:‘那得灵敏至此,吾小友也。’”[3]81这则故事同样见于张岱《自为墓志铭》一文,在《自为墓志铭》中张岱对于这件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哉?”[4]在《快园道古》中,幼年神童的故事与其他张岱早慧的事迹一同罗列于“夙慧”这一门类,少年的春风得意自然不必说,但将《快园道古》与《自为墓志铭》互相参看,这其中是张岱在国破背景下个人命运的变化的错愕和遗憾。以张岱家族的显赫,若明朝没有发生甲申之变,也许张岱仍然可以延续张氏的荣耀,即便他科举不仕,他也能够风花雪月悠游一生。但这一切在甲申之乱划上了句号,无数个类似张岱这样的官宦家庭土崩瓦解。荣华富贵转眼成空,怀念故国亦同样是怀念过去的生活,个人的命运与故国的命运高度重合,沧海桑田的感慨包含着对于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唏嘘,让遗民们在各种作品中都流露出浓浓的黍离之悲。
二、志节部中的节义观念
《快园道古》虽然没有明言模仿《世说新语》,但从编撰形式来看,《快园道古》无疑继承了“世说体”的写作方式。在对比《快园道古》与《世说新语》的门类,其中既有相同的门类亦有不同的门类,不同门类的设置反映出作者分类上新的需要。志节部作为《快园道古》中相对于《世说新语》中的新增门类,其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在同时代的其他“世说体”的创作中,也有着类似的门类,如《女世说》中的“节义”、《玉光剑气集》中的“忠节”和《南吴旧话录》中的“忠义”,对于气节的重视似乎是当时笔记创作的一种流行倾向。雷雅淳在《明清之际世说体对〈世说新语〉的继承与转换》一文中提到:“尤其可注意的,是忠、介、节等字眼,均散见于几部世说体中,可见这些不被《世说新语》用以命名门类的人物特质,在明清之际被这些作者有意识地关注、强调。这反映了笔记作者的理想价值观,因此想尽力让这些人物名垂青史。”[5]如果将张岱明朝遗民的身份与《快园道古》中志节部相重合,便不难理解为何张岱要设置这样一个新的门类,这是一位明代遗民气节观念的展示,同样也是垂训后代的气节教科书。
(一)坚定不移的遗民立场
在《快园道古》志节部中记录着这样的一批人,他们要么远在江湖又或是身在庙堂,但他们却不曾向权势低头,尽显不卑不亢的真我本色。身处官场的笔记有文衡山乞归一条、李崆峒拒跪一条、商为正和庞当鹏共治福建。分别讲述了文衡山请辞决心强烈终于如愿所偿;俞中丞监督平寇,沿用两广惯例,要求司长们下跪,李崆峒以“吾奉天子诏督诸生”为由拒绝下跪;福建人感恩商为正、庞当鹏体恤民情的三则故事。这三则笔记展示了官员不为名利所动的政治操守,不畏强权的铮铮傲骨和勤政爱民的政治素养。而记录远在江湖的人物事迹分别为颜木避匿高官故人求见;刘青田笑徐舫就聘金陵;岳正题小像曰“如感赦汝,再敢不敢”;文衡山致仕归,杜门不见贵戚;王谷详拒出仕。这些都刻画了官员远离官场后洁身自好或主动疏远政治的事迹。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张岱自身对于这些官员在官场内外能够保持本分的欣赏。他们身居官场则有底线讲操守办实事,官场之外则与政治保持距离,不与在朝官员交往以保持自己的清廉节操。两种人物的记录透露出张岱对于一个优秀官员的标准,同时这些记载与张岱的遗民身份也产生了一定联系,前者给予他精神上的激励,后者则是隐居的榜样。“遗民”一词最突出的意义便在于“在易代之后因坚持对故国的忠诚而拒绝与新朝合作者”[6]9。张岱本人虽然并没能科举入仕,但是他也曾进入鲁王朝廷做过官。即便单单论及张岱家族的社会影响,张岱同样拥有着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自他遁入江湖,做了明朝遗民,便面临着如何保持遗民气节的问题。在志节部中记叙他人的故事同样可以视做张岱的自白。这些人在政治上选择了以疏远政治、抗拒权贵的方式,来实现洁身自好的目的。而张岱以这些人为榜样,在笔记中加以彰显的同时,也同时从这些人身上汲取道德力量。尽管《快园道古》中的这些人物与张岱本人的遗民身份有着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都在展示着一种坚定的立场并为之保卫的决心。张岱诗中有:“尔或不争气,予原不动心。故园松菊在,对此一开襟。”[7]96这首诗为落第归来的儿子所做,是张岱不慕荣华富贵,坚持遗民立场不肯动摇的真实自白,而在他隐居的那段岁月中,张岱亦实践着这样的信条。
(二)安贫乐道的人生志趣
《快园道古》志节部中还涉及到了关于金钱与气节的事迹,包括番人重贽求观清閟阁、唐六如晚年言志诗、文征明拒金和文衡山拒周王、徽王重金求见。番人重贽求观清閟阁体现了倪云林不为金钱所动,不肯番人观清閟阁的清高傲骨,唐六如晚年言志诗抒发了唐六如轻狂逍遥的人生态度,文征明和文衡山的故事则都旨在突出他们拒绝接受金钱施舍而安贫乐道、不为金钱所累的道德操守。总体来说,这些人共同体现了安贫乐道的人生志趣,不为金钱而屈服现实。明代遗民时常需要面临金钱问题,这些遗民往往隐居山林,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官员俸禄,又不善于稼穑,往往生活拮据。张岱自隐居之后,家财多为方安国所占据,一贫如洗,快园也被他人所占,张岱一家借住于此,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快园道古》中没有直接描写张岱生活贫困的笔记,只是在隐佚部中略有提到:“粗羹淡饭饱则休,破衲鹑衣暖则休,颓园败屋安则休……”[3]147张岱在笔记中几乎不谈自己的艰苦生活,但他却在诗中大量记录自己贫困的生活:“饿亦寻常事,尤于是日奇”[7]95又或是“日久粪自香,为农复何恨?”[7]44诗文中的抒情传统令作者往往自然而然地抒发内心的感情,而笔记并非如此,它的内容往往是取材于他人,它表露感情亦是通过他人的故事曲折地表露出来。张岱诗中描写贫穷生活之时表露出来的情绪和张岱在《快园道古》志节部中记录唐六如、文征明等人展现的精神气节是一致的,同样是轻物质、重精神的人生追求,不为金钱权力所动,为了内心的坚持而选择安于贫困生活的高尚情操。
(三)近乎洁癖的道德追求
《快园道古》志节部中倪云林的事迹反复出现,包括倪云林游太湖时遭张仕信鞭辱却一言不发;倪云林爱好干净每天盥洗的时候要换多次水,换衣服的时候要多次振拂,甚至斋阁前的树石也要经常擦拭;倪云林不见俗士以及客人咳痰于其庭前树下,倪云林索痰不得竟然将树全部砍去,这些事例都展示了一个有着高度洁癖的奇人形象。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认为:“人无癖不可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2]57张岱与其说是欣赏这种高度洁癖之人,不如说是对他身上折射出来的“深情”的赞叹。病态的人物形象强化了其行为的象征意味,洁癖的行为代表着一种极高的道德水准,它不容许一丝玷污。张岱笔下记录这样的人并不是兴之所至的偶然,它是张岱的心结,同样也是明代遗民中共同的心结。正如李瑄先生在《明代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中指出:“追求道德完美为明代遗民群体共有的倾向。”[6]339遗民们面对的是死殉者树立起来的极高的道德标准,而为了达到这个道德标准,生殉者就必须守住自己的节操。在实现这种目标的过程中,遗民有以极端的方式达到目的的做法,如“不下楼”“不出门”以及“水居”。这些事例与倪云林事迹中的病态如出一辙,展现了明遗民对于道德近乎苛求的执着。张岱在诗中也表露出这样的志向:“世事今如此,微臣敢不贫?”[7]135其中颇有以自苦的方式成全忠于明朝的心态,同样也是无瑕道德品质的体现。
三、隐逸部中的隐士观念
(一)不名之隐
在《快园道古》隐逸部的按语中,张岱探讨了如何成为一个隐士的问题。他认为许由、巢父这样的人算不上隐士,因为他们“身既隐矣,焉用名之”[3]142。而真正的隐士就应当像王君公那样“日日相见,而孰测其为兼山之遁乎”[3]142?张岱因此还划分了两种隐士:“小隐在山林,大隐在城市”[3]142,有小智慧的人避入山林来保全自己,而有大智慧的人则即便在城市中也能不令人发现自己的遗民身份。在笔记中张岱记录了龙潭老人批评吴康斋泄露自己隐居踪迹的故事,对按语进行了呼应,从按语和笔记记载的呼应中,可以看出张岱作为明朝遗民隐居的态度——崇尚不名之隐。践行不名之隐,一来表达了自己无心仕途的故国情怀,二来也表明了自己抗争到底的决心,三来也避免盛名之下舆论带来的流言蜚语。“气候既过颜色蔫,死灰冷落焉能热”[7]76。不为人知晓的生活,遗民们在其中获得了自我认同,保持了高洁的气节。
(二)隐逸之乐
《快园道古》隐逸部中记录了许多隐士古朴而逍遥的生活剪影,如虞原遽与何文渊以醋代酒剧饮相谈,时人谓之醋交的美谈,又如王元章种梅千树,居“梅花书屋”,卖梅子的文人雅趣生活。张岱还将自己的隐逸生活记录其中:“陶庵晚年号六休居士,白岳问其说,陶庵曰:‘粗羹淡饭饱则休,破衲鹑衣暖则休,颓垣败屋安则休,薄酒村醪醉则休,空囊赤手省则休,恶人横逆避则休。’白岳曰:‘此大安乐法也’。”[3]147笔记所记之处流露出来的是张岱善于挖掘清苦生活中的乐趣,能够苦中作乐的慧眼。和笔记中逍遥快活的隐逸生活截然相反的是张岱诗中展现的现实生活,如“寒暑一敝衣,捉巾露其肘”[7]39;“流徙未能安,饥馑又相值”[7]40;“空屋惟存壁,全家尽载船”[7]138。笔记中的美好隐逸生活只是张岱生活中极小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在为了求生而挣扎。以张岱为代表的遗民们希望过着富有文人情趣的隐逸生活,但现实是他们不得不为了生活放下文人的身段,从事辛苦的农业生产活动。他们所欣赏的隐逸诗自然不可能是白居易之流的闲云野鹤,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陶渊明,因为陶渊明与他们的命运更为相似。他们同样为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选择归隐山林,身居清贫生活亦能够得到满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亦是遗民心中的理想。笔记中隐逸生活就是这种理想的体现。而诗中表现的生活则是现实中遗民面临的困境,借描写这些生活苦难,作者自然不是希望同情或者怜悯,他们借这些苦难抒发的往往是尽管生活贫苦却依旧不改遗民本色的决心。苦难成为了遗民精神的试金石,遗民通过自苦的行为,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张岱在诗中也有这样的表达:“一贫真至此,回想反开颐。”[7]95
值得一提的是张岱是一个热衷于戏谑的人,面对生活中的困境,他也多以一种戏谑的姿态来面对。苦中作乐也是张岱在《快园道古》中展示的一种隐逸之乐。纵观《快园道古》,其中多选取了那些有趣诙谐的故事,在目录中又特意设计了戏谑部和笑谈部,可见张岱在编写《快园道古》的那一段艰苦生活中仍然不忘戏谑本色,通过那些有趣的言行故事来排遣遗民生活的苦闷。张岱作为遗民,虽然生活艰难,但却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
四、藏而不言的忠君思想
在《快园道古》的小序中,张岱提到这本书创作的背景:“张子僦居快园,暑月日晡,乘凉石桥,与儿辈放言,多及先世旧事,命儿辈退即书之,岁久成帙。”[7]7在与儿孙放言的过程中,张岱希望儿孙能够在诙谐中收获其中的教育意义,即“余盖欲于诙谐谑笑之中窃取其庄言法语之意,而使后生小子听之忘倦”[3]8。《快园道古》是一本诙谐幽默的教育书籍,在其中张岱向子孙讲述了许多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教育儿孙要如何做人处事。张岱提到“世间极正经庄严之事,无过忠孝二者”[3]7。在古代教育的过程中,忠孝教育可谓是核心,更何况张岱本人以遗民自居亦是尽忠思想的坚定实践者。张岱同样希望子女能够继承他效忠故明的心愿。其诗《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和《甲午次儿下第归二首》,前者寄托了张岱希望儿子保持气节,不仕清朝,后者则抒发了张岱对次儿落第的喜悦。但令人困惑的是,在《快园道古》中却仿佛有意避开尽忠这一问题,而最应当收录忠义事迹的盛德部中也只是标举孝行而无一则记载谈及忠的事例。
在《四书遇》里张岱提到:“成教”最难言之而成文,行之而可远。常想家居欲有所示子侄,令僮仆顾己所未至,不觉口中愧缩,以知“成教”在教所不露处。张受先曰:“事君”“事长”“使众”,只教君子一边说,不可着民言。我能“孝”“弟”“慈”,则“事君”“事长”“使众”道理便已在此,不待外求也。时文泛引移孝作忠等语,非是[8]。这里阐释了张岱认为要从孝顺观念出发,来教育儿女,从而使他们领悟忠君的思想。《四书遇》中的“成教”观念突出了张岱本人“以孝寓忠”的教育思想。用这种的观念来看待《快园道古》中的记载,那么实际上《快园道古》并不是在避谈忠,而是寓忠于孝,用孝来激发忠。《快园道古》中记有许多关于家庭和谐的故事,从中强调了子女孝顺兄弟和睦的家庭观念。这些故事既是在教育子女的家庭伦理,也暗藏了张岱教导子女忠君爱国的意图。
移孝作忠的观念自宋代便开始流行,在明朝更为兴盛,如明成祖朱棣在《孝顺事实》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盖事君之忠,即事亲之孝也。人惟父生而君食之,故事之如一也。忠孝岂有二道哉!”[9]此处便把孝等同于忠,甚至将忠放在孝观念之前,政治教化色彩很重。在《快园道古》中的成教观念却与此有着不同之处,正如《四书遇》中“时文泛引移孝作忠等语,非是”。成教区别了忠君与孝亲,通过一些具体的容易实践的孝的观念来联系抽象的不容易实践的忠的观念,可以说成教是以孝亲比忠君之志,二者感情是一脉相承的却终究有所不同。以孝行来渗透忠君思想的教育理念,是对当时移孝作忠的批判。这种批判带有浓重的阳明心学的色彩,强调本心和知行合一,讲究本心启发的特色。张岱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采取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极有可能的。在《快园道古》中并非在回避忠这一问题,恰恰相反,它通过孝引申出了忠,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教育后代,凸显了张岱的良苦用心和对于故明的忠诚。《快园道古》盛德部中也多是高官者不以高官自居,仍以孝亲为重的事例,突出了孝亲感情的动人而并非孝忠一体的政治宣扬。盛德之中赞扬的口吻,令人不禁想起张岱本人对于明朝的眷恋和忠诚,以孝行比忠于明朝的感情可谓自然而然而又一往情深。
——评杨剑兵《清初遗民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