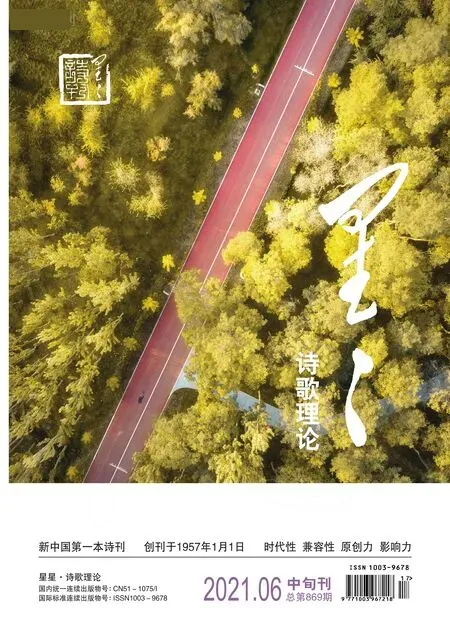从死亡的方向看
——读露易丝·格丽克《野鸢尾》
>>>纪 梅
野鸢尾
[美国]露易丝·格丽克
在我苦难的尽头
有一扇门。
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为死亡的
我还记得。
头顶上,喧闹,松树的枝杈晃动不定。
然后空无。微弱的阳光
在干燥的地面上摇曳。
当知觉
埋在黑暗的泥土里,
幸存也令人恐怖。
那时突然结束了:你所惧怕的,作为
一个灵魂却不能
讲话,突然结束了,僵硬的土地
略微弯曲。那被我认作是鸟儿的,
冲入矮灌木丛。
你,如今不记得
从另一个世界到来的跋涉,
我告诉你我又能讲话了:一切
从遗忘中返回的,返回
去发现一个声音:
从我生命的核心,涌起
巨大的喷泉,湛蓝色
投影在蔚蓝的海水上。
(柳向阳 译)
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野鸢尾》出自1992年的同名诗集,也是开篇之作。格丽克的主要中译者柳向阳曾在《代译序: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中,强调其诗集的整体性:“从《阿勒山》开始,格丽克开始把每一本诗集作为一个整体、一首大组诗来看待。”诗集《野鸢尾》共54首诗,笼罩着浓郁的宗教气息,其中包含7首《晨祷》同名诗,10首《晚祷》同名诗,以及以占诗集近三分之一的以草本植物为名的诗,如《延龄草》《蓝钟花》《紫罗兰》《红罂粟》等。
诗歌《野鸢尾》以讲故事的形式展开:“在我苦难的尽头/有一扇门。”格丽克的诗善以人格假面方式发声,在这里“我”是野鸢尾,在其他诗中是园丁、牵牛花、神话人物、宗教人物等。鸢尾的英文名Iris源于希腊神话中彩虹女神伊里斯。不了解这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如果格丽克使用典故,也是要以现代意识改写它。仅在视觉上,鸢尾花,特别是蓝色鸢尾,已经能够激发我们的诸多感知,它开得热烈又忧郁,高贵又神秘,孤傲又浪漫……而“野鸢尾”,更增加了生命力的坚韧、美得易碎和珍惜等想象。
当它开口说话:“在我苦难的尽头”,一段回忆的旅程打开了。
一个能看到自我尽头的讲述者,要么是垂垂老者生命将逝,要么是已然获得了重生。这一句为诗歌定下了神秘的基调。我们看到远处“一扇门”隐隐透光,不禁有步入其间的冲动。这种好奇旋即被打断,诗人用形式上的断裂,即分节造成的停顿,暂时安抚了听众欲知后事的急切。故事讲述者稍作停歇,而后缓缓道来:“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为死亡的/我还记得。”就这样,一节又结束了。我们继坠云雾:“你”又是谁?但能发现“死亡”出现了,可对应开头“苦难的尽头”。是啊,死亡当然是苦难,在很多情况下是最严酷的苦难,是“苦难的尽头”,代表着生的结束。但在一个疑似重生者的故事中,死亡或许只是一个苦难的事件,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头顶上,喧闹,松树的枝杈晃动不定。
然后空无。微弱的阳光
在干燥的地面上摇曳。
自我讲述转换为旁白,一个广大的场景显露出来:可能是在荒野,或森林里。与诗题暗合,这不是中产阶级的后花园,“野”鸢尾的命运没有女主人的呵护和垂青。它全靠自己。
在整部诗集中,荒野和森林是经常出现的场景,而高大的树木常常扮演太阳和低矮的草本植物的中介或阻隔:“当我醒来,我在森林里。黑暗/似乎自然而然,天空透过那些松树/光线密布。”(《延龄草》)“像我:在树荫里,在凉爽的石上蔓延,/在那些大枫树下。//太阳几乎触不到我。/早春,有时我看到它,正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升起。/那时树叶在它上方生长,整个地遮住它。我感到它/透过树叶闪闪烁烁,飘忽不定”(《野芝麻》)……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圣徒在荒野通过孤独和忏悔能够获得精神的纯净。这里诗人却没有指向忏悔。松树枝杈晃动不定,使阳光更加微弱,“在干燥的地面上摇曳”,荒野沉寂,观众不安:这里可以充当一桩谋杀的场地。诗人坐实了我们的忧惧:
当知觉
埋在黑暗的泥土里,
幸存也令人恐怖。
“黑暗的泥土里”是怎样的野蛮和酷烈,以至于“幸存也令人恐怖”?诗人没有过多交待,但在下一节告知我们,最令人惧怕的是“作为/一个灵魂却不能/讲话”。这才是最深重的黑暗。
本雅明曾在《论历史哲学》中写道,“历史清楚地表达过去”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者所言的“以它真正存在的方式”去确认它,而是“在它危险的瞬间一闪而过时抓住记忆”,只有这样“才能把传统从占统治地位的顺从中拽出来”,只有这样的历史学家“才具有在过去之中燃起希望的火花的才能”。不能抓住一闪而过的记忆,在本雅明看来,是对统治者的无力顺从,是“心”的惰性、麻木和绝望。它随后会生成对胜利者的移情并进一步“有益于统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所惧怕的,作为/一个灵魂却不能/讲话”,才是彻底被置于死亡的绝境。但可怕的噩梦“突然结束了”,在“僵硬的土地/略微弯曲”的时刻。这是野鸢尾的种子与黑暗抗争的战果:它为自己争夺了生机。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看起来并不起眼——土地仅是“略微弯曲”,一旁的鸟儿如常冲入矮灌木丛中。但随后的发展已不能遏制。
你,如今不记得
从另一个世界到来的跋涉,
我告诉你我又能讲话了:一切
从遗忘中返回的,返回
去发现一个声音:
“你”第三次出现了。我们已经明白:“你”也是“我”,是野鸢尾的前世。诗人把“我”分裂为两个自我。前世的“你”丧失了记忆,重生的野鸢尾对它讲话,唤它从遗忘中返回,去发现一个声音:自我的声音。这种友爱和鼓励,就像本雅明说的,“这是过去的一代和现在的一代之间的秘密协定。我们的到来毕竟是被期待过的。像我们的前辈一样,我们被赋予了微弱的弥赛亚的力量,一种过去所要求的力量。”当均质而空洞的时间被“现在”打破,“未来的每一秒钟,都有一扇小门,弥赛亚可以穿过它进来。”(《论历史哲学》,孙冰译)
从我生命的核心,涌起
巨大的喷泉,湛蓝色
投影在蔚蓝的海水上。
以近乎神秘的强劲韧性,野鸢尾从自我生命的核心涌起“巨大的喷泉”,以惊艳的蓝色光芒成为荒野上熠熠闪光的彩虹女神。曾经“干燥的地面”转而变成“蔚蓝的海水”。
在同部诗集的另一首诗中,诗人这么写道:“生命之物并非同等地/需要光。我们中有些人/制造我们自己的光:一片银箔/像无人能走的小径,一片浅浅的/银的湖泊,在那些大枫树下的黑暗里。”(《野芝麻》)格丽克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观念和力量的冲突在她那里激起的是身份的认知和个体的反抗:“做不了人并没有什么可悲的,/完全生活在泥土中也不会卑贱/或空虚:心智的本性就是要/守护自己的显赫”(《蚯蚓》)……在希腊神话里,彩虹女神伊里斯传达神的旨意时从不显示自己的主观性,她是忠诚的典范。但在格丽克的诗中,“微弱的阳光”(或隐喻上帝)无可指望,野鸢尾唯有凭借自我救赎的信念和坚韧的生命力冲破泥土,获得新生。它制造自己的光,也用生命的惊喜照亮荒野与听故事者。
——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