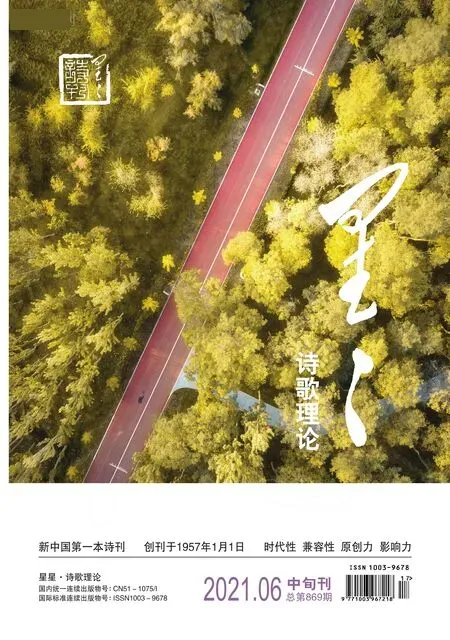艺术“翻版”,抑或艺术“再生”?
>>>卢 辉
应该说,将古今中外的艺术名人、名篇、名曲、名舞、名画等进行零星“诗化”再现的诗人不在少数,但像谢克强那样将古今中外的艺术名人、名篇、名曲、名舞、名画等进行全面系统、分类分列的“诗化集锦”与“艺术再生”,在当今中国诗坛还是比较少见的。谢克强这组《艺术之光》好就好在它呈现出人类的心灵状态和波段,它就像是人类情感的晴雨表,传递并预示着公众感情的振荡,折射出人类的思想、精神和艺术的轨迹,可见谢克强匠心独具。
诗歌从“写”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很像是一座雕塑,要的就是皮肤的纹络和思想的肌理。在中国诗坛,谢克强可以说是一位出色的“诗歌雕塑家”。他的诗歌“刀法”很犀利,往往能够在准确的意象“穴位”、延拓的意境“时空”、质感的思想“肌理”、直观的精神“立面”上进行雕镂,这四位一体的“刀法”在他的《艺术之光》这组诗中得到全面的运用。比如他写陶潜:“剩下的时间/在桃花源种几亩薄田/若是疲乏裹满泥泞/你就挽一抹白云荷锄而归/然后坐在庭院里/用酒去洗”。诗中的一个“挽”,是挽“一抹白云”;一个“洗”,是“用酒去洗”,多么出神入化的“直击点”,而这个“直击点”正是陶潜最能“出戏”的“节点”。的确,写艺术名人,最怕就是简简单单的“形象翻版”。一个诗人,写任何一位艺术名人,不管是直击、重现或回忆,要的就是具有“切肤”的“点位”。所到之处,能一针见血以及入木三分。谢克强写陶潜,若他仅在约定俗成的、属于陶潜的“境地”中,写一些悠然的、逸情的、梦幻的自然与文化语境,这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情景“复制”,只能算是搬出原有的“东篱式”的梦幻桃源,或者制造廉价的抖包袱式的蜻蜓点水的噱头。正是为了避开这些蜻蜓点水的噱头,他将艺术人物放入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节点,附在“历史”的影子中,并以感观、直觉、念想、情愫的“直通状态”,直接抵达那时,那地,那人,给人一种“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如真似幻的艺术效果。在谢克强看来,“复制”与“再生”的过程,就是要把诗人所表现的艺品分解为感性因素,并能重新将其组合成“出人意料”之物。正是丰富的情感、自由的想象和语词的张力在诗人驰骋的心中制造了许多奇妙的“酶”,它溢于言表并获得某种“超验”的表现形式,让诗歌传递出“艺术”之外的新感觉、新经验和新思想。
从谢克强这组《艺术之光》创作路径来看,用诗歌写名人也好,写名曲也罢,一方面,要让每一块汉字都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汉字的“自由”,对诗人而言,算得上是终身的、无法替代的奢侈品。比如他写《钢琴协奏曲:〈黄河〉》:“手臂波动着/顺着你充满血性的手指/不可理喻的白键黑键/跌宕起伏/以夺人魂魄的雄浑与湍急/奔泻一河激浪”。在这里,曲子与汉字几乎是对等的,曲子取悦于汉字,汉字同时反哺于曲子。当你试图也“手臂波动着”,你一定会感觉到有一股汹涌澎湃的黄河浪涛向你扑面而来,你完全可以乘上诗人为你提供的“诗歌之舟”在黄河里跌宕起伏。此时此刻,你真的可以享受到汉字本身在流动过程中带给你的冲击感、愉悦感、错落状和韵律美。另一方面,名曲大都是大家耳濡目染的“视听盛宴”。正因为大家熟知,它类似于“大词”,一种已被限定了的“大词”。倘若诗人仅仅把它作为诗歌的“注脚”,无法将它的“限定性”变成可感的“幻象性”,那么,它充其量不过是进入另一个常态思维的惯性中,不过是一个名曲的翻版。鉴于这种很可能落入俗套的僵局,谢克强取之词义的“弥漫性”,即语言的“张力”,重新进行排列组合,使名曲的“熟热”面孔被陌生化,被延拓化。这样的陌生化以及延拓化,就是意象的跳跃与意绪的粘连所产生的“错落美”和“张力美”。也就是说,谢克强并没有简单地复制或复述名曲自身,而是选取名曲的“动感”所延拓的“张力空间”,并将名曲推向“再视、再感、再思”的境地,让其在新的境地实现跨越式“回归”。正是因为谢克强看准了诗歌的自由与张力的二要素,强调了语言的自由与张力,激发人们对艺术的感知与再认识,使艺术客体能在“感知”的光照下被人看见,使艺术客体的色彩、旋律、形体产生新的冲击波,让读者可以感觉出艺术客体与伟大永恒的事物间的血缘关系,从而使艺术客体变得更加高尚而完美。
也许有人会问:名曲名舞早已“经典在先”,无论诗人如何妙笔生花,不过是步它们的“后尘”。其实,谢克强也深知自己行进的艰难。但是,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笔触进入“死胡同”,诗人要面对的岂止是名曲名舞的“经典在先”,而且还得面对名曲名舞作为文化积淀的“高峰”。究竟是仰望,还是仰望之后的攀登,谢克强选了攀登这一“自选动作”。以《杨丽萍:〈两棵树〉》为例:“在梦的边缘/线条的静止或者舞动/都以扩张的激情/擎一片蓊郁”。的确,名舞的“能动性”正是在于诗人能够迅速“截获”舞者最稳定的、最有效的那一部分的“肢体语言”,任它“游离式”的舒展。当然,此时的舒展就不能延用人们对该舞原有的思维或审美方式,而必须在诗人的牵引下,迅速形成诗人自己的“再编”系统,并与舞蹈作品进行有效的融通,形成“此舞”又仿若“彼舞”的效果。古往今来,名曲名舞一直是许多人无法逾越的“经典在先”的极致。因为自从它们成为教科书被固定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名曲名舞在引导许多人的思维习惯、精神跋涉、信仰皈依,甚至是很宿命的生活节奏、禀性、乃至品格等方面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根深蒂固的“模式”像一座灯塔,更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当谢克强念及“一任双眼蓄满二泉之水/汩汩泉水 倒映心空那一轮/冰清玉洁的冷月”时,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的《二泉映月》,悲怆性便不言而喻。也就是说,它的“悲怆性”很难被人分解开来,谢克强也不例外。那么,如何在“悲怆性”的基础上,去强化它的情景化,乃至弥漫状,是许多像谢克强这样的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将名曲放在思想的穿行中去充实《二泉映月》的“悲怆性”,去强化情景,重新去唤起人们的阅读快感与新奇感,这是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同时,和我们早已相遇的“经典”,因为它一直处在我们熟知的时间和空间的系统里,支撑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位,直接诉诸我们的那些感情、意愿和目的,与我们的精神生活朝夕相伴。正是基于“经典”如此丰厚的“先验性”,要突破这一“高点”,任何简单的想象或毫无感情的想象对“经典”都毫无意义。可见,谢克强一方面要被“经典”的先验性所浸透,另一方面,他又要大胆地把“经典”在自然或生命中通过“人本”的形态鲜活而生动地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就是一种天分。
当然,诗人天分的另一面,就是驾驭语言的天分。我一向认为调度汉字的“天分”来自对汉字的“偏激”,因为有了“偏激”你才有可能在“占有”汉字的基点上进行“生命化的调度”。有了对汉字的“偏激”,才会有技巧之外的“偶然性”与“弥漫性”。这样的话,既能高度享受汉字的“通灵”,又能感受到生命的“质感”。在谢克强看来,诗歌写作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载体”的问题,谢克强在《艺术之光》中所选的名人、名篇、名曲、名舞、名画等,就是想选用最佳的“载体”来写最好的诗。由此可见,谢克强创作《艺术之光》绝非是一时兴起,而是诗人本在的、亲力的、所见的、积淀的、世相的“突然放大”。这种“放大”,我把它叫着载体与自身之间的“双向投影”。比如,《徐悲鸿:〈奔马〉》中,“从边塞诗的第一行奔来/又向那一首歌奔去/蹄声踏踏卷一路狂飚/掠过唐诗宋词/掠过日月星晨/从我身边一闪而过”。可见,谢克强很善于利用名画这一“载体”与自身的创作进行“双向投影”。在这里,既有中国人所说的“感兴”“神遇”“兴会”“感应”“天机”的影子,又有西学里的“直觉”“灵感”“直观”“潜意识”“无意识”的影子,而这一切都直接根植于诗人个体生命的最高形态的自由。就《徐悲鸿:〈奔马〉》这首诗而言,符号、色彩、声音、思维是诗歌的“血液”。如此说来,按符号和色彩的功能,名画一定是可视的、立体的、多维的、层次的“诗歌空间”;按声音和内审的功能,名画又是流动的、跌宕的、回旋的、丰盈的“诗歌时间”。可见,任何的“审美”都有它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意念必须跟着载体来“缓解”和“分配”原有的审美模式和既定的原像,去唤醒“常态化”的“原点”。有了这个前提,诗歌空间才能被读者“侵入”。
一方面,他溺于艺术的核心区,具备了“历史”的昭示和“生命”的软化。另一方面,诗歌里的“载体”看似只有一种,却往往有密集的意象且布满了“寻根问底”的预示,有着一种“诡谲”与“傲然”的风范,呈现出载体与生命在“交感”中的“灵动”与“互补”,这便是我看好这组诗的缘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