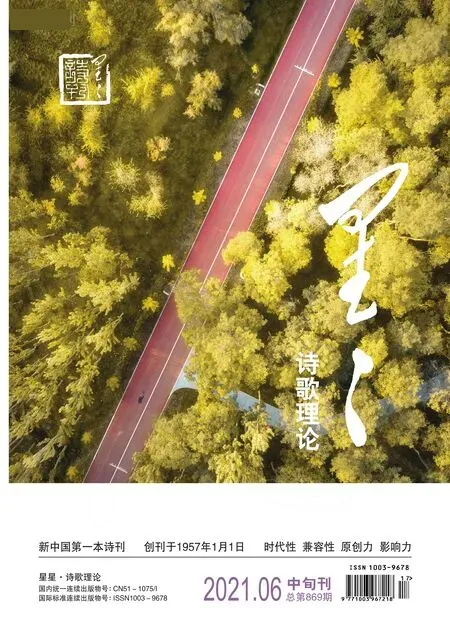在诗歌中行走
——读周笛《半醉半醒是一生》
>>>陈 希
周笛写了一本新书《半醉半醒是一生》,我开始以为是诗歌,她说是散文。直到亲见新书,方知是关于诗歌的散文——学术随笔。写一本读者喜爱的读物不容易,何况是关于新诗,而且是学术性的。但这本小书,好看耐读,行云流水,扣人心弦,如沐春风,文史交织,独到的审美感悟与深刻的历史理性融汇,显示现代诗学之醇美和乐趣。潜心写这样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不仅要花时间、耗精力,而且需要功力和才情。
周笛硕士就读于武汉大学。江城多山,珞珈独秀;山上有黉,武汉大学。武大不仅拥有风景如画的珞珈校园,而且有驰名的樱花诗歌节和珞珈诗派;既是诗歌创作的园地,也是新诗研究的重镇。从闻一多、沈从文到陆耀东、龙泉明,诗意珞珈,诗学传统源远流长,新诗研究自成一派。周笛在珞珈山学诗、写诗、论诗,硕士毕业攻读博士学位,继续从事新诗研究。
当然,我们读诗、写诗和论诗,不是出于功利之心,获取学位或名利,而是由衷的喜爱。爱是一种无私的付出,也是无穷的回报。确实,从诗歌中我们获益良多。诗歌是生命之花,好的诗歌能让你在幽暗中看到跳动的光泽,在孤独中听到奇妙的声音。黑格尔曾说:“艺术的真正职责就在于帮助人认识到心灵的最高旨趣”。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诗歌的滋润和支撑,我们的生命黯淡无光,会变得干涸而脆弱,沉闷而易折,缺乏生机活力。
分享新诗之美,感受诗歌之趣,首先不是将诗歌视为一种专业和技能,而是作为一种人生修养和艺术追求。从审美角度看,诗歌诉诸的是一种感受和想象,是一种期望和情怀,而不是知识或学问。正如北岛《关键词》所写:“我的影子很危险,这受雇于太阳的艺人,带来的最后的知识,是空的”。
学诗或写诗,主要不是学问和知识的探求,而是才情和妙悟的体现。但学问对创作其实是有助益,二者并不是水火不容,互相排斥,而是如同火种与燃料,彼此关联,互相成全。唐代杜甫有言“读书破万卷,下笔自有神”。学问不是创作表现的对象,而是创作的基础和动力。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曰:“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而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此说于诗歌创作的特殊艺术规律很有会心与识见,但后人误解其意,多强调“非关”二字,明清以来易“书”为“学”。其实严羽并非舍学言诗,而是强调读书穷理之重要,多读书、多穷理,才能获得“妙悟”。
写诗本身有学问,那论诗就更是要学问。周笛这本论述新诗的书显示的“学问”,并不是套用和征引书本或现成的知识和理论,而是“化用”诗学概念,描述时代语境,建造历史平台,知人论世,人本与文本结合,以人生际遇为主要线索,还原现代诗人与新诗的聚散离合,用灵敏和诗性的文字去解读其中深藏的多重内涵。
目前诗歌批评主要来自两个阵营,一是学院的论家写作,一是诗人的相互阅读与阐释等。比较而言,很少有小说家对同行的写作进行评论,而诗人多身兼论者,热衷写诗歌批评文章。他们根据自己的阅读趣味、诗学观念以及交游范围进行批评与阐释活动,但有时流于空泛片面和主观化,随意性较强。而学院出身的批评家,有时局限学科壁垒和理论窠臼,缺乏创作体会,难免隔靴搔痒,论述不到位不深入。学院论者周笛有过诗歌创作经历——也写过散文、小说和剧本,因而深谙艺术甘苦,更能够熟悉诗歌的语言、意象、肌理和表达,走进研究对象的本质深处。
周笛的《半醉半醒是一生》,属于诗歌随笔,讲述新诗发生的生动“故事”。读来也如在诗中行走,颇具感染力的语体方式,长于情境化的描述,言简意赅的解析,使得这本小书诗意盎然。《蝴蝶飞过沧海》以胡适的白话诗尝试来回溯新诗的发生,触摸历史,由人及文,立足本土现实语境,检视西方文学资源。《静穆的思索》论析沈尹默的《月夜》,展现“新诗的美德”。周笛主要从新旧诗歌主体与自然关系的差异来分析“我”的独立性,这当然不错,但我个人更看重这首诗以虚词收尾、仄声押韵,突破古典诗词的格律限制,这种语言形式体现了新诗的特质。《我的重生》《湖畔的小花》和《不仅仅有背影》分别介绍郭沫若、汪静之和朱自清的诗歌创作,或浪漫、或纯情、或写实,辅以爱情的离合,读来思绪纷纭,感慨万千。《在他乡》《在雨巷》《当爱已成往事》则是讲解象征派代表李金发、现代派代表戴望舒、智性诗代表卞之琳的诗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启人深思。情因诗而高贵,诗因情而流传。最后两篇《为一滴水定型》《一块碑石》,全景式论述冯至和穆旦的诗歌创作,重点解读《十四行集》《诗八首》,颇有深度和新意。
周笛的这本书点燃人们亲近新诗的热情。内容贯穿新诗的发生到发展,论及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个性的代表性诗人诗作,以点带面,生动描绘历史情境和基本脉络,揭示新诗的特质,交流探讨一些诗学问题,分享新诗之美,引导读者走进诗人精神世界,提高诗歌艺术修养和鉴赏水平,唤起诗心,追寻诗意。这是一本别出心裁的新诗史和心灵导游图。
新诗诞生已经百年,成为现代人审美和抒情的艺术方式。经过几代诗人不懈努力和创造性探索,新诗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形质双佳的诗作,构建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质和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诗的地位和合法性至今仍是问题,经常受到各种质疑,尚未真正走进公众生活。人们背诵和引用的多为古典诗词,中小学对新诗教育并不太重视,教材较少选新诗,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引爆的也是古典诗词热。
诗歌有新旧之分,但诗歌的艺术性无新旧之别。好诗都具有独到的意象、巧妙的言辞、完美的结构、新颖的表达,能动人之情、启人之思。当下新诗确实旌旗纷飞,山头众多,令人眼花缭乱,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特别是缺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胜境佳作。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新诗介入现实,真切自然,句式自由,语言灵动,这对于规矩严苛、疏阔苍白、同质化严重的古典诗词创作来说是一种借鉴。长期以来,佳作得不到褒扬和流播,劣诗得不到否定和指正,好的专业评论处于缺席和失语状态,导致新诗创作不景气,有些方面越来越泛滥。期待能有更多的新诗评论和读物出现,及时褒优贬劣、引导创作、提高审美,让新诗“飞入寻常百姓家”,带来真正的艺术繁荣。
附:周笛文章片段
第十章:《一块碑石——穆旦与<冥想(其二)>》
从残缺的“我”,到“没有人知道历史从这里走过”,正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穆旦寻觅到“我”完成生命的可能,在无解的死亡与循环里。那个写出残缺的“我”的少年,所想不明白的,现在这个完成了普通生活的老人终于明白了。生命是脆弱的,但生命是唯一的,一个变形了的、从本质残缺的生命个体,竭尽所能地体验普通的生活,这已经完成了他生命里的一种可能。“我”的残缺能否得到弥补,不仅仅在于“我”与世界,与他人,与万物之间建立了怎样的联系,而且在于在这孤独痛苦的本源里,“我”能不能坚持完成普通的生活。
如果说20年代的新诗是婴孩的哭啼,用肆意的呐喊拼命展示生命未来的所有可能;那么30年代的新诗是少年的呓语。雨帘里暧昧的情思、深夜笨拙的思考、临窗观望稚嫩模样的失落,——这些都像成长的节奏带来的忧郁,莫名,却不可回避;到了40年代,新诗于战火和生死的洗濯间,用个体生命的血肉填补了诗意的肌理,使其终于拥有了青年的形体。新诗从婴儿里飞翔的蝴蝶,孩子们手里的野花、星星、玫瑰,变为少年珍爱的镜子、百宝盒、鱼化石,再变成青年触目的鲜血、挣扎、旅途,现在,阅尽一个世纪的风华,它仍要回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