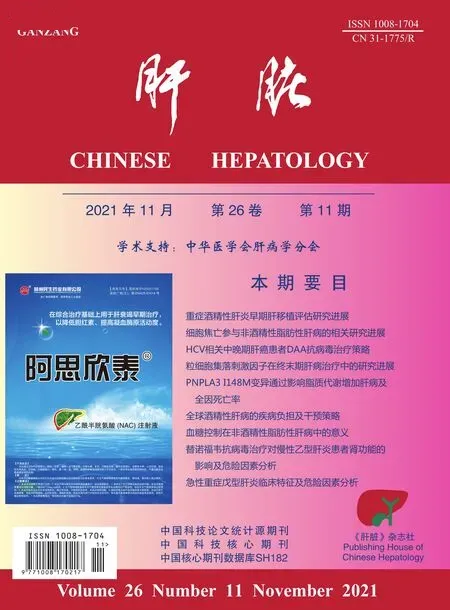腹腔镜手术切除与腹腔镜微波消融治疗肝血管瘤的疗效比较
吕超 李恒平 丁正华 孔雕雕
肝血管瘤在中年女性中最为多见[1-2],多数生长缓慢,尚未有恶性病变的报道[3]。确切的发病机制仍未明确,大多数患者可能是先天性血管畸形病变引起的[4]。瘤体较小时无临床症状,仅需观察。但瘤体较大时则可能出现各种症状和体征,包括上腹不适、腹胀、嗳气、腹痛等,可同时合并有出血、黄疸、血小板减少、纤维蛋白原减少等[5]。目前对于肝血管瘤的治疗,手术切除与微波消融在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6]。随着腹腔镜技术的迅猛发展,微创技术治疗肝血管瘤越来越受到临床医师的认可,而随之产生的术式——腹腔镜肝血管瘤手术切除、腹腔镜肝血管瘤微波消融术,也不断地在临床上得到应用。本研究统计了医院46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病例来源和纳入排除标准
回顾性分析自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血管瘤患者46例病例资料,按手术方式分为腹腔镜手术切除术组(A组)和腹腔镜微波消融术组(B组),A组18例,B组28例。纳入标准:①经影像学(如彩超、CT、MRI)及临床诊断为肝血管瘤患者;②年龄>18岁的单发或多发肝血管瘤患者;③依从性良好,对本研究表示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患有肝炎、肝硬化等肝脏疾病;②合并有心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危及生命的原发性疾病或精神病;③接受了其他有关治疗,可能对本研究效应指标造成影响。本研究已通过湖北医药学院附属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件号:2019KYLL00706)。
二、手术方法
(一)A组为腹腔镜手术切除术组 消毒铺巾后建立CO2气腹。取头高脚低位,腹腔镜探查腹腔内大体情况后,据腹腔内情况决定肝切除方式。切除方式有非解剖性肝切除与解剖性肝切除两种。非解剖性肝切除一般用于病灶位于肝脏表面或病灶为外生型的患者,采用Pringle法间歇性阻断第一肝门入肝血流,或在不阻断入肝血流情况下,在距肿瘤约1 cm处的肝脏表面切开肝实质,至深部沿瘤体包膜与周围正常肝组织之间的间隙将瘤体仔细剥离切除。解剖性肝切除则适用于病灶范围偏大,位置较深,累及整个肝叶/段的患者,先是解剖出预切除肝叶/段的G1isson蒂,再区域性阻断入肝血流,用电刀划出预定线,沿预定线进行肝实质的离断和切除。瘤体切除后取出送病检,肝断面予以电凝止血,据术中创面止血效果决定腹腔是否放置引流管。最后将各切口缝合。
(二)B组为腹腔镜微波消融术组 取仰卧分腿位,消毒铺巾后建立CO2气腹,腹腔镜探查腹腔内大体情况后,松解血管瘤与周围组织的粘连,钝性分离出肝脏。分离肝门后置入棉线套入肝门阻断管,备用阻断肝门,向膈下注入腹腔冲洗液,隔离肝血管瘤与膈肌。阻断肝门并记时,切开穿刺点处皮肤,在腹腔镜直视下,用冷循环微波刀刀头从肝表面消融致血管瘤塌陷,再由穿刺点斜行进针直达肝内包块,可选择不同穿刺点、不同角度穿刺消融。消融结束后,停止冷循环,逐渐拔出刀头,穿刺点加压包扎。
三、随访
采用来院复查或电话随访的方式随访。共52例患者纳入研究,A组20例,B组32例,A组2例失访,B组4例失访,最终本研究纳入46例患者(A组18例,B组28例)。随访时间为6~12个月,平均(11.61±0.802)月
四、统计学处理

结 果
一、基线资料的对比分析
分析显示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BMI、肿瘤直径、吸烟史、饮酒史及胆结石、高血压、糖尿病病史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二、手术相关效应指标比较
比较手术时长、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这三项指标,详见表1。B组的手术时长、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病例手术相关效应指标比较(±s)
三、肝功能变化效应指标比较
比较丙氨酸氨基转移(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间接胆红素(IBil)、直接胆红素(DBil)这五项指标术前、术后变化,详见表2。两组患者的术前指标(ALT、AST、TBil、IBil、DBi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而术后指标中,TBil、IBil、DBil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组的ALT及AST术后第1天水平高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ALT及AST术后第3天均逐渐回复至正常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两组病例肝功能变化效应指标比较(±s)
四、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效应指标比较
比较感染发生率、腹腔出血发生率、胆漏发生率、血红蛋白尿发生率、肾功能损伤发生率这五项指标。两组术后均未发生腹腔出血、胆漏或肾功能损伤。A组出现了1例术后切口感染,予以抗感染、切口清洁换药等措施后治愈。B组出现了2例术后血红蛋白尿,予以保守治疗后治愈。但两者的感染发生率、血红蛋白尿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五、远期疗效效应指标比较
比较术后半年复发率、术后1年复发率这两项指标。术后半年两组均未出现复发、术后1年B组出现例复发。
讨 论
尽管肝血管瘤的治疗方式多种多样,但在手术适应证、治疗方式的选择等方面,目前尚无统一规范,存在着争议[7]。在手术适应证方面,如今大多数研究将瘤体大小及临床症状的有无作为肝血管瘤的指征参考[8-10]。在治疗方式的选择方面,肝血管瘤的手术切除到如今仍被认为是疗效最为确切的首选方式[11-12]。
微波消融术治疗肝血管瘤最初应用于临床时,其产生的一系列并发症引起了人们对其疗效的质疑[13]。但随着腹腔镜技术和微波技术的发展及临床经验的积累,越来越多的防范腹腔镜微波消融术后并发症的方法被发现并应用于临床,腹腔镜微波消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越来越低。比如可通过术中间歇性肝门阻断、围手术期保证液体入量并碱化尿液等措施可最大程度地减轻对肾脏的损害,降低溶血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等。蔡熊等[14]回顾分析了56例肝血瘤微波消融术后患者,采用上述方法,血红蛋白尿发生率降至1.79%,未出现肾功能不全。与之对应,腹腔镜微波消融治疗肝血管瘤的手术指征不断放宽,其术后疗效也在逐渐改善。刘磊、王瑞官等[15-16]随访了多例行腹腔镜微波消融术的肝血管瘤患者,提示腹腔镜微波消融术对治疗肝血管瘤有确切疗效。本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通过本次研究发现,腹腔镜微波消融术组的手术时长、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均优于腹腔镜手术切除术组。术后第1天 ALT、AST 水平高于腹腔镜手术切除术组,这可能是由于微波消融术存在局部热扩散,对周围肝细胞损伤较大。但术后3天后两者水平无明显差异,这可能是由于腹腔镜微波消融术操作简便,对肝脏创伤小,有利于患者术后恢复。国内尚未有关于两术式术后胆红素变化的报道,本研究显示两术式术后胆红素无明显变化,进一步佐证了两术式的安全性。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与肿瘤复发率,两组无明显差异。对于腹腔镜微波消融术治疗肝血管瘤,笔者的体会是:该术式将腹腔镜技术与微波消融术结合,使其又多了腹腔镜的诸多相关优势。例如:①借助腹腔镜可以很大程度上扩宽腹腔探查范围,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腹腔内情况。②通过建立人工气腹,可拉开肝血管瘤与邻近脏器的距离,增大操作空间,也可腹腔镜直视下分离瘤体与周围组织粘连、向重要脏器(如膈肌)周围喷洒生理盐水等方式保护周围脏器。③在腹腔镜直视下可以及时发现出血并处理。④肝血管瘤患者多为女性,对腹部具有较高的美容需求,运用腹腔镜技术可以减少手术瘢痕。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属于回顾性分析,后续需进一步的研究,如需开展前瞻性、随机性对照试验以提供可靠研究结论。其次,这项研究是在单一机构进行的,多中心研究会更具说服力,后续需进行更多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综上所述,与传统的手术切除相比,腹腔镜手术切除与腹腔镜微波消融术两者都体现了微创的优势,远期疗效相近,而近期疗效腹腔镜微波消融术更优,具体采用何种术式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而腹腔镜微波消融术有着创伤小、出血量少、术后并发症少、恢复快等诸多优势,具有良好的研究价值及发展前景。